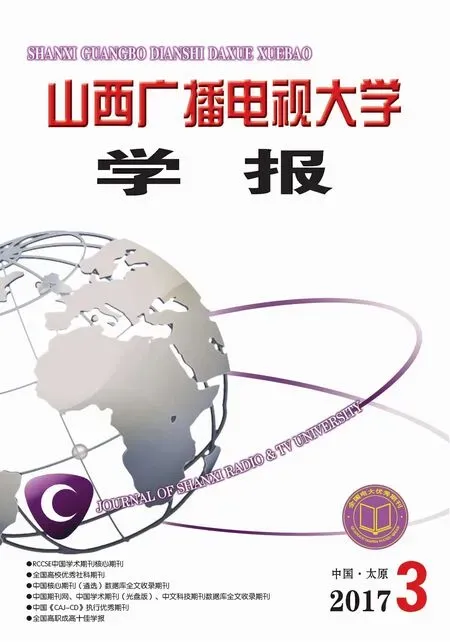论股东知情权
——以《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为背景的考察
2017-04-01彭炜玉陈春雷
□彭炜玉,陈春雷
(1.华东政法大学 经济法学院,上海 200000;2.同济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0000 )
论股东知情权
——以《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为背景的考察
□彭炜玉1,陈春雷2
(1.华东政法大学 经济法学院,上海 200000;2.同济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0000 )
知情权属于股东的固有权,是股东了解公司经营、维护自身利益以及促进公司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如何设计科学合理的股东知情权制度,统一股东知情权诉讼中的裁判规则是《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的重点和难点。知情权的制度设计是公司(大股东)与小股东博弈的结果,法律需要在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寻求利益的平衡,《征求意见稿》将知情权定位为固有权,规定知情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同时将知情权的行使主体进一步明确,排除了股东资格的限制,任何股东都享有知情权,但对司法实践中经常引起纠纷的隐名股东知情权的规定却付之阙如。此外首次规定公司若造成股东无法行使知情权,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进一步提升了对股东的知情权的保护力度,但相关制度不明仍会造成司法适用的混乱。可见《征求意见稿》无法做到面面俱到,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和研究的必要。
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知情权;检查人;固有权
现代公司实践中,侵害股东知情权现象颇为常见。通过查询北大法宝可知,我国股东知情权诉讼共有5626件,从2014年《公司法》修订至今,股东知情权诉讼在我国也有3953件。2013年以来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件数量呈现直线上涨趋势,特别是2014年修法以来,股东知情权诉讼已达4000件。《公司法》关于股东知情权的规定模糊是该类案件常发的主要原因。《征求意见稿》有关知情权的规定有了较大的完善,但仍不尽全面,有些规定较为模糊,易造成司法实践处理的差异。本文考察《征求意见稿》关于股东知情权的相关规定,并研究相关的司法案例,学习域外法之经验,以期对股东知情权制度提出完善之策。笔者主要就《征求意见稿》中知情权行使的主体、行使的方式、行使的范畴及知情权是固有权的性质、未能行使知情权的损害赔偿责任承担等方面具体展开分析。
一、股东知情权行使主体之探究
《征求意见稿》明确了股东知情权的行使主体,排除了股权转让后原股东的知情权,另外瑕疵出资股东仍享有知情权。《征求意见稿》对股东的股权份额及持股时间没有任何限制,即便只有1%股权的股东对公司相关资料信息仍享有知情权。但是隐名股东是否享有知情权《征求意见稿》仍然规定模糊。
(一)隐名股东知情权的适用
实践中,隐名股东出于种种原因不愿将自己的股东身份浮出水面,但因其与公司存在实质性的利益牵连,在公司或者大股东损害其利益时,会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在股东知情权诉讼中,相当一部分是隐名股东要求行使知情权的案件。理论界存在形式说及实质说两种观点:形式说认为由于股东名册具有推定效力,即在股东名册上记载为股东的,推定为是公司股东,在有限公司中隐名股东想浮出水面,行使股东权利,需满足经过三分之二股东同意的要件。形式说注重股东身份的外观,股东名册是公司内部认定股东身份的惟一依据,公司根据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名单支持相应股东行使知情权,对不在股东名册中的隐名股东请求行使股东权利不予支持。实质说认为尽管股东名册上没有记载隐名股东,但是隐名股东与公司具有真实的出资关系,应当享有股东权利。隐名股东违背了登记的公示性和公信力不应该具备知情权。实质说注重实际的出资关系,隐名股东“沉在水下”。在司法实践中,大部分法官支持形式说,知情权是具有股东身份的人才可以行使。我国公司法确认股东资格的条件包括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两个方面,实质要件即当事人履行了出资义务,形式要件即当事人记载于股东名册或者工商登记或者工商章程中,两个要件缺一不可。根据商事外观主义、保护交易安全及商事登记基本原则,判断股东资格应当首先进行形式审查。但在有关案件中,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支持隐名股东享有知情权,理由在于虽然我国关于隐名股东并无明文规定,但是公司法33条第3款规定了未经工商登记股东资格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由该法条可以推断出,工商登记只是对股东资格的公示,而非设定股东资格,当事人是否具有股东身份,应以是否具有真实的出资关系为依据。因此,当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在认定是否具备股东享有知情权时,既需要考虑工商登记记载、股东名册等外部要件,更重要的是针对是否真实出资、是否实际享有股东权利,是否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等综合考虑。但在大部分的法院裁判中,法官对隐名股东享有知情权持否定的态度,隐名股东的存在实际违背了公司登记的公信力。公司法规范大部分集中在公司组织等程序性规定,商事组织法一般考虑的是商事交易的效率、安全,不过分探求当事人内心的意思表示,追根溯源。从法律的形式要件上看,隐名股东就是真实的股东,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时按照股东名册记载通知股东,外部第三人与股东交易买卖股权时,也是按照工商登记,从这个层面看,隐名股东就是股东。笔者亦认为隐名股东不享有知情权,股东名册的记载具有使“公司免责的效力”,若允许隐名股东对公司享有知情权,公司具有审查实际出资股东的义务,否则隐名股东可能提起的股东知情权诉讼,对公司颇为不利。隐名股东对公司不享有知情权,但是他可以通过获得显名股东授权的方式对公司行使查阅权、质询权等;若显名股东不同意,隐名股东可以请求股东大会以期“浮出水面”。隐名股东在出资之初与显名股东成立股权代持协议,就应当知道股权代持背后的风险,应当自负其责。但是此次《征求意见稿》关于隐名股东是否享有知情权的规定模糊,易造成裁判标准的不明确。
(二)排除了股东主体资格的限制
有学者认为,若对股东查阅公司财务会计账簿等知情权不加以限制,则很可能造成股东知情权的滥用,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造成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股东行使知情权加以限制,譬如只有证明公司有错误行为才能查阅公司相关资料。但是《征求意见稿》未采纳这一观点,而是不论持股期限、持股数额,所有股东都有权要求行使知情权,这种一刀切的手段显然不够合理。笔者既不赞同对所有股东知情权都给予持股期限持股数额的限制,也不赞同完全不加限制,对所有股东完全开放。而是认为应当区分上市公司与封闭公司,对这两种公司分情况区别对待,上市公司公众股东人数过多,股权分散,若赋予所有股东都有权对上市公司行使知情权,很有可能造成上市公司经营的困境,上市公司每天的经营业务几乎就是“接待行使知情权”的中小股东。因此有必要对上市公司股东行使知情权给予持股时间、持股数额的限制,笔者认为可以参照公司股东连续180天持股10%可以行使撤销权的规定,但由于撤销权的行使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比较大,因此可以比照撤销权的行使要求适当减低标准,比如:连续股东原则:请求前一定期限(90日)已经成为在册股东;或至少已经持有公司发行在外的特定比例的股份(如5%)的股东才可以行使对上市公司的知情权。而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较强,人数较少,股东与股东之间基于信任组建公司,允许所有股东对公司行使知情权符合实际的需要,几乎不会对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产生影响,因此可以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行使知情权不予限制。
二、知情权是股东的固有权
知情权是股东社员权的重要内容,是区别于财产权的股东身份权,知情权是股东的法定权利,章程、或者其他协议都不能免除股东的知情权,股东把自己的财产投入到公司,且一般情况下也不参与公司的生产经营,若是不赋予其知情权或是任由章程等协议限制知情权,会造成大股东独控企业,小股东对公司情况一无所知的局面,公司成为了大股东的傀儡,因此将知情权定性为股东的固有权,章程不得限制是有一定的必要性。其次鉴于上述理由,股东作为公司的所有者,应当对公司存续期间的所有的资料都有知情权,而无需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一)公司章程或者其他协议是否可以限制股东知情权
知情权是股东的固有权,公司不得通过章程或股东之间的协议剥夺限制股东的知情权。此前关于公司章程是否可以限制股东的知情权,理论界观点不一:有些学者赞同《征求意见稿》的观点,认为股东的知情权是股东基于其社员身份而享有的固有权,知情权依附于股东的身份,权利是法定的,而非公司章程赋予的。但也有学者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内部的自治性规范,若在公司成立前章程制定阶段或者章程制定后转让股权,都应当视为接受了公司章程中关于限制股东知情权的。还有学者提出应该将公司的章程分为初始章程与修改章程两种,设立时候的初始章程是发起人股东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是股东之间的契约,股东应该遵守;而修改章程则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三分之二表决形式作出,少数股东对修改章程是不赞同的态度。对于初始章程即便股东一致表示同意放弃知情权,司法也无干预的必要。而在修改章程中,若是大股东利用其多数决机制剥夺或者限制了小股东的知情权,则司法有必要加强干预。 初始章程具有合同的机制,是全体股东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而修改章程只需三分之二同意,因此对于章程修正案不能以合同机制为基础。还有观点认为应当对知情权的内容加以区分,对于基础的股东知情权如查阅股东会董事会决议不应当加以限制,而对于更深层次的知情权如查阅公司的会计原始凭证、电话记录、传票、契约书等可以由章程加以规定。但笔者支持将知情权定性为股东固有权的观点,知情权是基于股东社员身份产物,公司法赋予股东的特定权利,公司章程虽然是股东之间的合意,初始章程是所有股东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但是章程可以“另有规定”的条款仅限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表决权、股权转让、股权继承、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等方面, 才可排除适用公司法的条款。因此若公司章程对股东的知情权作出了限制也不对股东发生效力。知情权是《公司法》设计的股东的权利,目的在于赋予不参与公司经营的中小股东充分权利知晓公司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若允许在公司章程中对公司的知情权进行限制或者排除,则《公司法》设计该项权利的目的就会落空。公司是股东作为投资者出资设立的团体,如若股东没有知情权就类似于瞎子过河,钱投进去之后却不懂钱的用处。笔者并不赞同将知情权的权利分为各个等级,只要是公司法中规定的股东知情权就是股东固有的法定的权利,不应当加以限制。其次初始章程虽然是公司设立之初发起人合意的产物,股东的知情权与股东的社员身份挂钩,初始章程也不得限制,章程修正案不是股东一致合意的结果,若承认其中限制股东知情权的条款,则会造成公司中一部分人享有知情权但是一部分人没有知情权的混乱局面。公司章程虽然不可以限制股东的知情权,但是可以对股东的知情权做扩张性规定,因为公司法为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赋予其知情权,公司对股东知情权作出扩张性规定符合公司法的立法目的,应当给予支持。
(二)知情权可否适用诉讼时效
知情权诉讼时效问题实质上是股东查阅范围问题。有观点认为知情权适用3年的诉讼时效,“除了法律另有规定,一般诉讼时效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三年”,因此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知情权受到侵犯之日起三年内行使知情权,换而言之,股东请求公司或者诉至法院要求行使知情权时,应当只能请求查阅前三年的会计账簿等资料。持续诉讼时效说认为股东的知情权是股东的身份权利,只要具有股东身份就理应享有知情权,因此对股东知情权的侵犯是持续性的过程,只要具有股东的身份资格就应当享有知情权。司法实践中,有法官认为股东知情权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诉讼时效是指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请求权将会导致权利人难以胜诉的制度,一般只适用于债权请求权,而知情权是股东的固有权,是与股东身份相挂钩的,知情权的行使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围与诉讼时效也无联系。”也有学者对股东知情权诉讼时效的时期提出质疑,认为现代商事社会追求效率的目标需要缩短知情权的诉讼时效,不能让股东躺在权利上睡觉,让公司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因此股东的知情权诉讼时效应当缩短至六个月,股东只能查阅提出行使知情权前六个月的账簿等资料。笔者认为,股东相对于公司处于弱势地位,股东知情权不能因为商事交易而受到折损,公司是股东意志的组织体,代表着股东的利益,若是因为担心损害商事利益而使股东利益受损(缩短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诉讼时效)易阻碍投资者的投资热情。股东的知情权是股东社员权的延伸,只要股东具有公司所有者的身份,知情权就一直持续享有,那么公司对知情权的侵犯就一直持续,股东的利益也一直受到损害的状态,公司的经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股东对公司会计账簿等资料的了解应该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三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即便股东身份持有的时间较短,股东对公司之前的资料也有一定的知情权,以此决定该公司是否值得长期投资,并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进行监督。笔者倾向股东的知情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股东对公司的会计账簿等相关资料具有查阅权不受时间的限制。《征求意见稿》虽然认为股东的知情权属于固有权的范畴,但未提及股东诉讼时效的适用,司法实践中出现过因股东知情权受到侵害而提起诉讼,公司以知情权已过诉讼时效提起抗辩,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亟待立法的完善。
(三)行使知情权的范畴
关于股东是否有权查阅公司的原始凭证,各地司法实践中虽然存在争议,但是较为普遍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享有查阅公司原始凭证的权利,如北京、江苏等地。山东省认为无论股份还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都有权查阅会计账簿(既包括记账凭证又包括原始凭证)。司法解释对股份有限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采取了区别对待,股份公司股东无权查阅记账凭证或者原始凭证,而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该权利。
美国《示范公司法》规定美国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畴之宽,股东在行使知情权时可以查阅的公司会计记录、财务信息应当包括公司的原始凭证。我国禁止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原始凭证是因为实践中股份公司股东人数庞大,为了避免对股份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造成混乱,而一律对股份公司股东查阅公司的记账凭证与原始凭证采取绝对禁止的态度。但是不可否认,股份公司的利益与每个股东的利益息息相关,股东的人数过多,每个股东不可能都参与到公司的生产经营中去,此时就会产生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在中国实际经营控制公司的是董事会,董事会是由股东会选出,但往往是大股东的代表,代表大股东管理公司,代表大股东的利益,大股东为了一己之利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在实践中也时有发生。原始凭证或记账凭证是最能反映公司真实财务等状况的,股东若对公司的会计账簿存在合理怀疑,在公司无法证明股东有不合理目的时,可以要求公司提供原始凭证。若是不赋予股份公司中小股东一定的知情权,在其利益受到损害时,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笔者认为仿照股份公司股东享有派生诉讼权的规定,对满足连续90天持股10%的股份公司股东,赋予其对公司记账凭证、原始凭证的查阅权。《征求意见稿》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享有查阅原始凭证的规定也较为合理,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较强的人合性,其成员基于信任而组建公司,赋予成员足够的知情权也是成员之间信任的表现形式。
三、知情权的行使方式
《征求意见稿》规定了知情权可以由股东委托第三人行使,这里的第三人往往是专业机构,但未引入英国的“检查人”制度,行政机关或法院或接受股东申请或主动指派“检查人”对公司的相关资料进行检查,可以使对小股东知情权的保护更上一个台阶,我国可以适当适用。
(一)委托第三人行使知情权
有观点主张知情权是股东的社员权的一种,与股东身份紧密联系,股东委托不具有股东身份的中介机构行使知情权,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征求意见稿》明确了股东可以委托第三人行使知情权,第三人当然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在现实中,可能股东纵然有行使知情权的权利,但是受限于专业知识等客观情况,股东对财务账簿、会计报表等专业、复杂资料没有能力检查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存在信息不实。因此赋予股东委托第三人行使知情权的权利,对股东的知情权是实质性的保护。但是若公司可以证明委托的中介机构有不正当目的(中介机构受雇于股东,与股东之间存在利益纠葛或者可能会侵犯公司的商业秘密),股东与公司之间很可能会陷入僵局。 在此情况下,“德国公司法赋予股东质询权与请求法院作出裁决的权利。”司法的介入有利于股东顺利行使知情权的同时避免股东与公司之间陷入僵局,德国的这项规定也可以运用到我国的知情权之中,不仅仅是股东行使质询权,只要当股东行使知情权时与公司陷入僵局,股东或者公司都可以申请司法介入,法官可以指派独立的中介机构对公司的资料文件进行审查,既保证了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又保护了股东的知情权与保障公司的商业秘密不被侵犯。指派独立的中介机构进行对公司资料进行审查的费用由该股东与公司平分,这既能避免股东因为不承担费用而随意申请司法的介入,浪费司法资源,也能促使公司尽可能地配合股东知情权的行使避免股东申请司法的介入。
(二)设立检查人制度
英国早在《公司法》中设立了“检查人制度”,1985年《公司法》第14章专门规定公司调查制度。第 431—432条规定“公司调查程序可以由公司、股东、法院与国务大臣四类主体启动。国务大臣可以依股东申请委任检查人,但若股东申请获得他们有理由获得的有关公司事务的信息时,国务大臣应当委任检查人。”英国对有权申请委任检查人的股东要求较高。 “股东或者公司提出申请的, 国务大臣有权要求申请人证明自己享有正当目的 (good reason ) , 且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不超过5000英镑的担保。若法院发布令状要求调查公司,此时国务大臣必须委任检查人。”英国的检查人制度运行时间较久,制度设计也比较完善,我国的公司法可以引入检查人制度(即相对独立的中介结构),不仅仅是股东、公司、法院都可以申请检查人对公司进行检查,公司的行政管理部门(一般为工商局,上市公司可以为证监会)也可以主动聘请独立的中介机构作为检查人对公司进行检查,对公司的相关信息进行全面的监督,保障股东行使知情权的权利的同时,也需要注重对商事经营效率的保护,若不管何时都允许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法院等对公司进行检查,会损害公司的经营效率,因此对此需要设定一定的触发机制,譬如:当股东的知情权无法得到保障,股东可以申请司法或行政机构的介入;或者当司法或者行政管理机关有合理的证据表明公司存在侵犯股东知情权的情形,可以主动进行介入。
四、无法查询的民事责任
《征求意见稿》规定:若公司未按照规定保存相关材料,致使股东无法行使知情权,则股东有权要求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是首次在公司法中规定公司侵犯股东知情权需要承担民事责任,是法律对中小股东保护的突破,但是该条规定颇不明确,股东未依法制作和保存公司文件侵犯的是全体股东的知情权,公司是否需要对全体股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是对财产权利受到真实侵害的股东赔偿其所遭受的财产损失?若是看成对全体股东知情权的侵犯,公司都要承担责任,在上市公司,股东人数众多,给所有股东给予赔偿数额也存在现实履行的障碍,同时对没有遭受实质性损害的公司的股东,公司赔偿的数额难以确定。因此笔者认为《征求意见稿》的该条规定,实质上是赋予了因为行使知情权受到障碍而遭受经济损害的股东请求公司赔偿民事责任的权利,而不应当对知情权遭受损害而并未造成实质性的经济损害的股东进行赔偿。《征求意见稿》突破性地规定了知情权遭受损害的股东有请求赔偿的权利,但是可能会在司法实践的运用中带来一系列的司法适用的不统一。可以增加股东对其遭受的损失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对损失部分公司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五、结语
我国的此次《征求意见稿》关于股东知情权做出了突破性的规定,对股东知情权的保护不仅仅是公司法的修改完善就可以完成的,还有赖于公司的治理机制的完善、法院诉讼体制的进步等等,但是法律法规的完善是基础。我国的立法者已经意识到了我国公司法关于股东知情权保护的薄弱,意图在司法解释中加强对股东的知情权的保护,同时寻求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利益的平衡。在享有知情权的股东身份认定中,司法解释四完全否定了股东转让股份之后对公司享有的知情权,不利于原股东的保护;司法解释中对享有知情权的股东未设任何限制,但笔者认为应该通过连续股东原则的限制以减少股东行使知情权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的不利影响。知情权是股东的固有权,不能受到限制。笔者认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原始凭证拥有一定的查阅权,只需提高股东的资格要求即可,因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理应对公司的相关会计账簿等享有相关权利,只是基于对公司管理的需求对股东的身份进行适当限制。鉴于公司的财务会计账簿等资料的专业性,股东可以聘请专业的中介机构对其资料进行审核,法院或者工商行政管理局也可以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聘请专业机构对公司相关资料进行核查。《征求意见稿》首次规定了公司需要对不能行使知情权的股东的违约责任,笔者认为只需对经济利益造成损害的股东需要承担相关损失,否则公司的责任过重。知情权是作为公司所有者股东的权利,但是对于公司来说则是责任与义务,公司需要对股东行使权利给予辅助。立法者在设计股东知情权时,应当充分考虑到股东的利益与公司利益的平衡、小股东利益与大股东利益的平衡,保障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任何一部法律都是利益衡量的结果,公司法也不例外,此次公司法司法解释对于股东知情权的规定已经有了长足进步,其中仍有部分不完善的地方值得进行修改,本篇论文期望可以对我国公司法知情权部分的立法完善尽到绵薄之力。
[1]甘培忠,刘兰芳.新类型公司诉讼疑难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53 .
[2] 陆鸣苏,桂南平,王成.原股东要求行使任股东期间知情权的认定与处理[J].人民司法 ,2009(10):81-84.
[3]郭晖.股东知情权行使类型化案例研究 ———以北大法宝司法案例为主线[J].产业科技论坛,2016(15):38-40.
[4]刘俊海.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修订本)[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55.
[5]雷鑫,吴明明. 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目的的正当性——以裁判思维为视角[J].法律适用, 2014(5):115.
[6]周友苏. 周友苏教授谈股东知情权等:建言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草案)[EB/OL] . http://www.aiweibang.com/yuedu/158161456.html,2016-5-7.
[7]Bebchuk.Limiting Contrual Freedom In Coporate Law:The Constrains On Charter Amendments,Harvard Law Review 1824(1989).转引自钱玉林.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检讨[J].法学研究,2009(2):71-80.
[8]托马斯莱赛尔,吕迪格法伊尔.德国资合公司法[M].高晓军,单晓光,刘晓海,方晓敏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242.
[9]李建伟.论英国公司股东知情权制度[J].社会科学,2009(12):83-90.
本文责编:赵凤媛
On Shareholder's Right to Learn the Truth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4 of Company Law (Draft)”
Peng Weiyu1, Chen Chunlei2
(1.School of Economics Law,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00; 2. School of Law,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00)
The right to leran the truth is one of the inherent rights belonging to shareholders. It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shareholders to know the operating conditions of companies, safeguard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ny. In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4 of Company Law (Draft)”, how to design a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system of shareholders’ right to learn the truth and unify the judicial rules in lawsuits on shareholders’ informational right is the key and difficult point. The system of right to learn the truth is a game result between major shareholders and minor shareholders of a company. It needs law to find an interests balance between them. In the Draft, the right to learn the truth is regarded as an inherent right and does not apply to limitation of action. The exercising subject of right to learn the truth has been specified. Restrictions on shareholders’ qualification are excluded, which means any shareholder is entitled to the right to learn the truth. However, rules regarded to dormant shareholders’ right to learn the truth, which frequently cause disputes in judicial practice, are still left in the blank. What’s more, in the Draft, it is the first time to stipulate that if the company causes the shareholder unable to exercise the right to learn the truth, the company will bear the corresponding liability, which effectively protects shareholders’ informational right. But corresponding system is still implicit. Obviously,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4 of Company Law (Draft) is still incomplete, needing to be further studied and consummate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4 of Company Law (Draft); the right to learn the truth; checker;inherent right
2017—05—04
彭炜玉(1993—),女,安徽芜湖人,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陈春雷(1982—),男,山东胶州人,同济大学法学院,在职博士。
DF411.91
B
1008—8350(2017)03—005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