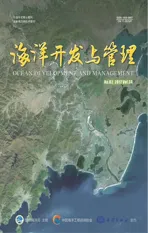中国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的形成条件、探测与保护探讨
2017-03-31蔺爱军林桂兰董卫卫胡毅林兆彬王立明
蔺爱军,林桂兰,董卫卫,胡毅,林兆彬,王立明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与海岸地质实验室 厦门 361005)
中国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的形成条件、探测与保护探讨
蔺爱军,林桂兰,董卫卫,胡毅,林兆彬,王立明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与海岸地质实验室 厦门 361005)
中国南海拥有丰富的水下文化遗产资源,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文章论述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的形成条件,分析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的探测现状,阐述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进展,指出当前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面临的问题,最后提出南海水下文化遗产探测的展望与保护的对策建议。
南海;水下文化遗产;探测;海洋综合管理
我国南海具有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古代人民在探索、开发和利用南海的过程中形成丰富的水下文化遗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水下文化遗产指“至少100年来,周期性地或连续地,部分或全部位于水下的具有文化、历史或考古价值的所有人类生存的遗迹”;包括:遗址、建筑、房屋、工艺品和人类遗骸及其有考古价值的环境和自然环境;船舶、飞行器、其他运输工具或其任何部分,所载货物或其他物品,及其有考古价值的环境和自然环境;具有史前意义的物品。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由水下文物、古港口、古航道、岛礁古代遗存和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文化线路遗存等组成,不仅具有历史、科学、艺术、经济等价值,而且作为中国人民最先开发、最先利用和最先占有南海的历史见证,在维护我国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 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的形成条件
海洋水下文化遗产是人类在探索、开发和利用海洋的过程中形成的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的形成条件包括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且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呈耦合效应。
1.1 自然因素
南海是太平洋西部的边缘海,面积相当于我国东海、黄海以及渤海面积之和的3倍。南海四周为大陆和岛屿环抱,北靠我国华南大陆,南抵大巽他群岛的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西起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包括西北部的北部湾和西南部的泰国湾),东至吕宋岛、民都洛岛、巴拉望岛和我国台湾岛。南海东部有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和巴布延海峡与太平洋相通,南部有民都洛海峡、巴拉巴克海峡与苏禄海相通,西南有马六甲海峡与印度洋相通。南海大体呈NE向延伸的菱形,平均水深1 000~1 100 m,已知最深点在马尼拉海沟南端,为5 567 m。
1.1.1 复杂的地形地貌
南海地形从四周向中央倾斜,围绕中央海盆依次分布大陆架和岛架、大陆坡和岛坡,大陆架上岛屿、浅滩、暗礁众多,曾母暗沙群以及南、北康暗沙群分布在这一区域,在长期内外动力地质作用过程中形成复杂的地质地貌。南海大陆坡和岛坡自大陆架向深海平原呈阶梯状下降,地形崎岖不平、高差起伏大,是南海地形变化最复杂的区域,发育有海台、海槽、深水阶地、海岭、海山、海丘、海底峡谷、斜坡等构造地貌类型。在北、西、南陆坡的海底高原上发育着不少珊瑚礁岛。
1.1.2 丰富的渔业资源
南海地处热带-亚热带海域,为世界海洋动物区系最具多样性的海区之一,渔业资源的动物区系具有种类丰富多样的特征。与邻近海区比较,已知鱼类数为东海的1.4倍、为黄海和渤海的3.56倍,甲壳类和头足类等其他生物也有类似的特征[1]。自古以来,南海丰富的渔业资源吸引我国大量渔民进行捕捞和养殖活动。
1.1.3 恶劣的气象条件
南海经常受热带气旋的侵袭,西太平洋热带气旋常越过菲律宾群岛进入南海。南海本身也是热带气旋的发源地之一,在南海激发和发育的热带气旋被渔民称为“土台风”,具有形成快、范围小、移动方向变化多的特点。南海四季均可能受热带气旋影响,热带气旋常带来大雨和暴雨,俗称“台风雨”,台风有时引起风暴潮(海啸)。
1.1.4 活跃的地震和火山活动
在中国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605年),一次世所罕见的大地震使海南岛约100 km2的72个村庄垂直下降入海3~4 m。至今每年5—6月海水退潮时依稀可见海中村庄废墟、庭院、碑坊、石桥、古戏台等,是我国唯一发现的海底地震废墟。
1.2 社会因素
南海及其东、西、中、南4大群岛,自秦始皇之世即开始纳入中国王朝直辖或自治地区版图,秦汉以降,代有经营[2]。
1.2.1 南海丝绸之路的开辟与发展
南海丝绸之路是中国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干,兴起于秦汉,发展于唐宋,鼎盛于元、明、清三代。10—15世纪中国舰队开辟往返阿拉伯、南亚、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之路,横跨南海和印度洋向西航行到波斯湾,携带瓷器、丝绸、茶叶到西方,返程带回香料、象牙和珊瑚,而舰队有时会终结在波涛汹涌的水域或狭窄的海峡中[3]。公元1405—1433年,郑和先后率领200多条船、2万多人七下西洋,历经28年,先后到达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岸、红海和麦加,其规模之大、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之先进、贸易之胜都达到历史巅峰。
1.2.2 古代中国官方对南海的巡逻监管
为适应南海开发新形势需要,宋代宋神宗于熙宁六年(1073年)置群管安抚司,统辖海南岛、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还采取各种保卫措施如设立水军加强海上巡逻,行使对南海和南海诸岛的主权。元代中国航海事业更加发达,元世祖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派大将史弼领兵5 000人远征爪哇[4]。
1.2.3 中国古代的朝贡体制
明朝初年,通过在南海诸国建立以中国为宗主国的朝贡制度,先后有50多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南海朝贡制度的实行对南海区域甚至印度洋沿岸区域产生深远影响[5]。
1.2.4 渔民的捕捞和迁徙活动
渔民以海为生、以舟为家,自古就是活跃在海上和南海诸岛的有生力量,留下了丰富的海洋文化遗产。
1.2.5 科学技术研究以及海战等
元世祖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特敕令郭守敬亲抵南海测验晷景,郭守敬通过实测得来的一些宝贵数据成为今天考定当时南海测点地理位置的重要科学依据[6]。此外,近代以来发生在南海的海战等也是南海水下文化遗产形成的社会因素。
2 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的探测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官方对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的探测始于1974年,当时广东省博物馆和海南行政区文化局联合对西沙群岛进行第一次考古调查,调查的岛屿包括珊瑚岛、甘泉岛、金银岛、晋卿岛、琛航道、广金岛、全富岛、永兴岛、赵述岛、北岛和五岛等,并在甘泉岛和金银岛进行考古试掘;1975年进行第二次调查,工作重点是对甘泉岛唐宋遗址的再次发掘。1987年广州救捞局与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在广东省台山县上下川岛附近的海面进行探测作业,打捞出200多件宋元时期的瓷器、银锭和铜钱等;1989年对此遗址进行首次水下调查,并将遗址定名为“南海一号”。1991年中央民族学院王恒杰教授到西沙群岛进行考古调查,在甘泉岛西北段发现史前时期的遗存,还在甘泉岛上采集到战国至汉朝遗物;1992年和1996年王教授又对南沙群岛进行2次考古调查,最远到达曾母暗沙,发现秦汉至明清历代遗存。1996年渔民在西沙群岛华光礁海域潜水时发现1艘沉船,后被命名为“华光礁一号”; 2007年中国西沙考古工作队正式对“华光礁一号”沉船进行抢救性发掘和水下考古调查工作。1996年中国西沙考察队对西沙群岛所属的岛屿、沙洲和礁盘进行大量的地面和水下考古调查,为日后的水下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
西沙群岛已往考古工作的重点主要是进行岛屿沙洲的地面调查,尚未开展科学的专题性的水下考古调查和发掘[7]。1998年12月至1999年1月,中国西沙群岛水下考古队在西沙北礁、华光礁、银屿等岛礁附近水域调查发现水下文化遗存14处,包括“华光礁一号”沉船遗址、“北礁三号”沉船遗址、“北礁一号”沉船遗址等重点水下文化遗产,这次水下考古调查真正拉开西沙群岛水下考古工作的序幕。2009年中国考古队员对西沙展开为期20 d的水下文化遗产搜寻,通过使用磁力仪、GPS定位仪、空中航测遥感等技术手段以及潜水探摸方式,新发现5处水下遗物分布点、7处水下沉船遗址。2010年中国考古队员对西沙永乐群岛和宣德群岛进行水下考古调查,经过35 d的海上作业新发现遗址32处。2012年来自宝岛台湾的臧振华先生对东沙群岛水下文化遗存进行调查,通过潜水探摸以及使用侧扫声呐、磁力仪等进行探测,共发现4处沉船遗址及5处遗物分布点。2014年1月24日由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艘水下考古船“中国考古01”号在重庆下水,船上设有潜水工作室、考古仪器设备间等舱室,装备有多波束测深系统、侧扫声呐系统、海洋磁力仪、浅地层剖面仪等先进的海洋地球物理探测设备,主要负责我国沿海、近海以及西沙群岛的水下考古工作; 2015年4月14日至5月25日,“中国考古01”号首次在南海进行水下文化遗产调查,完成“珊瑚岛一号”沉船遗址水下考古发掘、甘泉岛遗址陆上考古调查、“金银岛一号”沉船遗址水下考古调查、永乐环礁礁盘外海域物理探测调查等任务,发现7大类274件大小石构件以及许多水下疑点[8]。
海底沉船因其经济价值高昂且数量巨大,是最受瞩目的水下文化遗产,因此从沉船数量也可以从侧面反映我国南海水下文化遗产探测现况。据考古学家和专业人士估计,全球海洋中至少有100万艘沉船[9];而在中国沿海,学术界猜测宋元时期以来沉没约10万艘货船。南海是我国古沉船和遗物数量最多、水下考古最重要的海区[10],与地中海、加勒比海并称“世界三大沉船坟墓”。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南海沉船量为124艘,按船货平均运载量计算货物可达5万件,陆地文化遗存6处;目前发现的沉船总量还在不断增加,据国外数据不低于1 000艘[11],据中国水下考古中心报告不低于2 000艘[12],可见南海还蕴藏着大量未被发现的沉船,需要进一步详细调查。
由于南海面积广阔、水深较深,海洋地球物理探测技术和水下机器人探测技术在水下文化遗产调查中起到关键性作用。海洋地球物理探测的机制是利用仪器接收水下目标自身发出或反馈的信号,再通过解释和处理后得到目标物的信息;如重力法、磁法、放射性法等是利用仪器测量水下目标物本身具有的密度、磁性、放射性等发出的信号,声学法、电法等是利用仪器测量水下目标物反馈的信号。水下机器人探测技术包括遥控水下机器人(ROV)技术和自治水下机器人(AUV)技术等。
综上所述,从探测范围看,早期探测集中在岛礁及其邻近浅水区域:目前我国对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的探测中,对西沙群岛及其海域探测次数最多,取得成果也最丰硕;对东沙群岛及其海域探测取得初步成果,发现10余处沉船遗址;对南沙群岛及其海域探测尚未全面开展,考古工作非常薄弱;对中沙群岛及其海域探测次数也非常有限。从探测技术看,我国对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的探测经历3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期之前)是自由潜水和拖网探测阶段,自由潜水不仅工作海域水深较浅、下潜时间短,而且对人体潜水技能和身体素质要求颇高,工作效率低下,而拖网会增加水下文化遗产遗址受到破坏的风险;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2014年前)是专业潜水和仪器装备探测阶段,通过国外引进和自主研发,探测技术和设备性能有显著提升,装备包括多波束测深系统、旁侧声呐系统、海洋磁力仪、浅地层剖面仪和水下机器人等;第三阶段(2014年后)是科学考察与研究阶段,随着“中国考古01”号水下考古船的下水,船上装备各种先进仪器,整体性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标志着中国南海水下文化遗产探测水平迈入新阶段。
3 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进展
中国海洋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始于南海、重在南海。1974年3—5月,我国考古工作人员首次赴西沙群岛进行文物调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萌芽。1989年10月20日,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首次为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法律依据,该条例又于2011年1月8日修正施行。2014年1月,国家南海博物馆建设项目正式立项,将通过测量技术、仿真技术、4D渲染、动漫等手段提升展陈和互动效果,对保护南海水下文化遗产起到积极作用。2014年5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南海基地项目获批,建成后将是集水下文化遗产调查与保护、水下考古、出水文物修复、人员培训为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性水下考古基地。2014年6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前身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2009年9月设立的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获批正式成立,对于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目前西沙永兴岛水下考古工作站已开工建设,建成后将为加强西沙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拓展西沙文化遗产保护新领域起到重要作用。总体来说,经过40余年的发展,我国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取得让人欣慰的进展。
3.1 数量不断增长,内涵不断丰富
自1974年以来,我国在南海发现的水下文化遗产数量不断增长。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水下文化遗产探测技术的不断进步、仪器装备的不断发展和水下考古力度的不断加大,已先后在西沙群岛海域发现120余处水下沉船遗址,取得突出成果。同时,南海水下文化遗产文化内涵也不断丰富,不仅有沉船及其所载货物,还有古港口、古航道、岛礁古代遗址、沿岸历史文化遗迹、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遗址等。
3.2 保护理念创新发展
“南海一号”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南海水下考古发现之一。2007年12月,本着“整体打捞与搬迁”的原则,我国成功打捞出水南宋沉船“南海一号”,现保存于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古沉船“整体打捞与搬迁”的方法在国际尚属首次,不仅体现我国沉船打捞技术的进步,也表明我国沉船保护理念的创新发展。
3.3 保护和修复技术不断进步
在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和修复方面,实验室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我国在南海范围已拥有2个分别位于广东和海南的水下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位于海南省博物馆的出水文物保护实验室具有全国领先水平,我国第一艘专业水下考古船“中国考古01”号也设置出水文物保护实验室。在出水文物保护和修复技术领域,我国在水下瓷器和铁器修复方面已具有相对成熟的经验[13];此外李国清[14]提出海洋古沉船的保护处理方法,田兴玲等[15]分析研究“南澳一号”明代沉船木材类型、化学组成等信息,张治国等[16]对海洋出水石质文物表面凝结物进行分析和去除技术研究,耿苗[17]对海洋出水漆器残片进行几种加固方法的实践研究。
3.4 多部门协调合作,执法力度不断加强
2011年4月下旬至5月下旬以及2012年4—5月,为保护西沙水下文化遗产,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海南省文物局、海南省西南中沙群岛办事处合作组成西沙群岛水下文化遗产执法巡查工作队,开展西沙群岛海域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状况巡查和文物执法督查。2011年8月18日,国家海洋局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我国管辖海域内文化遗产联合执法工作的通知》,决定建立联合执法工作机制。2012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家文物局、国家海洋局举行西沙群岛附近海域文化遗产联合巡航执法专项活动,属国内首次水下文化遗产执法巡航。2012年6月21日,国务院批准设立地级三沙市,管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必将承担起更多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任。
4 我国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问题
4.1 资源数量、分布等信息依然不清
我国对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的调查时间起步晚、人才和装备也很短缺,目前对南海水下文化遗产资源的数量、分布等信息依然不够清楚。当前仅对西沙群岛及其附近浅水域的遗产数量和分布有较多认识,对东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水域的遗产数量和分布还处在初级认识阶段,对处在南海深水区的遗产数量和分布基本没有认识。
4.2 非法盗掘、蓄意破坏等行为现象时有发生
水下文化遗产被非法盗掘、蓄意破坏等行为在南海屡见不鲜,主要参与者包括国际商业盗宝公司、私人探险队、海盗、境外势力和违法渔民等。如,澳大利亚一家海洋商业打捞公司的职业寻宝人迈克·哈彻先后于1985年和1996年在南海盗捞2艘古沉船,为获得巨额利润,竟然故意砸碎“泰星号”清代沉船上的60多万件瓷器;“华光礁一号”南宋古沉船自1997年被渔民发现以来多次遭到非法盗掘,考古工作者找到船体时发现人为破坏痕迹明显;西沙群岛海域可见的沉船遗址几乎都呈现不同程度的盗掘和破坏,有些甚至被完全破坏。
4.3 经济建设、旅游开发等海洋开发利用活动的影响
随着南海沿岸、岛礁等区域经济建设项目的日益增多和旅游开发节奏的不断加快,南海水下文化遗产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威胁。当前海南省正在大力推进国际旅游岛建设,西沙邮轮旅游航线已于2013年4月28日开通,今后南海旅游业将越发繁荣,海洋开发利用活动也将越发加强,因此应尤其重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采取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
4.4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修复技术仍面临巨大困难
虽然我国在出水陶瓷器、铁器保护修复方面已有较为成熟的经验,但出水陶瓷器数量巨大,不仅保护修复工作量大,而且不同程度的破损和残缺也给修复增加难度。此外,在其他出水文物的修复过程中仍面临巨大困难,尤其是古沉船修复时间长、技术难度高、风险大,是出水文物保护修复的最大难题;如海洋出水木质沉船的铁硫化合物控制是世界性难题,目前尚未有成熟的处理方法可供借鉴。
4.5 法律法规欠缺
在水下文化遗产归属问题上,最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5年4月24日第四次修正)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而对中国毗连区、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的文物没有明确规定;最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2011年1月8日修正版)对遗存于外国领海内起源于中国的文物没有明确规定,显然对中国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不利的。在地方性法律法规方面,广东省有2009年3月1日起施行的《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广西有2014年1月1日起施行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海南省目前没有关于文物保护的综合性法规(1994年制定的《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已于2004年废止);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仅在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提到“水下文物”,《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仅在第十五条提到“水域埋藏的文物”,可见用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条款太少、内容笼统、操作性不强。此外,广东、广西、海南也没有专门用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
5 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的探测展望与保护对策
5.1 成立南海水下文化遗产探测技术和资源评价国家功能实验室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的探测取得一些成就,但探测工作主要围绕西沙群岛开展,在东沙群岛也有初步探测成果,而对南沙群岛、中沙群岛探测次数非常有限,几乎没有发现。就探测技术和装备而言,目前我国适用于南海水下文化遗产探测的专业考古船只有1艘,虽然装备性能已很先进,但随着探测范围的扩大、工作水深的加深,对探测技术、装备性能及数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就探测机制而言,当前探测工作开展主要限于文物部门,其他机构涉足甚少,而南海面积广大,仅依靠文物部门探测显然不足,因此有必要成立南海水下文化遗产探测技术和资源评价国家功能实验室(图1),从国家层面给予重视,为全面探测摸清南海水下文化遗产提供坚实的保障力量。

图1 南海水下文化遗产探测技术和资源评价国家功能实验室基本组织架构
查清南海水下文化遗产资源的数量、分布是保护修复的基础,学术的重视、技术的进步以及人才的培养是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修复的3个助推器。实验室的总体目标是以海底科学和探测技术为基础,提高我国南海水下文化遗产探测技术,为查清南海水下文化遗产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为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奠定基础,服务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实验室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水下文化遗产探测关键技术,此外要统筹处理各涉海科研和地质调查等部门有关南海海底探测的数据资料,通过对其进行数据后期处理和分析,圈出南海水下文化遗产可疑点,做出南海水下文化遗产资源分布评估。实验室重点研究内容为声呐探测关键技术,包括多波束测深系统、侧扫声呐和合成孔径声呐等;水下机器人探测关键技术;高分辨率浅地层探测关键技术;高精度磁测关键技术;海底数据处理与水下文化遗产资源评估等。
5.2 建立南海水下文化遗产数据库系统
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海洋水下考古、水下文化遗产挖掘和原址(或出水)保护修复等过程。加强对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科学技术的研究,重视对海洋出水文物实验室的软硬件建设,针对不同环境的原址和不同材质的出水文物应结合专业技术和管理方法对其进行相应保护。此外,建立南海水下文化遗产资源信息和监测数据库系统,实现对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的科学管理和实时监测,该数据库应是中国水下文化遗产数据库系统的一个重要分系统。
5.3 加快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进程
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的预备名单应包括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要加强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的理论研究,确定其主体范围和申遗重点,根据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全面调查分析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文化遗产点的价值、真实性、完整性和保护管理状况等,编制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申遗点保护管理规划,撰写世界遗产申报书。要借鉴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申遗成功的经验,精心设计海上丝绸之路申遗项目,通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进一步提升南海水下文化遗产内涵,兴起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热潮。
5.4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探索建立执法机制
国家和地方层面应尽快完善和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确保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有法可依”;在与海洋开发利用、保护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政策文件等中增加对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条款。在执法方面,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海洋局等部门要进一步深化合作,探索建立以专项执法为主、综合执法为辅、综合执法与专项执法并存的常态化、科学化、效能化执法机制。
5.5 推动建设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区
在南海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可行性的水下文化遗址建成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区,为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开拓新思路、树立新旗帜。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区、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正在建设的国家南海博物馆以及南海水下文化遗址公园等具有海洋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要充分发挥作用,一方面提高人们对保护南海水下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认识,培养社会各界海洋文化意识;另一方面通过设置合理票价,用以补充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资金。
5.6 积极推进海峡两岸交流合作
太平岛是南沙群岛中面积最大的岛屿,具有重要的军事和战略价值。海峡两岸要加强交流与合作,着眼大局与未来,共同对南海岛礁及其附近海域开展水下文化遗产探测与保护工作,为全面查清和保护南海水下文化遗产扫除障碍,亦为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贡献力量。
[1]唐启升.中国区域海洋学:渔业海洋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335-335.
[2]曲金良.“环中国海”中国海洋文化遗产的内涵及其保护[J].新东方,2011(4):22-27.
[3]HVISTENDAHL M.Maritime ambitions as China builds a modern armada,it is pouring money into underwater archaeology and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its early exploits on the high seas[J].Science,2014,344(6184):572-575.
[4]司徒尚纪.从海洋制度文化看历代中国政府对南海领土主权的管理(上)[J].岭南文史,2012(3):1-7.
[5]任念文.明初南海朝贡制度与封建国家海洋战略论述[J].太平洋学报,2014,22(8):94-105.
[6]李金明.元代“四海测验中”的南海[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4):35-42.
[7]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社会科学专辑Ⅰ:考古调查与文献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267-270.
[8]陈蔚林.“中国考古01号”满载而归[N].海南日报,2015-05-26(003).
[9]赵叶.海底沉船一百万[J].世界文化,2008(10):43-44.
[10]崔策.泉州与广东的古代海外交通贸易[J].广东造船,2015 (1):67-69.
[11]戎海.海南,下一站海洋文物大省[N].海南日报,2013-05-30(018).
[12]李培,方一庆.中国水下考古中心推测:南海古沉船不少于2 000艘[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06-13(02).
[13]杜颖.华光礁Ⅰ号重生之困[N].海南日报,2013-06-25 (004).
[14]李国清.出水海洋古沉船的保护[J].中国文化遗产,2013 (4):66-67.
[15]田兴玲,李乃胜,张治国,等.广东汕头市“南澳Ⅰ号”明代沉船木材的分析研究[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4,26(04):109-115.
[16]张治国,刘婕,田兴玲,等.海洋出水石质文物表面凝结物的清洗技术研究[J].石材,2013(12):38-42.
[17]耿苗.海洋环境出水漆器残片的几种加固技术实践[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17(4):100-103.
The Formation Conditions,Detec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LIN Aijun,LIN Guilan,DONG Weiwei,HU Yi,LIN Zhaobin,WANG Liming
(Thir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SOA,Laboratory of Marine and Coastal Geology,Xiamen 361005,China)
There are abundant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UCH)resources which have great value and significan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formation conditions of UCH,analyzed the detection statuses of UCH,illustrated progress of conservation of UCH,and pointed out the current problems during the conservation of UCH in the South China Sea.Finally,a series of prospective and suggestions that would be conductive to protect UCH of the South China Sea were put forward.
South China Sea,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Detection,Marine Integrated Management
P7;K87
A
1005-9857(2017)02-0058-07
2016-09-20;
2016-12-08
国家海洋局公益性项目(201305038);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41204100).
蔺爱军,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海洋管理与海域使用论证,电子信箱:malingshu21@163.com
林桂兰,教授级高工,博士,研究方向为海洋管理与海域使用论证,电子信箱:linguilan@tio.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