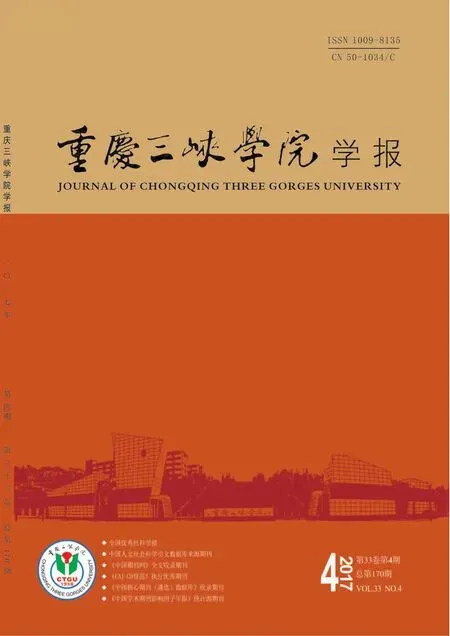《墨经》中的逻辑理论探析
2017-03-29崔雪茹
崔雪茹
(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四川成都 611130)
《墨经》中的逻辑理论探析
崔雪茹
(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四川成都 611130)
墨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建立起完整的逻辑学体系。因为其逻辑学体系围绕着辩论展开,因此被称为墨辩逻辑。墨子的逻辑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墨经》中。他在《墨经》里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并要求将辩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来学习,这是中国逻辑史上的首创。《墨经》认为辩的性质与作用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明是非、别同异、察名实、处利害、决嫌疑、审治乱。辩的程序是形成概念,进而判断,进而推理的过程,即“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三个逐次递进的步骤。在《墨经》中,后期墨家对形式逻辑的三条基本规律: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都有所述及。
矛盾论;同一律;排中律
墨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建立起完整的逻辑学体系。墨子的逻辑思想主要集中在其代表作《墨子》中《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这六篇旨在通过逻辑方式树立墨家的逻辑学观点。六篇合在一起,通称《墨经》或《墨辩》。《墨经》是中国古代第一次系统全面地提出逻辑学理论的著作,在中国逻辑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墨家首次在逻辑学意义提出“故、法、类”等基本概念,并把其作为逻辑推理的基本范畴,这些范畴也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推理之中。笔者试图从辩的性质与作用,辩的程序以及其中三条基本规律: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论述《墨经》中的逻辑学理论。
一、辩的性质与作用
《小取》开宗明义对逻辑学的对象、性质、作用作了高度概括:“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1]642
陈孟麟指出:“这是中国逻辑史上第一篇划时代的文献,它标志着古代中国对逻辑学的理解,已进入自觉的、并具有宏观水平的阶段。《墨辩》已认识到,认识客观事物,还要有一个重要的条件:思维的自我认识。必须认识到人们自己的思维,必须掌握思维本身的形式和规律,才能使思维正确反映世界并进行思想交流。这样就把人们自己的思维当作思维对象,在认识领域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方面。”[2]3
(一)辩的性质
墨辩逻辑学是后期墨家重视谈辩的产物。在《墨经》中,后期墨家给“辩”下了一个定义:
辩,争彼也。辩胜,当也。(《墨子·经上》)
辩,俱当,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不当若犬。(《墨子·经说上》)[1]478
所谓“辩”,就是“争彼”。那么,什么是“彼”呢?《墨经》中也有一个定义:
彼,不两可两不可也。(《墨子·经上》)
彼:凡牛,枢非牛,两也,无以非也。(《墨子·经说上》)[1]478
把《经》和《经说》中的这两条合起来,就可以看出,后期墨家所谓“彼”实际上是指一对矛盾命题。“争彼”就是围绕一对矛盾命题的论争。例如,有人说这是牛,有人说这不是牛,两人争论的对象是同一个,两人的结论却恰好相反,这才是“争彼”,才是真正的辩。如果争论的对象不同,那么,即使两个命题的形式恰好相反,也构不成辩。如有人说凡是牛(“凡牛”),有人说枢不是牛(“枢非牛”),这实际上是两个互不相关的命题,所以根本构不成辩论。对于一对矛盾命题来说,一方面,必有一真,不能够同时假,也就是说,“不可两不可”;另一方面,也必有一假,不能同时真,此即所谓“不两可”,亦即“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辩的目的就是判定辩论双方究竟谁的命题和事实相符(当),谁的命题和事实不符(不当)。辩必然有胜有败,和事实相符的(当),就属于辩论中胜的一方,不符的(不当)就属于败的一方。
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墨子·经下》)[3]152-153
谓:所谓非同也,则异也。同则或谓之狗,其或谓之犬也。异则或谓之牛,其或谓之马也。俱无胜,是不辩也。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墨子·经说下》)[1]535
(二)辩的作用
辩的性质既明,现在再来看看辩的作用。后期墨家把辩的作用和目的概括成了六点:
1.明是非
在后期墨家看来,所谓辩,就是判定争论双方真假对错的过程。既然有争论,就难免会有各执己见的事情发生。而相互冲突的见解(矛盾命题)不可能都正确,所以只有通过辩才能发现谁的说法与事实相符,谁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与事实相符的即为真,与事实不符的即为假。
2.别同异
“同异”和“是非”不同。“是非”是就认识方面而言,“同异”则讲的是对象本身的关系。但是,是非不分的根据常常在于同异无别,如庄周的“齐物论”即为其例。所以,要想明辨是非。就必须先区分开事物的同异关系。“别同异”是“明是非”的必要前提。
3.察名实
名即概念名称。实即概念名称所反映的事物。名实关系也就是指概念名称和它所反映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战国中后期,由于社会形势的急剧变迁,“名不副实”的现象极其严重,因而急需重新订正名实之间的关系。而在后期墨家看来,要想解决这一重大问题,就必须借助于辩的作用,因为只有弄清楚了为什么此名只能反映此实而不能反映彼实,此实只能由此名描画(《经说下》:“名若画虎也”)而不能由彼名描画,然后才可以谈得上名实相符问题。
4.处利害
“处”即判断和权衡,“处利害”意为具体衡量一件事物的好处和害处。后期墨家继承了墨子的功利主义思想,反对把“辩”只当作单纯的区分是非同异的理论活动,而认为它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它能给人带来实际的好处。“处利害”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在好坏利害没有截然两分的情况下,通过比较和权衡,就能够在利之中选取最大的,在害之中选取小的,从而达到一种比较理想的结果。
5.决嫌疑
“决”指判决,“嫌疑”指疑惑不明的事理,“决赚疑”即是对疑惑不明的事理做出正确的判断。在后期墨家看来,事物之间均有确定的区别,如果把这些区别看成疑似之物,那就无法从根本上分清是非和利害,所以,他们主张把消除疑惑亦看成辩的一项重要作用。
6.审治乱
和“处利害、决嫌疑”相比,“审治乱”是辩的更重要作用。前两者只是局限于个别的具体的问题,而后者则把范围扩展到了整个社会的治乱存亡。其结果,辩不但是处理个别问题的途径,而且成了治理国家的工具。这样,后期墨家所发展的逻辑技巧最终仍落实到了实际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之中。
二、以名举实
紧接着辩的六种作用和目的之后,《小取》篇又继续说:
焉(乃)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
为了达到“摹略万物之然”的目的,墨辩逻辑学派专门研究“论求群言之比”,即逻辑形式。他们用“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概括地揭示了概念、判断、推理这三种思维的基本形式。“以名举实”准确地把握了概念的本质:“举,拟实也。告之以名,举彼实故也。”(《墨子·经说上》)这里明确地指出:概念并不是对事物的直观描述或主观意会,而是一种理性活动的结果。“故”正是事物的本质,是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根本原因,用语词表示出来便是概念。这一论断与儒家“举相似”的提法有根本区别,与名家诡辩说也划出了明显界线。比如,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完全是以主观的、狭隘的宗法原则对“直”的曲解,而墨子的“揣曲直”(《墨子·贵义》),则是明确要求对是非曲直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墨家后学更是进一步用明确概念定义的方法对“类”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比如,公孙龙说“白马非马”,这是以感觉的多样性排斥理性的规律性。《墨经》则明确认为:“白马,马也。命之马,类也。”类是本质、是一般,而一般恰恰来源于特殊之中,白马是马正是抓住了白马这种个别所具有的规律性的东西,即白马的实质是马,而不是公孙龙所说的仅是“命色”。这正是抛弃了事物的偶然性而抓住了事物的本质。通过明确概念的本质特征,墨辩逻辑学派就将判断推理建立在坚实的逻辑基础之上。这样,整体性的认知方式才可能被精确严密的逻辑方法所代替,而思维的意会性、模糊性也就被断然排斥。
“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讲的是辩的性质,辩是一种反映事物真相,探求名、辞、说等思维形式之间关系的活动。“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讲的则是辩的程序和步骤。在后期墨家看来,整个辩的过程通常不外乎由一系列的论证(说)组成,而每一论证都是由表达判断的语句(辞)构成,每一语句又由表达概念的词项(名)构成,因此辩的程序实际上就是形成概念,进而判断,进而推理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小取》篇中就被概括为“以名举实”“以辞抒意”,和“以说出故”三个逐次递进的步骤。兹以“以名举实”例证之:
(一)名与实
名实关系是名辩思潮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名”可指语词,也可指概念,“实”则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或对象。名实关系即是语词、概念和它所命名、反映的事物或对象的关系。孔子最早提出正名的主张,要求以“名”正“实”,即先界定,理清“名”的意义,然后再用以规范人的行为。墨子则相反,主张以名取实,也就是说要根据“实”来判定“名”的恰当、正确与否。例如说盲人也可以知道皑是白色,黔是黑色,但是一旦把白黑两者放在一起,他就不能分辨了。所以真正的“知”还是靠“实”而不是“名”来决定。后期墨家继承了墨子的观点,给名实问题以进一步的论证。
首先,有“实”才有“名”,无“实”则无“名”。《大取》云:“名,实名;实不必名。”《经说上》云:“有之实也,而后谓之;无之实也,则无谓也。”“实”不是依“名”而存在的,有了某种“实”,然后才有相应的“名”,没有某种“实”,就没有相应的“名”。即使过去的“实”现在已不复存在,但仍可用“名”去描述。例如“尧之义也,是声也于今,所义之实处于古”(《经说下》)。意思是说,尧之义的“实”是远古发生过的事,尽管现在不存在了,但我们仍然可以用“义”之名去反映它。
其次,用名以举实。所谓“举”,后期墨家有一个解释:
举,拟实也。(《墨子·经上》)
举:告以文名,举彼实故也。(《墨子·经说上》)
“拟”是摹拟、反映,“举”即对“实”的摹拟和反映。换句话说,“名”是用来摹拟“实”的。但是,后期墨家并未停留在简单的摹拟说上,而是认为“名”是对“实”的本质的反映。“举彼实故”中的“实故”指的就是“实”的本质、根据,也就是说,“名”对“实”的反映是对其本质或规律的反映。这是一种抽象的思维过程,而不是简单的感性活动。在“墨辩”中,这种更简单的感性活动是用“指”来表达的:
思想交流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告诉对方对象的名字,一种是直接指着对象给对方看。列举我的朋友某某是富商,这是用“以名示人”,我的朋友可以不在眼前;指着眼前的动物说“这是霍”,则是“以实示人”。
但是,“指”的功能是有限的,有些情况是无法用“指”来传达的:
所知而弗能指。说在春也、逃臣、狗犬、贵者。(《墨子·经下》
春也,其执固不可指也,逃臣,不智其处。狗犬,不智其名也。遗者,巧弗能两也。(《墨子·经说下》)[1]536
春是一个人的名字,该人死后当然就不能指着他说;逃亡的奴仆,因为不知道藏在何处,所以无法指着他说;如果一个人不知道狗、犬的名称,单是用手指,同样无法让此人区分开这两个名称。遗失的东西也不能指着说,因为能工巧匠也不能制造出两个完全一样的东西。春、逃臣、狗犬、遗者还是一些具体的人和物,尚且不能用“指”来传达,那些抽象的概念、范畴就更不用说了。它们必须通过“名”这种概念来摹拟和反映。
再次,“名”必须符合“实”。后期墨家认为,既然名是用以举实的,那么“名”就必须符“实”。只有“名”符其“实”,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
知其所知不知,说在以名取。(《墨子·经下》)
说知,杂所智与所不智而问之,则必曰“是所智也,是所不智也。”取去俱能之,是两智之也。(《墨子·经说下》[1]538
知不知的区别正在于“名”是否符合“实”,符合者即能以名举实的,是谓知;不符合者即不能以名举实的,就是不知。
最后,“名”必须随着“实”变。后期墨家认为,名是人所命的,亦即是由人约定俗成的。随着“实”的变化,约定俗成的“名”就必须随着“实”而变。《大取》篇云:“诸以居运命者,苟入于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诸以居运命者,若乡里齐荆者。”这就是说,以居住地而命的名,必须随着地域的变迁而变化。一个地方早先属齐,那里住的人便叫齐人,一旦该地划归楚国,则那里的人就应该叫楚人了。如果“实”已经变了而“名”还没有变,那么这就叫“过名”。
或,过名也,说在实。(《墨子·经下》)
或:知是之非此也,有知是之不在此也,然而谓此南北,过而以已为然。始也谓此南方,故今也谓此南方。(《墨子·经说下》)
“过名”即是不符实际的“名”。譬如,过去认为某地是“南方”,而实为东南方,如果现在仍然称该地为“南方”,即就成为“过名”了。避免出现“过名”的主要方法就是“名”随“实”变,“名”及时准确地反映“实”。
(二)概念与语词
在“墨辩”中,“名”既可指概念,亦可指语词。概念是一种思想,它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或属性;语词则是一种符号,它是由人们约定而成。对此,后期墨家有明确的认识:
言,出举也。(《墨子·经上》)
言也者,诸口能之出名者也。名若画虎也。言也谓言,由名致也。(《墨子·经说上》)
这里的“举”就是“以名举实”的“举”,“出举”之“言”就是把人们所反映的内容用语词说出来,换句话说,言语就是把名说出来的口部动作,言语表现为一连串的语词(名)之组合。而“名”从举实的角度讲,是为概念;从出举的角度讲,是为语词。作为概念,名是对对象性质的反映,如画虎,画出来的虎并不是某个具体的虎,而是虎这类事物共有属性的形象说明。作为语词,名则是我们约定俗成的符号。一开始怎么约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旦约定,就不能随意更改。
惟吾谓,非名也,则不可,说在反。(《墨子·经下》)
惟:谓是霍,可。犹之非夫霍也。谓彼是是也,不可。谓者毋惟乎其谓。彼犹惟乎其谓,则吾谓不行;彼若不惟其谓,则不行也。(《墨子·经说下》)[1]542
“吾谓”是约定俗成之名。“惟吾谓”的意思是说离开约定俗成之名,而自己随意命名,这是不行的。譬如,大家已经约定“霍”指一种鸟,那么你称这种鸟中的任何一只叫“霍”都是可以的,但你把另外一种鸟也叫做“霍”就不行了。所以,为了保持语词的确定性,必须做到“谓者毋离乎其谓”。
对于概念与语词的关系,后期墨家认为,概念需要通过语词表示,但并不是所有的语词都表示概念。譬如,我们可以把狗这种动物命名为“狗”或“犬”,亦可以指着该种动物说“这是狗”“这是犬”。但是如果有狗于此,叱而呼之说“狗!”这里的“狗”就既不是语词,也不是概念,而只是一种情感的表达。
在后期墨家看来,概念和语词之间关系的完整说法应该是:一方面,一个概念可以通过不同的语词来表达。如:
同,二名一实,重同也。不外于兼,体同也。俱处于室,合同也。有以同,类同也(《墨子·经说上》)[1]480
知狗而自谓不知犬,过也,说在重。(《墨子·经下》)
异名同实,“墨辩”叫做“重同”。“重同”的意思是说,对于同一个对象(实),可以用不同的语词来指称,这些不同的语词(异名)表达的实际上是同一个概念。如“狗”和“犬”是二名,但所指的都是狗这种动物,所以,说“狗”就是说“犬”,说“犬”也就是说“狗”;知“狗”,就是知“犬”,知“犬”也就是知“狗”。狗和犬实际上是同义词。对于同义词,只承认知道一个而不知道另一个是错误的。
另一方面,一个语词也可以表达不同的概念。如:
且,言然也。(《墨子·经上》)
且:自前曰且,自后曰己,方然亦且。(《墨子·经说上》)
“且”这个语词是用来说明事物状态的。它有三种含义:1.指将要发生的事。如“且出门,非出门”,意思是将要出门,但还没有出门。又如“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年且九十”意思是说年龄将要九十了。2.指已经发生的事。如“病且不起”,意思是说病后不能起床。3.指两件事同时发生。如“且战且走”“且哭且诉”等等都是。同一个“且”字,表达的思想却包含了时间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三相。在辩论中,如果忽视了这种一词多义的现象,就会出现答非所问的情形。所以,后期墨家提出了“通意后对”的原则,要求辩论时首先弄清楚对方语词、概念或命题的所指,然后再来回答。
(三)名的种类
“名”是对客观事物的摹拟。客观事物的性质、数量纷繁复杂,相应地,作为概念之“名”的数量也就无限地多。为了便于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我们必须对名进行分辨、归类。后期墨家认为,分类需要遵循一定的准则:
牛狂与马惟异,以牛有齿,马有尾,说牛之非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无有。曰之与马不类,用牛有角、马无角,是类不同也。若举牛有角、马无角,以是为类之不同也,是狂举也,犹牛有齿、马有尾。(《墨子·经说下》)
牛和马是不同的类,但是以“牛有齿,马有尾”作为划分两类的根据则不可,因为牛和马都既有齿又有尾,因此作为分类的准则之一,必须是一方偏有、一方偏无,不能两方共有。后期墨家把这种准则概括为“偏有偏无有”。但是仅有“偏有偏无有”仍然是不够的,如牛有角、马无角,如果据此而说牛类不同于马类,这同样是狂举。按照“墨辩”,“类同”的根据在“有以同”,亦即构成一类事物的本质属性相同;同样地,“类异”的根据在“不有同”,亦即没有共同的本质属性。有角无角并不是牛类区别于马类的本质特征,因此不能作为划分这两类的标准。所以,作为分类的准则之二是,必须以事物之本质属性的有无为根据。
依据这两条准则,后期墨家对“名”进行了详细的划分。
首先,依据外延的大小把“名”分为达、类、私三类:
名:达、类、私。(《墨子·经上》)
物,达也,有实必待之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墨子·经说上》)[1]479
“达名”是外延最大的概念,包括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如“物”,凡是存在的一切东西都可以用它来表示。“类名”外延次于达名,大于私名,是包举一类对象的概念。如“马”,凡是具备马的本质属性的动物都可以叫做马。“私名”是外延最小的概念,它所指称的仅是一个特定的个体,如“臧”,作为奴隶的名字,它指的只是单独一个人。达、类、私三名正好相当于普通逻辑学中所说的范畴、普遍概念和单独概念。
其次,兼名与非兼名,这是关系到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时的名的区分问题。“牛马之非牛,与可之同。说在兼。”(《墨子·经下》篇)《经说下》篇对此做了详细的解说:“牛: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则或非牛而‘牛也’可。故曰:‘牛马非牛也’未可,‘牛马牛也’未可。则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马牛也亦不可。且牛不二,马不二,而牛马二,则牛不非牛,马不非马,而牛马非牛非马,无难。”
这段话的意思是:牛马是两类动物,当我们说“牛马”时,这个“牛马”,就是一个“兼名”。牛、马各是一类动物,我们称其为牛、称其为马,就不是兼名,而是类名。“牛马”这个兼名,既不等于牛,也不等于马(牛不非牛,马不非马,而牛马非牛非马),因为牛是牛,马是马(牛不二,马不二,而牛马二)。部分不能等同于整体,牛、马,都只是“牛马”这个兼名的一部分。“无难”,这是好理解的啊。
最后,依据对象的性质把“名”区分为“形貌之名”与“非形貌之名”:
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庙者,皆是也。(《墨子·大取》)[4]548
所谓“以形貌命者”,就是根据事物的形态、面貌命名的概念,如山、丘、室、庙都是。它相当于普通逻辑学中的具体概念。对于这类概念,必须知道它所反映的对象是哪一种,然后才能认识它。“不可以形貌命者”,即不能够指出具体对象及其形态、面貌的概念,略相当于普通逻辑学中的抽象概念。对于这类概念,虽然不知道它所反映的对象是怎么样的,但仍然可以了解它。
由概念的展开而进行判断就是“以辞抒意”。墨经认为,判断来源于客观事物,但主观认识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判断是否真实还有待于逻辑验证。为此,墨辩提出了对判断的要求:“名实耦”,即名与实相符,同时,《墨经》还对判断应该具备的结构作了说明:“所谓,名也;所以谓,实也。”判断的主词表示对象,叫“所谓”,判断的谓词说明对象,称作“所以谓”,其所体现的正是判断结构的客观基础。《墨经》还进一步对判断的类型作了全面的研究,提出了肯定判断、否定判断、全称判断(“尽”)、特称判断(“或”),假言判断(“假”),必然判断(“必”)等诸种判断形式,这些研究在逻辑史上是一个重大贡献。
对于“以说出故”的逻辑推理,《墨经》同样也有非常深刻的研究。《大取》曾对此加以概括说:“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在这里,“‘故’是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必然联系,即充足理由;‘理’指推理所呈现的逻辑手段,即推理形式;‘类’指个别与一般之间的关系的推理历程,即推理的逻辑方法”[2]58。在论及“说”(推理)的具体方式时,墨辩分别提出“止、或、假、效、辟、侔、援,推”等诸种论式,并一一加以具体说明。同时,又对“是而不然”“不是而然”等各种推理中的谬误作了明确的批驳。所谓“是而不然”,是说由肯定的真前提能得出肯定的真结论,但如果滥用这种推理形式,也可能得出肯定的假结论。比如:“其弟,美人也;爱弟,非爱美人也。”(《墨子·大取》)前提为真,但结论却是错的:因为“爱弟”是血缘关系,而“爱美人”则是审美观的体现。所以,不能由“其弟,美人也”推出“爱弟,爱美人”的结论,同理“车,木也”;但不能说“乘车,乘木也”。墨家进行这类精细严密的逻辑研究,不仅仅表现出他们对纯粹抽象思维的兴趣,而且反映出他们对理论思维规则的高度重视。
他们针对大量论解实践中的逻辑混乱,提出了“异类不比”的原则。即使对自己提出的逻辑思维方式他们也极力避免它在实践中的误用:“辟、侔、援、推之辞,行而异,转而危(诡),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墨子·大取》)而这种对思维规律的科学深刻认识,恰恰是中国古代大多数学派所欠缺的。
三、逻辑规律及其他
形式逻辑有三条基本规律: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同一律的内容是,如果一个思想是真实的,那么它就是真实的。矛盾律的内容是,任何思想不能既是真实的,又是虚假的。排中律的内容是,任何思想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这三条基本规律要求思维具有确定性,要求思想具有确定的内容,因而对一切思维形态都是普遍有效的。在《墨经》中,后期墨家对这三条基本规律都有所述及。
(一)同一律
后期墨家关于同一律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其“正名论”中:
彼彼此此,与彼此同。说在异。(《墨子·经下》)
彼:正名者:彼彼此此可,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此止于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则彼亦且此此也。(《墨子·经说下》)
“正名”由孔子最先提出,要求以名正实。墨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主张取实予名。无论是以名正实,还是取实予名,其目的都是要名实相符。后期墨家继承墨子的名实观,进一步提出了墨家的“正名论”:“彼”之名只能指彼之“实”,“此”之名只能指此之实。如“牛”之名只能专指牛之实,“马”之名只能专指马之实。这就叫“彼彼此此可”。对于兼名“彼此”来说,它也只能指“彼此”之实,而不能或仅指“彼”之实或仅指“此”之实。如“牛马”之名只能专指牛马,既不能仅指牛,也不能仅指马。这就叫“彼此止于彼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在“墨辩”中,“彼”和“此”主要起一种符号作用,相当于普通逻辑中的变项。后期墨家对“彼”、“此”和“彼此”的分辨,对“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的表述,已经很接近普通逻辑中同一律的定义。
在实际辩论中,后期墨家根据同一律提出了“通意后对”的原则:
通意后对,说在不知其谁谓也。(《墨子·经下》)
通:问者曰:“子智孰乎?”应之曰:“孰,何谓也?”彼曰:“孰,施。”则智之。若不问孰何谓,径应以弗智,则过。(《墨子·经说下》)
同一律要求概念明确,名实相符。但日常语言中一词多义是很普遍的现象,这就要求在谈辩中首先需弄清楚对方的意思,明确对方概念的所指,然后再来作答。如果不清楚对方的问题就去回答,很可能会出现答非所问的错误。如,提问的人说,“你知道孰吗?”应答者需要先问明“孰”是什么意思,否则就答曰不知就错了。
忽视或故意利用语词歧义而导致偷换概念、转移论题,都属违反同一律的错误。墨子本人对此已早有认识: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曰:“善为政者,若之何?”仲尼对曰:“善为政者,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子墨子闻之曰:“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叶公子高岂不知善为政者之远者近也,而旧者新是哉?问所以为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告人,以所智告之,故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墨子·耕柱》)
墨子指出,在叶公子高向孔子问政一事中,孔子实际上犯了转换论题的错误。叶公子高问的是怎样才能做到善政(“所以为之若之何”),孔子的回答则属于什么是善政(“善为政者”)。显然,这里孔子答非所问,违反了同一律的要求。另外,墨子对“攻”和“诛”“告”和“毁”等概念的分辨都说明了墨子本人对同一律的要求已有基本的了解。后期墨家可能正是在他的基础上才概括出“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这一思维规律的。
(二)矛盾律
后期墨家关于矛盾律的论述主要表现在对“辩”的定义上:
辩,争彼也。辩胜,当也。(《墨子·经上》)
辩: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不当,若犬。(《墨子·经说上》)
“彼”指一对矛盾命题,“辩”是围绕一对矛盾命题而展开的论争。对于同一个对象,同时下两个刚好相反的判断,如有人说这是牛,有人说这不是牛,就构成了辩论。后期墨家认为,一对矛盾命题不能同真,必有一假:“不俱当,必或不当”。也就是说,只要是关于同一对象的辩论,就总能区分出真假来。这是对矛盾律的精确表达。矛盾律的定义就是任何思想不能既真实又虚假。
矛盾律和同一律一样,要求思想有确定性。违反矛盾律,就会陷入自相矛盾的错误。而指出对方的自相矛盾之处,正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反驳批评的辩论方法。《墨子》一书中,这种方法用得很多,如:
世之君子,欲其义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则愠。是犹欲其墙之成,而人助之筑则愠也。岂不悖哉?(《墨子·贵义》)
世之君子,使之为一犬一彘之宰,不能则辞之。使为一国之相,不能而为之,岂不悖哉?(《墨子·贵义》)
世俗之君子,贫而谓之富则怒,无义而谓之有义则喜,岂不悖哉?(《墨子·耕柱》)
在利用矛盾律批评其他各派时,后期墨家还提到了一种特别的逻辑矛盾,即悖论。悖论的性质是:由它是真的,就可推出它是假的;由它是假的,就可推出它是真的。如果能从对方的论题里推出悖论来,那么对方的主张也就不攻自破了。
(三)排中律
排中律和矛盾律紧密相联。矛盾律是说一对矛盾的命题不能同真,必有一假;排中律则要求一对矛盾的命题不能同假,必有一真。两者各自强调了矛盾命题的一个方面。
后期墨家在定义什么是辩时,实际上在提出矛盾律的同时也提出了排中律:
攸,不可两不可也。(《墨子·经上》)
彼;凡,牛。枢,非牛。两也,无以非也。(《墨子·经说下》)
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不辩。(《墨子·经下》)
谓:所谓非同也,则异也。同则或谓之狗,其或谓之犬也。异则或谓之牛,其或谓之马也。俱无胜。是不辩也。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墨子·经说下》)
辩是“争彼”。“彼”的意思是既不能“两可”,也不能“两不可”。不能两可,则必有一假,这是矛盾律的要求。不能“两不可”,则必有一真,这就是排中律的要求。《经下》和《经说下》有一个更详细的解释,那就是“谓辩无胜,必不当”,“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辩是一对矛盾命题之争,按照排中律的要求,一对矛盾命题不可能同假,总有一个当者。那个当者就是辩论中胜利的一方[5]。
总之,墨家逻辑学派在中国学术史上第一次把思辨的内容和形式作了明确区分,并从思维的形式和规律上来保证论辩的正确进行。它既反对儒家的“举相似”的主观比附,又反对庄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不可知论,在认识真理、批驳谬误的人类探索主客观事物规律的过程中找出了一条科学的道路。
墨辩逻辑学尽管还有某些不足,墨子及其弟子在论辩实践中也偶有违反逻辑之处,但从中国学术史上看,墨家第一次明确地突破了儒家“正名论”的非逻辑思维,明确地将逻辑与政治分开,使逻辑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科学门类。这正是墨辩逻辑学的历史功绩,也是墨家对中国学术史最具价值的独特贡献。
[1] 吴毓江.墨子校注[M].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
[2] 陈孟麟.墨辩逻辑学(修订本)[M].济南:齐鲁书社,1983.
[3] 高亨.墨经校诠[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4] 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5] 钱爽.也谈《墨经》之“侔”——墨“侔”三款之我见兼商榷[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6(5):27-41.(责任编辑:李朝平)
On the Logic Theory in Mojing
CUI Xueru
(Faculty of Humanitie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Sichuan 611130, China)
Mo-tse established the complete logic system for the first time in Chinese thought. It is called“Mohist logic” because its logic system revolves around the debate. The logic thought of Mo-tse are mainly presented in Mojing. It was in this book he first put forward the logical concepts such as debate, category and causality etc. It then required learning debate as a specialized knowledge, which was the innovation in the Chinese logic history. Mojing described the nature and the role of debate mainly in six aspects: to distinguish right from wrong, to know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to observe both the form and the content, to balanc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o exclude the uncertainties and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s. The debate is the process of forming the concept, judging, and reasoning. It is namely three progressive steps “to define the truth with reference”, “to express the meaning with words” and “to reason the cause in the argumentation”. In Mojing, all the three basic rules were formed for the later Mohists formal logic: the law of identity, the law of contradiction and law of exclude the middle.
the law of contradiction; the law of identity; the law of exclude the middle
B81
A
1009-8135(2017)04-0115-09
2017-04-16
崔雪茹(1980—),女,河北石家庄人,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哲学、伦理学。
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当代大学生幸福观教育研究”(13YJC71000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