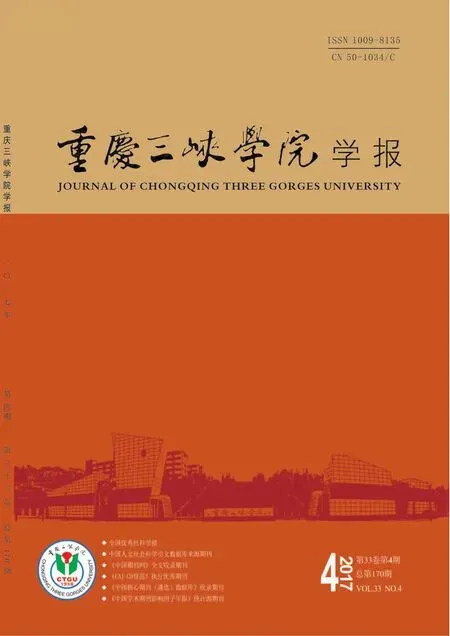中国天主教界对“一战”的思考
——以《圣教杂志》为视角
2017-03-29张士伟
张士伟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史研究中心,甘肃陇南 742500)
中国天主教界对“一战”的思考
——以《圣教杂志》为视角
张士伟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史研究中心,甘肃陇南 742500)
“一战”爆发后,《圣教杂志》站在天主教立场上,对战争进行了大量报道和深度分析。为唤起天主教教友的爱国心,该刊相继发表了多篇文章,引导教友对国家的含义、爱国必要性、战争、革命、教友是否参战等重大问题进行全方位思考,鼓励教友将来为保家卫国而战,澄清了时人对天主教的种种误解,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天主教;《圣教杂志》
《圣教杂志》是由神父李问渔于1879年在上海创办的全国性的天主教机关报。《圣教杂志》的作者群和读者群不但有中国各地的教友,还包括东南亚及欧美的教徒,具有人数多和国别多的特点,可以代表中国天主教届的主流思想。该杂志出版发行长达60年,期间发生了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等重要战争。尤其在1914年,为重新瓜分殖民地、势力范围和争夺世界霸权,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中国对德国宣战,也卷入战争漩涡,深刻地影响到我国的历史进程,也使社会各界返躬内省,忧虑国家的前途。那么“一战”爆发后,作为天主教的喉舌《圣教杂志》有何反应和认识?时至今日,中国学者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等多角度对“一战”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有关论文、论著数量汗牛充栋,但是还很少有考察“一战”与中国天主教的关系方面的论文或著作。本文以《圣教杂志》为视角,观察中国天主教界对于“一战”的反应。
一、《圣教杂志》高度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一战”爆发后,引起《圣教杂志》的强烈关注,刊发了棫才的文章《欧陆风云记》:“霹雳一声,杀机突起。巴尔干大战以后,甫越一年,而欧罗巴全洲又肇此惊天动地、血肉横飞之大惨剧。事起于奥储被刺,而祸乃延及全欧。大陆各国,若奥若塞若法若德若俄若英若比利时等等,悉卷入此风云惨淡之中,可骇可愕,莫此为甚。”[1]395该文详细介绍了奥皇之身世、奥储之历史、被刺之详情、死后之哀痛、奥塞之开战、各交战国之现状、日本之态度及中国之中立,并分析了德俄法、德英比间的启衅原因,尤其欧洲列强间的军备竞赛是战争发生的重要原因:“泰西各国,于近十年来,各竭其心思财力扩张军备,此国增一战舰,彼国必增二舰,以超过之;彼国增一军团,此国必增二团以抵制之。军费则有加无已,新军器、新爆炸品及航空之飞行机,则日新月异,力求制胜他人。名为和平,其实乃如健饭之壮夫,日饫甘肥,饱且欲死,苦不得一泄其内部之膨胀。若英若俄若法若德,均有此种现象,时机既至,触之即发。”[1]404-405
《圣教杂志》对一战的报道自始至终,内容非常丰富。先后发表了《欧战杂录》《欧战余声》《欧战逸韵》《欧战余声》《欧战鳞爪》《日德兰大海战纪实》《战事家庭谈趣》《欧洲议和草约大纲》《协约国答复德国答案文要略》《和会对奥媾和条件大要》等众多文章。其中有些文章直接翻译转载自法国报刊,如《自由报》《旅人报》等。在各期还开辟了“外国之部”一栏,跟踪报道“一战”的进程。该刊侧重刊登有关中国的文章,比如《中华民国中立条规》《日德青岛之战》《中日交涉始末》等,并力图向中国介绍最新的战略战术,比如刊登渔人的文章《西欧战壕记略》[2],详细介绍了欧战中战壕的建筑方法,包括如何选址、如何按照尺寸标准施工,以及战壕内的生活情况等,以期中国军方能掌握要领,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
从《圣教杂志》刊发的文章内容看,大都是站在天主教的立场上述评“一战”,如对热心公教的奥匈皇储被刺深表同情:“是太子之死,直关系欧亚二洲之安危,不仅公教中失一柱石也,记者对于此事,为奥国痛,为大局悲,且为公教惜。”[3]482但总体上,《圣教杂志》对“一战”的报道是比较客观和公允的,“欧洲大战,已数月于兹矣。其间胜负之数,言人人殊。各西报及路透社、东方通讯社等,所传之消息,须经各国检查而后发。军事秘密,未必尽得其真相。本报因是迟疑不敢遽载”[3]501-504。很多文章被国内其他报刊转载。应该指出的是,《圣教杂志》上有些文章的作者高瞻远瞩,能准确预测事件的影响。如沈钦造在《世界和平之根本解决》中指出:“凡徒恃巴黎和会及条约之一纸明文,以冀世界之永久和平者,是妄人也。”[4]由于条约的不公允或不完善,“不惟不足以为和平之保障,反能为引起战祸之籍口物耳。故欲以今人所定之条约,期后世之人永远遵守,不亦难乎?”果然不出其所料,1939年便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圣教杂志》对“一战”的思考与认识
“一战”中,欧洲民众的爱国心非常强烈,“欧洲各国,其平日非不有政党也,非不有反对政府之人也,而战事一起,则皆上下一心,以国事为急”[3]505。“战耗传来,交战国人民之侨寓东亚营商业、任教育,及受吾政府之雇佣者,皆弃其职业,带其妻子,联袂归国,以效命于疆场。”[5]2德国三分之一的壮丁拿起武器,走向战场。法国人口只有德国的十分之六,参战人数竟然也达到二百四五十万。“昔人云:师克在和。若欧洲各国之人民,可谓和之至矣。还顾我中国则何如噫!”[3]505与欧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民众的爱国心极其缺失,“今日吾国国民性之消失,实有一落千丈之势”[5]3。上层社会在争权夺利,甚至“托身租界,籍外人之庇护”。中下层社会羡慕欧人,“咸思依附其末光,以沾其余沥”。国民不爱国,列强对华分而治之,“欧洲各国利用吾国民之离心力,广布其语言,销行其商品,以施其同化之政策”[5]3。更可悲的是,“二十世纪之国家,苟不建筑于国民爱国心之基础上者,即幸不灭亡,亦奴隶国而已”[5]2。“一战”对国人的影响是“一为刺激吾国民之爱国心;二为唤起吾民族之自觉心”[5]4。为唤起我国民众,特别是教友的爱国心,《圣教杂志》相继发表了《战争与爱国》《天主教与爱国运动》《天主教与国家政权》《战争我人应有之思想》《天主教与战争》《公教对于战争之观念》等系列文章,引导民众对战争进行全方位思考。
(一)对“国家”的含义及爱国的必要性的思考
在当时国人的头脑中,“国家”的概念是模糊的,甚至分不清“国家”与“政府”的区别。《圣教杂志》认为:“国家之观念由家庭与家乡之观念,扩大而成;盖集家而成一乡一县一国;故国者家之扩张体也。国之组成,国与国人之关系,犹家之组成,家与家人之关系也,其关系虽有大小疏远之不同,然其理则一也。”[6]646国家与我们的关系密不可分,“国与我之休戚相关,无异家之与我;我之当爱国,无异之当爱家……故我亦当以相同之爱,爱我国之人民,土地,主权,犹爱我家之人,我家之物,我家之事也……只要爱,合乎理,顺乎性,不侵犯公义,不违背公理,则无往而非是也”。所以爱家必然爱国,“故爱国心即是爱家心之扩大者;人有不爱其家者,即无有不爱其国者。故曰爱家,即爱国:爱家族,即是爱国族、爱民族”[7]79。“爱国心之所由起,实为爱家心,爱乡心。聚人而成家,积家而成国,国家是家庭的集合,是家庭之总汇,爱国家就是爱家庭,就是爱自己,所以个人的兴亡,有关家庭,家庭的盛衰,有关国家。”[7]78“我家之历史,我家之家道,我家之家风,我家之悲欢事,与我皆一体相关也,因此一体相关之故,故我爱家之心根于我心而自然兴起也,爱国之心亦然,亦由国民与国家在种种之关系上而发生。”[6]646
什么是爱国主义?“在我们心目中,谁都有一种比个人利益,比血统关系、比党派发展更深切的心情,这便是所谓公众利益,为公众利益而有牺牲一己之必要,由此必要而成了志愿。这公众利益,就是罗马所称为公共事务,这种心情,便是爱国主义。”[8]214“家庭、阶级、政党和个人形体上的生命,比较起价值来,都在爱国主义的理想之下,因为这个理想,便是公理,而公理是绝对无上的,进一步说,这个理想,是应用于国家的公理,为大众所公认的,就是国家的荣誉。”[8]216
那么,天主教教徒有爱国的责任吗?《圣教杂志》认为:“国民对于国家有爱国的天职,天主教徒也是国民的份子,为什么可以不爱国呢?”所以,“国家是天主赋给我们的国家,是要我们爱慕它,拥护它,服从它”[8]216。人都当服从有权的长官,国民爱国是国家统一和有秩序的基本要素。“基利斯督的宗教,把爱国著为律令,没有一个纯精的基多信友,不是纯精的爱国志士。”[8]214国家是一个精神的团体,大家都该为一个社会组织服务,“不恤牺牲一切,在主持分派各人任务的领袖指导下,尽保障卫护的职责,便是舍身流血,也不得推诿”[8]214。
(二)对战争与教友是否参战的思考
当时国人认为天主教反对战争,根据是天主教十诫的第六戒“勿杀人”。更有人引山中圣训作为依据:“人若击汝左颊,更与以右颊。人若褫汝上衣,下衣亦勿拒。”他们认为:如果我国被外邦侵略,教徒必不肯执殳前驱,为国家效力。很多教友对战争也心存困惑,所以《圣教杂志》认为非常有必要向社会说明天主教的战争观。
1.慎战的思想
《圣教杂志》认为战争为天大的祸患,因为它“寡人妻,孤人子,伤人父母,扰乱社会之和平和国家之秩序,为公义公理之戕贼,战争所以当用尽种种方法以避免之也”[6]642。“一战”中,教皇多次发布弭战之谕,指出:“各国皆行酷虐凶暴,自相残杀,以为英雄见长,蹂躏及杀戮,毫无限制。战地上日见鲜血横流,日见负创垂毙之人,日见尸骸满目,环视此等交战人民,如是好勇斗狠,将疑谓果否为一祖所传耶?果否为同具人性耶?果否尚有人道主义存者也?”[2]98教皇痛惜“岂文明世界,皆宜悉变为白骨粼粼之战场乎”?呼吁“曷不速筹弭祸之法,使人民得庆生全,各国早以玉帛相见,何乐如之”[2]98?劝告交战国“两相退让、预筹公正及永久和平之条款”[9]。当然,天主教并不完全逃避战争,认为“然有时所用之方法至于极点,至战争不可避免,则战争已为紧要,而不能不战矣”[6]642。
2.“紧要”战争观
《圣教杂志》认为“紧要”就是国家的危亡到了“最后关头”,国民必须参战。具体指三个因素:“①一国之独立主权被蹂躏时;②一国国土之完整被侵略时;③一国当有之尊敬及光荣被侮辱时。在此任何一情境中,苟一切和平之方法,用之均不得其效,则为自卫计,战争已成为紧要。”[6]642圣多玛斯是圣教历史上最伟大圣师之一,他说:“使战争正当,只要有三种条件:①必须由国家领袖的权力才能宣战;②必须有正当的理由;③宣战的宗旨应该正当。”[10]63
3.教友是否参战
当自己的国家面临战争,如果参战是不是违反了天主的诫命?天主教教友有参战的义务吗?《圣教杂志》认为:“天主教诫命禁止杀人,也并非是说战争一定违法的,更不是说杀人者必当依法处以枭首极刑,或是一种恶意的屠杀,却是说:‘人不得无故杀人’。”[10]62故“战争一旦成为‘紧要’,则参加战斗,保卫家园成为最光荣之事”[6]642。从圣经来看,“圣奥斯定说‘如果圣教法律是绝对禁止战争的,那么,为兵士们救灵的劝告,应当在圣经里晓谕他们知道,教他们抛弃兵械,并和军队完全脱离关系了,但圣经训诫却给他们说‘你们应当厌足你们的饷酬’,所以圣经并没有禁止那些厌足饷酬的兵士们为他们号令的人战争,所以由国家领袖宣布为保卫国家和公共利益的战争,只要他的用意正当,就不是罪恶”[10]63。“圣奥斯定说‘教友宣战不为贪欲,不为残杀,而只为求得和平,铲除恶孽,推进公益的,这种战争都为正当。”[10]63从中可以看出,天主教赞成公正的战争,用武力抵抗外敌,以保卫国家,是理所当然的,毫不迟疑劝告士兵们应当个个成为战争的英雄。试看“一战”期间欧洲各国,凡是天主教教友,一旦听到征兵命令,无不踊跃参军,执干戈以卫国家,可见天主教非绝对反对战争。
1916年,《圣教杂志》刊登了“一战”中数位天主教将领的传略,详细介绍其生平,颂扬他们为保卫国家英勇作战的事迹,其目的是“谨揭一二公教将军之品格伟业,译登报端,以启发我中国公教人民之知识,使皆知军人资格之对于天主、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对于己身,引为准绳模范,而取为则效”[11]。《圣教杂志》以此鼓励中国的天主教教友团结起来,一旦我国遭到敌国入侵,大家就要忘掉自己的利益,牺牲生命,为国捐躯。
4.战争的益处
战争固为天大的祸患,但是战争还有些益处。“战争亦为天主所许。一国之中,人民更觉彼此之团结力,与亲爱之德。战争能为复兴民族,复兴民德之至善机会。”[6]641“然天主亦能以之转祸为福也,其福可见在道德方面,社会方面和宗教方面。”[6]644用战争的方式,还可以获得和平。“交战之国,能用种种合理的有效方法,制服敌人,使公义得以恢复,和平得以复还也。吾谓合理的有效方法,因为战争所用之方法,亦当依性律之所许可,及战时国际公法之所规定,非任何非法之战具,违禁之动作可任意使用也。”[6]643
(三)对革命的思考
革命与战争是双胞胎,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一战”引发了德国“十一月革命”及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圣教杂志》如何看待暴力革命呢?很多人认为天主教是反革命的,其实并不尽然。
首先,世俗政权直接授自天主,还是授自人民呢?自中世纪后,有些国家的君王常借口直接授权于天主,即君权神授,而罗马教宗始终未曾予以承认。《圣教杂志》认为:“历代天主教圣师与超性学士皆众口一词,肯定政权直接授自人民。”[12]207所以掌握政权者,必须对人民负责,人民也应该拥护本国政府,但并不意味着人民要无条件服从政权,“然若政权越出其界限,号令相反天主,危害社会公益之事,则政权已失其效用,执政者已非为天主之代表,而属下即有反抗之权利”[12]212-213。人民对于政府的反抗有三种,即被动反抗、自卫反抗和冲犯反抗。天主教认为前两种方式是正当的反抗,第一种“所谓被动反抗者,即不履行不道德不公正之法律,或往法庭请愿,或迁往他处,以避苛政之谓也。此为正当,亦性律所允许也”。也就是非暴力不抵抗方式;第二种“所谓自卫反抗者,即用武力对待政权之强迫履行不正当、不道德之法律。此亦属正当。此种反抗,非抗其政权,乃抗其武力也”。第三种“冲犯自卫,即滋事扰乱,用武力以干涉当轴,要求修改法律,或赔偿损失者也”。对于冲犯自卫反抗方式,欲得天主教认为正当,不得不遵守以下三种条件:“①采用武力,为恢复社会秩序;②采用武力有成功之希望;③当有正当之目的,即保全社会之公共目的。”[12]114
俄国的“二月革命”即是一次人民对暴政的“冲犯自卫”。《圣教杂志》如何看待俄国革命呢?“二月革命”爆发后,该刊在1918年第一、二、三期发表了《俄罗斯革命之因果》连载系列文章,从帝后之为人、史拉夫族人之革命思想、革命时之情形、欧战与革命之关系、俄罗斯革命之因果、革命时前衙署派之措施等方面,详细叙述了革命的原委,认为俄国人民的革命是反抗暴政的正义行动,“俄国史拉夫族人民苦于俄廷苛政久矣。观于近数十年以来,俄国之政治历史,则知俄民希望政治改良、制定宪法、革除专制积弊,酝酿已非一日矣。倘俄廷能体恤民艰,俯顺舆情,剔除苛政,锐意图新,改弦易辙,与民更始,毅然改行君主立宪政体,而庶政公诸国民,则革命之浪何自而来哉?特惜廷臣冥顽不灵,酷嗜专制,视国民如草芥,而蔑视民意,强施压制,加以政治腐败反日增月盛,遂使民心怨恨而涣散,不得已铤而走险,蓄谋革命耳”[13]。事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祸之作,非作于作之日。俗话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作者认为二月革命的内因是沙皇的残暴统治,外因是“大战开幕,专制政体之弊害愈显,乃促使革命风暴勃然兴起矣”[14]。所以“前俄皇室及专制政府之推翻,乃皇室与政府自招之也”[13]。从中可以看出,《圣教杂志》并非是反对人民革命的。
《圣教杂志》引导天主教教友对国家含义、爱国必要性、战争、革命、教友是否参战等问题进行全方位思考,鼓励教友为国而战,澄清了时人对天主教的种种误解。《圣教杂志》总结“一战”教训时说道:“由此可知,立国于世界上,非武装不能言和平。吾中国可以兴矣。”[1]404-405警示中国要屹立于世界之林,必须大力发展国防,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按照《圣教杂志》关于战争性质的标准,中国抗日战争就是中华民族在存亡关头,为保家救国而进行的一场正义的反侵略战争。抗战期间,该刊以笔为剑,痛斥日军暴行,鼓励教友拿起武器,狠狠打击侵略者。在该刊爱国宣传的感召下,天主教教友纷纷参军参战,积极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为保家卫国做出了贡献。日寇对该刊恨之入骨,1938年该刊被日寇强行关闭。
[1] 棫才.欧陆风云记[J].圣教杂志,1914(9):395-405.
[2] 渔人.西欧战壕记略[J].圣教杂志,1915(3):117.
[3] 棫才.论奥太子被刺原因及其遗事[J].圣教杂志,1914(11):482-505.
[4] 沈钦造.世界和平之根本解决[J].圣教杂志,1919(9:396.
[5] 伧父.大战争与中国[J].东方杂志,1914(3):2-3.
[6] 徐宗泽.战争与爱国[J].圣教杂志,1937(11):646-642.
[7] 消迷.天主教与爱国运动[J].圣教杂志,1937(2):78-79.
[8] 在天主教道理下之评判“满洲国”[J].圣教杂志,1934(4):214-216.
[9] 教皇本笃十五于欧战第四年之初劝告交战国元首筹备释怨媾和之谕[J].圣教杂志,1917(12):529.
[10] 天主教与战争[J].圣教杂志,1938(2):62-63.
[11] 渔人.少你斯将军传略[J].圣教杂志,1916(2):58.
[12] 赵石经.天主教与国家政权[J].圣教杂志,1935(4):114-213.
[13] 棫才,东蒙.俄罗斯革命之因果[J].圣教杂志,1918(1):2.
[14] 棫才,东蒙.俄罗斯革命之因果续[J].圣教杂志,1918(2):49.(责任编辑:郑宗荣)
About the 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y’s Thinking on World War I: Based on the Survey of Catholic Miscellany
ZHANG Shiwei
(Research Institute of Culture & History,Longnan Teachers College,Longnan,Gansu 742500, China )
After the broke out of WWI, Catholic Miscellany published significant and in-depth analyses standing on the Catholic position. To arouse patriotism of the Catholic, it then published a series of articles, guiding the parishioners to think about important issues such as the meaning of the Country, the patriotic necessity, war, revolution, whether going to war and so on, and encouraging catholic fight for country in the future. It clarified the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Catholic and waked up those confused people.
World War I; Catholic; Catholic Miscellany
K207
A
1009-8135(2017)04-0110-05
2017-04-25
张士伟(1967—),男,河北威县人,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圣教杂志》研究”(2014LSSK0200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