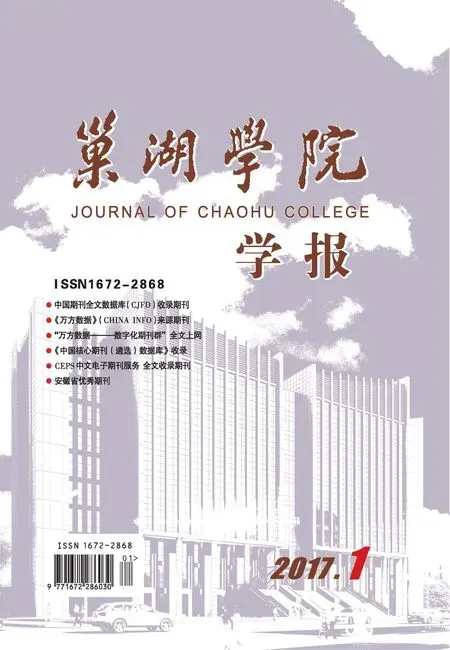史思明父子杀“胡”与政权失败
2017-03-29陶继双
陶继双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5)
史思明父子杀“胡”与政权失败
陶继双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5)
史思明杀害安庆绪时,连带屠杀与安庆绪同种族的胡人,史朝义弑父后,同样有杀害胡人的经历,这归根于史思明与安禄山不同种族之故。安禄山是落居东北的西域胡人,故能曲意迁就和拉拢当地各民族,反唐声势最为浩大。史氏父子则不同,更强调其突厥及土著的身份,导致种族联合的破裂,进而促使史朝义彻底覆灭。此巩固的种族团结的破坏,除一定程度上由政治形势变化所迫,史氏父子失策当属主要原因。
安史之乱;安禄山;史思明;史朝义;种族
安史之乱的失败,表面上是史朝义杀史思明引起的内讧所致,但深层次的却是内部种族之间的矛盾。史氏父子杀胡是为清除与安庆绪同种的嫡系,突出自己的突厥种以获得支持。然而史思明离不开胡人的经济支持,对胡政策又表现得有些犹豫,但史朝义因储位争夺,在杀害胡人方面则走向极端,以胡人和突厥为主干的多民族混同难以维持,整体实力大为削弱,因唐军施压和内部反叛的双重打击,安史之乱最终走向覆灭。但它的余烬,则生成最终葬送唐朝的藩镇。
1 安、史种族辨析
史书把史氏父子杀胡作为异种屠杀而突出记载,换言之,如果史氏父子与安禄山同种,也属胡人,则不会杀胡。然而安、史是否同种一直存有争议。学界对安禄山族属的讨论发起较早,当从1925年日本学者桑原骘藏首倡安禄山为康国粟特人起[1],到2005年钟焓在肯定安禄山为粟特人的前提下更倾向于安禄山已经有较为显著的内亚化特征止[2],期间八十年,论著不胜枚举。虽然在安禄山的族属问题上研究者的意见越来越趋同,但对史思明的族属争论仍然激烈。本文就对此问题研究较有影响的两篇文章,即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和宗教信仰》[3]和上举钟焓文,附之以早前较有影响的成果,谈谈笔者的看法。
荣、钟二文在谈及安禄山时,荣氏强调粟特文化在其身上留下的烙印,而钟焓则认为突厥化对安禄山的影响更为深刻;在对史思明的种族阐释上,荣氏则确言史思明是粟特人,而钟焓则捍卫旧说,力主史思明是突厥人。荣氏根据安禄山与史思明同乡出生的记载认为,“所谓‘同乡’,实即同出于一个部落的意思。”“史思明从出生到成长都和安禄山有共同之处,‘解六蕃语,同为牙郎’说明他也是个地道的粟特人”[3]。粟特人以经商为长,他们在徙居过程中往往聚集于一处,与他族相隔,因而确实存在“乡”等同部落的现象,但这能否适用于长期胡化与种族杂居的营州地区,恐难以定论。史载安禄山父为粟特胡种,母为突厥种;史思明与其相反,父为突厥种,母为粟特胡种,安、史二人俱是杂种胡。除史思明的父亲入赘妻族外,安姓的“乡”肯定是种族杂居的地带,不会是纯胡人聚集的地区。史载安禄山继父安延偃在“族落破”后离开突厥,他的转移只带寥寥几个家庭成员[4],可见这样的“族”更多与家族同义,难与“种族”甚而“乡”等同。如果安、史属同部落,史思明也难免转移,但史料中未见有史思明转移的记载,或许正好反映史思明有突厥身份的保护。如此似也可说明安氏部落只是众多部落杂处的“乡”中一小部而已。另外,此地的杂种胡甚多,本身即已反映粟特种族隔居的模式在不断地弱化,种族错居杂居越发普遍,因此,“杂种胡”的“杂”才能体现出它的应有之义。故而把“乡”等同部落,并进而得出他们就是同一个种族,在营州地域恐不具有普遍性。至于史思明“解六蕃语”,能否作为其属粟特人的重要佐证,恐也需依人而论。史思明生于此粟特人较多的杂居地,母亲又是粟特人,很容易为粟特人接受和容纳,从他和安禄山交好即可为证。对于聪慧的史思明,在此环境熏习之下,掌握这种语言技能实属可能。陈寅恪论此说:“观于史思明与安禄山俱以通六蕃语为互市郎,正是具有中亚胡种血统之特征。至其以史为姓者,盖从父系突厥姓阿史德或阿史那之省称,不必为母系昭武九姓之史也。”[5]甚为审当。然魏义天说史思明刻有“昭武皇帝”字样的谥册已被发现[6],这对史思明的粟特身份似乎更具说服力,后文将涉及之。
安禄山因其母改嫁之后,跟随安延偃辗转到岚州,就此脱离突厥环境而生活在纯粟特人家族中,其后与粟特人关系最密当与此有关。《安禄山事迹》载安禄山“长而奸贼残忍,多智计,善揣人情”,这一心态与其为人继子恐不无关系,从另一面则反映出他对粟特文化的体察与接受。但一直生活在营州的史思明却未见其与粟特胡人亲密接触的材料,相反却有他后来对胡人杀害的记载,而后又被其子错误地承继。另外,钟焓根据史思明“姿瘦,少须发,鸢肩伛背,廞目侧鼻”的长相,比对人种学,认为史思明是更多含有突厥血统成分的杂种人。不过钟焓在论述安禄山时以为,“至于其后来采用的‘禄山’一名则是来华粟特人常取的汉名,安氏以之为名当有增强麾下的昭武九姓粟特人对他的亲近感以更好地联络感情从而取得他们信任及拥护的政治意图。”[2]认为“禄山”之名是安禄山为其政治目的特意更改,这实出无据。安禄山之名,是其十余岁时到岚州后所称名,必乃父母所改。因而安禄山既不可能自己“以之为名”,也不可能预测到数十年后会成为一个反叛首领,而特地在儿时就给自己起此具有政治意图的名字。
我们从“胡”“羯”“羯胡”“柘羯”等称谓上也可发现安、史二人种族的区别。陈寅恪在其论著中认为“羯”“羯胡”“柘羯”等是昭武九姓的专称;黄永年则认为:“‘羯’已和‘胡’一样,成为少数民族至少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7]黄氏无疑是继承和发挥吕思勉的某些观点。吕氏《胡考》一文,赞成王国维“西域遂专胡号”的说法,但对王氏的西域人和匈奴人相貌相似一说则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胡之名,初本指匈奴,后乃貤为北族统称,更后,则凡高鼻多须,行貌与东方人异者,举以是称焉。……惟西域人则始终蒙是称焉。”[8]西域人相貌的独特才是其始终专此称谓的原因。巧合的是陈寅恪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在复陈述的信中说道:“赭羯、石羯本为西域民族中一族,实是专名。玄奘作《西域记》是,其义为战士(《新唐书·西域传》即用《西域记》文),盖先由专名而变为公名者。”[9]陈氏是否吸收了王、吕二氏的成果而有此一说不得而知,他缘何未将此说融入其论著中亦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对于黄氏指责的问题,陈氏早有思考。虽然二氏在专名和泛称之间有某些切合点,但二者分歧仍巨。对于陈氏来说,“羯”本是西域某一民族的称谓,由于其战士勇武而逐渐成为西域战士的泛称,正好符合其“羯胡”善战为安禄山所利用的思路。黄氏则不同,把“羯”的泛称扩大到整个北方少数民族。黄氏可补之处在于,以“羯”或“胡”来指称北方少数民族的乃汉人或中原人之专用,北方少数民族则绝不会以“羯”或“胡”自称,在涉及种族之争时,尤会说清楚。如:
(安)禄山谓(哥舒)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类本同,安得不亲爱?”翰曰:“谚言‘狐向窟嗥不祥’,以忘本也。兄既见爱,敢不尽心。”禄山以翰讥其胡,怒骂曰:“突厥敢尔! ”[10]
史思明“因骂曹将军:‘此胡杀我,我负汝何事,而行此悖逆乎!’”[4]
史思明屠戮胡人后,姚汝能感叹道:“自是禄山之种类歼矣”[4]。于兹三处可知,安禄山自称为胡人,史思明自认为突厥人,清清楚楚,不容混淆。可见突厥与粟特胡种族界限是分明的。由此推之,北方其他少数民族对自己族类的认识也当如此分明。故陈寅恪目“羯”“羯胡”“柘羯”为昭武九姓专称,同时将东北地区视为一个胡化地区,后又在其中区分出“杂种胡”的思路,是比较谨慎的。笔者则进一步以为,“羯胡”或“杂种胡”是被泛称的胡中之“胡”,与被泛称为胡的其他少数民族是有区别的。
2 史氏父子杀胡考辨
史思明杀安庆绪时,对其部下“数内三千三百人是随从庆绪者,亦杀之,食后方移入城。自是禄山之种类歼矣。”[4]目的是削弱安氏残余的忠实力量。无独有偶,史朝义在弑父后,派人回范阳密杀对自己帝位最有威胁的弟弟史朝清,范阳城因此几度陷入互相杀阀的混乱,所谓“城中相攻杀凡四五,死者数千,战斗皆在坊市闾巷间。”最后一场激烈的火拼发生在以阿史那承庆和高鞫仁为首的两派之间。“承庆入东军,与伪尚书康孝忠招集蕃、羯。”主要以突厥和昭武九姓胡为主;而“鞫仁兵皆城傍少年,骁勇劲捷,驰射如飞;承庆兵虽多,不敌,大败,杀伤甚众,积尸成丘。”[11]此“城傍少年”,“应由奚、契丹、高丽、靺鞨、室韦等部落组成”[12]。可见这次内讧已由一般性权利之争进而演变成不同种族间的仇杀。正因此,“鞫仁令城中杀胡者重赏,於是羯、胡尽殪,小儿掷於空中,以戈承之,高鼻类胡而滥死者甚众。”[4]军队种族的冲突,致使发生屠杀“胡”属少数民族无辜平民的惨剧:
阿史那从经略军领诸蕃部落及汉兵三万人至宴设楼前与如震会战。如震不利,乃使轻兵二千人于子城东出,直至经略军南街腹背而击之,并招汉军万余人。阿史那军败走于武清县界野营,后朝义使招之,尽归东都,应是胡面,不择少长尽诛之。于是朝义伪授李怀仙幽州节度。[11]
黄永年认为此杀胡之事纯属子虚乌有,是“从《晋书》卷一○七《石季龙载记》里套来的”,属于《史通》所说的“貌同心异”论,并引《蓟门纪乱》“两敌相向,不入人家剽劫一物,盖家家自有军人之故,又百姓至于妇人小童,皆闲习弓矢,以此无虞”为证[7]。黄氏之论难以释疑以下二点:一,《蓟门纪乱》《河洛春秋》《安禄山事迹》都是唐人作品,俱提及此事,不排除作者有相互因袭的可能。但从《通鉴》引《蓟门纪乱》《河洛春秋》的文章来看,二书不乏抵牾之处,应该属于两个系统。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则在谋篇布局和行文之间都比较缜密,可能反映此书为后起之作,借鉴了前两部作品,或因此书的价值好过前两部,促使了前者的湮灭。退一步说,如果三书确实承袭一个版本,三位作者会否同时不假思索一味因袭?姚汝能在谈到安禄山和安庆绪的墓志说:“其墓志叙述凶逆,语非典实,所记亦无可取,故略也。”[4]可见姚本人在写作时是经过审慎考察的。黄氏本人也说姚书 “实是研究安史之乱的第一手文献”[13],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因而可以否定上面完全因袭的揣测。二,黄氏所引《蓟门纪乱》的材料,反映的是城内以前争斗时对居民的态度,彼时火拼集中在上层,与下层百姓干系不大。但此次则属于民族间的冲突,连及杀戮对立民族无辜百姓则不致毫无根据。又,《蓟门纪乱》时而言屠戮百姓,时而又言与民无涉,这两条矛盾的记录同时出现在此篇短文中,作者再无条理恐亦不会疏忽至此。还有,荣新江在《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一文中,对安史乱后河北三镇的粟特人进行了爬梳,但奇怪的是,从幽州、卢龙二镇找不出可靠的粟特人存迹的证据,而在魏博、成德这两个相对南边的地方却有很多粟特人在乱后生活的迹象[14]。按常理揆之,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因为之前幽州、卢龙是粟特人聚集较多的地带,较魏博、成德为多,突然之间痕迹鲜存,实属可疑。笔者认为,原因主要在于范阳城中对胡人的屠杀和之后史朝义对阿史那承庆部队中残余胡人的清理所致。大体情况可能如此,随着安史势力南向不断扩张,营州等原范阳东北地带的胡人不断随之南下,以范阳为中心聚集在幽州治下,经过史氏父子几次屠杀,此地已不宜胡人继续定居,遂南下之魏博、成德二镇或靠近成德的幽州管辖地带定居。故而,《蓟门纪乱》关于杀胡记载大体是可信的。
另外,我们通过对安史军队主力构成的考察,也能看出史思明父子杀胡的可能性。关于此问题,讨论者也较多。大体有两种观点,一是胡人为主力说;二是东北当地少数民族为主力说。从安庆绪失败,身边只有“六千”多胡人可见,相比近20万大军,胡人在人数上绝非主力,即使由于战争消耗亦不当少至如此,所以主力当是东北本地少数民族人民。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忽视胡人的地位:
(安禄山)潜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宝,计百数万。每商胡至,则禄山胡服重床,烧香列珍宝,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罗拜于下,邀福于天,禄山盛陈牲牢,诸巫击鼓歌舞,至暮而散,遂令诸胡于诸道潜市罗帛,及造绯紫袍、金银鱼袋、腰带等百万计,将为叛逆之资,已八九年矣[4]。
胡人不仅为安禄山提供经济支持,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也不可低估,两《唐书》很多时候都用“羯胡”指代安史部队,正见其作用之大。由此我们不难推想,胡人人数虽少,但由于其与安禄山同种,有着共同的信仰,并为安禄山提供经济支持,其自身又善战,无疑是安禄山的心腹嫡系。吕思勉说,“文明人入野蛮部落中,往往为所尊奉。”[8]粟特胡人素质较高也是他们被安禄山倚重的重要因素。正因为粟特人是安禄山的嫡系,人数不多却享有较高地位,对史思明也多有不服,史氏父子之杀害粟特人则不至子虚乌有了。
3 安、史“帝”位统序与其政权失败
所谓帝位统序即安氏父子、安史、史氏父子帝位继承序列的正统性。透过对此问题的考察,可以看到史氏取代安氏的政策措置,及其最终覆灭的原因。
关于安氏父子、史氏父子帝位继承的紊乱,旧史认为是由安禄山、史思明二人性格暴烈,溺爱他子引起长子不满造成。钟焓另辟新说,对史朝义兄弟残杀事件认为是“史氏家庭内部‘以少子为尊’才引起其兄朝义的疾视,从而招来杀身之祸。 ”其俗与后来的蒙古同,以“幼子守产”[1]。“幼子守产”是蒙古习俗,一般来说是以长妻或嫡妻的幼子继承大部分遗产。细读史料,发现钟焓所论或不符合实情。史载史朝清是史思明的次子,按文意当指第二子,史思明中期降唐的时候,史载其“子七人皆除显官”[11],可以断定史朝清并非幼子。《安禄山事迹》记载史思明在回范阳后封妻辛氏为皇后、史朝清为太子。辛氏是否只有史朝清一子难以确定,如果有,肯定比史朝清小,那史朝清作为“幼子守产”将不符合条件,而其被立反是以皇后嫡长子的身份。不过《资治通鉴》却认为史思明回范阳并未册封太子,由于对长子史朝义失望,才暗自欲立史朝清。消息不慎泄露,引起史朝义及其党羽的不满,导致政变[11]。另外,史朝义发动政变时,史思明的宿卫将领曹将军向史朝义倒戈投诚,从另一侧面反映其集团对史朝义嫡长子合法性的认同。
我们也可以安庆绪杀父作为一个例证。安禄山在称帝时也未立太子,此时的长子正作为人质被困在长安,后为唐廷所杀,安禄山因此几得疯病,不排除安禄山有打下长安立长子的想法。作为次子的安庆绪此时登上了长子的位置,杀父也是由于安禄山对其不满而属意他子造成的。如此来说,“幼子守产”在安史集团内并未成为共识。有则著名故事说安禄山在玄宗前没给当时身为储君的肃宗行礼,并说不知储君之意,这似乎符合蒙古不立储而让“幼子守产”的说法。相反,史家把这则故事当作安禄山诡谲的一个典型来描写。换言之,安禄山对储君、太子之意的认识了如指掌。
相对安庆绪及史朝义,史思明承继安庆绪遭受挑战尤巨。史思明在火并安庆绪直至其死,一直努力团结内部不同派别。史载史朝义杀了史思明后,“诸节度使皆禄山旧将,与思明等夷,朝义征召不至。”[15]除史朝义能力不济,此事远因当推至史思明杀安庆绪之际。“思明将士或谋杀思明而附庆绪,盖怀禄山旧恩。事临发,情绪降,众皆恨之。”[4]对安庆绪剩下的“官健六千余人”,史思明令“令安太清等养育之,数内三千三百人是随从庆绪者,亦杀之,食后方移入城。自是禄山之种类歼矣。”史思明只杀其中一半左右,是安氏的嫡系和核心力量。之所以没有杀完,主要还是出于笼络胡人的考虑,胡人经济支持是史思明不可或缺的。故上文所提史思明“昭武皇帝”身份可能即于杀胡后不久树立的,从他身上有粟特血统来说,于情无不可;安庆绪杀安禄山后,赐史思明安姓,改名为安荣国,故于理亦可。这两点优势不仅为其争取统序的合法性所用,也透露出史思明被迫笼络胡人的隐情。为此,史思明杀安庆绪后,并未迅速进攻唐军,而是回范阳老巢休整,前后达七八个月之久。《通鉴》说:“思明欲遂西略,虑根本未固,乃留其子朝义守相州,引兵还范阳。”[11]
还有一事值得推敲,即史思明在杀安庆绪后“复称大燕,以禄山为伪燕”[4],史思明以打着为安禄山报仇的旗号登上帝位,因而他是以安禄山的继承人自居,而非革命者,那为何称安禄山所创燕国为“伪燕”,对其进行彻底否定?恐意指安禄山不是“燕”的正宗代表,潜在的意思即暗示安禄山不是突厥人,或更进一步说,安不是东北土著人。如果这个推论成立,恰可以证明史思明与安禄山相反,他是东北人土著的突厥人,是大“燕”国的真正代表,目的是树立自己土著正统,争取东北的团结和支持。这可以引一例为证,据《新唐书》卷二一二《卢龙镇》记载,唐文、武宗年间,卢龙接连发生内乱,后外籍人陈行泰和张绛相继掌权,吴仲舒说:“行泰、绛皆游客,人心不附。”意指外籍人在此地站立不住。结果如其所料,陈行泰不久被张绛所杀,而张绛旋即又被部下赶走。而作为土著的张仲武接手幽州之后,却有效地控制了幽州直到他死去。这就是说,土著比“游客”更具控制地方的优势。史思明恐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才树立自己的正统地位。他在临死时对史朝义说,“然汝杀我太疾,何不待我收长安?终事不成矣。”[15]虽然是出于对史朝义个人能力不振的估计,但更透露出对史朝义统绪威望不足,无法掌御大局的隐忧。正如史思明所料,史朝义恰是在统绪方面不自信,终由杀其弟史朝清而导致覆亡。
前已论之,范阳城内发生种族屠杀之事,是以突厥、粟特胡为一派与“奚、契丹、高丽、靺鞨、室韦”为一派的屠杀。最终,失败的突厥与粟特胡退至城外,没能出逃的全部死于屠刀之下,城内完全被东北本地势力控制。原来两派互相钳制,现在一派独大,这对他们选择降唐或继续支持史朝义无疑再无掣肘之忧。在妥协之下,城内同意让史朝义派遣的李怀仙作统帅。然李怀仙乃“柳城胡人也,世事契丹”,虽为杂种胡,经过几代,已然本土化了,所以能够统一城内各本土派系,混成一体。在史朝义逃亡之际,李怀仙选择降唐而叛之,导致其彻底失败。若史朝义不屠杀从城内逃逸的胡人,采取其他方式夺回范阳,恢复以前多族共存、相互钳制的状态,其败局恐不至如是。
[1]桑原骘藏.隋唐时代に支那に来往した西域人に就いて[C]//羽田亨.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东京:京都弘文堂,1926:624-626.
[2]钟焓.安禄山等杂胡的内亚文化背景——兼谈粟特人的“内亚化”问题[J].中国史研究,2005,(1):67-84.
[3]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和宗教信仰[C]//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编.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萃·史学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762-769.
[4]姚汝能.安禄山事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41-44、12、41-44.
[5]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上海:三联书店,2001:216.
[6]魏义天.粟特枳羯军在中国[C]//《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语言、考古的新探索,北京:中华书局,2005:235-240.
[7]黄永年.文史探微[M].北京:中华书局,2000:313-314.
[8]吕思勉.读史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177-1179、1191-1194.
[9]将天枢.师门往事杂录[C]//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13.
[10]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571.
[11]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7110-7111、7112、7048、7106-7108.
[12]李锦绣.“城傍”与大唐帝国[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281.
[13]黄永年.唐史史料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135.
[14]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J].暨南史学,2003,(12):102-123.
[15]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6:5382、5381.
THE DISCUSSION ON SHI SIMING AND HIS SON KILLING THE BARBARIAN IN ANCIENT CHINA AND THEIR FAILURE OF REGIME
TAO Ji-shuang
(Shen扎hen Technological College,Shen扎hen Guangdong 518055)
When Shi Siming killed An Qingxu,he also killed a large number of barbarians who came from the same race with An Qingxu.Shi Chaoyi had the same behavior after he murdered his father,because An Lushan and Shi Siming belong to different ethnic tribes.An Lushan is the western barbarian in the the northeast of China,and he accommodated himself to won over the local nationalities,so the momentum against Tang government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while Shi Siming and his son always emphasi扎ed their Turks and indigenous identity,resulting in large cracks appearing in ethnic joint,thus causing complete failure of Shi Chaoyi.The destruction of consolidation of the ethnic unity mainly results from Shi and his son’s misjudgment in addition to the changes of political situations to some extent.
Anshi Rebellion;An Lushan;Shi Siming;Shi Chaoyi;Race
K242
:A
:1672-2868(2017)01-0100-05
责任编辑:杨松水
2016-10-25
陶继双(1981-),男,安徽明光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博士后在读,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