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当代电影中的埃阿斯式沉默
2017-03-29陶悦宁
陶悦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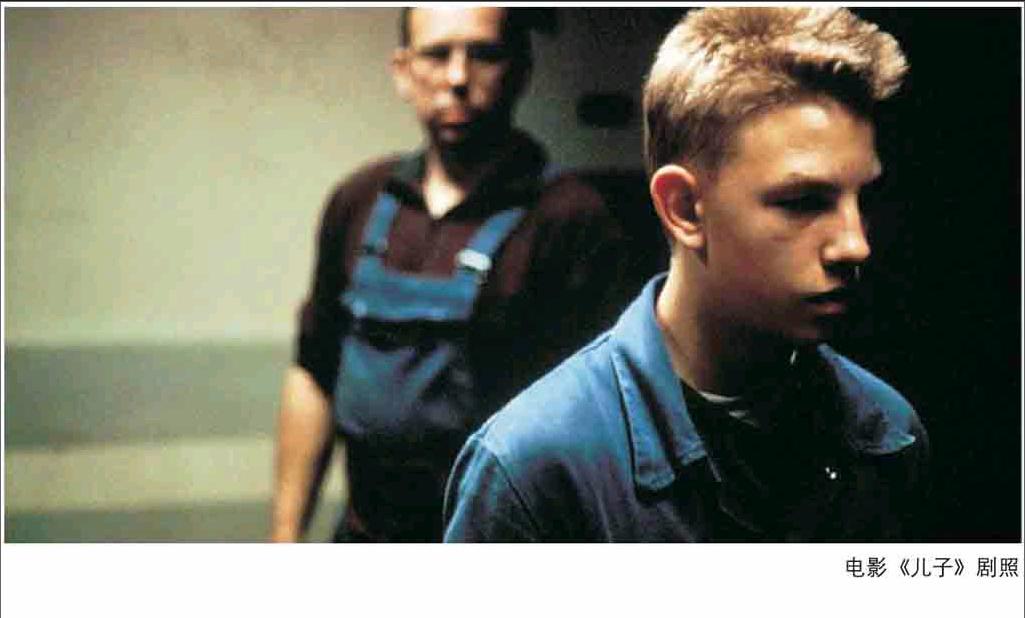
【摘要】 朗吉努斯在其《论崇高》中,将奥德修斯去往冥府向埃阿斯的鬼魂道歉,而后者沉默以对的场景,称作是整部《奥德赛》中最为崇高的部分。这虽然是朗吉努斯从古典修辞学角度所做出的评价,但崇高作为一个现代概念,“埃阿斯式沉默”所表现出的与人性有关的隔绝与断裂,在今天仍然有很大的讨论空间。本文选取《儿子》《趣味游戏》《四月三周又两天》《八月》和《清水里的刀子》五部中外电影,通过对其中特殊沉默场景的分析,讨论当代电影中埃阿斯式沉默的表现、效果以及在当下探讨崇高的意义。
【关键词】 当代电影;崇高;埃阿斯式沉默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我这样说,他没有回答,却同其他故去的死者的魂灵一起走向昏暗。他本可抑怒和我作交谈,我也愿意。”[1]216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奥德修斯经女巫指点通过冥土回家,在地府中,他遇见了昔日战友埃阿斯的鬼魂。埃阿斯身为仅次于阿喀琉斯的希腊英雄,因与奥德修斯的一场争执而自杀,未能死于战场。奥德修斯为此深感愧疚,他向那魂灵哀悼并且道歉,然而埃阿斯的回应却是什么也不说,跟随着其他鬼魂一道走入深渊。
古希腊作家朗吉努斯在其著作《论崇高》中对此评价:“不形之于言,却比任何谈吐来得高尚。”[2]84在他看来,埃阿斯的沉默与奥德修斯一系列精妙的修辞形成极其强烈的对比,后者站在胜者和生者的立场,使用大量辞藻来表明悔意,然而埃阿斯却沉默应对,以无言瓦解修辞,因而形成了崇高的风格,他也由此肯定了荷马的伟大。
这是朗吉努斯从古典修辞学角度出发所做出的评价,整部《论崇高》也旨在探讨语言的崇高风格,以期对这种特殊审美感知的生成机制及手段做出解释。但在全书完成之初它并未受到重视,直到中世纪后才被翻译成各种文字。书中关于崇高的探讨,极大影响了后世欧洲美学的发展,因而使之成为一个重要的现代概念。这种效果“延后”的原因在于,与智者派、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修辞学派不同的是,这些当时的修辞学理论基本都指向一种对情感和注意力的操控,认为修辞术可教,而朗吉努斯所讨论的崇高却是不可教的,更多是指向一种失控状态,即人在突破感性与知性临界点时的不确定性,而这种对不确定性的关注显然与现代的思考方式更为接近。由此,本题中“崇高”含义,并非现代汉语中崇高的含义,而应是一种临界状态的感受,对这种感受的把握能够带来什么,就是“埃阿斯式沉默”在今天被讨论的意义。
埃阿斯身为荷马诗中的伟大英雄,与奥德修斯争夺阿喀琉斯死后的遗甲,由于奥德修斯使用诡计导致他未能胜利,因而饮恨自杀。如奥德修斯所说,埃阿斯的鬼魂“本可抑怒”和他作交谈,但却最终含怒不语,走向昏暗。在这个场景中,埃阿斯的沉默所展现的是对自身不强大的承认,这种失落感传达出了人生中无可谈论又无可奈何的隔绝与断裂。面对奥德修斯,他已是失败者,作为一缕幽魂,他意识到了人之为人的局限与节制。因此,他的沉默是一种压倒性的情绪,可以唤起人们心中的挫折感,引发一种超越性的思考与行动,因而也就指向了崇高。
在电影中,同样存在大量沉默场景,但并非都能构成埃阿斯式的崇高。康德在其《判断力批判》中特别区分美与崇高,认为后者是“自然表象中感性之物由以被评判为适合于对之作可能的超感性运用”[3]106,即由理性运作的对经验的否定,而非想象力与知性的游戏。其表现在于克服感知性尺度时,因对经验把握失败而导致的失落与挫败感,是一种对于自我的否定,因而成为康德意义上的反思判断。在康德之后,后康德主义批判这种将感性与超感性区分的做法,认为二者从来都是交织在一起且使得主体参与其中的。尼采在《崇高者》一篇中更寫道:“这就是灵魂的秘密,惟当英雄离弃灵魂,方能在梦中接近。”[4]150其意指康德所谓的否定性克服已经失效。但无论以何种观点来看,本文所要在电影中寻找的埃阿斯式沉默,必然不是从经验出发而引起的一系列情感表达,而恰恰在于对经验把控能力丧失后的考察。
当代电影中的哪些沉默情节设置构成了此种崇高、这样的安排又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以及在当下探讨崇高有什么意义,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以下选取《儿子》《趣味游戏》《四月三周又两天》《八月》和《清水里的刀子》五部中外电影进行分析。
一、当代电影中的埃阿斯式沉默
沉默(silence)概念的涵盖面非常广,它指噪音或声音完全丧失的安静状态,推展开来也可以是一种无人说话的尴尬处境,或是某人拒绝谈论某事或回答某些问题的举动,以及其他任何沟通上的缺失,在这一点上最常见的例子就是日常言语和音乐。[5]1420沉默的行为或是现象在日常生活中频繁出现,已引起许多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与关注,如诺尔·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从政治学传播学的角度研究群体意见与沉默现象,乔治·斯坦纳的《语言与沉默》基于文学发展,针对语言文化的衰落对政治暴行深入反思。而在我国,学者们多从语用学出发探讨沉默的功能,在各种文本中进行话轮研究,按照莱文逊(Levinson S.C.)在《语用学》一书中的做法,将其分为话轮间沉默、话轮内沉默和话轮沉默。
从电影史来看,由于技术的限制,早期电影是既没有色彩也没有声音的。1895年6月,卢米埃尔兄弟拍摄影片《代表们的登陆》(Départ en voiture,1895),在放映时演员拉格兰奇站在银幕后将自己的台词重复了一遍,被电影史家乔治·萨杜尔(George Sadoul,1904-1967)称为“有声电影第一次天真的尝试”[6]7。三十多年后,导演阿兰·克劳思兰德(Alan Crosland,1894-1936)拍摄制作的影片《爵士歌王》(The Jazz Singer,1927)正式上映,在其中插入了歌曲与对白,标志着电影制作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有声电影的出现,宣告了“沉默”作为固有属性的瓦解,也因此在人声、音响、配乐等范畴方面出现的沉默状态,给观众带来了新的体验与解读路径。贝拉·巴拉兹在其《电影美学》的“声音”章节中谈到沉默:“在影片里,沉默可以成为一种非常动人的效果,可以起多种多样的作用,因为沉默固然意味着不说话,但它并不排斥各种各样的表情和手势。一个无声的眼色可以传达无限深情,无声的人反而更有表现力,因为一个默默无言的人的面部表情能够说明他沉默的原因,使我们感觉到他的威严、他的气势或他的紧张心情。在影片里,沉默丝毫不会中断动作的发展,而这类无声的动作甚至会造成一个生动的局面。”[7]218-219在这里,有声片中的沉默被认为是使得其他细节被增加关注的原因,将对影片情节发展引起新的紧张与新的意义。
沉默是有声片中对于有声状态的人为暂停,但同时也是对这种状态的补充。在叙事意义上,沉默能够体现影片的复杂性与开放性,而在观影体验上,沉默场景则能强化观众对于影片时间感的捕捉。从这一点来看,电影中的沉默场景似乎是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想象与回忆的空间,而在这空间之中又必然不只是存在唯一一种沉默的可能。本文中所要讨论的就是基于电影情节同时延伸到某种特殊情感判断的沉默场景,通过对埃阿斯式沉默在影片中的效果分析,发掘其在当下讨论崇高时所能够起到的作用。
在达内兄弟的电影《儿子》(Le fils,2002)中,木匠奥利维的儿子在五年前被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的少年所杀。五年后,当奥利维在自己的木工学习班中重遇这个杀人犯时,已经完成了官方赎罪程序的少年似乎并没有将他认出。但奥利维没有忘记,这场重逢勾起了他内心中压抑已久的情绪,使他无法保持冷静。在上课过程中,奥利维从不喊出弗朗西斯的名字,课程结束时也唯独不与这个男孩握手道别。但同时,他却又一次次地偷偷跟踪弗朗西斯回家,他的眼神无时无刻不追随着这个让他痛失爱子的少年。奥利维的这些怪异扭曲行为一直持续到了影片临近末尾处,当弗朗西斯说出“你能当我的监护人吗?因为你教我做木工,还关心我”时,他再也无法忍受,将那个具有毁灭性的秘密告诉了面前的人。
“你杀死的那个男孩,是我的儿子。”奥利维的话一出口,弗朗西斯立刻选择了逃跑,奥利维在他身后追赶,靠着年龄和身型的优势将弗朗西斯制服在地。他用双腿压住少年的胸膛,他的双手紧紧地扣住了身下人的脖颈。时间在这里被无限拉长,特写镜头从奥利维的双手移到了他的脸旁便不再变动,镜头中的他不断喘息,额头上的汗滴落到眼镜片上。之后镜头又切换到中景,奥利维松开了手,从弗朗西斯身上离开。
影片的最后,奥利维在木厂前将木料搬上拖车,没过多久弗朗西斯走到了他的身边,拿过剩下的木块将其安放到了车上。奥利维看着他,没有说一句话。
奥利维没有掐死弗朗西斯,甚至在后者回到他的身边时默许了其帮忙搬运木料的行为,整部影片就在奥利维的沉默中戛然而止。这似乎是观众喜闻乐见的场景——少年杀人犯被宽恕并且被接纳,但这是宽恕吗?
探究奥利维最终的沉默指向,需要追溯到他的前一个行为,即在追逐中他将弗朗西斯制服却并没有将其杀死,而这样的行为又使得我们不免回到影片的最初,追问奥利维为何不在认出弗朗西斯的时候即刻动手。
一个父亲在盛怒之下向杀害儿子的凶手复仇也是常常会被展现在荧幕上的题材,这其中的悲苦与压抑,或许是观众想要看到的。但奥利维却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伤害弗朗西斯的想法,只有在后者得知真相逃跑,而他立刻起身去追时,才让我们看到了一丝他想要复仇的冲动,但这冲动也很快消失在了他松开的双手上。与之相反的,奥利维更多向观众展现的是他与自身的不停斗争,那些扭曲又怪异的行为,故意冷落与偷偷跟随,甚至让弗朗西斯感受到了如同父亲般的关心与陪伴。而奥利维又何尝不是?他曾偷过弗朗西斯的钥匙潜入其房间,看那孩子抽的烟,躺那孩子睡的床,如果说这是他在弗朗西斯身上投注了对儿子的思念是太过牵强的,那么至少在那一刻他感受到的似乎也不是恨,而只是少年的飘零。
所以奥利维的沉默不是宽恕,而是一种不确定。他自己也无法明白自己的欲望是复仇还是原谅,他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一个。奥利维甚至要比从前跟踪弗朗西斯时更加挣扎,因为一切都已经说开了,而孩子又走回了他的身邊,那么接下来到底应该怎么做?在奥利维将弗朗西斯压倒在地的时刻,他意识到了后者在杀害儿子时的那种情绪,于是他最终强迫自己从冲动中抽离,将手松开。这是成年人的冷静与自省,但同时又是生命中的断裂,因为奥利维还是放不下。他的沉默带着对于自身的不确定,他意识到即使杀了对方也无法改变的事实,所以没有动手。
达内兄弟一贯的纪录片式拍摄手法,笔直地盯住角色本身,对其心理活动的刻画到了冷酷无情的地步,而这种内心的汹涌都隐藏到了奥利维的沉默之下。
哈内克的反暴力之作《趣味游戏》(Funny Games,1997)讲述了一个以游戏来进行恐怖杀戮的荒诞故事,全片没有直接描述血腥场面却令人不寒而栗,做到了让暴戾无因又使人心悸不已。影片中,主角一家来到乡村湖区度假,遇到了两个态度友好又需要帮助的年轻人,女主人不疑有他地将二人迎进家中,却不想换来的是一场毫无怜悯的囚禁凌虐游戏。整场杀戮在主角一家的别墅中完成,两个年轻人先后打死了主角家的宠物狗、敲碎男主人的膝盖、强迫女主人在所有人面前脱衣,紧接着提出开启一场死亡游戏的单方面决定,游戏的主题则为“明天到来之前主角一家全都会死”。在“游戏”过程中,年轻人们轻佻又无谓的态度与主角一家崩溃无力的神情形成强烈对比,导演将这种暴力无限制地放大,让两个白衣恶魔将全家人的尊严与信仰打碎。最后,男主人与儿子被开枪射杀,女主人则被捆绑后丢入湖底。明日到来,无人生还。
全片剧情紧凑,通过施虐者的暴力循环,让观众始终处于一种焦虑与不适的状态。但在这循环之中,仍存在一处长达180秒的停顿,两名杀手在开枪射死这家人的儿子以后暂时离开,摄像机给了别墅客厅一个全景且保持不变,镜头中出现了受伤倒地的男主人的双脚、被捆住手脚的女主人的上半身、躺在血泊中的男孩尸体,以及不断切换赛车画面的电视机。
此刻影片中的画面仿佛静止,只有电视机变化的亮度与节目声音能提醒时间的存在。女主人于1分17秒后起身,蹦跳着来到电视机前将它关闭,至此影片中所有声音全部消失,女主人就跪在电视机旁一言不发,全程没有朝死去的儿子看过一眼。
这场沉默为女主人同时也是观众划出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之中,女主人或许是在从过度崩溃的情绪中寻求平静,或许是在思考接下来该如何逃离,但更为可能的状况,她只是被吓坏了而已。过度叠加的暴行使得她的身心承受能力都达到了即将瓦解的状态,在这样的临界点上,她的所有情感已经被剥夺,脑中一片空白。她从静坐到起身去关掉电视的过程中都不曾看过儿子一眼,而那却恰恰是这短短几步中必然需要面对的事情,但她没有看。她从儿子的尸体旁跳过,最后背对着血泊中的小孩跪坐沉默,她不知如何面对也想不明白之前所发生的一切,于她而言实在是过于疯狂与恐怖。
对于观众来说,这样长时间的沉默是十分难熬的,但同时也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一般来说,儿子被枪杀后应该会有特写镜头,不论是给谁,但本片导演却将机位固定,让观众始终处在被动的客观视角去观察女主人的精神状态,实际上也是被强迫着去反思暴力本身以及在观影时希望从暴力中获得乐趣的行为。
“我的目的是在观众眼前呈现真正的暴力,让他们发现自己是如何成为施虐者的共犯……进而成为煽动下的受害者。”[8]162导演哈内克还原了暴力的本质,试图想让观众明白的是:暴力不是娱乐与消遣,而是一种无法承受的痛,无论是发生在谁的身上。
罗马尼亚影片《四月三周又两天》(4 luni, 3 saptam?ni si 2 zile,2007)讲述了在苏联解体前夕的1987年,当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罗马尼亚将堕胎定义为非法行为。影片女主角为了帮助自己的大学室友兼好友秘密堕胎,通过其他朋友介绍,联系到了愿意冒险做手术的医生,并且筹集到了一笔数目不小的手术费用。但就在做手术前,医生却认为钱的数目远远不够他去冒坐牢的风险,于是提出用两名女学生的身体来做交换。面对脆弱的好友,没有选择的主人公同意了这个要求,在廉价旅馆中承受侵犯之后,主人公的好友才得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流产。
由于事先与男友有约,女主人公中途暂时离开了旅馆,在到达目的地以后,她向男友问出了纠缠着内心的一个问题:“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你会怎么办?”男友的反应显得有些无措,他起初回避了问题的重点,坚持认为他已足够小心,这种事根本不会发生,而后在女主人公的再三逼问下,他才回答道:“也许……我会娶你。”
主人公回到旅馆时,好友腹中的胎儿已经流出,她用白毛巾包裹住将成型的血肉后冲下旅馆,在穿过一条又一条黑暗的街道之后,将其丢弃在了路边的垃圾桶中。
影片的最后,主人公与好友无声地对坐于旅馆的餐厅中,侍者端上一份由各类动物内脏所组成的菜肴,好友面无表情地将它吃下,而主人公沉默地看着她。远处传来某个婚礼现场的喧闹声。
在被医生侵犯之后,女主人公赤裸着下身冲进旅馆的浴室,用力搓洗自己。在中途离开去往男友家的公车上,她靠在窗前,无声地流下眼泪。在抱起胎儿的尸体下楼后,她害怕又紧张地穿梭于暗巷之中,急促而压抑地喘息着。
尽管无助且惶恐,主人公却独自承担着这一切濒临崩溃的局面,她或许恨过好友,却更多牵挂。然而当她最终回到旅馆,看着好友毫不排斥地吃下那些带着血丝的动物内脏时,她突然感受到了所有行为的荒诞性。男友在家中给出的那个回答也在此刻显得讽刺无比,因为好友无动于衷吃下动物器官的模样,或许就会是她的将来。影片最后,伴随着远处婚礼现场的喧闹声,餐厅窗外偶有车灯一闪而过,女主人公转头看向摄影机镜头,电影就结束在这里。
一镜到底的中景,逐渐扩展的裂痕,强烈的无力感在主人公1分04秒的沉默中蔓延开来,最后的疑问被隐于突然降临的黑幕之后——事情何以会坏到这个地步?
在大陆影片《八月》(2016)中,刚结束小升初考试的晓雷正享受着没有作业的暑假。他的父亲是电影厂的一名剪辑师,平日无事时会带着他去游泳馆学游泳、去田埂间捉蛐蛐、去电影院看免费电影……就像每个炎热又自由的夏天一样,影片中充斥着九十年代初内蒙小城里反复的家庭生活与大把的闲工夫,而晓雷就用他少年的眼睛观察着这个司空见惯的世界。
然而这个夏天又似乎有些不同,电视新闻中不断播报的国有单位改制新闻,宣告着铁饭碗的打破,晓雷父亲所在的电影厂也受到了改制的冲击,面临着解散重组的局面。家属院中的大人们看似平静,心却如同这夏日般燥热起来,晓雷仍旧百无聊赖地耗着,直到父亲为了生活远走他乡,他才真实地感觉到时间过去了,一切都在改变着。
在影片的后半段,电影厂举办了改制前的最后一次员工运动会,男女老少都参与到了拔河项目中,这时突然响起一条广播,说厂里的卡车启动不了了需要大伙去推,众人听了立刻就放下了手里的长绳,没有任何的迟疑。晓雷站在人群之后,安静地看他们往厂门口跑去,他知道自己的父亲并没有在这其中,而是坐在电影厂的暗房里剪辑最后一条片子。晓雷看着,没有向前也没有说话,接着在卡车成功发动的时刻,选择了一条小岔路,走开了。
国家政策的改变真正能够影响什么,晓雷或许不会懂。但父亲与他不再能够以员工及家属的身份免费看电影、厂里原先画海报的工人转行去街上刻字、与父亲关系极好的导演云叔离开了小城……这些都让他隐隐地感受到了生活的变化。究竟是什么他说不出,但看不清前路的现实却是片中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的,对未知的迷茫与自身的不确定化成了晓雷沉默的背影,他没有向前融入推车的人群之中,反而是选择了条岔路离开,这种无法向他人甚至自己言说的失落感,冲破了一整个时代来到我们的眼前。
《清水里的刀子》(2016)改编自回民作家石舒清的同名短篇小说。在影片中,穆斯林老人马子善的老伴去世了,他的大儿子准备将陪伴老人十多年的牛杀了来祭祀自己的母亲。马子善老人起初不同意,因为家中实在已经不宽裕,老牛还能用来分担一些农活,但大儿子希望能让生前活得辛苦的母亲不再受亏待,因此执意杀牛。老人最终同意了,且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对牛细心照料,可就在祭祀仪式的前几天,牛开始不吃不喝。
这让老人想起了穆斯林的民间传说,牛作为“大牲”,如果其死是被用作正途,那么牛在死之前就会预知自己的命运,它将在喝水的盆中看到一把属于它的刀子,由此不再吃喝,以期保持一个完全洁净的身体來迎接死亡。牛与老人一样已经接近暮年,它的行为促使老人生发出了自身对于死亡的感悟。为了清净内心的污浊,清清白白地离开人世间,老人在祭祀仪式之前将妻子生前向邻里欠下的五块钱还上了,随后他牵着牛去田野间散步,在那里看见了老伴的灵魂在田里耕作。
整部电影从老人妻子的葬礼开始,以牛之死作为结局,所有叙事都围绕着这两个死亡主题流动。在影片最后,杀牛祭礼即将开始,马子善老人提出要去一趟集市,儿子说:“大,今儿你不能走啊”,老人没有回答。
“牛知其死,他贵而为人,却不能知道。”[9]355在原作中,作者说这是令马子善最为伤痛的地方。然而在影片中,老人的沉默或许还含有更深的断裂。他从牛不再吃喝的行为中体悟到了死亡,并且已如牛一般洁净自己,按照穆斯林的宗教信仰来说,不论是对牛还是自身的死亡,他都理应能够从容面对,且看透这世间的生死循环。然而就在牛要被宰杀的时候,老人却发现自己仍然没有办法做到坦然面对。逝去的老伴,还有即将死去的老牛,都是如此,他的心中还是不舍。
对于儿子的挽留,老人没有作答,沉默许久后还是去了集市,直至日落才归。老人回家后,先去牛棚转了一圈,随后才打开院门,可见其心。
二、断裂之下的崇高及意义
崇高一词虽最早出现于古希腊作家之笔,但作为直到近现代才受到重视并引发讨论的一个概念,在现代美学研究中常被认为是美以外的最重要的审美范畴。然而在现实语境和具体判断中,却总会出现对于崇高很难避免却又十分普遍的误读。
以电影为例,在抗美援朝题材影片《英雄儿女》(1964)中,志愿军士兵王成在战斗中喊出了“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口号,在王成壮烈牺牲之后全军开展了向他学习的运动。在这里,王成的英勇行为被认定为崇高,而在现代汉语语境中,崇高似乎也包含了这样高大正面的形象。如此,以无所畏惧、英勇赴死的姿态煽动观众情绪的英雄片和战争片不胜枚举,大众也倾向于同意将其称作崇高。但这究竟是道德上的高尚还是美学意义上的崇高,显然是混淆的。
与朗吉努斯评价《奥德赛》极为相似的,是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其美学著作中曾谈到《约伯记》(The Book of Job),他认为其中对于恐怖与不确定性的描述是极为崇高的部分:“它包裹在无尽的黑暗之中,不是比最生动的描写、最清晰的画作所能表现的意象更令人敬畏、更令人震惊、更为恐怖吗?当画家们清晰地展现这些古怪的、恐怖的观念时,我认为几乎所有人都失败了。”[10]55由此,美学意义上的崇高并不是现代日常汉语中所表达的高大宏伟之意或是仅仅将其视为某种高尚的品德,而应是一种与恐惧有关的、主体去把握自身不确定性时的状态。
奥利维的挣扎、女主人的崩溃、女大学生的无力承受、晓雷的失落、老人的无奈……如上一节中所述,当代电影中的埃阿斯式沉默,其崇高表现几乎都不是高大正面的,而恰恰是基于一种痛苦,这种痛苦表现在沉默者突破自身感知性尺度时的不确定。在这种不确定之中,主体面对的不是丰富的经验或经验的正面生成,而是经验所带来的意识到自身无能的某种失落与挫败,是人生中无法谈论又无可奈何的断裂与隔绝。而在《英雄儿女》中,观众所能感受到的王成并不惧怕死亡,他是为了心中信仰而慷慨赴死。如果仅是从这一层面来理解人物且止于此,那么王成所完成的就只是一个合目的的道德行为,因而与审美上的崇高无关。
崇高不是纯粹的激情,也并非带善的宣教。对好的道德行为的赞叹并不能使我们得到相应的道德提升,反而会因无法把握其实质而成为教条主义。要真正地理解道德行为,只有回到其原初情境之中,回到那个感知性尺度被突破的临界状态,当我们感受到其中的恐惧与艰难甚至是无法自持时,才能够接近道德。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如果观众只是在观看一个悲惨壮烈的故事或是角色,而不亲自去感受那个临界状态,是不可能体会到真正的崇高的。因为简单的观看只能是被知性中的概念,固定了想象界限,从而放弃运用自身的理性能力,将一切都诉诸情感,而情感稍纵即逝,无法保持一种可靠的生命力。
这种回到原初情境又追回自身的自反行为,在评判崇高中是被必然要求的。康德在这一点上强调了反思空间的重要性,即在这个空间之中,我们不要急于行动,而是要去思考行动的可能性,去认识到自身理性的力量从而克服经验带来的失落,最后才达到崇高并由此展开自由的不受情绪支配的行动。但在后康德主义者看来,这样的一种空间到了现代已经几乎不可见了,感性与超感性、主体与客体总是交织在一起无法区分开来,人们在被恐惧或痛苦压倒时没法再去克服,而是深陷其中,这也是现代人体会崇高变得越来越困难的原因。
但反思的能力与行为总是不可缺少的。由此,电影或许是能够人为提供这样一个空间的较为合适的载体,而电影中的埃阿斯式沉默更可作为崇高体验的途径之一。当电影人物突然陷入沉默,观众在这无声的时刻才能开启自由想象的空间。也正因如此,我们甚至要呼吁多一些这样的沉默时刻,而且是让观众“难熬”的沉默。
在这沉默所提供的空间之中,观众从体会角色心境转换到感受自身的能力,同时影片中的空白又迫使其不能诉诸情绪而是寻求理性的帮助去思考问题。真正的崇高能让我们感受到自身拥有突破的能力,却同时不会狂热或是狂妄地认为能凭一己之力完全达到预想。在无法把握经验的情况下去寻求自身理性的帮助,实际上是对经验的一种否定,而就是在这样的否定中,真正的崇高者在行动时往往就展现出了安静甚至表面上的无动于衷。所以,当奥德修斯用了大量修辞来表达自己的悔意与哀思后,埃阿斯没有拒绝也没有接受,他只是沉默。恰恰是这种状态让我们不能在理性之外找到附着点,不能去依靠感情来理解他的沉默,而只能去直面生和死之间永远的鸿沟。如果埃阿斯回应了奥德修斯,那么这鸿沟就被填平了,也就失去了崇高的指向。现代人体会崇高尤为艰难,而通过对当代电影中的埃阿斯式沉默的感知,反思背后隐藏的惊心动魄的情感,在断裂中反思人性喧嚣,才是可行的方式。
当然,这里还是存在“过度解读”或是误读电影文本的质疑,需要明确的是,本文讨论当代电影中的埃阿斯式沉默,并非将关注点置于沉默的解读,而是在解读沉默时所发现的超越性的可能。
三、小结
古希腊作家朗吉努斯在其《论崇高》中,将奥德修斯去往冥府向埃阿斯的鬼魂道歉,而后者沉默以对的场景,称作是整部《奥德赛》中最为崇高的部分。这虽是朗吉努斯从古典修辞学角度出发所做出的评价,但由于其中的崇高指向一种失控状态,即人在突破感性与知性临界点时的不确定性,而这种对不确定性的关注又显然与现代人的思考方式更为接近,因此也就成为了一个极为现代的美学概念,“埃阿斯式沉默”也有了在当下讨论的意义。
在电影中,同样存在大量沉默场景,但并非都能构成埃阿斯式的崇高。本文以朗吉努斯的《论崇高》为切入点,通过选取的五部中外电影:《儿子》《趣味游戏》《四月三周又两天》《八月》和《清水里的刀子》来对其中的“埃阿斯式沉默”进行分析,讨论当代电影中这类特殊沉默场景的表现、效果以及在当下以此来探讨崇高的意义。
对于当代电影中的埃阿斯式沉默的讨论,是基于电影情节同时延伸到某种特殊情感判断的过程,在分析后可以发现,它必然不是从经验出发而引起的一系列情感表达,而恰恰在于对经验把控能力丧失后的考察。这种临界状态的感受,以及对这种感受的把握能够带来什么的讨论,就是当代电影中的“埃阿斯式沉默”所能够带来的超越性的可能。
参考文献:
[1](古希腊)荷马.奥德赛[M].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缪灵珠.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3](德)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4](德)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5]OUP Oxford.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6]陳晓云.电影学导论[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7](匈牙利)贝拉·巴拉兹.电影美学[M].何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78.
[8](法)米榭·席俄塔,菲利普·胡耶.哈内克论哈内克[M].周伶芝,张懿德,刘慈仁,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6。
[9]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M].鲁迅文学奖·宁夏作家自选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
[10](英)埃德蒙·伯克.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M].郭飞,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