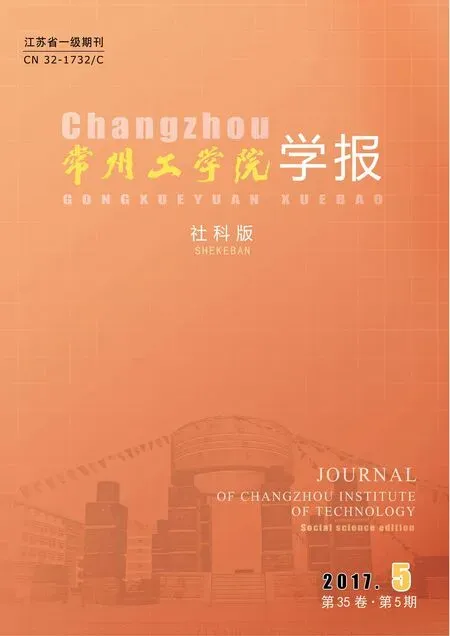从“台北人”到“纽约客”:白先勇对身份认同的追寻
2017-03-28许子斌
许子斌
(集美大学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从“台北人”到“纽约客”:白先勇对身份认同的追寻
许子斌
(集美大学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从大陆到台湾,再到美国,白先勇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身份危机。在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中,白先勇用文字写下了他对身份认同的追寻历程。“台北人”是一群身在台湾,心在大陆的“异乡客”,他们在新的社会现实的困境中逐渐失落了自我的身份。“纽约客”是一群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游荡的“漂泊者”,当在“别处”生活的梦想实现时,他们却在自我认同与他者想象之间构成了对立,并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DannyBoy与TeaForTwo是白先勇新世纪后发表的作品,展示了白先勇在跨文化际遇中,站在世界主义的立场上,实现了对身份认同的突围与超越。
白先勇;身份认同;追寻;超越
I206
白先勇曾在台北一住十一年,可他却说:“台北我是最熟的——真正熟悉的,你知道,我在这里上学长大的──可是,我不认为台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白先勇与“台北人”不一样,他的家既不在台北,也不在大陆。可他的家又不在美国,“他说,在美国七年,一身如寄,回到了自己房间,也不觉得到家了,飘飘浮浮的”。在美国时,白先勇想家,他曾说:“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和,很难解释的。可是我真想得厉害。”①客居异国他乡,白先勇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常有一种“无家可归”的彷徨与恐慌。在《从国族立场到世界主义》中,刘俊认为白先勇前期作品《谪仙记》《谪仙怨》看似在写“纽约客”,其实还是在写中国人,此时的“纽约客”只是纽约的过客,而白先勇进入新世纪创作的DannyBoy与TeaForTwo中的主人公才对纽约有了一种真正的归属感,因此,这反映出白先勇小说创作立场的变化,即从国族主义立场转向世界主义立场。朱立立则在《个体存在焦虑与民族文化忧患——兼论白先勇与存在主义的关系》中指出,在西方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白先勇产生了对个体生命认同的困境,而长期海外留学与生活的经历,使白先勇认识到战后台湾与整个海外中国人的生存困境,因此,在小说创作中,他将个体的悲剧融进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而本论文更注重的是,白先勇作品中的主人公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追寻,展示出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与生活环境中对自我身份的定位与认同。在《身份认同导论》中,陶家俊指出,西方身份认同理论历经三次大裂变,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模式:一是以主体为中心的启蒙身份认同,它建立在人是被赋予理性、意识和行动能力的理解之上,认为人是理性统一体,能够实现对自我精神世界的整合;二是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身份认同,它强调各种复杂社会经验对个人存在与意识的决定性;三是后现代去中心身份认同,其特征是去中心化,正如霍尔所说:“主体在不同时间获得不同身份,再也不以统一自我为中心了。我们包涵相互矛盾的身份认同,力量指向四面八方,因此我们的身份认同总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②而笔者赞同霍尔的身份认同理论,认为身份不是天生与固定的,而是一个人在其社会生活经历中,不断形成的对自我的认同,并随着时间与环境的流变,而不断发生改变,因此,身份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
一、台北人:身份失落的挽歌
1948年到1949年间,近两百万的大陆军民跟随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他们“从未把这个岛视为久居之地”③,并相信国民党政府的“反攻神话”,认为不久后就可以返回大陆生活。一年又一年,随着“反攻神话”破灭,他们才知道大陆是再也回不去了。直到四十年左右以后,他们“得以返乡探亲的那一刻,才发现在仅存的亲族眼中,原来自己是台胞,是台湾人,而回到活了四十年的岛上,又动辄被指为‘你们外省人’”④。在白先勇的笔下,他们就是“台北人”,是一群身在台北,却心在大陆的异乡客。他们自认根在大陆,而大陆却迟迟回不去,脚下的台湾,却又始终没有归属感。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身份也逐渐失落,变得模糊不清,遂成了一曲令人哀叹的挽歌。
白先勇被夏志清誉为“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其代表作小说集《台北人》写一群沦落在台北的大陆客。在《游园惊梦》里,钱志鹏将军在南京身居高位,钱夫人为桂枝香(窦夫人)请生日酒的那天,“梅园新村的公馆里一摆就是十台,擫笛的是仙霓社里大江南北第一把笛子吴生豪,大厨师却是花了十块大洋特别从桃叶渡的绿柳居接来的”。同时“梅园新村钱夫人宴客的款式怕不躁反了整个南京城”⑤,由此可知,那时钱夫人的富贵与排场。来到台湾后,钱志鹏将军已经逝世了,钱夫人一个人住在台湾南部,穿着有点发乌、过气的长旗袍,坐计程车来台北参加窦夫人的宴会。这时的钱夫人不仅失去了南京时的富贵与排场,她的身份地位也渐渐失落。在南京时,宴席上的主位,十有八九都是钱夫人占先的,她是钱志鹏将军的夫人,她从来也不推让。可在窦夫人的宴席上,直到赖夫人与窦夫人提醒之后,钱夫人才一阵心跳地去第二桌的主位坐下了。《岁除》里的赖鸣升,在大陆时,他是国军骑兵连长,并以参加过台儿庄战役而自豪。来到台湾后,他从军队退役,三万多退役金被一个山地女人骗得精光。不得已,他来到荣民医院做“伙夫头”,并时常拿医院厨房里的一点锅巴去喂猪。因此,医院的主管常常直起眼睛对赖鸣升“打官腔”。从大陆到台湾,赖鸣升失去的不仅是军职。更多的是,他曾经的身份认同在遭遇现实生活的困境后,逐渐褪去了色彩,渐趋模糊。因而,赖鸣升才选择在除夕这一天,花大价钱买礼物并跑老远去老部下家里过年。在老部下家里,他才能重新确认那已经逐渐失落的身份认同,回味起曾经的军队生涯与光荣往事。《一把青》里的朱青,曾“是一个十八九岁颇为单瘦的黄花闺女,来做客还穿着一身半新旧直统子的蓝布长衫,襟上掖了一块白绸子手绢儿”⑥。可来台湾后,朱青“从一个乐师手里拿过一双铁锤般的敲打器,吱吱嚓嚓的敲打起来,一面却在台上踏着伦巴舞步,颠颠倒倒,扭得颇为孟浪。她穿着一身透明紫纱洒金片的旗袍,一双高跟鞋足有三寸高,一扭,全身的金锁片便闪闪发光起来”⑦。在大陆时,原本清纯腼腆的朱青,因丈夫郭轸身亡,来台后,却变得浪荡起来。朱青失去了甜蜜的爱情,她的身份认同随着丈夫郭轸的逝去也一同失落了,于是,她放逐了自己。《花桥荣记》里的卢先生,来台湾后,忙着教书、养鸡,积攒钱财,渴望有一天能够和未婚妻罗姑娘完婚。卢先生在香港的表哥谎称可以把罗姑娘从大陆带到香港,并因此骗走了卢先生十根金条。在希望破灭之后,卢先生与洗衣婆阿春姘上了。在捉阿春偷汉子时,卢先生反被阿春打成重伤,并在不久后就去世了。未婚妻罗姑娘是卢先生的希望所在,也是卢先生借以确认自我身份认同的他者想象。当他者想象消失时,卢先生自我身份认同也就失落了,并因此走向堕落。
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在美国政府的扶持下,台湾经济开始起飞,从农业社会逐渐转变为开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社会在逐渐变化,而白先勇笔下的那些“台北人”却依旧眷恋于过去的美好生活与繁华场景,一个个在台湾的现实生活中败下阵来。钱夫人凭借钱志鹏将军的权势而获得的自我身份认同,随着钱志鹏将军的逝去,钱夫人的自我身份认同也随着失落。赖鸣升是凭借国军连长的身份和参与了台儿庄战役而自豪,并以此确立自我身份认同。然而在逐渐资本主义工商业化的台湾,台儿庄战役已无人关注,赖鸣升又从军队退役变成了社会最底层的“伙夫头”,并面临着生活的困境。于是,他在台湾的社会现实面前逐渐失落了自我的身份认同。朱青与卢先生一样,都是由于失去了恋人并远离了故土,感情世界的崩塌而致使身份认同的失落。从大陆到台湾,白先勇笔下的“台北人”在新的社会现实面前,演奏了一曲曲身份失落的挽歌。而随着那些大陆人来台日久,他们的子女也逐渐出生与长大。但第二代的“外省人”同样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困境,于是,他们选择了前往远方寻找自我的身份。
二、纽约客:生活在别处的身份困境
米兰·昆德拉在《生活在别处》中,将主人公雅罗米尔先后置于性爱生活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考察他怎样从“此处”走向“别处”,又怎样将青春的激情释放。一个人对“此处”的生活过于熟悉,使得他渴望摆脱日常机械化的生活,到“别处”寻找陌生、刺激的情感体验。小说集《纽约客》中的主人公们从台湾来到美国,作为一个“异乡者”生活在“别处”,在新的环境与社会文化面前,他们又该如何确认自我身份?
《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来美国六年,为攻读芝加哥大学文学博士学位,除了出外工作挣钱,就是一心在屋子里读书,过着苦行僧般的禁欲生活。他为了省钱,“在城中区南克拉克街一间廿层楼的老公寓租了一间地下室。这种地下室通常租给穷学生或者潦倒的单身汉住。空气潮湿,光线阴暗,租钱只有普通住房三分之一”⑧。在拿到博士学位那天,吴汉魂走出了他的小屋,来到芝加哥大街上。“他忽然觉得芝加哥对他竟陌生得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地理名词,‘芝加哥’和这些陈旧的大建筑,这一群木偶似的扭动着的行人,竟连不上一块儿。”⑨他茫然不知所措,失去了方向。在迷糊中,他梦见了母亲,并拒绝了母亲的召唤,同时用力地把母亲的尸体推落到棺材里。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看,他的行为意味着对母亲和中国文化的反叛,他拒绝了回到没有廿层楼大厦的台湾。而他又拒绝回到二十层大厦的地下室,喻示着他与西方文明的隔绝。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之间,他面临着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于是,吴汉魂自沉密歇根湖。《安乐乡的一日》中的依萍是一位全职太太,陪同丈夫伟成来到美国生活。她认同自己的中国身份,并期望把女儿宝莉训练成一个规规矩矩的中国女孩。可宝莉才进小学两年,就已经不肯讲中文了,并有时直呼依萍的英文名字Rose。每天吃过晚饭,丈夫伟成与女儿宝莉一起坐在客厅的地毯上看电视,讨论电视里的节目,有说有笑,非常开心。而依萍认同中国文化,认为电视里的许多节目十分幼稚无聊,于是“常常在他们身后干瞅着,插不进话去”⑩。在丈夫伟成与女儿宝莉都接受美国文化与认同美国身份的情况下,认同中国身份的依萍却常常融不进家庭活动,并偶尔与女儿爆发冲突,陷入尴尬的处境。而当地的美国太太们为取悦依萍,不断地向依萍询问中国的风土人情,使得依萍更加确认自己是中国人。因此,依萍无法融入美国社会,对中国身份的认同又给日常生活带来了烦恼。于是,依萍陷入了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谪仙记》中,李彤在美国有着较好的经济收入,也并不缺乏追求者,男友换了一个又一个,却始终没有结婚。与此同时,李彤的好友黄惠芬、张嘉行、雷芷苓却纷纷寻找到如意郎君,挣钱养家,结婚生子,过上美国式的中产阶级生活。可李彤是特立独行的,她并不想要好友们的那种生活方式,也不认同当时留美华人的身份,就如同她打牌一样,“要就和辣子,要不就宁愿不和牌!”而上海是回不去了,台湾又从未去过,而在国共内战时,父母亲人都在逃往台湾的海面上出事了。于是,李彤寻找不到自我的身份认同,便放逐自己,最终在威尼斯跳水自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台湾经济开始逐渐起飞,台湾社会疯狂崇拜美国,“从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将近15万台湾学生来美国攻读研究生学位。台湾大学……理科学生赴美留学者高达70%—80%”。当在“别处”的生活想象成为现实时,“纽约客”们并没有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白先勇曾说:“像许多留学生,一出国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产生了所谓的认同危机。对本身的价值观与信仰都得重新估计。”吴汉魂丢下在台湾的女朋友与母亲,孤身赴美留学,六年苦读终于获得博士学位,而此时母亲已经逝世,女朋友已经另嫁他人。吴汉魂在梦中拒绝母亲的召唤,放弃了自我对中国身份的认同,而美国女人萝娜却一直称呼吴汉魂为“你们东方人”“中国人”,以美国人的他者形象确认吴汉魂的中国身份。吴汉魂在自我拒绝与他者接受之间,展示了留美华人身份认同的尴尬处境。在《一把青》中,怕依萍不懂美国习俗,美国太太们争着向依萍献殷勤,并为取悦依萍,不断询问关于中国的风俗人情。于是,依萍在参加美国太太们的社交活动时,总得费劲做出一副中国人的模样。因此,在强势的西方文化背景下,依萍不自觉地扮演了一个弱势的中国文化形象。而依萍对中国身份的认同,又使得她在家庭生活中处于边沿位置。在他者建构与现实困境中,依萍陷入了身份认同的危机。李彤身在美国却无法认同美国,而想象中的故乡却又无法回去,凸显了留美华人无根的漂泊感,展示了留美华人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困惑。
三、跨文化际遇中的身份突围与超越
《台北人》写的是一群大陆人被迫离开大陆,来到台湾生活。他们的美好回忆全在大陆,而在台湾的现实生活与精神追求中却遭遇一系列挫折,所以他们虽身在台湾,却并不认同台湾。因此,他们是作为一个“异乡者”生活在台湾,他们与台湾是一种在而不属于的关系。《纽约客》写的是一群台湾人在美国的故事。他们大都是主动来到美国留学,并渴望融入美国社会。美国社会却一直以他者的立场确认他们中国人的身份,而他们与西方文化本身就存在隔膜。因此,他们无法认同美国社会,但却又无法全盘认同中国文化。于是,他们在中国认同与美国认同之间游离,成了一个个漂泊者。所以,他们与美国同样是在而不属于的关系。而在短篇小说DannyBoy与TeaForTwo中,主人公不再是以一个“异乡者”或“漂泊者”的身份客居他乡,而是对纽约有了一种真正的归属感,作品中的“纽约客”不仅有中国人,而且还有外国人的身影。
DannyBoy中的主人公云哥是一名同性恋者。他在担任教师期间,一直苦苦压抑自己的欲望,终因忍不住而用力搂住他的男学生,不能见容于台湾社会,被迫远走美国。来到纽约,云哥白天在图书馆工作,与一堆旧书籍打交道,晚上则四处游走追逐,在沉沦与堕落中,最终染上了艾滋病。在云哥对生命绝望而自杀未遂之后,他在圣汶生医院里被“香提之家”的义工照顾,并因此在“香提之家”遇见了他一生渴盼的DannyBoy。丹尼是一位年轻的濒临死亡的艾滋病患者,急需人照顾日常起居。在帮丹尼洗澡、换衣服、注射抗生素等各种事情中,云哥“心里突然涌起了一种奇异的感动”,“感到我失去的那些孩子好像一下子又都回来了,回来而且得了绝症垂垂待毙,在等着我的慰抚和救援”。在跨性别与种族的人类之爱中,云哥不仅挣脱了欲望的深渊,而且真正对纽约有了认同,并突破了种族与国家的界限,找到了自己的心灵归属并完成了对身份认同的超越。TeaForTwo中的主人公“我”是华人,“我”的恋人安弟是个中美混血儿,东尼是华人,而他的恋人大伟则是犹太人,珍珠是台山妹,百合来自德州。他们都是同性恋者,从世界各地,机缘巧合地相遇在纽约市曼哈顿上的“Tea For Two 欢乐吧”。“我”与安弟相遇于“Tea For Two”,并彼此相爱。在安弟生日那天,“我”送了安弟一架德国徕卡公司的相机,那是安弟看上很久,却由于价格昂贵而始终没有买下的相机。安弟收到礼物非常高兴,每天出门时,第一件事就是把相机放进配套的真皮箱子,摇摇晃晃跑到街上去。圣诞节前两个星期的一天,安弟遭到一个黑人强盗抢夺相机皮箱,在安弟拼命抢回相机时,安弟被强盗推落到铁轨坑道上,被开来的快车撞个正着。当“我”听到安弟的事故时,“记忆完全陷入了混乱状态”。随后不久,“我”离开了纽约,到爱荷华东部一个叫雪松川的小城隐居。安弟曾说过他一直有着身份认同的困扰,大概他幼年时他与他的中国母亲便遭到他美国父亲的遗弃,所以他觉得他身体里中国那一半总好像一直在漂泊、在寻觅、在找归依。可在遭遇抢劫时,安弟拼命也要抢回那象征着爱情的相机。那用生命捍卫着的爱情,使得安弟超越了国籍的界限并实现了对身份认同的超越。
在DannyBoy与TeaForTwo中,白先勇在跨文化际遇中实现了对身份认同的突围与超越。首先体现在小说名称的英文化。其次,小说的内容开始具有世界性题材,即文中涉及的同性恋与艾滋病。最后,小说表现的主题是具有人类普遍性的爱情。在DannyBoy中,云哥在照顾丹尼时,感觉到了爱与被需要,并因此实现了对身份认同的超越。在TeaForTwo中,“我”与安弟的美好爱情,更是揭示了人类的一种共相:同性恋是不分种族与国籍的,爱也是不分性别与种族的。在同性恋世界中,他们不再去追问“我是谁?”,是中国人也好,是美国人也罢,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想要寻找到爱,寻找到一个同性的伴侣。
从大陆到台湾,再到美国,白先勇实现了两次身份的转变,并最终站在世界主义立场上,实现了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超越。他的这份独特人生经历,是时代与社会共同造就的,但也必然能够给当下的移民群体提供借鉴。
注释:
①白先勇:《树犹如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85-386页。
②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第40页。
③④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217页,第229页。
⑤⑥⑦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2册),花城出版社,2009年,第104页,第14页,第20页。
10.3969/j.issn.1673-0887.2017.05.006
2017-03-30
许子斌(1991— ),男,硕士研究生。
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6YJA751015)
A
1673-0887(2017)05-0025-05
责任编辑:庄亚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