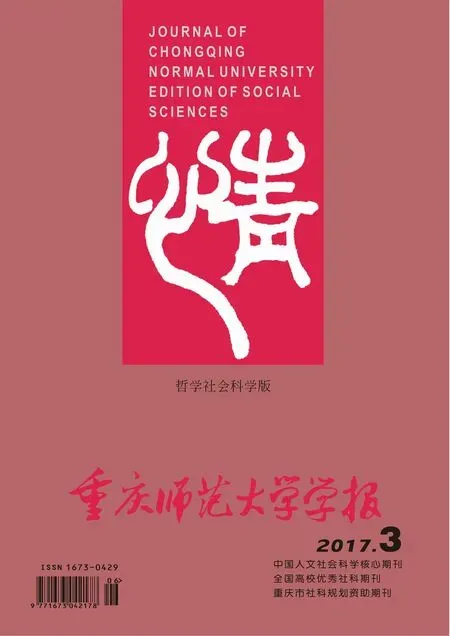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生态性镜像
2017-03-28李若岩
李 若 岩
(重庆师范大学 党委宣传部,重庆 401331)
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生态性镜像
李 若 岩
(重庆师范大学 党委宣传部,重庆 401331)
将“生态”“镜像”这组概念及其方法引入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研究领域,主要探讨保护、培育、传承民族民间文艺的理念和方法,从而着力解决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出精品的问题。少数民族民间文艺之镜,表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状态、折射了各少数民族的变迁景象;并在与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地理甚至民族关系等因素的辩证统一联系中观照着少数民族人民的思想、经历与畅想。对此,可以从生命性、逻辑性、系统性、发展性等角度来把握和讨论。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生态性;镜像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我国少数民族能歌善舞,长期以来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艺成果,这是我国文艺的瑰宝,要保护好、发展好,让它们在祖国文艺百花园中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1]从古至今,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在广阔的历史舞台和社会生活中,创作产生了丰富多彩、脍炙人口的民间文艺作品。这些作品是少数民族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朵朵奇葩,也是中国文化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发掘、催生、培育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精品就成为当代民族文艺工作者及其研究者必须要面临的课题。
一、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镜像性与生态性
将“生态”“镜像”这组概念及其方法引入以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研究领域,以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文艺为观测案例,研究少数民间文艺的生态性镜像,主要探讨保护、培育、传承民族民间文艺的理念和方法,着力解决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出精品的问题,从而为民族民间文艺传播力的提升凸显“内容为王”的传播前提。
这里必须要阐释的是“生态性镜像”这一概念和范畴。先说说“镜像”。古今中外的很多作家、艺术家以及文艺批评家们,大都谈到了文艺与人的关系。但说一千道一万,文学艺术是人学,它表现人、发展人。这一命题建构于文艺理论的框架之中。在此基础上,我们引入“镜像”这一概念来理解少数民族民间文艺与各民族人民的关系就比较容易了。简单地说,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犹如一面镜子,用生动形象的文艺方式,观照了各少数民族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表现了各民族人民的生活状态和进化历史。镜中之像的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对于少数民族人民来讲,是极为亲切的。因为这里的镜中之像聚焦了少数民族人民自身的生存状态和未来之愿景。在这面镜子之中,各民族人民既可以从不同角度看到他们自身的影子,又可以发现其中的某些元素真切地存在于他们自己民族的生命之中。
其次,要谈谈“生态性”。“生态学Ecology一词源于希腊文‘oikos’(原意为房子、住处或家务)和‘logos’(原意为学科或讨论),原意是研究生物住处的科学。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黑克尔(Haeckel)首次为生态学下的定义是: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2]1从黑克尔的解释及其学科后承者的理论建构中,我们可以引申出“生态性”这一概念,那就是——具有生态的特性,即:生物与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
把“生态性”这一概念引入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研究领域,就是要厘清少数民族民间文艺产生和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要深度解析少数民族民间文艺与其产生、传承、流变的外部环境和因素的辩证统一关系。具体而言,就是要把少数民族民间文艺放在多维生态系统中考量、观照。这里的多维生态系统包括:时代、社会、人口、大众、生活、民俗、文化、历史、地理、本民族、其他民族等关联的领域,创作、展演、研究、批评、传播等关联的环节,其他民族文艺等关联的族别文艺,以及其他元素。
由上述可推,“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生态性镜像”这一概念所表示的范畴为:少数民族民间文艺之镜,表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状态、折射了各少数民族的变迁景象;少数民族民间文艺之镜,不是简单的、机械的反映、模仿少数民族人民的社会生活,而是在与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地理甚至民族关系等因素的辩证统一联系中观照着少数民族人民的思想、经历与畅想。对此,可以从少数民族民间文艺镜像的生命性、逻辑性、系统性、发展性等角度来把握和讨论。
二、少数民族民间文艺镜像的生命性
在生态性视野中考量少数民族民间文艺镜像,首要的表现力就是其生命性。民族民间文艺镜像的生命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时间维度。少数民族民间文艺从古至今跨越了几千年的历史。这期间,各族系虽然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族系分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民族融合,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自然灾害。但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存在和发展仍然长盛不衰,其艺术魅力历久弥新。比如: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深刻的思想性和鲜明的艺术性依然吸引着当代的青年人。
二是类型维度。少数民族民间文艺从广义上说,是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和审美需要而创造出的属于自己的艺术,它涵盖了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戏曲以及民间工艺等多个艺术种类。从狭义上讲,有的学者也把它界定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其主要类型有少数民族民歌、民间长诗、民间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说唱文学、民间戏剧文学等。而其中每一类型又有若干种文学形式。比如:少数民族民歌包括创世歌、劳动歌、生活歌等少数民族古歌谣,也包括劳动歌、生活歌、时政歌、礼仪歌、情歌、谚语。再如:少数民族民间长诗包括少数民族创世史诗、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少数民族哲理诗、少数民族经诗、少数民族叙事诗等类别。
三是当在维度。这就涉及到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当下状态。从整体上看,当前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与传承的状态良好。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首先,正如前面所述,少数民族民间文艺是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满足自身的各种需求而自发创造出的属于自己的艺术。因此,少数民族人民一定在,也一定会创造出符合当代人精神需求的民间文艺作品。其次,在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今天,我国正从政策、资源、平台等方面保障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挖掘、传承。比如:于2016年8月16日至9月14日在北京举行的由国家民委、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呈现了多部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精品。再次,有许多理论家、学者都热衷于从事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批评和研究工作。大量有关的研究作品正极力丰富和发展着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理论,从而更有效地观照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发展。
三、少数民族民间文艺镜像的逻辑性
在逻辑学中,有这样的命题——设定A是条件、B是结论,如果由A可以推出B,同时也可以由B推出A,当然如果没有A,则一定也没有B,那么我们可以说A是B的充分必要条件,或者说B的充分必要条件是A。
在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研究中,也可以从充分必要条件的角度来考量少数民族民间文艺之镜的生态性。这样的考量首先要对上述命题中的A、B进行代换。设定A为某民族的某种历史文化、传统民俗以及族系基因,B为该民族的民间文艺的某种形态,对一些少数民族而言,则意味着A、B的同时在场。即:有某民族的某种历史文化、传统民俗以及族系基因,则一定有该民族的民间文艺的某种形态,反之亦然。
这样的现象,在少数民族民歌中并不少见。其中的少数民族礼俗歌体现得尤为典型。少数民族礼俗歌是与各民族的各种礼节、各类仪式相关的民间歌谣,它往往要融入人生的重要节点或重大仪式,包括满月、婚嫁、乔迁、宴宾、祝寿、远行、丧葬等。它一定会关联着少数民族的重要礼俗、重大祭典,有的甚至就是某一仪式的不可或缺组成部分。如很多少数民族都有哭嫁歌。典型的土家族姑娘在出嫁的时候,按照该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民族习俗,都会哭嫁,都要唱“哭嫁歌”。她们“哭”“唱”并举,作为迎接自己婚姻这一人生大事的方式。“假如出嫁时哭得不动人,往往会被人耻笑。”[3]353可以说,婚嫁习俗创造了“哭嫁歌”;而“哭嫁歌”显现了少数民族的婚嫁习俗。再如藏族人民的祝酒诵词(亦称“酒歌”)。按照藏民族的礼节习俗,藏族群众在参加各类节庆庆典或重大仪式的时候都必然会饮酒作歌。这其中的“歌”就是祝酒诵词。在藏民们看来,如果不唱酒歌是极为失礼的。敬酒时,“若不唱,受酒者可以拒绝饮用。敬酒者敬上酒,受酒者接过酒杯,即可要求敬酒者唱酒歌,有时敬酒者斟满杯中酒,走到宾客前即开始唱酒歌,唱到一半时,再将酒杯敬上,唱完酒歌再履行弹酒仪式及饮酒”[4] 37-39。可见,各类节庆庆典或重大仪式产生出了祝酒诵词;而祝酒诵词呈现了少数民族的礼俗状态。
几千年来,各民族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活动中自发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作品。这些民间文艺作品一方面适应了各民族特定的重大庆典和人生节点,成为了这些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携带了各民族群体的历史传统、伦理判断、生活态度、生命价值和民族基因。换言之,正是各民族具有了特殊的文化传统和礼仪习俗才催生出了许多优秀的民间文艺作品;而这些民间文艺作品呈现出了各民族特有的文化意蕴和民俗风貌。这正是少数民族民间文艺之镜显示出的双向推演逻辑。
四、少数民族民间文艺镜像的系统性
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并非是孤立的产生与发展的。它和其外部环境与因素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这种相互关联就形成了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生态系统。这是生态学给我们的启示。将少数民族民间文艺放在其生态系统中研究,就是要考量系统中各成分或要素与民间文艺之间的特殊联系。这里主要探讨几个处于一级“营养级”的要素。
一是民族历史纬度。这既包含了某一民族的某一民间文艺所处的民族时代,也包括了该民族的历史传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民族中,对文学民族性的理解和解读有很大不同。”[5] 5-10这是因为民族属于历史的范畴。它是随时间在不断的变化着的。如:蒙古语族诸民族在古代有蒙古、匈奴、鲜卑、乌桓等族,而跨越历史到了今天,则主要涵盖蒙古族、达斡尔族、土族、东乡族、保安族等。在历史的长河中,民族的分化和融合等使得民间神话等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类型的母题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二是地理纬度。“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的民间文艺风貌。在少数民族史诗中有一类典型的民间文艺现象。北方和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中都产生了许多史诗。但单从整体上看,其反映的内容截然不同:北方民族多英雄史诗,而南方民族多创世史诗。前者如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等;后者如苗族的《开天辟地》、壮族的《布洛陀·造天地》、白族的《创世纪》等。这种差异性与各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与环境有关。北方民族大多属于草原文化圈,他们逐水草而居,游走过活。为获取生活资料,各民族乃至各族系之间纷争不断。这使得人们呼唤、仰慕草原上的英雄。所以才会有英雄史诗。而南方民族大多处于山地稻作文化圈,生活资料的获取不需要游走,其方式相对稳定。各民族靠天、靠地吃饭,其关于天、地以及作物等的追问就会更多。所以才会有创世史诗。
三是民俗事象纬度。各少数民族人民常常将各自民族中的各类民俗事象、民俗活动放进民间文艺作品中,对其进行凸显、探源、阐释和歌颂。这里涉及两类民间文学类型,一是少数民族风物传说,如:鄂伦春族的《兴安岭和甘河》,彝族撒尼人的《石林》,布依族的《神剪》,朝鲜族的《三胎星》、《金达莱的传说》,白族的《望夫云》,维吾尔族《姑娘梳小辫和葡萄的由来》,回族的《巴里坤龙马的由来》,仡佬族的《首乌的故事》等;二是少数民族习俗传说,如:水族的《鱼姑娘》、布依族的《花米饭》、鄂伦春族的《乌娜杰逃婚》、畲族的《赤郎的故事》、哈萨克族的《狼姑娘》、纳西族的《火把节的由来》、哈尼族的《米色扎》、傣族的《泼水节》等。
四是崇拜与信仰维度。被称为“中国戏剧活化石”的傩戏,在少数民族民间也大量的存在。少数民族傩戏这种文学艺术形式,综合了少数民族图腾崇拜、民间信仰、历史文化、民间宗教、传统民俗、民间祭祀、民间歌舞、民间戏曲等元素。如:藏戏、布依族地戏、仡佬族地戏、壮族师公戏、彝族撮泰吉、土家傩戏、门巴戏等,各有异彩。其中,藏戏融合了藏族古老的祭祀仪式、民间崇拜以及宗教信仰,形成了多个艺术流派的藏戏系统,含纳广阔、影响深远。“1958年四川巴塘县业余藏剧团在昆明参加西南地区民族文化工作会议,演出了传统藏戏,被当时指导会议的夏衍赞誉为喷香吐艳的奇花——‘雪山上的红牡丹’。”[6]1
五、少数民族民间文艺镜像的发展性
动态性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特征。只有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有序运动才能促进系统的稳定。这就是说生态系统是在运动中保持平衡、促成发展。将这一观念运用于少数民族民间文艺之镜的研究,就是要探讨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
一是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发展需要不断地创新、不断地演绎,也需要在新的时代融入新的内容、新的理念、新的阐释。这是因为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并非是固定的、僵化的。它是具有开放性、变异性、口承性的艺术形式。我们可以举《阿诗玛》为例。1954年,《云南日报》发表了黄铁等人搜集整理的彝族撒尼人的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但《阿诗玛》产生于母系制时期与父系制时期之间。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极为漫长的历史时期。经学者们的研究,认为其核心内容在产生时就基本具备了雏形。然后,这个故事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被世世代代的撒尼人口耳相授、口口相传,不断地被增添进了新的内容、新的细节、新的思想。所以,我们说《阿诗玛》既是古老的艺术又是年轻的长诗。
二是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以及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民族山区所孕育的、并隐性存在的原生态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与民俗文化,也在经历着现代文明转型时期的阵痛。很多有价值的原生态文化现象及文明形态在逐渐的消亡。民族民间文艺工作者要将关注的眼光锁定在这些逐渐消失的文化生命上,要立在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站位上,真正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边远的民族山区,通过田野调查等方式,寻访、挖掘有价值的原生态民间文艺作品和民俗文化线索,尽可能多地打捞、收集原生态歌、词、戏文以及民俗文化资料,力争占有大量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并对这些第一手资料,进行真伪辨析、价值评估、分类整理和系统建档。
三是注重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生态系统内部诸要素的培育。因为这些要素都会对民族民间文艺的发展起一定的作用。除了前述中所提到的民族传统、历史文化、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民间民俗、崇拜与信仰等,当然也还有其他没有被较多关注的要素。这些要素如果都能得到较好的呈现与发展,那么其发挥的正向效能就会更高。在这样的格局中,与之相关联的少数民族民间文艺自身也会得到壮大。民族民间文艺工作者要做的,就是要系统挖掘各少数民族在民族文化、人文地理、传统习俗等方面的个性,使其民族性更加凸显。
四是发展少数民族民间文艺要更加注重原生态,要坚定文化自信并坚守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关注世界和时代的脉搏。“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要让各民族的艺术品格得到张扬,从而助推中华文化成为世界文化坐标系中的焦点和热点。
[1]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2).
[2] 尚玉昌.生态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 土家族简史编写组.土家族简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4] 岗措.藏族酒歌与酒文化[J].中国西藏,1996,(3).
[5] 朝戈金.文学的民族性:五个阐释维度[J].民族文学研究,2014,(4).
[6] 刘志群.藏戏与藏俗[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石家庄: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
[7] 马学良,梁庭望,张公瑾.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8] 梁庭望,黄凤显.中国少数民族文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
[9] 赵颖.逻辑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左福生]
On the Ecological Image of Folk Literature and Art of Ethnic Minorities
Li Ruoyan
(Propaganda Department,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401331, China)
The “ecological” and “image” this concept and method into the minority folk literature research field, mainly discusses the ideas and methods of cultivation,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folk literature and art, and efforts to solve the ethnic minority folk art quality problems. The minority folk art image, performance of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and reflect the minority people’s change of scene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nd with the ethnic history, culture, customs, geography and ethnic relations of factors such as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contact as minority people’s thoughts, experiences and imagination. In this regard, we can grasp and discu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logic, system and development.
ethnic minority; folk literature and art; ecological; image
2017-02-23
李若岩(1980— ),男,重庆垫江人,重庆师范大学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民俗学。
2016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培育项目(编号:2016PY58)“习近平传播思想视阈下民族民间文艺传播力提升路径研究”;2016年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编号:16SKGH050)“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生态性镜像与审美性传播研究”。
I22
A
1673—0429(2017)03—005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