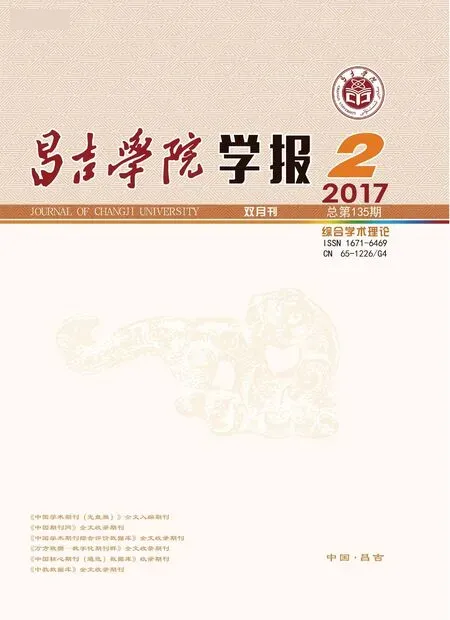男权社会的“话语霸权”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和塑造
2017-03-28王凌月
王凌月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男权社会的“话语霸权”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和塑造
王凌月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近来,随着学界对身体研究的关注,有关女性身体的研究越来越多,但在一个男性“话语霸权”的社会里,女性的身体是如何被规训和塑造的?文章先从中西方哲学、文学、神话等文化观念基本来源的角度分析了在男权社会文化中建构起的女性身体,继而分析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疾病的话语建构和男权“凝视”下女性眼中的自我与女性当代文化适应中的焦虑与风险,得出了男权社会的“话语霸权”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场域中对女性身体的深刻规训和塑造这一结论。
男权社会;话语霸权;女性身体;规训和塑造
一、女性身体被建构在男权文化中
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话语建构主要来源于哲学、文学和神话等人类观念的基本源头,并同时表现在中西方文化中。
(一)西方男权文化建构中的女性身体
身体问题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持久主题。西方社会科学普遍接受笛卡尔的观点,认为身体和心灵存在严重的对立,二者之间没有互动。[1]这一理念后来被延伸出很多相关的二元对立:理性—感性,太阳—月亮,精神—身体,男人—女人,这些二元对立的概念最终导致了父权文化价值观中对女性的性别歧视。[2]在有关女性特质的问题上,福柯认为,女性特质是男性欲望和权力的再现。在这种认识下,女性身体不是理性机器的肉体,而是被权威操纵的肉体,女性的特质通过男性创造的机制得以确立。性别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性别特质却是文化建构的结果,权力关系能够通过对性别特质的塑造来实现对女性身体的控制。这样看来,女性身体是西方文化的某种隐喻,蕴含着男权主导下西方社会的身体政治和秩序规范。[3]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虽是一部描写特洛伊之战的战争史诗,但其中却不乏女性的身影。无论是以布里塞伊斯为代表的女俘作为一种“战争荣誉”的象征,还是以安德罗马克为代表的妻子和母亲作为战争苦难的直接承受者[4],或者是以海伦为代表的因美色、失贞、性诱惑而导致战争兴起的女性,这部西方远古的经典诗篇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要么是直接被当做财产,不能以女性的身份发出声音,要么就是弱势群体的象征,只能承受战争恶果,无法有效反抗,要么就被视为邪恶的化身,引发战争和失序。在这里,女性身体被认为是财产化的、弱小的、邪恶的或是充满诱惑的,会引起混乱和动荡的。而这种对女性身体的认识一直持续到西方现代文学。在西方现当代文学中,女性写作已然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女性身体开始从被动的凝视走向主动和公开,然而在西方现有的文学秩序里,女性虽然在反抗和颠覆男权社会文学观念中充满狂欢,但这种狂欢却始终有着一种躁动和焦虑。
西方神话在讲述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时,宣称夏娃是从亚当的左肋中取出的一根肋骨。这样的神话叙述告诉我们,夏娃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亚当的一部分,没有亚当就没有夏娃。在产生人类这件事上,亚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夏娃只是附庸。西方神话中这种将女性身体视为男性身体的一个部分,并认为在人类生育和繁衍过程中女性只是附庸的看法,充斥在基督教文化的西方社会中,并成为了西方社会对人类起始的最初记忆。童真女玛利亚因受圣灵怀孕而诞下耶稣,这个故事更是在基督教文化中被广泛接受,玛利亚也被赋予了圣母的形象,是基督教神学的一位重要人物,在欧洲广受崇拜,甚至还形成了玛利亚神学。然而,新约正典中却没有玛利亚的完整生平,对玛利亚着墨最多的《路加福音》也仅仅提及玛利亚领报和怀孕两件事,当谈到耶稣开始讲道时,玛利亚便隐没不现了。[5]《新约》中有关玛利亚的部分不仅十分简约,并且有时还会出现指代不明和相互矛盾的情况。有关玛利亚是如何感受神灵而怀孕的,圣经著作里也没有明确的交代,玛利亚的生平多见于伪经和圣徒传记。基督教尽管在后来的经典中不断地将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加以丰满和再造,但都不能改变玛利亚最初在基督教中的次要和从属位置。仿佛玛利亚的存在就是为了造就耶稣,当她完成耶稣诞生的使命后,便渐渐失去作用,从女性身体的意义来看,圣母玛利亚形象的塑造,证明了女性的母亲身份,和女性承担的孕育生命的使命。
(二)中国男权文化建构中的女性身体
中国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将儒家思想作为社会正统和主流的思想。从儒家哲学来看,“男女有别”和“男尊女卑”是建构人伦秩序的两条根本准则。[6]《礼记·郊特性》:“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在这里,“男女有别”被看做是父子伦常的根本、礼乐有序的准则和万物相安的所在。《周易·系辞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尊坤卑,故男尊女卑。用乾坤之位来定男女之位,儒家就此而奠定了其性别伦理的基调。汉代董仲舒在男尊女卑的基础上,开始用阴阳来定男女,认为“夫为阳,妻为阴”,由此便开始了在中国哲学中男为阳女为阴的历史,女性的身体被深深地上了“阴”的概念,并时常被视为不祥之兆。这种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不仅存在于家庭领域,还普遍存在于政治、生产等其他社会领域,并且主导中国社会两千余年。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水浒传》和《红楼梦》,处处透露着一种利用女性的“通奸”罪名来隐喻对女性的性压抑,在这种有违伦常的空间里,在表达对女性身体压抑的同时,还不忘往其头上按一个通奸罪名的叙事方式,显示了在一个“男权社会”的话语空间中,女性身体和心灵受到的双重摧残。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表现两性关系时,主角和主体大多数都是男性,女性大部分只是匿名的逃逸者。在消费文学兴起后,女性成为主角,但这个主角地位的获得却是可疑的。这种可疑或许源于在一个消费时代中,女性也多是消费的一个部分而不是消费的一个主体。而在有关现当代的“身体写作”问题上,文艺批评家常赋予贬义色彩,因为文艺学是社会形态的一个部分,受到男权文化的限制。[7]
中国的神话传说,既有黄帝、炎帝、蚩尤等男性神灵,也有女娲、西王母、嫦娥等女性神灵,这些神灵共同构成了中国完整的神话世界。其中,女娲是作为人类始祖而存在的。无论是黄土造人传说,还是女娲与伏羲结为夫妻共同繁衍人类的传说,这一神仙形象都与人类起始有着密切的关联。而这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女娲“人首蛇身”的形象,为何人类始祖的形象要配以蛇身?汉斯·比德曼从象征的角度论述到“蛇的形状与男性生殖器相似,故带蛇女人的形象总是涉及到女人与有生殖能力的男人之间的关系。”[8]这说明,女性神灵的身体在塑造过程中或许没有摆脱过与生育有关的命运。并且在中国神话中,女神也多是以男神配偶、母亲、女儿或下属的身份出现。
二、男权“凝视”下女性眼中的自我及其对身体的规训和塑造
在一种男权文化的话语建构下,女性意识受到限制和压迫,女性对自身身体的认识便处于一种对男权话语的“凝视”下。在一种对男性话语权威的“凝视”中,女性眼中的自我及其对身体的塑造都是男性所期望和规训的。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身体的社会性。“女性特征”不仅包含着形体、发式、五官等体态特征,还包含着温柔、依赖、软弱、顺从等性格特征,这些特征并不是来自于女性的自然属性,而是来自于社会及其文化。女性主义关于身体的建构论观点认为,女性的身体是由男性的标准而定的,是附属的,次等的,女性身体的劣势在生物学和社会文化中被男性的标准合法化。
身体与父权制观念有着深刻的关联,美国学者凯特·米莉特提出的“父权制论”观点,认为男女的从属之分是社会把女性置于父权制统治下的结果。[9]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里生产出的关于女性的知识,不仅为男性所推崇,更是为女性自身所接受和认可。当这种关于女性的看法超越了性别的差异而成为一种普遍存在时,女性对自我身体的认识就深刻地打上了男权文化的印记。
男女两性身体构造的差异,尤其是性器官的差异,使得女性无法像男性一样通过暴露在外的性器官来认识自我的身体,因此,无论是对于男性还是对于女性本身,女性身体都是充满神秘和隐晦的,女性羞于观察自己的身体,被教导要表现出女性应有的气质,如顺从、软弱、温顺等,这些气质深深地为女性所认可和接受,并形成女性对自我身体气质认识的基础和来源。而这些气质恰恰都是由男性所定义的。由于女性无法对自身的身体形成高度的认识,因而她们对自我身体的看法始终无法超越男性的观念。即便女性渴望自由,寻求自我,但始终无力改变已经深深被束缚在一个男性“话语霸权”所建构的性别文化牢笼的这个事实。
在此背景下,女性关于自身形体的塑造,便处处透露着她们对男权话语的“凝视”与恪守。
男性审美话语对苗条体形的认可和推崇,形成地对女性身体的评判标准是苗条匀称。在这种源于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欣赏和期待的观念的影响下,女性越来越强烈地关注自己的体重,“减肥”成为女性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个话题。然而女性这种对自我身体的“减肥”暗示实则给女性带来了很多负面问题。它不仅影响女性的饮食,更会影响到女性的社交、自尊、积极性、对体育的认知和看法等很多方面。使得众多女性长期处在一种不合理的饮食状态,甚至很多女性会面临厌食症的困扰;身材肥胖的女性在社交中缺乏自信,也在身材苗条的女性面前自尊受挫,导致其在工作、生活的日常社交中缺乏积极性或是逃避社交;女性所崇尚的健身和瑜伽等体育活动,也多数都是为了减肥而存在。
同时,人们对于美貌的认知也深受男性话语标准的影响。男性审美制定的女性美貌的标准在不同的女性体态上,有着不同的要求。一般而言,面部、胸部、臀部、锁骨、手足等是一个女性是否性感和美丽的关键部位。男性美貌标准要求女性面部要立体,要丰乳肥臀,锁骨要明显,手足要白皙纤细。因此一个五官正常但却并不符合男性标准审美的长相,在很多现代女性的眼里已经成了一种劣势。这种劣势给女性的生存竞争增加了很多负面风险,比如求职、求偶、社会发展等,因此越来越多的女性对各式各样的整形术趋之若鹜。在一个“美丽制造”大行其道的社会,面部整容如隆鼻、拉下巴、割双眼皮、去眼袋,丰胸、肥臀,美甲、美足等等,每一样整形术都存在其危险性,稍有不慎便会毁容损身。然而众多女性不顾整容造成一系列恶性后果的既成事实和高度风险,义无反顾地走进修身美体的大军中,期待自己可以通过整形术获得美貌。
再来看服饰。女性服装与饰品的美丑往往是由男性来决定的,先说服装,时下流行的聚拢式文胸、露肩式上衣、紧身裤、丝袜、高跟鞋等凸显女性身材的服装,都是符合男性审美话语的身体标准的。这些服装将女性身形中被男性审美注意和强调到的部分凸显出来,让女性变得性感、妖娆。其次是饰品,当今,头饰、耳饰、手饰、腰饰、脚饰等女性身体各个部位的饰品日益繁多、华美,不管是为了凸显某个部位,还是为了提升品位和气质,女性佩戴饰品都是为了使自身符合美丽的定义和标准,而这一定义和标准往往是由男性审美话语来确定的。
在一个消费时代里,任何消费群体都在被建构之中。人们的消费已经不再来源于基本需要,而是源于一种被建构的需要,而且这种被建构的需要的重要程度早已远远超出人类的正常所需。将人类自然的身体作为一种过度消费的对象,已经成为消费时代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在这个消费时代里,女性学会了使用各种化妆品和装饰品来包装自己的身体,她们按照社会的既定审美和时尚让自己的体重、身高、化妆、休闲甚至是生育来跟随消费的步伐。这种消费文化和理念,让女性在一个失去理性思考的审美权威中不断沉沦,怂恿更多的女性消费者通过健身、美容、饮食、整容等来塑造自己美好的身体。而这其实是主流文化对女性身体更为严苛的控制,当下的消费文化正在对女性身体进行着一种类似标准化的塑造和管理。这些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在关于女性审美的议题中,美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深刻关联,以及审美标准、科技伦理、经济道德、政治权力等复杂社会因素的深度博弈。同时,在一个过度消费和快餐消费的社会中,人们一边享受着越来越精致的物质和精神产品,贪图着日新月异的诱惑,一边又在飞速地、不停地抛弃着已有的诱惑,随着消费重要性的日益增长,人们的价值观、日常生活、社会角色等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这就使得现代人在一个狂躁的消费文化中遭遇着各类认同的危机,女性在这些危机中,也不能幸免。
三、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疾病的话语建构
本部分主要是从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疾病的话语建构这一细节来体现其“话语霸权”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和塑造。选取了女性更年期综合症和女性厌食症这两种疾病来展开讨论。
(一)女性更年期综合症的话语建构
人类疾病的话语建构并不是仅就生理疾病而言的,很多疾病解释的建构过程都与社会及其文化深刻相关,特别在很多女性疾病上。以女性更年期为例,更年期原本是一个一般性概念,是指人从中年向老年的生命转折期或过渡期。然而一提到更年期这个词,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女性更年期综合症,仿佛“更年期”这三个字具有了性别倾向,特别地指向女性,其症状包括女性月经紊乱、出汗、失眠、情绪不稳,等。很多论断将更年期综合症视为是女性独有的,并且认为这些病症多数是由女性身体导致的。
但是,医学的认识和实践以及大众文化的传播和塑造在女性更年期的话语建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0]
医学上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更年期综合症”,这个概念将女性的更年期直接定义为一种医学疾病。其治疗方法和手段总体来说有两种,一种是切除女性生殖器官的去性化手段,另一种是通过补充雌性激素来加强女性性别特征的手段[11],这两种手段在女性更年期综合症的治疗中都很普遍。
然而有意思的是,在女性更年期疾病实践中,从业者大多数都是男性。女性更年期综合症的治疗,依靠的是男性医生的理解和判断。
在一个知识化、科学化的时代,人类在自身预期寿命和很多疾病的治疗中都有了明显而全面的提高,很多疾病在全球范围内消失,这些无疑都与现代医学的发展及其威力有关,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在对抗和控制疾病方面,医学有着不可替代的权威。这种权威促使医学以一种更加严厉的姿态来掌控对人类疾病的解释和治疗。在一种强大的医学权威笼罩下,女性更年期的问题从其产生的原因到社会对其的态度上都越来越问题化、负面化和污名化。戈夫曼认为,污名化源于刻板印象,常常出现于医疗背景中。其过程必然带有社会控制的因素。[12]将某些疾病污名化和问题化,可以为这些疾病患者的某些行为进行合理解释,通过这种所谓的合理解释来达到社会对其的理解和接受,进而达到减少冲突和社会控制的目的。并且,由于女性疾病的医学实践中男性从业者占绝对的优势,就使得女性的更年期健康问题长期为男性医学权威所掌握,这种带有明显性别化的权威医学体制均会给女性认识自身和其身体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大众传媒作为现代话语最基本的工具,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由大众传媒构建的文化意义具有明确的导向,它在对社会性别意义的建构上更是意义非凡,它一方面利用意识形态赋予男女两性不同的性别气质和行为规范,另一方面又不断强化和主导着这些标准和规范。[13]关于女性在大众传媒中的待遇,有学者提出了“象征性歼灭罪”的概念,即认为大众媒体和文化传统忽视、贬低和谴责女性。[14]在这种传媒背景下,我们来看一下更年期妇女的处境。
临床医学表明,处于更年期的妇女,经常出现失眠、情绪失控、多疑等症状,但在不同个体的身上会有很明显的差异,有些妇女症状严重,但有些妇女则很轻微或者根本没有。然而在很多影视剧作品中却常常忽视这种差异,并一再将更年期的妇女塑造成制造家庭冲突和矛盾的形象。久而久之,在这种强势传媒的大力塑造下,大众便形成了对更年期妇女的刻板印象。而处于更年期的妇女,面对媒体所塑造的自身的形象,却处于一种相对“失语”的境地,无法为自身遭遇到的这种状况作出应有的辩护。
同时,很多妇女在进入更年期以后,身体和容貌较年轻时有很大的变形和差异,在主流消费市场已经失去优势地位,成为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但在一些保健、美容、塑身等消费领域,更年期的妇女却成为宠儿。很多针对更年期妇女的广告,将更年期妇女某些方面的问题极端化和扩大化,这种广告叙述不仅为普通民众所接受,更为更年期妇女所接受,很多更年期妇女会按照这些广告的指引来塑造自己的身体。由一些针对更年期女性身体的传媒广告,来指引自己应该对自身身体作出何种安排和改变,这种行为,一方面固然是源于更年期妇女的主观自愿,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视作是她们所作出的“无奈选择”。因为她们在一种企图改变众人对自身看法的压力下,不得不遵从传媒的权威。
由大众传媒构建起的更年期妇女,不仅整体形象很差,而且身心均处于危险期。妇女若想安全度过这一危险期,得到身心健康,就必须听从大众传媒的指引和安排。在现代社会的文化规则下,更年期妇女的形象已经被塑造成型,任何一种媒体形式都参与了这项塑造工程,随着多媒体时代的到来,媒体塑造和诠释的更年期妇女形象不断被加工再造,媒体受众便在这种印象里作出自己的观念和行为选择。
(二)男性“审美权威”下的女性厌食症
男权社会所建立的审美标准,处处彰显着对女性身心的规训。权威审美观念将女性视为美丽、爱情和丰饶的象征,美貌“神话”让人们将女性理解为:美丽的女人是所向披靡的,外表是女人最好的风情资源。“女为悦己者容”的观念使体态和容貌成为女性生存的一个部分,更是女性对自我进行评价的一个标准。当男性普遍认为女人“以瘦为美”时,女性便将男性的这种评价标准当做自我塑造的标准,这常常会使女性压抑自我,在一种压抑的矛盾中,女性往往会出现身体的异样和人格的扭曲。神经性厌食症就是一种由长期的社会心理因素引起的食欲不振,是一种精神和躯体疾病。发病主要以女性为主。[15]厌食症多数表现为一种生理症状的疾病,但它与饮食节制的观念有着深刻的关联,这种疾病不仅存在于某一区域,而早已演化为一种世界性问题,在年轻人特别是富裕的年轻女性中开始普遍出现与饮食有关的疾病。[16]
厌食症的世界化现象让我们知道,一个男权社会在对女性进行评判时,绝不会只看她们的成就,在关注女性成就的同时,他们一定会关照女性的外表。在这种压力下,女性不得不在任何时候都关注自己的外表,以期达到社会成就和外表的双重肯定。所以维持身材的苗条就不再只是个人的爱好选择,而变成一种社会需要,节食减肥就成为众多女性的选择,而一旦开始强迫自己节食,就会陷入一种拒绝进食或呕吐的模式。
厌食症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公共话题,同样也无法躲开大众传媒的锐利眼光。许多减肥药品和瘦身运动的广告充斥女性消费市场,但因其对身体结构和机能迅速而又粗暴式的改造,导致的其他女性身体疾病至今仍然让很多女性记忆犹新。在女性消费领域,存在着一个由话语霸权、医学权威、大众传媒合力作用下的商品市场。在这个市场的不同领域,存在着对女性身体的不同解释,每一种解释都按照各自的需要建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男性话语的霸权在大众传媒的协助下,于复杂的社会背景中控制着女性的身体,影响着很多女性疾病的产生和发展。
四、女性在当代文化适应中的焦虑与风险
女性在当代文化适应中的风险和焦虑主要表现在科学技术、消费文化和大众传媒中。
在女性审美这个议题里,不仅包含了美学,还包含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深刻意蕴,女性审美里至今仍铭记着社会权力的印记,审美中蕴藏着丰富的政治学意涵,更是一种性别政治的表达。[17]一个由男性制定的审美标准与其说是女性自我认可的来源,不如说是女性跌入忧虑和痛苦的巫咒。女性标准形体的典范,除了能给人带来美的感受外,还能给女性带来深深的紧张和焦虑。女性的美貌神话在一种男权主义的“凝视”下,渐渐内化为女性对自身的规范和要求,并且她们在这种规约下严格地控制着自己的形体和言行。在适应当下全球化文化的过程中,被科学技术、消费文化和大众传媒包围的现代女性面临更多身体上的焦虑和风险。
要即时迅速地改变自己的自然长相和形体,当然要依靠科技的力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样化的美容整形的新材料和新手段、减肥丰胸的新体验和新感觉。我们的身体已然摆脱了周遭自然环境和生物周期的规训,越来越遭受科学力量和技术力量的入侵。福柯有一个“社会技术”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技术在人类身体上的作用。“所谓‘社会技术’,指的是身体越来越成为一种我们必须去‘塑造’而不是简单接受的东西。就是我们作用于自身身体功能运作的任何类型的常规干预,以便用特定的方式改变其运作。”[18]在科学技术的指引下,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狂热地进入美容院、减肥机构、健身房,通过抽脂减肥、吸脂隆胸、打针吃药、换肤漂色等各种所谓的新技术、新手段来改变和塑造着自己的身体。这种对身体美的无限追求成为一些女性极端的生活方式,也让很多女性为了追求迅速改变自己的身体,变得越来越与自己的身体为敌。然而,利用科学技术手段改变自己的身体,无疑会让女性的身体面临更多的风险甚至是伤害。
大众传媒的力量无处不在。它以其独有的、容易被理解和接受的方式,不仅传播商业信息,更成为当今社会灌输文化价值观念的有力手段。传媒所提供的价值标准、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无一例外地对人类生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它塑造着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同时又不断地对其进行再生产和再塑造。它不失时机地引导和营造着女性审美文化的走向和氛围,也不断指示着男女两性如何提升自己的魅力。仅就女性形体而言,身材苗条的观念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媒体宣传,在一种不间断的媒体宣传中,由于有着“理想身材”的美女模特这种人物符号的存在,女性出于对自身身材的焦虑和恐慌,就会开始各种各样减肥计划,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甚至产生很多与此有关的其他复杂问题。而前文所述的有关女性疾病的话语建构和科技力量、消费文化对女性身体的影响与改造等问题,也无一例外都受到了大众传媒的深刻影响和引导。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身体都不仅仅是单纯的生理事实,任何社会都会通过各种文化手段、社会规范和权力支配对男女两性身体进行规训和塑造。身体与社会、文化、权力之间有着深刻的关联。身体,早已被深深打上了种种权力的烙印。就女性而言,女性关于自身形体的认识一直处于一种对男权社会“凝视”的“话语霸权”之中,一个男权社会所建立的女性知识,一直在一种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交织的复杂场域中不断地被建构和再造,从而严格又深刻地规训和塑造着女性的身体。这种规训和塑造使得女性无法自主地管理和经营自己的身体,更无法理性地对待自己的身体。她们只能在别人的指引下,自愿或者不自愿地对自己的身体加以改变和安排。
我们希望随着女性主义理论和身体社会学的发展,以及女性意识的不断解放,能够让女性不断地走向人格独立和理性思考,同时在男女两性的共同努力下,实现对女性身体的真正关怀和规范。
[1](美)布莱恩·特纳著.身体社会学导论[M].汪民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3-4.
[2]刘岩.女性身体的文化规约与意义重建—巴特勒和伊里加蕾的身体书写[J].外国文学,2015,(04):128.
[3]杨席珍.西方文化中女性身体及其媒介呈现[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6):96.
[4]陈戎女.<伊利亚特>中的女性[J].求是学刊,2008,(03):116.
[5]代国庆.新约伪经与圣徒传记中的圣母玛利亚[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4):24.
[6]杨剑利.规训与政治:儒家性别体系探论[J].江汉论坛,2013,(06):94,101.
[7]谢玉娥.当代女性写作中有关“身体写作”研究综述[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3):106.
[8]汉斯·比德曼著.世界文化象征辞桂林[M].刘玉红,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268.
[9](美)凯特·米莉特著,宋文伟译.性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45.
[10]吴小英.更年期话语的建构——从医界、大众文化到女性自身的叙述[J].妇女研究论丛,2013,(04):88.
[11]吴小英.更年期话语的建构——从医界、大众文化到女性自身的叙述[J].妇女研究论丛,2013,(04):89.
[12](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社会学(第5版)[M].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22.
[13]苏红.多重视野下的社会性别观[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120.
[14]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87.
[15]陈超然,卢光莉,耿文秀.女性神经性厌食症与其人格的关系[J].心理科学,2009,(06):1465,1467.
[16](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社会学(第5版)[M].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09.
[17]程勇真.从“贤妻良母”到“女汉子”:中国当代女性审美形象分析[J].中国美学研究,2014,(02):109.
[18](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社会学(第5版)[M].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10,211.
C913.68
A
1671-6469(2017)-02-0043-07
2016-12-22
王凌月(1990-),女,河南濮阳人,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历史与民族学系硕士生,研究方向: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