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体的风景*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风景之发现”之前的叙景
2017-03-28中里见敬
中里见敬
作为文体的风景*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风景之发现”之前的叙景
中里见敬
日本评论家柄谷行人的《风景之发现》,从“风景”——“自我”这一对应概念出发,论述了日本现代文学的形成问题。与日本文学相类似,在中国小说领域中,古代小说和现代小说的风景描写,也大相径庭。通过研析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中“风景之发现”之前的叙景,探讨古代小说和现代小说认识框架的差异及其与文体的关系。
风景; 文体; “风景之发现”; 小说
引 言
文体的历史……是通过文体表露出来的认识之历史。它更是文人的文学态度之历史,即持续选择某一种文体,结果很快导致与事物的变化发生倾轧,一旦自我破裂,便又要寻求重生。
高桥和巳(1931—1971)《六朝美文论》*[日]高桥和巳:《六朝美文论》,《高桥和巳作品集9 中国文学论集》,东京:河出书房新社,1972年,第61页。
日本著名评论家柄谷行人(1941—)在其经典之作《风景之发现》中,从“风景”及其相对应的“自我”这一视角出发,论述了日本现代文学的形成问题。我们来确认一下作者的主要论点:
虽然描绘的对象各异,但中世纪欧洲的宗教绘画与中国的山水画在观察对象的方式上却是相通的。山水画家在画松的时候,他画的是松这个概念,而不是在一个视点和时空中所看到的松林。“风景”只能是“由一个持有固定视点的人统一把握”的对象。山水画的透视法并非几何学式的,因此看似只是风景的山水画中并不存在“风景”。*行人译《定本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试译之《第1章风景之发现》(https://www.douban.com/note/486082894/) 原文为柄谷行人《風景の発見》(《定本柄谷行人集》1, 东京:岩波书店, 2004年)第17页。中译本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是根据《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1980年讲谈社版翻译的。因后来柄谷行人本人进行了修改,出版了2004年岩波书店版,现不采用赵京华译本,而采用了根据《定本》翻译的行人译文。
柄谷行人还把绘画和文学联系起来,指出:
通过绘画分析文学,我们就会明白,现代文学以主观性和自我表现为特征这一看法正好对应于世界由“一个持有固定视点的人统一把握”。几何透视法是一种装置,它不仅创造出客观还创造出主观。然而,山水画家所描绘的对象并非由一个主观统一把握。其中不存在一个(超越论式的)自我。以文学而言,如果其中没有一套透视法式的叙述方式,那么所谓现代的“自我表现”就无以成立。*行人译《定本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试译之《第1章风景之发现》(https://www.douban.com/note/486082894/)原文为柄谷行人《風景の発見》(《定本柄谷行人集》1)第18—19,20页。笔者对引文做了调整。
明治20年代(1887—1896)日本现代文学逐渐获得了“一套透视法式的叙述方式”,从而发现了风景——客观;同时又创造了自我——主观。因此,“所谓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这个装置一旦成形出现,其起源便被掩盖起来了”*[日]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12页。原文为柄谷行人《風景の発見》(《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东京:讲谈社,1980年)第21页。此文在定本中被删掉了。。柄谷行人进一步阐述道:
关于现代文学的起源,人们一方面从内面性或自我,另一方面从对象的写实这两个角度进行了论述,但是双方并非各不相干。重要的是这种主观和客观历史性地出现了,换言之,在根本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象征形式”(卡西尔)。而且,它是一套装置,使自身在确立的同时其起源又被忘却了。*行人译《定本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试译之《第1章风景之发现》(https://www.douban.com/note/486082894/)原文为柄谷行人《風景の発見》(《定本柄谷行人集》1)第18—19,20页。笔者对引文做了调整。
柄谷行人在另一篇《内面之发现》中继续论述道:
正如风景从前就存在一样,素颜本来就存在的。但是,这个素颜作为自然的存在而成为可视的并不在于视觉。为此,需要把作为概念(所指)的风景和脸面处于优越位置的“场”颠倒过来。只有这个时候,素颜和作为素颜的风景才能成为“能指”。以前被视为无意义的东西才能见出深远的意义。(这就是我称之为“风景之发现”的事情。)*[日]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46页。原文为柄谷行人《内面の発見》(《定本柄谷行人集》1)第53页。定本增补了最后括号里的句子。
本文将剖析中国现代文学这一认识性装置出现之前,即“风景之发现”之前的中国白话小说中的叙景及其与文体的关系,力图从风景描写这一侧面探讨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特点。
一、古典白话小说中叙景文体的确立
南宋刊印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保留了唐僧取经故事的文体原貌。下述引文中,树人国的情景出现在“尽是”、“又见”、“只见”、“又睹”等词语之后,行文采用平仄工整的以四字句为主的骈体。
同样,下面的叙景出现在“忽见”、“只见”之后,平仄工整,四字对仗,并以“茫”、“浪”、“光”字押韵。

也有不使用“只见”等标志词,而在叙事中直接描写情景的例子。如下面的例子,平仄对仗工整,“稀”、“飞”二字押韵。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风景描写,可谓对偶平仄工整的通俗骈体,但并没有从叙事文中独立出来。该话本属于从说唱到小说的过渡阶段,正如小松谦(1959—)所言“其叙事文为四字一句或六字一句、节奏单调、毫无文采的文言文”*[日]小松谦:《「現実」の浮上:「せりふ」と「描写」の中国文学史》(“现实”的浮上:“会话”与“描写”之中国文学史),东京:汲古书院,2007年,第124—125,225页。。明清白话小说中,常常被作为引导叙景的标志词“只见”,在上述引文中仍保留了动词的实际作用,因此“只见”的宾语仅限于简短的2个或4个小句。
到了明代后期刊行的世德堂本《西游记》,叙事和会话部分的白话文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风景描写则以诗赋体形式插入文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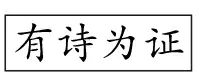
海外宫楼如上邦,人间歌舞若前唐。花迎宝扇红云绕,日照鲜袍翠雾光。
孔雀屏开香霭出,珍珠帘卷彩旗张。太平景象真堪贺,静列多官没奏章。
三藏下马道:“徒弟呵,我们就此进朝,倒换关文,省得又拢那个衙门费事。”行者道:“说得有理。我兄弟们都进去,人多才好说话。”(第39回)*《西游记(世德堂本)》2,《古本小说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金陵世德堂本影印,第977—978页。
明清白话小说中的风景描写为何采用诗赋这样的韵文呢?小松谦下面的论述颇有参考价值:
每逢情景描写时就出现赋或诗词,叙事文和韵文明显分工不同。换言之,叙事文缺乏描写情景的功能。上文提到了文言文中的散文不宜情景描写,情景描写主要通过韵文来完成。白话文也如此。情景描写由诗词或赋等韵文、美文来承担,这在中国是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与其说白话散文缺乏表现能力,不如说中国意念中的风景描写被固定在诗词的文脉中。*[日]小松谦:《「現実」の浮上:「せりふ」と「描写」の中国文学史》(“现实”的浮上:“会话”与“描写”之中国文学史),东京:汲古书院,2007年,第124—125,225页。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例子说明,说唱艺术中叙事描写和情景描写相互融为一体,并未分离开来。与此相反,白话小说的形式确立后,白话散文和诗赋韵文的功能也开始分化,情景描写由韵文承担。如此一来,与故事发展无关的叙景文章,逐渐被视为多余。明末文简本以及清代节略本出现后,描写情景的韵文部分甚至被删掉了。上面所引用的世德堂本《西游记》,三藏一行到乌鸡国的一段有184字;而在清代所刊的《西游真诠》中只剩49字:
师徒们在路上,那消半日,早到了乌鸡国城中。只见街市上,人物齐整,风光闹热。早又见凤阁龙楼,十分壮丽。行者请三藏下马……(第39回)*《西游真诠》2,《古本小说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年,乾隆四十五年刊本影印,第39回,第3叶b面。
可见从南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到明代《西游记》,再到清代《西游真诠》,这一叙景文体的演变,正符合白话小说文体确立和发展的过程。小川环树(1910—1993)从“散文化”这一视角出发,论述了从变文到白话小说的发展过程:
变文乃佛教文学,其特色在于韵文和散文的反复交替使用。由于讲述变文的俗讲僧脱离了佛教,加之宋代城市中勾栏的繁荣,促使说话艺术失去佛教色彩,而成为新的艺术。变文的手法最初用到说话艺术中(关于这一点并没有可以佐证的文献保存下来),说话逐渐朝散文化方向发展。明代白话小说还保留了很多韵文(或四六文)因素,这一点在《水浒传》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中很容易看到。这个阶段的白话小说已不是说话艺术的文本,而是模仿其形式的读本,但仍保留了前代的形态。《水浒传》到了明末清初金圣叹加工的七十回本,几乎看不到诗词和四六文的痕迹,可以说已经实现了散文化。*[日]小川环树:《变文と讲史》,《小川环树著作集》第4卷,东京:筑摩书房,1997年,第25—26页。最早刊于《日本中国学会报》6,1954年。后收于小川环树:《中国小説史の研究》,东京:岩波书店, 1968年。
小川环树的看法,与明代学者胡应麟在万历十七年序刊《庄岳委谈》中所谈颇为相近。
此书所载四六语甚厌观,盖主为俗人说,不得不尔。余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极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几不堪覆瓿。复数十年,无原本印证,此书将永废矣。余因叹是编初出之日,不知当更何如也。*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41《庄岳委谈》下,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第572页。
胡应麟说自己20年前看到的《水浒传》“尚极足寻味”,而20年后福建书坊刊行的文简本“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胡应麟为此感慨不已。下面我们看一下三种不同版本的《水浒传》对同一个场面的描叙:
1.容与堂本(万历三十八年[1610]刊)(文繁本,有骈文。【 】为夹批)
武松道,“我和你岀得城去,只要还我无三不过望。”施恩道:“兄长,如何是无三不过望。小弟不省其意。”武松笑道:“我说与你,你要打蒋门神时,岀得城去,但遇着一个酒店,便请我吃三碗酒。若无三碗时,便不过望子去。这个唤做无三不过望。”〔中略〕
且说施恩和武松两个,离了安平寨,岀得孟州东门外来,行过得三五百歩。只见官道旁边,早望见一座酒肆,望子挑岀在檐前。看那个酒店时,但见:
门迎驿路,戸接乡村。芙蓉金菊傍池塘,翠柳黄槐遮酒肆。壁上描刘伶贪饮,窗前画李白传杯。渊明归去,王弘送酒到东篱。佛印山居,苏轼逃禅来北阁。闻香驻马三家醉,知味停舟十里香。不惜抱琴沽一醉,信知终日卧斜阳。【可删】
那两个挑食担的仆人,已先在那里等候。施恩邀武松到里面坐下。仆人已自安下肴馔,将酒来筛。武松道:“不要小盏儿吃,大碗筛来,只斟三碗。”仆人排下大碗,将酒便斟。武松也不谦让,连吃了三碗,便起身。仆人慌忙收拾了器皿,奔前去了。武松笑道:“却才去肚里发一发。我们去休。”两个便离了这座酒肆,出得店来。此时正是七月间天气,炎暑未消,金风乍起。两个解开衣襟,又行不得一里多路,来到一处,不村不郭,却早又望见一个酒旗儿,高挑岀在林树里。来到林木丛中看时,却是一座卖村醪小酒店。但见:
古道村坊,傍溪酒店。杨柳阴森门外,荷花旖旎池中。飘飘酒旆舞金风,短短芦帘遮酷日。磁盆架上,白泠泠满贮村醪;瓦瓮灶前,香喷喷初蒸社酝。村童量酒,想非昔日相如;少妇当垆,不是他年卓氏。休言三斗宿酲,便是二升也醉。【都可删】
当时施恩武松来到村坊酒肆门前,施恩立住了脚,问道:“兄长,此间是个村醪酒店,哥哥饮么?”武松道:“遮莫酸醎苦涩,问甚滑辣清香,是酒还须饮三碗。若是无三,不过帘便了。”两个入来坐下。仆人排了果品按酒,武松连吃了三碗,便起身走。仆人急急收了家火什物,赶前去了。两个出得店门来,又行不到一二里,路上又见个酒店。武松入来,又吃了三碗便走。话休絮繁,武松施恩两个一处走着,但遇酒店,便入去吃三碗。约莫也吃过十来处好酒肆。施恩看武松时,不十分醉。武松问施恩道:“此去快活林还有多少路?”施恩道:“没多了,只在前面,远远地望见那个林子便是。”*《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传》2,《古本小说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第29回,第4叶b面—第7叶a面。
2.余象斗本(文简本,无骈文)
武松曰:“我叫你出城去,只要还我无三不过望。”施恩曰:“如何是无三不过望。”武松笑曰:“但遇酒店,便请我吃三碗酒。若无三碗酒时,便不过望。此是无三不过望。”〔中略〕
且说施恩和武松离了安平寨,径到孟州东门外来,行三五百步,早望见一座酒肆。那两个仆人已先铺下肴馔等候,施恩邀武松里面坐下,武松连吃了三碗,便起身离了酒店。未行一里,又见酒店。施恩武松两个坐下,仆人安排,武松连吃三碗,武松问施恩:“此去快活林还有多少路。”施恩曰:“前面林子便是。”*《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卷6,《古本小说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第12叶b面—第13叶a面。
3.金圣叹本(崇祯十四年[1641]刊)(文繁本,无骈文)
武松道,“我和你岀得城去,只要还我无三不过望。”施恩道:“兄长,如何无三不过望。小弟不省其意。”武松笑道:“我说与你,你要打蒋门神时,岀得城去,但遇着一个酒店,便请我吃三碗酒。若无三碗时,便不过望子去。这个唤做无三不过望。”〔中略〕
且说施恩和武松两个,离了安平寨,岀得孟州东门外来,行过得三五百歩。只见官道旁边,早望见一座酒肆,望子挑岀在檐前。
那两个挑食担的仆人,已先在那里等候。施恩邀武松到里面坐下。仆人已先安下肴馔,将酒来筛。武松道:“不要小盏儿吃,大碗筛来,只斟三碗。”仆人排下大碗,将酒便斟。武松也不谦让,连吃了三碗,便起身。仆人慌忙收拾了器皿,奔前去了。武松笑道:“却才去肚里发一发。我们去休。”两个便离了这座酒肆,出得店来。此时正是七月间天气,炎暑未消,金风乍起。两个解开衣襟,又行不得一里多路,来到一处,不村不郭,却早又望见一个酒旗儿,高挑岀在树林里。来到林木丛中看时,却是一座卖村醪小酒店。
施恩立住了脚,问道:“此间是个村醪酒店,也算一望么?”武松道:“是酒望须饮三碗。若是无三,不过去便了。”两个入来坐下。仆人排了酒碗果品,武松连吃了三碗,便起身走。仆人急急收了家火什物,赶前去了。两个出得店门来,又行不到一二里,路上又见个酒店。武松入来,又吃了三碗便走。话休絮繁,武松施恩两个一处走着,但遇酒店,便入去吃三碗。约莫也吃过十来处酒肆。施恩看武松时,不十分醉。武松问施恩道:“此去快活林还有多少路?”施恩道:“没多了,只在前面,远远地望见那个林子便是。”*《第五才子书水浒传》3,卷之三十三,《古本小说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第11叶b面—第5叶b面。
我们看到,容与堂本原来有743字的文本,余象斗本删节为179字;而金圣叹本除了删掉骈文外,基本保留容本原文。容与堂本对骈文两处加了“可删”、“都可删”的批语。由此可知,小川环树所说的“散文化”趋向在《水浒传》早期版本中已现端睨,到了余象斗本,正如胡应麟所言“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已经不足“寻味”。
二、风景的固定化
中国古典小说中出现的风景,并没超越柄谷行人所说的作为山水画的风景,它与现实景色写生显然不同。对此,小川环树有如下分析:
这些骈文或插词大多是对人物的容貌和穿戴,或风景(山路、建筑、庭园等),或结婚等吉祥场面,以及战斗情景等的描写。虽称为描写,但不是现代小说细致的、现实主义的、个性化的描写,而是每个场合有固定的套路。某一个插词并不具有无可替代的性质,也就是说,并非只能用于某一作品的某一处。而类似的情景描述,在哪个作品中均可套用同一描写方式。如做比喻,其功能与以前的摄影师照相时用作背景的布景相同。说话人背诵几种词句,到了叙景场合适当地拿出来一套,大概就是这样的机制。元杂剧中常见的诗是如此,平话中用的诗词也是如此。*[日]小川环树:《变文と讲史》,《小川环树著作集》第4卷,第25—26页。下点为小川环树所加。
小川环树的观点主要站在说话人或作者的立场,那么从读者来看,这些固定化了的风景描写意味着什么呢?为了将自然作为风景,首先需要某种认识性框架的存在。浅见洋二(1960—)指出,随着唐宋山水画的成立,“山水画的框架渗透到人们观看风景的视角中”,而且和绘画并行产生了“通过诗歌的框架把握风景的看法”。当时并非通过“透明纯真的视线”,而是通过“绘画和诗的框架”来把握风景*[日]浅见洋二:《中国の诗学认识》,东京:创文社, 2008年,第101—102页。。反之,也可以说,只有符合绘画或诗歌的意境,才能成为风景。假如站在这样一个风景认识性装置上来看,那么小说中出现千篇一律的“山水画”是顺理成章的。所以,为了描写充满诗情画意的风景,与其采用鄙俗烦琐的白话文或长于叙事议论的古文,还不如选择讲究声律措辞、富于形式美、带有抒情色彩的诗词骈文。在这一认识性装置中,老套陈旧的诗词骈文虽然更容易引发读者的想象力,却导致了小说中的风景描写过于千篇一律的程式化弊病。然而这种程式化给说话人乃至有着同样审美趋向的听众或读者都带来了方便。
那么,诗词骈文的程式化描写为什么能够引发作者和接受者极强的想象力呢?这是由文体本身的性质决定的。福井佳夫(1954—)指出:骈文创作的规范性涉及“对事物的看法和构思以及具体遣词造句(题材、结构、造句、典故、词汇等)”,“掌控着整个创作过程,如何感受,如何撰文,都有规定”*[日]福井佳夫:《六朝美文学序说》,东京:汲古书院, 1998年,第206,216—217页。。值得注意的是“固定化的内容和表现束缚了六朝文人的创作精神”,同时“老套的创作精神导致了固定化的内容和表现”*[日]福井佳夫:《六朝美文学序说》,东京:汲古书院, 1998年,第206,216—217页。。可谓文体和精神的一体化。“山水画”式的风景就是在文体和精神的互动中产生的一种模式。
上文所引“古道村坊”骈文(第29回),在《水浒传》第6回和第9回中分别出现:



(a)“古道村坊,傍溪酒店”和(c)“古道孤村,路傍酒店”,(a)“杨柳阴森门外,荷花旖旎池中”和(c)“杨柳岸晓垂锦旆,杏花村风拂青帘”酷似;以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为典故之 (a)“村童量酒,想非昔日相如;少妇当垆,不是他年卓氏”和(b)“村童量酒,想非涤器之相如;丑妇当垆,不是当时之卓氏”,也相差无几。一个村野小酒馆儿,宛如一幅山水画,给读者留下鲜明并固定化了的印象。
福井佳夫认为,骈文的修辞方式主要归纳为五种,即四六、对偶、声律(平仄)、典故、炼字。小说中的叙景文体除四六外已经不那么严格,但还是十分讲究对偶和声律,也多用常见的典故和华丽的词语。这种通俗骈体可视为将说唱艺人的声音融入白话小说中,使听觉和视觉相结合,便于酝酿气氛。
下面是姜书阁引用《武王伐纣平话》描写妲己的一段话:
在《九尾狐换妲己神魂》段中,形容妲己之美,说:“面无粉饰,宛如月里嫦娥;头不梳妆,一似蓬莱仙子。肌肤似雪,遍体如银。丹青怎画,彩笔难描。”接着,《纣王纳妲己》又说她:“面如白玉,貌赛姮娥;有沉鱼落雁之容,羞花闭月之貌;人间第一,世上无双。”类此之文,不胜列举。在今天看来,固然觉得都是熟滥套语,说不上有什么创造性的艺术技巧;但正因为如此,更可证明这些语言是当时及后世读者、听者和作者所普遍欣赏而乐于接受的。这些正是骈俪偶对的通俗文学语言。*姜书阁:《骈文史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521页。
白话小说的叙事模式借用说唱艺术“说话人”讲给“看官”的形式。即使叙事和会话部分用的是极为流畅自然的白话文,一旦说话人使用“怎见得”、“只见”等标志词开始情景描写,就必须采用骈文、七言句等说唱文艺的腔调。白话小说的这种文体特点和上述认识机制是相辅相成的。
三、个性化风景的萌芽
《水浒传》、《西游记》是根据流传积累下来的故事编写而成的;而《金瓶梅》是早期文人创作的长篇白话小说,但其叙景部分还是由诗词韵文来承担,说唱腔调相当浓厚。到了18世纪,吴敬梓(1701—1754)的《儒林外史》才出现了一些变化。其内容与英雄鬼神、才子佳人就毫无关系了,风景描写也与之前的小说截然不同:

在第14回,马二先生漫步西湖:

上述两处的风景描写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文体不再是诗词骈文,而是非常流畅的白话文。叙景部分与前后的叙事部分没有任何龃龉。第二,全知叙述者后隐退,从王冕和马二先生的视角观察并叙述风景,部分实现了内视角叙述。由此,大雨刚过后的白云和日光,荷花苞上的水滴,这些细致的自然景观叙述,是通过王冕的视线记录下来的。西湖的风景随着马二先生漫步移动,从不同角度得到叙述。紧接叙景,“王冕看了一回,心里想道”,“又心里想道”,“马二先生叹道”,用直接引语的方式引用视角人物的思考;或者“肚里正饿,思量要回去路上吃饭”,“吃得饱了,自思趁着饱再上去”,用间接引语引用人物的内心世界。“甚不好走,马二先生攀藤附葛,走过桥去”,这里讲述“甚不好走”的主体是叙述者还是马二先生,分辨不清,部分实现缺少引导动词的自由间接引语,似乎出现了叙述者的声音和马二先生的声音融为一体的效果。
上面两个例子已不是固定化了的“山水画”风景,而是根据每个人物感受的不同,从而观察到鲜明独特的风景,这就从仅为所指的风景朝着能指的风景迈进了一大步。
刘鹗《老残游记》(1903)的如下风景描写更进一步发展了白话文的叙景文笔:
到了铁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见对面千佛山上,梵宇僧楼,与那苍松翠柏,高下相间,红的火红,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绿的碧绿,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枫夹在里面,仿佛宋人赵千里的一幅大画,做了一架数十里长的屏风。正在叹赏不绝,忽听一声渔唱。低头看去,谁知那明湖业已澄净的同镜子一般。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里,显得明明白白。那楼台树木,格外光彩,觉得比上头的一个千佛山还要好看,还要清楚。这湖的南岸,上去便是街市,却有一层芦苇,密密遮住。现在正是着花的时候,一片白花映着带水气的斜阳,好似一条粉红绒毯,做了上下两个山的垫子,实在奇绝。

千佛山的风景是从老残的视角来叙述的,同时我们注意到他把眼前的风景比作“赵千里的一幅大画”。虽然仍保持拿绘画的框架来看风景这一态度,但叙景和老残心中“如此佳景,为何没有什么游人?”的感受连接得极为自然,这里的风景和人物是分不开的。
但是吴敬梓和刘鹗在叙景上的进步,并不意味着文人创作小说已达到“风景之发现”的境地,白话小说中的风景多半还是老旧套路的美文。请看李伯元《文明小史》(1903—1905)描写日本的场面:
面对日本的日光这个地方的风景,叙述者说的是老一套的四字句,看到的是中国式的山水画、中国的西湖,想到的是《中庸》的一节,“不禁叹古人措词之妙”。饶鸿生不是用自己的视线看风景,也不是用自己的话语叙述眼前的风景。值得注意的是,叙景之后,突然出现说书的说话人讲给看官的叙事模式,叙述者问“看官,你们想,山上怎么会有湖呢?不是大漏洞么?”,然后“原来”如此如此,开始解释。白话小说始终摆脱不了这种说书的叙事模式,因此,尽管有些文人努力磨炼描写技术,但还是很容易回到耳濡目染的骈体或诗词美文文体上来。
文学革命后的1925年,胡适回顾旧小说的风景描写,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小说转换为现代小说、旧白话文到现代白话、“风景之发现”前夜所经历的痛苦的演变。请看胡适的论述:
古来作小说的人在描写人物的方面还有很肯用气力的;但描写风景的能力在旧小说里简直没有。《水浒传》写宋江在浔阳楼题诗一段要算很能写人物的了;然而写江上风景却只有“江景非常,观之不足”八个字。《儒林外史》写西湖只说“真乃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一处是金粉楼台,一处是竹篱茅舍;一处是桃柳争妍,一处是桑麻遍野”。《西游记》与《红楼梦》描写风景也都只是用几句烂调的四字句,全无深刻的描写。(中略)旧小说何以这样缺乏描写风景的技术呢?(中略)我以为这还是因为语言文字上的障碍。写一个人物,如鲁智深,如王凤姐,如成老爹,古文里的种种烂调套语都不适用,所以不能不用活的语言,新的词句,实地作描写的工夫。但一到了写景的地方,骈文诗词里的许多成语便自然涌上来,挤上来,摆脱也摆脱不开,赶也赶不去。*胡适:《〈老残游记〉序》,《胡适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83—584页。原载于1925年。
结 语
本文从“风景之发现”的思路,探讨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叙景文体。柄谷行人指出“风景之发现”与“个人之发现”分不开,换言之“风景之发现”是一个现代性的指标。在《儒林外史》和《老残游记》的写景中,“风景之发现”已崭露头角,这是现代性的萌芽。最后以鲁迅《故乡》(1921)为例,来看“风景之发现”之后的叙景: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76页。下点为引用者所加。
正如叙述者“我”自己说明的那样,“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这里的风景随着看景人的思绪,有时美丽,有时苍凉。这段描写让我们亲身感受到由现代白话文这一崭新的文体所把握的“风景”,同时也感受到了触摸“风景”的“个人内心世界”。
【责任编辑:张慕华;责任校对:张慕华,李青果】
2016—11—01
中里见敬,日本九州大学言语文化研究院。
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