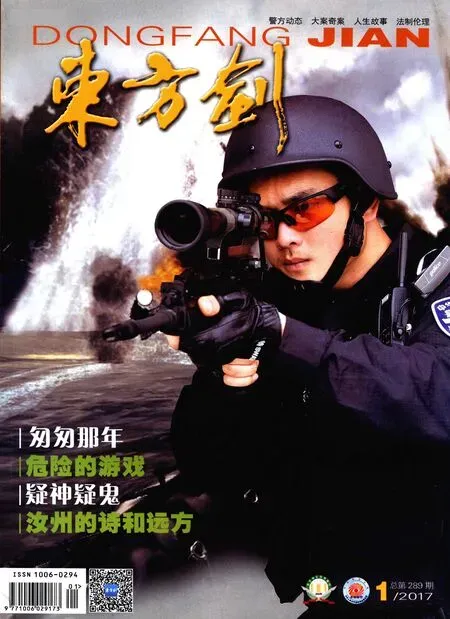匆匆那年(上)
2017-03-28◆蓝玛
◆ 蓝 玛
匆匆那年(上)
◆ 蓝 玛

楔子
眼前这个故事,和欧光慈三十多年前败走麦城的那个案子是前后相互呼应的关系。分开说不方便,必须搁在一起说才容易懂。
话说那时候欧光慈还是个青头小伙子,刚刚踏入一线不久,和现在相比成败不是很要紧。所以,走麦城对他来说并不是那么不得了。最要紧的是老杆儿踢了他一脚。可恨,那一脚险些把他的蛋踢爆——这才是关键的关键。
欧光慈身边的人都知道,队长生命中有一位大仙儿名叫老杆儿。这位老前辈对当年的欧光慈起到过重要的启蒙作用,为他后来的发展打下一个很好的底子。但此人爱急,急了就动手,刹不住车。他为那个案子恼羞成怒,一脚踢在欧光慈的裤裆里,险些把后来这位堂堂有名的神探当场踢死。
唉,从头说吧。欧光慈当年警校毕业先在一个区级小单位打过两年杂,功夫基本上荒废着。第三年忍无可忍考上了一个专门培养尖子的高级进修班,踌躇满志,准备学成以后大干一场。不料结业后被莫名其妙地安排到四川省南部一个偏僻的地方实习,带他的就是那位有名的老杆儿。老杆儿那时候还年轻,只比欧光慈大十二三岁,高大威猛,威风八面,破案的一把好手儿,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可惜的是此人心眼儿很小,小得像个娘们儿,这一点很不容易看出来。欧光慈分在他手下,老杆儿不动声色地作弄过小徒弟几次,结果次次都在小徒弟的智慧面前化于无形。于是他惊奇地发现这个尖嘴猴腮小个子很不简单,矛盾心理也就由此产生了。
什么叫乐极生悲?有了矛盾心理就要出麻烦,这就叫乐极生悲。或者说,搁在老杆儿身上就很可能乐极生悲。无奈的是,欧光慈当时太年轻,根本不懂这个,时时处处都想出风头——这就要倒霉了。
说起来那是一个云淡风轻的案子,或者说一开始连案子都还算不上,根本不可能太引人注意。后来的几十年,欧光慈时不时会想起那个倒霉的案子,总有些想不明白,那件破事儿怎么就把老杆儿搞火了,乃至于发疯似的给了自己那后果严重的一脚。因为那一脚,老杆儿不可避免地背了个处分。遗憾的是,他老兄不但不思悔改,而且严重地抵触着,于是乎又因为酒后打人并且拒不承认,最终被扒了警服,发配到一个县级企业搞保卫,人生从此完蛋——上帝呀,怎么会这样呢?
说不定一开始欧光慈就伤了老家伙的自尊心,换句话说,你不能表现得比师傅聪明,掌握不好这个,就容易出问题——甚至毁掉一个人。
老杆儿被开掉以后,欧光慈又在那儿干了半年多,然后回到了现在所在的城市当刑警,跌跌撞撞地发展到今天。这其中的三十多年,他当然没把老杆儿忘干净,但是实话实说,也没太把此人放在心上。时间如流水,欧光慈在时间的洗刷之下,像一颗包在石头里的钻石,最终光华四射,声震警坛。这么说吧,他压根就没想过,戎马半生,在马上就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那个让他欧光慈败走麦城的案子,那个让老杆儿赔进一生的案子,又一次搅乱了他的生活……
1
这是一个初秋的傍晚,欧光慈处理好一份复杂的结案报告,从办公室走出来准备上厕所放水。经侦组的小扁儿朝他嘿了一声,说刚才有人找他。欧光慈看看寂静的楼道问什么人找。小扁儿说没看见人,就听见楼下门房老李喊了两嗓子。欧光慈没太当回事儿,方便完接了一个手机,又给范小美发了一条短信祝她生日快乐,然后点上一支烟下楼回家。路过门房时他想起小扁儿的话,便朝门房老李嘿了一声,问是不是有人找他。
老李跟他要了一支烟别在耳朵上,说刚才好像有一个捡破烂的找他,太他妈烂了,没让进,喊了两声就把那人轰走了。欧光慈想不起自己什么时候认识过捡破烂的,他出门朝四周看了看,没看见什么人像捡破烂的,也就没把这事当真。
过马路朝西走下去,走着走着感到后边有人跟着。站住,回头,看见背后不远处的电线杆子下头站着个弓着脊背的大个子,正用眼窝里的一对诡异的小眼睛盯着他。那是一张脏乎乎的长方脸,灰白色的头发、胡子长成乱草一蓬。再看身上穿的东西,那简直不叫衣裳,完全是胡乱裹着的一层烂布片。脚上踩着一双破球鞋,左手拎着一个硕大的编织袋,里头装了些塑料瓶什么的。老李所说的捡破烂的无疑就是此人。
欧光慈凝视着那张脸,隐约觉得有那么一点儿眼熟。但是绝对想不起来是谁。他歪了歪脑袋,朝对方抬抬下巴,问:“你,找我?”
欧光慈不明白,刚才为什么没看见这主儿。
“废话,找的就是你。”对方硬生生地回了一句。
欧光慈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那家伙像头大猩猩似的朝欧光慈走过来,阴森地笑着,“妈的,小东西长成老东西啦。龟儿,认不得老子啦?”
他当然错了,从他张嘴说话那一刹那欧光慈就立马锁定了这个声音。心理学认为,听觉是最为牢固的记忆系统——看来不假。欧光慈的心瞬间像被一只看不见的爪子狠狠地攥住般痉挛了一下,十分不好形容地难受。但是他脸上没有任何表露,静静地反问了一句:“你是哪路神仙?”
“噢——看来你龟儿也不中用了。”对方又走上一步,探过脸来阴笑着,“实在对不住哟。想想嘛,老子险些个让你断子绝……”
话音没落,欧光慈的脚已经闪电般地踢了出去,身手老辣得连他自己都有些意外。只见那脚尖疾出疾停,眨眼间在对方的裆部收住——一气呵成。
对方一动不动,或者说,根本来不及反应。
欧光慈嘿嘿一笑:“老东西,你还没死呀!”
老杆儿怔了一下,嘿嘿地笑起来,眯着小眼道:“是呀,我死了你不是太寂寞了吗?”
欧光慈收回腿,朝地上啐了口唾沫。他没想到,自己和老杆儿几十年后的相见竟然是这样一幕。老家伙,还是那脾气,狗改不了吃屎。他嘘了口气说:“你也别把自己看得那么不得了,你在我心里没有什么分量——抽烟不?”
他掏烟的手不知怎么有些发抖。他知道,无论自己喜不喜欢眼前这个人,对方三十多年后的突然出现,依然使他有些不适应,既别扭,又多少有些开心。
老杆儿推开他的烟,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烟,弄了一根给欧光慈,又叼了一根在自己的嘴上,然后掏出打火机蹭了蹭脖梗子,啪地点燃了。
两个人点上烟。欧光慈深吸了一口,随即不由分说地揪着老杆儿的领口,把他弄到马路边的一个花池后头。他发现老杆儿确实老了,架子虽然不小,体重远远不如从前了。
欧光慈松开手:“你能不能把这身烂皮脱掉?我看出来了,你想让我可怜你,成心这么做的。想让我后悔,是吗?后悔当年对不住你,是吗?”
老杆儿像年轻时代那样晃了晃膀子,但是已经没有了当年那股子威风。七十出头了,落架的凤凰不如鸡。他哼了一声说:“龟儿,难道不是么?你他妈的现在混成气候了,老子却变成了叫花子。纵使你还有一点儿良心……”
“闭嘴!”欧光慈退后一步打量着老杆儿,“别装了,看看你破衣裳里边,分明套着件皮夹克。再看看你的袜子,干干净净,即便穿上破球鞋也遮不住。还有你的脖子,昨天肯定洗过澡,哪像叫花子那种比车轴还黑……脱了脱了,不然我不跟你说话。”
老杆儿没想到欧光慈的眼睛那么毒。他沉默了几秒钟,狠狠地抽了两口烟,然后把半截烟狠狠地摔在地上,刷刷两把扒下了破外套。随即从那只编织袋里翻出一双半旧的登山鞋,坐在花池沿子上穿好,把衣裳和破球鞋塞进编织袋,然后拍拍屁股站起来,恶作剧似的把编织袋远远地扔出去,准准地落在远处的那个垃圾桶边上。妈的,的确还是一条好汉。
“不废话啦,”他说,“找个地方喝两口。老子请你可以吧?”
欧光慈不假思索地表示同意。
三十多年不见了,一块儿喝点酒是非常应该的。小半辈子了,老家伙究竟怎么混的,他很想知道。更重要的是,老家伙突然找到自己,肯定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一定有事儿。他把老杆儿带到一个叫鹿回头的小馆子。平时他和自己的部下们常来这儿,不贵,味道也不错。名字起得比较讨厌——鹿回头。
小酒斟满,双方互相看着。馆子里没几个人,老杆儿的大胡子和四川话好像吸引了长麻子的小老板,额外地送了一碗四川泡菜过来,老杆儿很满意。
“一个月挣多少?”老杆儿举起酒盅抿了一口,不怀好意地看着欧光慈的脸,“上万有没有——早听说你他妈的大名鼎鼎了。”
欧光慈说你这人太低级了,好几十年不见,见面就是钱,能不能聊点儿别的?老杆儿说你小子搞得老子都快要饭了,连点同情心也没有吗?说说看,我又不跟你借钱。欧光慈早看出老杆儿没安好心,便故意把工资往多里说了些,想气气对方。却不料老杆儿阴笑着摆摆大手,对欧光慈的收入表示非常不屑。他说他虽然是一介草民,温饱却不是什么问题。他说他在老家包了两个小煤窑,别看屁大的两个洞,那也是两台小小的印钞机呀。然后他嘘了一声,说咱们不谈钱了,还是聊聊你的事业吧,是不是快退休了?
欧光慈分明看出老东西在成心贬低他,想逗自己发火,于是指指自己的鼻子:“这么说吧,只要老子愿意,干到死也没人反对。听明白了么——老子的事业比你听说的还有前景。倒是你,是不是整儿报销了?钱算个屁。”
这句话显然给了老杆儿一闷棍,老家伙哑火了。
欧光慈知道,所谓事业,是老杆儿最看重的,也是最不甘的,那是他的软肋。他摆摆手,不想继续刺激他:“废话不说了——大驾光临有何贵干?”
老杆儿沉默着,耷拉着眼皮看着酒盅。最后他抬起脸,恶狠狠地伸出三根手指头:“你他妈喝我三杯酒,喝完老子就说给你。”
“我要是不喝呢?”
“那你别后悔。”老杆儿抓住了酒瓶子,“你他娘的名气再大,不是还有个走麦城么?”
欧光慈的心“咯噔”了一下子,果然猜中了,老家伙确实因为那件破事儿而来。但他不肯喝三杯酒,只是拿起酒盅抿了一口,然后开始吃菜。老杆儿骂了一句也不勉强,边喝边吃,说了一些不咸不淡的废话,后来说得他自己都觉得没意思了,便咳嗽了一声,说:“算啦,反正有的是时间聊闲话,说正经的吧——你想不想把三十五年前那个案子捡起来?”
欧光慈转动着酒杯,盯着老杆儿:“这么说,你大老远的来找我,确实为了那案子?”
老杆儿用手背抹抹嘴:“废话吧你,不然我找你干啥——我又不喜欢你这张臭脸。”
欧光慈吃了两口菜,没有马上说话。老实说,照他现在的脾气,能把三十多年前那个破事儿搞清楚,倒贴钱他也愿意。真能把走麦城的事儿翻过来,他老欧没话可说。可是,那个缺东少西的案子有希望么?当年就没拿到什么线索,三十五年后再破这个案子,是不是有些扯淡?但老杆儿的突然出现不应该是无缘无故的,很可能有了什么重要的突破口。想到这里他问:“你是不是掌握了什么新东西?”
“那倒没有。”老杆儿显然知道他要这么问,摆摆手,又吸了吸鼻子,“不过你也用不着失望——我找到了案子里的那个哥哥。”
“付强?”欧光慈的眼睛马上眯起来,吐出一个名字。想当年,就是这个人物的出现,才有了后来的一切,最后导致两位走麦城。
老杆儿用手指头敲了敲桌面:“对,就是那杂种。狗东西消失了三十多年,终于让老子发现了。”
这当然是个好消息,但是欧光慈还是有些失望:“你觉得这个人的出现有意义么?事实上咱们要找的是他弟弟,那个叫付晓的人。”
“我知道,我知道。”老杆儿有些焦躁地抬起脸,看着天花板发呆,“付晓的重要性我又不是不知道,但是一下子不可能都找到,一步一步来么。你他妈给我句准话——想不想干?不想干就拉倒。”
“喝酒喝酒,你让我想想。”欧光慈的心确实动了。
2
回想三十五年前,欧光慈至今认为那个案子的发端应该是从弟弟付晓的失踪开始的。付晓失踪时恰恰老杆儿正闲得发慌,于是便主动带上欧光慈接手了那件事,接待了报案者,也就是付晓的哥哥付强。
欧光慈至今忘不了付强脸上那个大蒜头鼻子,后来他看了付晓的照片,发现这兄弟俩的鼻子真是太像了。所不同的是,弟弟付晓留着一脸短短的络腮胡子,样子很凶,而哥哥还好,那张脸刮得青乎乎的,干干净净。两个人都是长方脸型,眼角有些上翘。年龄相差两岁。不过哥哥由于在城里念了几年大学,反倒显得弟弟付晓更老成些。
在老杆儿颇有经验的询问下,这位哥哥大致叙述了弟弟失踪的前前后后。那时欧光慈还是个生瓜蛋子,只有倾听的份儿,插不上嘴。
付强叙述案子的时候情绪十分激动。他说他们哥俩很小的时候父母就不在了,是乡亲们你一口我一口地把他们拉扯大。后来他们找到了一个远房亲戚,才好歹算有了个归属。文革后恢复高考,两个人都想上大学,也都有基础试一试。但是因为穷,最终只有哥哥参加了高考,并且考中了。为了这个,弟弟付晓一怒之下只身出走,和亲戚断了往来。付强找过,找不到。随后付强在南方的一所不错的大学读生物学,也慢慢和亲戚疏远了。说到这些的时候付强很伤感,觉得一切都是因为自己读大学造成的,客观上伤害了弟弟。就是因为这个,大学毕业后他想对弟弟进行一些尽可能的补偿。
毕业那年是1982年,付强32岁,单身。
1982年的时候,弟弟付晓已经不在外边流浪了,在巫山县的一个林场当林业工人,负责一片很大的苗圃。付强当时手头正有一个实验项目,他提出带着那个项目到弟弟付晓的那个林场去进行种植试验,付晓没说行,也没说不行。付强原本想带个伙伴同去,但是由于自然条件等原因,没人愿意跟他去。更因为他刚刚分到那个研究机构没多少日子,找不到人替他说话,所以就只身去了。
和预料中的一样,弟弟付晓对他的到来毫无兴趣,还是林场的头头从中起了些作用,付强才好歹留了下来。几年不见,付强觉得弟弟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沉默寡言,对什么似乎都没有激情,包括找女朋友这种事。他这个做哥哥的由于一心搞业务,婚姻的事情也没进入议事日程。两个光棍一个锅里吃饭,一天说不上三句话。付强觉得弟弟的心灵之窗已经完全关闭了,他试了不少方法,基本没用。所以兄弟俩相处得十分难受。当然,由于社会身份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经济条件不同,共同语言基本没有。哥哥付强是有身份的人,各方面的条件确实是一个林工无法相比的。这一点林场的人看得比他们兄弟俩还清楚。在后来的调查中,老杆儿带着欧光慈询问了不少林工,大家都说弟弟付晓恨他哥——只不过这句话付强没说而已。
林工们其实很是同情弟弟付晓的,都说付晓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如果当年上大学的是他,恐怕会比哥哥付强还要有出息。被问到的人几乎都认为,弟弟付晓的失踪显然和他哥的到来有些关系。连付强本人也不否认这一点。
反正一句话,付晓的确不见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欧光慈记得很清楚,付强来报案是在付晓失踪后的第五天。付强说开始的几天他并没有想过更深层的东西,觉得弟弟有可能因为什么事情或者什么人而临时离开几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回来了。其中他给几个可能的人打了电话,回答都是付晓没来过。由于林场比较偏,林工们居住得也比较分散,所以不方便到处打听。直到第四天,事情才传开去,付强也真正急了,第五天来到了老杆儿面前。
老杆儿很敏锐地问付强,你所谓更深层的东西是指什么?付强迟疑了一会儿说,会不会是遇害了?随即他马上否定自己,说找了这么多天,没有听见任何人说见过死人,仅仅是自己的瞬间想法而已。
老杆儿和欧光慈获得的第一手情况大致就是这些。如果这时有什么刑事案件,他们恐怕也就不理睬这个事儿了。付晓毕竟是个成年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回来了。可那些天确实没事,加上老杆儿是个闲不住的人,就带上欧光慈跟着付强去了那个林场,还带了一条狗。那个林场好像叫双溪林场。
结果和最初的感觉差不多,找了两天一无所获。林工付晓确实莫名其妙地没影儿了。老杆儿和欧光慈倒也敬业,第三天还是按照商定的计划跟付强去见老龙口的一位叫五爷的守林人。付强说那位五爷知道的事情非常多,说不准会有什么线索。但是可恨的是,付强头天晚上出门解手门牙磕在一块石头上,活生生地磕掉了,脸肿得跟馒头似的。老杆儿正好对这事儿也失去了兴趣,便带着欧光慈回来了。
这时候欧光慈第一次向老杆儿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现在回想起来,老杆儿的不高兴大概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老杆儿这人混账就混账在不愿意听别人的意见,尤其是这个黄口小儿的意见。欧光慈的建议是,应该去见一见那位五爷,那一带地形复杂,人员构成也复杂,找有见识的人问一问,即便没收获,也不损失什么,而且可以给付强一个比较完整的交代。老杆儿虽然不悦,最终却也听从了这个建议,硬是把受伤的付强拉上,找到了老龙口那位五爷。
五爷是个看上去平平常常的人,瘦小沉默,问了半天也说不出什么。付强和他也不怎么熟悉,询问的时候几乎没说什么话。最后五爷有些不耐烦地说,你们何不到黑山牙子去看看,前些天我觉着有人去了。
这话引起了老杆儿的重视,因为黑山牙子是个地势险要的地方,曾经出过人命。他追问五爷什么人去过黑山牙子,五爷说老子怎么知道,就是听见狗叫。我那只老狗还是很厉害的。
老杆儿不再废话,跟五爷借了那条老狗便朝黑山牙子去了。欧光慈和付强在后边跟着。走出不远,五爷追了上来,说他想起一个情况,说同一天的同一时刻,他好像看见黑山牙子对面的山梁子上有几只黑山羊,六七只的样子,让他们找找看,应该有个放羊的。老杆儿谢过五爷,继续上山,走出一身大汗。大约走到黑山牙子半山腰的时候,五爷那只狗狂吠起来,朝着山上跑去。两个警察顿时来了劲头,紧跟着狗往山上跑。却不料那个付强突然两条腿一软坐在了地上,他说他怕。欧光慈心头一跳,马上注视老杆儿。他看出,老杆儿也有了和自己一样的感觉。
是的,付强一定认为弟弟出事了。
两个警察已经顾不上管他了,一口气跑到了黑山牙子山顶。那条狗还在叫,在山头上胡乱绕着圈子。老杆儿不愧是个有经验的家伙,他抱住狗的脖子,小心地蹲下来搜索着崖头附近的地面。随即朝欧光慈勾勾手指头,让他注意地面上的痕迹。
欧光慈马上就看出来了,地面上有搏斗过的迹象,而且有一道拖拽的印记直直地延伸到悬崖边上。老杆儿无声地朝崖头努努嘴,而后手指朝下指了指。欧光慈明白,恐怕有人被扔下去了。两个人没有马上下山,而是把周边仔细地找了几遍,一无所获。
事不宜迟,老杆儿起身朝四周看看,而后果断地做了个手势,两人便朝山下跑去。付强正在朝山上走,看见他们奔下山,便跟了下来。下到山下往北跑,荆棘丛生,根本没有路。几个人什么也顾不上了,因为前边的老狗越叫越凶,显然发现了什么。三个人气喘吁吁地冲到沟堑的深处,看见那条狗在前边打着转地咆哮。跑到近前时,蓦地站住。首先看到的是两条腿,平伸着,一只脚上穿着球鞋,另一只脚光着。付强怪叫一声扑上去,老杆儿敏捷地勾住了他的脖子,把他甩在地上。两个警察慢慢走上前去,马上看见了趴在地上的那个死人。
死人趴在地上,背上的衣服裂开一条大口子,露出了里边的红背心。老杆儿让欧光慈不要动,随即小心地走过去蹲下身子。他看了几秒钟,伸手摸了摸那人的脖颈,已经没有脉搏了。他指指不远处的付强,让欧光慈把他带过来。付强先是有些胆怯,随即看见了死者的脚,表情有些奇怪地站起来,走到近前时他看见了死者的后脑勺,眼睛马上睁大了。
“这……这是谁?”
老杆儿咦了一声:“不是你弟弟么?”
付强的嘴唇有些哆嗦:“不……不像,付晓的头发没有秃呀,没有。”
是的,眼前这个死者的后脑勺有些秃顶。
老杆儿有些变色,观察了一下,而后小心地托住死者的肩膀和腹部,一下子把那人翻了过来。他听见付强呻吟了一声,古怪地吐出三个字:
“不,不是……”
3
“欧光慈,你他妈记不记得,你就是从这时候开始作怪。”不是很亮的灯光映着老杆儿那张胡子拉碴的脸,老家伙有些怒气,用手指头敲着桌面,敲得盘子里的花生米跳舞似的,“现在看来你说的可能有那么一点儿道理。可是,想当年你狗日的还什么都不是呀!对不对?”
“天才和年龄没关系,讲究的是感觉。”欧光慈眯缝着眼睛,小小地抿了一口酒。几十年过去了,他不像当年那么冲动。
老杆儿攥起拳头捶着大腿:“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当初就是你这个狗屁‘感觉’把老子惹恼了。感觉感觉,你懂得什么叫感觉?”
“我到现在还是那个感觉,你莫非还想踢我一脚?”欧光慈觉得老杆儿依然那么可恨、那么扯淡。
“别他娘的废话了,咱们说说现在吧——你有没有兴趣跟我跑一趟,把这个破案子弄一弄?”老杆儿往嘴里扔了几粒花生米,咔咔地嚼着。
“你觉得有意义吗?”欧光慈歪着脑袋望着对方那张大脸,“想当年我随便说了说我的感觉,你就像牲口似的发疯了。男人的那个地方是随便踢的么?你发疯发得也太邪乎了。”
老杆儿埋下头,双手抱拳比画了一下:“不说了好不好?不说了。我其实就是看不上你那种胸有成竹的鬼样子,张嘴就说那个死人和付晓的失踪案有关系。你他妈的什么都还没搞清楚,怎么就敢开口?”

欧光慈把筷子拍在桌子上,提高了声音:“我就是那么想的,有什么办法?直到现在我还是那么想!问题的关键是,你老家伙那一脚把我踢伤了,耽误了工作,后头那案子不就搁浅了么?”
欧光慈说得不错,老杆儿把欧光慈踢伤后,事情被搞麻烦了,破案的事情被耽误了好几天。后来查清那个死者是林场附近一个村子里的二流子,人称四叔。破案工作就卡在了这儿不动了。老杆儿随后又闹出打人那件事情,被开除,破案就更难以继续了。据欧光慈所知,曾经派人调查了一下那个四叔,没有太深入,再后来欧光慈调走了,便远离了此案。听人说付强似乎找过公安局,还是为他弟弟失踪的事情没完没了。其结果是不了了之。不久,付强离开林场回了原单位。那个案子便从此成为了历史。
“那个付晓是不是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欧光慈问老杆儿。
老杆儿点点头:“可不是,几十年来,一点儿消息也没有。我估计是死了。”
“他哥哥呢,那个付强后来有过动静么?”
老杆儿摇摇头:“这个人事实上也等于消失了,我没有再关心他。”
欧光慈看着老杆儿:“那我就不懂了,你现在怎么突然开始关心这事儿了?”
老杆儿拿起小酒盅,一仰脖子喝干了。他攥着酒盅看着,说:“这么说吧,那个案子在我心里已经成了一块病,根本不可能忘。说到底老子这辈子等于毁在那个案子上,这是其一。其二,我现在是个自由人了,时间有的是,钱也搞到几个,所以想拉上你小子跑一跑,看看能不能有所收获——老弟,那毕竟是咱俩的一个耻辱对不对?”
“有什么突破口么?”欧光慈的心已经动了,但是他不想表现出来,“或者你想碰碰运气?”
老杆儿把两个人的酒盅斟满,抹抹脸说:“踢人那件事情我正式向你赔不是,磕头都可以。老子真心希望你能陪我走一趟,凭你的本事,应该能把这个案子搞清楚——怎么样,吃住我全管。”
欧光慈把酒喝掉,学着他的样子敲敲桌面:“我问的是突破口。”
“暂时还没有突破口。不过既然我把付强找到了,好歹也算个突破口吧。总之咱们从他入手,把他带上也可以,返回林场重新来过。”
“是找付晓,还是破那个死人的案子?”欧光慈决定使用自己的年假。
老杆儿举起杯子:“全听你的,老子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资本当老大了。”
欧光慈想了想,微微一笑,伸手拿起了酒盅……
没有什么犹豫,欧光慈第二天和上头打了个招呼,又跟几个手下交代了一下,下午4点多陪老杆儿上了火车。头一天到贵阳,第二天上午到了昆明。老杆儿告诉欧光慈,他碰上付强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他说他搞了七年小煤窑,此后就东南西北地跑生意赚钱。到昆明是去见一个生意上的伙伴。换句话说,他已经彻底把付强这个人忘光了,却没想到在昆明无意中看见了他。老杆儿说他不了解付强几十年来怎么混的,又怎么会出现在昆明,但是既然发现了,一种本能使他马上盯住了付强。老杆儿说他到昆明和他那个生意伙伴参加了一个什么发布会,在会上看见了付强,过程不复杂。起先他以为付强也是从外地赶来参加发布会的,会后才发现不是——付强居然调到昆明的研究机构了,而且分明已经成了上流人物。
跟踪发现,付强住在滇池畔的一栋独栋小别墅里,门口的铁笼子里蹲着一头藏獒。虽然年纪也不小了,但是自己开车,身体也挺不错的。
这是老杆儿目前了解到的有关付强的基本情况。
两个老家伙都是干警察出身,所以接下来的事情做得有条不紊。他们打了个车开到距离付强的别墅区不远的一家经济型旅社住下,然后把午饭吃了并且休息了一会儿,大约下午3点徒步来到了付强的别墅附近。
面对这样的别墅,欧光慈完全认定付强已经不是原先的那个付强了。用老杆儿的话说,狗日的发达了,身份不低,这是付强留给他的强烈印象。但是老杆儿强调,那家伙丝毫不懂得低调做人,把自己搞得跟个外国元首似的,老杆儿认为这样的人业务上恐怕还可以,但走到这一步,绝对不仅仅是靠本事得到的。欧光慈虽然没见到付强,但是接受老杆儿的理论。
两人没有上前敲门,他们不想搞得那么直来直去。他们想观察一下,进一步找一找感觉再说。一下子把自己摆在明面上容易被动。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小别墅静悄悄的。只出来过一个保姆模样的女人在小菜园拔了几根葱。老杆儿和欧光慈都是有一把年纪的人了,这样的蹲守还是很考验人的。欧光慈提出还是直接见面的好。老杆儿说等等,再等等,我想给狗日的来个意想不到的。
下午5点30分左右,付强领着个小女人出来了。欧光慈一眼就认出了对方。基本没变,只是从青年版变成老年版了。他算了一下,觉得付强恐怕有六十七八岁了。让他感到有意思的是,人一旦有了身份整个感觉就不一样了。现在的付强看上去很有些做派,文质彬彬的,跟在身边的那个小女人因为过于妖娆,反倒显得有些和付强不般配。老杆儿说那小女人恐怕是付强的小老婆。所谓的老牛吃嫩草。
付强夫妇当然没注意到有人在监视,开上小车走了。欧光慈两人赶紧拦了一辆出租,紧跟上去。车子穿过了大约整个昆明城,在机场路附近的一家会所拐入停车场。欧光慈两人紧盯住不放,进门的时候欧光慈不得不亮了亮警官证,顺利地走了进去。这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会所的多功能厅里响起了舒缓的音乐。一些感觉上身份不俗的客人陆续光临。欧光慈和老杆儿在角落里找了个不起眼的座位,远远地盯着付强夫妇。他们看见付强不时地起身和熟悉的人寒暄,风度翩翩地交谈着。欧光慈告诉老杆儿,感觉上来客多为知识分子。老杆儿说恐怕也有苍蝇,说着指了指门口一个烫飞机头的家伙。
整个晚上基本上没有什么不正常,两个人看出这是一次类似于业内高端人士的交际会,无甚特别之处。要说特别,那就是身份不够进不来。两个人有些坐不住,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合适于见面的场合。不过合适的场合很快就出现了,而且出现在他们没意识到的人身上——就是付强的那个小女人。
就在付强和几个差不多的人物喝红酒谈事儿的时候,去卫生间的小女人愤愤然地快步回来了,小脸红红地说有个不要脸的男人摸了她的屁股。付强马上傻了,然后愤愤地站起来带着小女人去找那个男的。结果摸屁股者竟是那个烫飞机头的家伙。女人有了老公撑腰,扑上去要抓那飞机头的脸。对方敏捷地躲过,随手拧住了女人的腕子,强调他没有摸女人的屁股,仅仅不留神碰了一下女人的小腰。因为女人那天晚上穿的是旗袍,那个部位极其突出,甚至极其淫荡。面对这场面,付强显然受不了了,上去就要抓飞机头的领口。却不料飞机头手比他快,搡开小女人,一家伙就把付强顶在了冬青树旁边的大理石柱子上。付强的脖子被勒住,喉咙里发出一种十分难听的声音。
周围的人围上来不少,却面面相觑无人上前。
小女人杀鸡似的叫着,终于引来一条好汉。只见一个大胡子几个健步冲过去,一把薅住飞机头的头发,另一只手闪电般地打在对方的腮帮子上。飞机头姿势古怪地飞出两米多远,仓皇地爬起来跑了。大胡子怪叫一声,噌噌地追上去。等保安跑来的时候,这一幕刚好结束。
整个场面全乱了,付强悻悻然地和几个朋友打了声招呼,带着他的小女人走了。一直在回响着的音乐也莫名其妙地停了。
外边光线很暗,时候已经不早了。付强领着小女人走到车子跟前,从两侧上了车。却不料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另外两个人身手敏捷地从两侧的后门也上了车,砰砰地关上了车门。
其中一个正是刚才帮忙的大胡子。
突然出现的情况显然把付强搞懵了,他有些不知所措地转过身子看着后边的两个人。大胡子朝他开心地笑笑,双手搓了搓脸。另一个小瘦子没什么表情,耷拉着眼皮,嘴角叼着一支没有点的烟。
“噢噢,稍等。”付强突然反应过来了,从口袋里掏出钱包,“带得不多,二位想要多少?”
话音没落,钱包已经被大胡子抓到了手里。付强和他的小女人不敢说话,眼看着大胡子打开钱包数里边的钱,边数边叹,直到把那个小瘦老头搞烦了,让大胡子把钱包还给人家,然后拍拍付强的肩膀,问:“老兄,仔细看看,还认识这个人么?”
“听……听口音是我们老家的人。”付强收回钱包,凝视着老杆儿的脸。
当然,人,他绝对是认不出来了。
老杆儿张开大巴掌,挡住下边的胡子。付强目不转睛地看着上半边脸,还是认不出来。在微弱的车灯下,欧光慈发现付强也确实老了,皱纹满脸。但是长年不再栉风沐雨,这张脸确实变得很文气,不得不承认上流社会的人就是和普通老百姓不一样,连模样都有所改变。这使他不可避免地想起了他那个消失的弟弟,林场工人付晓。
想当年,付晓就已经对兄弟俩身份的不同,以及由于身份的不同所带来的社会地位的不同有所表现了。这一点在几十年后完全凸现了出来。
“哦,天哪,你是……”
他听见付强突然发出一声来自内心深处的呻吟,的确很突然,甚至吓了他一跳。
“你是那个……”付强张大了嘴。
老杆儿打了个响指:“警察——老杆儿。”
4
三个人是第三天一早上路的,开的是付强的另一辆车,SUV。付强原本很不想去,理由是那案子已经三十多年了,这时候去不可能有什么收获。再说三个人都年纪不小了,恐怕经受不了路途的颠簸。欧光慈说你别把我算进去,我比你们俩都小,现在仍在一线。老杆儿则强调用不着跟付强客气,那个案子直接牵涉到他弟弟,而他弟弟三十五年无影无踪,不能就这么算了,尽管我们年纪大了,但是我们仍是警察。欧光慈警告他,住嘴,你早不是警察了。
对于这两人的身份付强倒不是很在意。他为难的是年纪大了,手头还有一些研究项目要带学生,最主要的是,他坚持认为三十几年后调查当年的案子不会有结果。后来他想起什么,说,要说弟弟三十五年无影无踪也不完全是事实,在出事后七八年的某个时候,有人似乎在深圳看见过他。说这话的目的明显地是想说付晓有可能没死,只是不愿意露面而已。但是老杆儿和欧光慈同时捉住了另一个重点。老杆儿说你别忘了,那个案子里还有一个莫名出现的死者四叔,说不定和付晓有关系呢。欧光慈补充说,是的,那个案子比咱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我劝你还是暂时放下手里的事,跟我们跑一趟。
付强最终答应了。
三个老头儿就这样上了路。三个人都会开车,倒不至于很累。但是从昆明到双溪林场毕竟距离遥远,直到第二天傍晚才到。三个老头坐车坐得不想说话,当晚糊弄了肚子就睡下了。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他们决定先去公安局找一找当年的调查档案。欧光慈后来调走了,不知道公安局有没有继续下去。老杆儿说听说他们还是继续查了查,弄清了那个死者的基本情况,但是凶手是谁没有结果。随即老杆儿转脸对付强说,你觉不觉得杀人这件事儿是你弟弟干的?否则他为什么会失踪?
付强马上急了。因为来的路上聊的都是案子,老杆儿和欧光慈也好几次想把话头往付晓的身上引,想必付强是听得出来的。但是最终谁也没有明说,相互间也就没有产生冲突。没想到老杆儿这时候突然使出杀手锏,气氛立刻就不一样了。不过有意思的是,付强虽说急了,但是反驳得很没底气,毕竟他没有哪怕一点点理由证明他弟弟没杀人。叫喊了半天,欧光慈烦了,说这种狗屁争论还是算了吧,看完材料再说不迟。
但是很遗憾,公安局早把三十多年前的东西打包收起来了。加上老杆儿早已不是警察,现在那些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哪路神仙。欧光慈倒是有几个人听说过,但是并不是因为他当年在这儿干过,而是因为他后来的名气。因为这些名气,人家还算帮忙,好歹找到了那包历史材料。和欧光慈估计的差不多,材料里的东西没什么有价值的内容。看了好半天,才只在一份很短的调查笔录中发现了一个他们都没掌握的情况——公安局找到了那个死者的一个侄子。老龙口的五爷提供过线索。五爷当年跟老杆儿和欧光慈说过,在出事的山梁子对面看见六七只黑山羊,这个侄子就是那个放羊的。但是材料里说的内容比较模糊,那个侄子说他看见了对面远远的山崖边上有两个人扭打在一起,其中一个非常像他四叔。后来的事实证明死的就是他四叔。但是对另一个人他说得不太肯定,说觉得有些像双溪林场一个采购。他说那个采购跟四叔的老婆有些勾搭……材料里这里使用了一个括号,里边写着这样几个字“不好意思地”。那一年这个侄子刚刚十一岁,说到“勾搭”这两个字可能会是这个表情。但是小孩子仅仅说“有些像那个采购”,并没有肯定是。这就使得事情不太好判断了。公安局的人说,那个侄子应该还在,就在双溪镇住。
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看来下一步只有一招,就是到双溪镇去找那个侄子。付强这时候的表现很矛盾,一方面他对调查本身就毫无兴趣,声称自己不过就是个开车的;另一方面又很不放心,想知道他弟弟付晓到底有没有杀人。他烦躁地说,案子毕竟过去三十多年了,有查清的可能么?我现在一点儿信心也没有。欧光慈很不客气地告诉他,既然老子出动了,就绝对不会空手而归。说话的时候那对小眼睛里头有很厉害的一种东西在闪烁。付强闭嘴了。欧光慈又把目标转向老杆儿,说你当年不让我发表意见,还给了我要命的一脚。现在我想让你知道,这次我出来了,就是要让你老小子知道知道我的感觉。现在我觉得这个案子很可能比咱们想象的还深,还复杂,甚至会大大出乎你我的预料,这是我现在的感觉。
欧光慈既然说出这种话,两个人也就不敢言语了。
找那个侄子很费了些劲,最后在一个唱地方戏的小戏班子里找到了。见面的时候他正在给一个老师傅模样的胖老头子掏耳朵。三个人一看见此人的长相都吓了一跳——这个侄子左脸留着长头发,遮住了耳朵,另一边头发却很短,看上去非常不舒服,而且长着一张细长的脸,一副狰狞样。他哑着嗓子告诉来人,他的左耳朵被人削掉了。
戏班子正在一个镇子上一座又老又破的祠堂里排练折子戏,局促而阴暗,一个个跟牛鬼蛇神似的。弄清楚了三个人的来意,一只耳(欧光慈心里给这人取的名字,他的本名叫唐思言)把人带到附近的一个看上去很有些年头儿的茶馆,跟谁都没商量,便要了一壶好茶。
“也就是说,你们要调查三十五年前那件事儿?”唐思言用茶碗的盖子仔细地拨开茶叶的浮沫,很认真地吸溜了一口茶,然后看着欧光慈的脸问道。
欧光慈知道,眼下只有自己身上还有一股子杀气,老杆儿虽然虎彪彪的样子,其实只是个皮囊。付强则处在可有可无的地位,毫无精神。他学着唐思言的样子用茶盖拨拉着茶叶的浮沫,歪着脑袋看着对方的表情:“对,想请你谈谈那件事儿。公安局的人说,目前能和那件事儿扯上的人只有你了。”
“噢,别别别……别这么说,我和那件事儿毫不相干。当年我才十来岁,不懂什么事。”唐思言连连摆手,仿佛在撇清什么污秽的东西。
欧光慈不慌不忙地说:“可你看见了黑山牙子悬崖上扭打在一起的那两个人,这没错吧?”
唐思言说没错,当年自己就是这么说的:“我看得很清楚,挨打的就是我四叔。”
“你看见他被那个人从山崖上推下去了?”
唐思言没有在乎欧光慈的追问:“这倒没有,我去追两只羊,回头的时候我四叔已经不见了。我当时没有多想,你们知道,一个十岁的孩子还没有那么多心眼儿。后来听说我四叔摔死在山崖下边,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后来也是这么交代的。”
“好,现在我问你。”欧光慈敲敲桌面,目光逼人,“你到底有没有看清那个把你四叔推下山崖的人,那个人到底是谁?”
唐思言停顿了几秒钟,好像在思考,又好像在权衡,最后说:“这么说吧,当时我觉得那人像林场的一个采购员,姓郝。可是后来听人说,那个采购员出事的时候不在林场,在郑州。”
哦,事情有意思了。
(未完待续)
特邀编辑/浦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