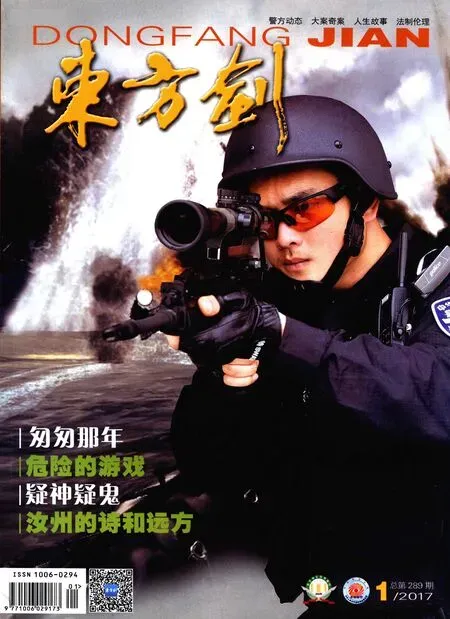煮米闻香(下)
2017-11-14鲍尔吉原野
◆ 鲍尔吉·原野
煮米闻香(下)
◆ 鲍尔吉·原野
在德国熬小米粥
起先我不爱吃小米,怪其不圆滑香糯,柴。我媳妇爱小米粥无数年,诱我食之。我食而上套,觉出其好。小米粥之好如良善人与你肚肠对话,说的都是贴心话。这种粮食极尽朴素而后香,大香无味。而颜色温润,是有来历不张扬的君子思路。
赴德前怕行李重,踟蹰再三,带一小袋小米。我经过北京的、法兰克福的、斯图加特的奔波,脑子被各种信息搅得彻底乱套。入住房间,觉得先要做一件事。想了半天,是撒尿,一撒了之。又想,小米粥?对头。房间里厨具齐全,用亮晶晶的德国钢锅熬小米粥。拿米袋,一看乐了,上印:“龙凤之乡翁牛特”,这是我老家的小米。
为什么乐呢?看到“翁牛特”,脑子里出现老家的口音,跟德语一点不一样,小米跟这几天吃过的面包起司也不一样。窗外的德国森林跟建筑与小米更不配套。熬出小米的香味,混入收音机播放的交响乐中,更可乐。我对“咕咕”冒泡的小米说,你们是翁牛特第一批赴德粮食,为两国传统深厚友谊做出卓越贡献,贡献若何,少顷由我肚肠验收。
喝小米粥,想起杨远新。他是我友好,我俩友好二十多年。去年杨赴翁牛特担任旗委书记。我对他说,你升官,我发财,我要搜刮点好东西。远新说:我们不发达地区没啥好东西,最贵重的玉龙在国家博物馆呢,牛羊和树没法送你,只有杂粮。我说来点小米、荞面吧!收到啦,翁牛特的小米粒更小。别的小米煮粥,单位体积五千粒,它可达一万粒。米多,营养就多,这是我发明的说法。它的米色黄中微绿,玉色。味香,香得不嚣张,贴近心地。在这儿喝过,我觉得灵魂(姑且这么说)某处某螺丝和这里的扣“啪哒”合上了。
后几天,我让翁牛特小米与德国同行们开展联谊活动,增进互信和相互了解。小米和德国之Bulgur同煮,和Seitenbacher煮,我也不知这是啥米。产生新味,像洋泾浜德语。乱整吧,你们进肚子之后打擂吧,如“德中同行”项目的主题——灵感与创新。为了省时,我在小米粥里卧德国“行走中的鸡的蛋”,卧香肠片,还卧什么呢?收音机不能卧,还卧过德国胡萝卜、卷心菜。我不讲什么口味,跑步消耗大,一句德语听不懂消耗也大,营养够就行了。食物到了肚子,只是多糖纤维素蛋白质,搞吧,只是有点糟践小米的美味。隔三天,我还要吃一锅纯小米粥,否则灵魂那个螺丝和扣不“啪达”。
有一回,把空锅放在刚关的电磁炉上,锅底遇热变色。损坏德国公物如何是好?各种擦法均不奏效,后用黑妹牙膏擦之,明亮如新。这么新的锅底让我高兴得忘了刷洗,煮小米粥,出薄荷味,我以为是幻嗅。一吃,确是牙膏之味。怎么办?粥舍不得丢掉,吃了。有人说,“上帝关上一扇门,一定打开另一扇窗。”那么,上帝让我吃有牙膏味的翁牛特小米粥的好处是什么呢?想了半天才知道,另一扇窗是不用刷牙了。
大 米
万物当中,如果不算人,又美又有用的是米。
大米在稻谷时期已经很美,稻穗带出黄金的色彩,如金箔包颗粒。谷化为米,特别在煮熟之后,大米展示出白玉一般、珍珠一般的温润雪白。有的东西煮熟之后离原来面目相距十万八千七百里,如酱肘子,与在猪身上不可同日而语。什么角瓜、西红柿熟了都变了样子。稻变米,煮熟之后金变玉,了不得。
大米熟了比生米更美,它身上每一部分都像棉花一样开花了。我们吃的大米饭实为大米花,此花糯软、晶莹、隆松。面对一碗大米饭,不吃,看上三分钟,一定生出赞美心,其色泽可与任何珠宝相比,三五成团。倘若米粒孤零零落在桌上,人也想把它收起来。
我想,人的种种好,比如聪明智慧美貌,其实都是粮食的好。人买家具爱问材料,紫檀的、花梨的,材料决定成败。人是什么材料的?虽是肉的骨的筋的,其实还是粮食蔬菜肉蛋奶提供的原材料。如果有人请教我:你是什么材料的?我恭敬回答:大米的。
人闭上眼睛想一想,大米——这么好的东西,洁净、雪白、清香的东西进了人的肚子,人能不好吗?能不聪明善良吗?好好吃,吃一辈子,这人肯定长寿。反过来说,人吃了大米之后,还打架、骂人,实在是不应该。这话是我替大米说的,大米愿意进好人肚子。
科学讲,大米不过是淀粉、碳水化合物。我觉得科学家对这个事还没研究清楚。它除了化学性、多糖的分子结构,其精神性还没有弄清楚。大米是阴性的,跟水、银白的云彩是一伙的。高贵的品质让它散发香味,同时不妖冶袭人。这个香只有味蕾知道。我还想一件事,大米喜聚合,喜众来众往,因此吃饭在碗里留一个饭粒实在不应该。静心看一碗矗成尖堆的大米饭时,看来看去,觉得它们有笑容,浅淡、喜悦的笑容。
人习惯用钱买那些别人没有的东西自珍,曰收藏。我看天下的好东西都在眼皮底下,大米就是一种。吃一辈子大米,看一辈子大米,福气已经够大了,用不着再收藏什么古里古怪的东西了。
粮食的神性
我羡慕那些吃饭很慢、一直吃尽碗里最后一颗饭粒的人,最后那颗饭粒,可能正是农民弯腰从地里捡起来的那颗谷粒。见到这样的人,我岂止是羡慕,简直会景仰他。
吃饭占用了人生很长的时间,虽然它够不上恢宏大气,它也真不需要恢宏大气。相反,小气和安静适合于每一顿饭。
慢慢用餐、吃干净每颗饭粒的人,身上至少有两项美德。第一是懂得感恩,感恩实在是要从敬重粮食开始。你看和尚去饭堂用餐,身上要穿戴袈裟、着正装,看上去一派庄严气象。我有幸与和尚一道吃过饭,他们手捧着饭钵,眼睛盯着钵里的饭,既用心又清净。和尚们肃然起敬的仪容,是对粮食做出的礼拜。古代真有人在吃饭前对饭食拜上几拜,以示感恩。为什么要对粮食和饭食恭敬呢?结论是:对入口的饭都不恭敬,还能恭敬谁呢?如果仅仅恭敬明星而糟蹋粮食,岂不本末倒置了吗?是粮食让你生命延续,而非明星。和尚们吃饭不说话,说话轻慢了粮食又不利于消化。科学认为,进餐说话会影响到从胃到胰腺的一系列功能。而你看和尚们专心吃饭,能体会到一样美。他们吃净饭粒用开水洗一洗碗,喝下去,那真是干净极了。以前,我见到我妈吃完炒米用茶水涮一涮喝下去,觉得愚不可及。如今知道,我这样想才愚不可及。我还没有到达他们的境界,从粮食中领悟天地馈赠之厚意。
他们身上的第二项美德是享受福气。福气在哪里?有人告诉我,福气就是手挎LV。我问LV跟VCD是一回事吗?他回答:你是个老土。老土不一定不会享福,李白和苏轼都不洋,都是尽享天地大美的有福之人,他们都不知LV与百达翡丽。
福气在哪里?如果让我回答,首先回答是吃粮食。好东西生长出来而非生产出来。别不相信,你在心里算吧,粮食、柑桔、葡萄、牛奶、蜂蜜、珍珠、翡翠、鲜花都是生长出来的、上帝手里的东西。只有薯片、汽水、电视剧、口香糖这种烂东西才是生产出来的人的产品。
慢慢地享受生长出来的东西,是生命与生命相遇。每一颗粮食都有自己的滋味,越咀嚼越有味,身上充实。事实上,当粮食进入人的身体,是阳光、雨水、土地的香气和蛙鸣在你生命中循环,它不仅是碳水化合物,还是天地的能量。
人常说吸取天地之精华,天那么高,地那么厚,你如何吸取?人有可能接触到的天地精华,也只有粮食和水。天地不光生长精华,还以眼睛观人,看到不丢弃每一粒粮食的人,会生出欢喜心,赐福给他们。
一粒米重如山
一个人在童年所接受的观念,无论它来自谣曲、格言或俗语,会牢固地烙在心底,终生明晰。就是说,你在成年之后用理性的、分析的手段也无法驱逐这种观念。
童年的心地是一片空旷的、满是蜂蜜的田野,即使一片羽毛飘下来,也会牢牢粘住。
我长久不忘的一句话,来自童年,是母亲说的:
——一粒米重如山。
这话的本意是珍惜粮食,但它对我却没有止于这一层含义,如戒律、或更神秘的谶语。每粒米在我眼里非常神圣。我感到对粮食的轻狂会导致一场莫名的灾难。
因此我吃饭不敢剩饭粒,脚踩地上的米粒则不自在。倘若在街上看到垃圾里有白花花的大米饭,便要触目惊心。这时,那句话不召自来。
——一粒米重如山。
山可以把人压死,你怎么敢去亵慢?尽管我曾用各种道理试图解开这个可怕的来自米的威胁,但无效。每当心思在剩饭之间犹疑时,它在心里朗朗响起——一粒米重如山。
我摆脱不了它,只好顺从。如同拜物教的一种,也可以叫“恐米症”。
恐惧是一种古老的情感,从人类早期开始,一直追随到今天。对一些不明白的事情,不妨去怕,反能心安。现代人的问题不是怕得太多,而是什么都不怕。在这种心态下受到伤害最多的是环境与资源。如今,科学把中国人的心灵从鬼神的阴影下解放出来,同时又为生活提供了便捷与富足的可能,仿佛一个挥霍的时代已经到来。在这种“什么都不怕”的境况下,环境日益恶化。譬如中国已经成为造成大气臭氧层破坏的有害气体排放国,譬如黄河断流、甘肃的月牙泉干涸、治理前的淮河甚至不能供养微生物,以成毒河。这样的例子太多,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怕,而不管子孙后代有没有饭吃。
佛教中有“不杀生”之说,这种庇护不仅包括了人也包括了野生动物。伊斯兰教在“斋月”期间、太阳彻底落山之前信徒不能进食。饥饿感导致怜悯心,一个从来不知道饥饿滋味的人永远也不会怜悯穷人,同时“斋月”也是对资源中最重要一种——食物的珍重,使人想念并爱粮食,像我一样不敢踩在粮食身上。而基督徒要在每餐之前背诵祈祷文。他们赞美上帝的时候选在吃饭之前,大有深意,实际是在赞美人类得以苟活到每一顿饭的理由是由于他们仍然据有资源,包括产生资源的环境。基督徒把这样的赞美献给上帝。事实上,每一种宗教包括民间禁忌产生的原始动因,都包括了这样的考虑:人的生存与使其生存的环境之间的共生关系。如果一个人不敬畏粮食,那么天地间还有什么其他可以敬畏的东西吗?如果一个人不爱护环境,那么他到底要爱什么呢?在成为人的食物之前,米是庄稼,是漫山遍野的精灵,是土地怀里的孩子,是天神牧养的畜群,是生长绿色的种子,是陆地结的珍珠。
我在电视里看到,当东北的灾民在屋顶被救到船上时,他们死死盯着在洪水里露出一点穗的高粱,泪水旋眶。那种神色,如与亲人执手诀别。对佛门中人来说,“不杀生”,甚至包括了不损害一草一木的含义,它们均有佛性,哪敢随意摧折。佛经中透露过这样的意思,草木虫蚁不仅有佛性,而且可与释迦牟尼平等,谁敢害它们?
我的朋友、小说家郭雪波是我同乡。一次他说,咱们科尔沁人实际信萨满教,信奉多神。山里树上都是神,谁也不敢砍树。我一想,的确如此,故乡人不砍。不久前我在西康的贡嘎雪山脚下的一间客栈里和藏人聊天。他们信本波教,也是多神教。
我问,树上有神吗?一个红脸膛的名字叫安波的藏人自豪地说,那当然。我说,谁也不砍树?他说,那当然。在风雪中,我一下子想起郭雪波说过的话,人那么聪明干嘛?哪如信萨满教,至少树们平安。郭和我一样,无比爱树。
我在信萨满教之前,已经奉行“拜米教”。虽然有虚伪的时刻,譬如饭馊了,我指使媳妇倒掉,勿使吾心不安。假如是剩菜我则弃之并不手软,因为心里没有“一粒米重如山”这样的芥蒂。尽管饭菜在生物学上都叫蛋白质或碳水化合物,在经济学上叫资源。
童年的观念会有这么大的力量,我则盼望天下母亲在为孩子开蒙之时,把爱护环境与珍惜资源输入孩子的头脑,使其奉行终身,这实在比乱七八糟的知识,以及钢琴书法等末流小技更合人性。一位优秀的母亲会在生活中找到一个小小的又是常常见到的东西放在孩子的心上,让他毕生恭谨,譬如——一粒米重如山。
我母亲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母亲。
(全文完)
发稿编辑/姬鸿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