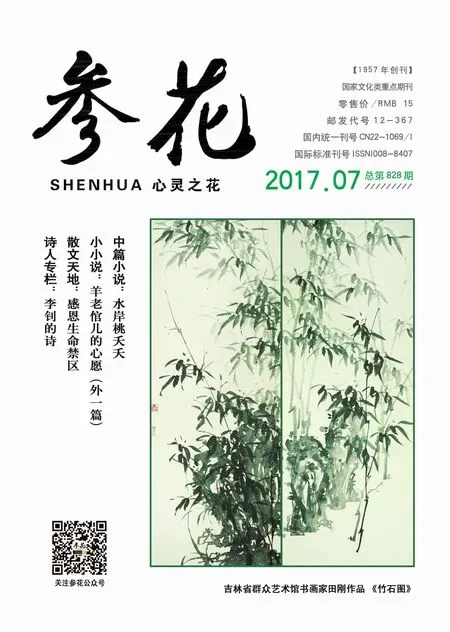人文关怀与底层意识
——观曹征路《那儿》中的新人民性
2017-03-24张超
◎张超
人文关怀与底层意识
——观曹征路《那儿》中的新人民性
◎张超
新世纪初,底层文学写作成为探讨的热点,它本身继承并衔接着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传统,在新世纪新的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下形成“新人民性”的文学特色。作为底层写作旗手之一的曹征路,所创作的《那儿》鲜明地展现了传统产业工人所携带的“神性”特质在今天的境遇,其批判现实的手法源自左翼文学的传统资源,以其“新人民性”的时代特征实现对左翼文学传统的衔接。
《那儿》 底层文学 新人民性
孟繁华在“崛起的福建小说家群体”研讨会上,针对林岚的小说创作,提出“新人民性”的概念。“新人民性”是指文学不仅应该表达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表达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愿望,同时也要真实地表达或反映底层人民存在的问题。在揭示底层生活真相的同时,也要展开理性的社会批判。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和民主,是“新人民性文学”的正义。在实现社会批判的同时,也要无情地批判底层民众的“民族劣根性”和道德上的“底层的陷落”。因此,“新人民性文学”是一个与现代启蒙主义思潮有关的概念。[1]这一“新人民性”概念的提出,为左翼文学与当代底层文学间的关系做出了十分清晰的说明与解释。
一、底层文学的新人民性与左翼文学的“神性”异曲同工
对林岚文学作品的讨论可以说是学界对底层文学讨论的开端。到了2005年,随着曹征路《那儿》的发表,引起了批评界对底层文学更为广泛的探讨。小说塑造的主人公“我小舅”是国有企业的工会主席、省劳模、副县级干部,在国企改革中,他看到国有资产被个人侵吞,工人阶级被“领导”出卖,他为了给工人们讨个公道,上访北京。但在被市领导找去谈话后,他心目中坚信不疑的世道公理竟被领导驳回。小说中虽没有直接描写这段冲突的经历,但是“我”在他刀刻斧凿的脸上却看到“一种神性的光辉”。这种神性源自朱主席对自身传统产业工人身份的认知与认同,同时这“现实”中的“神性”其实也是朱主席绝望的挣扎。最后,他用气锤砸碎了自己的头颅,奏响了工人阶级的挽歌。在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作品中,“神性”是小说主人公的一个普遍特征。茅盾笔下的吴荪甫是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虽然他依靠国民党军警来镇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表现出封建性的一面,但是他仍具有强烈的国家和民族意识,在外遇帝国主义经济打压、内逢买办资产阶级暗算的恶劣环境下,仍与赵伯韬等人展开着殊死的较量。在动荡时局中,吴荪甫怀着振兴民族工业的雄心,期待开创一个时代;朱主席在改革浪潮中则是怀着“英特纳雄耐尔”的决心去挽留一个时代,两者都具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信仰,矢志不渝地为一个群体寻求安妥的“神性”。小说也正是在通过朱主席这个人物表现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的同时,表达了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愿望。
二、左翼文学的特质
左翼文学源起于20世纪30年代“左联”的文学创作。由于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左联”自身的阶级视角和“国防文学的提出”,对其创作的文学作品有所“规训”,文学作品在政治需求和时代诉求的规约下,形成有限的话语空间,并形成了一股“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创作思潮。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左翼文学也在不断地变化、更新和延异。在当代文学思潮下,文学作品不再是单一的政治话语。在八九十年代,文学作品的创作一直试图摆脱政治因素的束缚,希望完成中国自“五四”以来的第二次文学启蒙。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经历伤痕、反思、寻根、改革等文学思潮,逐渐向着“纯文学”的方向发展,其先锋性不断凸显,且更加重视语言及形式的创新。值得注意的是,在八九十年代的主流文学创作中,虽然力图去政治化,但是作家及同时代知识分子仍旧将个人与时代和社会相结合,在诸多文学作品中塑造出一个“大写的人”,在将人的个性与合理欲望加以展现并进行肯定的同时,将个人放入全社会的浪潮中加以塑造,而且作家也以社会性和时代性的视角,通过文学作品审视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代作家大多和共和国一同成长起来,鉴证历史的流脉,有极大的社会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在90年代末期,“新写实”写作异军突起,以其更为纯粹的个人化叙事吸引了读者的眼球,但由于其过于琐碎地记述个人生活,而暴露出其创作弊端。虽然其中的女性主体意识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大众传媒市场化和消费化的过程中,这样“琐碎的女性写作”的价值却体现在了满足男性读者的猎奇心理上。在同时期的先锋写作和“纯文学”写作中,文学作品越发重视语言和形式的写作,以期摆脱所有的外在的社会历史因素,而醉心于“文字的游戏”当中。这是在新时期以来,文学自身发展道路上的一个极值点,但是它恰恰忽视了文学即“人学”这一重要属性,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社会关系与社会责任在文学作品当中的体现。在长久地脱离创作源泉以后,“纯文学”的创作亦日渐干瘪。在新世纪,80后作家快速成长,一个典型的代表是践行了当代“成功学”的作家——郭敬明。他的作品以《小时代》为标志,大时代也许只是文学作品当中的背景摆设,故事的主人公则是围绕着自己特有的小生活圈展开叙述。另外,甫跃辉以一名“城市中的他者”作为故事主人公的小说创作,通过“意识流”的写作手法,更传达了青年一代在城市生活中的孤独与幻灭。 但都“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
三、“新人民性”文学与左翼文学的衔接
在这样的文学思潮嬗变的过程中,文学作品与左翼传统,即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关注人生人性,剖析社会生活,反映社会问题的写作传统和写作精神,渐行渐远。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暴露出中国社会在现代性过程当中的种种社会问题。在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冲击下,个人的欲望与诉求得到前所未有的肯定,人们迎来了一个个性张扬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困惑之下,以林岚、曹征路等作家为代表的“底层写作”登上当代文坛,获得广泛的关注。他们的创作大多以社会底层人的生活为创作素材,通过对他们苦难境遇的书写,传达出当下工农底层生活和境遇。鲁迅在写给友人李秉中的信中曾说:“然以昔曾弄笔,志在革新。故根源未竭,仍为左翼作家联盟之一员。”曹清华提出,这表明鲁迅于左翼作家身份之上寄托的是他未竭的革新知之志。事实上,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所强调的就是他对左翼的看法。他所谓对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以及反对关在屋子里、高谈彻底的主义,便是要求左翼作家承担起关注现实、追求革新的社会责任。[2]进行底层写作的作家们,以现实主义为创作手法,以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经历为叙述体裁,以进行社会剖析和批判为核心创作意旨。可见,当代底层文学延续着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左翼精神内核。但是随着文学思潮交替与变更,今天的左翼精神已不再是30年代的受到左联“规约”、肩负政治使命的文学创作精神。因此,更为准确地说,当代底层文学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转型和延异。
[1]刘中树,张学昕,主编.学院批评文库[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9.
[2]曹清华.何为左翼,如何传统[J].学术月刊,2008(01).
(责任编辑 葛星星)
张超,男,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