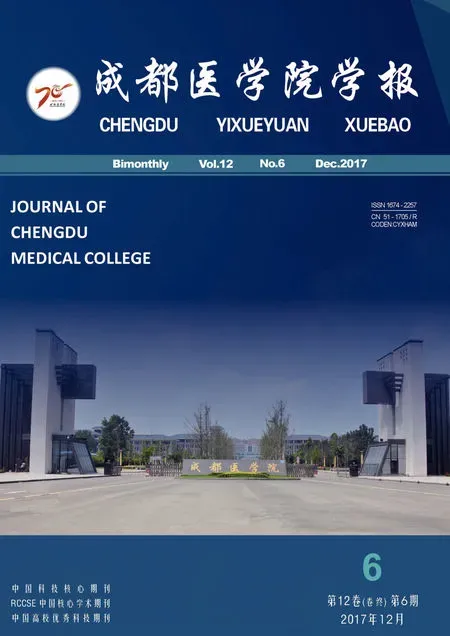轻度认知障碍研究现状*
2017-03-24邱月虹罗跃嘉
邱月虹 ,王 晶,罗跃嘉,2,关 青,2△
1.深圳大学 心理与社会学院(深圳 518060);2.深圳市情绪与社会认知科学重点实验室(深圳 518060)
·综述·
轻度认知障碍研究现状*
邱月虹1,王 晶1,罗跃嘉1,2,关 青1,2△
1.深圳大学 心理与社会学院(深圳 518060);2.深圳市情绪与社会认知科学重点实验室(深圳 518060)
轻度认知障碍;认知神经科学;老龄化
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发达国家人口负增长趋势加剧,人口老龄化已成为21世纪的全球性问题。在当今中国,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人口增长率得到了明显控制,但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受增长惯性与周期性等因素影响,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如何正确对待老龄化以及如何防治老化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促进成功老化已成为当今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轻度认知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 被看作AD的预警信号,相对于AD的不可逆性,早诊断和早干预 MCI更具意义。随着神经科学研究技术的发展,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等已广泛应用于实践,这为MCI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持,为进一步探索MCI的相关脑机制奠定了基础。
1 相关概念界定
1.1 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成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1]。1982年,联合国第97届会议规定,划分老龄化的标准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者>65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即标志着这个国家或者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
1.2 正常老化与成功老化
正常老化为无疾病老化[2],指与增龄相关的功能状况无改变或改变甚微的老年人群。主要特点有:1)正常老化者脑内神经纤维保持良好,海马体积无明显缩小,脑室无明显空洞[3];2)正常老化者对情节记忆、一般知识和习惯性动作保持相对完好,操作性记忆和学习能力总体保持完好[4-5];3)正常老化者生活可自理,人际关系良好[6]。常态老化是指有与增龄相关的改变,但未达到病理变化和残疾程度的老年人群,或介于病态老化和成功老化之间的“正常人群[7]”。目前,国际上采用S4标准界定成功老化的评价标准[8]。
1.3 MCI
流行病学中,MCI代表除认知正常和痴呆之外的内涵广泛、程度各异的认知状态,可以由任何病因造成,病情可以好转、稳定或进展为完全痴呆。MCI作为介于正常老化和痴呆之间的一种临床状态,主要表现为患者出现与年龄不相称的记忆力下降表现(典型的记忆减退),亦可出现其他认知功能轻度损害,但还不足以影响患者的社会及工作职能,未达到痴呆的诊断标准[9]。其核心症状是认知功能减退,根据其病因或损害位置不同,可累及记忆、语言、执行功能、结构技能等一项或多项功能损害[10]。依据患者是否存在记忆领域内的认知功能损害,MCI被分为两大类:遗忘型MCI与非遗忘型MCI。MCI作为介于正常老化与痴呆之间的过渡阶段,是痴呆早期诊断研究中最活跃的部分,它为痴呆症的防治提供了一个“机会之窗[11]”。此外,相较于发病率为1%的不可逆性痴呆,发病率在14%左右的MCI更具预防和干预的意义[12],对提前干预痴呆“窗口期”及推动成功老化有重要作用。
1.4 AD
AD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13],以记忆障碍为主,辅以失语、失用、失认、空间视觉和执行功能损害,并伴随人格和行为改变的全面性痴呆[14]。AD病因未明,但研究发现,早老蛋白ps-1、ps-2等遗传基因[15]、教育水平[16]、器质性损伤如脑梗塞[17]等都是AD发病的高危险因素。目前把65岁以前发病者划分为早老性痴呆;65岁以后发病者称老年性痴呆[14]。
1.5 MCI与AD的区别与联系
MCI的认知功能损害一般只局限于一个或者几个认知领域,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完好,达不到痴呆标准。MCI是AD的预警信号,可以进展为AD,所以MCI也被称为过渡时期。AD则以全面痴呆为主,认知功能多领域受损,符合痴呆的诊断标准,患者日常生活基本无法自理,且该病具有不可逆性。从病理方面来看,神经元的丧失是区别MCI和AD的重要指标。有研究发现,在海马-海马周围结构中,尤其是内嗅区皮质有大量的神经元坏死以及患者的Meynert基底核区胆碱能神经元减少15.0%以上证明其为AD,反之则为MCI[18]。根据Tierney等[19]的研究,MCI向AD转化的平均年转化率为10%~15%,5年转化率高达50%以上,远远高于普通老年人,因此MCI被很多学者公认为“痴呆前期状态”,代表着AD的极早期状态。
2 MCI的分型
Peterson等[20](1999)认为,MCI主要有3种类型:1)遗忘型;2)单个非记忆认知区域损害(single non-memory MCI, s-nmMCI);3)多个认知区域的轻度损害或称为认知型轻度认知损害(multiple-domains MCI, m-dMCI)。
2.1 遗忘型轻度认知障碍(amnestic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aMCI)
aMCI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发展成AD的类型,aMCI 主要分为aMCI-s和aMCI-m,是aMCI不同发展阶段的表现[21]。其中,aMCI-s以孤立的记忆障碍为主,aMCI-m则涉及记忆、语言、执行等多个认知损害。有关MCI的影像研究表明,遗忘型MCI患者与正常老年人的区别主要是海马体积的减少[22]。除此之外,大部分遗忘型MCI患者都存在内侧颞叶结构神经性病变,因此导致其操作性记忆任务障碍[23]。虽然遗忘型MCI对AD有着高转化率,但适当的记忆训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记忆功能,防止病情恶化[24]。
2.2 非遗忘型轻度认知障碍(nonamnestic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naMCI)
2.2.1 s-nmMCI/m-dMCI 该类型MCI以单纯语言、行为障碍为主,患者其他认知功能保持正常,属于非遗忘型MCI。此外,此种类型的MCI可发展为原发性进行性失语或者额颞痴呆[9]。单个非记忆认知区域损害转化与aMCI的转化不尽相同,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发掘。m-dMCI和s-nmMCI都属于非遗忘型MCI,该类型症状相对较重,但仍达不到痴呆标准,容易发展为AD及其他相关疾病[9]。
2.2.2 血管性轻度认知障碍(vascular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vMCI) 即脑血管疾病引起的MCI,vMCI也属于非遗忘型MCI,其症状较严重,治疗效果较差,且极易发展为AD。类似于这种脑部器质性疾病引发的MCI均包括在MCI分型范畴中。周爱红等[25]研究显示,高血压患者更易患皮质下小血管病,而这正是vMCI的危险因素之一;而糖尿病也作为vMCI的一个高危因素,它可通过引起脑血管疾病或者其他神经退行性病变而引发认知障碍,这提示我们在日后的治疗中可通过控制血压和血糖水平预防和控制MCI 的发展。除此之外,酒精成瘾也会导致患者形成酒精依赖型MCI,针对这类患者,当务之急是戒酒和监控其血压水平,防止其症状进一步恶化。
3 MCI的诊断标准
Kral[26]于1962年最早提出了“良性老年健忘症(benign senescent forgetfulness, BSF)”的概念,该症被看做MCI的前身。1982年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进一步提出了“年龄损害记忆(age-associated memory impairment, AAMI)”的概念[27],其强调的是与年龄相符的记忆减退,记忆测验得分低于年轻成年人至少一个标准差。目前临床上对MCI的诊断依赖一系列综合检查,具体流程如下。
3.1 病史采集与体格检查
病史采集分为现病史与既往病史。现病史包括了解患者的发病时间、具体表现、病情进展等,掌握该患者身上的具体症状,有无并发症,以及初步掌握发病线索与致病原因;既往病史则关注患者患病前是否罹患器质性疾病、颅脑外伤等有可能导致MCI的疾病,尤其应注意患者精神发育状况,是否吸烟、酗酒、中毒等。而体格检查主要针对患者有无明显的躯体症状,如周围神经病变等,这些都可对MCI的病因诊断提供线索[28]。
3.2 神经心理评估
目前,国际上通用的MCI诊断标准为:1)主诉记忆障碍,且有知情者证实;2)总体认知功能正常,但可有某一认知方面的变化,例如语言、记忆、执行功能、空间信息加工等;3)日常生活能力正常,可以自理;4)与相同年龄和教育程度者比较存在记忆损害,记忆功能评分在匹配组分值1.5标准差以下;5)不够痴呆诊断标准[19]。
此外,临床痴呆评定量表(clinical dementia rating, CDR)评分0.5分,简易精神状态检查表(mini-mental state of examination, MMSE)>24分均可作为诊断MCI的辅助标准[29]。
3.3 影像学检查
影像学检查主要借助于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和fMRI等技术,一方面通过给患者颅脑进行断层扫描定位患处,另一方面可确定类似梗死、积水、肿瘤等致病原因;fMRI能有效区分MCI的特异性,目前用于诊断与监测病情。此外,在基础研究中还常采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术(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和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术(single-pho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 SPECT),了解组织器官的血液灌注和代谢情况,探讨具体功能的变化发展[28]。
4 MCI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
4.1 行为学研究
在行为学方面,20世纪90年代涌现的转基因痴呆动物模型是一种间接性研究,但直到目前尚无一种痴呆动物模型能够完全模拟人类痴呆的病理学过程和临床特点,不能完全解释人类疾病过程,仍需人体验证,但可能最终获得相反结果。而国内有研究[30]探讨MCI的精神行为症状特点,运用神经精神问卷(neuropsychiatrie inventory, NPI)以及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综合评估被试的精神行为症状,通过对照研究发现,MCI患者更易产生包括激越、易激惹、睡眠行为等精神行为症状,在饮食习惯等方面与正常组无明显差别。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MCI在行为学上的特异性,对日后临床诊断与区分有重要意义。但由于目前针对MCI与其他老化型认知疾病的划分界限尚较模糊,因此精神行为症状只能作为参考和附加指标运用在临床研究中。除此之外,有研究[31]发现,适当的行为锻炼,如力量、柔韧性、平衡感、精细活动以及日常生活能力锻炼等,对MCI患者控制病情延缓发展有积极作用;尤其是心理干预与疏导,可适当减轻MCI患者对患病的羞耻及挫败感,为后期治疗和康复提供支持[32]。
4.2 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
4.2.1 神经影像学 已有相关研究[33]表明,通过利用fMRI技术,可明显找到MCI在脑结构上的标志,MCI患者相比于正常老化的个体,其海马体积有明显缩小(但尚未达到AD的水平),且其萎缩的程度与发展为AD的可能性呈正相关。这也是目前可以借鉴的用以区分MCI和AD的手段之一。但仍有不足的是,海马萎缩并不能显示出MCI和AD的特异性,根据抑郁症的神经可塑性假说,该症状也可存在于其他类似于抑郁症等疾病中[34]。国内主要利用fMRI研究MCI患者的计算能力、视空间能力等层面的脑神经机制,对于精确定位脑区域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fMRI在记忆功能的研究中已取得相当大的突破,关于情境记忆、语义记忆以及工作记忆的脑区域定位,已发现MCI患者词语辨认和代偿机制与常人的差异[35]。fMRI虽具有精确度高等优点,但仍存在造价昂贵、无法大规模普及等局限性。除此之外,另有PET研究发现,MCI患者大脑局部的葡萄糖代谢及灌注与正常老化者存在差异,荧光标记脱氧葡萄糖-PET(FDG-PET)发现向痴呆转化的MCI者,右侧颞顶皮质及内溴皮质的局部葡萄糖代谢降低,相应的血流灌注也降低。该影像学研究结果可用于预测痴呆转化的MCI(正确率为56%~75%),在此基础上,再将其与神经心理评估(如视空间功能)相结合,则预测的准确率最高可达90%[9,36]。不仅如此,Wolf等[37]通过利用现已成为研究MCI及AD的有力工具的SPECT技术,发现在顶叶血流量和葡萄糖代谢程度上,MCI患者和正常老化者也存在差异,MCI患者顶叶血流量和代谢程度有轻度降低,且两侧半球不对称,这一发现对进一步认识MCI有重要意义。
4.2.2 神经电生理研究 如今,神经电生理的技术发展迅猛,在心理学领域中的应用也日益增加,目前MCI的神经电生理研究主要运用ERP技术,ERP通过有意地赋予刺激以特殊的心理意义,利用多个或多样的刺激引起相应的脑电位[38]。其中,P300作为ERP研究的一个重要成分,已在脑疾病尤其是痴呆性疾病等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广泛应用。Golob, Johnson和Star(2002)通过对比MCI患者与正常老化者,发现MCI患者P50 波幅增加, P300潜伏期明显延长, 这表明MCI患者大脑多区域综合信息处理能力降低,注意力减弱,这与AD相似, 然而其N100、P200、N200成分与正常老化者并无显著区别, 表示该类患者在知觉过程、刺激识别等方面功能相对完好,达不到痴呆标准。该研究为MCI的脑机制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也在另一方面为ERP技术在MCI领域中的使用展现了新的路径[39-40]。除ERP外,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m, EEG)技术也是研究MCI的热门手段,Brunovsky等[41](2003)利用EEG来诊断痴呆,该研究发现,不同程度(轻、中、重)痴呆患者的α波均表现为减少,并且δ波增多,因此推测这种表现与痴呆程度有着高度相关。EEG技术虽然对研究痴呆患者的大脑功能区域有重要作用,但由于EEG技术的时间分辨率不如ERP,其对于进一步区分AD和MCI以及精细的时间和空间定位方面还存在较大局限性。
4.3 生物及遗传学领域研究
国外研究者发现,MCI患者和AD患者的ApoE4基因存在差异。在70岁之前,AD患者的ApoE4出现频率增加,然而MCI患者却并没有变化。除此之外,在年龄较小的群组中,ApoE4基因也被看作是提示MCI向AD转化的一个重要标志[42]。但目前尚缺乏强有力的证据证明ApoE4基因与认知水平与记忆能力退化直接相关,因此目前对该基因的研究及其作用还存在较大的争议和空白[43]。除了ApoE4基因,CSFtau蛋白也是目前用于AD诊断的标记之一。有相关研究表明,CSFtau蛋白水平升高与MCI发展成为AD有相当大的关联,这也说明了CSFtau蛋白水平对预测MCI患者向AD转化的可能性有一定的参考价值[44]。有研究[45]认为,大脑电信号传导中断可能是导致β-淀粉样蛋白积累的原因,恢复神经回路产生特定电震荡可激活免疫细胞并清除大脑中的β-淀粉样蛋白,实验中采用特制的LED灯以消除小鼠体内的β-淀粉样蛋白积累。此外还有研究[46]通过高半胱氨酸水平以及高水平的低密度脂蛋,或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等方面,研究老年人认知功能下降的危险因素。但目前的生物学研究大多存在证据不足的情况,尚未出现公认的生物学标记,无法进一步验证特异性或标志性因素[47]。
4.4 MCI的相关因素研究
MCI作为一种多因素疾病,其病因不能由已熟悉的神经或精神疾病解释,目前针对MCI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遗传生物学:生物学领域已公认神经纤维缠结、β-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是AD主要影响因素[48-49],在早期AD患者中就已出现老年斑及神经纤维缠结,而MCI作为AD的极早期阶段,研究MCI患者脑脊液中β-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对MCI诊断和AD预防都有重要意义[50]。2)人口学因素:增龄是MCI独立危险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MCI的发病率也随之升高[20];由于工作性质、生活习惯的不同,男性的认知能力衰退较慢,相比女性MCI的发病率更低,这提示性别因素可能对MCI有一定影响[51];此外,教育水平、经济状况、居住地等,均对MCI发病造成一定影响。3)生活方式:不良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如酗酒、吸烟等[52])会增加MCI的发病概率并加剧向AD转化的风险。目前公认的防治MCI的方法主要是保持规律健康的生活习惯,多参与体力与脑力锻炼,获得良好的社会支持等[53-55],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较少,因此其具体机制与方案尚不清楚。4)血管危险因素:脑器质性疾病(如脑卒中、糖尿病、动脉硬化、心脏病等)是MCI发病的高危因素,并且该类型MCI向AD转化的风险非常高[56]。其中,高血压的影响最明显,血压升高会对记忆、注意等领域造成损害,从而影响MCI的发生发展[57]。
4.5 目前MCI研究的局限性与困难
当今MCI的诊断工具主要以量表为主,涉及主观陈述部分较多,量表组成因研究而异,导致诊断标准无法统一,与正常老化、AD的划分标准尚不明确,标准化程度较低,进而限制了有关MCI的转化机制研究。当务之急是使概念、诊断标准和研究方法统一起来,建立标准化的研究工具和实验方案。另一方面,面对不同国家、文化背景下的特定人群,目前尚无针对性的测量工具,这对MCI的敏感性研究和临床干预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此外,MCI作为一种重要的老年认知疾病,目前针对该群体高级认知功能老化机制的研究尚待挖掘。
MCI属于老年慢性病的范畴,由于病情回溯存在很大的困难,加之老年人对自身状态察觉不足,缺乏相应医学常识以及文化水平有限,这对目前的研究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4.6 MCI研究的发展前景
未来针对MCI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以下几点。1)制定标准化、专业化的评价标准,明确正常老化、MCI和AD的划分界限。这是研究MCI的基础,必须从认知发展的角度入手,探究不同潜在发病机制对认知衰退过程的影响。2)完善测量工具及手段,鉴于MCI的特异性,筛查工具应考虑老年人视力、听力、肢体残障等方面,计算机软件的升级运用将对MCI筛查起到技术革新的作用[58]。3)电生理技术主要指ERP、EEG、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等,随着各种方法和指标的革新,研究者越来越关注神经突触活动在MCI和AD中的变化,挖掘其在痴呆预测、转归及治疗方面的价值,与其他各项辅助检查相结合将成为未来研究的热点方向[59]。而在影像学领域,近年来除了fMRI,空间探测脑磁场的脑磁图(magnetoencephalography, MEG)、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磁共振波谱分析(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MRS),光学成像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技术(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fNIRS),以及传统的X线放射影像和超声影像技术等,在MCI研究中的应用也愈发广泛,综合运用这些手段将可以从形态学、功能、代谢等角度对MCI进行诊断研究,有助于提高MCI诊断的准确性和特异性[60]。4)中医学认为,MCI病位在脑,脾胃亏损所致肾精亏虚是发病根本。提倡补益、化痰活血为主的治疗手段,对改善MCI患者认知能力、提高血清乙酰胆碱等有积极的治疗作用[61-62],因此将中医运用于MCI的防治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突破口。5)在生物遗传学方面,有研究[45]为MCI和AD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未来针对MCI的研究也在向无创治疗、多靶点治疗迈进。MCI的基础研究也越来越关注于从分子水平上寻找MCI的发病机制。目前,多学科交叉研究已成为研究MCI的热点方向,通过综合利用各技术手段、整合各学科研究成果,可以更全面地研究MCI的发病机制及转归、治疗与愈后,并进一步挖掘其与AD的区别与联系。
5 小结
综上所述,MCI在老龄化趋势日益严峻的今天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研究热点,目前前期的MCI的诊断与研究主要集中于认知神经、行为研究、生物遗传及社会学等领域,其为进一步研究脑老化的神经机制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其尚且缺乏标准化的测量工具和界定标准,难以确定干预时间窗和转化趋势,使其研究尚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在之后的研究中,不仅要构建MCI的结构及预警模型,设计多维成套的标准化认知评估工具,更要注重研究的细化和深入,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对MCI展开研究。
[1]孙艳波. 人口老龄化现状与护理方向[J]. 中国现代药物应用, 2013, 7(9): 199-200.
[2]Killiany R J, Meier D S, Guttmann C R. Image processing: global and regional changes with age[J]. Top Magn Reson Imaging, 2004, 15(6): 349-353.
[3]Wenk G L. Neuropathologic changes in Alzheimer's disease[J]. J Clin Psychiatry, 2003, 64(Suppl 9): 7-10.
[4]刘阳. 正常老化与轻度认知损害[J]. 国外医学(老年医学分册), 2009(3): 132-134.
[5]Davidson M. Alzheimer’s disease and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J]. Dialogues Clin Neurosci, 2009, 11(2): 109.
[6]王琼宇, 李凌波, 邓铸, 等. 老年人的老化态度与认知老化的关系[J]. 心理技术与应用, 2016, 4(6): 336-343.
[7]吴文源. 成功老龄的研究概况[J]. 中华全科医师杂志, 2006, 5(6): 337-339.
[8]李春波, 张明园, 张新凯. 成功老龄的初步研究:判别标准及其相关因素[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00, 20(2): 67-69.
[9]赵永波, 周晓琳. 轻度认知障碍[J]. 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 2004, 4(5): 389-392.
[10] 郭起浩, 徐岩. 不同病因所致轻度认知功能损害的神经心理检测比较[J]. 内科理论与实践, 2015, 10(2): 92-94.
[11] Austrom M, Lu Y. Long Term Caregiving: Helping Families of Persons with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Cope[J]. Current Alzheimer Research, 2009, 6(4): 392-398.
[12] Huang J, Meyer J S, Zhang Z,etal. Progression of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to Alzheimer's or vascular dementia versus normative aging among elderly Chinese[J]. Curr Alzheimer Res, 2005, 2(5): 571-578.
[13] 黄滨, 韦海楼. 阿尔茨海默病病人的护理进展[J]. 护理研究, 2016, 30(12): 1422-1424.
[14] 陈心怡, 杜怡峰. 神经肽与阿尔茨海默病相关性的研究进展[J]. 中华神经科杂志, 2017, 50(1): 63-66.
[15] Scheuner D, Eckman C, Jensen M,etal. Secreted amyloid beta-protein similar to that in the senile plaques of Alzheimer's disease is increased in vivo by the presenilin 1 and 2 and APP mutations linked to familial Alzheimer’s disease[J]. Nat Med, 1996, 2(8): 864-870.
[16] 闫洁, 袁森. 老年人阿尔茨海默症发病及患病相关因素研究[J]. 中国疗养医学, 2016, 25(5): 550-551.
[17] Schneider J A, Wilson R S, Bienias J L,etal. Cerebral infarctions and the likelihood of dementia from Alzheimer disease pathology[J]. Neurology, 2004, 62(7): 1148-1155.
[18] Estévez-González A, Kulisevsky J, Boltes A.Rey verbal learning test is a useful tool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in the preclinical phase of Alzheimer's disease: comparison with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normal aging[J].Int J Geriatr Psychiatry, 2003,18(11):1021-1028.
[19] Tierney M C, Szalai J P, Snow W G,etal. Prediction of probable Alzheimer's disease in memory-impaired patients: A prospective longitudinal study[J]. Neurology, 1996, 46(3): 661-665.
[20] Petersen R C, Smith G E, Waring S C,etal.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clinical characterization and outcome[J]. Arch Neurol, 1999, 56(3): 303-308.
[21] Writing Goup of the Dementia and Cognitive Society of Neurology Committee of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Alzheimer's Disease Chinese.Guidelines for dementia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China: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J]. Zhonghua Yi Xue Za Zhi, 2010, 90(41): 2887-2893.
[22] Arnáiz E, Jelic V, Almkvist O,etal. Impaired cerebral glucose metabolism and cognitive functioning predict deterioration in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J]. Neuroreport, 2001, 12(4): 851-855.
[23] 柏峰, 张志珺, 宇辉, 等. 轻度认知障碍老年人情节记忆功能的磁共振成像研究[J]. 中华精神科杂志, 2008, 41(1): 29-32.
[24] Rapp S, Brenes G, Marsh A P. Memory enhancement training for older adults with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a preliminary study[J]. Aging Ment Health, 2002, 6(1): 5-11.
[25] 周爱红, 魏翠柏, 秦伟, 等. 皮质下小血管病所致轻度血管性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及临床特征[J]. 中华神经科杂志, 2011, 44(3): 167-170.
[26] Kral V A. Senescent forgetfulness: benign and malignant[J]. Can Med Assoc J, 1962, 86: 257-260.
[27] Crook T, Bartus R T, Ferris S H,etal. Age-associated memory impairment: Proposed diagnostic criteria and measures of clinical change-report of a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work group[J]. Developmental Neuropsychology, 1986, 2(4): 261-276.
[28]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写作组. 血管性认知障碍诊治指南[J]. 中华神经科杂志, 2011, 44(2): 142-147.
[29] Petersen R C, Thomas R G, Grundman M,etal. Vitamin E and donepezil for the treatment of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J]. N Engl J Med, 2005, 352(23): 2379-2388.
[30] 张贵丽, 刘帅, 任志宏, 等. 不同类型轻度认知障碍的认知损害及精神行为症状的比较分析研究[J]. 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 2015, 32(3): 214-219.
[31] 祝小丹, 邝景云, 谭连芬. 轻中度老年期认知功能障碍患者认知行为干预的效果观察[J]. 护理学报, 2014, 21(9): 56-59.
[32] 刘坤. 行为干预和心理疏导对老年轻度认知障碍患者的影响与效果分析[J]. 医学信息, 2013(17): 95-96.
[33] Jack C R Jr, Petersen R C, Xu Y,etal. Rates of hippocampal atrophy correlate with change in clinical status in aging and AD[J]. Neurology, 2000, 55(4): 484-489.
[34] Anisman H, Matheson K. Stress, depression, and anhedonia: caveats concerning animal models[J]. Neurosci Biobehav Rev, 2005, 29(4/5): 525-546.
[35] 吴小三, 程怀东, 汪凯. 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记忆监测[J]. 中华医学杂志, 2009, 89(15): 1037-1040.
[36] Tabert M H, Albert S M, Borukhova-Milov L,etal. Functional deficits in patients with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prediction of AD[J]. Neurology, 2002, 58(5): 758-764.
[37] Wolf H, Jelic V, Gertz H J,etal. A critical discussion of the role of neuroimaging in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J]. Acta Neurol Scand Suppl, 2003, 179: 52-76.
[38] 易雪岚. 事件相关电位P300在儿科的临床应用[J]. 健康必读(中旬刊), 2012, 11(10): 352-352.
[39] Golob E J, Johnson J K, Starr A. Auditory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during target detection are abnormal in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J]. Clin Neurophysiol, 2002, 113(1): 151-161.
[40] Frodl T, Hampel H, Juckel G,etal. Value of event-related P300 subcomponents in the clinical diagnosis of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Alzheimer's Disease[J]. Psychophysiology, 2002, 39(2): 175-181.
[41] Brunovsky M, Matousek M, Edman A,etal.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 degree of dementia by means of EEG[J]. Neuropsychobiology, 2003, 48(1): 19-26.
[42] 吕小荣, 钟远. 轻度认知障碍及阿尔茨海默病与载脂蛋白E基因多态性的相关性[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2, 32(5): 917-919.
[43] Luis C A, Loewenstein D A, Acevedo A,etal.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J]. Neurology, 2003, 61(4): 438-444.
[44] Petersen R C, Doody R, Kurz A,etal. Current concepts in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J]. Arch Neurol, 2001, 58(12): 1985-1992.
[45] Iaccarino H F, Singer A C, Martorell A J,etal. Gamma frequency entrainment attenuates amyloid load and modifies microglia[J]. Nature, 2016, 540(7632): 230-235.
[46] Smach M A, Edziri H, Charfeddine B,etal. Polymorphism in apoA1 Influences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evels but Is Not a Major Risk Factor of Alzheimer’s Disease[J]. Dementia and Geriatric Cognitive Disorders Extra, 2011(1): 249-257.
[47] Kawas C, Gray S, Brookmeyer R,etal. Age-specific incidence rates of Alzheimer's disease: the Baltimore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ing[J]. Neurology, 2000, 54(11): 2072-2077.
[48] van Rossum I A, Vos S J, Burns L,etal. Injury markers predict time to dementia in subjects with MCI and amyloid pathology[J]. Neurology, 2012, 79(17): 1809-1816.
[49] 韩丽珠, 王文静, 褚忠海, 等. 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脑脊液中β-淀粉样蛋白42及磷酸化Tau蛋白的水平检测及意义[J]. 实用医学杂志, 2014, 30(19): 3079-3081.
[50] Dubois B, Albert M L. Amnestic MCI or prodromal Alzheimer's disease[J]. Lancet Neurol, 2004, 3(4): 246-248.
[51] Lee L K, Shahar S, Chin A V,etal. Prevalence of gender disparities and predictors affecting the occurrence of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J]. Arch Gerontol Geriatr, 2012, 54(1): 185-191.
[52] Barnes D E, Haight T J, Mehta K M,etal. Secondhand smoke, vascular disease, and dementia incidence: findings from the cardiovascular health cognition study[J]. Am J Epidemiol, 2010, 171(3): 292-302.
[53] Grande G, Vanacore N, Maggiore L,etal. Physical activity reduces the risk of dementia in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subjects: a cohort study[J]. J Alzheimers Dis, 2014, 39(4): 833-839.
[54] 戈改真, 汤哲, 贾小青, 等. 北京社区老年人轻度认知障碍与饮食习惯的相关性研究[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09, 29(8): 1025-1026.
[55] 关青, 王春艳, 王利群, 等. 多重干预对早中期老年性痴呆患者综合能力改善的影响[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09, 29(14): 1836-1837.
[56] Li J, Zhang M, Xu Z Q,etal. Vascular risk aggravates the progression of Alzheimer's disease in a Chinese cohort[J]. J Alzheimers Dis, 2010, 20(2): 491-500.
[57] Elias M F, Wolf P A, D'Agostino R B,etal. Untreated blood pressure level is inversely related to cognitive functioning: the Framingham Study[J]. Am J Epidemiol, 1993, 138(6): 353-364.
[58] 张立秀, 刘雪琴. 老年轻度认知障碍的筛查评估工具研究进展(综述)[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8, 22(2): 129-132.
[59] 李晓裔, 邵西仓, 周华东. 神经电生理检查在轻度认知功能障碍中的研究进展[J]. 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2014, 24(5): 61-64.
[60] 刘祥雏. 磁共振成像新技术在轻度认知功能障碍诊断中的应用[J]. 医学综述, 2014, 20(19): 3583-3585.
[61] 曹慧娟, 郁志华, 陈久林. 轻度认知障碍的中医研究进展[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15, 17(8): 1729-1733.
[62] 郭仁真, 周文泉, 罗增刚, 等. 黄连温胆汤加味治疗老年轻度认知障碍痰浊阻窍证的临床研究[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0, 30(1): 33-36.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1.1705.R.20171009.1606.010.html
10.3969/j.issn.1674-2257.2017.06.025
R749.1
A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31571129;31530031 )
△
关 青,E-mail: guanqing@sz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