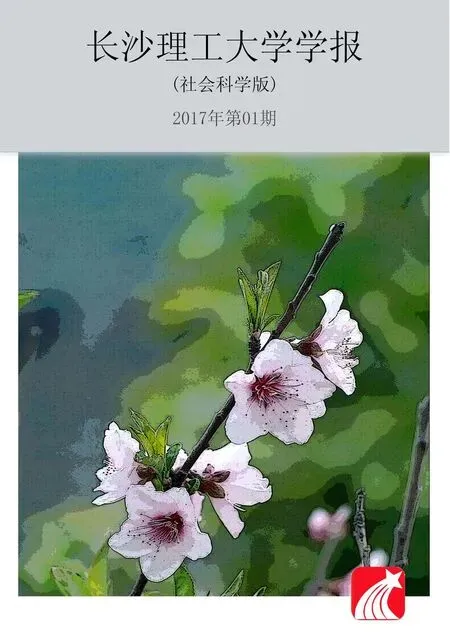中西传统与新诗的现代性
2017-03-23陈太胜
陈太胜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5)
中西传统与新诗的现代性
陈太胜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5)
声音、翻译和新旧之争,是新诗现代性三个最主要的方面。借助诗人本人的翻译这一中介,中国新诗作者立足于中国本土语境,使新诗有了自己不同于旧诗的新的形式,新的声音、语调和思维方式。中国现代诗学对中国古典诗学的批判与接受,是在中国诗人接受了西方诗学影响的背景中进行的。20世纪中国许多诗人的“夭折”,其中很大的原因,即在于他们没有始终以“诗人”自命,没有将书写“诗人之诗”作为自己终生的使命。
新诗;现代性;传统;声音;翻译
一
讨论与中国新诗有关的问题,或称为中国现代诗学研究(这里诗学研究的对象特指中国现代的新诗),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我在《声音、翻译和新旧之争——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之路》一书①中从个人感兴趣的角度来谈。
我一直关心的问题是:“新诗”到底是什么?当然,它是“诗”,而且是“新的诗”。“新诗”之“新”,是因为它的历史据说从胡适开始尝试用白话写诗的1916年算起。这样,它经常被视作“古诗”(新文化运动期间经常用另一多少带有贬抑意义的称呼,即“旧诗”)的对立面,似乎它的“新”主要即在于它和“古诗”的不同上。这便是一般的古/今,或新/旧问题。据说(一般今天提倡“国学”的人常用讥讽的语调谈及此),“新诗”之“新”得理直气壮,还因为它自觉顺应了世界大势,是从洋人那儿学来的。一般讨论新诗的人,以及新诗的作者,只要不是无知,无不(不得不)承认新诗之“新”的来由,确实受了外文诗的启发,像用白话写诗,像写起来分行,都无不学自西方。这便是一般所谓的中/西问题。在那种准备又一次堂而皇之、理直气壮地提倡“国粹”的人看来,“新诗”的这两个“新”,都相当可疑,并显得“可耻”,简直没有理由。好多准备清算或忽略民国文化的人,几乎都持这种立场。
出于对新诗与古诗明显的“差异”的强调和重视,我有意不将新诗视为一种与古诗相延续的新的汉语文体,而是把它视作一种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诞生的新文类(new genre)。当然,要说中国现代小说与戏剧(话剧)是一种新文类,而不是与中国古典小说和古典戏曲相延续的新文体,要更易被学界所认同。但是,恰恰是基于这一点,我把新诗视作一种新文类,并希望这有益于人们对新诗现代性的认识。这样,新诗的现代性问题,便也是一种新诞生的文类的现代性问题。
新诗在自己通向现代性的路上,上面提到的古/今,或新/旧问题,即是自新诗诞生以来就存在的“新旧诗之争”问题。而上面提到中/西问题,除了其他一些因素(像文学观念),主要的就是翻译问题。另外,新诗作为一种新的文类,其之所以能够成立,当然最主要的还在于它自身的形式,即用白话写的一种特定的语言现象。我从上面这三个问题中拈出了三个关键词,即声音(它是新诗形式和语言的代表)、翻译和新旧之争。在我看来,这是新诗现代性的三个方面,甚或是三个最主要的方面。它们是我设定的讨论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几个维度。首先,是中国新诗的形式问题。例如,新诗的格律化和自由诗问题,新诗的分行、押韵、节奏、格律、语调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放到新诗的“声音”这一问题中加以讨论。二是中国新诗的“翻译”问题。这要讨论的并不是字面上所理解的中国新诗被翻译成外文的问题,而恰恰相反,是外国诗的翻译在中国新诗中的作用和影响问题。第三,是新诗中的“新旧之争”问题,即新诗与旧诗之争的问题。这是自新诗诞生开始就存在的老问题。即使是在今天,还有人不无荒唐地认为这是没有解决的问题。因此,“声音”“翻译”和“新旧之争”是贯穿该书始终的三个关键词。
我在《声音、翻译和新旧之争——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之路》一书的第二至八章,以1915—1950年间有代表性的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梁宗岱和卞之琳等七位诗人、学者为个案,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新诗在其通往现代性之路上的两个重要问题,即新诗的“声音”与“翻译”。当然,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新旧之争”问题。我尤其注重从文体的层面(“声音”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一个概念),考察新诗通过“翻译”这一中介所受到的外来因素的影响;同时,我关注这种外来因素如何通过诗人的写作,或有意识的诗学被本土化,从而成为一种催生新诗的现代性,并导致其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甚或是不可或缺的因素。通过对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卞之琳等人的研究,不难发现,借助诗人本人的翻译这一中介,中国新诗作者立足于中国本土语境,使新诗有了自己不同于旧诗的新的形式,新的声音、语调和思维方式。
该书的第九、十两章,则讨论中国现代两位重要的诗歌理论家——叶公超和废名与“新旧之争”有关的新诗理论,一为格律诗的理论,一为非格律诗(即自由诗)的理论。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与“翻译”问题相关的中/西问题,必然会带来与中国传统的接受相关的新/旧问题,亦即一般的传统与现代的问题。显然,该书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当时的理论家立足于新诗的现实语境所能作出的最为精到的回答。
该书第十一章专门讨论一个跨越了两个世纪的重要诗人,即彭燕郊,着重对他后浪漫主义的写作风格,独特的抒情声音,以及散文诗写作所体现出的新诗现代性的一种可能作了探讨。
该书以众多不同的个案,从不同的角度,对新诗通向现代性道路的几个重要方面,即“声音”“翻译”和“新旧之争”三个问题作了探讨。由“翻译”问题入手,我重点考察了中国新诗作为一种新的文类的文体状况(“声音”),并延伸到了对中国现当代争论不休的“新旧之争”问题的探讨。在这当中,通过翻译外文诗及相关诗学的介绍和接受,西方诗学与中国古典诗学由不同的时空都汇聚到了中国现代文学这一现代的时间和空间上来了。这也正是新诗在其现代性之路上的现实处境。我相信:无论是西方诗学,还是中国古典诗学,要谈其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都只有放到中国现代文学这一现实场域中来才是合宜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到个人(诗人)在这当中的创造性作用。
二
对于西方诗学、中国古典诗学与中国现代诗学的关系,已有的研究和评论,向来多集中在它们平行的、单向度的一面,似乎两者是不相联属的两个部分。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卞之琳等诗人的外国诗翻译,以及翻译与他们本人的写作实践的关系的探讨表明:中国现代诗学对中国古典诗学的批判与接受,是在中国诗人接受了西方诗学影响的背景中进行的,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中国诗人接受的西方诗学及中国古典诗学影响,都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与场域中进行的,无论中西诗学,它们都是在这一现实的语境和场域中被重新阐释和“赋意”过了的。完全可以理解,在文化的接受和影响中,并不存在真的原封不动地被接受或影响了的东西。以之对新诗进行贬低或非议的人,首先是违反这一基本常识的。这当中便包括谴责新诗没有继承古诗的传统,新诗太受西方的影响,新诗是用中文写的外文诗,等等。
诗人冯至在1984年谈到新文学初期的继承与借鉴时说,关于“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开始一向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新文学继承和发展了中国进步文学的传统,另一种则认为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冯至说:“这两种看法各自有它的理由,但不能只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把两者结合起来,才符合实际。可是先后次序要明确一下,那就是先有了西方文学的影响,新文学才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而不是相反。”[1](P218)这种说法颇有意思。我想,这种判断不仅适用于“五四”初期的鲁迅、胡适、郭沫若,即使是对后来的作家来说,基本上也是适用的。以戴望舒、卞之琳和何其芳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何尝不是如此?冯至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其中的意义,在于打破了一般将对西方的借鉴与传统的继承互相对立起来的简单做法,并且强调,正是由于对西方文学的借鉴,才激发了对中国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这样的见解,大概也只有像冯至这样的诗人才能提得出来,并看得如此之深。冯至在这篇文章中谈到,“五四”初期的文学家,正是在读了西方18-19世纪著名的小说之后,回来再看《红楼梦》与《儒林外史》时,才逐渐认识到它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诗歌与戏剧身上。“过去被轻视或忽视的李煜、李清照等人的词,以及元代的戏曲和散曲都被提升到与《诗经》《楚辞》、唐诗同等的地位。那时,人们用西方文学这面镜子来照中国文学,便发现了许多被埋没、被轻视的精品。这些精品被发现,得到份所应得的评价,形成一个新的传统,这就改变了‘五四’以前中国文学史的陈腐面貌,有利于新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因为只有看到了本国文学里富有生命的优良传统,新文学才能有稳固的基础。”[1](P221)冯至的这段话说得朴实、精到而且深刻。它同样也可以适用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人的诗歌写作,以及理论家梁宗岱的理论建构情况,因为这些诗人和诗歌批评家们无不都是“用西方文学这面镜子来照中国文学”,才发现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另一面。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讲,这是一种使传统获得新的生命力的方式。这何尝不也适用于戴望舒、卞之琳等诗人的情形?也正是冯至,在1982年回顾戴望舒与卞之琳的诗歌创作经验时说:“戴望舒和卞之琳与前边提到的李金发完全不同,他们融合西方象征派诗人的诗的艺术和中国旧诗词的传统,写出来的诗既有民族的特点,也有个人风格,但字里行间常常显露出西方现代诗歌的精神。”[2]这确实是相当深入的评价。在我看来,这正好精到地评述了戴望舒和卞之琳新诗写作的艺术成就。
深受欧洲象征主义(特别是艾略特的诗学观念)影响的卞之琳,多次谈到他“戏剧化”的写诗技巧与中国传统“意境”论的关系。在他本人看来,象征主义与中国传统诗学似乎是可以正相符合的东西。他曾说他早年刚开始学习写诗时,“在学了一年法文以后,写诗兴趣实已转到结合中国传统诗的一个路数,正好借鉴以法国为主的象征派诗了”[3]。对此,他曾在1978年有较详细的总结:
我写白话新体诗,要说是“欧化”(其实新诗分行,就是从西方如所说的“拿来主义”),那么也未尝不“古化”。一则主要在外形上,影响容易看得出,一则完全在内涵上,影响不易着痕迹。一方面,文学具有民族风格才有世界意义。另一方面,欧洲中世纪以后的文学,已成世界的文学,现在这个“世界”当然也早已包括了中国。就我自己论,问题是看写诗能否“化古”、“化欧”。
在我自己的白话新诗体里所表现的想法和写法上,古今中外颇有不少相通的地方。
例如,我写抒情诗,像我国多数旧诗一样,着重“意境”,就常通过西方的“戏剧性处境”而作“戏剧性台词”。
又如,诗要精炼。我自己着重含蓄,写起诗来,就和西方有一路诗的注重暗示性,也自然容易合拍。
又如语言要丰富。我写新体诗,基本上用口语,但是我也常吸取文言词汇、文言句法(前期有一个阶段最多),解放后新时期也一度试引进个别方言,同时也常用大家也逐渐习惯了的欧化句法。
从消极方面讲,例如我在前期诗的一个阶段居然也出现过晚唐南宋诗词的末世之音,同时也有点近于西方“世纪末”诗歌的情调[4]。
在这里,卞之琳将“化古”与“化欧”视为能够同时在自己的诗歌写作中实现的目标,认为“古今中外颇有不少相通的地方”。对此,他列举出了四点:一是中国传统的“意境”与西方“戏剧性处境”的相通;二是中国诗的“含蓄”与西方注重“暗示性”一路诗的相通;三是文言词汇、文言句法与“欧化句法”的相通;四是晚唐、南宋诗词与西方“世纪末”诗歌情调的相通。囿于讲这番话的时代氛围,卞之琳将这种相通定位为“广义的现实主义和广义的浪漫主义”,其实,准确地说,这种相通点正是建立在现代主义的美学原则基础上的。也正是这种相通点,促进了卞之琳本人与戴望舒、何其芳等现代派诗人诗歌写作的成熟。
卞之琳在总结戴望舒的诗歌写作成就时,也曾经说:
与此相应(指上文提到的戴望舒“在思想上、艺术上三阶段的曲折演进”,引者按),戴望舒诗艺的发展也显出三个时期。这都有关他继承我国旧诗,特别是晚唐诗家及其直接后继人的艺术,借鉴西方诗,特别是法国象征派的现代后继人的艺术,而写他既有民族特点也有个人特色的白话新体诗。他对建立白话新体诗的贡献是不容低估的,也能用写在不同时期的具体诗篇的比较和对照来作出评价。
望舒最初写诗,多少可以说,是对徐志摩、闻一多等诗风的一种反响。他这种诗,倾向于把侧重西方诗风的吸取倒过来为侧重中国旧诗风的继承。这却并不是回到郭沫若以前的草创时代,那时候白话新诗体的倡导人还很难挣脱出文言旧诗词的老套。现在,在白话新体诗获得了一个巩固的立足点以后,它是无所顾虑的有意接通我国诗的长期传统,来利用年深月久、经过不断体裁变化而传下来的艺术遗产。接着就是望舒参与了成功的介绍法国象征派诗来补充英国浪漫派诗的介绍,作为中国人用现代白话写诗的一种有益的借鉴。在这个阶段,在法国诗人当中,魏尔伦似乎对望舒最具吸引力,因为这位外国人诗作的亲切和含蓄的特点,恰合中国旧诗词的主要传统[5]。
这段话若引用西方哲人的话讲,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同者唯同者知之”。就对中国现代新诗的总体贡献而言,戴望舒的成就,正在于卞之琳所谓的“既有民族特点又有个人特色的白话新体诗”。这种新体诗的现代性意义,恰恰在于它是对徐志摩、闻一多诗风的一种“反响”,是“把侧重西方诗风的吸取倒过来为侧重中国旧诗风的继承”。其实,这何尝不也是卞之琳本人的诗歌写作成就呢?
很有识见的批评家李健吾在评论到以戴望舒、卞之琳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当时的“前线诗人”时,曾经这样说:
他们属于传统,却又那样新奇,全然超出你平素的修养,……所以最初,胡适先生反对旧诗,苦于摆脱不开旧诗;现在,一群年轻诗人不反对旧诗,却轻轻松松甩掉旧诗[6]。
或许,我们可以说,戴望舒与卞之琳的新诗写作的功绩,正在于达到了传统与现代的某种平衡。在这里,旧诗的传统、西方的现代主义都融会贯通了。这正是新诗现代性的根本所在。
当然,无论中西传统,它们都是在中国被现代这一现实的语境和场域所“转化”过的。在新诗发展了九十年之后,在新世纪初,对于新诗传统的讨论,居然在一般公众中间助长和加强了这样一种疑问:新诗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尤其令人感到困惑的是,这样的疑问是由郑敏这样一位得到诗界认可的诗人提出来的。②郑敏教授似乎是以沉痛的心情,在历经半个世纪的新诗写作之后,宣称新诗的“破产”的。在一个新诗的局外人看来,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地说明新诗是一个应该否定的文类的呢?我不想在这儿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读者只要将郑敏的相关言论与上述冯至、卞之琳的言论加以比照,孰对孰错,孰轻孰重,就可自己作出判断。我这里还要特别指出一点,是郑敏没有把“传统”作为一个需要后来的人重新加以解释的东西加以理解,相反,她过分简单地把“传统”理解成了某种既成的、一成的不变的东西。她之赞美中国古诗有成就,有传统,以至通过庞德这些人对西方现代诗有影响,她之指责新诗没有成就,没有传统,一方面,当然在于她不能像王佐良那样看到穆旦写作的成就,也不能像叶公超、李健吾、废名那样看到新诗真正的成就;另一方面,即是上面说的她对“传统”太过本质主义的理解。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艾略特曾经说:“假若传统或传递的唯一形式只是跟随我们前一代人的步伐,盲目地或胆怯地遵循他们的成功诀窍,这样的‘传统’肯定是应该加以制止的。我们曾多次观察到涓涓细流消失在沙砾之中,而新颖总是胜过老调重弹。传统是一个有广阔意义的东西。传统并不能继承。假若你需要它,你必须通过艰苦劳动来获得它。”[7]或许,这样的“传统”观念,是郑敏所无法理解的。至少从她写的那些文章中,我是没有看出来。学者奚密通过自己对中国现代诗的研究,也曾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融合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是建构性的还是解构性的,传统在现代汉诗中的运用显示,传统不是一些僵化的实践和不变的成规的总合,而从来就是一个不断演化,不断成长的有机体,不断向个别作者的修正和新颖的诠释开放。”[8]确实,这样有关“新诗”与“传统”的结论,才是符合中国现代新诗发展实际的。
三
显然,《声音、翻译和新旧之争——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之路》一书竭力为新诗的成就和新诗的现代性“辩护”,尤其是为民国期间新诗的成就作某种“辩护”。这与自新诗诞生来就常见的对新诗的怀疑、否定,及近些年常见的质疑“五四”新文化,质疑民国文学和文化成就(更不用说新诗了)的做法不同。谈到对“五四”新文化的质疑时,孟泽曾经说:“对于‘五四’启蒙知识者的诘难,隐含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焦虑,然而,我们甚至不具备‘五四’时代启蒙知识者的心智、学识、勇气和肝胆,有的是相比‘五四’时代一点也没有淡化的功利主义,所谓诘难,因此常常显得轻薄。在总体上,我相信,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对于‘五四’启蒙精神的反正,而是如何使启蒙走向深入,作为所谓‘学术’,需要从‘是什么’的认知与判断,走向‘为什么’的洞察与澄清,并由此在古今中西之间,建构常识常情常理。”[9](P293)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在该书中所做的工作,主要即是努力要做新诗“是什么”的认知与判断,并试图解释新诗“为什么”是“新”的,即具有现代性的。
可以看出,我努力要“挖掘”新诗人的成就。譬如:一般评价不高的胡适的成就(主要通过废名的评论);徐志摩的写作中除了“抒情绪”(显然,这不是我所欣赏的)之外,还有“叙事实”的另一面;郭沫若除了“高音”的诗之外,还有真正体现其性情的“低音”的诗。当然,我真正赞赏的,是像戴望舒《雨巷》之后的写作,以及卞之琳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写作。此外,还包括该书没有专门讨论的艾青20世纪30年代后期与40年代初的写作,冯至《十四行集》中的部分诗作,穆旦20世纪40年代的写作。或许,这些都是我心目中民国年间新诗最好的一些诗人及其作品。可以看出,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不得不在自己的心中设置许多界线,最后,许多诗人的写作都不得不加上严格的时间界限。换言之,在我高度评价民国时期的新诗写作的时候,我其实不得不承认,我高度赞赏和期许的诗人有时太让人失望了:胡适就像别人评论的那样,没等到真正的收获,就走开了,不再写新诗;徐志摩在写作正要出现新的气象的时候,又罹难早逝;至于郭沫若,变得太快,最后就这样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人神共愤”的诗人,成了“文”“人”偏至的“典范”;戴望舒在其诗艺炉火纯青,可期待获得更高成就的时候,也不幸早亡(当然,他此时已经由香港回到北京,即使再活上几十年,按一般的惯例,我们也不应当对他有更大的期待);卞之琳,与另一个诗人冯至一样,很快地浪费了自己绝佳的诗歌写作才华,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再也一事无成(何其芳比他还要更早些)。孟泽曾将中国新诗中的这种现象称为普遍的“夭折”现象,他说:“几乎无法挽回的普遍的‘夭折’,以及因为政治纠结、社会动荡、文明交汇而更加醒目的‘人’‘文’偏至,直接决定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品质和状态。所谓的‘新诗’,在差不多一百年中,似乎没有达到它曾经期许的程度,或者说,没有达到旁观者以及后来者(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思)所希望的程度,‘看不到那希望形成的灿烂的事实’。”[9](P7)从这方面来说,如从“人”与“文”最高的期许来看,我们确实觉得上述这些诗人太让人失望,他们确实没有像有些外国作家(尤其是俄国作家)那样争气,将一切东西(历史、个人的命运)化成了最高的诗和文学。从这方面来说,我不得不承认孟泽下述这样的话的正确性:“吁求或诺言总是落空,苦难带来的不是开阔,而是狭窄,是限制,而不是解放,是简单的对立,而不是大度的宽容,是肤浅的应激表白,而不是深沉的含茹,是枯瘦,而不是丰腴。”[9](P7)我不得不承认,我上面讨论的全部诗人,都只具有将自己一生中的一些时间活成真正的“诗”的程度,而没有人将自己全部的一生都活成“诗”,真正配得上我们所谓的“文学”,即那个关于“人”和“文”最高的期许。
一般地,人们常将中国20世纪这些作家的艺术生命的“夭折”现象,归根于外在世界的动荡:军阀混战,政治腐败,外敌入侵,政治哄骗……简直有太多理由可为他们文学和艺术上的“夭折”和失败寻找借口。但若按文明史的一般惯例,我们还是可以对文学和艺术有额外的期许,正是在严酷的环境里,月桂树的叶子也曾一度返青、变绿。狄德罗这样的思想家可能会认为,黄金时代只可能产生一首三流的诗,唯有在苦难的浴血中方可能产生伟大的诗。诗人无法避免人类各种形式的“奥斯维辛”,今天也是如此,但诗人至少还可以有自己的思想和良知。诗人像在黑暗中摸索的盲人,但应该比一切自以为“眼明手快”的人都要有远见,因为他对人、对人性有自己的期许,因此才可以用自己的诗揭示这个世界中某些被遮蔽的东西。诗,永远无法在行动和实践的意义上承担什么“铁肩担道义”之类的东西,它哪怕要有承担,肯定也只是诗人理想中的女性贝特丽采柔弱的怀抱,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她只在你认为“无用”的地方思考、判断和发挥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诗人”的普遍“夭折”现象,在表面上体现为“文”的陷落,但究其实质,还是“人”的陷落,“人性”的陷落,“思想”的陷落。甚至可以讲,他们在短暂的“五四”启蒙后,并未真的建立起足够现代性的“文”和“人”的概念和思想。“文”的夭折更多的还是自己整个内心世界的夭折,自己整个思想的夭折。
或许这也是我高度评价彭燕郊的一个理由,他或许称得上是中国20世纪众多诗人中“例外”的“例外”。在这个意义上,他的高度就是新诗自诞生以来所达到的“高度”。这不仅仅是就作品来说,而是就新诗对“人”与“文”那最高的担当来说。或许,他真正地实现了废名“诗人之诗”的理想。说来或许很多人都不会相信,20世纪中国这么多诗人的“夭折”,其中很大的原因,即在于他们没有始终以“诗人”自命——他们太容易把自己想成或要成为别的身份,没有始终将书写“诗人之诗”作为自己终生的使命。他们太容易为“外物”移其志了,他们太不能坚持自己关于“文”和“人”的理想了。
孟泽在谈到新诗时,曾经这样说:“中国的现代转型,并不是局部的鼎革和简单的借鉴、嫁接、吸纳、替换,而是一种经典文明的整体解构与重构,一种新的创生,其中至关重要的核心就是‘人’‘文’的重新定义和安排。必须获得‘人’‘文’的新的诠释与定义,才可能建构新的审美主体性,建构新的美学章程。也就是说,必须有一种根本性的‘人’‘文’开辟,才可以指望拥有新的生命境界和审美境界。”[9](P5)这段话确实触及了民国以来中文写作中相当关键的问题。我们所期待于文学的,其实何尝不就是人的问题呢?只有在文学真正揭示了我们的存在境遇和生命境界的某种秘密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真正地谈论“文学”和“人性”,才可以说在“奥斯维辛”之中和“奥斯维辛”之后仍然还可以有诗。
[注释]
①本文为作者即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声音、翻译和新旧之争——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之路》中的最后一章,即第十二章的部分内容。
②可参看郑敏于21世纪初几年发表的相关文章,主要有:《关于汉语新诗与其诗学传统10问》(《山花》,2004年第1期),《中国新诗八十年反思》(《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关于诗歌传统》(《文艺争鸣》2004年第3期)等。
[1]冯至.新文学初期的继承与借鉴[A]//冯至.冯至全集(第八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2]冯至.中国新诗和外国的影响[A]//冯至.冯至全集(第五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180.
[3]卞之琳.赤子心与自我戏剧化:追念叶公超[A]//卞之琳.卞之琳文集(中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187.
[4]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A]// 卞之琳.卞之琳文集(中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459.
[5]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A]// 卞之琳.卞之琳文集(中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348—349.
[6]李健吾(刘西渭).《鱼目集》——卞之琳先生[A]//咀华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82.
[7][英]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A]// [英]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M].李赋宁,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2.
[8][美]奚密.现代汉诗——1917年以来的理论和实践[M].奚密,宋炳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199.
[9]孟泽.何所从来——早期新诗的自我诠释[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Tradition and the Modernity of the New Poetry
CHENTai-sheng
(CollegeofLiberalArts,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The voice, translation, and the old and the new, are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of the modernity of new poetry. With the help of the poet himself translation as an intermediary, based on the Chinese native context, the Chinese new poets have made their own new forms, new voices, intonations and ways of thinking different from the old poems. The criticism and acceptance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ics by Chinese modern poetics is carried out in the context of the acceptance of western poetics by Chinese poets. Many Chinese poets in the 20th century "collapsed", one of the reasons is that they do not always "poet" self-proclaimed, not regard writing "poet's poem" as his life mission.
new poetry; modernity; tradition; voice; translation
2016-11-30
陈太胜(1971-),男,浙江仙居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和现代诗学研究。
I207.25
A
1672-934X(2017)01-0063-07
10.16573/j.cnki.1672-934x.2017.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