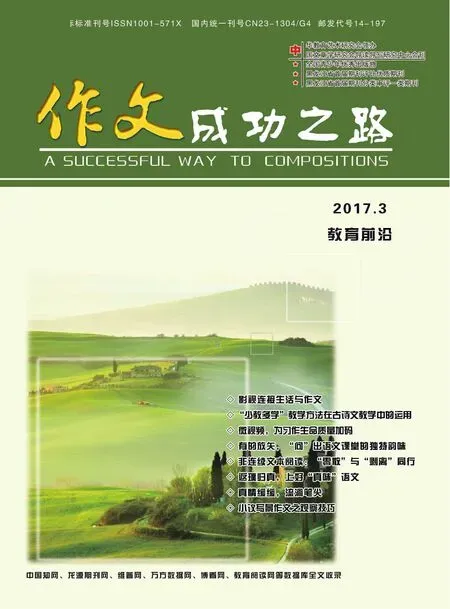庭院深深深几许
2017-03-23山东省邹平县第一中学高二34班李静怡
山东省邹平县第一中学高二34班 李静怡
庭院深深深几许
山东省邹平县第一中学高二34班 李静怡
雨,敲打着明净的窗,落在丛丛翠绿的凤尾竹间。窗前,只有外婆一个人踏着老旧的缝纫机,吱吱呀呀,一针一针走入女孩的梦。
红色的尘土,混在狂风暴雨中漫天卷来。金属剧烈碰击,车笛竭力嘶鸣,路上激荡着滚滚红水,世界,仿佛融在一片血雨之中。
女孩站污秽与混沌里,不知身处何处。那是什么?她远远地望见——一扇棕色的木门。蓝色的“星级文明户”门牌上,镶着十颗银光闪闪的星星。
是外婆家吗?女孩瞪大眼睛,伸手推门,血雨被阳光瞬间穿尽,只剩蓝汪汪的天空下,如水般温润的小院。
“汪汪!”是阿黄的声音! “汪汪!”
“阿黄你在哪儿?”女孩焦急地喊了起来。东屋,空无一人;西屋,堆满了破旧的家具;北屋,紧闭着门。
“阿黄,你在里面吗?”女孩用手使劲抠着门缝——门突然开了,一个湿漉漉的小家伙窜出来,扑到女孩身上。
“狗崽子!竟敢把澡盆踢翻了!”老头操着粗浑的嗓音,骂骂咧咧地趟过污水,满身泡沫。
“外公……”
“呦呵,宝贝疙瘩!”瘦老头丢下破盆,擦擦胡子上的白沫,双手在衣服上胡乱抹了抹,马上露出了笑容,“你外婆刚给你裁了一身衣裳,说啥,要带你去抓蚂蚱,晚上炸了吃……”外公一边捉阿黄一边对女孩说。
外婆的大绿花裙子,绣满了青蝴蝶。
“外婆,等等我!”不知何时,女孩跑到了田埂上,她扛起小网,裙子上的蝴蝶在风中若隐若现。
“乖乖,你在这儿等着。我进去,里面捉得多哩!”外婆将一大袋蝗虫交到女孩手里,一转身钻进过人的莪蒿丛,不见了踪影。
这里是外婆的绿豆地吗?女孩问。她使劲摇头,眼前一片绿意,只有远处一个小黑点不时冒出来,浮在碧波花海上,让女孩心安。
一只白蝶落在女孩的身上,腻歪地依偎着“青蝶”,宛若一枚玉璧。
她忽然记起外婆家的兔儿和猫儿们,那是外婆卖光全部绿豆换来讨她开心的。
“外公外公,兔儿们都去哪里了?”种满石榴与月季的小院里,女孩问。
“兔子?都养到汽站里去了!那地儿宽敞,就该野出个性子来!”外公豪爽地喝了一碗酒,不再理睬女孩,自顾唱起了年轻时的战歌,“爬上飞快的火车, 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天渐渐阴沉,月光里的歌声,转瞬间,被血雨打得粉碎……
一阵电话铃响起,她猛然从梦中惊醒,揉揉眼睛,窗外,泠泠冷雨,坠入鳞次栉比的高楼深处。
“三百块?太少了!北屋不租的,东屋租给他吧……”外婆挂了电话,停下缝纫机上的半根金线,走进屋来,“有人要租咱们老家的屋子,他嫌条件太差,钱不多,我叫你妈帮着看看。”
“厂子里的工人,大老远过来,工资不高,再说,你也知道那是什么地儿。”长大了的女孩,话语间透出成熟的气息。
雨还在下,楼角的凤尾竹簌簌地滴着水珠,洒在洁白的大理石甬道上,沐浴在雨中的欧式小路灯晕染出柔和的光,映着泉眼里,格格不入的老旧缝纫机的影子,悠悠地转动。
离开了老家的外婆,来到城市,灯红酒绿,繁弦急管,就这么穿梭着。
清晨,去公园和戏友们唱吕剧,学胡琴;傍晚,在会所里跳舞,下围棋;偶尔,外婆会独自踩动当年唯一陪嫁的缝纫机,在教堂悠远的钟声里,望向窗外——
灰蓝的天空下,黑色的十字架,孤零零地立在城市中央。
“宝贝,明天是你外公的祭日。”外婆的声音从从哒哒的针线声中传来。
女孩怔了,她回过头,看着针脚下织出密密的花纹,开始细细数落日子。
“汪……”阿黄悲痛的呻吟声揪着小女孩的心,在生命的尽头,女孩竟不敢看它,只听着身后,苍老的声音渐渐消失;
兔儿,卖掉了;
小花咪,误食毒鼠药,死了;
青蝴蝶,不知飞去了何处;
大雨冲刷出一片高大的工厂,红尘埋葬了美丽的小院,外公得了癌症,去世了。
……
外婆的裙子已缝了大半,女孩望着窗外一线蓝天,不敢想象红土覆盖的乡下。
时过境迁,城市的步伐带走了一切。莪蒿葱葱,夏虫嘶鸣,以乡村污染为代价的城市繁华,何日能结束?外婆的绿豆糕,成了节日里永远的摆设;飘逸的花裙子,压在衣柜的最底层,可外婆依然坚持做着,在每个日落时分,幻想外孙女玩累了回来,抓起桌上的糕点,狼吞虎咽——“乖乖,又把花裙子弄脏了!”一切,在越来越暗淡的星光背后,渐渐消失。
“吱——”老缝纫机停止了转动,外婆的裙子上,绣满了青蝴蝶,一如当年田埂上那般纯粹质朴,在清风抚摸下,宛若一枚玉璧。
血雨过后,十颗星星已生锈脱落,女孩缓缓地推开木门,寂静的小院里,空无一人,阿黄昔日的小窝,浸泡在水中,没有了蝴蝶,枯死的银杏,披满红尘。走过栅栏,穿过铁网,女孩细细摸索着记忆里的尘埃。
夜,黑了,没有月光。破旧的屋檐下,女孩独自倚在窗前,沉沉睡去,满天的红尘还在飞扬,像洁白的雪花,落在女孩细细的发丝上,迷离了夜与黎明,缝纫机吱吱呀呀的转着,外公的歌声再次唱了起来: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