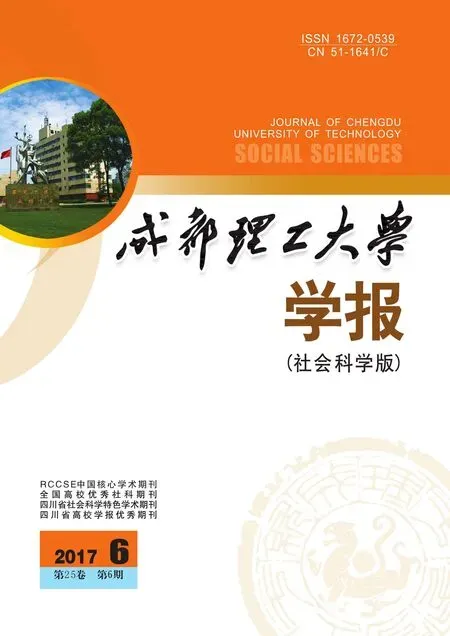叙事预示与读者期待
——对贾平凹《白夜》中神秘语言的探讨
2017-03-23张冬梅刘永志
张冬梅, 刘永志
(成都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成都 610059)
叙事预示与读者期待
——对贾平凹《白夜》中神秘语言的探讨
张冬梅, 刘永志
(成都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成都 610059)
贾平凹长篇小说《白夜》中对目连戏的渲染和对测字算命的细节描写形成了文本的神秘性。作者在小说语言上的神秘性民俗化,以及对文本超验现实人物情节上的安排和结构上跨越时间的模糊性处理,有体现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叙事预示。但是读者在阅读体验中因缺乏对相关神秘戏曲的语境知识而无法形成有效的图式联想和参照,从而造成文学美学赏析上的阅读障碍。
《白夜》;贾平凹;神秘性;叙事预示;读者期待
《白夜》是陕西作家贾平凹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创作的商州乡土文化系列中的一部长篇小说。不同于《商州》《高老庄》的农村视角,《白夜》叙述的是西京城中一群普通人的平常生活。主人公夜郎因进地方戏班打杂而结识了城中的各色上下人物,他和这些普通人经历了种种爱与恨、行善与被骗、希望与幻灭、愁闷与荒诞的故事。
理解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离不开对文本、作者和读者三方面的探讨。瑞恰兹在《意义的意义》一书中把意义概括为三个方面:文意、意旨和评估[1]。通过读者的阅读行为,文本意义才能具体化、现实化,但是读者的理解是否就是作者赋予文本的真实意义,这和读者的自身阅读语境有关,也和文本的语言制约有关。对《白夜》一个强烈的阅读体验是书中人鬼不分、阴阳交错、故事语境神神叨叨。那么,自然地,读者会疑惑其文本的神秘性是否是作者有意为之的文学实验?其文本语言符号的背后所指是否能顺畅地从作者流向读者?通过对文本的特点、作者的叙事预示以及读者阅读期待的分析,我们要进一步认识贾平凹的创作理念,以及影响创作意义和读者体验意义之间通道的障碍。
一、文本的神秘性
语言刻画意象,而意象隐喻主题。对《白夜》文学主题的阐释离不开对再生人和鬼戏这两个语言意象符号的探讨。故事中反复穿插再生人的故事情节,再生人死而复生却又伤心再亡,再亡自焚后留下一把钥匙,这把鬼钥匙居然被活人拾得作为稀罕物珍藏于身,这种夸张的文学想象远远超出了读者的自然期待!还有那目连戏,也是鬼戏,戏中唱本人神不分、人鬼合一,但目连戏却是至今还在真实上演的一种民间地方戏曲。通过这些意象符号的渲染,《白夜》将现实与虚构、真实与魔幻、心性与兽性表现得生动有形,神秘性与现实性和民俗性结合得自然圆融。
再生人的故事不仅在结构上首尾呼应,同时,鬼钥匙开启小说主要人物的一一登场。小说以“宽哥认识夜郎的那一个秋天,再生人来到了西京”[2]1开篇介绍人物出场,结尾是夜郎上台扮演目连戏中的鸟鬼,化身精卫,拨动古琴,鸣叫着:“如果它不溺死我的女儿身,我是以人的形象享受人的欢悦与烦恼,可它却把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非人非鸟!”[2]307精卫填海,如同愚公移山,传统文化不看重机械劳动的费力无功,而赞扬的是持之以恒的精神价值。此时,“宽哥惊异的是那形象多像自己看到的再生人自焚的情景”,只是再生人是坐在火里,鸟鬼是站于海里,而虞白站在台下,泪流满面,“随着肩臂的抽搐”,“项链上吊着的是那枚钥匙——再生人的钥匙”[2]307。这里,那隐含阴阳两界的鬼钥匙、生死轮回、凤凰涅槃,一连串的语言密码,暗示着都市社会中市井人物在现世中解决不了的矛盾、挣扎、躁动和无奈,似乎只能寄托在浴火重生的来世隐喻里。
目连戏是夜郎在鬼戏班吹埙时舞台上演出的《目连救母》的戏文。小说中说“那是集阴间和阳间、现实和历史、演员和观众、台上和台下混合一体的演出”[2]5,事实上也是如此。在白夜的后记里,贾平凹对目连戏有类似的介绍,“它是中国戏剧的活的化石”,“为人民群众节日庆典、祭神求雨、驱魔消灾、婚丧嫁娶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3]309。一部鬼戏,就如同走进丰都鬼城,让观众读者看到的是地狱鬼,威慑的却是现世人。
小说里假借托梦释梦来映衬现实不足为奇,《白夜》里不止梦境,测字算命也信手拈来。当虞白听到一个“滑”字就惊悚联想到“出什么人命了”,这样的细节安排让读者在半信半疑中体验到玄妙奇异。虞白解释,“字中有骨,见了骨不是伤就是亡”[2]276,说得好像有几分道理。更玄的是,吴清朴顺眼看到门上的铆钉,就想写个“铆”字,刚写到一半,笔却没水了,于是先生测字算命,什么“字里有金旁最好,这生意是能发了财的”,“墨断有田土散之象”,“铆字一半为柳,柳又不全,柳不全者为败柳,残花败柳为妓,莫有钱栽在妓女身上”[2]30-31,巧舌如簧,真真假假。此后吴清朴的命运走势也有相似之处,似是而非,不由人不信,但又不能全信。动荡变化社会中的肉眼凡胎往往哀叹人生的虚无渺小、命运的不确定难预料,他们求助于卜卦算命,虚构与现实交织错接,紧张的心理难得地在外力关照下能归置放松片刻。
二、作者的叙事预示
《白夜》写作于1995年,在随后1998年完成的小说《高老庄》里,贾平凹在其后记里谈到对于小说的思考,认为,“我的小说越来越无法用几句话回答到底写的什么”,“这样的作品是很容易让人误读的”,“这缘于我对小说的观念改变”[3]280。从写作时间的衔接上以及故事人物和结构安排上分析,《白夜》应该属于这类创作。具体来说,作者创作观念的实验和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要素有吻合的地方。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工业电器和电子产品更新换代的时间跨度越来越短,技术上的不连续、不稳定、不确定,断裂无序甚至突变,让现代生活充满了压力和危机。人类精神上的绝望也体现在对文学表达形式的摸索上。以前,19世纪中后期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其创作的目的是要宣示某种价值观,通过故事叙述上的线性发展、情节表达上的因果逻辑推理,在常规的时空环境中,塑造具体典型的人物,进行道德教化。但随后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小说强调人的内心活动,深入人的潜意识,打破时空局限,弱化人物形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则彻底多元化,患“精神分裂症要求回归到原始流时代的理想”[4],“所谓的意义只产生于人造的语言符号的差别”,“是读者的解读使这种符号组合获得了某种意义。”[5]
(一)超验的现实
“《高老庄》里依旧是一群社会最基层的卑微的人,依旧是蝇营狗苟的琐碎小事”[3]280,《白夜》也是如此。像长牛皮癣的基层民警宽哥、秦腔丑角南丁山、宾馆发廊女颜铭、改行卖饺子的考古所研究员吴清朴,甚至有些权贵,但也不过是在官场派系斗争下被无辜牵连而后回归教职却为争个教授职称而脑出血瘫痪了的前市府秘书长祝一鹤,等等。在浮躁的社会欲望中,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这些边缘人在理性中挣扎,在贪欲中迷惘,逐渐被城市病所同化吞噬。
考古员吴清朴因为爱情而停薪留职,下海帮助陷于家庭兄嫂夺利的女朋友经营家庭饺子馆,却又因为女朋友傍了大款而重回考古队,最后却在山上拍摄古殿建筑时被山蜂蜇死;一向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民警宽哥又一次学习雷锋想帮助乞讨的孤寡母子能搭个免费班车回老家,义务做了个证明,却不想那女人是个逃跑的人贩子,宽哥被革职除名,只能做个汽车配件经销部的推销员,但又不会请客送礼、胡说冒撂、开假发票送回扣而完不成销售任务,连基本工资都要倒扣,家里三天两头吵架;宾馆发廊女颜铭有长相有身材也有追求,她在学习时装模特表演,夜郎以为从此他就有了爱情和美好,不想在二人第一次恩爱后却发现了残留有红颜料水的鱼尿泡,及至孩子生下来后不像爹不像妈,奇丑无比,二人闹离婚时才知颜铭生来丑陋,为了改变命运的不公而去做过整容……“之所以种种离奇的事件发生,……那都是大自然的力的影响”,“我中年阶段的世界观就逐渐变化”[3]278。“大自然的力”是什么?就如活活的虫子突然被人无意踏死,山崩海啸、瘟疫饥荒,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大自然的力量逼显人类的渺小无助,现实生活中充满了太多不确定的因素,一股轻风般的变化就能让贱如草芥的普通人家的正常和规范来个翻天覆地。《白夜》中市井人生的压抑和沉闷不由得让人心酸惆怅。
(二)混沌的整体
中年后的贾平凹“开始相信了命运”[3]277,经历了人生的种种事变,焦躁着整个人类的恶性事故和重重危机,他读《山海经》《易经》,开窍于混沌。《山海经》上讲的混沌,是个生命,原本没七窍,有了七窍后混沌却死了。“作品要写得混沌,不是文字的混沌,是含义的混沌。越是平白如话的文字而能表现混沌的意象,作品反倒维度更大。”[6]具体来说,“我尽量原生态地写出生活的流动,行文越实越好,但整体上却极力去张扬我的意象。”[3]280
《白夜》的说话,就如给家人和亲朋好友说话,说的是平平常常的生活事。主人公夜郎,和贩豆芽菜的、卖病死烧鸡的、偷下水道井盖的这些市井闲杂粗人租住在一个大杂院。祝一鹤曾介绍夜郎到市图书馆做过临时招聘人员,夜郎知恩图报,一直出人出钱照应年过半百孤身一人随后又“失聪亡音”瘫痪在床的祝一鹤。虞白上辈人家道中落却躲过了政治运动,夜郎爱慕虞白弹琴焚香,诗画人生,爱情高尚美好得让夜郎自惭形秽。发廊女颜铭倾心于他,但夜郎却有意无意地一而再地纠结于颜铭的贞洁,固执地把自以为是的骄傲抬在头顶放不下来……这些个故事,就像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一样,摆个“龙门阵”,嚼个左邻右舍的舌头,鸡毛蒜皮样的家长里短。夜郎在戏班吹埙,戏曲舞台上下进出,生活和演戏自由转换。人生如戏,生活和舞台,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戏班是个鬼戏班,台上台下人鬼不分,阴阳穿梭。人生善恶,谁能分清好坏曲直?
后现代主义小说用非线性叙事解构并重建小说世界,时间跨越过去、现在和未来,现实与幻想、历时和共时在事件的碎片化讲述中建立实现。元小说甚至“一边叙述故事,一边告诉读者这篇故事是如何虚构的”[5]。尽管贾平凹不屑于“那些企图要视角转移呀,隔离呀,甚至直接将自己参入行、文等等的做法”[2]309,但我们看到《白夜》的结构上有类似于后现代主义小说中打破时空限制的尝试。
(三)语言民俗化神秘化
后现代主义小说超越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限,把文学变成了读者大众的文学,表现出一种通俗化倾向[5]。基于作者对文学语言“平白如话”,“说平平常常的生活事”的尝试,《白夜》中的人物出身市井,行文说书中流动的地域特色、风土人情具体独特的民俗性,同时也拉近了与普通读者的文学距离。
《白夜》发生在西京。尽管“西京”不可能是行政管理意义上的商州或西安,毕竟小说是虚拟的艺术,但文本中字里行间自然流露出的地域性是作家与故土之间割离不断的血与肉或故土和家根。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文化、特定的地域增加了文本的阅读体验。看到鬼戏班班主南丁山的师父丑老脚临终冲喜时师弟孝敬的羊肉泡馍,灵堂里亡者家属做的羊腥汤面片,这个西京还能是哪儿呢?再生人还魂返家时,戚老太太留吃饭,“那一顿饭是新上市的槐花拌了面粉做就的焖饭”,“槐花是蜂吃的东西,拌了面蒸出来如银团玉块,这样的饭菜以前西京城里人家常吃,而今已属罕物”[2]3。“笑问客从何处来,牧童遥指杏花村”,乡愁留在了舌尖的记忆里。
乡愁故土还留在方言土语的记忆里。“你还弹嫌颜铭呀?!”[2]30,知道“弹嫌”是什么意思吗?在上下文里,夜郎不接话,因为他也是听到老头丧妻后有钱又娶了个年轻的随口一说“只剩下我这没钱的,甲男配丁女”,原来“弹嫌”就是看不上、嫌弃。“夜郎啬皮,虞白却是大方的”[2]215,猜想原文的对立语境即可知“啬皮”就是“大方”的反义。贾平凹是陕西商州人。商州,地处陕西省东南部的秦岭南坡,西邻西安,东通鄂豫。“商州现属西北地,历史上却归之于楚界”[3]278。战国七雄最终被地处西北的秦国一统中原,又历经两千年的朝代更迭,明清时的“湖广填四川”,笔者作为四川人,长期在外求学工作,当普通话已成为工作生活的常规语言后,看到这样的乡音,猛然想起妈妈的话,忘却的记忆瞬间又复活了。
后现代主义小说在语言表现形式上具有通俗化倾向,有时还用语言游戏、神话隐喻、哲学戏仿、黑色幽默等情节结构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读者转换成作者,阅读活动转换成作者的创作,阅读是对“原作的变更”,对“创作的延续”[5]。《白夜》里有很多这样的尝试。文中不乏传统神话形象的喻世隐喻、梦境的解构、测字算命、还有虞白借打笑夜郎的迷糊引申出对卡夫卡以及批评家自以为是的嘲笑,以及鬼戏班师父丑老脚气死于抗美援朝战俘营里的告密者,竟然几十年后成了台商并回大陆投资坐上了市政府的宴席这样的荒诞幽默。
三、读者阅读期待
小说文本一旦离开了作者的创作进入读者的阅读过程,读者的阅读期待是否就是作者的叙事预示呢。认知语言学通过对原型、隐喻等模式的研究试图揭开语言表达和意义理解之间的关系,其中,图式理论被广泛地用来解释阅读听力理解过程。图式理论认为,理解过程不仅是对作品文字逐一被动的理解,更多的是作品文字激发了读者对储存在自己大脑中的原有知识的再认知。图式就是这些先前知识分门别类的认知框架,它给读者提供一种认知理解的参考体系,是对新信息的输入进行类比、预测、推理和评判的标准。理解过程是一种主动的“猜测—证实”的过程[7],这一过程涉及关联和预设。
对文学作品评判的标准具有强烈的个人特征和时间地点差异。一般说来,文学批评应以文学经典为参照系,主要考察两项指标,一是作品的精神内涵,二是其审美形式[8]。图式理论借助对文学经典的参照,有助于我们对具体的文学作品进行客观的评判。意象图式来自人们的体验经验,人们通过意象图式转化和映射进行预测和推理。意象图式为隐喻映射提供了理论基础,映射的结果就是人们可以凭借具体的物体来推理抽象的概念[9]。
对于《白夜》里的目连戏,贾平凹在其后记中坦承“目连戏对于许多读者可能是陌生的”[2]。笔者不知道目连戏,通过查询百度百科[10],才知道为什么该戏的名字是“目连”:目连是佛经里的一个僧人。目连僧是佛教始祖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是个孝子,曾历尽艰辛到地狱解救母亲。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再结合儒家道家思想宣扬孝道,目连故事以戏曲形式在中国民俗化,戏中的风土习俗都是当地的人情讲究。目连戏作为祀神戏,常在打醮祛灵、酬神还愿等场合演出,从太阳落山开始演,一直演到第二天的日出,甚至可以连续演出七天七夜,演出气氛庄严乃至阴森恐怖。目连戏的最早文字记录始于南宋,被誉为中国戏曲的“戏祖”。现在,目连戏在安徽徽州、湖南辰河、河南南乐等地方还有较大影响,是国务院2006年批准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综合百度介绍的以上这些知识,现代城市读者在小说阅读过程中恐怕很难有即时的语境同化。由于缺乏相关的知识积累和生活铺垫,读者对于小说中目连戏的相关阅读容易忽略跳过,甚至在繁复的剧情文字描述中产生反感,更谈不上文学意象映射的隐喻理解和对其审美形式的欣赏。
贾平凹没有明确点出小说中“穿插目连戏的意旨如何”[2]309。与贾平凹一样擅长乡土文学描写的莫言对此有相同的尝试。莫言在《檀香刑》中移植茂腔的戏曲语言[11],因为他认同汪曾祺的观点:挽救衰退的文学形式“只有两样东西:一是民间的东西,一是外来的东西”[12]。尽管莫言和贾平凹都在民间戏曲以及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对接中寻宝,但是莫言自己也难断定这样的实验是否成功[11]。
批评的有效性在于“把作家文本纳入一种预设范畴并生产出新的文学常识”[13],阅读体验借助于读者对经典的参照和对文学语境的认同,文学的情结始终在现当代,魔幻是服务于现实生活的,贾平凹也承认于此:“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3]279。妖魔鬼怪、民俗传说等奇闻异事不全是体现作家个人的语言风格或独特的审美情趣,也不全是让读者体验猎奇冲击。读者对离奇夸张的情节、神秘大胆的语言的阅读期待是参照自身经验来进行预测、类比、推理和评判的主动学习过程,文学设计最终离不开映射现实本身的文学根本。
毫无疑问,贾平凹思想丰富,著作等身,在影视作品霸占观众时间和灵魂的当下,坚持纯文学创作更是难能可贵。时隔二十年后,翻看这本当时没有《废都》般轰动的都市小说,认为文本中的农村鬼戏唱本因文学爱好者缺乏相关的生活基础而阻碍了对小说的深层次理解;而对文本中另外像测字算命、方言土语、民俗餐食这些陌生的材料,读者却可以通过借鉴生活中的类比来展开联想和比较,进一步激发其主动探险的阅读体验;贾平凹随后也再次转向乡村题材的创作。诚然,语言的陌生化是吸引读者关注的有效手段,但是,读者的阅读认知离不开自身前期所积累的特定的时空关系中百科知识的参照和映射。
[1]童庆炳. 文学理论要略[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244-245.
[2]贾平凹.白夜[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
[3]贾平凹.高老庄[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
[4]杨仁敬.序言[M]//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详解.中文版.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2.
[5]陈世丹.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详解[M].中文版.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5.
[6]贾平凹.说舍得:中国人的文化与生活[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47.
[7]张维友.图式知识与阅读理解[J].外语届,1995(2):5-8.
[8]刘再复. 文学的初衷与功能——“文学常识二十二讲之三”[J].东吴学术,2015,(1):77-86.
[9]刘丽华,李明君. 意象图式理论研究的进展与前沿[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7):110-117.
[10]百度百科.目连戏[EB/OL].(2016-05-15)[2016-01-19].http://baike.baidu.com/link?url=s4Nwzl--25Fluzo90m5QDZB4vSfBdKfyI_8zyNtzrkTg-jTSgeyAlmxwBlH29XOe_5lmEoog4isQUJjd0stfZ_.
[11]莫言.我的文学经验:历史与语言[M]//陈晓明.莫言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194-205.
[12]莫言.影响的焦虑[M]//陈晓明.莫言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189-193.
[13]程光炜.魔幻化、本土化与民间资源——莫言与文学批评[M]//陈晓明.莫言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151-167.
编辑:邹蕊
NarrativeExpectationandReaders’Expectations:AStudyoftheMysteriousLanguagesinBaiYebyJiaPing-wa
ZHANG Dongmei, LIU Yongzh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Sichuan 610059, China)
BaiYe, a novel written by Jia Ping-wa,is typical of mystery with a variety of such narrations as Mulian Drama and fortune telling by splitting Chinese characters. The narrative expectation of the writer is a bit experimenting of postmodernism literature with some similar literary skills like mysterious languages,dialects,plots beyond the reality,vagueness in time structure,however, readers,unfortunately, do not have the same expectations due to the lack of schema reflection or reference from relative contexts,thus leading to some obstacles in aesthetic appreciation.
BaiYe, Jia Ping-wa, mystery, narrative expectation, readers’ expectations
I207.67
A
1672-0539(2017)06-0081-05
10.3969/j.issn.1672-0539.2017.06.016
2016-11-30
四川省教育厅2014年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价值多元化背景下对语言危机的社会语用实证研究”(14SA0033)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成都理工大学校级科研创新团队基金的支持
张冬梅(1972-),女,四川德阳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刘永志(1968-),男,四川苍溪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