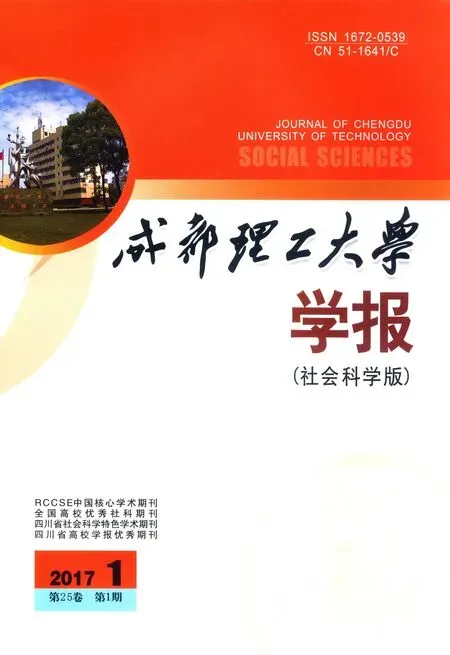理解今日城市:当下小说创作中的城市书写热点分析
2017-03-22范晓东
范晓东
(西南民族大学 文新学院,成都 610041)
理解今日城市:当下小说创作中的城市书写热点分析
范晓东
(西南民族大学 文新学院,成都 610041)
城市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小说中关于城市的书写是城市文化变迁的重要记录形式。新世纪以来新创作的小说中,关于城市文化的建构,包括有建构于消费文化之上的城市物质奇观、现代思维与传统伦理的颉颃、城市灰色空间中的底层叙事、社会变革中的官场生态与环保书写等多个维度。在文学研究中,对城市书写的观照与研究应是进一步予以努力的方向。
新世纪小说;城市书写;城市文化
20世纪以来,城市化与全球化成为不可逆的发展趋势,在城市化结出硕果的同时,文化与社会的巨大变迁也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社会层级分化,弱势群体生存状况愈发糟糕;自然资源遭到破坏,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现代化进程中人性异化问题更为突出。中国的城市化在20世纪90年代开启了加速行进的节奏,北上广等大城市向特大城市或“全球城市”迈进,中小城市也在快速发展。种种巨变裹挟着乡土中国向现代城市转变,社会转型造成了文化上的巨大变迁,进而重塑了当代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生活状态。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方式,文学在记录社会、历史变迁方面,有它独特的地方。本文拟从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中的城市书写切入,希望通过文本分析,对中国当代城市有一个印象式的把握。将分析文本限定为新世纪小说,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量:一方面,当代中国于新世纪初期以明确的身份正式加入全球化浪潮,城市化带来的变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深入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种外来文化思潮和本土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促使当代作家从全新角度去思考今日变局和随之而来的问题。另一方面,小说是新世纪文学中最为关注城市的文学样式。纵观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从消费主义风行到底层叙事崛起,再到现实主义的回归,这条线索与城市化引起社会巨大变革的发展轨迹暗暗相合。新世纪小说创作中的城市书写反映了城市文化变迁,也呈现出全球化与本土化、现代与传统对当代文学的深刻影响[1]3。下文将从消费主义、传统伦理和现代思维的颉颃、底层叙事与变革期的社会问题这四个当代城市文化热点出发,分析当下小说中的城市书写。
一、建构于消费文化之上的城市物质奇观
古汉语中的“城市”由“城”与“市”组成,如果说“城”可以理解为城墙或者要塞,那么“市”就是集市了,是交换剩余产品的地方。在中国,“市”所包蕴的商业功能,长期以来被政治功能与文化功能压抑,但它的生命力异常顽强,并未消失。城市化以来,中国各类城市一致向商业化进发,物质得到极大丰富,也促成了人们思维现代化的转变。在此背景下,消费主义渐而走到城市舞台中心,成为突出的城市文化热点,它不仅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还导致了文学叙事内容与形式的变化。对城市是消费社会和享乐空间这一观念的认可,应是作家使用消费主义话语描写城市的重要原因。浓厚的消费主义文化表达兴趣,促使作家用小说为读者呈现出一个沉湎于物质消费的幻城奇观。
在部分书写城市的小说中,大手笔的物质消费和无节制的欲望经常出现,这种叙事与炫耀和夸大城市生活的表达并无二致[2]。此类叙事最先在20世纪90年代的卫慧、朱文等人的作品中出现,他们捕捉到了时代变化的讯息,精心描绘商业化社会的物质盛宴,这些表达触及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与这种生活方式背后的时代,表现了对城市生活和消费文化的探索热情,这一点应予以充分肯定。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小说呈现的对商品消费恋物癖式的膜拜把城市生活塑造成了一个消费主义神话。对此,张柠教授用不无幽默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还没有哪一个商品博览会可以和卫慧的‘博览会’相比”[3]。新世纪之后,郭敬明接过了卫慧等人的写作主题,营造了上海这个耀眼的消费幻城。通过商业运作模式,郭敬明用小说这一形式记录了消费主义时代的生活景观。小时代系列中,他对商品消费的书写热情不亚于卫慧,《小时代2.0虚铜时代》罗列了一众上流社会的消费品和生活空间,对物质和消费进行大肆铺陈,以此搭建了一个奇观展览与欲望展演的舞台,这座脱离现实的消费主义至上的幻城,强烈刺激感官,以饮鸩止渴的方式抚慰着现代人在急速、陌生、碎片化的生活里麻木、无奈的心理状态。
郭敬明之外,张欣笔下的物质“展览会”也值得一提。与卫慧、郭敬明等人不同,她剔除了无节制的欲望表达,在下层女性与上流社会男性的恋爱故事中加入了男权批判观念,如《浮华背后》、《夜凉如水》等小说,讲述了下层女性进入上流社会的复杂经历。然而,小说对上层社会奇观式生活场景的过度呈现,客观上让小说很难达到先前设定的批判意图,反而给处于社会低阶层的人群以震惊式的眩晕与诱惑,引发对于功名利禄的新一轮追逐。
从20世纪90年代的卫慧到新世纪的郭敬明,再到“亦雅亦俗”的张欣,这类城市书写的一般逻辑是将具有震惊美学效果的城市物质与奇观在小说中进行罗列,由此小说会具有强烈的现代城市意味。但是,对物质主义毫无批判的拥抱与似是而非的批判力度,也使作品脱离了思想内涵与审美精神这些文学的应有之义。缺少了思想深度的消费主义叙事,外表炫目,内在却空洞无物。
二、现代思维与传统伦理的颉颃
城市化背景下的当代生活自有一套与传统伦理观念悬殊的价值体系。城市化包蕴的市场化特征将工具理性思维、货币哲学与实用态度等现代性观念浸润于城市人的思维、生活和行为之中,人们的生存形态也必然发生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而当代中国的城市化与现代化混杂了多种文化,在文化杂糅的情况下,思维转变不再是简单、直接的方式,而呈现出对抗、融合的纠结状态。一方面是传统伦理的逐步退守,另一方面是传统思维与现代观念相妥协,形成新型伦理关系。
(一)“致无尽联系”:传统伦理濒于解体
对于拥有五千年农耕文明的中华民族来说,传统伦理建立在血缘的基础上,维系人们日常交往的是血缘与人情;现代理性交往方式则以职业为主,人际圈以此为圆心向外扩散[4]。处在文化杂糅环境中的中国当代城市,各种文化观念来袭,传统伦理中牢不可破的血缘纽带受到严重冲击,浓厚的人情已经稀薄、疏离。孙惠芬的《致无尽联系》通过主人公回老家过年这一典型事件表现了传统伦理和现代观念的冲突与交锋:深植进骨髓的传统观念让主人公必须花费精力去维系以血缘为主的文化命脉;而生活在现代城市这一客观现实又决定了他也必须维系个人在充满竞争的社会中发展所依凭的人脉资源。疲于应对的“无尽联系”,彰显出两种文化的对抗与传统伦理的逐步退守。
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则展现了传统伦理的分崩离析:原本坚固的父子关系在技术理性控制下的现代人的思维方式里不堪一击。父亲李四将亲情看得非常之重,而生活在城市里的李四子女早已接受现代观念,他们依照现代城市文化逻辑,认定李四是不怀好意的骗子。父子之间的交往达到如此困难的地步,天然的亲情在现代思维面前不堪一击,固执地与子女所代表的现代理性思维对抗的个体李四,他的悲剧是注定的。拒绝现代思维的李四在子女眼中是那么可笑和神经过敏。
(二)“相爱的日子”:临时契约的新型伦理关系
中国城市化的复杂性使城市人的日常生活不仅受到以血缘为主的传统伦理关系的制约,还受到以工具理性为重要特征的现代思维的挤兑。在这双重甚至多重文化规则制约下,城市人的生存境况极其复杂,这种复杂有多种形态,如前论述的消费主义至上对城市人生活观念的影响、传统价值观的崩毁,此外,城市繁复、平庸和碎片化的生活无形中对理想与崇高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解构和颠覆。在变动不居的城市生活里,没有什么是具有永恒价值的,“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5]。马克思的这句论断放在眼下或许过于悲观,但理想和崇高在今日城市成为需要被隐藏的字眼却是不争的事实。工具理性和货币哲学对传统日常生活形成解构,临时契约关系出现,削弱了固定、永久的人际联系。当下小说中出现了大量临时性、功利性的新伦理,它剥除了责任、使命等宏大的部分,情感、欲望与婚姻被完美分离了[1]88。毕飞宇《相爱的日子》中的两位被甩到城市边缘的年轻人无可奈何地在没有资本拥有婚姻的情况下维持着规律的性爱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感受到了额外的情感需求,却心照不宣地保持沉默,直至这段关系在女孩遇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后黯然结束。两位年轻的都市男女在传统价值观和功利理性之间徘徊,在严酷现实面前小心翼翼地不让情感介入,这种工于计算的城市生活让他们身心疲惫,原本固有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原则也悄无声息地被消解。进城务工人员中,这种新伦理更多地表现为临时搭建的夫妻关系。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呈现了在城市化影响下一个小城市里的变化。两个异乡打工的中年人各有家庭,为了生活结成临时夫妻,表面上看和正常的家庭生活并无不同,甚至还生出些许的温情来,但究其实质,仍是出于各取所需的利益考量。异乡的艰难生存境况使务工人员渴望在这种脱离了至亲血缘和天然情感的临时性关系中减轻负担、获得些许慰藉。
诞生于当代城市的日常生活新伦理祛除了血缘和情感,规避了责任和使命,如果从经济方面考虑,无疑是城市生活中灵活性较大、较为合算的选择;但规避了情感和责任的短暂性伦理关系,终究难以成为生活的常态。
三、城市灰色空间中的底层叙事
新世纪小说底层叙事关注的群体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进城务工人员,另一类是城市化进程中被抛到边缘的人群,比如在变革时代中没能跟上社会主流的城市原住民与国企改革大势裹挟下的下岗工人群体。上述两类群体占据的生存空间往往是远离城市社会生活中心的边缘地带,“边缘”不仅指称地理意义上的城中村,还指与城市正常、规范、正式的生活空间对立的城市灰色地带、异质空间[6]。
(一)无土时代:难有归属的进城人员
城市灰色地带往往处于无名状态,生活于此的底层群体的权利、利益和基本保障严重缺乏。于这一群体而言,完全融入城市的正常生活目前看来尚是遥远的梦想。基本权利和利益保障的缺失使这一群体无法充分享受社会变革红利,他们的生活状况和自身素质因而难以改观,这又进一步使更深的伤害指向他们,如此循环只能让他们的处境越发糟糕。所在空间生存资源的短缺导致了一系列的对抗城市正常生活空间的行为,尤凤伟《泥鳅》中的国瑞,用最笨拙的方式对抗城市,然而无论他在城市中心怎样穿梭,都无法得到身份的合法认可。进城务工人员进入城市中心如此艰难,不仅是由于这一群体与城市文化上的隔膜,还因为城市人对外来人口的拒绝,城市现代文化对乡土文化存在天然的排斥。《无土时代》里的木城出版社社长达客认为,大量进城人员扰乱了城市原本的正常秩序,他对他们的排斥与拒绝非常明显。张鲁镭的《美丽鞋匠铺》则在一个看起来温馨、和谐的故事中尖锐地表现了城乡观念的巨大差异和难以调和。高档小区住户春天偶然与小区鞋匠铺的夫妻春花和刘波成了朋友,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他们之间可以说是相当和谐,但文化、观念、认知的巨大差异最终显示出强大力量,短暂的温馨过去,他们成为陌路,甚至有了很深的隔阂。与张鲁镭不同的是,迟子建讲述的底层人物很少与城市中心发生关系,她的关注目光放在对进城民工困境中仍保有坚韧品格的颂扬上,如《踏着月光的行板》中的王锐、林秀珊夫妇,他们一开始就将自己放在城市中心之外,虽然也为在城市里得不到认可而烦恼,但没有融入城市的强烈渴望。王锐、林秀珊夫妇的这种生活状态在今天的打工群体中并不少见,这也从侧面凸显了城乡文化的巨大差异。
(二)霓虹灯下:扭曲灵魂的边缘生存
曹征路的《那儿》《霓虹》描述了国企改制大潮中下岗的职工群体的艰难生活,作家将下岗职工面临的各种困境安排在主人公倪红梅身上,强化了被甩向边缘的这一群体的生存困境。倪红梅在下岗之前处于城市中心,是优秀的技术工人,是被城市社会认可的人,下岗之后的生活艰难非常,习惯了计划经济的倪红梅跟不上社会变革的节奏,她找不到一份维持生活的工作。严峻的生存形势、冷酷的社会现实迫使她走向沉沦,走上了出卖身体、出卖灵魂的不归路。与倪红梅一道,阿红和阿月也是在货币哲学冷酷的生存法则下将务实主义奉为圭臬,不谈感情、避开崇高。当维持基本生活成为横亘在她们面前的巨大困难时,谁有资格批判她们的务实与麻木,谁又能忍心苛责她们的金钱至上呢。这些先前拥有城市正常生活的人们被城市化进程甩出中心,边缘化、缝隙化生存成为生活常态,作为城市的原住民,如若不被城市接纳,就再也无可退守。
几乎是在消费主义叙事落潮的同时,底层叙事崛起,且占据了城市书写的半壁江山,底层这个庞大群体的生存境况关系重大,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与书写不仅应当且非常必要。
四、社会变革中的官场生态与环保书写
在城市化的时代大背景下,社会变革中出现的问题必然会成为城市生活的关注热点,其中官场问题关乎政治,环保问题关乎民生,两者均为当下热点话题。受当代中国政治环境制约,涉及官场生态的小说多属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如陆天明的《省委书记》与周梅森的《我主沉浮》,可认为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通过小说文本达到维护官方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目的。这类小说在叙事中加入官方意识形态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消除或者说遮蔽了其他类型城市书写中呈现的恶劣的城市形象[7]。比如《我主沉浮》中的省长赵安邦,他对城市化进程中特定群体利益受损问题的思考即含有为失误的改革决策辩护的意味,他认为改革必然需要试错,必定会有相关群体的利益与权利受到损害,这是不可避免的。按照赵安邦省长的逻辑,改革具有原罪性质,决策失误就这样被部分遮蔽了。从另一角度看,主流意识形态小说也并非是政治话语的传声筒,在为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某些问题辩护的同时,它们也对恶劣的官场生态提出严厉批判,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维护相关规则和社会安定的作用。
中国文学历来与时代现实有着坚实的对应关系,为生民立命、为时代作见证或许是中国作家的一种偏好,这种文化遗传因子也出现在当下的生态小说中,作家发挥文学的社会参与功能,直接切入严峻的生态现实,不仅对世界环保潮流作出了积极回应,也表达了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忧虑与思考[8]。当下生态小说中有一类是高度写实的生态文学,逼近于纪实作品,如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几近写实地讲述了青藏高原盗猎者与保护者之间惊心动魄的斗争,作者对主要情节发生地的可可西里进行了精准描绘,对斗争过程的描写也与现实贴合。另一类生态小说加入了虚构与想象,环境虚化,但表达的情感非常真实,比如张炜的《怀念黑潭中黑鱼》,以回忆贯穿全文,讲述居住在水潭边的一对老夫妇和一群来历不明的黑鱼的故事,黑鱼请求这对老夫妇的接纳,他们也曾与黑鱼相处和谐,但后来抵不住诱惑将黑鱼出卖,黑鱼就此消失。张炜的故事多具寓言风格,这篇小说也在传奇讲述中意味深长地表达了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思想,包含了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谴责与批判[9]。冯苓植的《驼峰上的爱》给读者的感觉异于前述两类,小说没有刻意展示严峻生态现状,平和、安静地讲述了一头骆驼与几个小孩儿日常生活中的温情相处,这种对人与动物诗意生存的美好场景的展现所能达到的效果也并不比愤懑怒吼的控诉来得弱。
五、结语
社会转型期的复杂现实形成了当下中国城市文化的混杂、流动特性。当代中国迅疾的改革与开放使各种文化一拥而入,文化形态杂糅与并置、国家幅员辽阔与情况复杂,让今日城市面目神秘、不易把握。本文试从当下多元的城市文化热点切入,以新世纪以来的小说为分析文本,以期从文学作品中看见今日城市的大略样貌,但当下城市书写文本体量庞大、情况繁复,限于个人能力,预期意图难以完全达成。在今日中国,城市与乡村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的诸多问题,特别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人性异化均与城市化和城市多元文化密切相关,对城市书写的观照与研究应是进一步予以努力的方向。
[1]王兴文.城市化的文学表征——新世纪小说城市书写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3.
[2]罗刚,王中忱.消费文化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6-16.
[3]张柠.文化的病症:中国当代经验研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118.
[4]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自身现代化的文化透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02.
[5]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4.
[6]陶东风,周宪.文化研究(第十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11.
[7]刘起林.官场小说的价值指向与王跃文的意义[J].南方文坛,2010,(2):116.
[8]雷鸣.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几个问题的省思[J].北方论丛,2008,(4):46.
[9]雷鸣.危机寻根:现代性反思的潜性主调——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09:133.
编辑:鲁彦琪
Understanding Today’s Cities:An Analysis of the Hot Spots in the Urban Writing in the Creation of Novels
FAN Xiaodong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hengdu Sichuan 610041,China)
Urbanization has a profound and a full range of influence on Chinese society, novels about urban writing is an important form of recording changes of city cultur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new creation of novels, about the urban culture construction includes the construction in cultural consumption of urban material wonders, the multiple dimensions of modern thinking and traditional ethics of antagonistic, urban grey space in the bottom of narrative, social change in the officialdom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writing. In literature research,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writing of the city should be is the direction to be further efforts.
The novels in the new century ; urban writing; urban culture
10.3969/j.issn.1672-0539.2017.01.018
2015-04-15
范晓东(1990-),女,河南固始人,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
I022
A
1672-0539(2017)01-009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