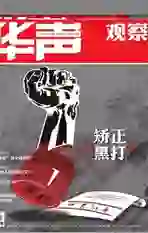黑人大叔迪亚拉 来华坐堂三十年
2017-03-21胡晴
胡晴
一位年过七旬的老者,按照医生的要求,将双手放在桌上。为他接诊的是一位皮肤黝黑、牙齿雪白的黑人医生。他身着白衫,口袋中插着一支笔,娴熟地用双手为老人号脉,凝眉细看、观察患者的脸色、辨识舌苔,和蔼地问病……大谈体质之热性凉性,中文流利并且会说几地方言,而他开方时书写的中文,在中国人看来都是刚毅、洒脱大方,别有韵味。
他的名字叫迪亚拉,来自西非的马里共和国,这是西非的一个内陆国家,距离中国有1万多公里。
阴差阳错遇见中医
迪亚拉的家里共有五个孩子,他排行老三。爷爷曾是当地的草医,父亲则是马尔卡拉医院的院长。
1984年,迪亚拉由马里政府选派到中国深造。到中国之初,他先在北京医科大学普外科学习,后却渐渐被中医的博大精深所吸引,于是决定弃“西”从“中”。“既然来到了中国,就应该学习有中国特色的中医。”他来到广州中医药大学,在那里读完了5年的本科。
“大学第一学期‘医古文只考了40多分,好惨哦!”说起第一次尝到考试不及格的情景,迪亚拉笑着摇了摇头。学习中医需要大量古代典籍知识,不懂这些怎么能学好中医呢?为了迅速提升自己,迪亚拉不仅向同学请教,就连古装剧都是他的老师。课余时间,他看古装剧、听古戏、逛博物馆,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中国文化。看到不认识的字就去翻新华字典,医学古汉语字典也被他翻得破破烂烂,甚至掉了页。迪亚拉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到了“研究”中国文化上。他认定,中医就是他一生的理想追求。
一展身手家乡认可
1990年暑假,迪亚拉回到了家乡,决定到医院一展中医之长。当时,毕业于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妇科专业的师兄是医院的院长。师兄听说迪亚拉要来医院坐诊针灸,脸上露出了怀疑的表情,还把中医称为“巫术”。
一天,一个怀有四个月身孕的孕妇因打嗝到医院就诊。之前,师兄已经为其诊治过几次,并未见效。无奈,这次师兄将患者带到了迪亚拉面前。“你这个搞巫术的,来看看这个病人有没有办法治?”师兄脚都没迈进迪亚拉的诊室,说完话就要走。“你别走……”迪亚拉一边忙着将患者扶至病床上,一边对师兄说。
迪亚拉在患者手腕的内关穴和脚上的公孙穴进针,行针5分钟后,患者症状缓解。紧接着,他又在患者背部定喘穴行针。约半个小时后,孕妇打嗝的症状完全消失了。“太神奇了!”师兄感叹道。
拒绝了师兄的盛情挽留,迪亚拉再次回到中国深造。在广州学了中医的“岭南派”,又去四川拜在“神针杨”杨介宾门下学习“峨眉派”。2012年他还进入了湖南中医药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开展临床科研。11年苦读,他最终成为全球第一位获得中医博士学位的外国医生。
日久生情有了真爱
博士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迪亚拉在成都一家中医院坐诊。“没有一个人找我看病。”他对着空荡荡的诊室守了三天,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隔壁诊室排着长队。终于在第四天,一个患者推开了大门看到他,惊慌地叫了一声就跑出去,诊室总算是有了一点动静,他也没觉得委屈,直接推门追到了挂号台。
“我是来看中医的呀,怎么黑黢黢的呢!”患者对着护士用四川话抱怨了一番。迪亚拉都听懂了,他说:“这样吧,我给你扎针,如果没有效果,我不收你一分钱。”他就这样争取到了第一个病人。把脉、看舌头、分析、扎针,迪亚拉细致而熟练。第二周,这名患者给他又带来了自己的朋友,这样的口耳相传之中,迪亚拉成为了一个小有名气的黑人中医。
事业步入正轨,爱情也悄然而至。迪亚拉信奉基督教,常到成都顺城街的一家教堂去,他在那里认识了当时27岁的杨梅。她由于长时间操作电脑,眼睛日渐近视。迪亚拉为之扎针,止住了视力下滑。他又建议她戴耳环:“对防近视会有作用。”
接触多了,双方都有了一定好感。小心谨慎的杨梅刚开始对迪亚拉心怀芥蒂,但她发现迪亚拉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和渊博的知识,慢慢地,她从心里接受了这位非洲黑小伙。
杨母有风湿,杨梅邀请这位黑人朋友为母亲治疗。第一次来串门的迪亚拉不像别人一样称呼二老为“伯父”“伯母”,而是叫“爸”“妈”。杨梅的父母一听很是恼火,要赶迪亚拉走。迪亚拉连忙解释,在马里,一般称呼上年纪的熟人为“爸”“妈”,才化解了危机。迪亚拉给杨母扎针,杨梅热情地端茶递水,俩人亲密得很,杨梅的父母很快就看出了端倪。杨父坚决反对女儿与之来往——马里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实行着一夫多妻制。最终,迪亚拉以真诚打动了杨家父母。
1997年8月,迪亚拉、杨梅在成都天主教堂举行了结婚仪式,不久有了一对可爱的儿女。
术德兼备培训村医
迪亚拉的第一份工作还没做多久,院长找到他:“你的病人是最多的,但是你的奖金是最少的,你不能多开一点药吗?”迪亚拉拿来工资条,奖金是172.5元,还不足他读书时补助的零头,院长第三次找他谈话的时候,他也递上了自己的辞职报告。
辞职后,迪亚拉加入无国界医生组织,担任协助麻风病和大骨节病项目的医疗官。
迪亚拉来到云南,他发现那边的乡村医生状况不容乐观。“这支队伍(乡村医生)曾经为中国的医疗发展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础,但如今却得不到重视,所以我要帮助他们。”迪亚拉向当地政府申请,让乡村医生来免费学习,他包揽他们的路费、住宿费、伙食费,毕业之后还要送他们三大件(听诊器、血压表、体温表),除了这些,还有工作服、一些药品和书籍,让他们回去安心开展工作。
坚守乡村行医17年,迪亚拉仅在云南红河州就培养了村医3000多名。红河6个老少边穷县,90%的村委会都有了自己的乡村医生。
未雨绸缪内外开花
每当有人把中医看作伪科学,迪亚拉比中国人还着急,他说他和中医同行要做的最重要事情,就是把中医整套體系推广到西医世界,而不是改变中医自身向西医妥协。中医在众多质疑声中,依然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不仅仅是因为国家政策的支持,更多的是中医这个整体医疗体系的效果为世人所见证!
他正打算把在非洲学过中医的人联合起来,成立一个集科研、教学、医疗于一体的中医诊疗中心。“像在中国培养乡村医生一样,在非洲开展此项培训。同时用中医的方式,研究、开发非洲草药。”
迪亚拉博士后课题就是围绕治未病的,研究抗病毒的中药。“中医治未病是伟大的,能够防患于未然。中药不仅有治疗功效,还有预防作用。中药,或者中药措施,通过扶正祛邪,就可避免、减少病毒感染。”
摘编自搜狐健康、山西新闻网、《 人民日报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