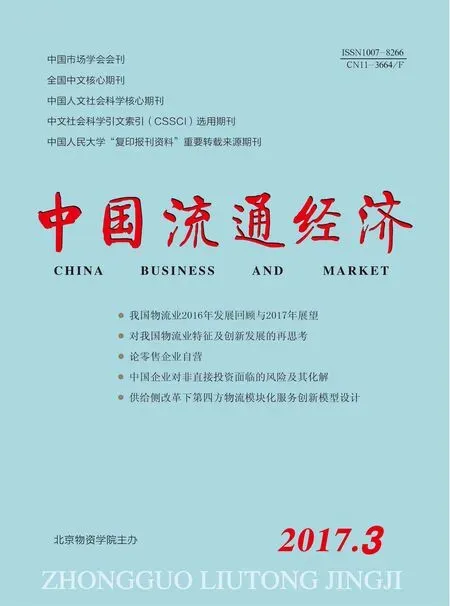论京津冀地区制度协同发展的困境与思路
2017-03-16魏丽华
魏丽华
(1.河北省委党校,河北石家庄050016;2.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市100091)
论京津冀地区制度协同发展的困境与思路
魏丽华1、2
(1.河北省委党校,河北石家庄050016;2.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市100091)
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有效的制度安排是改善生产力、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主要原因,制度设计的优劣以及协同性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多年来,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一直踌躇不前,其主要原因在于制度设计协同的滞后。尽管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对各地均有好处,却因有效制度供给不足,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不能协同,博弈行为主体谈判地位不对等,传统制度设计的路径依赖固化既有利益格局,导致市场分割状态依旧,既无法实现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也无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进而形成了集体行动难题。而要进一步推动三地合作进程,创造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良好制度环境,必须构建制度协同体系,强化制度设计体系中利益的协同性,强化制度供求结构的有效性与均衡性,强化政府在制度供给中权力行为的边界性。
京津冀;制度协同;个体利益;协同利益;权力边界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现状
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专家学者以各自的研究领域为基础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描绘了一幅幅美好的蓝图。然而,三十多年过去了,与一体化发展早已实现常态化、规范化的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相比,京津冀地区协同效果黯然失色。究其根源,可能因为京津冀地区核心城市带动力不足,辐射效应弱,存在着区域间的辐射封闭与逆向辐射;可能因为京津冀区域发展差异过于悬殊,无论是“一核独大”的北京,还是“双核的”京津,均是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进而导致了对河北明显的虹吸效应,制约了区域一体化进程;可能因为三地合作关系复杂,各自为政现象突出,政府对经济发展干预较多,行政主导型经济痕迹较重,市场机制发挥不充分;可能因为产业关联度弱且产业同构,负面影响三地协同发展。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基于不同视角探讨了导致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滞后的原因,丰富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体系,但从制度根源入手对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滞后根源进行解析的研究尚有待进一步深入。
制度作为经过多次博弈建立起来的规范,是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规则与实施机制的结合。它既是制度供给者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也是偏好不同的制度行为主体不断博弈最终形成的一种均衡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是内生的。作为内生变量,有效的制度安排是提高生产效率与要素市场配置效率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基于此,制度设计的优劣与协同性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就京津冀地区而言,多年来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发展一直踌躇不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制度设计协同性的滞后。
二、京津冀制度协同的困境
京津冀一体化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无论是基于历史的角度,还是基于发展的现实,三地间均存在着盘根错节的渊源。尽管实现三地协同发展对各地均有好处,存在共同利益,却因有效制度供给不足,导致市场分割状态依旧。这既导致资源和生产要素无法达到最优配置,也导致市场机制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进而形成了公共选择理论所讲的集体行动难题。
(一)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非协同性
根据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设,个体在社会互动行为中会自然而然地选择对自己最有利、能最大化自己收益的行动策略。因此,在经济社会运行中,某一地区的最优选择就是本地区利益的最大化。然而,区域经济发展作为一个开放性系统,经济体系中的各种行为都是相互的,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个行为主体利益最大化选择与另外一个行为主体利益最大化选择的冲突。正如囚徒困境所揭示的那样,个体理性选择驱使下的非合作博弈,其结果往往都是无效率的,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所导致的可能会是集体的非理性。
长期以来,京津冀各地区在制度安排上仅仅顾及自己眼前的“一亩三分地”,仅仅关注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不重视协同利益的推进,主要考虑以个体利益为核心的单体化发展。例如,北京凭借自身所具有的首都行政属性,考虑周边地区利益诉求不够,而且需要周边地区为自己服务。例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些学者就曾一度提出把河北的秦皇岛市划归北京的设想,以解决北京没有港口的短板,类似设想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城市发展单极化的思路。津冀两地亦是如此,其中两地对港口资源的争夺就是典型例证。渤海湾密集分布着天津港、秦皇岛港、京唐港、曹妃甸港、黄骅港等五大港口,这些港口腹地交叉重叠,岸线连接紧密,货源配置相似,产业结构雷同,对货源市场的争夺从未停止过。更让人担心的是,两地大规模建设各自港口的热情依然不减,而在当前世界经济下行的态势下,很多港口码头都处于闲置状态,已经造成了资源要素的极大浪费。正是由于每个行为主体都仅仅关注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而无视或弱化协同利益的推进,且对已经发生的利益冲突缺乏有效的制度来加以调节,结果导致京津冀协同制度推进的长期停滞。
(二)博弈行为主体博弈地位的不对等性
制度的有效设计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在京津冀三地博弈中,行政关系的多重交叉性使得京津冀三地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是平等的兄弟省市关系,其背后却夹杂着中央与地方、首都与普通行政区之间的特殊关系,这就决定了三地间更为复杂和微妙的多重利益属性,也正是这种复杂关系的存在,决定了作为利益博弈行为主体的三方地位关系的不对等性。在三地中,河北省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战略取向,还是在资源利用、产业布局、大型投资项目争取等方面,都处于极其弱势的谈判地位,河北省的产业结构、产业政策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目标都要受到京津发展战略的牵掣,要从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服从服务于京津发展战略,包括放弃一些地方利益和目标。
河北所处的弱势地位在省级主要领导干部的身份、任命与更替上也可略见一斑。众所周知,各省市区主要领导干部在省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舵手”功能,其身份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该省市区在全国区域发展中的相对地位,反映该省市区在区际谈判中话语权的大小。在当前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共计25人)中,在京津有过任职经历的有4人(王岐山、张高丽、郭金龙、孙春兰),在河北有过任职经历的只有1人(胡春华),而且是短暂停留后即赴他省任职。同时,北京作为众多央企、金融机构、跨国集团总部的聚集地,实力雄厚,也有可能会在某些方面或者某种程度上对制度供给产生影响。
主要领导干部相对稳定和较长的任职期限,对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二十多年来,河北省主要省级领导干部更迭频繁(详见表1),对河北省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难以挽回的影响。

表1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河北省历任省委书记、省长任期情况
与京津两市(详见表2、表3)相比,可以清晰地看到河北省主要省级领导干部频繁更替的情况。表1显示,在20世纪90年代到2015年底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河北经历了8位省委书记和8位省长,平均每位省委书记的任职期限是2.75年,每位省长的任职期限是3.15年。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更替更加频繁。在从2002年底到2015年底的13年间,河北经历了5位省委书记和5位省长,平均每位省委书记或省长的任职期限是2.6年。在5位省委书记中,年龄最大的任职时已经62岁,最小的任职时是54岁;任职时间最长的是5年9个月,最短的是1年7个月。在5位省长中,最年轻的任职时是45岁,年龄最大的任职时是59岁,任职时间最短的是1年6个月。截至目前,担任省长时间最长的是现任省长张庆伟,已经4年有余。由于任职时年龄偏大(临近退休即将离开政治舞台)、任职期限较短(短暂停留后即到他省任职),导致河北省领导阶层更容易缺乏可以持续作为的预期。同时,出于风险规避的考虑,更容易缺乏足够的激励机制来改善地方治理效率问题。
此外,在省级主要领导干部频繁更替的同时,还存在作为省级一二把手的省委书记、省长彼此间搭档频繁更换的尴尬。比如,在白克明同志担任省委书记的4年多时间里,先后与钮茂生、季允石、郭庚茂等3位省长搭档;在张云川同志担任省委书记的4年时间里,先后与郭庚茂、胡春华、陈全国等3位省长搭档;在张庆伟同志担任省长的这4年多时间里,经历了张庆黎、周本顺、赵克志等3位省委书记。省委书记、省长的频繁更换以及一二把手搭档间的不断调整,对地方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是深刻的。自2000年以来,河北省先后经历了“两环开放带动”“一线两厢”“打造沿海经济隆起带”“三年大变样”“经济强省,和谐河北”“四大攻坚战”“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等发展战略,平均每项战略持续时间仅为2.14年。
而在与之相对应的时期,北京经历了5位市委书记和7位市长(详见表2),且呈现出明显的市长升任市委书记的特征(如陈希同、贾庆林、刘淇、郭金龙等);天津经历了5位市委书记和4位市长(详见表3),每位市委书记和市长的任期都相对稳定,且很大一部分或者先在天津担任主要领导然后到中央任职,或者先在中央任职然后到天津担任主要领导(如李盛霖、戴相龙、张高丽、孙春兰等)。京津冀三地主要领导干部的安排,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制度安排背后多重的利益考量。
(三)传统制度设计的路径依赖导致了既有利益格局的固化
在制度经济学看来,初始或既有的制度安排会给新的制度安排打上深深的历史烙印,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而路径依赖形成的原因在于,既有的制度安排造就了既得利益格局,形成了一种强化而稳定的均衡状态。这也进一步说明,要打破既有利益分配格局,造就新的制度均衡,需要付出的成本将是巨大的。

表2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市历任市委书记、市长任期情况

表3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天津市历任市委书记、市长任期情况
一般来讲,制度的变迁通常会带来财富、收入、权力在不同利益群体间的重新分配,这就决定了各种制度安排并非完全取决于效率原则,还取决于不同利益集团的规模、地位及其对制度的影响力,从而直接决定了既有制度安排在特定情况下的非最优化。而非最优化的制度安排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或强势群体拥有更多资源,可以影响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从而以牺牲他人利益甚至以缓慢的经济增长为代价来换取自身特殊的利益。[1]这种非最优化的制度安排在路径依赖的影响下,导致新的制度安排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既有制度细枝末节的修补,很难从根本上触动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
从历史的角度看,河北作为省名出现始于1928年。1928年7月,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在天津成立,省会设在天津。之后,省会曾先后迁往北平、天津和保定。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标志着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消亡。1949年7月,为便于统一领导,便于恢复和发展生产,便于进行各项建设事业,恢复了河北省建制。1949年8月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省人民政府驻地设在保定市,共辖4个市(唐山市、石家庄市、保定市、秦皇岛市),10个专区(其中包含天津专署),10个镇,132个县。[2]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的成立是河北省政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河北省结束了长达12年的冀东、冀中、冀南、太行等几个行政区分割的历史,开始走向统一。[3]然而,以1949年9月北平更名为北京并成为首都、1949年11月天津成为直辖市这两大事件为标志,很快掀起了京津冀行政区划调整的两次浪潮。第一次行政区划调整的浪潮主要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在这次浪潮中,原本属于河北省的顺义、良乡、大兴、房山、通州、昌平、怀柔、密云、平谷、延庆等地相继划给北京市,形成了北京今日的行政版图。第二次行政区划调整的浪潮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在这次浪潮中,河北省境内的静海、武清、宁河、蓟县、宝坻以及唐山遵化境内的一些公社相继划给了天津,形成了天津今日的版图。而导致京津冀行政区划不断调整与变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围绕水资源和国土资源而展开的博弈。
从现实发展看,随着建国后国家工业化战略的推进,全国各地开始着手建立各自相对独立的产业体系,京津冀地区亦不例外。受当时片面追求GDP的激励与考核机制影响,北京开始着力于发展生产,在不具备任何资源优势甚至严重缺水的情况下成立的首钢就是盲目构建“大而全”“小而全”工业体系的典型例证。而随着生产型城市框架建构的完成,北京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除港口和资源等少数领域外,基本已经不再依赖津冀的拱卫。此外,天津与北京关于经济中心的竞争由来已久,天津与河北既有产业体系的高度重构以及资源结构的同质化竞争更是进一步恶化了彼此间的协作关系。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交通活动范围的扩大,三地间彼此的产业依存关系日渐淡薄,进一步稀释了本已脆弱的经济关联。
受诸多历史与现实因素影响,国家宏观战略与微观利益博弈的权衡导致京津冀三地的制度安排并没有完全遵循净财富最大化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则,诸多制度体系的效率也并非最优。区域治理主体之间博弈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京津冀三地行政关系的特殊性,使得各行为主体在三方利益博弈中面临多重利益的权衡。
例如北京,一方面它是直辖市,代表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单元,对地方利益的追求和关注决定了其在经济发展中与周边地区的竞争性;另一方面它又代表着首都,是中央政府所在地,这就决定了其既需要经济发展处于发达水平,又需要拥有良好的生态和社会发展环境。而目前北京既有的产业,或者辐射半径过小,扩散能力有限,主要集中在京郊附近,对临近的津冀两地辐射能力弱;或者与周边地区的差异过于悬殊(如高新技术产业等),周边省市无力承接。这导致了京津冀三地经济内生衔接性不足,外生互斥性较强,经济和技术协同性较差。北京不仅未对我国北方或者环渤海地区产生明显的拉动作用,即使在京津冀区域内部京津对河北的拉动作用也非常有限,很难与广州对广东、上海对苏浙的拉动作用相比。究其制度根源,主要在于很多市场行为被政府行为替代,很多扩散力被行政区界阻隔,很多互补优势被无序竞争袭夺。因而,行政区域性的地方保护、政策包围圈、边界阻隔等高层行政管理体制,成为横亘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重要壁垒。
再如河北,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省份,承载着7 000多万人口生存与发展的重任。这就决定了它一方面面临地方利益与中央利益、本省利益与相邻省市利益的权衡,面临省内经济利益、社会利益与生态利益的权衡;另一方面,作为与北京毗邻的省份,无论在社会稳定方面,还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均肩负着拱卫首都的重任。同时,对地方领导者而言,还面临着自己所代表的行政区利益与个人政治利益的博弈。上述利益在很多情况下的不一致性无疑增加了博弈的难度与选择的复杂程度。例如,京津冀三地共饮同一水系,共享同一生态屏障,生存发展环境唇齿相依。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河北都在作为京津的经济腹地和生态屏障,独自承担着环境保护和生态维护的重担,京津两市受行政区划属性影响在生态维护协同体系中明显缺位。且河北在京津两大直辖市区位、人才、资金、信息、市场等方面优势的挤压下,既面临着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维系发展的压力,又承担着拱卫首都、维护生态与社会稳定的重担,其弱势地位显而易见。其中,河北的张家口、承德地区既是三地的生态敏感地区,也是环首都典型的贫困地区。多重利益博弈导致河北经常处于首尾无法兼顾的尴尬境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京津冀整体发展环境的协同统筹。
三、京津冀制度协同发展的思路
与传统经济学更多强调竞争相比,制度经济学更多强调合作的重要性。基于制度建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短板,构建制度协同体系、深化三地合作进程、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势在必行。
(一)强化制度设计体系中利益的协同性
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的行为关系存在相互性。在社会关系背景中,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应以不侵害他人的利益为前提。对整个社会而言,以损害他人利益为代价的利益最大化并不是真正的利益最大化。因为被损害者总要采取报复策略,从而会导致获取他人利益行为人的福利损失。[4]制度经济学中的囚徒困境,就质疑了亚当·斯密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发地把个人利益最大化行为转化为社会福利最大化行为的论断。与个体理性不是群体理性的充分条件一样,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也不是群体利益最大化的充分条件。根据囚徒困境的定义,在一定的条件下,刻意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最终结果并不一定是自利,却很有可能是两败俱伤,形成一种与当事人个人初衷相悖的困境,而集体理性选择下的合作博弈则很有可能带来最优选择。因此,将制度设计的重心更多地放在合作上,将关注点更多地放在协同利益而非个体利益上,这样的制度安排才有可能效率更高。
区域协同发展要求实现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无障碍跨界流动。然而,当前我国地方经济一直存在明显的“碎片化”现象,即同一国家内部存在着大量拥有一定自主权力的地方政府。自主而分散的多中心政府致力于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无法解决大区域内各种各样的矛盾,从而会造成一种“有组织的混乱”。同时,各中心政府间受自利性驱使会引发地区利益冲突,导致各中心政府运用行政权力阻碍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进而构成了现阶段我国区域协同发展进程中的主要矛盾,京津冀地区亦是如此。
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其他各界,一直有声音主张通过调整行政区划来化解京津冀之间的利益矛盾,寄希望于通过调整行政区划来促使外部竞争内部化,以此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这在某些特定区域范围内或许有效,但如果由此认为调整行政区划是包治区际矛盾百病的“灵丹妙药”,则未免有些过于天真。京津冀地区既缺乏长江三角洲那样的政府全力推动,又缺乏珠江三角洲那样充分发育的市场,单纯调整行政区划未必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因为,导致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滞缓的根源在于制度体系的行政分割性而非协同性。基于此,构建以协同利益最大化为主要内容的制度体系,以协同化的制度纽带联动三地市场协同化进程,成为解决这类问题的一剂良方。
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实际上是各行政区之间利益博弈的过程。行政区划造成的鸿沟导致利益主体与决策主体背离,管理边界与功能边界错位,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失衡。各行政区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其最终的博弈均衡解就是能够实现各方利益的动态平衡,并获得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或卡尔多—希克斯改进(Kaldor-Hicks Improvement)。
这就需要正确把握区域联合与区域竞争之间的关系,将三地的目标和聚焦点从各自“一亩三分地”的利益最大化转到区域整体实力、综合竞争力、协同影响力的提高上来。京津冀三地人缘相近,地缘相接,历史渊源深厚,在自然环境与社会安全领域唇齿相依。京津的人才、技术、资金、信息等优势是河北省短缺的要素,而河北省广阔的市场空间和生态环境是包容京津发展的重要堡垒。一味的牺牲、完全的配角经济不可能推动河北省实现转型升级与跨越式发展,也不可能实现河北省建设经济强省的战略目标。
协同化的制度体系内生于聚焦在“面”(大区域)而非“点”(某个特定的省市区)上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安排。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面”(大区域)上的各主体可以实现区域内部的集体行动,包括设定区域协同目标和规则、内容和程序、手段和途径,做出协同化的公共决策,组织并协调区域集体行动,形成区域内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协作治理。具体而言,就需要平衡京津两个超大城市与河北省中小城市之间的发展落差,统筹三地利益诉求,谋求协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畅通无阻,其中尤其要在高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公共服务制度创新领域谋求新的突破,以协同化的制度体系为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保驾护航。只有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水平达到相对的均衡,人口、资源等要素的畸形集聚才能够得到有效的分解。
(二)强化制度供求结构的有效性与均衡性
在制度经济学看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并不在于资本形成的规模或者各种现成的其他战略性变量的变化,而在于基本制度环境的特征以及这些基本规则实行的程度。[5]在经济社会运行过程中,有效制度供给的不足、低效或无效制度供给的过剩以及制度供需之间的结构性失衡,都会导致制度安排的低效率。
联系京津冀地区发展实际,可以看到,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多年、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漫长历程中,随着产品与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市场规模的扩大以及技术水平的提高,相关要素的变化均对新的有利于促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制度安排产生了新的预期,进而产生了对新的制度设计的需求。然而,受旧有计划经济思维的影响,受传统制度设计路径依赖的制约,更有效率的一体化制度设计迟迟没有出台,更多政策规划依旧是对原有利益格局的修修补补,尚未触及关系三地核心利益格局的深层次问题,结果导致了有效制度供给的不足,无效或低效制度安排的过剩。制度供需结构的失衡既延缓了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也在无形中拉大了京津冀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的发展差距。
放眼当前,可以看到,在区域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集团化态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单体城市已经很难在国际舞台上形成综合竞争优势。区域竞争形式正在由过去传统的城市间竞争向城市群竞争转变。受全球经济产业链条化影响,区域经济体内的各城市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京津冀若要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中脱颖而出,全力构建我国经济崛起的“第三增长极”,就必须尽快摒弃传统做法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通过构建有效而均衡的制度结构体系来为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提供保障。
构建有效而均衡的制度结构体系需要以协同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深刻把握影响制度供需与制度结构均衡的若干因素,改革过时和低效的制度安排,代之以更具有创新性、更富有效率、更能够反映时代要求的制度框架,实现制度供需结构之间的有效匹配。比如,打破以行政区划属性为边界的制度设计,积极探索跨区域GDP分计与税收分成机制、区域生态利益合理补偿分担机制等。同时,摒弃各种强化行政边界的刚性约束的非市场化行为,探索尝试以区域协同度作为考核评价地方经济开放度的重要指标,充分激发市场机制、创新机制、合作机制在制度设计与协同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合作型而非竞争型制度设计提高区域要素市场吸引力,改善区域整体福利状况。
(三)强化制度供给中政府职权的边界性
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曾经提出过经典的诺斯悖论。在诺斯看来,由于政府目标函数的多元化,国家作为博弈规则的主要提供者,在界定产权、凭借国家权力来构造有效的产权结构、制度安排、经济发展必要条件的同时,也会对个人的财产权造成侵害,导致所有权的残缺。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也会造成无效的产权与制度安排,并进而制约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国家的存在既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是有限理性的博弈主体。有限理性决定了在区际利益博弈过程中,如果不对政府行为附加任何边界限制,就不可能达到利益的均衡,也即存在帕累托改进的可能。因此,为实现制度供需结构之间的平衡,构建有效的制度协同体系,就需要合理限定政府在制度供给中的行为边界,最大程度地避免政府在制度供给中的缺位、错位或者越位。
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既是一个社会制度变迁的过程,也是一个既有利益格局调整与再平衡的过程。导致京津冀协同发展多年来进展迟缓的一个制度性原因就在于,政府职权过度延伸,进而导致了市场发育的不充分。一直以来“强政府、弱市场”的现实,既激化了典型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所带来的恶性竞争、贫富分化、生态恶化等矛盾,加剧了区际利益的非均衡性,也极大地影响了京津冀市场机制的发挥,扭曲了市场在要素配置中作用的发挥,形成了低效制度对高效制度的排挤,进而造成了制度供给中的“柠檬市场”,直接导致了京津冀地区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之间日渐悬殊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因此,要改变这种现状,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规范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边界,让市场机制和社会化机制等在要素配置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加快政府制度创新,加强各地区之间的协同发展和政策一致性,突破行政体制对产品和要素市场化的阻碍。
这就需要优化政府在权力配置与要素配置过程中的合理边界,科学定位政府在制度协同体系构建中的角色与作用,通过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负外部性的地方保护。要深入推动经济运行与要素配置中的去行政化进程,在深入推进京津冀经济社会发展协同化战略研究的同时,进行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市场运行机制建设为主题的规划与战略实施路径研究,为协同体系的构建搭建平台。
过去三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是经济社会有活力的地方,政府都把手中的权力最大限度地下放到了基层,下放到了市场,下放到了企业,下放到了社会,实现了宏观调控的微观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活力能否充分释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有序推进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否拥有良好的制度与市场秩序,而这首先需要实现体制机制的协同创新。要通过协同性的简政放权,让作为创新科技与文化软实力国际中心的北京,让作为现代产业体系中心的天津,让作为战略支撑带的河北,各司其职,联袂而动。[6]比如,为三地主要领导人在相关方面提供高度大体相当的平台,实现领导职能权属范围的对等化;释放北京作为首都而集聚起来的大量政治、社会、经济职能以及由此而附属的大量权力资源、政策资源还有医疗、教育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实现要素配置领域的公平均等化;积极探索横向转移支付、央地间财税制度安排、区域协同GDP考核标准、跨区域财税分成、GDP分计等制度设计,实现利益协同分配的均等化,等等。
[1]程恩富,胡乐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66.
[2]石虹,严兰绅.当代中国的河北(下)[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400.
[3]李振军.有关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的几份重要文件[J].档案天地,2009(12):25.
[4]李军林.制度变迁的路径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9.
[5]“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课题组.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若干问题[J].经济研究参考,2003(56):7-13.
[6]张燕生.以制度协同创新推区域协同发展[N].人民日报,2014-06-04(05).
责任编辑:陈诗静
On the Dilemma in Beijing-Tianjin-Hebei Development and the Way of Thinking of That from the Angle of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WEI Li-hua1,2
(1.Hebei Committee Party School,Shijiazhuang,Hebei050016,China;2.The Graduate School of Central Committee Party School,Beijing100091,China)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the effectiv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is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improving productivity and enhancing the efficiency of factor allocation.For a long time,we have not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and the main cause for that is the lagged behind coordination in institutional design.Though there are the common interests i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this region,there is still market segmentation because of the inefficient effective institutional supply,the not coordinated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interests,and the not matched negotiation position of different game behavior main bodies.And all of this will lead to“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with the problem of the not optimized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nd factors of production,and the ineffective role of market mechanism.To deepen the cooperation in this region and create the sou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this region,we should establish the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system,strengthen the interests coordination in institutional design,strengthen the effectiveness and balance of institutional supply and demand structure,and strengthen the boundary of government power in institutional supply.
Beijing-Tianjin-Hebei;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individual interests;coordinated interests;power boundary
F061.5
A
1007-8266(2017)03-0088-08
2016-12-20
2014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协同发展战略下培育京津冀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研究”(HB14YJ005)
魏丽华(1979—),女,回族,河北省易县人,中央党校研究生院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河北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