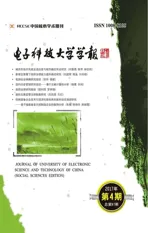都市圈地方政府整体性协作治理机制研究
2017-03-14郑戈溪
□崔 晶 郑戈溪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 100081]
都市圈地方政府整体性协作治理机制研究
□崔 晶 郑戈溪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 100081]
随着城市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都市圈公共事务的协作治理问题越来越突出。构建不同利益主体间的整体性协作治理机制是实现都市圈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间的信任与沟通机制是实现整体性协作治理的运作基础,利益分配与补偿机制是地方政府间协作治理有序推进的保障,监督和评估机制是提升都市圈地方政府协作治理整体绩效的关键。
整体性治理;协作机制;都市圈;地方政府
近年来,在城市和都市圈治理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有关超出地方政府管辖界限和政府部门职能界限的公共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合并模式、多重政府模式、政府职能连接模式、复杂网络治理模式,以及公共选择模式等区域地方政府协作治理的模式[1]。现实中,政府部门间跨越彼此界限,跨越不同政府层级,跨领域合作的案例也越来越多。然而,由于区域管理中的“碎片化”或行政分割现象不断出现[2],信任机制、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导致了都市圈地方政府间难以达成长期有效的协作。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践证明,整体性治理理念和机制的缺失是导致区域公共事务治理中行政分割,区域地方政府间协作关系不稳定甚至协作低效的重要原因之一。佩里•希克斯(Perri 6)认为,整体性治理的核心问题就是找到恰当的、有效的和可接受的方式,来实现组织间关系的平衡[3]118。由于整体性治理理论以协作、整合、“跨界性”为特征,强调区域治理中的跨部门协作,关注区域内政府之间、政府和其他社会参与主体之间的合作机制的形成,进而关注整体利益,在都市圈地方政府协作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建立都市圈地方政府整体性协作治理机制,是解决地方政府协作困境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的要求。本文将在信任与沟通机制、利益分配与补偿机制、监督和评估机制等三个方面探讨都市圈地方政府整体性协作治理机制。
一、地方政府协作治理的信任与沟通机制
希克斯强调,不同政府层级之间、政府部门之间的信任,以及政府部门与非政府组织和私人组织之间的信任构建,是实现整体性治理的关键。都市圈地方政府整体性协作治理机制的基石就是不同利益主体间信任的构建。针对很多大都市区地方政府陷入的集体行动困境,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认为,必须重建社会资本,营造公私部门之间、邻里社区之间的友善和互信[4],“社会信任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伦理道德的核心组成部分,它维持了经济发展的动力,确保了政府的绩效。”[5]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认为人们的交易行为深深地嵌在社会网络之中,并且由人们之间的互动而产生的信任有助于阻止不法行为[6]。法国社会思想家迪尔凯姆(Émile Durkheim)认为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是任何社会运行的保障,是契约的前提条件。信任是一种组织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要委托人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利益置于某种风险当中。福山(Fukuyama)认为,信任是委托人就他们所期望的行为和利益对代理人的依赖[7]。可见,信任是协作治理中的粘合剂,是协作各方达成意愿的基础和保障。
组织间的信任关系是由两个维度决定的,即组织间信任的原因和信任的体现方式。一个组织总是会基于某些原因而信任某个组织,而信任的原因不同会导致不同的信任方式。总的来说,组织间信任关系的构成基于以下几个原因:(1)经验。信任一般是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如果组织间有过合作的经验,这种经验会证明彼此之间是可以信赖的。历史上有着良好的合作经历,那么就较为容易建立信任关系,所谓“熟悉培养了信任”。如果合作历史薄弱,或没有先前的合作基础,那么就不容易达成信任;(2)声誉。组织的声誉是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参考。人们一般会信任有着良好合作声誉或名声的组织,而我们也会认为这些组织会珍视他们的良好声誉,继续保持这样的声誉而不会轻易破坏它。在这个意义上,声誉就像是一种担保或抵押物,是信任关系建构的保障;(3)共同的特性。组织间有着共同的历史或文化渊源,或者在地缘、流域、气候等因素方面具有较高的同质性,会使得他们之间具有较强的协作基础;(4)制度因素。组织间建立信任关系也基于各种各样的制度因素。一般的制度因素包括违约事件法律补偿的可获得性,而一些特别的制度因素包括组织提供的保证和担保,或者其他的质押物[3]119-120。
由于以上不同的原因会导致不同程度的信任方式。首先,最低层次的或仅仅处于谨慎试探阶段的信任是组织对其他组织某种承诺、威胁和其他做与不做某件事情的意图的信任。其次,更高一级的信任是组织间凭借法律准则,公开地或私下共同签署契约并执行之。这种信任关系可能需要组织能力水平作为准入门槛,即组织间要签订契约,相互之间都要有合作内容所要求的能力。最后,高级的信任层次是组织间的友好善意阶段。组织间的信任达到超越契约具体条款的阶段,即契约中体现的组织间的信任关系弹性更大。在相互关系中,一个组织可以把某些不利于它自身利益的条款放在一边,而有利于自身利益条款的内容可以扩大,而不仅仅拘泥于契约条款的内容[3]120。
在很多情况下,组织间的信任并不是基于一种原因,而是多个原因的组合。进一步说,如果组织达到了友好善意阶段的信任,那么也就意味着已经经过了谨慎试探阶段和签署契约阶段。因此,任何一种信任关系体现在信任原因和信任方式两个维度上都不是一一对应的,即信任关系并不是体现在一个原因对应一个方式的点上,而是体现在一块区域上。
然而,经验和声誉是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构建起来的。因此在初始阶段,组织是不是要与另外的组织建立信任关系主要取决于另外两个原因,即共同的特性和制度因素。这里的制度因素包括对于合作另一方的特殊法律义务、上级政府所要求的惩罚和奖励。如果这种信任关系成功建立,那么很有可能随着信任原因和方式的发展,会最终达到友好善意阶段。
因此,整体性协作治理之信任机制的构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历渐进式的几个阶段:
(一)谨慎试探阶段:建立对话与沟通渠道
谨慎试探阶段是构建整体性协作治理信任机制的初始阶段或低层次阶段。在这一阶段都市圈各个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或私营部门之间可以就某些承诺的意向展开对话,建立横向的交流与沟通渠道。通过这些初步的沟通,都市圈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可以了解彼此的基本政治、经济、文化情况,以及对于合作的某些承诺。正如阿格拉诺夫和麦奎尔所言,在城市政府的协作过程中,地方官员需要向潜在的合伙人兜售思想,调动合伙人对协作及协作目的的承诺和支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创造环境促成合作人之间的交往[8]。这样有助于合作各方对于拟协作项目的理解。在这一阶段,协作各方之间的信息流是至关重要的,构成信息流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重要元素就是信任、行为规范和连接网络。另外,这一阶段的对话与沟通,也被看作一种共同学习的过程,当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非政府部门或私营部门就潜在协作项目进行一种平等的讨论,各方畅所欲言,就会形成新的知识,促进共同理解,使参与者形成共同的理念与秩序,从而形成一种集体认知。
我国都市圈地方政府之间的高层行政首长双边互访和多边协商以及各类研讨会、交流会、论坛等,都属于这一对话与沟通阶段。通过地方政府领导带队的各种学习、交流和访问活动,加之现今各个都市圈组织的论坛和研讨会等活动,都市圈各个利益主体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不断加深了解,对于拟合作项目有了初步的认知,初始的信任阶段就建立起来了。
(二)签署契约阶段:调和矛盾与冲突
经历了试探性的对话与沟通阶段,都市圈各个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或私营部门之间可以依据法律准则,共同签署合作契约。契约或合同在公共部门比在私人部门更为常见,因此,大量的交易行为从原来的(信任的)合作者中产生[9]。签署契约阶段是构建整体性协作治理信任机制的更高一层阶段。当然,契约的达成要经历各方深入谈判,探讨如何考虑所有相关方的利益,如何调和彼此的利益冲突和目标冲突。深入谈判时,利益主体是通过讨价还价、推销、协商等方式来进行而不是发布信息或仅仅听行政命令的方式。此外,契约的达成还有赖于都市圈内各利益主体具备契约内容履行和承担方面的基本能力。因此,协作契约的签订,关键取决于合作各方谈判和关键问题的探讨过程,而这一过程又取决于各方能否努力寻找到对不同意见的创造性的解决方案[10]。
签署契约阶段是都市圈内各级和不同地方政府之间寻求良好治理方式的协商阶段。例如,美国肯塔基州的路易维尔市(Louisville)就与其所在地的杰弗逊郡(Jefferson County)签署了多边联合治理协议。在合作治理协议中规定,路易维尔市和杰斐逊郡政府共享本区域的个人及企业所得税,并划分了共享份额,其中路易威尔市政府享有58.7%的税收额度,杰斐逊郡享有41.3%的份额。协议还具体划分了两个政府的合作细则,路易维尔市政府主要负责该区域博物馆、图书馆和动物园的管理,以及城市公共危机管理,杰斐逊郡政府主要负责区域范围内的公共安全、环境保护和土地规划等事务的管理[11]。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合作的还有美国的匹兹堡市(Pittsburgh)和加拿大的汉诺威(Hanover)。这种地方政府间以合约的形式所签订的协议,较好地处理了合作双方的利益,如税收共享,并明确了双方承担的责任,如公共服务合作,从而能够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多方面实现合作。
在我国,随着都市圈合作的深入,也正在从信任的谨慎试探阶段向契约签署阶段转化。地方政府间从单纯的互访交流向签订合作协议的阶段迈进。如前文提到的,近几年来,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等都市圈签署了大量的,涵盖区域经济、文化、旅游、人才、环境等各方面的合作协议。这些签署的协议,就是保证都市圈地方政府合作的契约,为都市圈地方政府整体性协作治理的推进奠定了基础。在具体方式上,我国都市圈地方政府推行了共建产业园区、建立跨区域产学研平台、构建管委会+投资公司模式、推动“飞地”经济合作模式等都属于这一信任阶段的活动。
(三)友好善意阶段:促进共同理解和信任。
区域内地方政府间建立共同的信任是需要时间的,友好善意阶段是高级的信任阶段。这一过程超越了契约签署阶段对契约条款的依赖,都市圈各个利益主体会深入理解区域内各个成员的优势、劣势,以及他们在合作关系中想要得到什么,会主动理解其他成员所关心的问题和愿望,并认真考虑或接受他们的观点。此外,区域内各个地方政府对跨界合作的内部和外部的意义,以及合作所产生的变化对其他组织的影响都有着深入的理解。这种信任关系体现在区域合作中,区域成员之间会有着互相理解互相谦让的行为,能够更好的实现都市圈整体利益。因而,协作行为中的信任意味着一种义务和预期。合作中各方都不对另一方的利益造成不必要的损害,不背叛目的,对合作者要尊重和公平,合作各方都知道如何得到、在哪里得到所需资源[12]。“这种信任义务对协作链条的统合非常重要,它不仅关注边界内的具体的、可测量的交易,也关注边界外的具体交易。”[13]
例如,地方政府合作模式中的“城市社区”(urban community)就属于这种较高层次的信任阶段。城市社区就是都市圈内各个地方政府在保持各自独立性的同时,集合起来成为一个城市社区进行合作的模式。由各个地方政府官员组成的大都市区议会负责管理地区间议题,并且从各个地方政府征收共同税来贯彻整个城市社区的广泛的目标。这种合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各方深入的理解和信任,以及人口结构、社会和经济支柱。法国的里昂市和马赛市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城市社区,城市社区的形成大大降低了“外溢性”,各个地方政府成功地分享了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和公共文化、体育中心等设施。在马赛市,通过城市社区模式征收了大量共同税,加大了对中心商业区、海滨区、铺设轻轨铁路、发展公共交通等的投资,以此来促进马赛市的重建[14]。
在我国当前的都市圈地方政府合作中,友好善意阶段的信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真正达到促进共同理解与信任的都市圈的合作还没有实现。但是区域地方政府间的对口支援方式可以看作是这一信任阶段的雏形。对口支援是我国特有的区域合作方式,一般是经济发达地区对于边疆地区、灾害损失严重地区或者重大工程对口地区的支援。虽然对口支援这种合作方式基于共同的理解和信任,但这种合作是在中央政府主导下促成的,因而不是各个地方政府主动达成的。另外,对口支援的临时性、任务性等特点也阻碍了合作的进一步推进。
二、地方政府协作治理的利益分配与补偿机制
都市圈公共问题的外部性是推动区域内各地方政府达成合作,实现区域共同目标的重要力量[15]。一般来说,协作的潜在收益较高,而区域主体协商、监管和执行政治契约的交易成本又较低时,往往能够达成区域合作[16]。在都市圈地方政府合作过程中和合作后,尤其是生态和环境方面的合作,都会出现合作成员间的利益不均衡状态。因而,利益的分配与补偿是都市圈地方政府合作的重要方面。基于上述协作治理信任机制所构建的伙伴关系,都市圈利益分配机制强调区域内地方政府之间实现利益的分享,规范各主体的利益表达与分配行为,防止利益分配不公。都市圈利益协调与补偿机制的构建主要针对与生态环境相关的流域治理和大气污染治理等方面的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分配与补偿。另外,有关区域产业利益的补偿可以通过中央政府的财政补贴和税收返还等形式对地方政府进行补偿,从而使地方利益的分配达到比较公平的状态[17]。
具体来说,都市圈利益协调与补偿机制,尤其是有关生态和环境方面的利益协调与补偿机制,是由一系列的政策工具组成的。托马斯•思德纳(Thomas Sterner)认为,环境与自然资源管理的政策工具包括了四大类:利用市场、创建市场、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其中,“利用市场”工具包括了:补贴削减,针对排污、投入和产出的环境税费,使用者收费(税或费),执行债券,押金-退款制度,有指标的补贴,退还的排污费和信贷津贴;第二类工具“创建市场”包括:创建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私有产权和地方分权,可交易许可证和权利(如排污许可证与开采许可证),国际补偿机制;第三类工具“环境规制”包括了:标准,禁令,(不可交易的)许可证或配额,与一种活动(如分区规划)的时空扩展有关的规制,以及执照与责任(如责任债券、执行债券、执行保险金和赔偿金);第四类工具“公众参与”包括信息公开,加贴标签和社区参与等[18]102-105。国外对于生态补偿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生态服务购买来实现。生态服务购买分为政府购买方式和私人交易方式。政府购买方式是政府直接投资和提供项目基金的补偿方式。政府购买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征收生态或环境税费,如德国、瑞典、荷兰等国家都设置了垃圾填埋、碳排放、硫磺排放等税种。美国的大部分环境税也都用来支付指定的环境项目,如美国超级基金(Superfund)、美国溢油责任信托基金(Oil Spill Liability Trust Fund,OSLTF)和其他基金[18]151。再如,纽约市就向其水源地特拉华流域的农民提供生态补偿。由纽约市提供资金用于上游农民控制农场污染物生成,控制污染的技术咨询、设施购置、控制管理等所产生的费用都由纽约市承担,并且向特拉华流域两岸退耕的农民提供补偿,帮助农民在保证水源清洁的基础上开发其他能够获取效益的产品[19]178。
目前,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的方式主要依赖于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和上、下游政府间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因此,利益补偿方式比较单一,还需要探索多种补偿方式共同组成都市圈地方政府整体性协作治理的利益协调与补偿机制。具体来说,我国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推进利益协调与补偿机制的建立。
(一)纵向财政转移支付机制
纵向财政转移支付机制是中央政府的直接支付机制,也包括上一级政府对区域内地方政府的纵向转移支付。在我国公共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方面,中央政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央政府直接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一直是一种最为主要的补偿方式。作为区域的共同上级政府,中央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启动了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工程、生态公益林保护、重点地区湿地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三江与长江上游防护林工程等大型生态补偿项目,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灾后重建、整治江湖、兴修水利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对区域生态环境进行国家补偿。这种转移支付的特征是由中央政府提供专项基金,富裕的省区进行一定的补贴[20]。纵向财政转移支付还包括区域内作为上级政府的省、市政府对其辖区内为生态环境保护做出贡献的下级政府和当地的居民的转移支付。这种地方的纵向转移支付主要依赖于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21]。我国的广东省、浙江省和福建省等经济发达地区的省份就对本地区的地方政府进行生态补偿。如1999年和2001年,广东省和福建省先后在省内实施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这种纵向的地方财政转移支付还难以实现[19]163。
(二)横向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
横向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主要是指流域上、下游政府之间的生态补偿机制。上游政府如果为环境保护做出了牺牲,那么享受清洁水资源的下游地方政府就应当给予上游政府一定的补偿;如果上游地方政府由于工业发展导致了河流污染,给下游地方政府带来了损害,那么上游地方政府就需要对下游地方政府进行赔偿。从理论上来说,这一补偿机制是最为基本的一种生态补偿机制,但在实践中,由于上下游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困难,这种横向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还需要中央政府或双方共同上一级政府的协调才能实现。当然,我国有些地方也已经开始尝试这种补偿机制,这些地区大多是下游富裕地区对上游水源区或库区的补偿,像北京密云水库、东江源区、千岛湖流域、珠江流域、金磐扶贫开发区“异地开发”等。这种横向补偿机制的资金来自于省、市或县级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或补贴[20]。例如,北京市对于河北省承德市、张家口两市的生态补偿。位于北京密云水库上游潮河发源地的承德市和张家口市为了保证首都用水的清洁,关停了大量重污染企业,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水土保持和生态治理,这些措施限制了两市的经济发展并给两市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为此,2007年北京市拨出部分资金支持河北省的怀来、赤城等县市进行生态保护,并给予“稻改旱”农民以补偿[19]164。
(三)私人交易和市场贸易机制
虽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支付方式在我国都市圈利益补偿机制中占主导作用,但并不妨碍市场机制在利益补偿中的作用,利益补偿的实现形式也可以通过私人交易和市场贸易这样的市场机制来实现,从而更多地发挥市场的力量。私人交易和市场贸易就是市场机制的具体体现。私人交易是生态服务受益方和支付方之间的直接交易。通常适用于交易对象较少,产权明晰的情况,通过谈判或中介确定明确的价格[22]。如哥斯达黎加水电公司对上游植树造林的资助和澳大利亚马奎瑞河“灌溉者支付流域上游造林协议”等[19]176。与私人交易方式不同,市场贸易机制适用于生态服务市场中买方和卖方数量较多或不确定,并且可供交易的生态服务也是可量化的、可分割的商品形式的情况[22]。市场贸易机制的建立是基于科斯定理,认为生态治理中的外部性问题可以通过减少交易成本,进行明晰的产权分配等方面来解决。因而,市场贸易机制的建立需要创建有关自然资源的私有产权,区域资源与环境管理中的特殊产权就是排污许可证和开采许可证[18]。因而,构建自然资源的区域产权市场,实现水资源等的优化配置是十分必要的。美国的排污权交易(许可证交易)是较为典型的案例。为了减少美国流域的水污染,由政府部门根据历史资料向排污者发行数量有限的排污许可证,或者通过拍卖的方式将许可证出售给最高竞价人。每一张许可证上标明在特定时期内其所有人可排放的单位污染物,许可证可在排污厂商之间交易,如果厂商自己的排污水平低于规定的排放水平,那么就可将剩余的许可证出售给其他厂商或者用来抵消本厂其他设施的过度排放[23]。
在我国,也出现了一些类似的市场交易机制,如东阳、义乌水权交易,黑河流域水权证,宁蒙“投资节水、转换水权”等等。其中,2000年浙江义乌与东阳的水权交易是我国首例跨城市水权永久转让交易。双方规定,义乌市一次性出资2亿元购买东阳市横棉水库每年4999.9万立方米水的使用权,水库所有权仍归东阳市所有[24]。这种交易方式的实现需要对各行政区的水权进行初次分配,由地方政府或水务公司作为水权的代表者,有偿转让水权,通过市场机制使流域上下游地方政府之间的用水得到约束和优化[25]。
(四)公众参与机制与生态标记
都市圈地方政府之间的生态补偿还可以通过生态标记等公众间接支付生态服务价值的方式来实现。也就是说,如果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商品时,愿意以较高价格购买经过认证是以生态友好方式生产出来的商品,那么公众实际上支付了附加在该商品生产上的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在这方面,欧盟的生态标签体系推行的较为成功,从1992年推行这一体系以来,鼓励企业从产品设计、生产、销售到使用环节都遵循节能减排的生态保护标准,并在消费者中宣传这种“绿色产品”,使得消费者逐渐认同贴有生态标签的产品[22]。像瑞典的“环境选择”计划、德国的“蓝色天使”计划、加拿大的“环境选择”、美国的“绿色印章”、日本的“生态标记”等都是生态标记方式的体现[18]191。
目前,我国的生态标记产品的消费市场正逐步形成,公众对于绿色标识的生态产品的认知也在不断加深,只要价格体系得当,公众愿意购买生态标记的产品。因此,一方面要鼓励接受生态补偿的地方政府进行生态标记产品的生产,另一方面要建立区域的绿色消费体系,鼓励地方政府进行绿色采购,从而达到生态补偿的目的[22]。
(五)非政府组织参与机制
很多区域公共物品都有“外部效应”,也都会面临“搭便车”和“公用地悲剧”问题,因此,在都市圈地方政府有关公共事务的协作治理中,还需要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利益分配与补偿中规定不足。非政府组织参与机制是指在区域利益补偿中,由非政府组织作为补偿主体,为区域生态补偿中的流域上游或水源地等的政府或民众提供资金或其他补偿形式。非政府组织参与都市圈利益分配与补偿项目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国内外基金会的资金投入,各类大学或研究机构对于补偿标准的评估等。像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多瑙河的生态补偿项目、在我国的洞庭湖退田还湖项目都是通过捐助方式购买当地生物多样性或湿地环境,以起到生态保护的目的,并且不需要偿还资金[19]173-177。在这一过程中,非政府组织与当地政府、私人企业、研究机构、当地民众进行广泛的合作,帮助当地民众解决了生计问题的同时,也实现了对于生态资源的保护。由于我国非政府组织总体上呈现发展缓慢的局面,因而非政府组织和民众对于生态补偿机制的参与是非常微弱的。
除了以上五种方式,地区间的产业转移和扶贫开发政策也不失为区域生态补偿的一种方式。由于水源地或流域上游通常是经济落后地区,我国不少发达地区通过产业转移政策,把某些产业转移到被补偿地区,以带动当地工业发展,对被补偿地区失去的发展机会成本进行补偿[19]189。当然,对贫困地区的产业转移也可能伴随污染企业的转移,加剧上游地区的环境保护难度。因此,这种形式的补偿一定要确保经济落后地区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推进产业转移。
三、地方政府协作治理的监督和评估机制
构建都市圈整体性协作治理的监督和评估机制是实现都市圈整体性治理的重要环节。除了依赖区域合作成员间的横向监督和评估,这一机制的实现还主要依赖于纵向的科层权威(上一级政府)或区域合作组织对都市圈治理网络的适度干预。正如弗利兹•沙泼弗(Fritz Scharpf)曾指出的,区域合作治理发生在“科层制的投影之下”[26]。在都市圈整体性协作治理中,包含两个维度的监督和评估机制:
(一)横向监督和评估机制
都市圈整体性协作治理的监督和评估机制的建立,一方面需要加强横向的区域内各个地方政府之间对协作事项的监督和评估,另一方面,还要加强都市圈地方政府与参与到合作协议中的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监督和评估,强化彼此间的双向监督。具体来说,横向的监督和评估机制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都市圈地方政府对区域公共事务合作协议的执行进行监督。这种监督主要是明确区域各方所签订合作协议的监督主体、监督责任和监督方式的规定,并加强合作协议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的监督和评估。在都市圈地方政府签订了有关人才、产业、交通、环保等方面的合作协议后,都要进行协议执行的评估,并把评估的结果给各方进行反馈。都市圈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信息共享机制,及时地把合作协议的执行情况通报给合作方,从而保障各个地方政府能够对合作协议的执行进行追踪和调整。
其次,都市圈地方政府可以就大气污染、流域治理等生态环境治理建立联合监测和监察机制。近年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的水污染和大气污染事件频发,各个都市圈地方政府也开始建立相应的联合监测和监察机制应对区域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生态环境联合监测机制是由都市圈内各个地方政府对于跨域环境问题展开的政府合作与监督。一般由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部门共同制定区域水质和大气监测方案、监察点位、监测频次、监测指标,并报上级环保部门备案。在这一过程,可以构建都市圈环境监测网络,推进区域大气、土壤、水环境等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区域监测数据库等的建设,共同发布区域大气或水环境监测报告。环境联合监察是都市圈地方政府对跨行政区环境违法行为展开的联合执法,如对跨界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和区域重点污染企业的排查,或者是地方政府对于相邻敏感区域的重点污染源进行交叉执法,以督促区域环境问题的解决[27]。
(二)纵向监督和评估机制
上一级政府或跨区域整体性合作组织在都市圈整体性协作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区域的上一级政府为都市圈设置了协作目标,进行政策引导,并会评估和审查区域合作工作的成效。尤其在区域公共问题的利益协调和补偿过程中,通过拨款和专项治理基金的设立,与跨区域整体性合作组织一起,对都市圈地方政府的协作成效进行有效监督。例如,对于环京津贫困带地区扶贫专项资金的拨款过程中,上级国家机关如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地区经济司和国务院扶贫办公室都可以作为京津冀都市圈地方政府协作的监督方,对于随意挪用、滥用扶贫资金和“三农”专项资金做法予以监督,使得专款专用,从而保障各个行政主体的利益,同时提升区域的整体利益[28]。另外,上一级政府和跨区域整体性合作组织通过收集与传播合作各方的信息,可以实现良性沟通,从而加强区域各个地方政府、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间的信任关系,有助于合作目标的达成,并最终提升实现区域合作的整体绩效。
其次,纵向监督和评估机制要与地方官员的晋升和激励机制结合。都市圈地方官员围绕GDP增长而进行的晋升锦标赛是造成区域生态治理中地方政府合作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29]。因而,必须建立差异化官员考核评价体系,不以经济增长率来评定政绩,将生态环境、经济发展质量等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形成新的指标评价体系,规范地方官员的行为趋向,形成新的官员晋升和激励机制,这将有助于推进都市圈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分配,并推动他们之间的协作达成。在这方面,我国许多省份已经开始探索新的评价指标体系,如浙江、四川、内蒙古自治区开始试点环境保护指标作为晋升和激励的“硬指标”,北京市也在2014年《中共北京市委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提出,落实对本地区领导干部的自然资产离任审计,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不以地方GDP增长率来评定政绩,引导区县政府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区县功能定位、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上来[30]。我国各个都市圈的不同地方政府如果能够注重各自产业机构的优化,按照各自的优势资源和特点发展产业,如水源和生态保护地可发展生态经济和可循环经济,中心城市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等,那么产业同构现象就可以得到解决,地方政府之间单互补性增强,那么都市圈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效力就会提升。
最后,纵向的监督和评估机制还要配套必要的约束和惩罚机制,这一机制是实现都市圈共同协作目标的有力保证。约束和惩罚机制需要通过都市圈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协议来体现,协议中明确各方在协作中的责任和义务,以及违反规定后应承担的相应责任和违反合作协议所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以惩罚性的制度约束来使违规者付出成本。如果都市圈的某些地方政府不执行或消极执行区域合作协议,那么就需要对他们进行处罚,处罚形式可以是罚金或者减少合作基金的措施,甚至可以取消他们参与都市圈整体性合作组织的成员资格。
(三)第三方机构的监督和评估机制
都市圈整体性协作治理的监督和评估机制还包括了第三方,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公众,对于区域事务协作治理的监督和评估。通过引入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对地方政府的合作行为产生有效约束和控制。在监督方面,加强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对与其合作的地方政府的监督和评估,同时也要加强公众对于区域公共事务合作事项的监督。例如,有的学者建议,应在长三角地区建立长三角社会突发事件治理的信息公开和督办机制,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定期地、规范地、无保留地、详尽地将本区域的经济政策信息发布出来,接受公众监督、查询、了解、分析和评价[31]。另外,在评估方面,企业或者民间“智库”可以发挥他们的咨询与顾问作用,为区域合作提供诸如生态价值评估等方面的技术支持,以促进地方政府与半官方机构、行业协会、学术团体等之间的交流,从而形成多领域、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合作机制。
四、结语
构建都市圈不同利益主体的信任和沟通机制、利益分配与补偿机制、监督和评估机制等协作治理机制是实现都市圈整体性协作治理的关键。信任机制是整体性协作网络的运作基础,信任与沟通机制的建立需要经历谨慎试探阶段的对话与沟通渠道的建立,签署契约阶段的矛盾与冲突的调和,以及友好善意阶段的促进共同理解和信任等三个阶段。在我国当前的都市圈地方政府合作中,友好善意阶段的信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真正达到促进共同理解与信任的都市圈的合作还没有实现。
在都市圈地方政府合作过程中和合作后,尤其是生态和环境方面的合作,都会出现合作成员间的利益不均衡状态。因而,利益的分配与补偿是都市圈地方政府合作的重要方面。利益的分配与补偿机制就是要充分考虑各主体的利益诉求,规范各主体的利益表达与分配行为,对有些地方政府进行补偿,从而使地方利益的分配达到比较公平的状态。利益分配与补偿机制的构建首先需要发挥中央政府和区域上级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作用,并在中央政府的督导下积极制定相关区域协作事务的法律法规。通过纵向财政转移支付机制、横向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私人交易和市场贸易机制、公众参与机制与生态标记、非政府组织参与等机制,保障都市圈地方政府合作顺利、有序的进行。都市圈的监督和评估机制需要由都市圈地方政府间的横向监督和评估机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纵向监督和评估机制、第三方机构的监督和评估机制来组成,使得都市圈的各个行动者的协作行为都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和监督。
[1] SAVITCH H V, VOGEL R K. Introduction: Paths to new regionalism[J]. State & Local Government Review, 2000,32(3): 158-168.
[2] 刘君德. 中国转型期“行政区经济”现象透视—兼论中国特色人文-经济地理学的发展[J]. 经济地理, 2006, 26(6):897-901.
[3] PERRI 6, LEAT D, SELTZER K, et al. Towards holistic governance: The new reform agenda[M]. United Kingdom:Palgrave Macmillan, 2002.
[4] PUTNAM R D. What makes democracy work[J].National Civic Review, 1993, 82(2): 101-107.
[5] 罗伯特•D•帕特南. 使民主运转起来[M]. 王列, 赖海榕,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6]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 481-510.
[7] FUKUYAMA F.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creation of prosperity[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8] 罗伯特•阿格拉诺夫, 迈克尔•麦奎尔. 协作性公共管理: 地方政府新战略[M]. 李玲玲,鄞益奋,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78.
[9] UZZI B. 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embeddedness for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organization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6, 61(4): 674-698.
[10] INNES J, BOOHER D. Consensus building and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collaborative planning[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00, 65(4): 412.
[11] SAVITCH H V, VOGEL R K, LIN Y. Louisville transformed: A survey o f a city before and after merger[M].New York: M. E. Sharpe, 2009: 164-184.
[12] FERGUSON R F, STOUTLAND S E. Reconcieving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field[M]. 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9.
[13] BARBER B. The logic and limits of trust[M].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3.
[14] SAVITCH H V. Territory and power: Rescaling for a global era[C].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Guangzhou: Sun Yat-sen University, 2011.
[15] FEIOCK R C. Metropolitan governance: Conflict,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M]. Washington 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4: 7.
[16] HECKATHORN D D, MASER S M. Bargaining and the sources of transaction costs: The case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J].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Organization, 1987,3(1): 69-98.
[17] 马海龙. 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利益协调机制构建[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13(3): 90-96.
[18] 托马斯•思德纳. 环境与自然资源管理的政策工具[M]. 张蔚文, 黄祖辉,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19] 陈瑞莲, 任敏. 中国流域治理研究报告[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20] 郑海霞, 涂勤. 中国流域生态环境服务补偿案例进展[C]. 第四届中国农业现代化国际研讨会暨第8届欧洲中国农业农村发展论坛论文集, 2010: 470-485.
[21] 窦玉珍, 冯琳. 美洲地区生态效益补偿比较研究[C].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学术年会优秀论文集, 2006.
[22] 高彤, 杨姝影. 国际生态补偿政策对中国的借鉴意义[J]. 环境保护, 2006(19): 71-76.
[23] 保罗•R. 伯特尼, 罗伯特•N. 史蒂文斯. 环境保护的公共政策[M]. 穆贤清, 方志伟,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4.
[24] 李曦, 刘梅. 中国水权交易的探索与实践[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25] 陈瑞莲, 胡熠. 我国流域区际生态补偿:依据、模式与机制[J]. 学术研究, 2005(9): 71-74.
[26] SCHARPF F W. Games real actors play: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ordination in embedded negotiations[J].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1994(6): 27-53.
[27] 王玉明. 珠三角城市间环境合作治理机制的构建[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2011, 23(3): 62-68.
[28] 赵华颖. 环京津贫困带治理中的地方政府横向府际合作机制构建研究[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12.
[29] 崔晶. 都市圈地方政府协作治理[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64-66.
[30] 文静, 赵鹏, 王硕. 北京将不以GDP评区县政绩,引导区县转方式调结构[N]. 京华时报, 2014-01-14.
[31] 赵定东. 长三角区域性社会突发事件治理中的地方政府协作机制分析[J]. 辽东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11(5): 19-26.
Study on Mechanisms and the Network Mode of Holistic Collaboration Governance in Metropolitan Area
CUI Jing ZHENG Ge-xi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governance issues of metropolitan area are increasingly given atten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mechanisms of holistic collaboration governance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in metropolitan area, such as trust and communication, interest distribution and compensation, and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Based on these mechanisms, this article will study the network mode of holistic collaboration governance that consist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 NGOs and private sectors for providing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attain long-term and stable cooperat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in metropolitan area.
holistic governance;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metropolitan area; local government
D035
A
10.14071/j.1008-8105(2017)04-0015-08
编 辑 张莉
2017 - 03 - 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环境协作治理中的府际关系及政府与民众关系研究”(17BGL164);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区域协同视角下的京津冀都市圈地方政府大气污染协作治理研究”(14JGB07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崔 晶(1975- )女,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郑戈溪(1990- )女,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