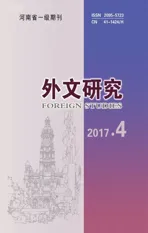论麦卡勒斯《金色眼睛的映像》中的“畸人”形象
2017-03-12浙江大学王晓雄
浙江大学 王晓雄
美国南方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的第二部小说《金色眼睛的映像》(以下简称《金》)于1941年出版单行本。当时的人们并不能理解这样一个奇谲、压抑的故事(Hendrick 1968: 390),甚至还出现了恐慌。有人给卡森打来威胁电话,原因是卡森在其第一部小说《心是孤独的猎手》中流露出对黑人的同情,而这部《金》又表明了她是个酷儿(卡尔 2006: 136)。显然,该威胁者发现了卡森作品的自传色彩。相较于其他作品中直接出现的女孩形象*卡森小说中的女孩形象,例如《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米克,《婚礼的成员》中的弗兰奇以及《神童》中的小女孩都被塑造得很中性化,疏离于人且热爱音乐,基本可看作卡森青少年时形象的写照。,《金》的自传色彩并不那么明显,但是小说深刻地展现了卡森对于性别问题的关注,其中人物在性别上表现出的与周遭环境的格格不入,正是卡森自我形象的一种投射。而这种格格不入也许就是评论者们念兹在兹的“怪诞”*论者们分析卡森小说“怪诞”的表现方式,借用巴赫金的怪诞理论和麦卡勒斯自己的定义,并把她放置在南方作家群中进行讨论。伊哈布·哈桑在《麦卡勒斯:爱的炼金术与疼痛美学》一文中首次将麦卡勒斯对“怪诞”的哥特式表现手法放在南方文学传统的背景中讨论。萨拉在《再探南方怪诞:巴赫金和麦卡勒斯的个例》中认为,南方怪诞或哥特小说表现为在封闭空间中塑造畸人形象,并在无爱的环境中施展暴力、激情和反常的性,多数论者认为怪诞小说以寓言的方式展示了生命的极度痛苦。另:本文“畸人”的说法源于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作品Winesburg, Ohio,国内译为《小城畸人》,“畸人”原文为grotesque,故此处讨论的“畸人”与“怪诞”同义。(林斌 2005: 160; Gleeson-White 2009: 57),这一风格在《金》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相较卡森其他作品,论者对《金》的关注更少,相关论述也都抓住其怪诞风格,从各角度切入*论者分别从酷儿理论、精神分析、生态伦理等角度入手,分析小说怪诞人物的成因和给予读者的启示。(Adams 1999; Austen 1974; 岳继洋 2009; 张长辉 2012),更多将目光聚焦于人物的反常,而似乎不太关注人物的心理和行为变化过程。萨拉指出,卡森笔下畸人形象皆是“可产性”(productive)(Gleeson-White 2003: 38)的。本文受此启发,拟以《金》中艾莉森和潘德腾两个人物为例,结合人物心理变化机制来阐释卡森“畸人”的“可产性”,探究其在性别身份问题上的个人体悟和时代关怀。
一、畸人的双重性和未完成性
上文提到,萨拉将卡森笔下畸人形象概括为“可产性”的,其实是在强调畸人形象的不确定性,可导向多种可能。卡森本人对此种不确定性有着相当的关注,其中既有对暧昧身份的怀疑和焦虑,又有对获得多种可能性的希望。
卡森曾写过一组诗,名为《双重天使:关于起源和抉择的冥想》,其中最后一首为《父,我们生命的广度培养在您的形象上》,现试译如下:
我们为何分裂于双重天性,如何被设计成这个模样。
父啊,我们生命的广度建立在何种形象上?
放逐者的子孙,在是与非的花园里,
受到善与恶可逆的嘲笑,
无助地转向。路西法,你的宇宙之子的兄弟,
你的化合刚刚开始,
你就说它已经结束,
我们饱受分离与分裂之苦。
心中却闪耀着基督的幻象,
尽管我们先天就被扭曲,双重地构建。
父啊,我们生命的广度就建立在您的意象上。
(McCullers 2001: 292)
诗中,卡森举出的“对与错”“善与恶”都是截然的二元对立,我们,匍匐于天父脚下的子民们,忍受着这两者的分裂,可是却又在不断地“转变”。卡森下笔之时,应该是窥见了人之为人的双重混乱,她所创造的人物也不自觉地“先天就被扭曲,双重地构建”,只是这上帝的合法化还未完成,我们还须努力应付身体的芜乱,等待最后的构建完成。卡森自己所说的双重构建正是萨拉指出的“并置性和未完成性”(Gleeson-White 2003: 7),也恰与巴赫金的怪诞现实主义理论相合。巴赫金与卡森一样重视双重性,他批评施涅冈斯在评论拉伯雷的时候,根本无视这样一个基础。他认为,解决拉伯雷的世界质的多样性、形象以及关联的丰富性,就必须了解“客体不但可以超越其数量界限,而且可以超越其质量界限;可以超越自身而与其他客体混合”(巴赫金 1998: 357)。“能再生、二体合一的怪诞形象”(Gleeson-White 2003: 6),这是处于文学艺术静态世界的施涅冈斯所无法理解的。巴赫金强调的也是正反同体性和未完成性,拉伯雷笔下各种怪诞人体和筵席形象,都处在不稳定的、变化的状态之中。事实上,巴赫金提出双重性的人体,是为了驳斥现代规范的人体。他认为现代人体是既成的、封闭的,切断了人与人、人与世界的联系,失去了本应有的世界观的功能。但需要指出的是,两者关键的区别在于,巴赫金提出双重性与未完成性是指向世界的,卡森的怪诞人体特征则一直指向个体的生存体验,因此卡森构建基于自我的言说就更令人动容。但两者对于怪诞人体状态的认识却是一致的,如同巴赫金对人体的动态解说——它“是形成中的人体。它永远都不会准备就绪,业已完结:它永远都处在构建中,形成中”(巴赫金 1998: 368)。
因此,落实到《金》中的人物艾莉森和潘德腾,一个是自主意识觉醒的南方女性,一个是恐慌于同性情欲的双性恋者,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双重构建的畸人。他们努力使自身合于环境的规约,但是内心的渴望又诱使他们逃脱规约的制控,在两极之间摇摆、挣扎,最终只能走向毁灭。
二、两性规范外的畸人形象
《金》中描述的世界是和平时期的哨所,卡森一再强调其乏味与单调。彼时卡森与丈夫移居费耶特维尔,一个极其闭塞保守的小镇,《金》中滞闷无趣,条规森严的军营正是小镇的映射。军营作为一个男性社交世界,在强调等级制度、拒绝躐等交往的同时,也强力维持美国南方的性别规范。总体来说,军营世界贬斥女性气质的出现,同时,它又要求作为附属的女性恪守女性规范,丝毫不能逾矩。
艾莉森与潘德腾正是试图逾越性别规范的特例。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组形象,利奥诺拉和兰顿少校,则是卡森刻意为之的规范形象。利奥诺拉是潘德腾上尉的妻子,卡森笔含微讽地描述她长相俊俏,“脸上带着圣母马利亚般的茫然的宁静”(麦卡勒斯 2007: 7)。她身体丰腴健康、充满活力,与病恹恹的艾莉森形成对照。利奥诺拉符合军营男人的所有审美,最重要的是,她有点弱智,但“这一悲哀的事实从未被人发现”(麦卡勒斯 2007: 18)。而兰顿则是男性气质的典范,他健壮孔武,不学无术,而胃口又奇好,这与艾莉森、潘德腾又形成鲜明对比。在此,食欲、健康、才识与性别规范微妙地联系一起,卡森以此全方位地展现畸人在规范世界里的怪异处境。
艾莉森和潘德腾体现的是畸人性别身份选择的双重性,当规范与自主意识出现碰撞时,是向性别规范寻求庇佑,还是奋力坚持自主意识,就成为他们难以抉择的问题。有论者指出,卡森人物的怪异体现在“对强加身份类别的反抗”(Adams 1999: 552)上,但艾莉森与潘德腾的自我诉求又时时陷入痛苦的压抑,面对性别规范的诱惑又时时犹疑。因此,两性间的畸人形象摇摆在规范与反抗之间,他们的彷徨、犹豫体现出卡森式怪诞的双重性和可产性。艾莉森和潘德腾的意识过程,可分为最初对女性气质的贬抑到自我怀疑,直至最终的明确自我追求,而一旦明确,便导向最后的毁灭。
如上所说,军营是一个男性社交场所,军阶、地位之外,最可标榜的就是个人的男性气质。塞吉维克(2011: 1)曾提出“同性社会性欲望”,用以定义“男性纽带的形成”,而列维·斯特劳斯将女性描述为男人之间的交换物,父权的社会组织形式即通过男人互相交换女性而平息竞争,形成同盟;而这种同盟的父权组织形式下,男性必然是被构建成异性恋的,因此自然而然地导致了“恐同”以及“厌女症”的心理,他们同时导向对女性和男性身上女性气质的厌恶(塞吉维克 2011: 3-5)。《金》中,军营里的人们对自我男性气质的维持和对女性气质的贬抑即可以此解释。而潘德腾在性方面“保持了男性与女性特质的平衡,他拥有两种性别的敏感,却缺少两种性别的活力”(麦卡勒斯 2007: 11),他从小跟着姨妈们长大,身上有着较浓的女性色彩。但一入军营,他自然而然地强调起男性气质,追求加官进爵,并娶了利奥诺拉这个肉感美丽的女人为妻。他殷切地遵循并捍卫男性性别规范,因此,有论者提出他在“身份监牢”中“同时扮演着看守和囚犯的双重角色”(林斌 2008: 99)是很形象的。潘德腾其后的转变正是一个身份的“越狱”过程。在卡森的小说中,女性气质总是与小动物意象缠绕一起。某晚,潘德腾“躁动不安,需要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发泄出来”(麦卡勒斯 2007: 12)。这种躁动一直伴随着潘德腾,可看作是长年压抑的同性情欲的躁动。他在路上发现一只猫,有着“柔软温存的小脸”,“温暖的毛”(塞吉维克 2007: 13)。他轻抚着小猫,犹如抚摸内心柔软的部分。但很快,他匆匆看下四周,把小猫丢进了结冰的信槽里。在此,小猫正是潘德腾女性成分的象征,他由起初的爱惜转为嫌恶地丢弃,正代表了他对于自我女性成分的态度。艾莉森在这个意义上与潘德腾同质,她因爱喂养流浪动物,以及为死鸟哭泣而遭到丈夫的嘲笑。她身边环绕着许多小动物意象,也是女性气质的集中体现,因此不被潘德腾待见。由此可见,同为压抑自我的畸人,两个人却仿若执仇,不禁令人深思。而潘德腾的妻子利奥诺拉,作为一个丰腴、强壮、充满活力的女人,她的存在似乎只为了证明潘德腾心理或者生理上的性无能,她的女性气质越强烈,就越衬出潘德腾男性气质的疲弱。因此,当利奥诺拉肆无忌惮地在房内裸身来去,潘德腾会愤怒地大喊:“我要杀了你!”对他人或自我女性气质的拒绝,是为了葆有自身的男性气质,说到底仍是父权对自身之外两性的制控。
另一个“畸人”是艾莉森,她也是越来越发现自我内心的渴望,但又囿于规范的森严,对自我产生怀疑和压抑。在小说构建中,卡森让这两人都在规范和越轨之间摇摆,竭力营造畸人形象的动态特征。
艾莉森是一个有思想的女性,她回想自己生命中最幸福的日子,是在寄宿学校教女孩子们诗歌的时候。那时她与许多流浪猫狗为伴,给它们喂食。猫狗意象再次出现,这被认为是女性化、病态的意象,却是与整个军营氛围格格不入的美好品格。艾莉森追求智识和艺术上平等的对话。她与小男仆间保持类似亲友与母子的关系,以及和中尉建立起纯洁友谊,他们交流音乐、舞蹈和文学,这样的小团体在军营人们看来极为古怪。艾莉森的追求显然对丈夫造成了极大压力。兰顿少校回到屋内,总是在桌上摊着一本深奥的文学书,然后从衣橱下面抽出一本低俗杂志,津津有味地看起来。兰顿无法喜欢他的妻子,他与整个南方的性别规范立场一致,女人应该如利奥诺拉一样肉感、美丽并愚蠢,因此,少校与利奥诺拉成为情人并不让人意外。艾莉森得知此事后极为痛苦,她原本对利奥诺拉不以为意。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肤浅的女人,却处处受男性的尊重和喜爱。艾莉森在女性规范前垂下头来,她的自我修持和智性追求被丈夫的出轨击得粉碎。她竟对丈夫的情人产生了奇特的友谊,同时她开始编织毛衣,这古希腊以降的女性职业行为,证明了艾莉森试图贴近女性规范的努力。此后,她在高烧中剪去了自己的女性器官,乳头,可见其对自我女性身份的迷惘,她实在不明白为何自我认知和规范之间会相差如此之远。自我认知追求的受挫,使得她拼命学习做一个规范女性,但是她已注定无法回归到那样一个“理想”的状态。
类似地,潘德腾是靠压抑同性欲望并寻找男性镜像来靠近男性规范的。小说讲到,潘德腾本性中有个可悲的缺陷,偷窃。他七岁时迷恋一个欺负过他的恶霸,于是从姨妈那儿偷来存发罐送给那个人。因此,潘德腾的偷窃行为是与同性欲望联系在一起的。波伏娃曾指出,盗窃罪是一种含糊的“性的升华”,“破坏法律和违反禁忌的意愿,被禁忌和冒险活动所引起的高度兴奋”(波伏娃 1998: 409)。这一行为体现了潘德腾亟待释放同性欲望的需求,但是他同时又畏惧这一需求可能引来的后果。因此,成人后,他在一个晚宴上偷了把甜点匙,一种和存发罐一样都是阴柔之物的东西,被艾莉森撞见。艾莉森朝他嘲弄地笑笑,示意二人的共谋关系。但潘德腾并不领情,他痛恨艾莉森身上的女性气质,也痛恨她窥见自己的隐私。他在营中大肆捏造传播艾莉森的流言,可证明他对自我性别越轨的遮瞒和回避,同时也说明同为弱势群体的反抗者们也很难互相携手,向规范的回归使得他们产生自我怀疑并互相指摘。
小说提到潘德腾先后迷恋上兰顿少校和士兵威廉姆斯。他这一个悲哀的癖好,恋慕自己妻子的情人,最初是为自身寻求男性镜像。小说暗示了潘德腾的性无能,他的微薄的男性气质在妻子的情人兰顿那里获得弥补,因此兰顿作为南方男性规范,是潘德腾第一个男性镜像。小说中潘德腾自认对威廉姆斯的迷恋和对兰顿的并不相同,但细究文本可知,他最初对威廉姆斯的感觉仍逃不脱男性同性社交的关系,有人将其爱慕解为“自私”(Presley 1972: 41)亦不无道理。潘德腾注意到威廉姆斯是因后者将咖啡倒在潘德腾身上。萨拉和罗杰·奥斯丁都发现这种男性间的冒犯与《水手比利巴德》中的相似处。在《水手比利巴德》中,比利将汤泼在纠察官身上,与威廉姆斯同出一辙,萨拉视之为“性交流的标志”(Gleeson-White 2003: 49)。在塞吉维克看来,此种类似于性的交流,是对被冒犯者男性气质的侵犯,潘德腾此后的种种行为都是维护自我男性气质的努力。他期待抓住威廉姆斯的把柄,如同纠察官时时找水手比利巴德的茬儿。直到后来,他还幻想和年轻士兵展开一场肉搏,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其间已经夹杂了潘德腾的爱恋之情。但男性化的搏斗话语,更多还是对自我的捍卫。威廉姆斯深具野性的原始男性气质,令潘德腾深深着迷,但他最初的着迷与对兰顿的镜像学习比较类似,当潘德腾让自身存在的女性气质缓缓流出之后,他对威廉姆斯的情感才悄悄发生改变。
艾莉森在最后的时间里,终于开始考虑与丈夫离婚的问题。她与丈夫的生活向来不合拍,起初她期待生养孩子,以母亲的身份巩固自己的女性身份,但以孩子的夭折告终。丈夫的出轨使她深深怀疑自我追求是否得当,于是她向利奥诺拉偏移,试图重建自我的标准女性身份。但她的智识和脾性根本不允许她这么做。她在有限的条件里,试图离开丈夫过上独立的生活。比如设想与小男仆一起,做一点生意或者买一条捕虾船。但是经济问题又使她只能求助于丈夫,她希望丈夫能借她点钱用以起家。因而,艾莉森的独立永远无法摆脱对丈夫的依附,卡森敏锐察觉到经济问题是很多要求独立的女性跨不过的坎。丈夫兰顿对此恐慌不已,赶紧把艾莉森送入疗养院。这是从一个规训空间(军营)进入到另一个规训空间,甚至更甚。在疗养院,畸人被赤裸裸地贴上疾病标签,是被完全控制的他者。兰顿满意于自己给妻子找了个费用如此昂贵的疗养院,但第二晚,艾莉森就心脏病发作死了。
相较而言,潘德腾的转变虽然也难免毁灭的结局,但有着更多的乐观因素。上文已论及,潘德腾对威廉姆斯的镜像迷恋在悄悄转变。兰顿曾与潘德腾有过一次交谈,他表示:“任何成功假如是以不合常态为代价,那就是错误的,因此也不应该带来幸福。简而言之,打个比方,与其去发现和使用适合圆孔的非常规的方桩,还不如勉强把方桩插进圆孔里,因为后者在道德上是可敬的”(麦卡勒斯 2007: 134)。也只有那一次潘德腾坚决表示反对,他向自己的灵魂深处看去,看见的是自己变形的影像。虽然他仍旧以规范的目光来审视自我,但这一次,他全盘接纳,并不试图改变。因此,有论者述说潘德腾的同性倾向是厌弃女性自我,追求男性自我的表现(林斌 2008: 99)恐怕不太确切。这充其量只是对“前期的潘德腾”的描述。因为潘德腾的以上说辞,就像是他的自我确认,他渐渐挣脱出军营世界的规约,导向对威廉姆斯自然的爱。他看着军营里群居的两千多人,听到里面传出的叫喊声和说话声,这种热闹场面使他想起自己的孤独,于是眼里涌出了泪水。在这一次经历中,潘德腾真正体验到自己所走道路的偏差以及心中的真正渴望。在被教导男性气质、默认异性恋模式的时候,梦想着加官进爵是潘德腾最大的追求,所以他常念叨“少将潘德腾”,期待尽快达成愿望。但经历并认识到自己可怜的孤独之后,他抛开了官阶梦想,甚至希望自己是“二等兵潘德腾”,这样他就能与威廉姆斯平起平坐,跨过等级的制约正常地交往。有论者提出,这种军官对士兵单向的爱恋在小说历史中屡见不鲜。并且,军官总是年纪大些,显得没有活力甚至怪异,而士兵总是年轻健康、英俊迷人,其实这其中“有一种含蓄的对等关系:性健康等于异性恋”(Austen 1974: 353)。如果说威廉姆斯是健康的异性恋的象征,那么反之,潘德腾则代表了双性情欲不堪规约重负的孱弱,以及公众印象中的古怪。潘德腾在幻想中,希望自己能恢复年轻和活力,如同威廉姆斯的一个孪生兄弟。这大概是非异性恋者的共同理想,要在公众的视线里洗刷各种偏见,和异性恋者一样不会引起额外的争论。此时的潘德腾已越来越认同自我的性别身份,和威廉姆斯的例行照面对他来说像幽会一样甜蜜,他陷入了爱情的狂想,原本呆板的人一时间变得天真、狂热、起伏不定,为之后的枪击做好了情绪准备。真正标志潘德腾认同自我的是他最后对军营的想象,“他在心里面看见了整洁的一排帆布行军床,光秃秃的地面,没挂窗帘的明晃晃的窗子”,这是“不加修饰,苦行僧式的”的房间,是干练的男性身份的象征。在这房间里,潘德腾还设想了一个“捆着铜丝的古色古香的雕花柜子”(麦卡勒斯 2007: 140),正与“不加修饰”的房间形成对比,是潘德腾置入其中的女性成分的象征。如此,潘德腾身上的两性气质谐和共存。因此,这个军营是他对同性情欲的最好设想,朴素简单,也是对怪异的刻板印象的反击。
但是潘德腾显然过分乐观了,他的单方面迷恋从来都没有得到过任何回应。当潘德腾撞破威廉姆斯偷窥自己妻子并将之射杀的时候,人们提出各种说法来解释,比如在“内心博弈中,他输给了自己的道德评判,自断了精神交流的路径”,因而“枪杀了暗恋着的情人,彻底将自我埋藏”(周琳 2010: 32),再如威廉姆斯的“越界行为激发了他的本能反应, 他当场亲手杀掉了士兵,以实际行动捍卫了‘身份监牢’”(林斌 2008: 99)。人们仿佛都倾向于认为潘德腾是出于维护军营秩序或是丈夫尊严才下了杀手。但是彼时,荣耀和官阶对潘德腾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军营秩序并不应该成为他射杀爱恋对象的原因;道德判断的束缚早在潘德腾自我觉醒之时便已瓦解;至于丈夫尊严,则更没有说服力,潘德腾的妻子之前就与兰顿有染,潘德腾心知肚明也不点破,反而奇异地迷恋上了兰顿,如今的威廉姆斯也是同理。其实,潘德腾在最后辨认出威廉姆斯的时候,他的心跳都快停止了,可以想象处于平日的爱情狂想之后,那时的他会如何期待威廉姆斯的到来。可是威廉姆斯是来偷窥他的妻子的,他的想象瞬时崩塌,他好不容易认同的性别身份,好不容易自我许可的同性迷恋,被威廉姆斯的性取向击得粉碎。潘德腾努力刻画的隐秘的同性爱情,仍然无法避免女性的染指,他的绝望和愤怒使得他扣下扳机。射杀威廉姆斯不仅是愤懑的宣泄,同时也断了潘德腾自己的去路,毕竟威廉姆斯是他爱慕的对象,因此他的举动有着自我毁灭的悲壮。虽说以毁灭作结,但潘德腾的愤怒愈盛,则愈表明他对自我身份认同的看重。
综上,作为卡森笔下的畸人形象,迷茫时期的艾莉森与潘德腾一样,双重性啃噬着他们的心灵。因其未完成性,他们身上体现着两极之间的力量对比,这种对比反映出性别规范的规训力量和畸人寻求抗争的意志之间的张力。他们身处两极之间,从向规范的学习,转为偏离规范,寻求自我的真正诉求,虽然都以毁灭作结,但却令人动容。
三、麦卡勒斯“畸人”形象之探源与发展
我们讨论卡森笔下“畸人”形象,不免往美国文学长河里寻觅血缘。詹姆斯·谢维尔在考察美国文学的畸人传统时列出了一串名字,从霍桑、麦尔维尔、爱伦坡、舍伍德·安德森直到福克纳(Schevill 2009: 3)。我们一般认为,是舍伍德·安德森是真正将畸人形象系统地推上文学舞台的,他的创作深深影响了美国南方文学的后起之秀,卡森作为其中之一也多少继承了安德森的衣钵。
安德森的《小城畸人》中有两个人物值得一提。一是小说开篇的作家,在他身上,我们奇异地发现了巴赫金所说的“能再生、二体合一的怪诞形象”(巴赫金 1998: 357),这是巴赫金所推崇的导向生生不息的理想人体。他的职业注定了他的能产性,他动用他的笔触赋予美丽的、有趣的、奇形怪状的畸人们以生命力。事实上,作家不仅是提纲挈领之人,他自身也是畸人。这畸人借巴赫金之语是“永远处于革新中的生命的穿堂院,是死亡和妊娠无穷无尽的容器”(巴赫金 1998: 369),因其独特的双重性获得了类似妊娠的能产性,得以繁衍生息,与自然宇宙接驳。二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记者乔治·威拉德,他的职业也表明了他可以较方便地出入他人的生活,因此在安德森的构思中,他成为了一根引线,穿过每一位畸人,串联出一幅小城畸人的群像。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安德森和卡森之间的隐隐呼应,作家的双重能产性人体在卡森那里得到回应。只不过在前者,是充满象征意味的诗意描述,在卡森这里,落实到了个体的生存状态,记者乔治的出走在卡森这里是畸人希求挣脱两性樊笼的美好愿望。安德森对畸人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解,他说一个人一旦努力按照“自己的真理”过活,就变成了畸人(安德森 1983: 3)。意即畸人们对自我真理坚持过笃,因而与周遭人群格格不入。至此,我们发现,畸人们其实并不“畸”,他们的征状来自他们对正常交际的畏惧以及有时在无趣的生活中寻找欢愉,所谓的“正常交际”是指与小镇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正常”人们打交道。但欧文·豪严厉地指出,那些正常人是“平庸乏味的人”,根本不能与畸人们相提并论(Howe 2009: 201)。因为畸人们心中尚存“真理”,尚存用以构建自我的独特的材质。到了卡森笔下,畸人们的个性更加丰满,原本单一的真理与现实的冲撞演变成了两极偏移的内在机制。卡森在继承安德森畸人形象的时候,开阔了畸人们的内宇宙,使他们更加富有动态的层次。
本文伊始,笔者曾言道,卡森的作品是有自传色彩的,因而她笔下的畸人形象的部分源头正是她自己。我们往美国文学史追溯的同时,不能忘却她投注于作品的个性元素。卡森自身对音乐、舞蹈、文学的热衷与艾莉森同出一辙,她从小与人群格格不入,被他人认为是怪异的,也与艾莉森处境相仿。如果说,艾莉森的塑造是回应卡森对女性身份的态度,那么潘德腾这一人物的出现则可算是卡森对自我双性欲望焦虑的纾解。卡森的双性恋倾向不是秘密,她爱过的女人和男人一样多,痴迷的程度也毫不逊色。她自己也不讳言,对自己的男性性格极为当真,甚至跟好友说,“我生来就是个男人”(卡尔 2006: 167)。在卡尔的传记里,我们能看到好多类似的自我表白,似乎卡森对自我身份是确证无疑的。但恐怕未必如此,有论者认为卡尔“并没有考虑到社会和政治压力及其造成的伤害,这种压力促成了卡森对于生活的抗争,以及其作品对人类情感的理解”(Stanley 1977: 312)。卡尔虽然也提及卡森的性取向,但并不太关心这事,有时还以之为情绪不稳的表现。事实上,卡森面临的世俗压力是巨大的,她与丈夫里夫斯都曾陷入双性欲望的纠缠,并因此带来互相的不满。直到50年代,诺曼·梅勒还曾写过:“如其他许多异性恋者一样,我当真认为同性恋和邪恶之间是有着内在联系的,这对我来说似乎极为自然”(Austen 1974: 353)。这看法代表了整个群体的立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即便是在卡森和里夫斯身上,我们也很难看到他们对于双性恋身份的强烈认同。因此,卡森在女性身份和性取向上都是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他者,早早尝尽边缘苦涩的她,将眼光投注于弱势群体也毫不为奇。早在《伤心咖啡馆之歌》发表时,有人指责卡森反犹太就令她委屈难过了很久,事实上卡森痛恶对任何少数人群的歧视,这种完全相反的误解尤其令她伤心。
詹姆斯·谢维尔曾探索美国畸人文学的发源,认为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工业时代机器技术压倒个人自主的胜利(Schevill 2009: 3)。事实上,人们常用来评论安德森诸如对农业文明的眷恋,对机器工业文明的贬斥等话语,已涉及到对现代性的反思。当然安德森究竟是觉察出了现代性进程的谬误,还是仅仅以遗老遗少的立场做一概的拒绝,恐怕很难考证,但他这种姿态延续到了卡森及其后来者身上。美国南方因为古老的农业结构,造成许多土地的毁弃,整个南方表现出经济落后、民众情感匮乏的情况。劳森指出,直到六七十年代,“南方仍保持了一种褊狭、守旧、闭塞的文化传统”(Presley 1972: 37),当这种传统与现代化进程交融时,出现了令人遗憾的局面。狭隘和充满偏见的旧传统和强调规整、非个性化的现代文明将畸人们逼到了孤独和隔离的墙角,两性规范的压制力在此尤为严苛。至卡森笔下人物的时代,现代规约和法令的罗网更是越织越密,而传统保守、充满偏见的民风乡俗似乎并未见好转,两性形象的刻板标准仍然落在狭隘的观念里。不过也正因此,那些他者形象在自我觉醒之时才会那样决绝。
应该说,卡森在继承美国畸人传统的同时,深切地融入了自身在性别身份上的挣扎和抗争,二战后彷徨、压抑、混乱的时代图景在她那里幻化成闭塞的军营(小镇),其间两性规范变成了沉重的镣铐,努力挣脱镣铐的弱势群体在卡森的注视下获得发声的权利。令人欣慰的是,畸人在冲撞过程中,表现出了坚强的韧性。卡森似乎在向我们暗示,对性别规范的超越永远是流动性、可产性的,对于自我性别身份的把握总可以在规范与规范迮狭的缝隙间,操演出一定的可能性。
Adams, R. 1999. “A mixture of delicious and freak”: The queer fiction of Carson McCullers [J].AmericanLiterature71 (3): 551-583.
Austen, R. 1974. But for fate and ban: Homosexual villains and victims in the military [J].CollegeEnglish36 (3): 352-359.
Gleeson-White, S. 2003.StrangeBodies:GenderandIdentityintheNovelsofCarsonMcCullers[M]. Tuscaloosa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Gleeson-White, S. 2009. Revisiting the southern grotesque: Mikhail Bakhtin and the case of Carson McCullers [C] // H. Bloom (ed.).Bloom’sModernCriticalViews:CarsonMcCullers. New York: Infobase Publishing. 57-72.
Hendrick, G. 1968. “Almost everyone wants to be the lover”: The fiction of Carson McCullers [J].BooksAbroad42 (3): 389-391.
Howe, I. 2009. The book of the grotesque [C] // H. Bloom (ed.).TheGrotesque. New York: Infobase Publishing. 199-207.
McCullers, C. 2001.TheMortgagedHeart[M]. New York: Mariner Books.
Presley, D. 1972. The moral function of distortion in Southern grotesque [J].SouthAtlanticBulletin37 (2): 37-46.
Schevill, J. 2009. Notes on the grotesque: Anderson, Brecht, and Williams [C] // H. Bloom (ed.).TheGrotesque. New York: Infobase Publishing. 1-11.
Stanley, J. P. 1977. Fact and interpretation: Reflections in a golden eye [J].PrairieSchooner51 (3): 312-313.
巴赫金. 1998. 巴赫金全集(第六卷) [M]. 钱中文等,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波伏娃. 1998. 第二性 [M]. 陶铁柱, 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弗吉尼亚·斯潘塞·卡尔. 2006. 孤独的猎手: 卡森·麦卡勒斯传 [M]. 冯晓明,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林 斌. 2005. 卡森·麦卡勒斯20世纪40年代小说研究述评 [J]. 外国文学研究 (2): 158-164.
林 斌. 2008. 权力关系的性别隐喻——麦卡勒斯《金色眼睛的映像》中哥特意象的后现代解读 [J]. 国外文学 (4): 96-104.
麦卡勒斯. 2007. 金色眼睛的映像 [M]. 陈黎,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舍伍德·安德森. 1983. 小城畸人 [M]. 吴岩,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 2011. 男人之间 [M]. 郭劼,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岳继洋. 2009.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解读《金色眼睛的映像》 [D]. 硕士学位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
张长辉. 2012. 人物·自然·异化——基于《金色眼睛的映像》的分析 [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 (3): 61-64.
周 琳. 2010. 论卡森·麦卡勒斯小说中的“孤独症” [D]. 硕士学位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