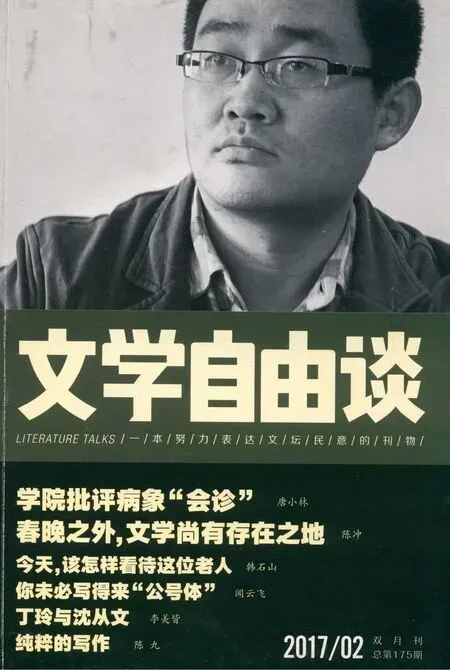经典作家的经验给我们的启示
2017-03-11邢小利
邢小利
经典作家的经验给我们的启示
邢小利
李建军的《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以下简称《并世双星》),内容厚重、广博,是对400年前中西方两位经典作家、伟大作家比较研究的力作,也是一部交响乐,关于历史,关于现实,关于文学、文化、文明的交响乐。书中对很多问题的阐述稳健而犀利,文采斐然,读起来让人有一种含英咀华的感觉。
对汤、莎进行比较研究,涉及东西方戏曲、戏剧、文学、思想、文化、时代背景、政治文明等很多方面,需要有“开阔的文化视野和成熟的人文精神”(梁实秋语)。《并世双星》视野宏阔,同时又能站在当今学术前沿,对相关问题既有宏观的总体把握,更能从细微处入手,进入艺术欣赏的境地。比如关于“活文学”与“死文学”之辩,关于“文学”与“纯文学”之辩,关于汤、莎的作品及其艺术性,李建军都能深入艺术的肌理分析,特别是像汉语之韵致这样一些有时只能体味其妙,而难以分析的问题进行深入地分析。所以,无论是谈思想还是分析艺术,这部著作都能深入其里并将其展开,没有那种凌空蹈虚的空话,没有不着边际的昏话。
李建军借汉诗《秋风辞》中的诗句“兰有秀兮菊有芳”来概括和评价东西方这两位巨擘,认为对他们强分轩轾没有意义。比较研究的意义,在于对他们所处时代的政治和文化环境进行分析,进而联系戏剧家个人的生存境遇和创作道路,比较他们在审美和伦理方面的异同,总结出他们艺术创作的伟大经验和这种经验资源对后世的启示意义。书中有对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两部爱情经典作品《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牡丹与玫瑰”的分析,也有对两位戏剧家艺术世界总体性的研究,有对比较研究中引出的相关问题的梳理,有对两位戏剧大师的接受史和研究史的再研究,进而理出一些有价值、有美学意义的命题,探讨两位戏剧大师所呈现出的美学与艺术伦理共同性的问题和意义,概括、总结出三个“伟大的共同性”:人格、人生哲学、再度创作。
经典作家的伟大经验给我们有很多的启示。《并世双星》比较研究的是400年前东西方的两位经典作家,该书在一个非常广阔的时空中所发掘和讨论的一些命题,对文学艺术来说,涉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有些问题既具有历史性,也能让人感觉到深深的当下性、现实性以及未来性。比如时代对作家、对艺术的深刻影响,比如作家的人格、精神境界对文学艺术的作用,比如创新和如何创新等问题,我觉得都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对未来的创作也有一定的规箴意义。
从时间上来说,汤、莎是同时代人,考察作家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老问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很早就论及时代、世情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从时代角度比较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是《并世双星》的一个重点。李建军认为,他们的志趣有很多相似性,但生活的空间不同,亦即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文化环境、政治文明等条件不同,他们的命运、文运、心境以及美学选择、叙事策略,当然也包括其艺术世界所呈现出来的风格也就不同;时代在他们的身上打下了非常鲜明的烙印,他们艺术上的很多选择既是个人的,也是时代的。
李建军认为,文运取决于时代,而莎士比亚之为莎士比亚,是他幸逢其时。李建军分析说:“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人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而他的写作,则是其时代的精神镜像。”写作需要最低限度的自由——安全地思考、想象和表达的自由。在一个极端野蛮的时代,只有少数勇敢的人,才敢于在积极的意义上写作,而大多数人,或选择沉默,或满足于虚假的或不关痛痒的写作;即使是那些勇敢的写作者,也不得不选择一种隐蔽的写作方式,例如隐喻和象征。汤显祖象征化的“梦境叙事”,就是一种不自由环境下的美学选择;而莎士比亚的全部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极大的自由感和明朗感,则彰显着写作者与写作环境之间积极而健康的关系。
李建军说,从物理时间上看,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确乎是同时代人;但是,从文明程度看,他们则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时代——汤显祖的时代落后莎士比亚的时代,何止四百年!”在李建军看来,就想象力和才华而论,汤、莎两人“在伯仲间”,但境遇和命运,却全然两样。莎士比亚生活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没有伊丽莎白时代的伟大精神,就没有莎士比亚的辉煌成就”。故此,莎士比亚的写作,“在题材取舍、主题开掘、风格选择、修辞态度等几乎所有方面,都表现出一种自由而积极的状态”;即使涉及政治和权力的主题,也不用左顾右盼,不怕“触犯时忌”。而汤显祖生活在一个落后而野蛮的前现代社会,恐怖氛围里的静止与和谐,是这个社会的突出特点。他怀抱利器,无由伸展,处处碰壁,一生偃蹇。就是在这种“无可奈何”的写作环境里,他努力不懈,这才创造出“临川四梦”的不朽成就。
李建军关于时代对作家及其文学影响的阐述,不仅在于作家的个人命运以及人格精神这些大的方面,让人印象深刻,感受真切的,还在于他关于这种影响达于文学修辞方面的阐述。
关于汤显祖的创作,李建军认为,“从文学精神来看,汤显祖无疑属于现实主义作家。但是,从写作方法来看,汤显祖的‘临川四梦’,除了《紫钗记》大体上是用写实的方法创作出来的,其他三部全都是象征主义性质的作品,就此而言,可以说,他是用象征主义方法来写作的现实主义作家”。他认为,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之“梦境”,是作家在“被动的境遇”中所选择的一种“积极的策略”:“汤显祖的象征主义写作既是被动的,也是自觉的。”“在技巧的背后,人们可以看见强大的皇权专制,可以看见意识形态诡异的面影”。
李建军指出:“在任何专制主义的写作环境里,现实主义都是一种被敌视和压制的写作方法。”元代的专制统治也很黑暗和严重,知识分子的地位也很低,但因为少有“文字狱”,作家和艺人的自由空间也就相对大了一些。而与元代相比,明代社会的思想天空就要黑暗得多,文化生态环境也要恶劣得多。因此,作为一种安全而积极的叙事策略,汤显祖喜欢写梦境,写梦境中有奇人异事,“梦境中事,子虚乌有,容易打马虎眼”。“临川四梦”,《紫钗记》《牡丹亭》以梦写人之至性至情,特别是《牡丹亭》,人可以因情而死,又因情而生,这是对人性至真、至纯、至美的肯定和赞颂;《邯郸记》《南柯记》则借梦境对现实生活和虚妄的人生追求进行讽刺和批判。无论是肯定和赞颂,还是讽刺与批判,以梦境来表现,都是一种“安全而积极的叙事策略”,这让我们对时代与文学关系的认识,似乎更为内在。展开来看,中国古代文学以诗词和文章为主流,这显然与古代作家的身份构成有关。古代作家基本上是文人士大夫,他们文化高,修养深,且大多居于社会的上层,而诗词文章需要一定程度的文化和修养,才能创作和欣赏,所以,一般而言,诗词文章是文人士大夫的文学,某种意义上说是“贵族的文学”,而不是平民的文学。现代以来,时代强调文学的社会改造功能,白话文就大行其道,后来提倡“为工农兵写”甚至“工农兵写”,更强调人民群众的语言特别是口语化,文学中“文”的色彩就有些淡化,而“野”的味道就浓了一些。受这种时代思潮和文化风气的影响,现在的文学,对诗词和文章明显地不太重视,甚至完全忽视,人们一提文学,似乎只是指小说。作家身份的构成,从古至今,由文人士大夫而平民而工农兵(此时作家的主体,就是工农兵或工农兵出身者),这种时代对文学的要求和对作家的选择,历史脉络非常鲜明。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谓“朦胧诗”的兴起,显然也与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特别是政治状况有关,是时代造就了诗歌“朦胧”的修辞方式和叙事策略。
李建军在论及汤、莎两位作家创作的伟大经验时,其中有两点概括:“创作的时代性”和“集体性共创”,我觉得对当前的文学创作特别富有启示性。
创作的时代性就是当代性。作品的思想、精神和问题首先立足于当代,针对的是当代,即使是历史题材的写作,所指涉的也首先是当代。有了当代性即时代性,然后才有可能上升到超时代的普遍性。李建军认为,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首先是属于自己时代的作家,他们的“再度创作”,给后世的作家提供的有价值的经验资源,其中首要一个就是时代性。“任何自觉的写作,都是首先针对自己时代的写作。它必须首先立足于当代性,然后再由此上升到超时代的普遍性。”而“一部毫无时代性指涉的作品,不可能成为超越时代的伟大作品;一部不能感动自己时代读者的作品,也很难感动后来时代的读者。”这就要求,“无论多么古远的题材”,“都要将它转化为关乎时代生活的叙事内容,都要将自己时代的情绪、问题和经验灌注进去”。这些论述和分析中的点睛之笔,读之豁人耳目。这种经典作家的伟大经验,对那种有意无意回避时代重大问题和普通情绪、忽视时代对文学创作的要求,特别是对现实题材的创作,具有警醒和启示作用。也可以说,李建军在这里的研究和论述,也有他的“时代性”。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给人以启示的经验资源,还有一个是“集体性共创”。李建军说:“集体性共创是我整合出来的一个概念,其基本内涵是:一切成熟意义上的文学创作,都是以前人或同代人文学经验为基础,是对多种经验吸纳和整合的结果,因而,本质上集体性的,而非个人性的;是由知名或不知名的人‘共同’参与和创作的,而不是由一个人师心自用独自创作出来的。它涉及了对独创、生活和内心封闭性等问题的理解和阐释。”这个“集体性共创”观点,说清了创作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创作”固然是一种个人的“创造”或是某种程度、某种意义上的“独创”,但也确实是“以前人或同代人文学经验为基础,是对多种经验吸纳和整合的结果”。认识到这一点,对创作非常重要的一点启示,我认为就是我们要充分尊重和学习前人或同代人的文学经验,要 “会通”古今中外的文学经验。这样,也许可以少一些那种“无源之水”和“无根之木”的所谓“独创”,少一些那种不能与时代、与他人“对视”和“对话”的“自言自语”。
李建军在这里的理论分析也有其“时代性”。针对当下一些关于“独创性”的言论,他说:“对文学来讲,很多时候,‘独创性’是一个充满陷阱的概念。文学上的完全的‘独创’或‘创新’,是不可能的。因为,新的经验产生于旧的经验;只有在旧经验的基础上,才最终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亦新亦旧’的经验。在文学上,完全与旧经验没有关系的‘新经验’是不存在的。”这些论述,对当前文学创作中长期流行的关于“独创”和“创新”的一些错谬观点,如所谓的文学和美学、后人与前人“断裂”一类甚嚣尘上的说法,确实有补偏救弊之用。
《并世双星》是一部扎实的学术著作。书中所有立论,许多很有见地的观点,都有极扎实的论据做支撑,论证严密,以理服人。同时,又以饱满的感情以及华彩篇章打动人,很有感染力。这是一部思与诗并美的学术著作。李建军对东西方两位伟大作家创作经验的发掘和提炼,无疑是当今创作以及未来创作不可忽视的一个经验资源。这是《并世双星》纪念两位戏剧大师应有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