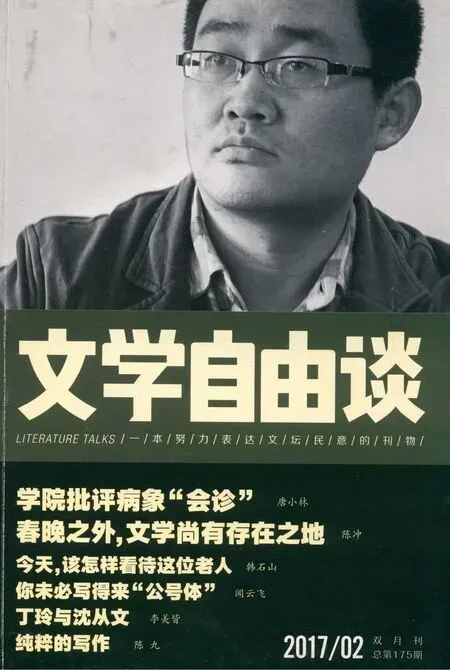丁玲与沈从文
2017-03-11李美皆
李美皆
丁玲与沈从文
李美皆
虽有胡也频却仍然苦闷着的丁玲,必然期许另外一位异性的到来。冯雪峰出现了。那是1927年冬天,她和胡也频“同居”两年之后。那时候,丁玲已经在《小说月报》头条位置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也写好寄走了。《梦珂》的发表使她有了一笔稿费,她想利用这笔钱去日本留学,冯雪峰就经人介绍来教她学习日语了。
沈从文是这样写冯雪峰的出现:
自然的,这先生上课一礼拜后,两人之间便皆明白了这种学习有了错误,她并不适宜于跟这个人学习日文,他却业已起始跟她在学习爱情了。
沈从文把冯雪峰视为乡巴佬,事实却是丁玲敬慕冯雪峰更多一些,但以沈从文对丁玲的复杂感受,可能是不愿意正视这一点吧?
丁胡之间并无夫妻之实,丁玲认为自己依然拥有恋爱的自由。因此,冯雪峰虽然“后到”,但和“先来”的胡也频拥有与丁玲恋爱的同等权力。可是,胡也频不允许,而且是那种幼稚莽撞冲动的不允许。冯雪峰可能觉得太不堪,便离开了北京。冯雪峰来到上海后,从《小说月报》上读到了《莎菲女士的日记》,立刻给丁玲写来长信,讲述他的读后感,虽然也有批评,但更多的是肯定和看重。收到冯雪峰长信的丁玲,迫不及待地去了上海,此时距冯雪峰离开北京只有两星期的时间。胡也频则追随丁玲来到上海。丁玲对斯诺夫人说:我们一同在上海只过了两天时间,我们三个决定一同到杭州那美丽的西湖去,这在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从沈从文的《记胡也频》《记丁玲》中可以知道,在上海的两天,丁胡二人在沈从文的住所因为冯雪峰闹得非常厉害。
冯雪峰曾是湖畔诗人,杭州是他熟稔的旧地,所以,他早到杭州,租好了西湖葛岭的房子。“冯雪峰替我和胡也频在杭州葛岭找了房子,我们三个人在那个地方住了一晚上。”“见到雪峰,丁玲仍然有说不完的话,她再次感到离不开雪峰。”胡也频当然受不了,回到了上海。沈从文的《记丁玲》写道,胡也频是“在一次流泪赌咒的情形下跑来上海”的,而且“准备不再回转杭州”。
的确,这在丁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她爱的是冯,但对胡也不是没有感情;而且,在别人眼里,她和胡既已同居,就已经是夫妻了。在这场爱情的拔河中,女主角既然是矛盾和为难的,两位男主角爱的力度就非常重要了。胡是进取之势,冯是退让之势,一个热情逼人,一个严肃自持。在两个男人的拔河中,女主角便倒向力度大的一方了。但她其实是希望倒向另一方的。
影响结局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性。
丁胡虽已同居两年半,但并未发生性关系,只是形式上的夫妻。转折是从胡也频赌气返回上海时开始的,沈从文在其间起了关键性作用。
《记胡也频》中,沈从文说他跟胡也频“在一个大木床上谈了一夜”。这一夜谈了什么呢?《记丁玲》中说得更清楚:他尚告给我两人虽同居了数年,还如何在某种“客气”情形中过日子。我便就我所知道的属于某种科学范围的知识,提出了些新鲜的意见,第二天,就又把他打发回到杭州去了。
沈从文的“新鲜的意见”,跟他在劝解丁胡几天前吵架时观察到的“她先前正缺少些出自男子的隐密事物”,是一脉相承的,核心就是性。
沈从文很得意于自己的导师角色,《记丁玲》中他写道:
这次回去,我对于海军学生所作的一番劝告,大致很有了些用处,风波平息了,一切问题也就在一份短短岁月里结束了。
两人住在西湖葛岭一个单独院子里,大约将近三个月。三个月中的生活,或者因为新增加了那从前所缺少的成分在内,故两人简直像一对同度蜜月的伴侣。……海军学生到后与朋友们谈到西湖时,常用作新郎的风度,以为在西湖所过的日子,回忆时使人觉得甜蜜快乐。
沈从文心知肚明胡也频回杭州后丁胡之间迈过了一道怎样的槛,如新婚夜闹洞房的人那样心知肚明。是他使胡也频做成新郎的,他因此简直也怀了准新郎一样的幸福感。他这一写,也算是立此存照了:丁玲做成新娘,都多亏了他呢。可是,晚年的沈从文跟女助手王亚蓉谈起丁玲时,情形却是这样的:
王:外界问沈先生和丁玲是不是以前有什么恋爱类的关系……
沈:没有,没有。幸好没有这种关系。
沈:后来耶鲁学者说:总是他们两人吵架,沈劝解又劝解,不然胡也频早跑掉了。
王:她跟胡也频时,不也跟冯雪峰吗?
沈:是的。她可以说乱得很,长得又不好……跟萧乾也有来往,萧乾不理,主要是让人给她捧场,讲清楚的。
王:齐光说,那时她在延安使劲追彭XX。
沈:彭说我不愿意看她。没办法,老太婆啦!
王:我听别人讲她写的东西和她本人一样,只是放荡。
沈:她整天打牌。她写的文章胡也频怎样子前进,和冯雪峰纯粹是精神上的友谊,那和冯达又是怎么一回事呀!就不提啦。
沈从文完全忘记了,这个“乱得很”的丁玲,当初还是承蒙他对胡也频的“教导”,才初涉男女之事的。沈从文也完全忘记了,他当初看这“圆脸大眼长眉的女孩子”的眼神,是脉脉而饶有兴味的。《记胡也频》《记丁玲》中沈从文看待丁玲,虽不是奉为女神,至少也是不乏喜爱的。若不含情,看在眼中的绝不是那个样子,写出来的绝不是那个语气。
可是现在,提起丁玲,字里行间只是透着一个意思:没人要的女人。听沈从文说的,倒好像丁玲追着胡也频不放似的,与他自己写的都不符。丁玲才三十出头,就被他幸灾乐祸地说成是别人不愿意看的“老太婆啦”。胡也频的“前进”,是沈从文始终无法理解的,但胡也频的牺牲、成为烈士总是事实吧?这难道不是“前进”的结果?丁玲写的不符实吗?丁玲从来没有强调她与冯雪峰只是纯粹的精神友谊,《不算情书》已经公开了一切,1937年她对斯诺夫人谈到冯雪峰时也很坦荡。更匪夷所思的是,连“写的东西和她本人一样,只是放荡”这样的话都出来了,完全就是一个长舌妇跟一个小男人议论另一个女人的情形。这是一位男作家,而且是一位所谓伟大的男作家的气度风范吗?你还觉得他有那么高洁纯正地道吗?不看这个语境中的沈从文,你能想象他还有这么真实“可爱”的一面吗?这种小丈夫气,与鲁迅笔下摇嘴鼓舌的小丙君委实有得一拼。除却白眼看鸡虫,难道你还能对他青眼相加吗?
沈从文对于丁玲这种与女性性别有关的特定评判,先就有失君子风度。那无非就是自古以来针对女性的最方便的攻击。就算交恶,一个男人,专在这些地方对女人下手,也不见得是君子。周作人在《书房一角·扪烛脞存》中说:“鄙人读中国男子所为文,欲知其见识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对佛教以及女人如何说法,即已了然无遁形矣。”周作人所说乃“为文”,沈从文此处是“说话”,而“说话”与“为文”,原出一辙。
这是1982年冬天,沈从文与王亚蓉在火车上的聊天,当时丁玲还在世,二人已交恶。沈从文大概也就是随便发泄一下而已,没想到会被发表出来,否则,至少要为自己的形象负一点责,不至于说出来的话变成文字摆在这里,让自己难堪,也让别人鄙视。
沈从文和王亚蓉还有一些对话,也可圈可点:
王:她从南京监狱一出来,就住您家,住多久啊?
沈:没多久。那时我家很窄,我妹妹、大姨全住我家。照顾她吃饭和钱。一得势就忘记了。
——丁玲不是进监狱,是软禁。丁玲从软禁中逃到上海,都是冯雪峰安排秘密居住,不可能住沈从文家。
王:她主要讲的誓言,就是她要被捕她就死?
沈:她没讲死,只是说我决心死。结果不但不死,活得还好。
王:结果不但没死,还给人家生了一个小孩。
——这是希望丁玲死吗?连沈从文自己都说丁玲不是叛徒,却还为她没死而颇感遗憾似的,这是安的什么心?
王:您送她回湖南的照片不应该给她。
沈:我家现在还有几张呢。送她回去我们在山上照的。有凌叔华、陈源,都是鲁迅骂的。我,丁玲,胡也频和丁玲的儿子,是在武昌城上,我们送走孩子就轻松了,看武昌啊!我在武汉大学教书,把他们招待得很好。丁玲捕后写信给吴稚晖,吴是她舅舅。吴不管,他是国民党右派。只有我傻头傻脑帮她找了蔡元培,蔡元培也不管。当时都怕啊!后来是汪精卫那边的一个中央委员把她保出来的。她那时不是党员。
——不至于几张照片给不给都要计较吧?何况这都是半辈子之前的事了。这武昌城上,到底有没有丁玲的儿子?前面说孩子在武昌城上,后面又说孩子送走了。事实上是不在。沈从文上了年纪,又是在闲聊中,有些记忆不准确,或前言不搭后语是正常的,但记录者既然要发表出来,不至于连基本的整理和纠正都不做吧?吴稚晖是丁玲的舅舅,丁玲是汪精卫那边的中央委员保出来的,这都是完全没影儿的事。丁玲1932年入党,1933年被捕。半个世纪后,沈从文却还说她被捕时不是党员,看来他真是不了解丁玲,或者太过信口开河了。
王:就是现在她有什么作用呢?
沈:也没有。没有人啊,什么斯大林奖金,那个完全是政治上的……
——这样议论和判断丁玲的没用和没势,不正是市侩的实用标准和势利心态吗?
王亚蓉可能是爱导师心切,意欲同仇敌忾,为导师贴金和鸣不平,但效果却是适得其反,不自觉地暴露了师徒二人的小肚鸡肠心胸褊狭境界低下,既有损沈从文的形象,也有损她自己的形象。这样热心地帮倒忙,沈从文本人也未必乐意接受吧?同样是助手、秘书的角色,丁玲晚年的秘书王增如就不同,即便悉心维护丁玲,说出来的话也不至于降低到三姑六婆鸡零狗碎的程度。
丁玲与沈从文的友谊,首先是由于胡也频的连结。一个是好友的爱人,一个是丈夫的好友,这是他们友谊的基础。二人之所以交恶,抛却这些零零碎碎无法确证的表面事,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是个性太不相同的两种人,走的是太不相同的两条路。丁玲这样的大女人,对沈从文可能是有点不欣赏的,一开始就不欣赏,但有胡也频在中间连结,还好;后来没了胡也频连结,各自的道路也有了更大的不同,可能就更不欣赏或直接看不上了。沈从文对丁玲,后来也是看不上,他与王亚蓉的对话已充分显示。
他们之间的友情已近乎亲情。要知道,29岁的胡也频是穿着沈从文的海虎绒袍子就义的,这样的“同袍”之谊,哪是寻常可比。沈从文不仅两赴南京营救胡也频,而且在胡也频牺牲后陪伴寡妇雏子回到湖南老家,将遗孤托付给外祖母抚养,对逝去的胡也频已尽到了充分的朋友之义。但是,友情越深,就责之越深,近乎亲情的无条件,所以,丁玲对于沈从文在她被捕后没有照顾她的母亲与儿子,颇感凉薄和难受,1938年对朱正明谈到时已有微词,晚年写的《魍魉世界》中也提到了。左联成立“丁、潘(注:指潘梓年)营救委员会”时,需要沈从文帮忙请来丁玲的母亲和儿子,以加大营救的砝码,沈从文没有合作。丁玲虽表示沈从文“向来胆小,怕受牵连,自是不必责怪的”,内心其实是不满的。但沈从文对于丁玲的被捕并非不管不问,他发表了《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两文,谴责国民党政府的“绑票”行为。传言丁玲被害时,沈从文还创作了小说《三个女性》来哀悼丁玲。沈从文这两种不同的行为其实并不矛盾,陈漱渝先生分析得很中肯:看来一贯表示“中立”的沈从文对于跟左翼人士采取联合行动,比进行独立的营救活动有着更多的顾忌。
友情虽生嫌隙,但并未破裂。建国后至1955年丁玲落难前,丁玲处于顺境,而沈从文却因受到左翼文坛的批判而患上近似被迫害狂的癔症,惶惶不可终日。听说沈从文试图自杀的消息,1949年丁玲到北京后的第三天,就去探望和开解他,使精神濒于崩溃的沈从文略感安慰。丁玲先后去看望过他多次,还赠予二百万元,这是一个不菲的数目。沈从文给丁玲写过三千余字的长信,诚恳地谈到自己的精神问题:“已深知个人由于用笔离群、生活离群转成个人幻态,涉于公,则多错误看法,近于病态而不健康,涉于私,即为致疯致辱因果”;同时,请求丁玲转告有关方面,希望能得到中共的谅解,安排他从事工艺美术研究。丁玲有没有转达沈从文的请求不知道,但这个结果已经有了,沈从文很快到历史博物馆上班去了。1950年丁玲写《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对于早年与沈从文的友谊是承认的。1952年沈从文又给丁玲写信,请她推荐发表文章和向她借钱。沈从文那种文章,是自己参加土改后写的,拼命往“主旋律”上靠又靠不上,却比小学生作文还幼稚,本身就是在别处已遭退稿的,丁玲怎么推荐?沈从文转向工艺美术研究,绝对是正确的选择,但又何尝不是尝试“主旋律”写作失败后的正确选择。至于借钱一百万,丁玲接信后马上就派人送去了。诚如丁玲的儿子蒋祖林所写:如果真如丁玲对沈从文冷淡那种说法,那么以沈从文这样一个清高、自尊的人,怎么会向一个蔑视自己,即便是身居要津的人张口借钱呢?
1980年代初二人交恶后,沈从文在给徐迟的信中说:当她十分得意那几年,我却从不依赖她谋过一官半职。几乎所有老同行,旧同事,都在新社会日子过得十分热闹时,我却不声不响在博物馆不折不扣做了整十年“说明员”。
沈从文的意思很明白:她风光的时候,我没沾上光。对这没沾上光,他是略有不满的。但到了1980年代沈从文风光之后,几乎一边倒的看法是: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远避政治,保持了独立人格,虽不得志而犹荣;丁玲在政治上得志,一副“左”的革命嘴脸,对老朋友沈从文无情无义,不仅不加提点,而且态度冷漠和傲慢,致使沈从文精神更加趋于崩溃。
首先,没有热情拥抱,并不代表无情无义,无情无义的指责是不成立的。丁玲去看望过沈从文,对于沈从文的求助也是尽力满足的。要说她不够热诚,那是真的,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和社会氛围之中,还有多少知识分子之间是热诚的?何况,丁玲跟沈从文性格本来就不那么相投,以前的友谊主要是基于胡也频的纽带作用,胡也频没了,他们之间友谊的淡化是必然的。又何况,丁玲对于自己被捕之后沈从文不够义气相助,心中已生嫌隙。二人对于革命的理解和道路的选择本来就大不相同,又分别多年隔膜多年,再在新中国相聚,难有志同道合的同志之间的交流是很自然的。再加上沈从文被郭沫若的批判吓破了胆,疑神疑鬼,心理病态,连家人都不耐烦了,本来就不欣赏其软弱性格的丁玲自然也不耐烦多打交道。要说变,那不光丁玲变了,沈从文也变了。我不认可一阵风来就一边倒,反对以政治视角来阐释一切。决定打不打交道的,可能不是胸中丘壑,也不是笔底风雷,而只是感性上的舒不舒服。丁玲对沈从文的看法,从年轻到老没变过。他在天堂时你不喜欢,到了地狱你就一定要喜欢,才能表明自己道德正确吗?你不喜欢的人倒了霉,你就一定要喜欢他,来显示自己的君子风度吗?沈从文本人也不会这么做吧?一个得势的人对待一个不得势的人,只要不是为了避免“势利眼”的帽子而刻意示好,“势利眼”的评价,对他往往就是预设好的定见,他只是自然而然,却就无可逃脱地“坐实”了。
其次,有些人怀揣善良的愿望,认为沈从文处于当时的高压氛围下,极度需要丁玲出手相助,只要丁玲力挺他,他就一定会挺过去的;丁玲且唯有丁玲能使他免于恐惧和崩溃,可丁玲却高高在上见死不救。这愿望虽然善良,但实在是天真,沈从文所感受到的当时的氛围是弥天的,丁玲一个人能够扭转吗?她能够替沈从文撑天吗?丁玲难道比郭沫若更有影响力吗?如果她有那能耐,自己就不至于在1955年落难了。
我无意把丁玲举为圣人,甚至原本也不想为她辩护。之所以说这些,完全是看不惯一些人必须在圣人和小人之间取舍的思维惯性:既然丁玲和沈从文有矛盾,既然自己是站在沈从文一边的,就一定要把沈从文举为圣人,把丁玲贬为小人。世间人事,是这样简单斩截的吗?你我皆凡人,圣人和小人能占多少?多数人还不是介乎圣人和小人之间吗?知人论世爱凭想当然,实在是没意思透了。
1955年丁玲落难后,沈从文的处境又比她好些了,但也帮不到她什么,二人几无交集了。1960年,丁玲从北大荒回京参加第三次文代会,天天坐冷板凳,充分感受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林斤澜1999年回忆,作协在这次文代会期间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丁玲来到会场时没人搭理,散会后去公共汽车站的路上,沈从文追上去要跟丁玲说话,但丁玲有意回避,不愿交谈。沈从文此时的热情,恐怕只能让丁玲发窘了。让主流人群看到她跟沈从文这样的不先进分子为伍,那无异于活现,证明她确实不先进。
1980年沈从文在给徐迟的信中说,在她因内部矛盾受排挤时,都是充满同情。到明白转过山西临汾(注:原文如此,应是长治)时,还托熟人致意。这次致意未见丁玲提过,或许是没有传达到;即便传达到,可能丁玲也不稀罕吧。
丁玲和沈从文之间再生龃龉,是始于1979年,日本汉学家中岛碧女士访问丁玲,送给她两本书:沈从文写的《记丁玲》与《记丁玲续集》,是香港某书店据1939年的初版本翻印的。不能确定丁玲是否首次知道这两本书,可以确定这是她首次看到。中岛碧女士还有一些疑问,比如,《记丁玲》中说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同住”,这意味着什么?这疑问给了丁玲极为不良的刺激。
我查了一下,沈从文自己在三人身上用到“同住”这个词,就一句话:“在几人同住上海的时节”。这句话还是在说别的时顺带提到的。至于这“同住”的可疑内容,是指1929年三人合办《红黑月刊》时,短期合租了一栋三层楼的房子,住的除了他们三人,还有沈从文的妹妹和母亲、丁玲的母亲,同时兼作办公处。从人员构成和房子的大小,就可以知道,所谓同住,无非是共同租住一套房子而已,三个人不仅住的房间不同,就连楼层都不同:沈从文和妹妹、母亲住三楼,丁玲、胡也频和丁玲母亲住二楼。
当然,三人也在同一个房间住过,那是丁玲和胡也频到上海后、去西湖前的两天。沈从文在《记胡也频》中写:最初这两个人来时,就留在我那个住处,那时我在上海法租界善钟路一户人家楼上赁了一间房子,他们初到上海我算是他们最熟的人。《记丁玲》中写:两人虽在上海住过,这次来上海既不预备久住,故一来就暂且住在我那地方。那时节我住处已经从亭子间改为正楼大房,房中除去一桌一椅一木床外,别无他物。两人因此把被盖摊开,就住在我房中楼板上。
可是,这个时候,丁玲与胡也频都尚未有“同居”之实,再加上一个沈从文,又能怎么样呢?丁玲与冯雪峰约出去吃顿饭,胡也频都要怒到动手的,他怎么可能让沈从文生出什么花边!
他们之所以会“同住”,原因有三:一、经济原因,说白了就是穷,图省钱;二、太相熟,太要好,无隔膜,连性别都不是那么介意;三、沈从文的温软,引不起胡也频和丁玲的性别戒备,若是一个虎视眈眈的猛男,断不会如此。可是,就是这样因陋就简的“同住”,被看客演绎成了“三人行”“大被同眠”。一说到丁玲,就会有人眉飞色舞会心暧昧地表示:丁玲,那可是个人物。而接下来,证明丁玲是个人物的,就是与各种男性名人、大人物的传说,这些传说,又数“三人行”“大被同眠”最为奇葩。这种为坊间所津津乐道的烂俗传说实在令我不耐烦,这也是我要专门拿出笔墨来写写丁玲与沈从文有关的这一切的原因。
“三人行”“大被同眠”的绯闻原本是关涉到三个人的,可是,其中被“污名化”的,只能是女人。对于男人,或许这还是骄傲的资本呢。顾彬的《三访丁玲》中写到,第二次访问(北京,1983年10月31日)时,当《当代》杂志的编辑冯先生说遇罗锦是个“堕落的女人”时,丁玲好像突然敏感起来。她想知道,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一个男人。丁玲的敏感、丁玲为遇罗锦所做的辩驳,几乎等于女性的自卫。同样的事情,性别由“男”置换为“女”,性质与色彩就会完全不同。男女同污而污水不泼男人,这是中国源远流长的集体无意识。“三人行”的格局,注定了作为女性的丁玲的“污名”是摆脱不掉的。“莎菲”又被拿来佐证了丁玲的个性解放乃至性解放。二者互证,使丁玲俨然成了“吃瓜群众”眼中“不疯魔不成活”的新女性代表。但事实正相反,青年丁玲是一个宁静内向的人,她自言“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沈从文对她的观察,也是一个“凝净看百样人生”的女孩子。也许有人是由丁玲复杂的情史来逆推她年轻时的“开放”,但这种逆推是毫无道理的。就算一个女人有N个男人,你也不能随便牵来一个,说这是她的N+1个。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能想当然。
丁玲被如此符号化,与沈从文《记丁玲》《记丁玲续集》中的记叙不无关系。这些书应和了大众对于桃色的兴趣,因而影响颇大,成为了解丁玲的“第一手资料”,造成普遍的误导,这是让丁玲大为气恼和无奈的。沈从文并非刻意如此,只是他的趣味主义的濡湿的眼光和缠绕黏腻的文字表述,很容易造成那样的阅读效果。这样的东西本来就“老年不宜”,何况丁玲经过数十年政治文化的改造,已经充分体会到作风问题是何等毁人。她一直是流言的受害者,都一大把年纪了再看对自己的略显绯红的书写,多么难以忍受是可想而知的。
丁玲在1980年3月发表的《也频与革命》一文中,终于有机会将沈从文痛斥一番。她说《记丁玲》一书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意在告诉读者:不要相信此书的真实性,更不要据此来了解和研究我。
丁玲写在沈从文生前,他有机会公开答辩,可是他没有。不但没有,在1980年美国汉学家先访问丁玲,听了丁玲对这两本书的意见,又去访问沈从文时,沈从文说:“过去的事已隔多年,我记不清了。如果我和丁玲说的有不一致的地方,以丁玲说的为准。”沈从文的隐忍,为他赚足了斯文的好评,显得丁玲更加斯文扫地。
《记丁玲》以《记丁玲女士》为题连载于1934年的《国闻周报》时,沈从文致编者函中说:“此文……在方法上,有时既像小说,又像传记,且像论文。体裁虽若小说,所记则多可征信……此文以之作传记读,或可帮助读者了解此女作家作品与革命种种因缘……”可见,沈从文很强调本书的可信性。他又在1982年对周健强说自己写的是“真人真事”。无论主观还是客观方面,该书明明有不少夸大失真处,却被当作传记来对待,作为传主的丁玲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丁玲曾有对两书逐条批驳的冲动,后来想想作罢。作罢是“转念我个人所受的诬蔑,有比沈从文更甚者,如我能忍受,那么沈从文的这本书就不值什么了”。冯雪峰之子冯夏熊撰写了批驳沈从文的长文《丁玲与〈记丁玲〉》,丁玲都建议不要发表,“实在认为他也受过一些罪,现在老了,又多病,宽厚一些好了”。丁玲作罢是顾念与沈从文的旧谊,不愿失之宽厚,但她的《也频与革命》一文,已经让许多人认为失之宽厚了。部分原因在于,丁玲晚年声誉下降,而沈从文晚年声誉日隆,人心向背已经有了预设的分野,大背景对丁玲先已不利。
丁玲虽未逐条公开批驳,但在《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书页上做了127条眉批和旁注。学者陈漱渝看过丁玲的127条批语后,著文 《干涸的清泉——丁玲与沈从文的分歧所在》(《人物》1990年第5期),记录并分析了丁玲的这些批语——
《记丁玲》第41页—42页:……她的年岁已经需要一张男性的嘴唇同两条臂膀了……倘若来了那么一个男子,这生活即刻就可以使她十分快乐。丁批:沈从文常常把严肃的东西,按他的趣味去丑化。我很不喜欢他的这种风格。在他的眼睛里,总是趣味。
《记丁玲》第71页:她虽然同这个海军学生住在一处。海军学生能供给她的只是一个年青人的身体,却不能在此外还给她什么好处。丁批:混蛋!
《记丁玲》第137页—138页:她的年纪已经有了二十四岁或二十五岁,对于“肉体与情魔”的电影印象则正时常向朋友提到。来到面前的不是一个英俊挺拔骑士风度的青年,却只是一个相貌平常,性格沉静,有苦学生模样的人物……丁批:看把我写成一个什么样子,简直是侮辱!完全是他的低级趣味的梦呓!
连“混蛋”都骂出来了,可想而知其暴怒程度!如果沈从文就在眼前,不知她会不会跳起来给他一耳刮子。沈从文对于一个异性这么容易揣测到性苦闷上去,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自己的微妙和复杂心理吧?沈从文写此文时已经知道,丁胡此时根本没有“发生关系”,他却依然这么写,所以,这反映的只是他自己心理的真相。沈从文一厢情愿地顺着自己的逻辑,先来设定丁玲的性苦闷,再来留意性苦闷的解决,总之是不脱性的眼光。可是,如果丁玲的苦闷真是因为他所理解的“花痴”,丁胡此时就不会是有爱无性的状况了。
沈从文的这种狎昵的趣味,确实暧昧发黏,使得《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的文本空间很不干爽。沈从文内心可能确有猛虎,但这两个文本,充分渗出了一个细嗅蔷薇的沈从文。沈从文的软与硬各在哪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这二文的黏腻感是毫无疑问的。沈从文为什么会写得这么黏腻?首先,他看丁玲作为女性的种种,是有情的;正因为有情,丁玲的性别感才那么凸显。遗憾的是,这种年轻时的有情的性别感,在晚年却仿佛成了他认定她“乱得很”的内在支撑,也成了别人眼中的丁玲之“肉体与情魔”论的证明。其次,沈从文写丁玲时,以为丁玲已死。正如丁玲1985年6月25日在给别人的信中所写:我生气。一直生气,他以为我死了,他在写《记丁玲》时,谣传我已死。认为丁玲已死,他的笔端才更有情;认为丁玲已死,他写时才更放得开。如果意识到有一天要为传主所看见,他会谨慎得多——写《记胡也频》时,有丁玲在,他就写得收敛很多。这也是沈从文此后多次见到丁玲,却从未提及这两本书的原因。当年他写得有多放恣,现在她发泄和还击得就有多放恣。
丁玲在《也频与革命》一文中要申明的更重要的问题,是沈从文“对革命的无知、无情”“对革命者的歪曲和嘲弄”,具体地说,就是对她和胡也频之革命的无知和歪曲。
在革命这个问题上,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确实毫无共同语言,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鸡同鸭讲、彻底免谈的话题。胡也频和丁玲所做的,沈从文看着不对;而沈从文写出来的,丁玲看着不对,胡也频若看了,也会觉得不对。在丁玲几十年为政治所苦,深知政治高压线之可怕,又为解决自己的历史问题而绞尽脑汁时,看到沈从文把她和胡也频年轻时的革命说得那么不革命,甚至是荒唐——比如,把胡也频的转向革命定性为受革命宣传蛊惑而产生的非理性行为,把她从事的左翼文艺运动视为 “博注上的冷门”等——这怎能不让她担心和恼怒?丁玲的批注有:“你谈这些干什么,表现你的政治才识吗?”“以小人之心!”“可笑!只有你菲薄左联。”“这时左联刚成立。只有你觉得是稀奇的。也频既不告诉你,可见认为同你不必再谈什么了!”“表现他对政治的无知,懦弱,市侩心理而外,没有别的。”“胡说。”可见丁玲读到时有多么怒不可遏!
丁玲有她的不可爱,但也不是沈从文的拥趸者所以为的那种不可爱法。丁玲确实有情绪化的弱点,但她的发作,绝非无事生非的妇人之恶毒。当然,我也认为丁玲没必要那么生气,以致于一时愤激,说出一些情绪化的过分的话来。尽管沈从文写得有点趣味主义,带着他自己的有色眼镜,但他是用心写的,不会有人比他写得更贴皮贴骨。沈从文为她的一段人生留下了一个细致精微的备案,可能比她自己去写还要细致精微。事实方面的些许出入是可以理解并原谅的。历史过去一小时,都不再是历史本身。人的印象可能有偏差,每个人看问题的不同角度也可能导致偏差,只要不是刻意歪曲,就不必严加追究。
沈从文当时没有公开还击丁玲的《也频与革命》一文对他的斥责,但在编十二卷本《沈从文文集》时,拿掉了《记丁玲》《记丁玲续集》。不公开还击不代表沈从文没有情绪,事实上,他在1980年7月2日给徐迟的长信中,很情绪化地提到了此事,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想必他已经料到,这封信有一天会被发表出来的。果然,丁玲去世三年,即沈从文去世半年之后,徐迟在《长江文艺》1989年1月号发表了这封信。丁玲生前,多少还有点为沈从文的隐忍而不好意思,孰料他并未隐忍,只是他的发作要在他和她都死后才见天日,她再没机会发作回去罢了。
沈从文用“最伟大女作家”来讽刺丁玲,说她的《也频与革命》一文“狠得可怕”:“乍一看来,用心极深,措辞极险。但是略加分析,则使人发笑。”说她多年来所受的委屈不敢找人算账,却拿他出气:“主要是我无权无势,且明白我的性格,绝对不会和她争是非。”沈从文当然也难免情绪化和过度阐释。但说丁玲用老朋友来“开刀祭旗”以恢复“天下第一”的地位,显然是不客观的。丁玲晚年的主要精力是用于自己的历史问题平反,沈从文根本不在她注意的范围内,连“眼中钉”都算不上。
沈从文认为丁玲对他的不满,一是嫌他对她“举得不够高”,二是嫌他提到了她所忌讳的第二个丈夫——冯达。事实上,陈漱渝看了丁玲在书上的所有批注,发现在涉及冯达的地方,并未作任何批注。而丁玲自己在回忆录《魍魉世界》中,也没有避讳冯达。
沈从文极其注重与胡也频的友情,包括他看待丁玲的感情生活,都是站在胡也频的情感立场上。即便在给徐迟泄愤的信中,他也说:我对他们夫妇已够朋友了,在他们困难中,总算尽了我能尽的力。所以,他不与丁玲公开对阵,除了自己性格原因,以及有些东西难以辩驳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看在胡也频的面子上。他与丁玲曾经的友谊,很大程度上是与胡也频友谊的延续,他尽的是对好友的遗孀遗孤的道义,丁玲受惠于此。也正因此,丁玲对沈从文很有把握,甚至可以说有点“恃宠而骄”。她知道沈从文曾经欣赏过她,又有胡也频的面子,必然会对她心软。虽然二人在这一次交锋中都有些情绪化,但我不认为他们的关系已经恶化到恨之入骨的程度。丁玲是一个大女人,只要二人还能再聚首,她可能会放下自己的不快,而且,她或许以为沈从文也会原谅自己的任性吧?她绝没料到,沈从文对她的有过之无不及的恶性回击,其实生前已有,死后竟会轰轰烈烈发表出来。他人的掺乎也是一种离心力,为了给别人看,他们也必须把决绝的姿态维持到生命的最后了。丁玲早沈从文两年去世,沈从文对外没有任何表示。但我相信,他的内心不会毫无波澜,至少,三个人的青春年代,会像潮水一样,从他脑海一一涌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