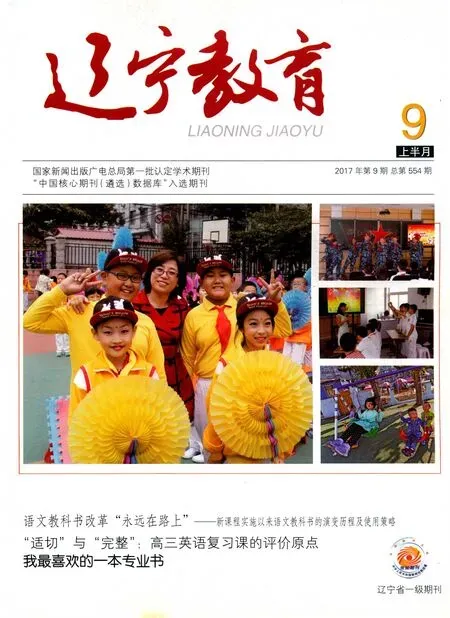语文教科书改革“永远在路上”
——新课程实施以来语文教科书的演变历程及使用策略
2017-03-11戴正兴
◎戴正兴
教苑
语文教科书改革“永远在路上”
——新课程实施以来语文教科书的演变历程及使用策略
◎戴正兴
语文教科书的变革是一个不懈追求、不断超越、不断否定、不断革新的过程。2001年《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 颁布,催生诸多版本语文教科书面世。2011年《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稿)》 实施,开启了语文教科书建设的新征程,使语文教科书的使用开始从“教教材”向“用教材教”转变,从“教本”向“学本”转变。
语文教科书;变革;使用策略
语文教科书是语文课程内容的主要载体,在教育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考察新课程改革以来,语文教科书的发展历程以及语文教科书使用策略,有助于我们了解语文教科书变革的全貌,把握新编教科书的特点,树立科学的教材观,用教材教文育人。
一、20套语文教科书:创生于新课程改革的大潮中
2001年新一轮课程改革拉开了序幕,我国语文教育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经历了一个不断变革的过程,语文教科书的变革则是其重要的内容。
2001年,教育部颁布《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随即审查通过了不同版本的20套语文教科书(小学12种版本,初中8种版本)。语文教科书的整体格局和呈现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较之以往的语文教科书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存在的弊端也显而易见。语文教育研究者和一线教师以敏锐的眼光审视和分析语文教科书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回望与评论。
语文教科书的每一次变化都会引起社会的热议,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常态。可以说,语文教科书(实验本)是在批评、质疑、挑战声中走过了15年。
(一)批评:研究者从多维视域出发,批评语文教科书(实验本) 存在的种种弊病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的温立三撰文,指陈新世纪课程标准语文教材编制的四大弊病:一是单薄的古代经典;二是缺失的语言知识;三是单一的编制类型;四是分割的阅读写作。
北大教授曹文轩批评语文教材不够“美”。他认为,当下的语文教材无论在理念还是体制、体例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局限性。各种有形无形的限制、仍旧还显落伍的评判标准、编写人员阅读视野的狭小以及近年来一些偏激的语文观念,导致了语文教材存在缺憾。
2009年7月,朱自强、王荣生、徐冬梅等七位关注小学语文教育现状的学者和一线教师,就几种小学语文教材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历时三天的分析讨论,对所谈内容整理成《小学语文教材七人谈》一书,提出“儿童本位”的教育理念。专家指出,现行教材“缺少儿童本位的教育理念,很少考虑到儿童文化的人文性,因此与小学生的心灵常常相隔膜”“儿童本位成为我们七个人所共同主张的语文教育理念和语文教材编写理念。这是我们为中国的小学语文教育进一步深化改革所设定的主要方向”。
2010年9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批判》一书将矛头对准小学语文教材。该书以教材点评的方式,刊发了一个名为“第一线教育研究团队”的民间研究团体的研究报告——他们以使用最广的“北师大版”教材、“人教版”教材、“苏教版”教材中涉及母亲与母爱的文章为研究对象,认为存在“四大缺失”,分别是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一些国家媒体刊发了这项研究报告,一度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学本化”是语文教材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多种版本的新课标语文教材在“学本化”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张永祥撰文总结了语文教材“学本化”建设中存在的五个方面问题:一是导学模式简单化,重结果轻过程,不能有效的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二是导学形式较为雷同和陈旧,缺乏富有时代特色的设计;三是导学内容显得“平庸化”,难以指引学生学习;四是传统导学方式没能真正体现出“为学生学习服务”的特点;五是导学内容“科学化”水平不高,影响了导学效果。
著名儿童文学研究专家朱自强在《儿童本位:改革语文教育的一剂“良药”》一文中,直指中小学语文教材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低估儿童的语言能力和审美能力;二是偏离与儿童语言发展相结合的语言系统;三是违反儿童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四是忽视儿童生命所拥有的有价值的人文性。
对小学语文教材的评价,来自“一线用户”的声音很有发言权,表达了他们对小学语文教材的看法,总体来说“感觉好的课文还是偏少了一些”,教材太“正襟危坐”,教材中有些文章的教育意义太浓厚,担负了爱国主义、亲情教育等太多责任,表现也很直白。他们希望多看到一点文质兼美的文章。
教科书造假受指责。语文教科书收录“假课文”的现象由来已久。所谓“假课文”,被诟病的主要原因就是故事是捏造的,但人物是真实的,也就是说,给历史上真实的人物炮制虚假的故事,像《爱迪生救妈妈》中,虚构了七岁的爱迪生用镜子聚光帮助医生在家给妈妈进行阑尾炎手术的事情。类似的假课文还包括《华盛顿与樱桃树》,文章捏造了幼年的华盛顿砍倒家中一棵樱桃树,因主动向父亲承认错误而得到原谅。有专家指出,“假课文”被逐出教材,该反思教材编写价值观了。
(二) 质疑:集中表现为选文的变化,即选文的增删与替换
语文教科书选文的争论成为一个喋喋不休却又语焉不详的论题。一个时期以来,语文界对语文教科书内容的增删、选文的“进进出出”引发了诸多不同观点的碰撞,争议不断。
入选语文教科书三十多年的红色经典范文《狼牙山五壮士》《回忆我的母亲》在某些省市和出版社的实验课本中被删除或调整后,引发了社会的讨论和争鸣。
在某些出版社实验版的教科书中,鲁迅的作品有所减少,引发了语文教科书该不该“去鲁”的激辩。支持从教科书中减少鲁迅作品的“支持派”与反对减少鲁迅作品的“反对派”各执一端。
儿童读经好不好?有人力挺,有人质疑,有人反对。力挺者认为,经书里融化了先人对人性、人生的思考与探索,表达了先哲们对真善美的思考;质疑者认为,在生活方式多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今天,“读经”的主张散发出深厚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反对者认为,无论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还是从人的发展角度来审视,都应该反对儿童读经。
自莫言获得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以后,“莫言作品是否进教材”就成了出版界和语文界的热门话题,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理性思考者有之。
周杰伦的《青花瓷》,金庸的《雪山飞狐》能否进语文课本,同样引来争议。
(三) 挑战:《对抗语文》 和 《开明国语课本》 PK语文教科书,受到公众甚至一些学者的热捧
2011年叶开曾因出版作品《对抗语文》,将公众对语文教育长期积累的负面印象激发出来,引发大众关注。2014年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对抗语文,编著了“新版课本”《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叶开曾多次批评当下的语文教学存在的“五宗罪”,那么他的《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能否破解语文教学“五宗罪”,与现行语文教科书PK能否胜出,人们不愿做裁判。但有人认为,该书所选文章有品位、有情趣,可读性强,在浮躁的功利语文时代,对于重建人格、重构精神、开阔视野、滋润学生干渴的心灵起到难以替代的作用。也有人认为,能否称得上中国最好的语文书,衡量的标准应定位在:它是否凸显语文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是否突出语文课程的核心目标——学习祖国语言文字的运用。这应该是我们思考的重要问题。
在小学语文教科书(实验本)受到批评的同时,民国国语读本开始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受到关注和好评的民国国语教材,主要是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于6年前出版的号称影印本的《商务国语教科书》和《开明国语课本》。民国小学国语课本值得称道的,除了它所秉持的儿童本位教育理念,还有它所采用的儿童文学方法。梳理历史,以求借鉴,这对我们反思、纠正现行教材存在的问题是有帮助的;但是有识之士提醒,八十年前的国语课本对于今天孩子的阅读,已显得陈旧和肤浅了。回溯历史,需要我们放出理性的眼光,进行主体性思考,以避免新的迷失。
教材作为学校教育的一根颇为敏感的“神经”,稍有变动就会引来轩然大波。有识之士认为,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教材提出批评、质疑,这都是必要的,反映了人们对母语教育的关注。既然是实验教材,就允许有个实验过程,其长短得失,应当在广泛调查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去认真总结,而那种动不动把当下的教材视为“垃圾”,甚至鼓吹要“对抗语文”的颠覆一切的思路,以及“翻烧饼”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既不能解决问题,还可能制造混乱。
二、部编语文教科书:定格在新课程改革的历史发展与现实背景的坐标中
中小学教育联结千家万户,语文教科书受众广泛,有着广大的读者群体,具有成为新闻事件的基础,社会关注度高,批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某些媒体也拿教材炒作,这也引起了中央的注意。为了贯彻中央的相关指示,2011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稿)》颁布后,教育部出面聘请主编和编写专家,调集了全国最强的编写队伍,经过4年的艰苦打磨,一套全新的、体现国家意志、以主流教科书面目问世的语文教科书“部编本”迎来了美丽的嬗变,为打造特色的语文教科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部编语文教科书在全国发行使用,这无疑是小学语文课程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语文教学走向以提升核心素养为靶向的重大行动。新编语文教科书“新”在哪里?这是人们最为普遍关心的问题。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王本华在《中小学教材教学》撰文,介绍部编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的主要特色与创新之处。一是双线组织单元结构,强化语文学习的综合性和实践;二是重视阅读能力与阅读兴趣的培养,建设“三位一体”的阅读体系;三是选文注重经典性、语文性、适用性、多样化,强调文质兼美,尤其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传承;四是加大课型区分,多层次构建自主学习助学系统,有助于学生自主建构阅读方案,形成阅读能力;五是强调学生自主活动、体验,引导学生在语文综合实践中获得语文能力;六是合理安排各种语文知识,随文学习,学以致用;七是通过各种途径,特别是利用新技术手段,建设开放而有活力的教材体系。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对语文教科书的编写提出了10条建议,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教材观”,随着“部编本”的问世,各种版本的语文教科书经过全面的修订或重编,守正创新,各具特色。
北师大版语文教科书:坚守特色,细致梳理,减负提质;浙教版语文教科书:特色显著,亮点多多;苏教版语文教科书:彰显教材特色,完善教材体系,优化教材风格;湘教版语文教科书:既体现语文的规律和特点,又体现学生学习语文的特点和规律;冀教版语文教科书:以独特的编写思维、鲜明的特点在众多教科书中占有一席之地。
各种版本语文教科书和“部编本”一同投入使用。语文教科书的这种开放的姿态,正在成为语文课程改革的“新常态”。
三、课程标准的实施和语文教科书的开发,促进了对教科书使用的研究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明确提出:“应认真钻研教材,正确理解、把握教材内容,创造性地使用教材。”语文教育界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提出了一些适应新课改、更为全面的教科书使用方法、策略和艺术,使语文教科书的使用开始从“教教材”向“用教材教”转变,从“教本”向“学本”转变。
研究者基于多元视角,从不同层面提出教科书使用的优化方略。
(一) 宏观层面:研究者聚焦“立德树人”的总目标,提出语文教科书必须体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
自2016年秋季起,渗透国家教育改革精神、凝聚多年教学实践成果的部编语文教科书及其他各版本修订语文教科书已在起始年级投入使用。教科书中的新思想、新内容如何落到实处,人们对此十分关注。人民教育出版社陈先云在《小学语文》撰文提出,教好新编语文教科书,需要增强六个方面的意识。一是国家意识。在教学中要充分发挥语文教科书在育人方面的独特价值,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民族团结教育、海洋与国家主权意识教育、法制教育。二是目标意识。教师在理解教材、把握教材时要突破人文主题的桎梏,增强目标意识和语文要素意识。三是文体意识。教学中在教好应用文、记叙文等实用文为主体的基础上,进行初步的文学启蒙教育。四是读书意识。要克服课外阅读边缘化,促进儿童阅读进教材、进课堂、进课程,给学生如何读课外书以全方位的指导。五是主体意识。倡导自主、合作的学习方式,防止语文教学回到机械的、烦琐的语言训练老路上。六是科研意识。要将教材的研究、使用当作一项系统的、长期的工程,把教育科研视作教材使用中的一个重要工作。
(二)中观层面:深刻理解教科书编写的指导思想、体系、模式
要对全套教科书及某一册教科书的编写意图、体例安排、知识结构、选文特点、实践环节、学科综合等各个方面梳理清楚,通晓总体思路,规划教学框架。
“部编本”语文教科书结构上有明显的变化,为避免很长一个时期较为流行的“人文主题”组元或“人文与文体”混合组元带来的不同弊端,新编教材创新设计,采用“人文主题”与“语文要素”(语文知识、语文能力、学习策略、学习习惯以及写作、口语训练等等)双线组织单元的结构。北京大学中文系温儒敏教授在小学语文教科书培训会议上提出,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可以按照新教材的单元顺序来安排教学,但不能拘泥于人文主题,要特别注意语文知识、能力的落实这条线。还要注意把单元中阅读、写作、综合性学习等几方面结合起来。
(三) 微观层面:重点在于如何解读教材、理解教材、处理教材
目前国内小学语文教科书均为“文选型”教材,教科书中的课文一般是名家名篇,语言文字和思想内容都堪称典范,所以要利用好教科书这一范本,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提出“教师应创造性地理解和使用教材”。语文教师应以怎样的视角透视文本并做出相应的教学处理?范国强在《文本解读的多维视角及其教学》一文中提出四点要求。一是作者视角:把准文本的价值取向;二是读者视角:读出自己的独特理解;三是语文视角:凸显学科的本体特征;四是学生视角:遵循教学的基本规律。
杨帆在《语文文本解读的困境和出路》一文中提出,语文教师要想准确进行文本解读,就应树立“一主三辅”的文本解读观,即以文本为主体,以作者原意、编者立意、读者“共意”为辅助,四者共同参与,相互补充,构成准确合理的文本解读标准。
在现行语文课程背景下,语文教师如何运用课文来教语文?
上海师范大学吴忠豪教授提出三点建议:第一,要依据课文合理开发课程内容;第二,要根据学生的特点合理地选择课程内容;第三,依据认知规律有效设计教学流程,其流程应该是“认识领会——实践运用——反思总结”的过程,努力实现从“教课文”到“教语文”转变。
由于新课程的实施,以及新教材的使用,给小学语文教学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之风,无论教学观念如何更新,教材如何变革,对教学来说,深入钻研教材是永恒的要求。语文教师结合教学实践,提出不少建设性的意见。
北京市特级教师,全国著名语文教育专家张光璎,提出钻研教材五步走:第一步,先当“读者”,弄懂文章中的“字词句段篇”;第二步,站在“作者”的位置,从中心思想的高度推敲文章是怎样布局谋篇和遣词造句的;第三步,站在“编者”的位置,理解教材怎么体现课标的年段要求,从识字、阅读再到习作,从贴进“字词句段篇”到学生“听说读写思”等综合能力的提升;第四步,站在“学者”的角度,思考学生的实际,决定教学内容的取舍和教学方法的设计;第五步,从“教者”自身考虑,如何处理好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的关系。
徐凌云在《钻研教材的“四三二一”》一文中,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提出“四点”“三路”“二法”和“一变”钻研教材的策略。“四点”即抓住特点、把握重点、找准难点、剖析疑点;“三路”指的是作者的行文思路、教师的教学思路和学生的学习思路;“二法”即教师的教法和学生的学法;“一变”指的是教师转变教学观念,从素质教育的高度教语文。
有的教师经过反复实践提出解读教材要进入文本——“山是山,水是水”;跳出文本——“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回到文本“山还是山,水还是水”。理解教材要纵横联系,领会意图,把握目标。处理教材要整体入手,兼顾局部,为生成而预设。
有的教师提出钻研教材要“四心”相通,即一要了解编者的心,二要理解作者的心,三要锤炼学生的心,四要体现教者的心。
如何使教材发挥最大的价值,有教师提出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沟通教材、内化教材,并通过教材展开想象,引导学生沟通教材,以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解读教材,使其发挥它最大的价值。
近年来,文本阐释呈现多种视角,什么样的解读是正确的,什么样的解读是越界的,这是许多语文教师一直困惑的问题。有识之士提出,解读可以博广,但拓展必须注意“度”与“界”;解读可以“多元”,但教学应尊重文本价值;解读可以深挖,但教学必须强调“生本”。
四、随时代而改变是语文教科书与生俱来的属性,语文教科书改革“永远在路上”
“部编版”语文教科书是对新课程改革形成的“实验版”语文教科书的继承与创新,体现了时代价值诉求对语文教科书编制的引领。经过4年多的打磨,20轮的评审,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空间。然而,教科书无论如何更新,总是滞后,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有识之士坦言,“教科书内容的选择与修改是典型的无结局性无未来性的,总是可以再选择再修改的,总还有没有选择或没有修改到的”。回顾语文教科书历史变迁,对语文课本的“变脸”或是增删,这个被人称之为“世界级”的难题,从未有停息的时候。语文教科书的改革“永远在路上”。
语文教科书是语文教学之本,是教学的凭借和依据,要充分发挥它的整体功能,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教科书使用上应力求做到:在“守正”基础上“创新”,在“创新”指引下“守正”。
[1]温儒敏.“部编本”语文教材的编写理念、特色与使用建议[J].课程·教材·教法,2016(11).
[2]袁振国.当代国外教学理论[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3]叶开.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M].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
[4]颜禾.对语文教科书使用问题的回顾与思考[J].教育评论,2014(2).
[5]余琴.重唱老调:谈钻研教材[J].教学月刊,2005(2).
[6]陈先云.增强六个意识,教好部编小学语文教材[J].小学语文,2017(2).
(责任编辑:李阳)
戴正兴,江苏省丹阳师范学院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