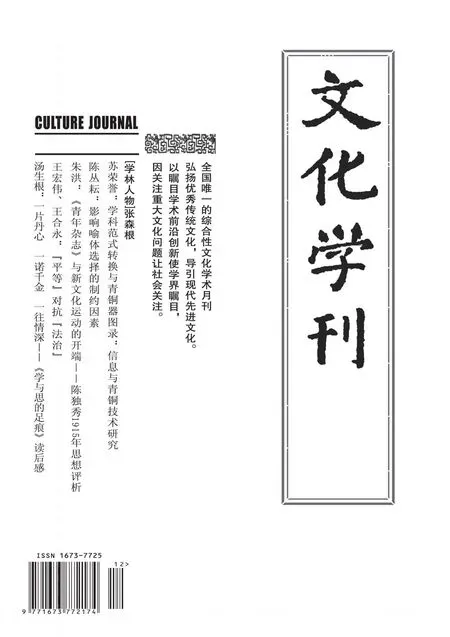钱钟书与徐复观:“比兴”观之异同
2017-03-11张晓晓
张晓晓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0 )
【文史论苑】
钱钟书与徐复观:“比兴”观之异同
张晓晓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0 )
《诗经》自整理成书以来,研究它的人归纳为赋、比、兴三种作法。其中比兴的问题较多,自古以来备受争议。在中国文学史上,很多学者对此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认识,但往往各执己见,难成定论。通过阅读钱钟书与徐复观两位先生的《管锥编》和《中国文学精神》,从兴的“意味”、“兴”之物在何处以及对于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的看法三个方面来分析他们对于比兴的认识。
《诗经》;比;兴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比兴也随之成为中国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给后世文人提供了写作的方法与鉴赏诗文的角度。钱钟书和徐复观两位先生在《管锥编》与《中国文学精神》中对“比兴”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一、“兴”的意味
胡寅《斐然集》卷一八《致李叔易书》载李仲蒙语:索物以讬情,谓之‘比’;触物以起情,谓之‘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颇具胜义。“触物”似无心凑合,信手拈来,复随手放下,与后文附录而不衔接,非同“索物”之着意经营,理路顺而词脉贯。[1]
比,有如比长絜短一样,只有处于平行并列的地位,才能相比。只有经过意匠经营,即是理智的安排,才可使主题以外的事物,也赋予与主题以相同的目的性,因而可与主题处于平行并列的地位。兴的事物和诗的主题的关系,不是像比那样,系通过一条理路将两者连结起来,而是由感情所直接搭挂上、沾染上,有如所谓“沾花惹草”一般,因而即以来形成一首诗的气氛、情调、韵味、色泽的。[2]
钱钟书先生所说的“索物”(比)之着意经营与徐复观先生所讲的意匠经营观点是一致的,都强调作者的深思熟虑、理智安排,从而与作者内心想要表达的感情相契合,突出物体的可比性。“‘触物’似无心凑合,信手拈来”和“由感情所直接搭挂上、沾染上,有如所谓‘沾花惹草’一般”同样强调“偶然的触发”是兴的必要条件,强调感情的直接触发,仿佛诗人的“神来之笔”一般,强调时间的短暂。但是钱钟书先生认为兴的部分与后文没有衔接,不同于“索物”(比)之着意经营,显得理路顺而词脉贯,显然没有关切到兴在诗中的价值和意义。对于徐复观先生而言,认为兴“即以来形成一首诗的气氛、情调、韵味、色泽的”,从而肯定了兴在诗中的作用,暂且称之为“兴”的意味。
钱钟书和徐复观对于“兴”的分歧上,实际上来自于朱熹比兴说的两个方面,只是两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诗》之兴,全无巴鼻。后人诗犹有此体。(《语类》八十)
振录云,多是假他物举起,全不取其义。
比虽是较切,然兴却意较深远。也有兴而不甚深远者,比而深远者,有系人之高下,有做得好底,有拙底。(《语类》八十)
比意虽切而却浅,兴意虽阔而味长。(《语类》八十)[3]
钱钟书先生侧重于“《诗》之兴,全无巴鼻”。在《管锥编》中提到:“徐渭《青藤书屋文集》卷十七《奉师季先生书》:“诗之‘兴’体,起句绝无意味,自古乐府亦已然。”[4]他与徐渭的观点一致,认为起句的“兴”没有意味可言,因此钱钟书先生认为兴“与后文附录而不衔接”。徐复观先生则看重“兴意虽阔而味长”,其实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钟嵘早已认识到兴的意味。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5]徐复观先生同时继承和发展了钟嵘和朱熹的观点,兴在诗歌中是有价值的,表现在它形成了一种氛围弥漫在诗歌中,奠定了全文的感情基调。正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6],茂盛娇嫩的桃花烘托了婚礼当天喜气洋洋的氛围,使人有一种欢乐喜悦之感。另一方面,徐复观认为随着诗人表现技巧的自觉加强以及文学修养的逐步加深,素朴的形式便会演变为复杂的形式。这种素朴的形式是指诗歌中“兴”的位置的改变,代表了诗歌发展的趋势。他认为钟嵘所说的“文已尽而意有余”,虽然“尽”是文章末尾,但是诗歌结尾后兴的意味仍然存在,这不仅增强了诗歌的表达效果,也便于读者体会诗歌的情境氛围。然而诗是感情的触发,不论“兴”的位置在前或在后,对于诗整体蕴味的形成没有任何影响。
二、“兴”之物在何处
钱钟书先生和徐复观先生皆认为“触物”是偶然的触发,那么,此物是眼前之物还是内心之物呢?
项安世《项氏家说》卷四:“作诗者多用旧题而自述己意,如乐府家‘饮马长城窟’、‘日出东南隅’之类,非真有取与马与日也,特取其章句音节而为诗耳。《杨柳枝曲》每句皆足以柳枝,《竹枝词》每句皆和以竹枝,初不于柳与竹取兴也。[7]
钱钟书认为后人对于兴体的运用,仿佛思维定势一般。起初“柳枝”出现的时候,它只是自然界中一种普通存在的植物。偶然在一次特定的场景中,人们折柳送别,进而激发了内心的依依惜别之情,而后世之人纷纷效仿,这种“物象”也就由眼前之物转化为心中之物,即代表特定感情的意象。意象本来就是诗人审美情趣的凝结,饱含诗人的感情,是诗人赋予它情感,使它成为带有主观感情的客体。“昔我往矣,杨柳依依”[8],远征玁狁的战士看到垂柳在微风中摇曳,想到当年远离家乡的场景。徐复观先生侧重于“触物”是眼前的,从前文“兴”的定义中可以看出。但是他并没有否定心中之物对于兴的作用,他认为《关雎》的作者是先有了对于美好婚姻的向往,偶然看到雌雄相恋的雎鸟,由此触发了内心的情感,因此作“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9]。钱钟书先生侧重于《诗经》中的“兴”之物对于后世诗歌的影响,后者侧重于探讨《诗经》中“兴”起之物在文中的本来价值和意义。
三、两者对于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的看法
钱钟书先生和徐复观先生在论述比兴这一问题时都运用了《文心雕龙·比兴》篇,并且产生了分歧。
《诗》文宏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10]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是“兴”即比,均主“拟议”、“譬”、“喻”;“隐”乎“显”乎,如五十步笑百步,似未堪别出并立,与“赋”、“比”鼎足骖斩也。六义有“兴”,而毛郑指目之“兴也”则当别论。刘氏不过依傍毛、郑,而强生“隐”“显”之别以为弥缝,盖毛、郑所标为“兴”之篇什泰半与所标为“比”者无以异尔。[11]
“五十步笑百步,似未堪别出并立,”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刘勰所阐释的比兴,并不存在实质上的差异。而且他对于刘勰强生出“显”“隐”之别,是持否定态度的。徐复观先生认为“附理”之“理”,是由感情反省出来的理智主导着感情的活动。所谓“起情”之“情”,即是感情直接的触发、融合。由此证明他认为刘勰的比兴说是有区别的。两者之所以产生不同的看法,显然也受到了前人观点的影响。
郑玄在《周礼·大师》“教六诗”下注云:
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
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
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12]
从郑康成对于比、兴的定义中可以看出,他用“见今之失”和“见今之美”来区分二者,但是把定义运用到概念中的时候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比如毛传以为《邶风·柏舟》和《邶风·绿衣》是兴,但是前者叹仁人之不遇,后者是庄姜自伤,哪有什么“见今之美”呢?显然自相矛盾,“比显而兴隐”显然是把概念扩大了,却显得模糊。表现在“显”和“隐”之间由于人们认知能力的不同,会存在理解上的偏差。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从这方面来看,徐复观先生没有从整体上进行关照,显然有断章取义的嫌疑。“《三百篇》中如‘匏有苦叶’‘交交黄鸟止于棘’之类,讬‘兴’发唱者,厥数不繁。毛、郑诠为‘兴’者,凡百十有六篇,实多‘赋’与‘比’;且命之曰‘兴’,而说之为‘比’,如开卷之《关雎》是。”[13]《文心雕龙》是以宗经为先旨的,在一定程度上他无法摆脱汉代经学的束缚,很容易使“比、兴”混为一谈,所以他认为《关雎》是歌颂后妃之德。由此可见,钱钟书与徐复观两位先生对于“比兴”的认识,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的,他们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向人们提供了一种认识古代诗歌的思路和方法。
在后世诗歌中,比兴很少以独立的形式出现,而是常常相互融合在一起,二者相辅相成,对于诗歌意境的形成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通过阅读钱钟书和徐复观两位先生的作品,向我们提供了欣赏诗歌的角度。我们应该从诗歌本身出发,深入体会作者所要抒发的情感,以此提高鉴赏诗歌的能力,感悟中国文学的深厚底蕴。
[1][4][7][11][13]钱钟书.管锥编[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110-113.
[2]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22-23.
[3][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 .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2069-2080.
[6][8][9]高亨注.诗经今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8 .96.114.229.
[5][梁]钟嵘著,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19.
[10]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1.324-326.
[12][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Z].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2.796.
I206
A
1673-7725(2017)12-0208-03
2017-10-09
张晓晓(1992-),女,山东济宁人,主要从事宋辽金元文学研究。
董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