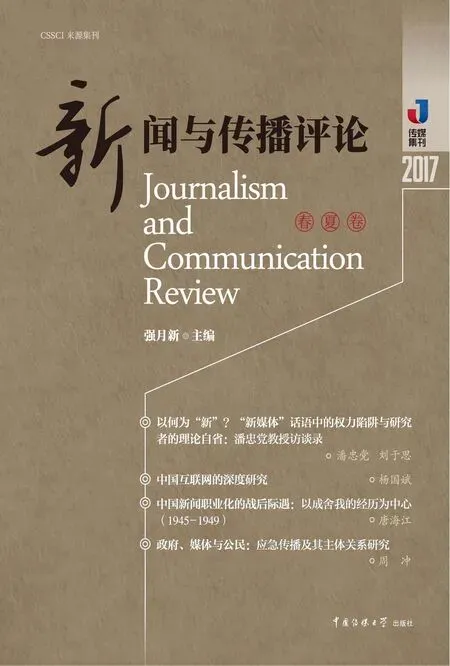公共利益的重新定义:数字浪潮下欧美传播政策的价值重构
2017-03-11◎陈映
◎ 陈 映
公共利益的重新定义:数字浪潮下欧美传播政策的价值重构
◎ 陈 映*
面对数字新媒体的发展以及融合,公共利益作为欧美传播政策价值基础的地位日益显著。在这种背景下,何谓公共利益?它包含哪些基本要素?这些要素在数字浪潮下如何被重构?……这些问题成为欧美传播政策转型与变革过程中争议和讨论的核心议题。有鉴于此,本研究将围绕“政策使命视角下公共利益组成要素的转向与扩充”“政策应用视角下公共利益的重新诠释”以及“政策实现视角下公共利益达成路径的选择”三个问题,探讨数字融合背景下欧美传播政策中公共利益标准在定义、阐释以及路径设计等方面的变化。
公共利益,欧美国家,传播政策,数字融合
一、研究缘起与背景
著名学者伊契尔·索勒·浦尔(Ithiel De Sola Pool)在《自由的科技》(1983:2)一书中曾指出,美国传播领域存在三种不同的政策模式:印刷品政策模式、“共同载体”(common carrier)*“共同载体”是指业者虽然拥有传送媒介内容的管道,但不负责内容的产制,亦无法决定何种内容得以传送。政策模式以及无线广播电视政策模式。事实上,除了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北美和西欧国家以及新西兰、澳大利亚等非西半球的发达国家*本文旨在揭示这些国家和地区变革传媒政策的共同规律与经验。为行文方便,接下来将统一采用“欧美国家”或者“欧美”等整体性概念来指代这些研究对象。本文并不认可“欧美”是一个笼统、均质的概念,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国情、传媒生态和政策路径等方面都拥有种种差异甚至是对立,但它们也具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这些共同或者相似的特征正是本研究得以开展的前提。,其传播系统也都是在这样一套分业管制体系下运转:无线广电媒体*主要包括传统的AM和FM广播电台、VHF和UH频段的电视等。要受到所有权以及节目内容等方面的管制;印刷媒体在言论自由的保护下,“以自愿和个人主动为特征,政府和管理部门几乎不起什么作用”(McQuail,2006:15);通信、邮政和信息技术被归入“共同载体”领域,主要依靠竞争政策进行调适,并且“主要侧重于管理所有权、结构、使用权,并没有关于内容的管理”(McQuail,2006:15);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虽然要受到“必载”(Must-carry)和所有权等规范的约束,但其受限程度也远小于广电媒体。在这套差异化管制体系之下,印刷部门(书籍、报纸、杂志)常常被认为“是一个非政策性的领域”(McQuail,2006:15);以电信政策(telecommunication policy)为代表的共同载体政策将经由其网络传播的内容视为私人内容,长期以来也不归属传媒领域。因此,长期以来,传统意义上的“传媒政策”(media policy)作为一个在价值上与民主政治紧密关联的概念,主要被用来指代无线电广播电视媒体政策,并与主要强调经济价值的“电信政策”一词明确区分。但随着媒介融合的推进,这三大原本相互区隔的政策领域面临着严重的边界冲突问题(Van Cuilenburg & Slaa,1993),并开始日益汇流。在这种背景下,欧美各国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传播政策(communication policies*注意英文使用的是复数,意味着内在政策模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一词,企图将“社会的整个传播系统”(Van Cuilenburg,2009)——既包括“媒体”服务也包括“电信”服务,既包括电子媒体也包括非电子媒体——都纳入进来。
一个日益整合的传播政策体系的逐渐形成,即意味着过往差异化管制体系的崩溃。因此,如何构建一个适用于不同媒体的管制标准成为当下欧美传播政策转型的一个重要问题。过去,广电媒体之所以受到差异化“重度管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稀缺性原则”,即广电媒体赖以传播信号的电磁频谱被认为是一种稀缺的公共资源,管制是为了避免这些资源被垄断、独占或者在使用中相互干扰;二是“影响力原则”,即无线广电媒体以其易得性和强大的渗透力、感染力,被认为是一种遍及且具有入侵性的媒体。这些传统逻辑的起点都是无线广电媒体的科技特性,显然并不适用于卫星电视、互联网等新兴传播媒体*如,在“遍及性”以及“传媒作为入侵者”的逻辑下,欧美国家普遍采用了一种基于时间以及分级播出的内容管制路径,但这种路径显然不适用于那些以非线性、互动以及个性定制为传播特征的新媒体。对于新环境下欧美国家传播管制正当性的消解与重建问题,详见笔者另文:陈映.当代欧美国家广电媒体管制正当性的消解与重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10)。。同时,随着传播资源越来越丰富,“稀缺性原则”已在相当程度上被消解;而自新西兰于1989年以及美国于1993年启用频谱竞拍制度之后,竞争性拍卖也逐渐成为欧美国家频谱分配和管理的基本手段,频谱作为公共物品的理论也开始发生变化。因此,在媒介以及产业间界线日渐模糊的今天,这些传统逻辑已不足以承担重构一个整合性传播政策体系的任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更具共性的问题——传播媒体功能性的达成,即媒体资源(如频谱资源)为何而存在或者媒体作为公共服务的本质是什么——开始成为欧美传播管制的思考起点,体现在具体的传播政策中则是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标准作为政策价值基础的地位日益显著。
事实上,公共利益在欧美传播管制史上并不是一个新鲜词汇。公共利益作为一种超越个体利益和反映社会中所有成员共同利益的公共善,在欧美国家被认为是“政府民主政治理论的核心”(Schubert,1960:7),一直是政府管制尤其是大型、垄断性企业和公用事业管制的正当性基础。传媒作为“教育、协商、统合机制的重要提供者”(Croteau & Hoynes,2006:30),被认为是促进和实现整个社会和政治民主化的关键因素。因此,当无线广电媒体被纳入政策体系,公共利益很快也成为管制正当性的基础,旨在指引传媒培养和提供能够有效参与民主决策的“知情公民”。在过去几十年里,许多国家在核发广播电视频谱执照时,都要求使用者承担相应的公共利益责任。由于内涵和意义的不明确性,这一概念在应用过程中一直面临种种争议、非议与反对,但其在欧美传媒政策和法规中的地位却不仅没有动摇,反而日益显著。如在美国,公共利益这个概念在1934年的《传播法》中出现了11次,而在1996年的新《电信法》中则出现了40次之多(Napoli,2005:70)。不过,从无线广播电视,到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再到互联网,公共利益标准也一直在随着媒介技术的演进与发展而不断地变化、拓展。过去,公共利益标准建立在资源稀缺的基础上,其内容主要由政府以“公共受托人”的身份来界定,并经由频谱资源的分配结构来进行规范;现在,面对以海量、互动、分享、融合等前所未有的传播方式为特征的数字革命,欧美政府“已不能再次依靠追逐利润的渠道商来忠实地扮演受托人的角色”(Lennett,Glaisyer & Meinrath,2012)。在这种背景下,何谓公共利益?它包含哪些基本要素?它到底是谁的利益?在政策设计与决策中应该如何阐释?又应该如何有效达成?……诸如此类问题成为欧美传播政策转型与创新必须要回答的关键问题。
有鉴于此,本文将围绕“政策使命视角下公共利益组成要素的转向与扩充”“政策应用视角下公共利益的重新诠释”以及“政策实现视角下公共利益达成路径的选择”三个问题,来探讨欧美传播政策中公共利益标准在定义、阐释以及路径设计等方面的一些变化,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欧美传播政策的演进与内涵。
二、公共利益内涵要件的转向与扩充:政策使命的视角
公共利益应该由哪些内涵要件构成?这是理解公共利益标准先要探讨的问题。一直以来,公共利益作为欧美传播政策的价值基础,被认为是一个多面向的概念,包括加强自由意见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s)、促进多样性(diversity)、增加市场竞争(competition)、促进本地性(localism)以及确保普遍服务(universal service)等五大内涵要件*对于传播政策中的公共利益标准,美国著名传播政策研究专家纳波里(Napoli)教授提出了一个包含上述五大内涵要件的理论模型。这个理论模型虽然是基于美国广播电视政策的分析而抽离形成的,但事实上,其次级原则及其所包含的内涵同样适用于欧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传播政策分析。如,竞争、本地主义、普遍服务等概念亦频繁地出现在欧洲各国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传播政策文件之中,欧洲各国的传播政策虽然较少使用“diversity”一词,但具有共同指向的“plulism”一词亦是传播政策的一个核心原则,而美国传播政策中“自由意见市场”原则所蕴含的精神亦存在于言论自由、公共领域等欧洲传播政策文件中常见的表述之中。因此,本研究将借用纳波里的这一理论模型来分析公共利益组成要素的变化情况。关于这一理论模型的详细阐述参见Napoli,2005:70。或者原则。事实上,这些原则都是欧美传播政策中存在已久的政策使命,并且至今仍保持着在传播政策中作为永续价值的地位。在数字传播时代,这些原则作为公共利益的要素构件,在传播政策的制定、诠释与应用中愈加频繁地出现;但面对日益融合的传播市场,这些原则显然已无法沿用过往的定义和诠释,并都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了再建构。
(一)自由意见市场:由“供给”市场转向“接收”市场
作为公共利益标准的首要原则,自由意见市场有两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广泛的民意参与以及一个自由、公开的竞争性市场,即公共利益标准的另外两大要素构件——传媒多元化原则和竞争原则。作为一种规范原则,自由意见市场在数字融合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同在:一方面,由于传输渠道增加、市场参进门槛降低以及媒体把关功能弱化等变化,“广泛民意参与”和“自由竞争市场”的实现障碍获得不同程度的清除;另一方面,随着传媒集中、垄断和信息生产同质化问题的日益严峻,传播消费碎片化和分殊化,以及共同讨论机会的日益减少,意见市场的多元性、异质性受到更大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欧美传播政策对于意见市场的理解与阐释明显地由强调“供给”转向强调“接收”。即,在信息极大丰富的背景下,意见市场的主张不能仅仅满足于内容的供给,其意涵还必须隐含着另一个假设:“个人必须能够通过一个理性的评估过程,合理且公平地衡虑所有意见”(Ingber,1984),即公众能够在被充分告知的情况下实现有效的自我治理。而在这一“接受”框架下,所谓的“市场”被扩充理解为“能近用到所有意见的场域,在那儿所有的意见也都能被公平理智地考虑”(Entman & Wildman,1992)。因此,在数字融合时代关于自由意见市场的政策议题已不再局限于意见如何丰富、多元以及市场如何自由、竞争等这些问题,优势或者强权意见的霸权如何避免、“信息的组织分类、过滤和近用的限制”(Balkin,2004)以及如何在不同意见市场之间建立“互连”(interconnected)以减少“协同过滤”“市场区隔”“圈内审议”等问题所带来的侵害,都成为重要议题。
(二)传媒多元化:近用多元问题的凸显
传媒多元化作为公共利益的内涵要件,源自于意见市场“尽可能广泛散布来自多样甚至对立立场来源的资讯”(Associated Press v.United States,转引自Napoli,2005:28)的规定。在当下数字融合不断推进、传媒数量和种类不断增长的背景下,欧美各界有关传媒多元化的争议与讨论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加。但随着传播生态的变化,这一原则的内涵也被重新审视。过往,这主要是一个与表达自由紧密相连的原则,经常被等同于传媒数量多元、传媒种类多元、传媒形态多元、传媒产权多元以及传媒声音多元等概念(陈映,2013a),所强调的只是内容在传送方面的多元,而缺失对内容接受方面多元的诉求(Napoli,2011)。在传媒资源日益丰富和集中的现实下,传媒多元化作为政策原则的诉求已日益从内容传送多元转向内容接受多元。在接受多元的政策诉求下,“数字鸿沟”如何消弭以及公众信息筛选能力和媒介素养提高的问题,即“不同公民近用市场的能力、他们如何参与传媒的生产、他们的声音如何才能被听到”(Bautista,2012)等有关近用多元(exposure diversity)的问题,成为政策的核心议题。因此在数字融合背景下,传媒多元化作为传播政策原则的终极价值已不再是对公民多元需求的满足,而是要提供一个面向社会公共事务的开放、无偏见的论坛,以促进公共意见和社会共识的形成。
(三)竞争原则:成为一个优先原则
公平、有效的竞争被认为是意见市场得以形成并运转良好的一个关键要素。因此,在传媒多元化原则之外,欧美传播政策还普遍聚焦于另外一个冲突性原则:竞争原则。竞争原则的主要政策诉求是要保障传播市场的竞争力和活力。在数字浪潮下,随着传播产业对民众生活以及社会经济全面而持续的渗透,传播产业的融合发展成为一个与民众福祉、产业转型与升级以及提升国家竞争力密切相关的重要议题,而促进传播产业的竞争和发展则成为欧美各国传播政策的优先目标。在这种背景下,竞争原则成为公共利益的优先原则,表现为:经济的发展在欧美传播政策的构建中获得了更多的优先权,自由化、市场化以及私有化成为传播产业发展的主要基调,而具有明显市场经济取向并且主要依赖于市场机制的“管制放松”一词则左右着欧美融合政策转型的整个过程。国家/政府在媒介所有权、频谱分配等经济性管制中的角色逐渐减淡,规管部门更多地从事前管制转向事后管制,各国普遍放松甚至不进行事前的所有权限制,只在掌握了反竞争行为的证据之后才对市场进行介入干预;同时,在市场准进、频谱分配等方面更多地转向市场机制,一般竞争法以及行业的自治在传播管制中的角色也变得越来越重要,等等。
(四)普遍服务原则的演进:内容的扩张与逻辑的转换
作为一个源自电话管制的概念,普遍服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慢慢成为广播及无线电视系统在规范上所重视的问题,并在有线电视的部分管制上得到了应用。不过,虽然电信和广电市场都有普遍服务的原则,但它们在过往分别适用不同的规范。如,在电信市场,普遍服务主要通过基于普遍服务基金的业者分摊制度来推行;在广电领域,普遍服务在许多国家都是通过建立一个公共媒体(public service brocasting,PSB)或者必载规范来实现的。现在,数字融合以及随之而来的政策融合打破了普遍服务在电信和广电市场上的区分,使不同领域的普遍服务概念渐趋融合。在这种背景下,欧美传播政策在普遍服务规定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在政策工具的采用上,越来越强调对新技术和服务的包容性和接纳性,强调普遍服务可以通过任何传播网络来提供,从而使得网络中立日渐成为普遍服务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其次,传统广电政策领域的普遍服务目标主要是通过内容规制(如必载规定)或者传媒结构规制(如公共广播电视制度的设立)来实现的。但在全网IP化、数字化以及信息传播打破载体限制之后,传播网络的接入(access to networks)问题在普遍服务政策的构建中也变得日益重要;最后,在媒介无处不在的背景下,如何消弭基于信息接收多寡而形成的数字鸿沟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如何“把人们带向技术”,即公众信息素养和媒介素养的培养问题,成为各国创新普遍服务制度的刻不容缓的议题。
(五)本地性原则的艰难“复兴”:定义、话语框架与政策路径
在伴随数字化而来的全球化浪潮之下,强调传播服务于社区需求和利益的本地性原则也已到了“需要彻底重组或到完全抛弃的地步”(Napoli,2005:24)。本地性原则从一个基于“空间”的概念转变为一个更加“社会性的概念”,内容本质即特定内容是否能够彰显所代表社区的利益以及在文化、价值和政治上所共享的兴趣和观念,成为本地性相关政策的思考起点。不过,尽管“本地”概念的高度语境化、个人化特征获得普遍承认,但对于什么是“本地的”这一问题,各国依然没有统一答案;同时,在内容维度下,“本地”概念定义的准确性和可操作性又成为各国传播政策制定与实施中的难题。因此,虽然各国都认为“在这个数字时代,本地性原则的恰当定义可能不同于过往时代的定义”(Ali,2013),但最后都还是落到了基于“空间”的定义上面。在采取何种政策工具、何种政策路径来满足本地服务要求这一问题上,地方媒体系统的健康发展无疑是一个核心议题。而在这一议题下,地方媒体的所有权问题、本地公民的参与问题以及地方观点的多元化问题等备受关注。同时,“危机”成为各国共识的一个话语框架,而诸如地方媒体的生存困境、本地新闻的数量缩减等现象或问题,则是相关讨论的前提。与“危机”框架相对应,“如何化解”成为欧美各国有关本地性原则的争议最为激烈的一个议题。在这一议题下,数字新媒体能否承担起服务本地市场和需求的问题成为讨论的焦点。但综观欧美各国的最新政策,落实本地性原则的任务仍然主要落在无线广电媒体身上。同时,欧美各国也依然主要依赖商业媒体来实现这一原则,这又不可避免地把“本地”转换成一个“众多同质消费者的组合体,只不过这些消费者聚居在一个特定的空间”(Ali,2013)。
三、公共利益诠释的争议与特征:政策应用的视角
在讨论完公共利益的基本内涵构件之后,接下来要回答的是:公共利益在欧美传播政策过程和实践中该如何诠释、应用才能最终有效地达成?即,在实施传播政策时,哪些类型的社会需求应该被认为代表公共利益的要求?而在新媒体环境下,哪些需求是最亟待解决的?
(一)公共利益诠释的语境化特征
对于公共利益标准的政策应用,欧美各国的争论聚焦于是否要制订有关公共利益标准的具体细则这一问题上。以美国于1998年成立的数字电视公共利益责任总统咨询委员会(Presidenti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Public Interest Obligations of Digital Television Broadcasters,PIAC)的相关讨论为例,赞成者认为只有制订有关公共利益标准的细则,“才能使得这些准则确实有效,也才能对媒体行为做出有效评价”;但反对者认为,细则化操作导引的做法“并不符合数字媒体时代的多元化景观”(PIAC,1998)。最后,一个“最小化的公共利益要求”获得认同,即公共利益标准应该“不给数字媒体增加任何不必要的负担”,同时“适合广播、有线、卫星等所有的传媒领域”(PIAC,1998)。因此,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哪些要求可以或者应该被纳入这个“最小化的公共利益要求”之中。对于这一问题,目前暂无一个统一的答案。如,美国的总统咨询委员会在经过多次讨论之后,提出将提供社区服务*指数字媒体应该努力寻找并发现共同体的需求与利益,并在其节目中反映这些利益与需求。、提供公共服务报告、发布公共服务声明、播出公共事务节目以及为听力障碍观众准备字幕等内容作为电视公司取得数字电视执照的要求(PIAC,1998)。而英国媒体改革统筹委员会又更多地是从传媒多元化角度出发来构建公共利益标准体系的。如规定报纸媒体兼并时对于公共利益主要要考量两点:一是新闻报道的准确性以及观点的自由表达;二是每一个市场的报纸都要提供足够多元的观点*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edia Reform (CCMR).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interest.[EB/OL].(2011-11-04)[2014-03-12].http:∥www.mediareform.org.uk/wp-content/uploads/2013/04/The-media-and-the-public-interest.pdf.,等等。
因此,对于何谓公共利益,其实并不存在一个可以清楚、明确勾画出来的项目表。欧美各国对于公共利益的言说其实是高度语境化的。谁在言说?言说对象是谁?以及,在什么样的政策使命或者政策目标下来讨论?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并界定了有关公共利益的细则化表述。不过,仔细观察欧美各国对于公共利益标准的政策阐释和应用,依然可以发现:欧美传播政策中的公共利益标准始终都是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在处理。
(二)公民vs.消费者:“公共”是谁?
“‘公共’是谁”是欧美各国共同关注的第一个问题。即这个“利益”到底是谁的利益?是公众抑或产业,或者国家的利益?在欧美国家,虽然由于“管制俘虏”等问题的存在,政策的最后结果有时会将“公共利益”转变为“产业利益”或者“国家利益”,但在政策目标以及应用设计阶段,“公众”毫无疑问是其最主要的目标指向。因此,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公众”是谁?对于这一问题,检视各国传播政策可以发现,它们对“公众”一词的阐述至少包含两种理论范式的解释:一是基于民主理论的“公民”概念;一是基于经济理论的“消费者”概念。因此,在很多时候所谓的公共利益也就被分解为“公民的利益”和“消费者的利益”两大块。如,英国2003年的传播法开篇便明确规定Ofcom的职责有二:一是增进公民在传播事务方面的利益;一是通过促进竞争的方式,增进消费者在相关市场*即Ofcom管辖的所有服务、设施、设备或者目录市场。的利益。虽然美国的新《电信法》开篇即表明要“确保美国消费者以更低廉的价格获取更高质量的服务,同时鼓励新传播科技的迅速部署”,而并未明确使用“公民”概念,但在有关的政策讨论和修订中,“公民”一词亦是频频出现。同时,回溯近几年各国对有关传播政策的阐释和应用亦可发现,其对公共利益概念的理解和应用其实一直是在“公民的利益”和“消费者的利益”之间来回较量与平衡。对于两个概念在公共利益概念范畴下的关系,各级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普遍强调这是“一个整体”(Carter,2003),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但批评人士则揭示出了“公民的利益”和“消费者的利益”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如,Ofcom的前主席大卫·卡瑞(David Currie)曾在一场演讲中宣称,在目前这种管制放松、市场机制为主导的政策路径下,“公民利益不过是市场在满足了消费者利益之后所剩下的东西”(Currie,2003)。
(三)想要vs.必须要:什么是“利益”?
在“公共”一词以及由之而来的“公民”与“消费者”两个概念间的紧张关系之外,“利益”一词也一直是公共利益标准在阐释和应用中模糊性的又一根源。在资源稀缺且以线性传播为主的模拟时代,所谓的利益很多时候被界定为“无信号干扰”“多姿多彩的节目”“家庭所有成员都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对地方公共事务的讨论”“少儿以及弱势群体的保护”以及“公民知识或者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的获得”等条款。而在这些条款的表述中,选择权、知情权、表达权等概念无疑是“利益”一词的核心。在这个以丰富、互动、个性化等为特征的数字化传播时代,这些“利益”指向中的很多规定依然适用,但检视欧美各国近年来有关传播政策的文件或讨论便可发现,数字时代所强调的“利益”已或多或少地发生改变,公众(或消费者)对媒介的近用权利、近用能力以及互连、透明等内容亦被纳入进来。如,在传播技术从模拟时代迈进数字时代之后,对于“利益”的强调则更多地从过往的“无信号干扰”“频谱的合理分配”等内容转向“降低市场准进门槛”“网络中立”“相同服务,相同管制”等主张,即一个公开、公平、透明的市场竞争环境;在资源从稀缺到极大丰富之后,“多姿多彩的节目”“消费者的多样选择”等主张逐渐被“近用大众媒体的机会”“消费者的信息筛选能力”“公民的参与”“规模经济与市场公平竞争”“所有权多元”“地方性媒体系统结构性的健康发展”等主张和问题所取代;而在互动传播模式代替了过往的线性传播模式之后,“公众在充分告知下的自我治理能力”“不同公民近用市场的能力”等“接受”面向的议题也逐渐被纳入“利益”的范畴。因此,“利益”其实也是一个说不清、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
总体而言,对于什么是公众或者消费者的“利益”这一问题也存在两种阐释方式:一种是把“利益”解读为兴趣,认为“公众的兴趣即定义出公共利益”(Fowler & Brenner,1982),而“一个大多数听众感兴趣的节目就是这个节目公共利益的最好体现”(McLaren,2003);另一种则认为“公共利益并不总是等同于那些公众感兴趣的东西”(ICO,2013)。如,在2007年英国卫报集团和美国自由撰稿记者布鲁克诉英国信息委员会和BBC一案(Guardian Newspapers Ltd.and Heather Brooke v.the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 and th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中,英国资讯法庭(Information Tribunal)便曾明确指出,“对公众而言是有趣的与(那些)作为公共利益必须要知道的(东西)之间有很大不同”(ICO,2013)。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利益观经常交叉甚至同时出现在欧美传播政策中,但事实上前者主要是把“公共”理解成“消费者”,而把消费者的利益理解为消费者想要拥有的(want)东西,其实质是消费者主权;而后者则是更多地从“公民”这个视角来理解的,因而所谓的“利益”就是公民必须拥有的(need),类似于一种“有益品”(merit good)。因此,正如Ofcom战略和市场发展部(Strategy & Market Developments)的理查兹(Richards)所指出的:“消费者视角下的公共利益聚焦于消费者的想要的东西和个人的选择;而公民视角下的公共利益则主要指的是为社会长远发展所带来的好处,而不是个人的短期利益,如文化、认同、学习、参与等所带来的‘更广泛的社会利益’。”(Richards,2004)
因此,公共利益概念在欧美传播政策中的应用一直是混乱的、复杂的。在数字环境下,欧美国家一直希望在“公民的利益”和“消费者的利益”、“有趣的”和“必要的”、“个人的”和“社会的”、“长期的”和“短期的”等矛盾关系间建立一种有效的平衡机制。但事实上,面对技术发展、市场竞争、产业效益、国家发展等种种更为显见的压力与诱惑,欧美各国的传播政策更倾向于从“消费者”角度,而不是从“公民”角度来定义“公共利益”;同时,更倾向于把“公共利益”解读为“通过市场力量就能够获取的东西”(陈映,2013b)。
四、公共利益达成路径的演进:政策实现的视角
即使“何谓公共利益”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也依然存在一个问题有待讨论:在数字融合时代,公共利益如何才能有效达成?围绕这一问题,欧美传播政策的以下动向值得关注。
(一)管制放松:传播政策的“自由化、市场化与减少管制”转型
面对传播技术以及市场的变化,欧美各国政府纷纷从那些涉及市场发展的管制领域撤出,各国普遍掀起一股放松传播管制的浪潮。简而言之,这股放松传播管制的浪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结构管制方面,更多地从事前管制转向事后管制。放松对传媒所有权以及跨媒体所有权的限制,只在掌握了反竞争行为的证据之后才对市场进行介入干预,已成为欧美传播政策的一个明显而普遍的变化。同时,各国还纷纷通过调整或改革频谱分配制度和机制、网络基础设施政策等来构建一个开放、弹性的市场机制,并简化市场准进管制程序,降低市场准进门槛。如,在频谱的分配方面,更多地引入市场力量,包括采用竞争性拍卖的手段来分配频谱资源;允许频谱资源进入次级市场进行交易,从而使得新服务的提供者不再受限于进入市场的时机;以及,逐步放宽甚至解除对频谱用途的限制,让频谱与媒体执照之间适度脱钩,等等。
其次,一些早先建立的内容管制体系遭遇瓦解。以美国为例,其在1981年取消了广播商们对其节目和广告内容进行自我检查的自律机制;在1984年取消了20世纪20年代所确立的一条重要条款:广播商必须到达广大公众,寻找并发现这些共同体的需求,在节目中反映这些需求;在1987年甚至废除了著名的公平原则(Fairness Doctrine),等等。时至今日,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在传统广电领域的内容管制已遭遇大规模的削减,仅仅剩下本地节目、儿童保护等为数不多的责任条款*如,波顿基金会(Benton Foundation)在一份发表于2005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现在美国传播政策中保留下的内容方面的责任条款仅仅剩下以下8个项目:1.大量的非特定的本地节目;2.每周三个小时的适于儿童观看的教育和信息节目;3.加入V-chip分级系统(V-chip ratings system);4.禁止在儿童可以看到的时候播放不雅节目;5.禁止所有的香烟广告以及在儿童节目时段限制广告的数量;6.为政治候选人提供特别的近用;7.在公民或团体受到攻击时,为他们提供捍卫自己权利的机会;8.为听力或视力有障碍的人群提供近用权利。。
最后,随着传播资源的日益丰富以及公共广电媒体收视率和市场占有率的下滑*如,英国BBC 1982年的收视率为38%,2003年下滑至23.3%。,公共广电系统的存在价值也开始受到质疑。一些反对者宣称,“那些旨在捍卫社会价值内容的干预还不如直接资助内容的生产商,而不是公共媒体”(Kafle,2011)。这些挑战和质疑反映到传播政策中,则体现为各国在市场公平名义下对公共媒体与商业媒体利益的平衡以及在管制中更多地引入市场的工具。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不少国家开始允许公共电视台以播出商业广告作为补充收入。而进入21世纪以后,公共媒体公共经费的削减也提上了政策的议程。放眼未来,“包括执照费、国家捐赠补助、税收、广告、赞助,特别是随选频道的计次收费服务,或是销售书籍、光盘等”(Bron,2010)在内的一种混合式的经费模式已逐渐成为各国公共媒体发展的支撑。
(二)再管制:新规则、新手段与新方法
在放松管制的同时,传媒集中与垄断对公共利益的可能危害引起了欧美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在这个以互动、融合为特征的新传播环境下,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管制显然已变得缺乏弹性且容易产生副作用。因此,围绕“如何在市场与竞争以及在自由与管制之间寻得平衡”这一问题,欧美各国近年来展开了一场“再管制”的改革运动。
首先,面对数字融合对过往的分业管制体系的冲击,网络中立原则及其所包含的透明性、互连性和非歧视性等要求逐渐成为欧美各国在基础设施管制方面的重要原则。而确保“竞争者及潜在竞争者得以在无差别待遇的情况下,开放近用既有主导业者的传播通讯基础设施”(罗世宏,2004)则成为各国传播政策变革的一个核心任务。同时,频谱分配、交易的市场化以及频谱使用的自由化成为各国频谱政策的主要方向。各国纷纷建立并且创新频谱资源的拍卖制度,探索建立频谱租借和共享机制;探索实行频谱执照与业务相脱离的办法,允许有执照者改变原许可所设定的技术、应用限制,甚至将所获许可的频谱资源进行租借或转售;同时,建立闲置频谱资源回收机制,促使部分执照尚未到期但目前闲置未用的频段能够回收,重新分配给其他业者。
其次,面对数字融合对所有权集中可欲性的刺激,以及对数字浪潮下经济、技术发展以及国家竞争力等经济利益的考虑,各国纷纷调整或改革了传统的所有权管制路径:其一,探索改变对相关市场的定义以及有效竞争的测量方法。如,欧洲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传媒产权限制的测量指标建设方面,由原来对一个公司所拥有的传媒数量的考量转向对受众份额的考量,而在2002年的时候,更是转向对广告市场份额(advertising market)的考量;其二,更多地依赖作为事后管制机制的一般竞争法。其三,为弥补竞争法在确保传媒多元化以及传媒服务于公共利益方面的不足,引进基于逐案判断的公共利益测试方法,同时在所有权多元这一问题上,更多地考虑内容多元、公众对传媒的近用等问题,而不是仅仅考虑谁拥有或谁控制媒体这个问题。
最后,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全球化和网络化的压力以及对内容失控的恐惧,欧美国家又呈现出一股较为明显的“内容再管制”(刘昌德,2006)趋势。如,美国曾先后出台《儿童电视法》*美国从1990年开始施行《儿童电视法》(the Children's Television Act of 1990),该法要求在白天播放的儿童电视节目中有相当程度的教育内容。《传播净化法案》等多部内容管制法案。同时,1992年《有线电视法》和1996年《电信法》也同样包含对节目的控制和限制条款。不过,在市场自由化、商业化以及新媒体去中心、平权化发展的背景下,这种带有明显干预色彩以及集权特征的内容管制路径在欧美社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抵制*如,美国于1996年出台的《传播净化法》最终以美国最高法院作出《传播净化法》违宪的历史性判决告终 ;美国随后出台的《儿童色情保护法》(Child Pornography Prevention Act)、《儿童网络隐私法》(Child Online Privacy Act)和《儿童在线保护法》 (Child On-Line Protection Act)等多部以互联网内容为管制对象的法案,也全部无一例外地受到依据第一修正案的质询和挑战。。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欧美国家开始探索从直接的内容监控转向建立一种基于技术以及行业自律的内容管制体系。例如,在《儿童在线保护法》被判无效之后,美国国会又于2001年出台《儿童互联网保护法》,强调通过过滤软件来屏蔽属于淫秽或儿童色情的图像,并且防止未成年人获取对其有害的材料。因此,在价值逻辑和市场逻辑之外,技术逻辑也正在成为重塑公共利益标准的一股重要力量。
(三)非商业的力量:一种超越“所有权—内容”路径的整体思路
数字融合的发展给欧美新闻业带来了一场前无未有的生存危机:一方面,过往新闻业所倚重的重要舞台——报业、广播电视业等传统媒体均面临受众、广告等节节下滑的严重挑战;另一方面,数字新媒体的商业模式仍不明朗。面对这些挑战,一种超越既有商业模式以及“结构—内容”管制路径的公共利益实现方式正浮出水面。一是结构管制的思路开始从商业媒体内部的结构平衡问题转向整个传媒生态结构的构思与调整问题。在这一转向下,“商业媒体和非商业媒体这‘价值生产’的两端之间关系的重构”(Bollier,2002),开始成为思考“公共利益如何达成”这一问题时的一个重要抓手。公共广播(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PSB)是否应该扩展到公共媒体(public service media,PSM)?基于慈善基金、社会捐赠、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 (low-profit 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tion,简称L3C)、传媒雇员所有制(Worker-owned media)等形式的非营利媒体,在促使媒体回归和服务公共利益方面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政策的重要议题。二是在市场与政府之外,公民(或者消费者)自身以及作为中间结构的公民社团、NGO等非政府力量在秩序构建中的作用被强调。如,在阿斯彭(Aspen Institute)关于新媒体环境下的公共利益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英国著名学者阿萨·布里格斯(Asa Briggs)提出,“新媒体环境下的公共利益标准应该建立在‘互联网自身的用户驱动和自治原则’之上,在互联网持续发展和变化的同时,支撑性的传播渠道和内容的建设也应该被纳入公共利益的范畴”(Bollier,2002)。因此,面对公共利益达成路径如何优化的挑战,一个“市场—国家—社会—媒体”合作的多中心治理结构成为理想的传播政策。而在这种多中心治理的基本语境下,欧美国家开始向治理共同体转型,政府的角色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冲击而弱化,而公民以及公民团体等第三部门的价值,尤其是作为受众的公民(或消费者)的“自我赋权”能力得到了强调。正如Ofcom的首席执行官卡特所强调的,“今天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正在被赋予更多的权力。数字电视、互联网以及越来越普遍的宽带都给了用户更多的选择。作为一个管制者,我们要反映这个(变化),并且欢迎和鼓励它。管制者再也不能决定……人们‘应该’要什么”(Carter,S.,2013)。因此,在欧美传播政策关于公共利益达成路径的设计中,类似“自我管制(self-regulation)”“共同管制(co-regulation)”“有管制的自律(regulated self-regulation)”或者“受监督的自律(audited self-regulation)”等在市场与政府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日渐浮现。
结 语
综上所述,对于数字环境下传统公共利益标准的不适合性,欧美各国普遍已达成共识;但对于数字环境下的公共利益标准到底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应该如何实行等问题,欧美国家还没有找到一个广为认同的答案。不过,对于“何谓公共利益”这一问题,欧美国家的政策讨论和实施始终围绕着以下几个问题在处理:一是公共利益作为一种公共善,是与传媒服务于政治的终极目标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即使是在放松管制的浪潮中,对于公共利益的诉求和强调也都不能削弱;二是欧美国家很多时候都把公共利益视为一种“市场失灵”,即将之看成是一个与“竞争”“市场”等经济性概念相对立的价值性的概念,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又往往依赖市场机制来实现公共利益的目标;三是欧美传播政策对于公共利益的讨论和政策设计,自始至终都是在“公民vs.消费者”“市场vs.干预”“放松管制vs.再管制”等各种矛盾、紧张关系中进行的;四是“自由和管制的创造性结合才能为传媒和传播领域的公共利益保护提供最坚实的基础”(Collins & Murroni,1996:16),这几乎已成为各国的普遍认识。因此,面对数字化的挑战,欧美传播政策的转型实际上是在国家干预主义和自由经济主义之间寻找折中方案,但在全球竞争、经济增长等技术资本主义话语下,又不可避免地在本质上和“市场”相连。因此,要简单地说清楚欧美传播政策的公共利益标准是什么,以及这一标准在数字化背景下将何去何从,恐怕不是一件易事。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公共利益标准具有模糊性和流动性,但一直以来都是欧美传播政策中较为普遍认可的标准和原则。在因应数字融合挑战而构建新型传播政策的过程中,对于“为何规制”以及“公共利益到底为何”这两个问题,欧美各国政府也进行了大量的政策评估与征询工作。因此,“为什么”的问题,即政策价值的问题,其实是欧美传播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的、根本性的问题。当前,面对日新月异的传媒科技,我国的传播管制体系也在经历着一场调适与变革运动。面对快速更新与发展的传播技术与市场,如果没有一套价值的指引,只是“以片断琐碎方式个别因应每一项政策或科技,则会导致不一致且未经整合的决策数量的增加”(Napoli,2005:3)。因此,在推进三网融合以及传媒产业转型与升级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先解决好媒体性质、媒体功能等根本性问题的认知问题,并进而发展出一套能横跨不同媒介、产业且兼具适应科技发展之弹性的基础原则与价值体系。
陈映.传媒多元化意涵:政治、经验与规范三个维度的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13(1):109-116,124.
陈映.美国传播政策中的公共利益标准:概念的表征及演进[J].国际新闻界,2013(10):65-76.
陈映.当代欧美国家广电媒体管制正当性的消解与重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10).
刘昌德.台湾商营电视节目内容管制的演变:结构去管制下的“内容再管制”[J].广播与电视,2006(26):77-116.
罗世宏.开放近用、有效竞争与公共利益:宽频视讯服务市场的管制架构[J].新闻学研究,2004(78):107-142.
MCQUAIL,D.媒体政策——夭折?[M]∥霍华德·裘伯.传媒政策与实务.昝廷全等,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NAPOLI,P.M.传播政策基本原理:电子媒体管制的原则与过程[M].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
ALI,C.Where is here? an analysis of localism in media policy in three western democracies[D].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BALKIN,J.M.Digital speech and democratic culture:a theory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f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J].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2004,79(1):1-58.
BAUTISTA,M.F.Mapping“diversity of participation”in networked media environments[EB/OL].(2012-11)[2013-12-22].http:∥www.umass.edu/digitalcenter/research/working_papers/12_001_Fuentes_MappingDiversityOfParticipation.pdf.BOLLIER,D.In search of the public interest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a report of the Aspen institute forum on communications and society[EB/OL].(2002 )[2013-08-06].http:∥www.aspeninstitute.org/sites/default/files/content/docs/cands/PUBLICINTEREST.PDF.
BRON,C.M.Financing and supervision of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R].IRIS Plus report of European Audiovisual Observatory,2010.
CARTER,S.Speech:the communications act:myths and realities[EB/OL].(2003-10-09)[2014-02-25].http:∥media.ofcom.org.uk/speeches/2003/the-communications-act-myths-and-realities-thursday-9-october-2003/.
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edia Reform (CCMR).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interest[N/OL].Preliminary briefing paper.(2011-11-04)[2014-3-12].http:∥www.mediareform.org.uk/wp-content/uploads/2013/04/The-media-and-the-public-interest.pdf.
COLLINS,R.& MURRONI,C.New media,new policies[M].Cambridge:Polity,1996.
CROTEAU,D.& HOYNES,W.The business of media:corporate media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M].(2ndEd).New Delhi:Pine Forge Press/Sage,2006.
CURRIE,D.Speech to the English National Forum Seminar[EB/OL].(2003-07-07)[2014-01-18].http:∥media.ofcom.org.uk/speeches/2003/english-national-forum-seminar/.
ENTMAN,R.M.& WILDMAN,S.S.Reconciling economic and non-economic perspectives on media policy:transcending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2,42 (1):5-19.
FOWLER,M.S.,& BRENNER,D.L.A marketplace approach to broadcasting regulation[J].Texas law review,1982(60):207-57.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ICO).The public interest test: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R].Report of ICO.20130305 Version 2.
INGBER,S.The marketplace of ideas:a legitimizing myth[J].Duke law journal,1984,2(1):1-91.
KAFLE,T.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a paradigm shift to public service media[EB/OL].(2011-08-28)[2014-05-12 ].http:∥www.academia.edu/518713/Public_Service_Broadcasting_A_Paradigm_Shift_to_Public_Service_Media.
LENNETT,B.& GLAISYER,T.& MEINRATH,S.Public media policy,spectrum policy,and rethinking public interest obligations for the 21st Century[EB/OL].(2012-06-01)[2013-10-05].http:∥www.current.org/wp-content/uploads/2012/08/Public-Media-Spectrum-Policy-New-Am-Fndn-June-2012-pdf.pdf.
MCLAREN,C.A.Brief history of the public interest standard[EB/OL].(2002) [2014-04-22].http:∥www.stayfreemagazine.org/ml/readings/public_interest.pdf.
NAPOLI,P.M.Exposure diversity reconsidered[J].Journal of information policy,2011(1):46-59.
Presidenti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Public Interest Obligations of Digital Television Broadcasters(PIAC).Charting the digital broadcasting future.Final report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public interest obligations of digital television broadcasters.Washington,D.C.December 18,1998.
POOL I DS.Technologies of freedom[M].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Richards,E.Speech to Westminster Media Forum on the Ofcom review of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EB/OL].(2004-05-25)[2014-03-14].http:∥media.ofcom.org.uk/speeches/2004/speech-to-westminster-media-forum-ofcom-review-of-public-service-broadcasting/.
SCHUBERT,G.The public interest: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a political concept[M].New York: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60.
VANCUILENBURG,J.& SLAA,P.From media policy towards a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policy:broadening the scope[J].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3,8(2):149-76.
VanCuilenburg,J.On competition,access and diversity in media,old and new:some remarks for communications poli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J].New media & society,2009,1(2):183-207.
RedefinethePublicInterestStandard:TheValue-establishmentofCommunicationPolicyinWesternCountriesintheDigitalEra
Chen Ying
With the rise of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media convergence,the public interest as the golden rule has gained ever more salience and become the primary rationale of communication policy in western countries.But the public interest as a concept with so much fluidity and ambiguity has yet never been clearly defined.So questions such as how the concept can be redefined,what ingredients the standard contains and what changes have happened to these ingredients with digital revolution,are with great concern in western countries.This paper researches on the transition of public interest standard through focusing on three questions.Firstly,what the changes are of ingredients of pablic interent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mission.Secondly,how public interest is redefined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application.Thirdly,what choice are made to achieve public interest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achievement.
public interest,western countries,communication policy,digital convergence
* 陈映,新闻学博士,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与新媒体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传播规制与政策。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厅2014年创新强校重大科研项目之创新特色(人文社科)项目“多媒体融合的规制变革与政策体系研究”(2014WTSCX119)、广东省优秀青年教师计划资助项目“基于未成年人保护的网络内容规范与治理研究”(YQ2015120)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