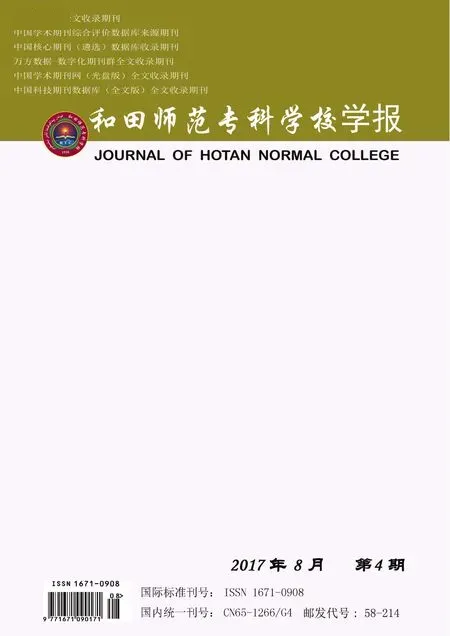论左思诗歌创作对汉魏风骨的继承
2017-03-11陈祥伟
陈祥伟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系,江苏 南通 226019)
论左思诗歌创作对汉魏风骨的继承
陈祥伟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系,江苏 南通 226019)
初唐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说:“汉魏风骨,晋宋莫传。”这一论断与客观实际不符。左思是西晋诗人,其代表作《咏史诗》八首批判了压抑人才的门阀社会,抒发了个人的怀抱,语言刚健有力,运用了比兴寄托的手法,具备了“汉魏风骨”的特点,是对“汉魏风骨”的继承。
左思;咏史诗;风骨;建安风骨;汉魏风骨
初唐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在这篇序文中,陈子昂为了反对齐梁以来片面追求声律、对仗和词藻等形式之美而忽视充盈之内容的浮靡诗风,提出了恢复汉魏风骨的主张。这本无可厚非。但他认为晋宋两朝的诗歌创作也没有继承汉魏风骨,这就有失偏颇了。晋代大诗人左思的诗歌创作就明显具备汉魏风骨。
一、“风骨”内涵辨析
在论证左思诗歌创作具备汉魏风骨之前,我们先要分析 “风骨”这一概念所具有的内涵。
自刘勰在文学批评领域首倡风骨论之后,学界对“风骨”内涵的理解就见仁见智,难有定论了。代表性的观点如周振甫先生认为“风”是指作品内容上的美学要求,要求内容的骏爽。有了风这个美学要求,才能感动人。“骨”是对文辞的美学要求,要求文辞的端直;[1]詹瑛先生认为“‘风’是属于感情方面的”,“‘骨’是属于内容方面的”;[2]叶嘉莹先生认为“风”当指一种感动的力量。“骨”应该是以内容情意为主,以作品之结构为辅所形成的。[3]他们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借鉴。本文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刘勰《风骨》篇中的理论部分和所举实例,对“风骨”的概念进行辨析。
关于“风”字,刘勰解释说:“《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4]对此,叶嘉莹先生评曰:“如果从《诗经》六义来解释‘风’字,则其意自当以‘感化’为主。不过当‘风’字普遍用于一般文学批评之时,则其含意便已经不限于六义的政治教化的感化之意,而应该有着更为广义的‘感化’之意了,这种‘感化’实在应该兼指外物与作者心灵间相触发的一种感动,与作者表现于文字中的一种足以读者感动之力量而言”[5]将“风”释为感动的力量,可以说是揭示了“风”这一概念的本质内涵。但“风”只是作家“志气”在作品中的符契,符契即表征。关于“气”,范文澜注云:“本篇以风为名,而篇中多言气。《广雅·释言》‘风,气也。’……《诗大序》‘风以动之。’盖气指其未动,风指其已动。”[6]“未动”指藏于作者内心。“已动”指表现于作品。此处“志”字,结合下句“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当指感情。故“风”乃是作者感情与感发力量的统一体。所以刘勰又说:“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情”与“风”之间是内在本质与外在表现的关系,是一体之两面。
那么什么样的感情才具备感动人的力量?所谓“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7],通常来说,哀怨愁苦的感情更容易打动人心。刘勰所言“怊怅”,就是指一种怨恨失意的感情。但在刘勰看来,具备“风”的感情并不局限于哀怨之情。我们且看其所举之例:“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相如上《大人赋》,本以讽谏武帝好神仙之事,而武帝读后反飘飘然有凌云之气。在赋中,相如描写了大人因不满人生短促而驾龙遨游四方,与仙人交游,场面阔大,气势飞扬,极尽游仙之乐。由此可见,但凡能移人心志,即使是欢愉的感情,也是含“风”的。故刘勰的“风”,对于何种感情,并没有固定之指向,只要能具备真正的感动人心的力量,就是有风力的作品。
关于“骨”字,刘勰解释说:“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他将“骨”与“辞”并举,表明“骨”并不单纯地就是文辞。就像身体依附骨骸才能直立,文辞也必依附“骨”才能成篇,则“骨”实在应该指文章的内容和结构。而内容与结构又要依靠文辞来表现,所以刘勰又说:“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端直”是对文辞的要求,“写文章的时候,要说真实而正确的话,不要诡巧的言辞。”[8]故“端直”就是要求文辞真实正确。下文刘勰又对文辞提出了精要凝练的要求:“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接着刘勰又从反面阐释:“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如果内容贫瘠,文辞繁富,结构杂乱无序,则是作品无骨的表征。结合刘勰正反两方面的论述,可知“骨”是作品充实的内容、精严的结构与真实正确、精要凝练的文辞的统一体。
刘勰所举有“骨”之作的例子是潘勖的《册魏公九锡文》:“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对于该文,论者多认为其使用的词汇、构成的语法,多是取法《尚书》《左传》《论语》《孟子》等典籍,典雅庄重,所以骨力高超,至于其内容,则认为“其事鄙悖”[9]。王运熙先生甚至以此否定“骨”指思想内容:“潘文歌颂曹操功德,为曹操建立新王朝制造舆论,从封建道德标准看,其思想内容并无足取。如果骨的涵义像有些同志所说,是指思想内容,那末《风骨》独独举此文作为骨峻的正面例子,那也是奇怪而令人难以理解的了。”[10]其实这是以孔子《春秋》大义标准来看待汉献帝给曹操加九锡之事的。所谓“九锡”,锡即赐,九锡就是天子赐给权臣的九类物品。权臣先受九锡之礼,接下来就是其本人或其子嗣禅代。故九锡之礼往往预示着朝代鼎革,政治色彩明显。从《春秋》大义的标准看,曹操就是篡位的乱臣贼子,故其事卑鄙悖乱。但刘勰生活在齐梁之时,政权更迭频繁,多数士人并不以忠节为重,所以在刘勰看来,曹操受九锡之礼,并不鄙悖。这篇文章之所以被视为骨力高超,除了其文辞摹范经典外,充盈的内容和谨严的结构也是必不可少的要素。文章可分为三段,第一段写汉献帝自述时世艰危。其摹范经典之文辞,多在此段。然若非时世艰危,与所引经典之史事相合,则其文辞便无所依附,失其“端直”而无骨了。第二段铺叙曹操所取得的十一项重大功绩。这些功绩皆是实录,史书中皆可查考。第三段写赐土封公,赐“九锡”。从内容上来说,该文毫无夸大失实之处,正是这些充盈的内容,撑起了文章典雅精要的文辞。王运熙先生认为“骨”无关乎思想内容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从结构上来说,潘文首叙天下动乱,天子孤危,次述重臣赫赫功勋,最后条述“九锡”原因及赐物意义,思维严密,条贯井然。此种结构,成为后世此类作品的范式,几乎没有改变。因此,从刘勰的文学批评实践来看,充实的内容和精严的结构是支撑起作品文辞的不可或缺的骨干。
至此,我们可以对“风骨”的内涵作如下概括:“风”是作者感情与感发力量的统一体,“骨”是作品充实的内容、精严的结构与真实正确、精要凝练的文辞的统一体。
二、“汉魏风骨”内涵辨析
下面再对“汉魏风骨”概念的内涵作一辨析。
在文学批评实践中,不少人将“汉魏风骨”和“建安风骨”等同起来。如李宗为先生认为“建安风骨”“大抵相当于陈子昂《修竹篇序》中所说的‘汉魏风骨’”。[11]其实这是两个并不完全相同的概念。“建安风骨”作为文学批评术语,首由宋严羽提出。他说:“黄初之后,唯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12]阮籍是正始诗人,由此可知严氏“建安风骨”概念不包括正始诗歌。而陈子昂在序文中将“正始之音”与“建安作者”并举互文,则“汉魏”显然指汉代的建安之朝和魏代的正始之时。所以,“汉魏风骨”与“建安风骨”在时间所指上并不一致,前者包涵了后者。
那么何为“建安风骨”?对于这一概念,学界也一直未有定论,有的观点甚至完全相反。如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建安诗歌)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一方面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悲凉慷慨,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建安诗歌这种杰出成就形成了后来称为‘建安风骨’的传统。”[13]王运熙先生则反对这种观点:“建安风骨是指建安文学(特别是五言诗)所具有的鲜明爽朗、刚健有力的文风,它是以作家慷慨饱满的思想感情为基础所表现出来的艺术风貌,不是指什么充实健康的思想内容。”[14]其实一个时代艺术风貌和时代背景是密不可分的。建安文人生活于动荡乱离的时代,看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象,内心必然产生一种悲悯哀怜的感情,也会自然生发出一种乘时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豪情壮志。他们将这些思想内容用真实准确精要的语言在诗中表达出来,便形成了鲜明爽朗、刚健有力的文风,形成了“建安风骨”的美学风貌。
刘勰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15]正是因为当时社会动乱,诗人饱经沧桑,思想感情常常激昂慷慨,所以诗歌显得梗概多气。“梗概”一词,研究者多认为即慷慨之意。但古人言贵精简,一句之中,一般不会重复用字。王运熙先生认为此处“梗概”释为“不纤密”“大概”之意,[16]这个解释较为合理。建安诗歌用大概而不纤密、疏朗多气的语言反映现实,抒发志向,便形成了清俊爽朗、刚健有力的风貌。故建安风骨的形成,离不开充实健康的思想内容。
至此我们可以给“建安风骨”作如下解释:由于建安诗歌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一方面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表达了悲凉慷慨的情感,形成了鲜明爽朗、刚健有力的文风,所以有着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
陈子昂所说的“汉魏风骨”还包括正始诗歌。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是阮籍和嵇康,但嵇康的诗歌较少,现存诗作主要是四言诗,所以能真正代表正始诗歌的主要是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五言)。阮籍诗歌与建安诗歌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从内容上说,其《咏怀诗》写的是魏晋鼎革之际的时事,有人称之为“魏晋易代的史诗”[17]。阮籍不满于司马氏,但又不敢正面反抗,还要与新朝虚与委蛇,内心充满了深深的苦闷,这是《咏怀诗》具有强大感染力量的源泉。所以,在创作本质上,阮籍和建安诗人一样,都是主体精神对时代环境的抗争。而在表现手法上,为了远祸全身,避开司马氏的猜忌,阮籍不得采用隐晦曲折的比兴寄托手法。这也是正始诗歌与建安诗歌的不同之处。建安诗歌多用赋法,直接表现社会的乱离和百姓的苦难,直接表现个人志向和慷慨悲凉的情怀,虽然曹植后期诗歌也多用比兴,但不能代表整个建安诗歌的特色。而且,从陈子昂感叹齐、梁诗“兴寄都绝”来看,他正是要提倡运用正始诗歌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这应该是陈子昂言“汉魏风骨”而不言“建安风骨”的原因。
要准确把握“汉魏风骨”的内涵,我们还要探究陈子昂对这一概念的理解。这就要从他对东方虬《咏孤桐篇》的评价中去寻找。所谓“骨气端翔”,当指该诗文辞能够正确地表现内容,情感跌宕起伏,有飞动之势。所谓“音情顿挫”,当指语言抑扬顿挫,具诵读之美。所谓“光英朗练”,当指语言鲜明疏朗精练。所谓“有金石声”,当指语言刚健有力,掷地有声。而“发挥幽郁”,则是指诗歌抒发了诗人郁结在心中的怨愤之情。
从对“风骨”“建安风骨”和正始诗歌的考察中,结合陈子昂在序文中对齐、梁诗歌的批评及其对《咏孤桐篇》的评价,我们可以给“汉魏风骨”作出如下概括:作品有充实的内容,能够反映社会现实,抒发个人情志;作品有感动人心的力量;作品的语言鲜明精练,刚健有力,能正确地表现内容;表现手法上提倡运用比兴寄托以表达深隐的感情。
三、左思诗歌创作对汉魏风骨的继承
左思文学作品的代表作是《咏史诗》八首。以下就从《咏史诗》的内容、感情及语言入手,探讨其对汉魏风骨的继承。
(一)寒士的苦闷
《诗品》评价左思为“文典以怨”[18]。“典”指左思富有古典文化修养,在诗歌中多引用史实。“怨”即抒发对社会、政治的慷慨之情。这里有必要探讨左思“怨”情产生的根源。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其二)
涧底劲松,郁郁葱葱,高大挺拨。山上弱苗,尽管在体貌上根本无法与劲松相提并论,但由于侥幸生长在山顶,地位就高于劲松,并用自己的阴影遮蔽了劲松。显然左思在用自然景物来比兴现实政治。晋代选拨人才的制度,沿用的是魏文帝以来的九品中正法。这种方法被晋朝贵族利用、操纵,成为压抑寒门士人的门阀制度。这一制度的弊端,当时就有人认识到。段灼曰:“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沈者哉。”[19]左思正是从自身经历出发,认识到这种制度对寒门人才的扼杀,才大力予以批判的。
左思出身寒微,其父本是卑微的小吏,以才能升至殿中侍御史。左思要想像他父亲一样成为光耀家族的人物,除了勤奋学习,并没有其他的资籍。此外左思还有一个足以让他自卑的苦恼,就是他的“貌寝口讷”[20],容貌丑陋和口吃的缺陷在任何时代都足以让人产生自卑心理,但在左思的时代让人感受得更加强烈。因为那是一个特别重视容貌美和清谈的时代。卑微的出身和肉体的缺陷让左思更加注重与清谈玄学不同的文史之类的实学,也让他能够全身心地去进行文学创作。他用一年的时间创作了《齐都赋》,用十年的时间创作了《三都赋》。他要凭借文学才能出人头地。但是,使洛阳纸贵的《三都赋》虽然给他带来文学上的声名,却没有带来仕途上的帮助,仅仅被贾谧请去讲《汉书》,做了贾谧的二十四友之一。就连他的妹妹左棻被召入后宫成为贵嫔,也没能给他在仕途上带来多大的帮助,只是让自己成功地做了秘书郎,以便完成《三都赋》的创作。
这种遭遇带给左思的是苦闷和激愤。自己明明是天分极高的“英俊”,社会理应给自己充分发挥才能的机会,但无论怎么努力,自己始终沉沦下僚。这是自己的错吗?不是,这是社会的错,是只问出身不问才能的门阀制度的错。左思一边批判压抑他的社会,一边从古人那里寻求安慰。因此,门阀制度是左思“怨”情生发的根源,也是他创作《咏史诗》的心理动机。
(二)志士的怀抱
用豪言壮语抒发远大志向往往会令读者热血沸腾,激动不已,这应该是言志之作具备风骨的根由。但若无实才而空言大志,则肤廓空泛,惹人讥笑。左思则才与志合。
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
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
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
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爱爵,长揖归田庐。(其一)
在这段自我介绍中,左思首先对自己卓越的才华表示了自负。六朝人一般认为贾谊与司马相如是汉代文学的高峰,如《宋书·谢灵运传论》:“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21]左思把自己比作这二人,是毫不掩饰对自己文学才华的矜持。由于《三都赋》的存在,也没人质疑他的这种自矜。此外,他还熟读兵书,真可谓文武双全。
接下来左思向世人表达其强烈的用世之心。他谦虚地把自己的才能比作“铅刀”,一把刀质很钝的刀,但仍期待一割之用。当时蜀已败亡,晋国的敌人有南方的吴国和西北的羌胡。左思梦想驰骋疆场,平灭二国,然后功成身退。在这里,左思不仅表现了高远的志向,还表现了崇高的品格。他所追求的,并不是个人的功和名,而是国家的赫赫功业。
在第三首中,左思表达了相似的志向: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
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
临组不肯绁,对圭宁肯分。连玺耀前庭,比之犹浮云。
段干木与鲁仲连,随便的寝卧、轻松的谈笑间就解除了国家的危难,功高如许却不肯接受厚褒重赏。左思借这两个古人表达了自己理想的出处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左思在诗歌中抒发怀抱和批判社会现实之间是存有因果关系的。正是因为高才远志无法实现,左思才去思考症结所在,从而发现门阀制度的罪恶并痛加笔伐的。
(三)刚健的文辞
晋代诗歌普遍重视文采,讲究词藻华美,对仗和排偶。只有左思不事雕琢,质朴疏朗。钟嵘谓:“其源出于公幹。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22]公幹即建安诗人刘桢,钟嵘对刘桢的评价是“真骨凌霜,高风跨俗”[23],认为他是有风骨的。说左思源出刘桢,显然认为左思也是一个有风骨的诗人。左思用史实来抒发慷慨愤懑之情,而且写得精当贴切,说明左思的文辞能够精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情感。“野”,指左思的诗不像陆机那么追求对偶、雕琢和修饰,“深”,指左思的诗歌在内容上比潘岳深刻。
左思的“野”,是为了让自己的情感得到更准确、更强烈的抒发。如果一首诗对仗太多,会导致意象繁复,文辞纤密,词气不畅。在这点上,左思继承了建安诗人“梗概而多气”的语言风格。对于左思的“野”,日本学者兴膳宏曾作过饶有趣味的揣测:“对‘野’这个字,左思自己可能也会苦笑着颔首接受的。他可能会说;‘野’就‘野’吧。与其堆砌空洞的词藻,还不如‘野’好。我在苦苦地思索:如何在贯彻‘野’的同时,把全身的激动转化为读者自身的激动。”[24]
左思的语言富有表现力,能将左思的形象、胸怀、品格、感情等鲜明地表达出来。如第一首“卓荦观群书”中的“卓荦”一词,就将左思读书时超然的姿态刻画出来。“卓荦”是卓绝出众的样子。左思读书并不像一般的士子只注重字句的雕琢和考证,而是站在一个通观的高度把握其大处,反而能够真正有所得。这真是一种超然的非凡的姿态。再如第五首“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中的“振衣”和“濯足”两个词语,写得气象高远,将左思清高自洁的品格、傲岸不屈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左思文辞的刚健与他充沛的感情是分不开的。左思的咏史,不是单纯的叙写史事,而是借史事来抒情。“太冲咏史,初非呆衍史事,特借史事以咏己之怀抱也。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证之。或先述史事,而以己意断之。或止述己意,而史事暗合。或止述史事,而己意默寓。”[25]正是因为这点,朱自清将咏史诗作为比体诗的一大门类:“后世的比体诗可以说有四大类。咏史,游仙,艳情,咏物。咏史之作以古比今,左思是创始的人。”[26]左思用他勃郁难平的强烈感情来安排诗歌,所以诗歌语言刚健激烈,读者能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强大的感发力量,这是左思诗歌具备风骨的最根本原因。
通过考察左思的诗歌,可以发现其诗歌内容充实,批判了压抑人才的门阀社会,抒发了个人的怀抱,语言刚健精练,富有表现力,并且运用了比兴寄托的手法,显然具备了“汉魏风骨”的特点。因此,陈子昂“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的论断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1]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22. [2]詹瑛.文心雕龙义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052. [3]叶嘉莹.钟嵘诗品评诗之理论标准及其实践[M]// 叶嘉莹.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14. [4]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513. [5]叶嘉莹.钟嵘诗品评诗之理论标准及其实践[M].叶嘉莹.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14. [6]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516. [7]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1671. [8]舒直.略谈刘勰的“风骨”论[N/OL].光明日报,1959-08-16. [9]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517. [10]王运熙.文心雕龙探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01-102. [11]李宗为.建安风骨[M].北京:中华书局,2004:11. [12]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55. [13]游国恩.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226. [14]王运熙.文心雕龙探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16. [15]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674. [16]王运熙.文心雕龙探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12. [17]陈赓平.论阮籍〈咏怀诗〉是魏晋易代的史诗[J].兰州大学学报,1982(3). [18]徐达.诗品全译[M].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26. [19]许嘉璐.晋书[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1095. [20]许嘉璐.晋书[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2033. [21]许嘉璐. 宋书[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1466. [22]徐达.诗品全译[M].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26. [23]徐达.诗品全译[M].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12. [24]兴膳宏.左思与咏史诗[M]//兴膳宏.六朝文学论稿.湖南:岳麓书社,1986:29. [25]张玉谷.古诗赏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51. [26]朱自清.诗言志辨[M].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81.
2017-05-20
2015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晋宋诗歌风骨研究”(2015SJD675);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PPZY2015C249)阶段性成果。
陈祥伟(1975-),男,江苏南通人,硕士,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