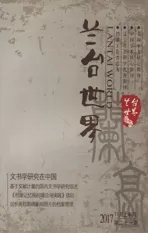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唐代巫觋文化新探
2017-03-11赵橙
赵橙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200241)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唐代巫觋文化新探
赵橙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200241)
巫觋文化在唐代政治与民间社会均占有一席之地。李唐王室一方面尊道教为国教,另一方面受胡族内亚性的影响,使得巫觋屡见于职官制中。唐前期以武则天、韦后为代表的宫廷女性利用巫术弥补参政劣势,国家政权中的巫风盛极一时。至后期,儒学的复兴致使巫术在中央层面的生存空间渐受挤压,日益堕入民间,成为唐宋之际思想变革的一大面相。巫觋在地方社会扮演着诸多角色,他们在努力开拓活动空间的同时,仍须面对世俗政权的不断干预。
唐代巫觋巫术国家地方
K242
A
2017-07-02
提及唐代的思想文化,佛道两教无疑占据着主导地位。然钩沉史籍,不可否认巫觋、巫术也曾在唐代的政治与社会文化中扮演着十分重要之角色。本文欲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有唐一代巫术这种亚文化存在进行考察。首先探讨巫觋在唐代官制中的生存空间,并追问这一空间是否有其传统。接着基于性别主义的立场审视巫觋与政治间的关系问题,即武、韦乃至其他的后妃、公主、宦门女性是出于何种原因信奉或利用巫术?与男性统治者是否存在差异?巫觋与政治间的关系在唐代前后期是否有所变化?士人群体又是如何看待巫术?最后考察巫觋在唐代民间社会的活动状况,剖析他们是如何在国家与社会的夹缝中寻找活动空间的。
一、唐代巫术源流考
孙英刚在考察中古时期的信仰体系时,立足谶纬、灾异、历法等层面将这一时期称之为“神文时代”。在此基础上,笔者以为倘若从更为“灰暗”的巫术角度展开论述,这一称谓同样成立。巫鬼之风在唐代大量残存,巫者的身影在职官制度中清晰可辨。据《旧唐书·职官志》所载,唐代太医署下设咒禁博士一人、咒禁师二人、咒禁工八人、咒禁生十人,其中“咒禁博士掌教咒禁生以咒禁,除邪魅之为厉者”[1]1875-1876。另有太卜署设太卜令一人、太卜丞一人、卜正二人、卜博士二人,“太卜令掌卜筮之法……凡国有祭祀,则率卜正、占者,卜日于太庙南门之外。岁季冬之晦,帅侲子入宫中堂赠大傩”[1]1876-1877。可见巫术的医疗与祭祀功能在唐代的官僚机构中分别得到认可。然进一步思考,为何仅是此两种功能得到承认,这一制度是否有其本身的源流承续?以下笔者就这一问题略作讨论。
众所周知,道教在有唐一代被奉为国教,而其在创立之初,即与巫术、医术紧密相关。如《后汉书·孝灵帝纪》注引刘艾《纪》云:“时巴郡巫人张修疗病,愈者雇以米五斗,号为‘五斗米师’。”[2]349同书《刘焉传》注引鱼豢《典略》亦云:“太平道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2]2436可知符水、禁咒是道教治病救人、弘扬道法的常见手段。正是道教这种“尚医”传统致使以医术、方术见长的高道如孙思邈、叶法善等,备受李唐皇家的礼遇。孙氏所著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就掺杂有大量的道教思想与咒禁、符印之术[3]411。此外,《唐六典》“太医署”条注云:“有道禁,出于山居方术之士;有禁咒,出于释氏。以五法神之:一曰存思,二曰禹步,三曰营目,四曰掌决,五曰手印;皆先禁食荤血,斋戒于坛场以受焉。”[4]似乎禁咒术与佛道二家均有渊源。事实上穷其本源,笔者以为释道二教中的咒禁、祝由之术当属于巫术之范畴。宗教本脱胎于巫术,故而两者仪式在很大程度上混杂重叠,后人难加区辨。此其一也。
其二,林富士在论及中古时期帝王崇信巫者之缘由时,提出巫术的两大分支,一者是江南地区的巫觋文化,一者是非汉民族的巫觋传统[5]。笔者认为唐代职官制中的用巫之事可溯源至后者。首先来看北方游牧民族萨满信仰之下巫术参与医疗的情况。譬如北齐娄皇后本是鲜卑人,其在弥留之时“衣忽自举”,遂听信女巫之言改姓石氏[6]124。北周武帝宇文邕的生母文宣太后亦出自鲜卑,巫医的身影同样出现在她的病榻前[7]842。再如西魏文帝悼皇后郁久闾氏源于柔然,其在临盆之际也有巫医侍奉左右[8]507。巫者作为医护人员似在非汉民族中相当普遍。
至于巫术与祭祀的关系,最明显的一例是北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焘即位之初,“立囗囗神十二,岁一祭,常以十一月,各用牛一、鸡三。又立王神四,岁二祭,常以八月、十月,各用羊一。又置献明以上所立天神四十所,岁二祭,亦以八月、十月。神尊者以马,次以牛,小以羊,皆女巫行事”[9]2735。天赐二年(405),又“复祀天于西郊”,用“女巫升坛,摇鼓”主导着整一祭典[9]2736。无独有偶,北方胡族如突厥、吐蕃、高车等,亦同样信奉萨满巫觋:史载突厥之民“敬鬼神,信巫觋”[10]1864;吐蕃在与其臣属会盟时,“令巫者告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之神”[1]5220;高车“每震,则叫呼射天而弃之移去。来岁秋,马肥,复相率候于震所,埋羖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说,似如中国祓除,而群队驰马旋绕,百匝乃止”[8]3271,信巫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巫觋风俗甚至也为深为胡化的汉人所浸润。杨隋在受命之初,高祖即遣“兼太保宇文善、兼太尉李询,奉策诣同州,告皇考桓王庙,兼用女巫,同家人之礼”[10]136。开皇十四年(594)又下诏:“东镇沂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无闾山,冀州镇霍山,并就山立祠。东海于会稽县界,南海于南海镇南,并近海立祠。及四渎、吴山,并取侧近巫一人,主知洒扫,并命多蒔松柏。”[10]140似乎隋代女巫在国家祭祀系统中所起的作用亦不容小觑。杨坚虽为汉人,然其长期居于北方,委身异族政权,故在生活习惯与文化认同上多沾染胡俗。正是基于此,杨隋时期的巫风并不亚于先前任何一胡人政权,并成为唐代宫廷巫术兴盛之滥觞。
二、性别视域下的唐代巫术与政治
除国家官制中明文规定的生存空间外,巫觋的身影也同样穿梭于唐代的帝室宫闱之内。检视史籍,笔者发现有多位公主、后妃崇奉巫术,甚至达到佞信的境地。譬如,太宗女合浦公主,其身边便聚集了一批沟通鬼神、占断吉凶的术士巫者。史载“浮屠智勗迎占祸福,惠弘能视鬼,道士李晃高医,皆私侍主”[11]3648,“视鬼者”大抵同于“见鬼者”,乃唐代巫觋之别称①。而太宗另一女城阳公主亦在麟德年间涉事巫蛊案件[11]3647,遗憾的是此事的前后始末未见有相关记载。
据《旧唐书》所载,高宗废后王氏在与武则天争宠的过程中,“密与母柳氏求巫祝厌胜”[1]2170。厌胜系巫术之别种,即以巫祝诅咒厌恶的人或事以达到制胜之目的。然《新唐书》中的记载与此相龃龉,认为王氏求巫祝一事系武氏诬蔑之词[11]3475。诚然究竟何书所载更为可信已无从考证,唐代前期宫廷内部巫风之炽盛却也能由此窥见一斑。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武氏本人确实颇信巫道之术。其为皇后时,“将入洛,至阌乡东,骑忽不进”[12]2255,遂召巫者询问缘由。麟德初,又召“方士郭行真入禁中为蛊祝”[11]3475。即便是临朝称制后,其对妖妄之徒的信赖也并未见丝毫减退。天册万岁元年(695),“河内有老尼居神都麟趾寺,与嵩山人韦什方等以妖妄惑众……太后甚信重之,赐什方姓武氏”[13]6610。大足年间“有妖妄人李慈德,自云能行符书厌”[14]66,武氏听闻后便将此人纳于宫中。如果说上述种种仍止于武氏个人的信仰层面,那么以下两例则充分显示了巫术在其秉政时期是如何介入政治斗争的。史载永隆年间,武后与明崇俨私为厌胜之法,并试图借占相之言以铲除太子李贤的威胁[1]5097。其后在打击綦连耀谋反案时,同样以道术为由,牵连海内贤士三十六家[1]4848-4849。
中宗、韦后时期,这股尚巫之风依旧延续,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以左道隆显者甚是普遍。如善“符禁小术”的叶静能[1]2174、善“方伎”的郑普思[11]5754被分别委以国子祭酒、秘书监的要职,以掌学政教化。郑普思妻第五英儿也因“鬼道”得幸于韦后,出入禁中[1]2878。另有女巫赵氏被封为陇西夫人[1]2173。唐代外命妇共分六等,依次为妃、国夫人、郡夫人、郡君、县君、乡君[11]1188,陇西夫人为第三等。这些外命妇多因其夫或其子位高权重、备受恩宠而得以晋封,体现的是妻以夫荣、母以子贵的原则。此处,赵氏却凭借通巫之才打破了传统意义上性别与阶层之区隔,实属罕见。除此之外,巫觋彭君卿亦颇得韦后倚重。景龙三年(709)关中大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什八九”,群臣纷纷奏请中宗移驾东都。韦后家在杜陵,不乐东迁,因而唆使彭君卿劝服中宗云“今岁不利东行”,此事遂罢[13]6756。另外,韦后的宗亲亦有仰赖巫术者,如冯七姨“信邪见,豹头枕以辟邪,白泽枕以祛魅,作伏熊枕以为宜男”[12]2295。
由上可知,武、韦统治期间,宫廷内外俨然充斥着一个挟巫鬼道术秉政弄权的庞大团体。至睿宗即位,这一团体并未倾覆,而是继续对政坛时局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景云年间,尚书宋璟、御史大夫毕构针对“斜封得官者二百人,从屠贩而践高位”的时弊,上书要求奏停斜封官。对此,“见鬼人彭卿受斜封人贿赂,奏云见孝和,怒曰:‘我与人官,何因夺却’”[14]7。彭卿即是上文所述的彭君卿,此人正是借招魂之术有效遏制了裁汰斜封官员的局面。另,太平公主与李隆基政争激烈时,曾指使术士向睿宗进言,“慧所以除旧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变,皇太子当为天子”[13]6792,企图以星占之术挑拨睿宗父子二人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慧范,作为一名精通巫术的婆罗门僧,其先后依附于武后、韦后、太平公主诸人,在政治权贵的庇佑下历经数次政变,依然颐指气使、煊赫一方[14]114。
至玄宗时期,巫风之盛始有所收敛消退,术士巫者虽已不具规模,仍偶能发现宫室妃嫔求诸巫觋的情况。如玄宗皇后王氏因无子时常忧惧被废,故而“导以符厌之事”[1]2177。武惠妃暗结李林甫废黜太子,事后其“左右屡见为祟,宫中终夜相恐,或闻鬼哭声”,于是召来巫觋破除鬼祟[15]172-173。另,玄宗子琰有二孺人,争宠不相和,“乃密求巫者,书符置于琰履中以求媚”[1]3260。
以上,我们不难发现宫廷女性信巫的大致情形:或借巫术驱凶避祟,如冯七姨、武惠妃;或为争宠求子诉诸巫道之术,如高宗废后王氏、李琰孺人;或将巫术视作其参与政争的非常手段,如武、韦及太平公主。不同于男性帝王将对巫术的偏好限于个人生活,女性统治者更乐于将这种崇奉带入政事。究其缘由,笔者认为与巫术本身是一种边缘性的文化存在有关,故而常被同在政治上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加以利用。众所周知,女性参政缺乏主流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支持,这一点在唐代也概莫能外。而巫术的神秘色彩恰能有效地弥补这种性别劣势,使之摆脱传统儒学意义上内/外、阴/阳之区隔。与佛道等高层次的政治缘饰相比,巫术的实践性、谶纬性更强,故在渲染其统治合法性、实施政治打压的过程中往往更胜一筹。正是基于此,巫术成为唐代女性干预政事的一项重要资源。
三、崇禁之间:唐代巫术的生存空间
当然,巫术也同样为男性所利用,成为谋乱叛逆、制造舆论的有效利器。如安禄山在谋逆前利用女巫奉自己为神灵,史载“禄山踞重床,燎香,陈怪珍,胡人数百侍左右,引见诸贾,陈牺牲,女巫鼓舞于前以自神”[11]6414,从中我们既能发现胡人信奉巫教的痕迹,亦不难窥见安氏欲通过此种方式蛊惑人心、收买舆论之心态。再如魏博节度使赵文死后,罗弘信借巫者之进言“白头老人使谢君,君当有是地”,自言受神之旨当继为节度使,众人遂立之[11]5939。诚然弘信之得立固然有牙兵拥护,但巫觋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亦不可否认。此种借鬼神之术为谋反篡位寻求合法性的做法,也同样见于唐末庞勋起义[11]4776、董昌割据两浙[11]6467-6468的前后。
正是鉴于巫术往往与谋逆相联系,故而也成为打击政敌的绝好口实。武德初年,刘文起“家中妖怪数见,文起忧之,遂召巫者于星下被发衔刀,为厌胜之法”。事发,“高祖以之属吏,遣裴寂、萧瑀问状”。裴寂本与刘氏有隙,故借此认定文静、文起兄弟有叛乱之心,劝高祖除之[1]2293-2294。又如隋室后裔杨慎矜与史敬忠私为厌胜之术以驱祸,事为女婢所泄,玄宗大怒,知李林甫素来忌惮慎矜之才华,便告林甫,林甫遂假借酷吏吉温阴害之[16]52。按理,刘氏、杨氏奉巫以驱凶辟邪当属于个人行为,却不幸为政敌所构陷,曲解为反叛之举,不得善终。由此观之,巫术诚为政治斗争更添了一层变幻诡谲之色彩。
巫术既能攸关时人之性命,更是深刻影响着官员们的仕途升迁。例如睿宗时,刑部尚书赵彦昭与“女巫赵五娘左道乱常”,遭殿中侍御史郭震弹劾,被贬江州,客死他乡[1]2968。宣宗时期,太仆卿韦觐为求官请于女巫,反为女巫诬告,宣宗明知冤情,但其祷祝巫事属实,故仍贬韦觐潘州司马[17]1288。值得关注的是,代宗在历数元载罪状的召敕中写道“阴托妖巫,夜行解祷,用图非望,庶逭典章”云云[1]3413,然笔者管及所见,尚未发现有此事的相关记载,颇疑此说仅是当时较为普遍的治罪托辞。
如上文所述,受胡化与女性干政的影响,唐代前期巫风盛行。那么至后期,特别是在儒学复兴、强调正统的思想环境下,这一政坛风尚是否有所退减呢?考稽史料,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自玄宗年间起,巫术在国家政治中的生存空间日益狭小,越来越多的士人排斥甚至要求禁断巫术。诚然,唐代前期反对巫术的言论亦不乏其词,譬如吕才在其《叙葬书》中谈到,“巫者利其货贿,莫不擅加妨害……野俗无识,皆信葬书,巫者诈其吉凶,愚人因而徼幸”[1]2723-2726,不过吕氏是站在一个阴阳术士的立场上指责巫者之行骗妄语。中宗时,左拾遗辛替否上疏谏曰,“至于公府补授,罕存推择,遂使富商豪贾,尽居缨冕之流,鬻伎行巫,咸涉膏腴之地”[1]3155-3156,主要是针对巫觋官致高位、富贵凌人的社会流弊提出批评,并未涉及巫术活动本身。
玄宗即位后力主改革武韦以来的弊政,在此情形下大批巫觋作为韦后、太平公主之党羽遭到清洗。另外,玄宗在位前后也曾两次颁布《禁卜筮惑人诏》与《严禁左道诏》。尽管这一时期的“祛魅”并不彻底,仍有王屿等人以巫术祷祝得到玄宗、肃宗父子二人的赏识;但王屿之行径已有士人加以抵制,如其所派遣的为肃宗祛除鬼祟的女巫在地方上行事猖狂,为黄州刺史左震“破锁而入,曳女巫阶下斩之,所从恶少年皆毙”[1]3618。代宗即位之初欲听任道士李国祯祭祀淫祠,对此梁镇[1]3619、苏源明[11]5773二人先后表奏,劝诫代宗勿信巫祝淫祀而废先王之祭典。其后代宗诞日,佛、道之徒竞相祈祷,中书舍人常衮进言道:“今军旅未宁,王畿户口十不一在,而诸祠寺写经造像,焚币埋玉,所以赏赉若比丘、道士、巫祝之流,岁巨万计。陛下若以易刍粟,减贫民之赋,天下之福岂有量哉。”[11]4809以上,梁镇、苏源明、常衮的言论虽非针对巫术,但均是从儒家立场出发,将巫祝与佛道一同视作蠹流,横加贬斥以维护正统之纲纪。
正是鉴于肃、代二宗重阴阳祠祝的流弊,德宗“尤恶巫祝怪诞之士”,其即位不久便诏令“罢集僧于内道场,除巫祝之祀”[1]3623,对巫术左道予以明确禁断。后遇有司奏请修缮宣政内廊,而太卜奏云:“孟冬为魁冈,不利穿筑,请卜他月。”然德宗未顾这些禁忌,“卒命修之”[1]3623。文宗时,李听为邠宁节度使,邠州衙厅相传不利修葺,隳坏日久。李听到任后不以为然,云“帅臣凿凶门而出,岂有拘于巫祝而隳公署耶”,遂命修之[1]3684。以上种种,似乎都预示着伴随理性主义的归复,这种禁忌类的巫术正日益受到上层人士的鄙薄和质疑。他们的行为、论调与唐代后期兴起的古文运动相交织,共同构成宋代儒学的新方向,即由“神文”而“人文”。在此过程中,佛道、巫术、谶纬等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信仰体系被再次斥为怪力乱神,其对政治生活的影响日趋衰弱,只得落入民间另觅生存之根基。
四、唐代地方社会的巫术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最早的巫术具有全民性。尔后随着社会职能的不断分化,巫术渐为某一阶层据为专利,政治领袖同时掌握着沟通鬼神的最高神权。至轴心时代,理性文明的登场迫使巫术的地位逐步下降,其民间性日渐突出。中古时期,鬼神色彩不仅在国家政治中较为浓厚,与此相并行,巫术在地方社会同样颇具生命力。诚如浮休子张鷟所言:“下里庸人,多信厌祷,小儿妇女,甚重符书。”[14]62虽是责难的口吻,却也道出了巫术在下层社会之普遍流行。
有唐一代巫觋活动具有广泛的地域性,各地的巫俗亦不尽相同,其中尤以荆楚、江淮及岭南一带为甚。王维曾作《鱼山神女祠歌》两首,分别记述东阿地区女巫蹈舞以迎神、送神的场面[19]6-7。另一首《凉州郊外游望》则描绘西北田间赛神的热闹景象[19]151。值得注意的是这三首诗中,王维并没有表现出对巫术参与民间祭祀的反感,相反倒是对女巫纷然起舞、罗袜生尘的姿态投之以欣赏的目光。
不同于北方,南方地区潮热多山,瘴疠之气弥漫四塞,由此所产生的右巫风俗也颇异于北方。元稹在《赛神》一诗中写道,“楚俗不事事,巫风事妖神。事妖结妖社,不问疏与亲”[20]4478。在元稹看来,荆楚地区充塞的巫风已到了严重影响家人生计的境地。刘禹锡被贬朗州的十余年间,也创作有多首反映当地淫祠赛神的诗作,而这些神祠与祭祀活动恰为巫觋提供了重要的谋生之地。《阳山庙观赛神》一诗即是生动的写照:“汉家都尉旧征蛮,血食如今配此山。曲盖幽深苍桧下,洞箫愁绝翠屏间。荆巫脉脉传神语,野老娑娑启醉颜。日落风生庙门外,几人连蹋竹歌还?”[21]672首联提到的“汉家都尉”即是这座生祠的主神梁松,因他征蛮有功被奉为神灵;尾联描写赛神结束后众人竹枝踏歌的场景则颇具楚地特色。刘氏的另一首诗作《梁国祠》:“梁国三郎威德尊,女巫箫鼓走乡村。万家长见空山上,雨气苍茫生庙门。”疑同样是吟咏这座生祠,只不过这次祭祀的目的在于求雨[21]1470。
此外,江岭也是巫风炽盛的一大区域。作为吴郡人的陆龟蒙有诗云“江南多事鬼,巫觋连瓯粤”[20]7161-7162,由此推测吴、越/粤之地的巫俗大抵相类。不同于荆楚巫者依托于淫祠,江淮地区的巫觋往往是凭借个人法术之灵验吸纳信众。譬如有土人何婆巫术高明,致使“士女填门,饷遗满道”[14]63。楚州薛二娘“自言事金天大王,能驱除邪厉”,亦为乡人所崇奉[12]3872-3873。
当然,在古代社会,即便是所谓的民间信仰也往往夹杂在世俗权力与社会秩序之间,从而丧失其本身的纯粹性。以下即以巫术为例,透视唐代政治力量是如何介入民间并影响其在地方社会的生存空间。据《旧唐书》所述,狄仁杰在充任江南巡抚使时,奏毁淫祠一千七百余所[1]2887。戴孚《广异记》则云:“高宗时,狄仁杰为监察御史,江岭神祠,焚烧略尽。”[12]2371如前文所述,大量的神祠、祭祀与赛神活动是巫觋在民间的重要依托,狄仁杰此举无疑对巫术之生存发展构成巨大威胁。无独有偶,李德裕在浙西任职期间,亦锐意肃清巫鬼之术。史载:
德裕壮年得位,锐于布政,凡旧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江、岭之间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厉疾者,举室弃之而去。德裕欲变其风,择乡人之有识者,论之以言,绳之以法,数年之间,弊风顿革。属郡祠庙,按方志前代名臣贤后则祠之,四郡之内,除淫祠一千一十所[1]4511。
此处,李德裕以礼法并用、恩威兼施的手段整顿江南尚巫鬼的风俗,成效显著。不过单就这条史料记载我们也很难断言江岭地区的巫风究竟得到了多大程度的改观。从狄氏、李氏前后废黜的淫祠数量来看,巫术在民间的反弹力量亦不可小觑。
相较而言,刘梦得、柳河东等人在地方上移风易俗的举措则略显温和。刘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1]4210不同于狄仁杰、李德裕直接捣毁淫祠、严厉打击巫俗的做法,刘氏并未明确反对巫觋、压制他们的生存空间,而是与他们相杂共处,通过变换唱词内容的方式以宣扬儒学教化。另外,柳宗元在《柳州复大云寺记》中写道:“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偭仁。病且忧,则聚巫师,用鸡卜。”对此,他一方面宣传佛教不杀生的观念,“唯浮图事神而语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另一方面又以儒家仁爱思想教化民风,“严其道而传其言。而人始复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成效颇著[22]752-753。可见代表政权意志的地方官员,其对民间巫术、淫祠的态度与举措是复杂多样的,这一方面有待我们做进一步考察,以更好地理解唐代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博弈。
综上,通过对唐代巫术源流、巫术与性别、唐宋变革、国家政治与地方权力等诸问题的考察梳理,从不同视角辨识巫术在有唐一代所享有的生存空间:巫觋之所以能厕身于唐代的职官制度,与李唐王室一方面尊道教为国教,另一方面沾染胡族风俗密切相关;唐代前期女性参政蔚为大观,在此过程中巫觋与女性紧密结合,使得自身被边缘化的地位得到充分改观,国家政权中的巫风盛极一时;尔后伴随着武韦时期的时弊得到矫正,唐代后期正统性的强调、儒学的复兴,巫术在中央层面的生存空间呈现日渐狭小的趋势;尽管巫觋在唐代地方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仍不得不面对世俗权力的不断干预,在国家政权与民间习尚之间求得一线生机。上述这些认识有助于我们打破理性主义框架下将巫术简单斥之为“封建迷信”的偏见,从古人的内在逻辑出发重新审视巫术及其与政治的关系,以补中古思想研究之缺。
注释
①明人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卷39《乔势天师禳旱魃秉诚县令召甘霖》序言中写道:“话说男巫女觋,自古有之,汉时谓之‘下神’,唐世呼为‘见鬼人’”,即是例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85-686页)
[1]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 于赓哲.唐代医疗活动中咒禁术的退缩与保留[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
[4] 李林甫.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2014.
[5] 林富士.中国中古时期的巫者与政治[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104-111.
[6] 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7] 令狐德棻.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
[8] 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 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1] 宋祁、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 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13]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4] 张鷟.朝野佥载[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5] 刘肃.大唐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6] 郑处诲.明皇杂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4.
[17] 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8] 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9] 王维撰,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0] 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1] 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2] 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赵橙,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