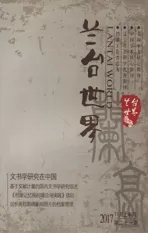抗战时期西北联大的教育生活及其影响
2017-03-11刘俊凤
刘俊凤
(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安710121)
抗战时期西北联大的教育生活及其影响
刘俊凤
(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安710121)
在抗战爆发后的高校内迁中,西北联合大学师生历经艰难困苦,终驻足于陕西城固。在整个迁移整合的过程中,西北联大师生努力传承大学教育之精神,播撒学术研究与现代文化之种芽,为近代西北地区高等教育体系之形成奠定基础;避居秦山巴水间而弦歌未断,在物质生活的清贫中始终精神饱满、乐观平和,呵护联大的生机和活力,彰显“勤朴、公诚”之校训;在富有战时教育特色的军事训练生活中,以对“自由”和“教育”的向往和坚守,令这一块大学精神和传统的生发地保持了一份难得的独立。
西北联合大学师生生活坚守
G127;K262.9
A
2017-06-07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以国难之际,教育不可中断为重,决定高等院校合并内迁,坚持培养人才,为抗战建国保存精华。在同时期的内迁高校中,以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最为引人注目,两校合并当时京沪津的数所名校,历经艰难困苦、颠沛流离,终于分别在西南之昆明、西北之城固驻足,在抗战的大后方形成南北呼应之势。一面于战火纷飞下,竭力保障大学教育之完整;一面在清苦艰涩中,努力传承大学教育之精神。
唯西南联大、西北联大各自渊源不同、风格迥异,加之所寄地域之差别,使各自在这个特殊的发展时期,以不同的特色造成深远的影响。笔者不揣浅陋,基于抗战时期西北联大的相关文献资料,试图通过抗战时期的西北联大师生的部分教育和学习生活,从生活史角度解读今日西北地区的大学所继承的、往日西北联大时期形成的大学传统与风度,以彰显西北联大对西北地区高等教育,乃至中国高等教育的深远影响。
一、落地即生根开花——内迁分立中的“亲土”
1937年11月1日,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组建的西安临时大学,在古都西安正式开学。百余位教授和千余名学子聚集在简陋零散的校舍中,开始了在大后方的大学教育和学习生活。这所于国难之时组建临时大学,一经落脚西北,竟似一株蓬勃的枝芽,扎入到这广袤厚重土地中,慢慢生根、开花。
抗战初期的西安城内,络绎不绝地涌入来自战区的人口,一时间车水马龙、嘈杂纷繁,不复往日的宁静,愈发显得城市的落后和陈旧。西安临时大学的教师们,不得不分散居住在市内民房、饭店和招待所,学生们则分别集中居住在三个校区的临时大通间宿舍中。不过,临大师生既没有过多纠结、苦恼于生活上的种种不便,也没有因临时而存“五日京兆之心”,在正常课堂学习之外,纷纷走出书斋,走进西北开发建设的现场,结合地方资源,开展学习考察,是为学术研究融入地方社会之始。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开发西北、建设大后方的计划全面付诸实施。西北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地区,亟待各种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临大农学系教师与武功西北农业专科学校交流合作,获赠农作物、园艺作物种子百余种以及昆虫标本十余种,充实临大农学系的教学资源,也为日后同西北农业专科学校共同成立西北农林高等学府奠基。地理学系的郁士元、殷伯西教授分别带领学生组成考察队,对西安周边的终南山、灞桥、汉城未央宫各处开展自然及人文景观调查,邀请了全国著名的水利专家、时任陕西水利局长的李仪祉先生,为师生详细讲解泾惠渠的水利问题。在旋即开始的南迁和整合过程中,随着学校的分立和合并,西北联大师生们参与地方社会的范围也不断扩大。
1938年4月,西安临大迁至汉中城固,更名为西北联大。次年8月,西北联大分立出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本校则更名为国立西北大学,随后又吸纳了陕西省立师范、商业、医学等专科学校,初步搭建起了日后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框架体系。分立后的西北联大,虽不同处,而风度依旧,学术服务地方建设的传统被承继和延续。
国立西北大学如同司令台,学术专注于西北文化的振兴和发展,考古、地质调查不辍,学子富有责任感,更具吃苦耐劳之精神;国立西北工学院的师生能坐冷板凳,学习研究用功甚勤,以“三多”(老鼠多、跳蚤多、破鞋多)、“三少”(警报少、女生少、西装少)著称各校之间;西北师范学院注重教师素质培养,体育活动频繁;医学院师生专心细致,细声慢做,学习、生活中均亲如一家;联大之农学院与原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成立的农学院虽远在武功,校园力求先进时尚,而研究实验始终奉行科学实干、为改良农业而服务的宗旨。
与省会西安相比,陕南经济的不发达,更推动了师生们解决问题的创造性研究活动。不仅自己解决一些教学上的需求,还帮当地百姓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初到城固,教学纸张极为匮乏,化学系师生就收集地方树木原料,分析出当地所产構树的织维比较长,可以造纸,遂利用实验室分离转化,造出质地洁白平滑的白纸。本为当地一大财源的桐树,因为抗战交通断阻,无法出口多被废弃。师生感于资源的缺失与浪费,着手实验研究,以裂化桐油制造汽油,既发掘利用地方资源,又贡献抗战。汉中十八里铺盛产甘蔗,当地糖房一贯使用旧法炼制,某年突然出现早霜,糖浆不能结晶,眼看一年心血付之东流。坊主求助联大师生。师生们经过调查,确认是旧法落伍,转化糖太多,漏盆中温度过低,导致结晶与母液不能分离,帮坊主化解了危机。科学研究服务于生产,反过来也推动了科学研究。解决了糖房问题的教授因此提出了结晶分离之理论和方法,写成《糖液中石棉粉过滤之效果》的学术论文,发表于美国化学工程杂志[1]39。西北联大的师生们,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播迁流离中,始终与这块土地密切联系、结合着。
抗战胜利后,国立西北大学回迁西安,更担负起了西北学术重地的责任。地理系、地质系的师生们,率先将考察视野拓宽至关中地区。经济学系和边政学系的师生则开始将西北作为考察研究的范围。1947年11月,国立西北大学经济系与陇海铁路局商定共同进行西北经济考察,对西北区域经济进行了广泛调查。边政学系早在1944年秋,即由杨兆钧副教授率领边疆考察团去青海进行历时两个月的调查。1948年暑期,在谢再善、阎锐及朱懿绳的带领下,边政学系21名大四学生赴新疆见习四个月,行程两万里,对民族、宗教、社会、经济、习俗制度、文化等等做了综合的考察[2]386-387,388,390。
这种落地即扎根的态度,也促成了西北联大学生服务社会、服务西北的行动。至抗战后,在国立西北大学学报复刊统计的不完全数据中,第7届、第8届毕业生中,已有近73%的学生留在西北从事社会服务工作[3]。剔除战乱导致个人选择趋向安全考虑的影响,这种服务于地方社会的做法则多来自于时代给予个人的责任感,以及教授们给学子的激励和榜样。地理系教授殷伯西,出身书香世家,于英国深造归国,颇具绅士风范。他在西北联大至国立西大执教多年中,身先士卒,活跃于西北地理考察活动,亲自带领学生实地考察,又将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所得大量资料用于教学中。受其影响,学生中多有对西北边疆之研究与建设发生浓厚兴趣者。如学生于书绅不仅以《新新疆与西北国防》为毕业论题,还决意毕业后一不做官、二要横涉瀚海,远走边陲,数次拒绝前往陪都及优厚待遇的工作,执意入兰州工作[1]65。
由于西北长期远离政治文化中心,高等教育发展一直缺乏先进的外来资源,而随着西北联大的到来,师生们一方面将地方社会纳入学科研究视野,一方面又将文化风与创新力散播于地方社会。若不论对大学自身建制和发展的消极影响,整个西北联大整合播迁的过程,更多的是传播现代科学力量、造福地方社会的深远影响。
二、偏居而弦歌未断——乐城生活中的“坚守”
1938年3月中旬,西安临时大学师生一千五百余人,开始了徒步从宝鸡越秦岭达南郑的南迁之旅。同年4月,以西北联合大学之名,落定陕南,校舍分立于秦巴汉水之间的城固、南郑、勉县各处。至抗战胜利后(1946)回迁西安之前,八年的乐城生活,成为整个抗战时期西北联大师生们最深刻、最美好的记忆。
早在南迁之旅前半年,学生组织的下乡宣传队,一面宣传抗战建国,一面深入地方生活、调查地方社会实情,其中包括各县道路、旅宿条件、食品、物价等等。校方也提前拟定《行军办法》,并安排了行军各大队、膳食委员会、运输队等各种组织机构。这场罕见的旅行就是在校方的有效组织和师生有条不紊的准备中开始的。
交通工具的缺乏和人数的庞大让这场旅行随时会出现停滞和骚乱。但在有关记述资料中,所见却是,安步当车的学生们在云逐人移的秦岭山间,偶尔觅小路而行,不时与行驶在曲折迂回公路上的汽车争先,汽车与人,旋和旋离、一呼一应,笑乐声震动山谷,漫漫长途之枯燥劳累为之一扫而光,迁徙之苦竟然转化作春游之悦。每晚集体落宿在租住民房中,通讯组以收音机收听中央广播消息,次晨以大纸书写张贴屋外,使各中队队员及时了解当日新闻,当地居民识字者也多伫立围观,得以知道国家大势。对这些衣衫俭朴、满面风尘,但守纪有序、快乐轻松富有青春气息的联大学子们,沿途投宿人家都报以惊诧的目光和热诚的招待[4]。显然,对师生们而言,国难中的迁徙流离赋予他们的不是避难的畏惧和愁苦,而是与联大同为一体,同舟共济,共赴希望,共享尊严与光荣。
国难之时成长起来的西北联大,也聚集了一大批爱国的饱学之士,他们于颠沛流离、生活清苦之中,仍不忘为人师尊的职责和榜样力量。临大初成,教授们即布告全校:在环境窘迫的情况下“究能保存若干学术研究精神,弦歌未断,黉舍宛然,特殊训练之外,不忘正常教学,埋头苦干,冀成学风,此未始非我一群学人领导知识青年共体国家维持战时教育之至意所致,然亦其力求精诚战胜危机之一种心理建设也”[5]。
正所谓精神不坠,文脉不辍。教授们在学术方面成果斐然,在讲堂上的兢兢业业、沉静平和之状也深深影响着联大学生们。
文学院的黎锦熙教授,是著名语言学教和方志学家,其关于修订方志的创见和实践即在城固西北联大时期形成。1938年9月,他受聘任城固县志续修总纂,仅一月时间,草成近九万字的《续修工作方案》。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时,因其“实是泛陈现代新修方志之要旨及方法,但就城固一带举出实例,其用不限于一邑”,命名为《方志今议》。先生在学术上深思熟虑、筚路蓝缕,在城固六年间,深入陕西各县调查,先后主纂陕西城固、洛川、同官、黄陵、宜川等县志。不仅是民国县志中的创新和成就,更是陕西地方史研究的宝贵方志资料。
与学术研究相比,课堂上的师者风范,更是西北联大于艰难困苦中坚守精神的生动展现。历史系教授陆懋德永远是一身蓝布大褂,一顶瓜皮小帽,上课时先写满一黑板文字,然后正好讲到下课。他不仅学术精湛,有全部用外文讲授之水平,更是风趣幽默,时有在紧张讲课中,突然指着一位学生说,“你的眉毛很好,不要吊”,令正在高度紧张跟随听讲的学生忽然得以轻松,课堂陡然生趣盎然。文学院的王守礼教授,得知前来请教的学生赵毅参加演剧,颇为担忧的询问动机为何?当听说赵是以演剧为志向而非沽名钓誉之举时,颇为欣慰,此后常与他讨论至深夜。在生活不宽裕的情况下,还叫学生到家中进餐讨论,殷殷关爱、奖掖后学之情,令学生多年后忆起仍是热泪盈眶[1]63。以教育为职守,饱受战乱之苦、拖家带口的教授们,一俟站在讲台面对学生时,一切物质上的困苦和个人的艰难,都仿佛被他们用破旧的柴门轻轻掩到身后。
在教授们的榜样力量下,联大学子也格外珍惜难得的僻静和安定的学习环境。工学院课业繁重,学生却毫不松懈。深夜,在原始油灯烛光下,研究着航空理论科学。白日,于一日学习疲劳之余,登高瞭望,仰天长啸,心旷神怡。医学院学生不仅聚焦实验室显微镜下,专心致志,观察人所不能见之东西、学习济世活人的法宝,更于每年四月三十日举办学院解剖节,全体师生员工停课一天,齐聚解剖墓前举行公祭,奉敬奠爵、诵读祭文,缅怀被解剖者的伟大贡献[6]。学问之外,更有悲天悯人医者之心的养成。
联大学子的晨读更是乐城的一道靓丽风景线。在太阳还没升起的濛濛清晨,城野的田边、树下、土台上,就遍布了年轻的男女学生:有练习唱京剧,有排练话剧的;有的朗诵诗歌,有的练习歌唱发声,练习讲演的人眉飞色舞、抑扬顿挫,如入无人之境;练习俄文德文的同学嘴里不断发出气泡一样的“不都不都”之声,练习法文的则张着嘴巴发出啊哈啊哈的怪声调。虽世事多艰辛,而天地有大美,联大师生沉浸其中,流连忘返。曾出任工学院院长和出长国立西北大学的赖琏教授,数年后还念念不忘“陕南乐城环境优美,为研究学术胜地,每忆畴昔情景,不禁神往”[7]。
在颠沛流离期间,学校不仅是求学问道之殿堂,也成了全体学生的家。举凡衣食住行,皆由政府贷金提供、学校统筹安排,同时因学生家庭境况不同,又有个人选择的点缀。
淡食有章法。集体膳食是主要形式。进驻乐城后,各学院举办食堂,学生每顿以数人一组,围桌共餐,菜饭则视各院的情况。医学院的学生因为全系公费,伙食冠于各院,几乎每天都有红烧肉吃。学生选举组织了伙食委员会,担任米面柴菜的办理职责,必须办理的有声有色而才能得到同学的认可[1]22。惨淡如历史系的状况,则大多时候是八人一桌的大烩菜,还是水煮的。对实在熬不过食堂饭菜清淡的学子来说,城固街头小吃的美味就成了大家不约而同的美食记忆。其中,城固北街“老乡亲”的牛肉泡馍独占鳌头,又有白水羊肉、醪糟蛋等等。
衣着服被有传统。在西北联大学子中,除了中装、西装之外,最具典型意义的装束就是蓝布大褂,外套一件黄棉袄。这是早先学校所发放的御寒制服,经费停止后,学生们一届届传送,接替穿戴,竟成为学生印象中“世界上最舒服、最实用、最美好的服装”[1]49。
住行间其乐融融。出于条件限制,学生们居住的学校集体宿舍,通常都是大通间、大通铺、上下两层,但学生们不以为苦。常常在课业之余,徜徉于乐城的城野美景中,流连忘返。昔日法学院的学子,忆及当年柴门乐读之生活,有杂咏记称:正院几回廊,弦歌深动肠,才看海棠红,又数枇杷黄;后院茅屋住,墙外野花香,同窗皆年少,谈笑常无疆[1]75。
检视当年学子们多年后的回忆,令人称奇的是,虽然大家对于当时物质生活的匮乏皆有同感,但深藏记忆之中的却多是于清贫中透露的生趣和美好。如果说回忆者通常会选择性记住在艰难中的美好部分是出于潜意识,那么促就这一潜意识的当是当年学子中普遍存在的,对国家和民族的信心、对个人未来的希望,以及基于这种信心而产生的乐观情绪。
抗战胜利后,在机关学校回迁浪潮中,西北联大(此时已更名为国立西北大学)也踏上返程。但它把骨架和精神留在了以国立西北大学为马首的众西北高等学府中。然战后的国立西北大学师生,旋即陷入又一场艰苦的考验中。1946年底,西安物价腾贵,公教人员薪津过低,生活濒临绝境,学生虽享有公费襄助,却也是勉强维持。为鼓励师生在艰难中坚定职守和努力学习服务社会,时任校长刘季洪教授一边支持西大、西农、西工各校教授们向国民政府联名请求调整薪津待遇,一边诫勉学生们“事业成功之基本条件有三:一为科学态度。二为建设兴趣。三为平民生活”[8]。继刘校长之后,陕西籍的马师儒、杨钟健教授先后出掌西大,更是发扬陕西人的精神,把勤朴、公诚的校训发扬光大,于濒临绝境的经济条件下,团结西大师生坚持教育学习。
是昔日联大在艰难孤寂中的静默自持,让弦歌未断之精神绵延不绝。
三、备战而黉舍宛然——军训生活中的“自由”
在何兆武先生口述的《上学记》一书中,曾提到当年西南联大的自由之风气令师生受益匪浅。相较而言,西北联大所驻留的西安,恰是促成统一抗战的西安事变爆发地,这令国民党对西安的高校监管格外严密。为防止一般青年思想分歧,投向中国共产党,以西安为发轫,国民政府命令从1937年夏开始,高中以上学校全体学生,必须接受二到三个月的集中军训。其训练宗旨为:指正青年思想,改善青年行动,养成尽忠报国、努力服务的革命青年[9]。抗战之际,军训更加成为青年学生掌握一定军事技能、养成抵抗侵略的能力,实现全民备战的重要内容和必然手段。本是读书声朗朗的校舍,因为统制青年思想和备战的需要,一时间恍若军营,要想延续大学自由民主精神,实非易事。然而,强制的说教和严厉的束缚并不能压制这群不断接受新知识和思想的青年学生。于是在“指正思想”的军事训练过程中,学生们活泼、率真的行为,恰似无辜的犯错,频频展现出压抑不住的自由天性和理性思考。
为配合“指正青年思想”的军事化教育要求,西北联大经校常委会决议,裁撤教务处,增设训导处,实行导师制。从一年级学生开始加强对个人思想的训导。要求学生每日临睡前完成一篇日记。以对自己生活的反省与认识为主旨(包括每日起居行动、思想、言语、修己、治学、应事、待人等),逐日略记,随见反省,述其迷悟。教员在文字、思想、事实三方面评阅后,再按周录送给各院主任导师,分别审核登记其生活情形,以利于训导。然后返还学生,逐周装订,每期一册,形成个人历史记录。导师及教员,则可随时调阅[10]10。大概这一规定,过分明显地透露了管制学生思想的用意,在一贯崇尚“自由”、“民主”的大学里,显然难以被师生们认同,有关这一极具个人生活色彩的资料,竟在联大校友多年后的回忆中,不见只言片语。有关这一规定的运行反馈等讯息,也在此后的联大校刊(含国立西北大学)中,寻无踪迹。至少表明,联大师生们更倾向于采取了遗忘和淡漠的方式,默默捍卫着他们的“自由”。
进驻乐城当年,西北联大即被编入陕南支队,举行首届暑期集训。雨中行军、集合待命、打靶、军事演习、阅兵,一系列的军事训练活动,让从未有过军旅生活的学子们兴奋,也让他们着实锻炼了一回体力,增长了军事常识。不过,学生们毕竟不是职业军人,虽然身体上的锻炼和意志上的磨练使他们受益匪浅,但教官们在思想上的强行灌输和行为上的专横做法却令他们难以认同,于是各种消极和积极的“抵制”就频频出现。
先是行动上“破禁”。在每次被教官用一两个钟点强迫灌输一套政治说教时,学生们大多采用直立注视而充耳不闻的方法熬过时间;反感教官声称“脏水不能饮,也不过两月”的蛮横,不顾教官严令去茶房偷净水止渴。因为不满于重体力训练,而轻视军事技能训练的安排,有的学生宁可被罚,在野训的极度疲劳之后,消极地走着跑步,也不愿遵行教官的严令,走在大街上高歌进行曲。
其次是对集训发生质疑。对于教官们习惯于用粗暴、武断的方式指责学生思想不够服从的做法,学生们不仅反感,更开始质疑集训的宗旨。原来,学生们大多希望到军队去,可以接受实用的军事技术训练,如军用电报电话等,但是集训令他们颇为失望。在训练队长官们看来,只要学生们由“文”的学校进入到“武”的集训中,就是文武结合了,其实就是把学生当作新招募的士兵对待。而在学生看来,大学的实验室和技术知识,如果能和军队的训练内容融合在一起,才能够算真正地文武结合。因此希望“以后的集训,应该是一个尽量包容文武的实质,尊重各自所学,而且彻底的合作起来,化合文武实质的一个学校,不偏重,不歧视,务使适合于国家民族之需要”[9]46。
因此,集训时期举行的出队会餐仪式反倒成为了学生眼中最富有生动教育特色的一项。当每队举行出队仪式时,全体教官和学生齐聚在校场,六人一组席地而坐,以中央的升旗台为中心,围成党徽的形状,每桌放一盆猪肉烩白菜,两盆馒头。奏乐升旗后,一声令下,伴随着管子号的节奏,大家开始狼吞虎咽。饭毕,时任汉中警备司令、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主任祝绍周专门对学生训话。称学生聚餐所排列的队形是一个“党徽”,中间是“国旗”,寓意国家是建筑在中国国民党的基础上,每一个青年都是构成党国的一份子,都有卫护党国的职责。吃馒头的用意,在于馒头象征着日本军阀的头颅,人人可得而食之等等。对于国难家仇之际的学生而言,尚无心分辨党、国之关系,倒是更多受到“饥餐倭奴肉,渴饮倭奴血”的激励,情绪为之一振。
大学本应是研究学术的重地,培养高级人才的场所,但在特殊时期,因为被赋予了特殊的角色,其功能也因此丰富。在战时条件下,在播迁的过程中,来自不同院校和地区的师生们朝夕相处,无论研究学习、工作生活都如同处于一“室”,形同一家,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西北联大师生独有的风格与传统。譬如,清贫生活的一致性,让师生对物质生活的态度趋于一致,淡化物质的匮乏,而注重精神的愉悦和乐观的情绪,在学生中形成了同学之间不分彼此、相互借助,甚至以获得前届传递下来的制服为荣耀的小传统。又如迁徙中院校的分分合合之间,固然有内部分歧的不悦,但师生们却始终保持着随时随地、结合地方资源和建设进行科学研究和学习的稳重务实传统。而在相对严苛的政治环境中,以静默自持的态度,保持一份思想的自由和教育的坚持,更是对匮乏和专制的默默消解。如果说,西南联大是一朵盛开的奇葩,长久地炫目于国人的视野中,西北联大则如汇集而成的一股温泉,永远地渗透在了西北广袤的厚土中。
[1] 国立西北大学建校三十周年纪念特刊[N].台北.1969.
[2] 李永森,姚远.西北大学史稿(1902-1949)[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
[3] 西北联大校刊[N].第2期(民国27年10月)至第7期(民国27年12月).国立西北大学学报(复刊)[N].第24期(民国36年3月)至第35期(民国37年1月).
[4] 西北联合大学校刊[N].第3期.民国27年10月.
[5] 西北临时大学校刊[N].第5期.民国27年1月.
[6] 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复刊)[N].第37期.民国37年5月.
[7] 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复刊)[N].第27期.民国36年3月.
[8] 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复刊)[N].第29期,民国36年5月.
[9] 西北联大校刊[N].第12期.民国28年3月.
[10] 西北联大校刊[N].第9期.民国28年1月.
刘俊凤,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社会生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