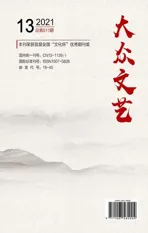回还是不回
——论旧海棠《橙红银白》中的女性形象
2017-03-11肖佳敏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10097
肖佳敏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210097)
回还是不回
——论旧海棠《橙红银白》中的女性形象
肖佳敏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210097)
在被现代化文明定格成“劳动工具化的人”的压抑困顿中,底层文学中的女性生命群像却越发鲜活、丰富起来,颠覆了以往任何文学史阶段的女性形象特征。正如《橙红银白》的独特之处,作者通过对一系列与传统女性形象愈来愈远的富有层次感的底层女性形象的侧面塑造和她们不论走进还是走出城市所作出种种选择而承受的阵痛的书写,揭示作者对被金钱社会异化的底层社会的观察和深刻思考。
《橙红银白》;底层文学;女性形象;回乡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社会转型的日益深化,“底层”这个词逐渐占据了人们的视野,一般是指生活在乡村的农民。而底层文学应运而生的大背景则是,由于社会的阶层结构分化以及群体差异越来越明显,导致社会矛盾也逐渐激化,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各种社会冲突也逐渐增多。《橙红银白》是作者旧海棠发表于《收获》2016年第4期的小说,俨然也是一部底层小说,整个故事以“我”(城市女青年)为视角,讲述了来自农村的三叔的家族史、进城打工史和辛酸的寻女史,在看似冲淡平和的基调中显示了对底层失败的深刻透视与关切,也完成了对底层人物造成伤害的社会原因和人性原因的深入分析。
一
《橙红银白》开篇第一句话便是:村庄空了。与城市相比,农村总是作为落后、凋敝、空旷的代名词出现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这样的开头乍看让人觉得未免老掉牙,然而接下来三叔与女儿回回的对话,颇具静谧的乡村画面感,不仅透露着三叔对过去农村的苦涩涩的眷恋,“村庄空了”,更是叹息、更是沉重。三叔三婶那一代人不可避免地从乡村走出去——置身于波澜壮阔的市场化进程。而烟囱里余烟袅袅的灵动,是对生活于其中的淳朴善良和勇于坚守等中国传统女性优良品质的最好诠释。然而现实是,恬淡宁静的乡村世界早已不能拴住所有女性的心,繁华时尚的城市对乡土世界中的淳朴女性频频招手,于是村庄里的女人便也是空白的了。
我们不难从作品中发现,在回回与三叔对话的后,《橙红银白》中第一位正式出场的女性是三婶。三婶似乎如同其他进城的乡村女性一样,所能从事的工作无非就是做工厂里的“一颗螺丝钉”,或者就是打杂工、卖东西,要么就当餐饮行业的服务员……总之,作为“三无人员”(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没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没有可靠的政治关系),像三婶这样的农村女性在城市只能从事最繁重的活动,城市对于她们辛苦的劳作仅仅给予可怜的物质(金钱)回报。然而,“三婶性子蔫,胳膊腿动作都慢”,“外面的活也干不好,经常辞工”,于是在所谓老乡张生的“追求”下,三婶换了工作,去了张生常常合作的五金店卖东西,接下来便有了老实巴交的三婶对婚姻的背叛。作为乡村女子的三婶被包养、抛弃,三婶最终还是回归了,寓意着三婶这类底层女性对乡村妇女的身份是根本无法真正摆脱与拒绝的,也折射了她们所面临的极为脆弱驳杂的两性关系和婚姻关系,说明她们在维持基本家庭稳定和发展过程中需要让渡的生活选项。
那么“回归”后三婶的命运又是如何呢?作者给了我们一个前后呼应的回答,“得好好养孩子,这是她出来后最大的觉悟了”,三婶又和三叔过在一起后,三婶对回回的教育理念受到了三叔的赞同,她不仅给女儿回回寄钱写信、报各种培训班,更是在回回念初中、高中的六年中在县城租了房,专门照顾回回。然而在高考前几个月,女儿回回却突然叛逆,为了逼女儿参加考试,三婶不惜拿刀捅向自己,由于失血过多,落下半身不遂。这结局说明,无论外出务工,还是留守乡村,三婶们都难逃被支配的命运。从根本上说,三婶们属于在社会现代化浪潮的裹挟下受挫的底层女性,她们虽然能走出家庭,走出乡村,走出“夫权”,最终却不得不“回”,因为尽管现代性在一定程度使底层女性打开原先封闭的空间,但某种意义上,她们进入社会,并非真正从所谓的“私领域”进入“公领域”,可以说她们只是从一种被支配状态(家庭)进入另一种被支配状态(社会)。
二
三叔、三婶以肉身磨砺在迁徙时代寄托一个脆弱的“底层梦”——女儿回回的上大学。回回,这个名字显然含有深意,回字两个口,像是要诉说无穷无尽的话语,然而作为小说中最重要的人,回回却总是沉默的,她内心的态度都是被隐藏起来的,只能猜测而无法直观。在高考的关口究竟发生了什么致使本来成绩很好的回回死活不去参加考试?她又是为什么进了监狱?是什么使她毅然决然地弃绝故乡、家庭和亲人?沉默的回回于是也成了一个现代性的象征:无数个体的卑微经验,始终处于社会压抑和自我压抑的沉默之中;“回”的意义是归来,可小说中回回却一去不复返,这暗示着对于新一代底层女性来说,故乡在她们身后沦陷,她们没有乡愁,她们迫切地去融入五光十色的世界;“回”的谐音有悔、毁等,在很多文学作品中像回回一样在乡村长大的姑娘单纯、透明、真实、可爱,对于生活和未来抱着美好的憧憬。《橙红银白》中明显呈现了三叔对没照顾好女儿的悔恨和金钱社会对底层女青年人格的异化。
为了寻找回回,三叔辗转于深圳的工地打短工。他所建筑的商务大厦将要成为中国第一高楼,也是新的城市地标。此时他得以隔着玻璃见识了展示中心的VIP洽谈室以及这座现代大厦不明来历的高级经理(公关小姐)。她的美丽、衣着和使用的最新苹果手机都让三叔印象深刻,她关了手机向里走的时候所爆的粗口“操”,也令三叔想起了寻女路上碰到的“橙红银白”那两个女孩。“橙红银白”也即小说的题目,指两个长着很长指甲的女孩,一个女孩的指甲涂成橙红色,另一个女孩的指甲涂成银白色。不管是如“橙红银白”般烫发、染指甲、戴墨镜、背挎包的时尚女孩,还是摩登大楼里走出来的所谓“高级经理”,装扮使她们跟本来容貌相距甚远,可是她们来自何处?作者暗示着,他们不是回回,可她们分明都是回回。这些乡村里的麻雀扑腾扑腾地飞向城市,成了玻璃房的金丝雀。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现代都市随处可见的女孩,她们随口爆出的粗口也惊人地一致。当她们爆出粗口的时候,她们自如地运用着一种男性的语言;在更宽广的社会体系中,她们也不可避免地陷身于一种异己的语言秩序之中。在这种横向的对照中,我们看到作者一种鲜明的返源意识:她分明要我们知道无数巍峨高楼的出处,要我们知道无数都市丽人的来路。玻璃镜面的现代高楼一旦投入使用,便不再接纳衣衫陈旧的建筑者;而光鲜亮丽的都市金丝雀,也拼命切断自己跟故乡的关联。如果说,三婶们那样的底层妇女身上还有忍耐、满足等女性图腾,那么更年轻一代的回回们则显得更加雄化和无性化,这是回回们在城市中的的生存状态,也是作者的审视和呐喊。
三
《橙红银白》中三叔寻女后最终到合肥来找叙事者“我”和“我”的弟弟大鹏,由于“我”和弟弟在大城市的住房都很紧张,两家都不能腾出地方来让三叔好好居住,三叔的悲痛一时间都无处安放。“我”其实也是从乡村走到大城市里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没有太高学历的底层女性,“我”既不属于“高级经理”那种层次,也不在回回们那种层次中,但“我”不仅是有作为城市底层女性的自省意识,也有对现代社会物欲横流中人性异化的反思和对同为底层女性的关切,但 “我”不愿听三叔絮叨的这种抗拒心理也说明了对乡村的抗拒,同时也代表“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和裹挟的一类底层女性罢了。
底层小说通常通过讲述老百姓的故事,来突现出现代生活本身的平淡和复杂,《橙红银白》中作为女性“我”的发声,使得作品不像传统底层叙事那样为批判和超越现实而努力,同时也并非现代主义作品中的主人公那样为人为异化的现实而焦虑痛苦。作者始终与现实和平相处,与生活处在同一平面上,她眼中的三叔既无反抗也无反思,他活着,如此而已,有种“余华式”的生命哲学化思考。作者对此也津津乐道,似乎不愿意去评价和干预所有有关的人和事,似乎想保持生活原有的诸多矛盾和原始形态,但是最拒绝煽情的作品却最令人痛不欲生,这就是简单的力量。
小说作为作家的一种生命形式,一种对生活发言的媒介,不可能没有思想和理性,正如塞米利安在《现代小说美学》里写的:“在小说创作中,作者的彻底的客观态度显然是一种幻象,没有一个作家在写作中能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底层生活小说的作家由于写作视角是从“生活内里写起”,因而他们都尽量避免在人物或是非方面做判断,同时又需要借小说表达出自身的生活理念,与读者交流,这种交流因为小说“叙述”内容的表达方式即叙述话语的魅力的存在而达到了审美的高度。“我”作为底层女性的身份来讲述,对三叔不单单是一种怜悯、同情,更是一种对个体生命的理解和尊重,不仅仅以一个清醒的旁观式角度为底层人物鸣不平,而且以平民化的视角为底层人物鸣不平,为底层人物的世俗的生命欲求而申诉。作品中的“我”的这个视角与社会启蒙角度不同,这种角度应该属于一种平民化的人文关怀,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或呼吁,不是通过对他们的生活的表现来阐明某些知识分子的立场,而是把文学性的表现真正落实在底层民众的人物形象上面,在美学意义上重建他们的生活。这种角度,着重描摹底层的日常生活、生命体验、世俗欲望和内心世界。作者的基本情感立场是同情和理解,是最底层境遇的申诉和发泄,是对底层灵魂的承认和呵护。这种角度更能让读者接受,其审美效应给读者更多的是一种关切、感动和温暖。只有在展示现代文明对底层群体的主体意识和文化观念的内在塑造中、底层叙事的内涵才有可能被真正开掘。底层创作在面对生活的苦难时,对底层群体的悲悯情怀应当务求理性的介入,避免悲情的泛滥。只有以理性的心态变现苦难,才有可能做到情绪的节制和情感的升华,而这将深刻影响到作品的审美范式、表达效果乃至思想深度。
[1]旧海棠.橙红银白[J].收获,2016(4).
[2]塞米利安.现代小说美学[M].宋协立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3]刘继明,李云雷.底层文学.或一种新的美学原则[J].上海文学,2008(12).
[4]孟繁华.底层经验与文学叙事[J].当代文坛,2007(4).
[5]孟繁华.女性文学话语的实践的期待与限度[J].文学自由谈,1995(4).
[6]吴著斌.底层文学在新世纪的总体特征[J].文学教育,2012(3).
[7]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