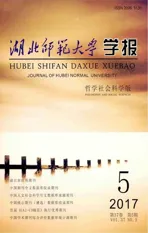幸福标准的社会性建构与主观幸福感
2017-03-10熊辉
熊 辉
(湖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幸福标准的社会性建构与主观幸福感
熊 辉
(湖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个体的幸福标准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主观建构的,它来自于个体对其主要参照对象的选择与比较。不同个体对主要参照对象的选择或建构不仅具有不同倾向性,而且还会在平行、上行、下行参照对象之间进行转换。一般来说,个体更多地根据其平行参照对象来考量自身幸福程度,但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个体将其上行参照对象“平行化”并据其“建构”相应的幸福标准。个体对其平行参照对象与自身之间相对较小的差距不太敏感,也能接受其上行参照对象与自身之间不是太大的差距。但是,如果差距超过了个体所能够容忍的范围,个体就会产生不公平、不公正感,并进而感受到不幸。
幸福标准;社会比较;参照对象;建构;主观幸福感
一、幸福与幸福标准
“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讨论话题和终极追求目标,但人们对“什么是幸福?”的问题经常感到迷茫,历史上的亚里士多德、康德等人也均曾表达过幸福概念难以界定的观点。这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情境之下,对幸福的感知或体验通常并不具备一贯性。实际上,当我们在大街上询问“你觉得自己幸福吗?”的时候,处于甜蜜热恋中的情侣可能会给予肯定回答,而当他们正在为购买婚房问题而大伤脑筋时却可能给予否定回答。央视记者也曾走遍大街小巷、天南地北,发出关于幸福的追问,大部分面对镜头的民众却表现出一脸的茫然。[1]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正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所说的“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之间的分离造成的,即,“幸福”二字通过其形、其声可以覆盖生活世界中所有的观念、所有处境下各个方面的“幸福”,而在具体情境下,个体要么不能确知他人提出的“幸福”二字具体所指是其自身工作、恋爱婚姻状况还是生活条件、家庭关系抑或是其他方面,因而无法回答自己幸福与否的问题;要么按照自己当下情形进行理解,更多是根据其当下自身经历的主导事件所引发的主导心境予以回答。“长期以来,人们关于幸福问题的探讨之所以始终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在相当程度上要归咎于他们在使用语言表达自己思想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分离。”[2]
但是,即便历史上存在着幸福条件论(外在因素)、快感论(身体因素)、心态论(精神因素)[3]等多种主张及其价值导向之争,但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在谈论或评价自身幸福程度时,最后均指向人类自身的各种欲望,尽管其“所指”宽泛且充满不确定性。用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幸福是欲望的满足”,也就是说,个体是否幸福的本质,必须从个体的主观感受即欲望是否满足之中去寻找。后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从经济学角度给出的幸福方程式,即:幸福=效用/欲望,则直接点透了幸福产生的本源。
这里的欲望,其实就是人们的欲望满足期望值,也就是其幸福标准,既有原始本能的,也产生于个体社会化过程之中,既有物质方面的,也包括精神方面的;效用,则是欲望的实现程度。一直以来,人们一方面强调通过提高效用(欲望满足程度)获取幸福,另一方面,似乎人们早就明确了解效用直接针对欲望起作用,故而有世界范围内的控制欲望之说和中国人的“知足常乐”之劝导。然而,人们始终难以对产生幸福感的核心——欲望满足期望值与欲望满足程度——给出一个明确、具体的答案。
实际上,人们欲望期望值——即幸福标准——的种类和高低大小,无论是具体明确的、模糊的还是隐藏在内心深处而不自知的,均来自于个体的社会比较。人们正是通过参照自己选定的个体或群体的现实状况“建构”了自身的“欲望标尺”[4]或“幸福标准”,因而,人们对自身是否幸福的认识具有参照性、比较性与相对性。
二、社会比较
物理学界的相对论曾引起过强烈的质疑和震动,但社会生活世界的相对性却一直并未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作为相对主义社会理论之一的社会比较理论从其产生、发展到具体应用上一直都存在着这样的困扰。历史上,虽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人早就讨论过社会比较问题,边沁、卢梭、康德甚至马克思也发现过社会比较的力量,但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我”(W·James)、“镜中我”(C·H·Cooley)、符号互动(G ·H·Mead)等概念和理论中才直接包含有社会比较思想,而到1954年,费斯廷格(Festinger)才第一次提出了社会比较的概念和理论,这也是历史上的经典社会比较理论。社会比较理论揭示了一个不言自明、但往往被人们忽视的事实: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个体进行自我评价、自身定位的真正直接的、客观的标准,他们总是通过与相似他人的比较,来评价自己特征和在群体中所处位置[5]。
虽然社会比较理论的提出被认为是人们开始用相对主义的视角来认识生活世界的重大突破,但是,令人感到讽刺的是,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个体一直就是社会中的个体,人们也一直是在与人的相处和互动中,彼此比较、参照,并据此来确定自己的态度、行为和所处位置的,而且人类社会的这个事实一直存在并将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是,人们却并不愿意直面幸福社会建设中真实且普遍存在着的社会比较现象,反而在强调经济学效用的思想影响之下,忽视了人类个体依据社会比较进行自我定位的天性,片面强调财富的增长与幸福感提升之间的因果联系,淡化甚至忘却了平等、公平、公正才是幸福之基,从而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出现所谓的“伊斯特林悖论”成为必然。
我们应该确知,在现实生活中,个体为了在日常生活中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定位,总是选择那些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的对象作为参照,并通过与该参照对象的比较来判断自身在现实世界中所处的位置。个体对幸福生活的感知,离不开对幸福概念的理解,更离不开与他人所进行的社会比较,社会生活中的个体,总是通过与参照对象生活状况的比较来确定其自身的幸福程度,因此,个体所选择的幸福参照对象直接影响着个体幸福标准与幸福感。
三、幸福参照对象的选择与幸福标准的建构
人类个体通过对参照对象的选择来建构自身的幸福标准。
对参照对象的研究来自于参照群体理论。早在1942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海曼就在研究个人社会地位时提出了参照群体的术语,1943年,T·M·纽科姆则运用参照群体的概念来研究大学生的社会观点,认为个人在心理上所从属的群体即其参照群体[6]。直到1949年,默顿才在其《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一书中,引入参照群体概念探讨“相对剥夺”问题,并从社会学角度系统地论述并确立了参照群体理论。
一般而言,参照群体可以分为规范参照群体和比较参照群体。规范参照群体是帮助个人确定并实施行为准则的群体,比较参照群体则是为个人提供与自己、他人、群体相比较、评价的标准和参考点[7],用以确定自身状况的群体。人们的幸福参照对象属于比较参照群体范畴,个人选择的幸福参照对象可以是某一特定的个体,也可以是某个特定的群体,还可能是虚构的个体或群体。
众所周知,社会比较理论经过多年的发展,提出了平行、上行、下行三种参照对象与比较类型,并对比较过程中的心理效应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社会比较的建构性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Goethals于1986年提出的建构性社会比较理论[8]认为,在社会比较过程中,出于某种动机,个体可能伪造或忽视现实信息,仅仅依靠想象主动建构或虚构他人的信息,并与自己头脑中建构的信息进行比较。
事实上,人们对自身的各种幸福参照对象的选择均是一个建构性的社会比较过程,不仅经历着“比较——选择——对比评价——再比较——再选择”等循环阶段,而且贯穿了人类个体的整个生命历程[9]。并且,在人的一生中,随着个体自身所处环境的变化和人生主要任务的改变,个体对参照对象的选择发生着相应的阶段性变化。人们在选择自身幸福参照对象时,主要遵循接近性原则、相似性原则、信息可获得性原则。毫无疑问,一般情况下,人们总是选择那些自己比较了解、与自己地理空间接近且在年龄、职业、学历、能力水平等方面有着相似性的个体或群体作为幸福参照对象,但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平等价值观的普及,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却可能以他所了解的任何人作为他的比较对象。另一方面,个体所选择的参照对象既可能是生活中实在的个体或群体,也可能是虚构与想象的。在西方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很好地说明了这种状况:“拿破仑嫉妒凯撒,凯撒则嫉妒亚历山大,而亚历山大却嫉妒根本不存在的大力神”。现实中的人们也是如此,他们不仅根据相似性并在接近性、信息可获得性原则的引导之下,将真正具有可比性的他人纳入自己的比较范围,而且也有可能为了达到某种比较目的,通过突出或夸大他人与自身之间的相似性,忽视二者之间差异性的方式,将那些在相似性较少、客观上不具可比性的他人纳入自己的参照体系之中。
这样,个体的幸福参照对象是一个包含着各种向度(收入、住房、职称职务、子女教育等等)的差序系列,每一个向度都包括平行、上行、下行三种参照对象。其中,个体在某一具体的人生阶段或具体的情景之下,总是最为关注某一向度,并在这个向度选择上行、平行与下行参照对象,且将其中一种作为主要参照对象,其他作为次要参照对象,有时还以某个个体或群体作为临时参照对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个人对幸福参照对象是一个建构性的系列,或称参照系,每个个体都会与他自身建构的三个层级的参照对象进行比较,并在比较过程中进行自我定位。其中,主要参照对象是个体建构自身幸福标准的最主要依据,并对个体的幸福感造成直接影响。个体所选择的主要参照对象不同,其幸福标准与幸福体验也就不同。
四、主要参照对象选择的倾向性与主观幸福感
不同个体因所处环境和自我评价、自我期望以及自身人格特点的不同,不仅关注的幸福向度不同,而且,在该向度上对主要参照对象的选择也具有的不同的倾向性。一般来说,个体倾向于主要与平行参照对象比较可基本维持幸福感,倾向于主要与上行参照对象比较会降低幸福感,而倾向于主要与下行比较对象相比则会提升幸福感。
(一)主要参照对象的平行选择倾向性与主观幸福感
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个体在大多数时候,倾向于平行选择主要参照对象,并据其现实状况确定自己的幸福基准。只要个体感觉到与其主要参照对象相比“不差”、“还行”、“差不多”,他就会有“总体幸福”的自我评价。如果个体明确觉知到自身与其“平行参照对象”相比“更好”,则会提升其幸福感,相反,则会降低其幸福感。
但是,人们并不能忍受自己的现实处境比其“平行参照对象”“差很多”。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在社会比较中,大多数人认为自身的能力、成就等高于一般人(“优于常人”效应[10]),他们往往很难接受他的平行参照对象即他心目中的“一般人”比自己“好很多”的现实,如果在自己的工作与生活中,他的平行参照对象即他心目中的“一般人”比自己“好很多”,他就会因此产生相对剥夺感,并在体验到不公平的同时也感受到自身的不幸。
(二)主要参照对象的上行选择倾向性与主观幸福感
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着自身定位和期望较高、喜欢上行选择主要参照对象的个体。一种情况是,有的个体习惯于以其上行参照对象的现实状况作为自己的现实幸福标准,这样的个体往往幸福感较低。事实上,他可能逐渐将其上行参照对象予以“平行化”,即突出二者之间的相似性,弱化或忽视差异性,即认为其选择的上行参照对象其实跟他“差不多”,自己也应该有与他相似的“幸福生活”。另一种情况是,在自我完善、自我进步动机的驱动下,很多个体倾向于以上行参照对象的现实状况为主要依据来制定其未来幸福标准,期望通过自身努力,在将来也能达到与其上行参照对象相似的结果。一般来说,这种状况对个体总体幸福感水平的影响不大,因为,虽然此时个体可能明确意识到他主要与其上行参照对象进行比较,但他其实内心仍然在明确地把自己归结为比其上行参照对象低一层次、并在潜意识中仍旧以其平行参照对象为依据判断自身幸福程度。换句话来说,个体意识中的未来幸福参照对象其实仍然是其现实中的次要参照对象。如果个体在现实生活中逐渐接近其上行参照对象水平,他会经常体验到快乐和幸福;但是如果遭遇多次失败或者是渐行渐远,而他意识中与其上行参照对象比较的意愿仍然十分强烈,则他会感到强烈的不幸,而在此时,其上行参照对象也就转变为其主要参照对象了。
现实生活中,人们承认自身与其上行比较对象之间的差别,也能够接受与其上行参照对象之间在现实状况上的明显差异。但是,如果人们的上行参照对象比自己“好太多”甚至数倍、数十倍,那么人们则很难接受。因为,出于维护自我尊严、自我价值的需要,人们不可能承认其存在价值远远低于上行参照对象,相反,他会认为该结果是对自己的一种贬损或剥夺,并进而产生不公平感和不幸感。以个人收入为例,现实中的个体,虽然他可能承认自己(的能力、贡献等)与其具有可比性的上行参照对象相比有差距,但他会认为只是“差一点”、“差不太多”,因而也就不能接受其上行参照对象的收入比自己高很多的现实(或许可以称之为“差不太多效应”?),并进而抱怨甚至指责分配制度的不公等等,从而加深自身的不幸福感。
(三)主要参照对象的下行选择倾向性与主观幸福感
日常生活中,一些自身定位和期望较低的个体,习惯于下行选择主要参照对象。这样的个体,往往有较高程度的幸福体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或许个体在主观认识上其实已经将其下行参照对象视作平行参照对象了。
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由于个体地位及其所处社会文化环境、自我定位、价值观的改变,其主要参照对象可能在上行、下行、平行之间发生变化或转换,进而影响个人幸福标准与幸福感。
五、主要参照对象的平行化转换与主观幸福感
在个体的生命周期中,由于社会环境和自身状况的变化,不仅其选择的参照系发生建构性变化,而且其中的主要参照对象也会在平行、上行、下行序列上发生建构性的转换。
(一)上行主要参照对象的平行化转换与主观幸福感
“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生活动力,这是一个明显的真理。如果不去或不能追求幸福,生活就毫无意义。”[11]社会化的个体,不得不屈从于这种主流社会生活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意义化的“幸福驱动力”(即个体追求幸福、积极向上的动力),也给绝大多数人带来巨大压力。一些研究发现,人们在心情糟糕的时候,更容易进行上行社会比较,在心情愉悦时则更多进行下行比较[12]。在很多情况下,个体经常会面临影响他“幸福生活”的重大压力(如现实生活中的住房、收入、职务职称晋升等等),此时的个体,可能在压力源方向上临时选择上行参照对象,如果其压力长期难以缓解,就会产生无尽的焦虑和烦恼,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可能频频进行上行比较。
当个体对上行参照对象进行比较的频率超过对平行参照对象比较的频率、因而其上行比较对象成为其主要参照对象的时候,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个体已经真实地与其上行比较对象处于同一层次,因而将原先的上行参照对象予以“平行化”,我们可以将其称为“自然平行化”(一种真实的平行化),此时,个体的幸福感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部分个体并不自足,在“幸福驱力”的作用下,他会重新向上寻找参照对象,若经过“努力”仍未实现其目标,他会因此重新体验到新的不幸福。另一种情况是,个体虽然意识到自身与上行参照对象在基础条件(如学历、地位、职业等等)上的差距,但在经常的比较过程中,不自主地以上行参照对象作为自己的主要参照对象,因此会更经常地体验到不幸。还有一种情况是,个体在经常的上行比较中,通过“突出相似性,弱化或忽视差异性”,将其上行参照对象进行“简单平行化”(一种虚假的平行化),即认为自己与其上行比较对象“其实是一样的”(如都是中国公民),此时,个体会就感受到强烈的不幸福。当然,个体在感受到不幸的时候,一般会主动进行平行或下行比较进行自我调节,以保持自我的心理相对平衡,使自己的幸福水平不致受到太大影响。
个体上行比较的频率取决于个体对自身的期望或目标定位、与上行比较对象接触的频率、对上行比较对象信息的掌握程度等等。“幸福驱力”或者“幸福压力”推动个体进行上行比较。在现实中国社会,不仅社会流动性增强、信息高度透明和通畅,而且个人生存与生活状况(如收入、住房等等)日益分化,人们的功利意识和平等意识也普遍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常常选择上行参照对象作为自己“幸福生活”的主要参照目标,一些人甚至基于某种相似性对上行参照对象予以平行化转换,并因此感受到强烈的不幸。在互联网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这种比较,青年农民工抱怨自身生活水平大大不如城市市民,普通国企职工对自身工资收入大大低于垄断性国企严重不满,普通市民又对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享有更高的医疗、养老保障愤愤不平……,他们的不满均来自一种说辞,即他们与比较对象有着“相似性”:都为国家建设付出了辛苦劳动、都是国家职工、甚至都是平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种简单平行化在造成不满和不幸福感的同时,将矛盾焦点指向了政府管理与相应的社会制度,进而产生社会不幸感。
(二)下行主要参照对象的平行化转换与主观幸福感
人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事事如意的。当个体在遭遇到失败或体验到不幸的某一时期,也可能临时与其下行参照对象比较,以维持自我概念,保持心理平衡,从而使自己的总体幸福感不至于下降太多。也就是说,人们在此时进行下行比较只是一种“为了使自己现在的自我感觉好一些”的应对策略。但是,如果个体长时间、反复地进行下行比较,不仅会在潜意识中产生一种自我认同感,降低其成就动机和对良好结果的期望,以至于不利于个体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而且,当个体的下行比较的频率高到使其下行参照对象成为其主要参照对象的时候,他就实际上已经将其归类至原来的下行参照对象同一级别,其原先的下行参照对象也就自然转变成为平行参照对象。在此过程中,个体先是感到不幸,但经过其一段时间的下行参照对象平行化适应之后,其幸福感将会有所回升。相反,若个体长期不愿进行下行参照对象平行化,则他会长期感受到不幸。
另外,Lockwood[13]的研究发现,与下行参照对象的比较对自我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单一的:如果个体感觉自己不会像下行参照对象一样不幸时,个体会感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从而对不幸感起到平抑作用;但如果个体感觉自己也会与其下行参照对象一样不幸时,个体会在感到其自我概念受到威胁的同时,提高保护自己免受同样命运的动机。
总体上,将下行参照对象予以平行化的个体较少,大多数在生命历程中处于下降趋势的个体均不满足于将其自身归类于其原先的下行比较对象之列,因而并会产生持续的不幸福感。
六、讨论:平等、公正是幸福社会建设之基
历史上,有很多学者对通过欲望的满足获得幸福持不屑态度,叔本华就曾说过:“凡夫俗子们以他们的身外之物当作生活幸福的根据,如财产,地位,妻室儿女,朋友,社交,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切;所以,一旦他失去了这些,或者一旦这些使他失望,那么,他的幸福的基础便全面崩溃了。换言之,他的重心并不在他自身。”[14]诚然,要获取幸福,单单只讲影响幸福的外在因素(条件论)并不靠谱,但倡导通过调整心态、控制自身欲望来“获取”幸福充其量也同样只能是一种“心灵鸡汤”。然而,我们无法否认,个人的幸福感与欲望直接相关,而个体欲望又是参照其所选取的参照对象而“制定”或“建构”的,也就是说,个体通过与他人的社会比较“建构”了自身的幸福标准。即,个人幸福标准是个体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互动,主动选择参照对象,并根据其主要参照对象状况,进行社会化建构的结果。
现代社会是一个流动性强、交通发达、信息开放且平等、公正价值观普及的社会,从理论上讲,个体可能将任何他接触到一定信息、并认为具有可比性的他人纳入其自身的幸福参照对象的范围之内。因而普通工人与公务员比较工资与待遇、农民工与大学教授比较辛苦程度和收入也就不足为怪。这种比较尽管不靠谱、也不被社会所接受,但的确能够给政府以警示:人们的幸福参照对象具有建构性,这种建构性的幸福标准以平等、公平、公正价值观为导向。
一个称职的政府,其最基本表现是能够架构和维护使其公民具有强烈的幸福感的社会。其幸福社会建设行动不仅仅在于物质条件的创造与幸福观念或心态的引导,更在于“干预”社会个体幸福标准的建构过程。而这种建构,其本质则是个体对其幸福参照对象的选择与社会比较过程。如上所言,在日常生活中,个体更多地选择平行和上行参照对象进行社会比较,他们对其平行参照对象与自身之间相对较小的差距(收入、地位、机会、权利等等)不太敏感,也能接受其上行参照对象与自身之间不是太大的差距。如果差距超过了个体所能够容忍的范围,个体就会产生不公平、不公正感,并进而感受到不幸福。因此,在人们的基本生存条件已经得到满足的中国现实社会,通过平等、公平、公正社会的建设和有效的国家调控,努力缩小个体之间的差距特别是权力和利益分配方面的差距,就可能形成大多数个体任意选择的主要参照对象状况与自身状况保持在相对较小、可接受的范围之内的基本格局,从而使“最大多数人感受到最大幸福”。然而,过度的平均必然带来效率低下的问题,究竟把人与人之间的差距限制在多大范围内,才能够既使人们感到可以接受并且觉得公平、公正、幸福,而又使其在实际运作中不至于影响经济和社会运行效率?这是我们在幸福社会建设中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另外,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社会公共秩序、公共环境卫生等对每个人的幸福感都施加同样影响,要提高个体的社会幸福感,必须对其进行全面改善或提高。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讨论并未涉及到个人幸福的纯情感层面,也未涉及到个人因生理原因或遭遇危机事件所引发的不幸,这些方面的幸福干预,需要另外一种宏观架构,如国家或地区层面社会工作体系的宏观建构与微观运作等等。
[1]蔡若愚.国民感觉不幸福,是因为不理解幸福的定义[N].中国经济导报,2013 年2 月19 日第 B06 版.
[2][3]俞吾金.幸福三论[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
[4]熊 辉.幸福感述论[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
[5]Festinger,L.“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Human Relations,1954,(7).
[6]秦晓敏,盛敏.参照群体理论综述[J].管理与财富,2008,(11).
[7]范玉静.中国农民工核心比较参照群体的选择[D].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8]Suls J.M,Wheeler L.,Handbook of social comparison:Theory and research.New York:Plenum press,2000.
[9]熊 辉.幸福参照对象的选择原则与类型[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
[10]周爱保,赵鑫.社会比较中的认知偏差探析:“优于常人”效应和“差于常人”效应[J].心理学探新,2008,(1).
[11]赵汀阳.论可能生活:一种关于幸福和公正的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2]李亚玲.对西方社会比较研究的新认识——社会建构主义视域[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13]Lockwood P.,“Could it Happen to You? The Impact of Downward Comparison on the Self”,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2,(3).
[14]叔本华著,范进等译.叔本华论说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责任编辑:胡乔)
Socialconstructionofhappinessstandardandsubjectivewell-being
XIONG Hui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Hubei normal university,Huangshi 435002,China)
The individual’s happiness standard is what the individual has subjectively constructed in social life and it comes from the individual’s choice of and comparison with the major referents.Different individual has not only different tendentiousness to the major referents’ choice and comparison,but also changes between parallel referents,upward referents and downward referents.In general,the individual measures his own happiness more by the parallel referent,but in real life,more and more individuals parallelize his upward referents and then “construct” the corresponding happiness standard according to that.Generally,the individual is not too sensitive to their relatively small gap between himself and the parallel referents,and he can also accept a not-too-big gap between himself and his upward referent.However,if the gap goes beyond the range that the individual can tolerate,the individual can feel unfair or unjust,and then feel unhappy.
happiness standard; social comparison; referent; construction; subjective well-being
C91
A
2096-3130(2017)05-0063-06
10.3969/j.issn.2096-3130.2017.05.016
2017—03—09
熊辉,男,汉族,湖北新洲人,湖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社区与社会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