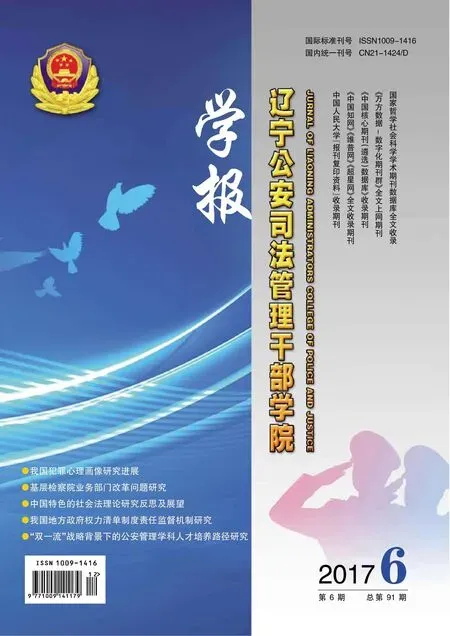中国特色的社会法理论研究反思及展望
2017-03-10丛晓峰
黄 涛,丛晓峰
(济南大学,山东 济南 250022)
【法律理论研究】
中国特色的社会法理论研究反思及展望
黄 涛,丛晓峰
(济南大学,山东 济南 250022)
对我国社会法理论研究的内容进行横向梳理,按照必然性研究、实然性研究、应然性研究进行分类。在必然性研究中,社会法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学者们已经取得了基本的共识;在实然性研究中,学者们讨论的语境不同,导致社会法的内涵与外延难以界定,难以形成理论体系建构的共识,但这种理论争鸣也体现了学术研究的繁荣;在应然性研究中,社会法的价值取向渐趋明朗,只是在表述上各有侧重。社会法是最接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的法。社会法的研究应立足中国土壤,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方向。
社会法;理论研究;述评
社会法理论研究历程,与我国制度建设的实践密不可分,也与社会形势的发展、社会问题的凸现密切联系。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法理论研究经历了初步摸索(1979—1992)、成长发展(1992—2000)及繁荣发展(2000至今)三个阶段。*钱继磊等根据中国期刊网对社会法研究的论文进行了时间上的梳理,实证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法研究的三个阶段。当然,我国的社会法研究早在解放前因循于德、日等国已经展开。参见钱继磊,赵晔.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法研究的实证研究———以中国全文数据库为样本》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4期社会法研究的三个阶段与我国制度建设的发展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也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需要政策的调整。政策推动立法实践,立法需要理论研究,理论研究反过来又影响制度建设。时至今日,社会法研究方兴未艾,学者们继续进行基础理论探讨的同时,也通过社会法的视角来分析更为具体的法律现象。更多的学者们突破了“学科为限的思维”,而转向“以问题为导向”的思考,从不同学科及思维范式中汲取资源为其所用,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将问题一步步推进,实现“知识的增量”。*邓正来语 参见 哈耶克的社会理论——《自由秩序原理》代译序,《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 1997年版 第2页完整意义的法学研究,一般包括必然性研究、实然性研究和应然性研究。*张文显认为,完整意义的法学研究,应当包括必然的、实然的、应然的研究,并对三类研究的内容作了说明。笔者认为这是对理论研究内容的横向分类。本文借鉴其思想,为了理论梳理的方便,对三类研究的内容作了限制性解释。本文所界定的必然性研究,是把社会法作为一种法的现象,研究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演化过程和途径,探讨社会法存在的必然性;所界定的实然性研究,是把社会法作为实然法,分析已经存在的社会法的性质特征、功能定位、运行机制等;所界定的应然性研究,是把社会法作为应然法,研究社会法的价值,包括价值取向、价值目标和价值标准等。三类研究的内容是彼此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之所以把我国学界对社会法的理论研究进行分类,目的是探寻我国社会法理论研究有哪些分歧,为什么会产生分歧,存在哪些理论共识,以期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法理论体系的建设有所裨益。
一、必然性研究——基本取得的共识
作为一种法律现象,社会立法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应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应运而生的。如果说农耕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公法发达的时期,工业社会(资本主义初期发展阶段)是私法发达时期,20世纪以来的现代社会则是社会法发达的时期[1]。作为一门法学学科,现代社会法理论的研究早在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俾斯麦时代就已经开始。因循于我国现代立法的传统,民国时期的学者对社会法曾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阶段,整个法学研究依附于政治而逐渐丧失了学科的独立性。直到改革开放后,有关研究和学科建设才陆续恢复。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取得了伟大成功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为应对新的形势、新的问题,我国社会立法逐步探索,深入实践,一系列关于民生、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陆续颁布。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社会法有关理论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
社会法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性维护方式贯穿于整个人类文明史。渔猎和农耕文明阶段,社会生产力缓慢发展,人类生存和社会性维护方式主要体现为氏族、部落、家庭、宗族乃至宗教。囿于生产方式的单纯,社会性的普遍联系无论是广度和深度都不发达。工业革命给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劳动分工、专业化、市场化、工业化以及资本化,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新的社会性问题凸现,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导致传统的公私法的调整方式不能缓和资本逐利的本性所造成的社会分裂,人类文明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于是,在社会连带思想的引导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社会改良,试图以新的社会性维护方式来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体现在立法上就是社会立法的出现。通说认为,现代意义的社会立法典型事件就是德国俾斯麦时代的一系列社会保险法的颁布。白小平[2]认为社会法的出现是一种客观存在,而非一种理性的可以设计。马金芳[3]从社会法的“逆向”生成机制的视角论证了社会法之生成是“合规律性的产物”,符合伦理维度上人性中“恶”向“善”转化的规律;哲学维度上辩证法的规律;社会维度上社会发展的规律;规范维度上法律自身发展的规律。曹燕[4]从社会学法哲学代表人罗斯科·庞德的“社会控制工程”理论理解法律的发展过程及其功能,认为社会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它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体现为基于社会结构多元化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文化精神变迁的社会利益之形成和法制化。郑尚元[5]也认为,“出现公法与私法之外其他性质的法律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社会法是以实在法先于理论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无论学者们从何种角度研究社会法,对社会法的内涵与外延有何种分歧,但作为一种法律现象和立法实践,对社会法的起源或者产生的时代、原因等问题,学者们普遍取得了共识。正如哈耶克所说,社会法作为一系列有明确目的的制度的生成,“既不是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并未明确意识到其所作所为会有如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简而言之,制度的生成“是人之行动的非意图的后果,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转引自哈耶克 《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 1997年版 第17页
二、实然性研究——不同语境的争论
(一)“社会法”的词源
学术概念必须表现为一定的“语言形式”。语言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表达者与接受者的信息传递不可能绝对精确。因此,消除一个给定术语的模糊性是不切实际的,至多能够做到“渐渐地接近消除模糊性”。法的世界也肇始于语言,法律的制定和运行也涉及语言的公开表达和辩论。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学研究其实不过是法律(学)语言的研究。法学最具特色的基本方法也是语义分析方法,正如威斯特根斯坦所说,“不弄清语言的意义,就没有资格讨论哲学”。*转引自张俊娜 “社会法”词语使用之探析 现代语文 2006年第3期纵观社会法学研究者们对“社会法”这一术语的使用,其含义极为模糊、不确定,造成了“社会法”一词的多义性,给学术交流和研究带来了一定的麻烦和困难,形成了“自说自话”的尴尬局面。
寻找一个学术概念的词源,无疑是接近消除概念模糊性的一条捷径。学者们为探求“社会法”的本质,自觉不自觉地走向这条道路。郑尚元认为汉语 “社会法”一词的使用,最早出于日本[6]。因为日本文字源于汉文,字形字义与汉文渊源颇深,日本学术界翻译西文著作所用的术语,很容易被中国人使用。赵红梅认为,第三法域之社会法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起源于德国[7],中国法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从德国和日本引进了 “社会法”概念。这也符合学术传播的规律。西学东渐,特别是制度文明的移植必须适应东方社会的土壤,大陆法系成文法的传统更易于被东方社会所接受,而英美的判例法传统至少在当时显然不适合西化之初的日本。追根溯源,作为学术概念的“社会法”源自于德国,德国也是较早制定了《社会法典》的国家。现代社会的发展的基本前提是劳动带来收入,收入满足需求的法则。这一法则在现代社会中可能会受到限制或阻碍,造成社会危机或者社会缺陷,而传统的公私法框架的法律系统往往无力面对新的社会危机和有效地矫正社会缺陷。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法律形态应运而生。19世纪最后十年,奥托.冯.基尔克和海尔曼.罗斯勒不约而同地称这种新的法律现象为“社会法”。可以看出,社会法这一术语的最初使用,“并非是用于概括和表述调整某一特定社会关系的法典”,而是“学者们在研究当时社会中新出现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立法现象进而构想出来的一个法学意义上的概念”。*参见 邱小平译《联邦德国社会法与社会立法》,出自马普学会论文集 1986年第一册
最初的社会立法主要是解决“劳工问题”,立法核心是劳动法和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法。在魏玛时代,不同于劳工的弱势群体摆在社会政策的面前,比如战争受害者、青少年、残疾人、房客、佃户等,原来主要针对劳工的社会法概念显然要扩大其含义。二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建立,国家即是社会,国家法包罗万象,大多体现了强烈的社会性。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对社会领域的调整完全是行政性的,这个时代劳动法的实质就是劳动行政管理法,社会保险的实质是国家保障,或者说是国家行政分配制度的一部分。这类社会主义法与本文所研究的“社会法”本质上是不同的,前者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而后者以市场经济为经济基础。虽然有本质的不同,但社会主义实践或多或少对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带来了借鉴,社会政策的改良无疑为“社会法”的正名起到了推动作用。
我国学者竺效[8]系统地考证了德、法、美、英、日等五国在立法实践和学术研究使用“社会法”词语的情况,分析了德、法、日、英、美五国在这一概念上存在的差异,指出日本社会法的学理概念与我国当前法学研究中所使用的社会法概念具有最大的相似性。而英、美两国几乎没有可以与国内目前所讨论的“社会法”严格对应的概念。
(二)社会法的不同语境
长期以来,定义“社会法”成为学者们孜孜以求的理论研讨目标,社会法内涵与外延的界定成为学术争鸣的热点。虽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理论界也形成了基本的共识,要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社会法”。吴学谦、王为农[9]综合分析了国外特别是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指出对社会法应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把握——广义社会法是指不同于公私法的“第三法域”;狭义社会法是指以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为核心的独立的法律部门。可以看出,社会法一词在本文中有两种语境:广义的理解是理论讨论的语境;而狭义的理解是立法实践的语境。竺效[10]将“社会法”语词归类为狭义、中义、广义和泛义四种,建议将相关语词统一为“社会保障法”、“社会法”、“社会法域”和“社会中的法”,试图把学术讨论中的法学术语与立法实践中的法律术语的语境统一起来,以求学术讨论和立法实践中有所针对。董保华[11]也认为社会法是以狭义的法典和广义的法群(法律门类)这样的结构存在,区别在于将前者或后者哪一个命名为“社会法”。两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补充。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的社会法理论研究存在“相当泛化的现象”。笔者认为,这是理论研究繁荣的表现,但需要在学术讨论和争鸣时限定“社会法”的语境。
可以看出,学者们的理论争鸣往往是由社会法的不同语境所导致的。不同视角、不同层次的理论探讨并没有带来社会法学术共同体的分裂,而是推动了社会法理论研究的繁荣发展。 也许我们不能在“社会法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形成统一一致的答案,这也是很正常的。正如“人是什么”这个命题,一直是人类的哲学追问。“所有的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的一切方面的联系”[14]。所以,试图对社会法作出一劳永逸的定义,显然是不客观的。如果不能回答“是什么”,从“不是什么”这个角度来认识社会法,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与社会法一词比较接近的词语有“社会(学)法学”(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和“法学(律)社会学”(sociology of law ;jurisprudential sociology)。社会学法学是法理学研究的一个学派,法学家研究法律规定和法的社会功用,侧重于规定性的研究,倾向于理论研究;法律社会学是社会学中的一门学科,是社会学家研究法(律)这种社会现象的社会学,侧重于描述性研究,倾向于应用研究。由于翻译的原因,“社会法”(Social Law,Droit social,Sozialrecht)一词与社会(学)法学(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的中文表达比较相似,但两者差别很大。从两个词语的英文表达可以看出,社会法是关于“社会”的“法”,意味着与关于“国家”的法(公法)和关于“市民”的法(私法)相对应;而社会学法学是“社会学”的“法学”,强调法对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或效果以及各种社会因素对法的影响,与分析法学、新自然法学、新康德主义法学或新黑格尔主义法学等学派并列。从法学(律)社会学(sociology of law ;jurisprudential sociology)的英文表达可以看出,该词语的意思是“法律中的社会学”或“法学的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术语。当然,如果抛开学科的壁垒,三个词的含义有错综复杂的联系。
三、应然性研究——渐趋一致的方向
作为应然性研究的社会法价值亦或功用的研究,学界也探讨颇多。如果把社会法的功用价值表述为“解决社会问题,维护人的社会权,保障社会安全,促进社会利益”,这种“大词”的表述应该是不错的,但又是非常笼统的。从应然的角度,学界主要围绕着“社会问题”“社会权”“社会安全”“社会利益”这些“大词”来展开对社会法价值的讨论。
(一)社会法应对的“社会问题”
法学界的社会法理论探讨中,无不涉及“社会问题”。有学者认为,解决社会问题是社会法的阶段价值取向,构建和谐社会是社会法的目标价值取向。*参见 汤黎虹 论社会法的价值及其取向 行政与法 2008.10这种表述同样也很笼统,“社会问题”“和谐社会”都是内蕴丰富的大词,到底什么是“社会问题”,应该是学者探讨的问题。社会问题是社会实际与社会期望的差距,社会中许多人遇到的共同问题,是公众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麻烦。社会问题极其宽泛,人类社会一直存在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工业革命带来了技术飞跃,生产以雇佣为主,人附庸于资本,贫富分化严重,社会冲突加剧,“劳工问题”成为工业社会的主要社会问题。国家立法对雇佣关系的干预,一方面保护劳工权益,另一方面也保证市场的平等竞争,这个阶段的社会立法主要是解决“劳工问题”。随着社会共济和连带思想的发展,保险理论被运用到社会立法的实践,应对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风险社会”。德国俾斯麦新政制定了一系列的劳工保险法,其他国家纷纷效仿。随着社会的发展,除“劳工问题”外,“环境问题”“教育问题”“住宅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小股东权益保护问题”以及老年人、儿童、妇女等特殊群体的权益保护等社会问题不断涌现,有些是新问题,有些是老问题新变化。这些问题为社会法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和机遇。正如余少祥所说,“社会法解决社会问题,并非解决社会问题的全部”,“并非所有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法都是社会法。”社会法解决的是“民众的生活问题”,以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为目标,以保护“公民生存权”为价值追求[12]。
(二)“社会权”的本土讨论
我国学者试图构造以“社会权”为核心概念的社会法理论体系,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李炳安认为,社会权的基本属性有三:社会权是继自由权之后的第二代人权,俗称“吃饭权”;社会权体现的是国家与公民之间最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社会权是以社会保障权为核心内容,不断丰富发展的权利群[13]。多数学者主张社会权是社会法的核心概念,应该用这个“核心范畴”来整合社会法体系的构建,这也体现了“权利本位”的理念。也有学者指出,社会法与社会权不是一一对应关系,社会法对应的只是一部分社会权利[14]。认识不一的主要原因是“社会权”的界定仍然很模糊,社会权是一系列的权利,而这一系列权利的共性特征,学界的认识还不统一。
对社会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学和社会学界。法学界主要从理论层面研究社会法的本质、属性、历史演变、内容、性质、效力以及规范研究;社会学界更多的关注社会现实,描述社会权利的实际运行情况。两者相得益彰,互相补充。当然,社会权的相关概念界定不统一,像“社会法”一样存在多种语境。语境的不同并不意味着没有理论共识。比如,多数学者认为社会权是一种基本人权,是自由权之后的第二代人权;社会权是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丰富的权利群。在社会权的研究中,有学者敏锐地觉察到中国社会权研究的国情特色。不同于西方社会权是对自由权反思,强调国家对自由权的“干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制度的管控型传统,似乎在明确社会权的同时,更应该防范国家对自由权的干扰[15]。
(三)社会保障与社会安全之分
英文Social security law,往往被直译成“社会安全法”,也有的意译为“社会保障法”。有学者根据德国社会法典的规范分析,认为实质意义上的社会法主要是指以社会公平与社会安全为目的的法律,其作用在于通过建立与实施社会给付制度,消除现代工业社会所产生的各种不公平现象[16]。可见,社会安全是社会法的目的之一。也有学者从国外的成文法名称分析,认为国外的社会安全法等同于我国的社会保障法,把社会法理解为“社会安全法”是不适当的[17]。笔者认为,西方世界之所以用social security,其立法的最终目的就是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保障资产阶级的统治安全,只不过手段不是强硬的,而是怀柔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充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发展到现在,资本的逐利本性仍然没有改变,只是笼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我国的“社会保障”一词强调的是“社会成员”的保障,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安全”的价值取向有本质的不同,尽管在内容形式上,我们需要借鉴西方国家的制度设计。诚然,西方福利国家所奉行的安全目标,要求将社会成员普遍的生活安全的期待作为社会法制度的考量,但其立法的资产阶级本质属性不容忽视,否则,就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的路径。
(四)社会利益的争论
社会法学者一般会承认“社会利益”的存在。社会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它“强调社会利益、社会本位、社会团体的重要性和优先性”,社会利益“不是指那种仅包括市民社会中的个体利益,也不是指政治国家表达和体现的国家利益,更不是个体利益简单相加或综合的社会利益,而是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对所有社会成员都有普遍意义的利益”。社会利益是“以文明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名义提出的使每个人的自由都能获得保障的主张和要求”。*转引自 余少祥 社会法“法域”定位的偏失与理性回归,政法论坛 2015.6,。参见董保华 社会法原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朱晓喆 社会法中的人 载《法学》 2002第8期;薛克鹏 经济法的定义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页;梁彗星 民商法论丛 第八卷 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页。虽然学者们的表述不同,所指各异,但一般都会以“社会利益”作为社会法的法意本位。也有学者对社会法的社会利益本位理论进行了批判。*余少祥认为,由于社会利益具有整体性、普遍性、可转化性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在实践中常常被滥用,成为政府部门和特殊利益集团侵犯个人权利的借口,因此,应警惕社会利益被干预者当做实现个人特殊利益和集团利益的“敲门砖”。引文见上注。笔者认为,社会利益的主体边界认识不一,造成了社会利益、公共利益、集体利益、团体利益、群体利益、国家利益几个概念混淆,难以辨识,其原因也是在于讨论的语境不同。辨析上述词语,需要在统一语境下,按照同一标准进行类别划分,找出他们的对应关系。比如,公共利益对应于私有利益;集体(团体、群体)*集体、团体、群体三个词都和个体相对应,但三者也有区别,管理心理学认为,集体是群体发展的最高层次,团体是群体发展的较高层次,笔者认为,三个词的主要区别在于组织性的强弱程度不同。利益对应于个体利益;社会利益对应于个人利益。而国家利益这个概念值得注意。国家不同于社会,“国家”一词对外带有主权,对内蕴含统治之意,有三层含义:地域的(country)、民族的(nation)、行政的(state);而社会是由某种共同特征组成的不特定的人群。国家利益只存在于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民法上的国家财产利益这三种情况,除此以外,国家不应当有自己的独立利益,否则就可能是非法利益[18]。
四、社会法研究的中国方向
总体而言,我国社会法理论研究百花齐放,异彩纷呈,虽然理论体系的构建尚待进一步探讨,但这也与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探索道路是一致的。之所以强调社会法研究的中国方向,是因为社会法的本位价值最接近社会主义的性质,社会法的机制更符合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社会法的调整内容也是解决发展中“不平衡”问题的迫切需要。
(一)社会法的本位价值最接近社会主义的性质
社会主义就其起源来讲,是作为工业化的结果于18世纪末在欧洲发展起来的[19]。在阐述社会主义的各种观点上,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可能一致认为,在描述人类活动时,首先必须按照社会关系而不是个人活动来进行。就分配生产报酬而言,应该从整个社会出发,从平等的社会成员出发,而非从特定的个人出发。社会主义的性质从本源上来讲是强调“社会利益”的。正如前文所言,社会法理论研究和现代社会立法实践源于德国,具有浓厚的欧洲大陆法系传统,也是对当时垄断资本主义面临的社会问题的反思与应对。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思潮与社会法的理论研究具有同源性,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分析和解剖;而在解决问题的价值追求上也具有同向性,即强调“社会利益”,通过公权力的干预(分配)来实现社会成员的利益。当然,可以说一切法的终极目标均指向社会公共利益[20],但是社会整体利益是社会法的直接本位,而传统的私法和公法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间接关注。于此相较,社会法是最接近社会主义性质的法。
(二)社会法的机制更符合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是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吸取发展中的教训,立足中国本土实际,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一方面,市场经济和工业化、信息化社会的发展道路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存在相似之处,面临类似的社会问题,需要借鉴域外经验。国外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我国社会法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另一方面,基于中国的现实与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仍然是社会法研究的根基和土壤。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体现在积极国家义务;体现在社会主义制度。私法的传统理念认为,个人是国家的本原,国家只是外在的保障;国家的目的不是追求“至善”,而是惩戒和避免“恶行”;国家只是承担“守夜人”的角色,保护的是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正是这种自由主义的传统,造成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种种罪恶和垄断资本主义面临的社会问题。社会法的出现是对私法机制调整社会关系的反思,强调国家干预以帮助穷人摆脱困境的必要性,要求政府代表国家进入原本不干预的私人领域,履行对特定对象的给付和其他义务[21]。可以说,社会法上的国家是“积极的国家”,不仅要惩戒“恶行”,而且要追求“至善”。这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相一致的,也符合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积极给付的传统。与传统的私法机制和以私法为基础的公法机制不同,社会法机制既有强制性,又有任意性,更符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三)社会法的调整内容是解决发展中“不平衡”问题的迫切需要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九大明确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参见十九大报告“不平衡”较之“不充分”的问题更加突出。*这种“不平衡”,本文主要是指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等发展中的不平衡。社会法关注弱势群体,构建社会保障,强调社会利益,尊重社会权利,应对社会问题。可以说,社会法就是通过法治手段,坚持“协调”、“共享”的发展理念,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会法是最接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的法。
[1]李蕊,丛晓峰.历史视角下的社会法范畴[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7(06).
[2]白小平.社会法起源新论——生存的社会维护和社会立法进程视角[J].时代法学,2013(04).
[3]马金芳.西方社会法的“逆向”生成机理——对“恶之花”结出“善之果”的评析[J].法学论坛 ,2013(11).
[4]曹燕.庞德法哲学视角下社会法之本原研究[J].法学论坛,2010(06).
[5]郑尚元.社会法语境与法律社会化[J].清华法学,2008(03).
[6]郑尚元.社会法的特有属性与范畴[J].法学,2004(05).
[7]赵红梅.第三法域社会法理论之再勃兴[J].中外法学,2009(03).
[8]竺效.社会法概念辨析——兼议我国学术界对社会法词语之使用[J].法律适用,2004(03).
[9]王为农,吴谦.社会法的基本问题:概念与特征 [J].财经问题研究,2002(11).
[10]竺效.法学体系中存在中义的“社会法”吗?[J].法律科学,2005(02).
[11]董保华.“广义的社会法”与“中义的社会法”——兼与郑尚元、谢增毅先生商榷[J].东方法学,2013(03).
[12]余少祥.社会法“法域”定位的偏失与理性回归[J].政法论坛,2015(06).
[13]李炳安.社会权—社会法的基石范畴[J].温州大学学报,2013(04).
[14]余少祥.社会法“法域”定位的偏失与理性回归[J].政法论坛,2015(06).
[15]邓海娟.近十年国内公民社会权问题研究述评[J].湖北社会科学,2010(11).
[16]杨士林.论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社会法的基本范畴[J].温州大学学报,2013(07).
[17]余少祥.社会法“法域”定位的偏失与理性回归[J].政法论坛,2015(06).
[18]吕忠梅、廖华.论社会利益及其法律调拉——对经济法基础的再认识[J].郑州大学学报,2003(01).
[19]戴维.弥勒主编,邓正来译.布莱克维尔政治思想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547.
[20]钱叶芳.“社会法法域说”证成[J].法学,2017(04).
[21]余少祥.社会法上积极国家及其法理分析[J].江淮论坛,2017(03).
ReflectionandprospectoftheoreticalresearchonSocialLaw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
HuangTao,CongXiaofeng
(JinanUniversity,JinanShandong250022,China)
The paper sorts the contents of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Social Law in China and classifies it according to the study of the necessity,the study of the factuality and the study of the probability. In the study of the necessity,the appearance of Social Law is an inevitable historical issue,on which scholars have obtained basic consensus;in the study of the factuality,the different contexts discussed by scholars lead to the difficulty of defining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Social Law,on which the theoretical consensus is difficult to be obtained,but this theoretical debate also reflects the prosperity of academic research;in the study of the probability,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Social Law is becoming clearer,with different emphasis on expressions. Social Law is the law closest to the goal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 study of Social Law should be based on the soil of China and adhere to the direction of Marxist jurisprudence.
Social Law;theoretical research;commentary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社会法的范畴与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3BFX143)”和济南大学科研基金重大基金项目“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野下我国地方立法本土资源研究(项目编号16ZD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黄涛(1975—),男(族),山东成武人,济南大学政法学院讲师,法学硕士,主要从事劳动法、社会法和经济法研究;从晓峰(1964—),男(蒙古族),济南大学法政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研究。
2017-10-13
D902
A
1009-1416(2017)06-059-07
【责任编辑:张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