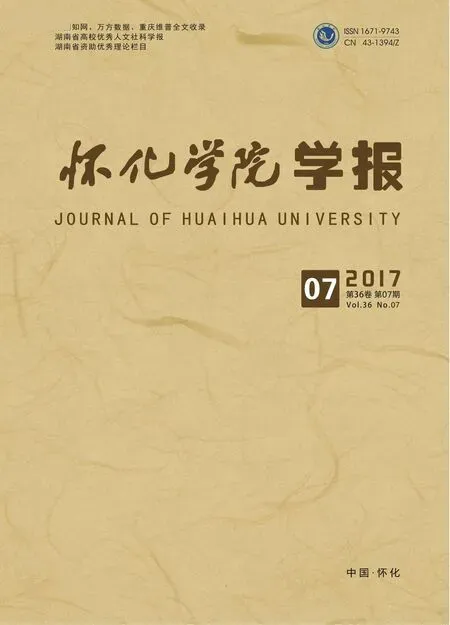破坏生产经营罪应否包括妨害业务的行为
——以淘宝恶意刷信誉行为为例
2017-03-10王筱
王筱
(中央财经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081)
破坏生产经营罪应否包括妨害业务的行为
——以淘宝恶意刷信誉行为为例
王筱
(中央财经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081)
关于破坏生产经营罪,理论上存在很多疑难问题。1997年刑法将破坏集体生产罪改为破坏生产经营罪,并将其从破坏经济秩序犯罪一章移植到财产犯罪的一章,其保护的法益已经发生变化,该罪不包含妨害业务的行为,应该将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与损害商誉的行为进行区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为了适应新型妨害业务行为的出现,应对破坏生产经营罪的行为方式进行进一步的扩张,将一些新型的妨害业务的行为通过司法解释进行具体规定。
破坏生产经营罪;毁坏型财产罪;恶意刷信誉
一、问题的提出
互联网时代下,破坏生产经营罪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同时也导致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着适用上的新挑战。2016年12月19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的淘宝恶意刷信誉案就是这一新型犯罪形式的典型代表,该罪最终被认定为破坏生产经营罪是专家多次探讨后的结果,但是该判决是否科学尚存在疑问。
基本案情如下:淘宝店的经营者大都知道,信誉对于淘宝店的经营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淘宝店的信誉高,那么其网店就会更容易被顾客搜索到。因此很多人会因为这一规则对自己淘宝进行刷信誉。为了防止有人利用这一规则作假,淘宝网监管机制一旦发现有网店采用虚假手段提升网店信誉,就会给予30日的单个商品搜索降权。2014年网店店主董某为了谋取市场竞争优势,雇用谢某在六天内多次以同一个账号大量购买A淘宝店的商品,并给予好评后退单。4月23日,浙江淘宝公司发现这一异常,并认定A店铺存在虚假交易刷销量的行为,决定对其进行降权处罚。4月28日,经A线下申诉后,淘宝公司才恢复了A的店铺搜索排名,据审计,这一降权行为给A造成的损失多达15.98万余元。关于此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董某、谢某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董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谢某免于刑事处罚。至此,全国首例因恶意刷信誉而获刑的案件尘埃落定。
要知道早在2012年11月,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就审理过一起“恶意差评师”案件,与前一案件不同的是,这一案件被认定为敲诈勒索罪。其原因主要是这一案件中存在敲诈勒索的主观目的,但是从客观上来讲,这一行为也妨害了生产经营行为,将其定罪为敲诈勒索罪而非破坏生产经营罪主要原因难道仅仅是因为二者的主观目的不同吗?由此可见,关于恶意刷信誉这一行为,司法实践的认定是十分混乱的。
二、存在的疑问
从上文的介绍中,我们不难发现关于这类危害社会的行为是否应当认定为犯罪,应当认定为何种犯罪,尚且存在需要探讨之处。从法理上分析,恶意刷信誉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则,但就目前的立法状况来说,不应当认定为破坏生产经营罪。理由如下。
(一)从客观方面来看,恶意刷信誉的行为与破坏生产经营罪的实行行为不具有相当性
有人认为,应当对破坏生产经营罪中的“其他方法”进行扩张解释,只要行为在客观上阻碍了他人的生产经营活动的进行,就属于破坏生产经营罪的实行行为,就应当以该罪名定罪处罚。采用恶意刷信用而导致竞争对手被降权的这一行为是一种对淘宝平台的欺骗行为,“这种欺骗手段,属于破坏生产经营罪的‘其他方法’。把‘其他方法’解释为包括欺骗手段,符合同类解释规则。”[1]笔者并不赞同此观点。根据同类解释规则,首先,当刑法分则条文在列举具体要素之后使用“等”、“其他”用语时,只有案件事实与列举的要素相当,才能适用分则条文中“等”或“其他”的规定,否则便破坏了构成要件的定型性,违背罪刑法定原则[2]。其次,刑法同类解释追求的是目的相同,即对法益造成的损害相同。再来看破坏生产经营罪中规定的实行行为——“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这些行为方式都存在着对物的暴力,是对现实存在的对象的物理损害,也就是说所谓的“其他方法”也必然是符合这一特征的一系列行为,而不应当包括没有对具体对象产生客观物理损害的恶意刷信誉的行为。另外,从法益保护的角度来看,破坏生产经营罪位列《刑法》财产型犯罪一章中,其所保护的法益是财产权益,其保护的对象是用来进行生产经营的机器设备、牲畜耕具等生产资料,通过保护这些生产工具、生产资料免受损毁而间接保护生产者的生产经营活动。只有通过破坏生产工具、生产资料进而对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了破坏,才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虽然恶意刷信誉的行为属于妨害业务的行为,也具有破坏生产经营的性质,但是其并未对生产工具、生产资料进行毁坏,因此不具备破坏生产经营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为了论证“欺诈手段”和对物的暴力行为属于同类行为,有学者还引用了外国刑法的相关规定作为论据,即意大利刑法第513条规定:“采用对物的暴力或者欺诈手段妨碍或者干扰工业或者贸易活动的……。”但是这一规定是有关妨害业务罪的规定,与我国的破坏生产经营罪并非同一罪名,二者具有不同的犯罪构成。关于破坏生产经营罪所侵害的法益,不能仅仅以“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的规定没有把破坏生产经营罪视为财产罪的先例”[3]为由就草率地将其侵害的法益归结与破坏生产经营秩序。因此将其作为论证破坏生产经营罪包含妨害业务的行为的论证未免太过牵强。在确定具体罪名的法益时,应以刑法规定为依据,以具体罪名所属的类罪名为指导。同类罪名具有同类性质的法益。在确定具体罪名的法益时,不应超出同类法益的范围[4]。
在当下互联网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确实出现了很多形形色色的妨害业务的行为,例如在互联网上进行恶意注册或者提供虚假信息等。这类问题确实严重妨碍了企业的经营活动,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但是由于我国并不存在妨害业务罪,导致司法机关难以对类似行为进行处罚。因此有学者提出应当对妨害业务的行为进行客观解释,将此类行为认定为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但是却忽略了破坏生产经营罪所具有的毁坏财产的性质,这种解释显然是不合理的。
(二)从犯罪对象上看,恶意刷信誉所指向的犯罪对象不符合破坏生产经营罪所指向的犯罪对象
我国《刑法》第五章乃侵害财产犯罪,其中包含十五个侵犯财产权益的罪名,通常可以将它们分类为占有型财产犯罪和毁坏型财产犯罪。其中占有型财产犯罪侵害的是所有人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财产本身往往并未被毁损;而毁坏型财产犯罪往往是作为犯罪对象的财产本身受到毁坏而使得财产所有人或者占有人失去某些财产权益。
从破坏生产经营罪在刑法体系中的位置上讲,破坏生产经营罪属于财产型犯罪,因此其侵犯的客体是财产权益,其所指向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有体物,而恶意刷信誉的行为虽然具有破坏生产经营的现实危害性,但是其侵害的客体并不是现实的财产权益,并且其犯罪对象也是不同于有体物的财产性权益,这种财产性权益所能带来的实际经济利益往往是难以估量的,与传统理论和实践中的破坏生产经营罪是有明显区别的。因此恶意刷信誉的行为并不能按照破坏生产经营罪进行定罪处罚。
(三)从立法目的上看,破坏生产经营罪的设定意图保护私有生产资料[5]
1979年刑法曾将破坏集体生产罪归属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罪”当中,在此种归类的之下,关于破坏集体生产罪所保护的法益,学界均认为是集体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并对此基本没有争议。但是1997年刑法将此罪名进行了修订,并将此罪的归属做了重大的调整,将其列入侵犯财产犯罪一章中,因而关于目前的破坏生产经营罪所保护的法益究竟是什么,学者们产生了较大的分歧,这也直接影响了司法实践中对一些行为性质的定性。某些学者认为,既然罪名的体系位置已经发生变动,对该罪名的保护法益也应当重新审视。当罪名的体系位置发生变化时,不应该忽视该罪名的保护法益的变动情况。毕竟,法益具有重要的解释论机能[6]。1997年刑法将这一罪名移位到财产犯罪的一章,其立法目的很明显是为了加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其作为故意毁坏财产罪的特别条款,是法律对私对财产尤其是对作为生产经营不可缺少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的保护。应该说破坏生产经营罪如同故意毁坏财物罪一样,都是对财产的保护,故意毁坏财物罪保护的是一般的财产权益,而破坏生产经营罪保护的是重要的生产工具、生产资料。这种立法模式并非我国刑法所独有,如德国刑法第27章规定的是物品损害方面的犯罪,其中第303条规定的是物品损坏罪,第305条规定的是重要生产工具的毁坏罪[7]。从社会背景、立法目的和整个法律体系上来看,破坏生产经营罪是毁坏财产型的犯罪,与妨害业务的行为不可混为一谈。
三、方案的选择
恶意刷信誉的行为确实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则,但是就目前的立法规定来看,显然已经超出了法律的前瞻性。破坏生产经营罪属于财产犯罪的范畴,而妨害业务属于扰乱秩序的犯罪,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犯罪混为一谈显然是不科学的。但是问题总是要解决的,无合理的方案不足以打消社会民众的疑虑和彰显立法的可预期性。下文是两种具体方案,以期待为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第一种方案是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破坏生产经营罪所保护的法益是生产经营秩序。这种情况在日本立法中也有存在,曾经在日本立法中就出现过罪名“站错队”的情形,在法律明确表明的情况下,将破坏生产经营罪所保护的法益明确为生产经营秩序并无不可。在此基础上,应当对“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中的“其他方法”进行列举式解释,将恶意刷信誉、恶意批量注册等新型的妨害业务的行为认定为破坏生产经营罪的实行行为。
第二种方案便是在我国今后的刑法中设立妨害业务罪,并将其列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这一章节中。在这种立法模式下,应该认为在某些犯罪行为上,妨害业务罪将与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构成法条竞合的关系,根据行为的具体犯罪构成来认定其触犯的罪名。以上述淘宝恶意刷信誉案为例,此行为可以认定为同时满足妨害业务罪和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的犯罪构成,根据法条竞合的原则,适用特别法的规定,以后者定罪处罚。由于我国《刑法修正案(九)》刚刚颁布不久,法律不可能朝令夕改,为了保证刑法的稳定性,目前比较可行的方法是通过司法解释,对破坏生产经营罪的行为方式进行进一步的扩张,将一些新型的妨害业务的行为解释到其中,以更好地规制司法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新型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1]高艳东.合理解释破坏生产经营罪以惩治批量恶意注册[N].人民法院报,2015-11-18(006).
[2]徐贤飞.该阻止施工行为不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N].人民法院报,2015-03-26(006).
[3]高铭暄,马克昌.中国刑法解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949.
[4]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89.
[5]王筱.破坏生产经营罪应否包括妨害业务的行为——以首例判刑的淘宝恶意刷信誉为例.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NTUy MDA0Mg==&mid=2651938157&idx=1&sn=0e45a3ba7164a77ca6b47 68ce2e68598&chksm=80672528b710ac3ee071cf1800222d1661ee513e a70a9cb704b65561be5aacb91ff18d1291c2&scene=0#rd.
[6]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16.
[7]德国刑法典[Z].冯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1.
A Breach of the Production and Business Operation Should Include Breach of the Behavior of the Business:a Case Study of Taobao Malicious Brush Credit Behavior
WANG Xiao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81)
As for the breach of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ory.In 1997,for example,the criminal law changed the damage collective production to the breach of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and transplanted it from destroy the economic order crime chapter to property crime in the chapter.The protection of legal interest has changed.It does not contain the detriment of the business behavior.The destruction of the production and business operation should be differentiated from the behavior of damage the goodwill.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we should enlarge the range of behavioral pattern of the crime and stipulate the new behavior of breach of the business through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a breach of the production and business operation;the damage type of property;malicious brush credibility
D924
A
1671-9743(2017)07-0094-03
2017-04-30
王 筱,1992年生,女,山东烟台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