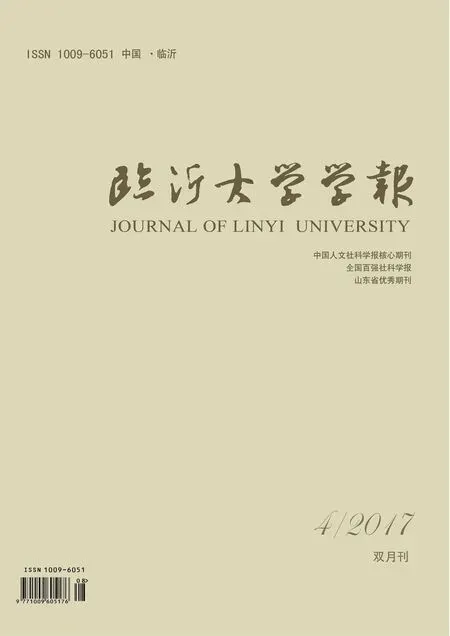读懂与说出:现代汉语诗歌黑暗书写的心理疗救机制
2017-03-10周俊锋
周俊锋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读懂与说出:现代汉语诗歌黑暗书写的心理疗救机制
周俊锋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文学治疗在现当代诗歌领域有着切实的研究意义,特别是面对当代混沌的现代性与社会人文的缺失,心理焦虑与精神压力成为一种社会病,诗歌创作与传播致力于个体心理疏导与社会心理疗救而进行积极探索。诗歌的疏导作用和心理干预,前提在于使读者读懂和产生共鸣。读懂即说出;说出即治疗。诗歌的文本阅读和有效阐释有其自身的界限与难度,在诗歌文本与心理疗救之间,读者读懂并产生共鸣,即帮助诗歌文本说出。文章从现代汉语诗歌中黑暗书写的表象分析出发,揭示黑暗书写的精神实质以及读懂与说出二者间的辩证关系,结合读者的阅读反应与接受心理来进一步阐释诗歌黑暗书写的净化疏导作用与心理疗救机制。
现代汉诗;读懂;说出;黑暗书写;心理疗救
现代汉语诗歌中的黑暗书写,特指现当代诗歌中对黑暗心理、黑暗意象进行刻画或描绘的书写表达,最终指向个体和社会精神文化危机的思考。对诗歌的黑暗书写进行定义,是复杂而又动态的过程。当下诗歌批评研究对于阴暗分裂性格、黑暗恐惧心理、黑暗意象母题的关注,形成“黑暗诗学”的研究传统,但本文所要着力探讨的“黑暗书写”在于书写表达的方式方法,笼统地将恐惧、悲观、绝望等情感内容划归至“黑暗书写”则略嫌驳杂。现代汉语诗歌的智性写作与隐性表达,在“政治”与“文化”语境下将诗歌的精神资源拓展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我们需要注意:诗歌的黑暗书写是一种“过程诗学”,即需要渗入文本来考察汉语诗歌如何通过诗歌技艺性表达凸显对社会文化进行理性反思的过程。而且,当黑暗书写的诗性表达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被“读懂”,文化和精神的反思才能够作为一种知识和方法,参与到日常社会生活的心理疏导与疗救工作中去,形成良性的心理抚慰机制,文学治疗才成为可能。因此,诗歌的读懂与说出,是汉语诗歌中黑暗书写进行心理疗救的必要前提;心理疗救在某种程度上的实现,首先需要厘清诗歌逻辑与日常逻辑之间的差异,理解诗歌艺术自身特有的言说和表达方式。
一、现代汉语诗歌中黑暗书写的表象与实质
考察诗歌文本,现代汉语诗歌中的黑暗书写在艺术表达方式上,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层面,包括黑暗氛围环境的直截描摹、幽暗心理的正面刻画,以及精神危机的理性反思。简而言之,现代汉语诗歌的黑暗书写从背景层面、个体心理层面、文化精神层面等维度,试验探索出一类相对稳定成熟的范式,围绕“黑暗书写”则有三类典型性的诗歌表达方式,即:明暗对比、主客二分、文化反思,在不同诗人的诗歌作品中有着内在的反映。
明暗对比,表面上看似是颜色、光线、景深的环境再现,直截描摹黑暗的氛围与环境,但却不等同于简单的背景复制。围绕灯光、黄昏以及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场景,诗人们着重抒写的黑暗、晦暝、昏灰、混沌、模糊等,在描摹社会环境的同时传达出一种内在的经验,即黑暗、晦暝、昏灰、混沌、模糊等本身作为矛盾体,一方面适应了特殊时代境遇下诗歌抒情主人公的复杂心理,同时也孕育着思想裂变的可能。通过明暗对比,最能够凸显人物性格与环境的异质性冲突,明暗冲突愈是不能调和,诗歌黑暗书写的张力则放大到极致,形成如“创伤体验”[1]27或“疾病书写”[2]95等。虽然明暗对比在不同诗歌中的体现程度有着差异,但却传达出一个共同的信号:黑暗书写不仅仅是背景环境的再现,在朦胧的表象背后还潜藏着隐秘讯息,这部分内容可能是一首诗歌内部真正想要“说出”和“表达”出来的深刻涵义。在诗人穆旦、卞之琳、海子、顾城、昌耀、张枣等不同诗歌中的明暗对比,往往是理解和读懂诗歌的关键点,研究者运用不同的批评视野和鉴赏方法常读常新,明暗冲突构成诗歌张力的同时,成为打开敏感、紧张、焦灼心理体验的一个豁口。明暗对比所呈现的对立和冲突,契合社会现实经验中诸种不可能的境遇下人们的真实感受。
主客二分,是现代汉语诗歌黑暗书写较为重视的表达方式,实际也是明暗对比的延伸。主客二分的冲突在具体表现过程中一类侧重自我和外部世界的冲突境遇,另一类倾向于展现自我与内部世界的心灵冲突,往往后者在现代汉语诗歌的黑暗书写实践中更加具有代表性。诗歌中的黑暗书写着力凸显自我的分裂与双重否定,心理自剖成为黑暗书写的典型书写范式。“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仿佛看到了另一种人类的昨天/三个相互残杀的事物被怼到了一起/黄昏,是天空中唯一的发光体/星,是黑夜的女儿苦闷的床单/我,是我一生中无边的黑暗。”[3]173“黑暗”在戈麦诗歌里被抽象成为一种特殊的境遇,苦闷、怨怼、混乱成为无法挣脱的精神束缚,因此“分裂”乃至“毁灭”成为戈麦这一类抒情诗人抵达事物内核的最佳方式。整体性、完整性的事物被重新割裂开来,在“三个相互残杀的事物”中呈现的首先是逻辑的混乱,在逻辑混乱中指涉“星星”“黄昏”“我”三类象征物之间的互文性。“星星”本来指向的是发光体,“黄昏”则应该指向的是黑暗,而“我”始终不能挣脱自身的灰暗面,成为分裂、矛盾的混合体。以北岛、食指、戈麦、昌耀等诗人为代表,主客二分的“分裂”成为重塑自我观念和个体价值的独特抒情范式,即在精神思想的否定与分裂中重新建构一个完整的、崭新的自我。因此,现代汉语诗歌的黑暗书写以“执拗”“拒斥”“破败”“倔强”“宣告”的精神姿态,传达着对生存、价值、希望的质疑和否定,戈麦诗歌中“深渊”“末日”“尸谷”“鬼影”“腐烂”“万劫不复”,以及“冷绿的太阳”“风干的火腿”“吹破的灯笼”等典型性诗歌表达,通过主客二分的“分裂”来探询常态性的价值和意义断裂后的精神出路。因此,黑暗书写中对“分裂”的聚焦抒写成为一种常态式的结构。主客二分带来的分裂,凸显诗歌黑暗书写的精神导向,以不可毁灭的精神力量“照亮人的生存”[3]426,能够“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3]424。
文化和精神的反思,在现代汉语诗歌黑暗书写的文本实践过程中有着根本性的地位。诗歌由于其特殊的精神指向和抒写方式,诗歌文本对“黑暗”的关注与青睐不是表面意义上的病态审美或消极扩散,而是追求经验的超拔,“常怀痛苦的,痛苦终将不再”。文化反思的力量,使得主体自觉与独立思考成为一种潜在意识和思维习惯,“黑暗书写”所面向的精神资源,源自于时代和当下社会思想生活的多个层面,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来反思文化、反思价值、反思时代,使诗歌具有与现实对话的能力。文化反思所携带的是一种省视自身的思想武器,而这为诗歌黑暗书写进行心理疗救提供可能的认识路径,诗歌以其敏感、深邃、超前的意识洞悉社会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病变”。昌耀《罹忧的日子》慨叹着“一个人这样走向成熟,却不足以反证人们怎样边做市侩俗子”[4]275,多多《哪里下着雨》写道“把烟灰和叹息抖到被允许的地方/一个无法忍受他人的人可以忍受自己了”[5]85,顾城则在《我是黄昏的儿子》中说“我是黄昏的儿子/爱上了东方黎明的女儿/但只有凝望,不能倾诉/中间是黑夜巨大的尸床”[6]90。这类型诗歌的沉重、抑郁、冷峻,很大程度上源于其“黑暗”母题的选择和强化,诗歌表面抒发的虽然是个体与小我,实则是更普遍意义上的价值探询,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对社会规训的警惕,对精神孤寂的沉思,从而整体上构成文化反思的重要内容。诗歌中的黑暗书写,以悖谬的书写姿态最终指向的是光明、理性的价值追求层面。
二、读懂与说出:诗歌黑暗书写与心理疗救的契合点
诗歌的思想内涵既包含浅层的字面意义,还包含深层次的隐喻意义。一首诗歌真正“说出”,意味着诗歌意义的最大限度释放,而诗歌读解的不彻底恰恰说明诗歌本身还未完全“说出”。诗歌只有完全“说出”,接受者才能够将一首诗歌较为隐蔽的思想内涵进行阐释与揭露,从这个意义上讲,读懂即说出。但诗歌的读懂,首先应当成为一个技术考量的问题,其次才是价值层面的评判。诗歌的难于读懂,往往是“懂”与“不懂”在某个层面的调和结果,从周伦佑提倡语言破坏,韩东认为“诗到语言为止”,于坚提出“拒绝隐喻”,再到耿占春所说“失去象征”,以及颜炼军谈论“象征的游移”等,不少诗论家之所以强调隐喻和象征对事物现象的遮蔽,而实际上又以另外一种方式参与、促成新的隐喻和象征。现代汉语诗歌的写作技艺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朦胧诗以来诗歌象征与隐喻的积极参与,因此复义、反讽、悖谬、戏剧化、陌生化的语言试验,均成为诗歌技艺的重要内容。“拒绝隐喻”排斥的不是隐喻作为修辞手法的诗歌表达方式,而是力图将隐喻修辞朝前推进一步,在“读懂”与“说出”的冲突关系中释放诗歌自身思想内容的丰富性。正因为隐喻和象征的参与,诗歌文体不断深化和形成其自身所特有的诗性逻辑,了解这一点是探究诗歌心理疗救的必要前提。
谈及现代性话语中的文学治疗主题,宗教、哲学所担负的诊断和治疗文化痼疾与个体心理障碍的重担开始逐渐向文学转移,需要注意的是“心理疗救”应当成为一种文学治疗的可能,而不是以自然科学的量化标准来简单强调社会效用。因此,我们在探究诗歌黑暗书写与心理疗救的契合点以前,并不急于将作者与读者、医生与疾病的复杂关系介入进来,而是为更好地切入现代汉语诗歌“黑暗书写”的文本细读过程,使一首诗歌的“说出”更加顺畅,同时更易于“读懂”。
文学治疗,在西方理论资源中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净化说、柏拉图的精神迷狂说、克尔郭凯尔关注主观精神的疾患、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弗洛伊德的艺术白日梦、拉康的自我镜像说等,以及弗莱《文学与治疗》、阿恩海默《作为治疗手段的艺术》[7]、卡伦·霍尼《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8]等均有着经典阐释。回顾文学治疗的相关研究,应当引起注意的是,诗歌黑暗书写与心理疗救的契合点,首先应当是社会主体与诗歌对社会文化与精神危机的共同关注,“寻觅介入现实和传统语境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在日常生活中挖掘诗意,写生存的境遇和感受”[9]234。社会公共空间下,诗人、读者对于社会文化问题与精神心理疾患的共同关注,使得“黑暗书写”的诗歌文本能够打开对话与交流的渠道,才有可能形成思想上的触动和共鸣。诗歌的心理疗救,只有建立在心理触动和思想共鸣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展开,因此“读懂”与“说出”的关系阐述更有利于形成诗歌接受过程中的心理触动和思想共鸣。
国内学者中,文学治疗的社会应用研究和案例分析已有较多研究进展,理论建构以叶舒宪《文学治疗的原理及实践》和《文学与治疗—关于文学功能的人类学研究》为先导[10]78,以及曾宏伟《文学治疗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11]95、武淑莲《文学治疗作用的理论探讨》[12]148等研究文章,在强调学科理论与研究支撑的大背景下,研究者相对忽略文学文本与心理疗救二者的契合点。同时,现代汉语诗歌的黑暗书具有智性写作与隐性写作的特点,在强调诗歌技艺的探索试验和个性创作的过程中,容易与读者以及社会知识结构形成隔膜。诗歌中的“黑暗书写”读不懂,成为文学治疗和心理疗救的巨大尴尬。有观点认为,“读不懂的诗就是不好的诗,没有商量的余地。因为它丧失了诗歌的基本要素,丧失了作为语言艺术之所以存在的根本理由,那就是它丧失了沟通与交流的基本作用”[13]82,用懂或不懂作为诗歌价值评判的唯一标准,略嫌武断。“读懂”与“说出”作为诗歌黑暗书写与心理疗救的契合点,如何更有效地读懂诗歌,恰恰是文学治疗与心理疗救开始的第一步骤。因此,读懂即说出,说出即治疗,在尝试读懂诗歌的经验传达过程中,需要了解并学习积累特殊的诗歌读解方法,以勘破诗歌隐喻和象征的隐秘内涵,使一首诗歌真正“说出”。
三、净化与疏导:黑暗书写的读解方式与疗救机制
对一首现代汉语诗歌的黑暗书写进行充分读解,抛开价值层面的评判搁置不说,暂且需要接受者从技艺层面来深入诗歌的内部肌理。象征和隐喻,赋予诗歌复杂而多变的想象空间,但任何一首诗歌放置眼前,必然具备合乎诗歌逻辑的线索。诗歌线索的梳理,对于现代汉语诗歌的读解异常重要,一方面是被称为“明线”的表层线索,另一方面则是隐喻和象征所赋予的“暗线”。现代汉语诗歌的黑暗书写,在浅层线索中多集中为环境背景的摹写作为感情基调的渲染,并以此映射叙事或抒情主体的复杂心理。但是,在深层线索的梳理中,黑暗书写的潜藏涵义则不被重视,诗歌的思想内涵并不能够完全“说出”。这样一种有隔膜的诗歌读解,客观上因为其文本分析的难度,而使得一部分接受者选择停留于浅层线索上的诗歌阅读。诗歌的黑暗书写不能完全“说出”,则诗歌的表达不尽彻底,因此文学治疗和心理疗救的开展时,心理净化与疏导的功能必定有所延滞。
以三种黑暗书写的具体形式来看,明暗对比、主客二分、文化反思凸显的是逆向式与否定性思维,即从痛苦、阴郁、冷峻、沉抑的“负面”书写中获得经验的超拔,探询生存价值与人生意义的内核。现代诗歌由于革命话语和历史存亡的考验,诗歌的黑暗书写大多采用明喻的方式写作,凸显明暗对比,表达国土危亡的忧思,臧克家、艾青、穆旦、冯至、辛笛等诗人多以小见大,对于旧中国的苦难书写则作为“明线”贯穿始终,主题宏大、庄重严肃,个人遭际与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传达启蒙、革命、抗战、爱国等历史经验与民族话语,“诗歌的主题精神及其文化价值观念为它置身的文化境遇所规范而具有的特征”[14]8。但与之不同的是,思想活跃的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黑暗书写风貌为之一振,朦胧诗歌、先锋诗潮成为八十年代的代言词,北岛、食指、海子、骆一禾、顾城、芒克等一大批诗人的横空出世,将诗歌黑暗书写的精神强度得到最大化呈现,“黄昏”“黑夜”以及伴随而来的自我分裂、价值重构成为八十年代诗歌所特有的精神指向。同时,八十年代诗潮在主客二分的趋势上愈演愈烈,甚至有着激进盲目的风险,这与特定的历史时代背景相关联。对八十年代末期的诗歌进行解读的过程中,需要注意暗喻或借喻方式的抒情表达方式,探究诗歌黑暗书写中自我分裂意识的起源与变化,抓住“暗线”。而90年代以后的当代诗歌创作,则将“暗线”继续进行弱化和消解,文化反思的力量与精神强度虽然不及前一时期明显,但却使诗歌表现社会、关注生活的能力大大增强,多元化、碎片化的现代生活百态悉数进入诗歌成为鲜活的素材。
比较而言,进入当代以来的汉语诗歌在黑暗书写的技艺表达上,更显复杂性。八十年代末期,海子、骆一禾、芒克、江河、杨炼等人诗歌在主客二分、文化反思的切入方式较为直截,更加青睐历史性与时间性的宏大主题,诗歌黑暗书写多呈现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精神勃发姿态。而过渡至90年代,继续创作的诗人多多、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以及口语诗歌韩东、伊沙、于坚等人,在创作风貌上更显杂芜与内敛,智性化与隐性化的诗歌写作成为“约定俗成”的局面,学院写作和民间诗人大多采撷片段、碎屑化的生活经验而切入现实,任意性较强,读解难度更大,当代诗歌“面对的是一个新历史的时间,它的内容与表现必须面向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时代”[15]121,诗歌的黑暗书写更多表达出现代人的紧张焦虑和精神压力。
以雷平阳的《荒城》为例,诗歌在破折号以前铺陈“知府”“县令”“保长”作为荒城的权力机构,但耐人寻味的是,构成荒城主要权力的人员则是雪山的雄鹰、还乡的老马、满身根须的榕树,崇高、威权、资历、精力在视野转换的过程中被废弃成为荒城,构成冲突与悖谬。而在权力的底层,“野草的人民,在废弃的街上和府衙/自由地生长,像一群还俗的和尚”[16]117,“自由”“还俗”等字眼恰在另一层面揭示出完美的生活理想,而且笃信:完美的生活理想与崇高、威权、资历、精力无关。有理由相信,诗人以文字寄托生活的理想,将现实世界隐喻为“荒城”,内心的焦灼孤寂感则溢于言表。而这所代表的黑暗书写,恰恰构成诗歌批判现实、直面生活的深层线索。臧棣《豆腐已用深渊煮过协会》一诗,“带毛的皮剥落后,深渊的深/确实有点惊人,但还是没有深过/用深渊煮过的豆腐”[17]270,“深渊”作为暗喻,在这里成为一种现实生活的映射。被深渊煮过的豆腐,以及豆腐被品尝,“我消失在我的身体里”,“多年前,你也曾消失在我的身体里”,主客二分的使用在臧棣的诗歌里由于“丛书”“协会”等诗体试验的加入而更具迷惑性。面对“深渊”,抒情主体并不忌惮于自我的分裂,被深渊煮过成为命定的遭际,“好像这是追寻你的一种方式”,诗歌愈是采用轻松、谐趣的笔墨描摹用深渊煮过的豆腐,则愈能够凸显抗拒和排斥的强力。臧棣诗歌中的这种“强力”被有意克制,采取戏谑的方式表达诗人对现实的态度和警惕,诗歌的黑暗书写愈加隐晦而智性化。
归究来看,现代汉语诗歌黑暗书写的心理疗救机制通过明暗对比、主客二分、文化反思等技艺性表达,“读懂”与“说出”良性互动并形成“文学与治疗”[18]二者相辅相成的有效机制。在诗歌读解的过程中,我们容易被固有的知识和经验所误导而形成诗歌解读的“意图谬误”,但学习和了解一定的诗歌解读技巧,从现代汉语诗歌的黑暗书写中真正领略诗歌还未完全“说出”的思想内涵,使得“读懂”成为可能,文学治疗和心理疗救则有继续进展的开阔空间。“黑暗书写”不是教人以沉重和冷峻的抑郁,而是勇敢直面黑暗本身,探索追求生命意义的价值内核,获得经验的超拔。现代汉语诗歌的“黑暗书写”直面现实,最终指向的是一种弘扬理性、文化反思的精神诉求,而不仅仅停留于“黑暗”本身的文学表达。读懂即说出,说出即治疗,文学和诗歌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身和当前的时代,现代汉语诗歌黑暗书写的心理疗救机制有着丰富的可能性和发展潜力。
[1]吕周聚.民族创伤体验与祛蛮写作[J].文学评论,2012,(3).
[2]黄晓华.医学与政治的双重变奏——论解放区文学的疾病书写[M].中国文学研究,2008.
[3]戈麦.戈麦诗全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4]昌耀.昌耀的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5]多多.多多的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6]顾城.顾城的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7](美)阿恩海姆.艺术心理学新论[M].郭小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8](美)卡伦·霍尼.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M].冯川,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9]罗振亚.20世纪中国先锋诗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0]叶舒宪.文学治疗的原理及实践[J].文艺研究,1998,(6).
[11]曾宏伟.文学治疗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J].学术界月刊,2009,(1).
[12]武淑莲.文学治疗作用的理论探讨[J].宁夏社会科学,2007,(1).
[13]邓程.新诗的“懂”与“不懂”:新时期以来新诗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14]王泽龙.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15]王光明.现代汉诗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6]雷平阳.山水课:雷平阳集1996—2014[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
[17]臧棣.骑手和豆浆:臧棣集1991-2014[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3).
[18]叶舒宪.文学与治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Adequate Reading and Pleasing Expression: the Darkness Writing and Psychological Therap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ZHOU Jun-feng
(College of Humanities,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ubei Wuhan 430074,China)
There is a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literature therapy in the field of modern poetry.With the disorder of modernity and absence of social culture,psychological anxiety and mental stress become a social disease,and poetry creation and communication have committed to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assistance.The premise for poetry’s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s to make readers understand and resonate.Adequate Reading means pleasing expression,and pleasing expression means effective treatment.Between the text of the poem and psychological therapy, the text reading and effective interpretation of poetry has its own boundaries and difficulty,the readers understand and resonate, that is,to help the poetry text express fully.The article begins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darkness writing in modern Chinese poetry and reveals the spiritual essence of darkness writing and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dequate reading and pleasing expression.The article also further explains the role of purification and the mechanism of psychological therapy in the darkness writing of poetry,combined with the reader’s reading response and acceptance of psychological.
Modern Chinese poetry;adequate reading;pleasing expression;darkness writing;psychological therapy
I207.25
A
1009-6051(2017)04-0050-07
10.13950/j.cnki.jlu.2017.04.006
责任编辑:徐元绍
2017-06-30
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创新创业基地项目“现代汉语诗歌的黑暗书写与心理疗救”(NO2015650011)阶段性成果
周俊锋(1990—),男,湖北丹江口人,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