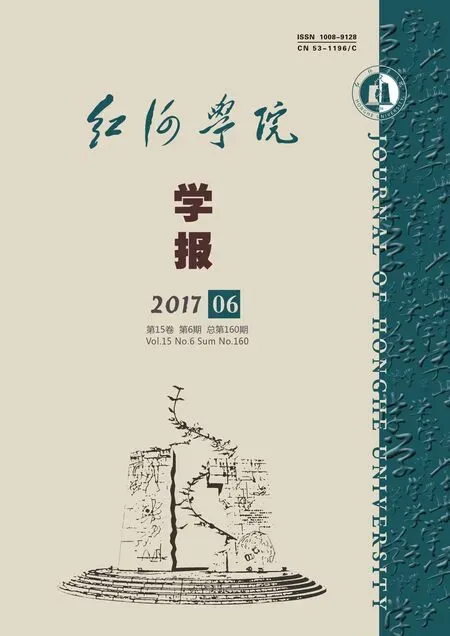中越彝族边民互市中的族群互动与国家认同研究
2017-03-10杨宗霖
高 文,杨宗霖
(1.红河学院国际彝学研究中心,云南蒙自 661199;2.蒙自经济技术开发区,云南蒙自 661199)
中越彝族边民互市中的族群互动与国家认同研究
高 文1,杨宗霖2
(1.红河学院国际彝学研究中心,云南蒙自 661199;2.蒙自经济技术开发区,云南蒙自 661199)
中越边民互市,带动边境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依托边境市场缓解越南北部山区的贫困,提高了边民生活水平。中越边境地区的彝族边民参与到边民互市的场域,通过互市彝族边民搭建了更为稳定交易网络,双方彝族边民的接触,促进边界彝族文化交流和碰撞,促进彝族边民的文化及民族身份的认同,也增强了彝族边民的国家归属意识,有利于两国彝族边民的国家认同构建。
中越边境;彝族边民;族群互动;认同研究
一 引言
边民互市是指居住在边界线20千米附近的边民,在政府指定的开放点和集市上,按照规定额度进行商贸和交易行为的活动。参加边民互市的两国边民,持与自己身份相符的证件,而参与小额贸易的企业需要依法向省级部门批准,并报国务院备案。边民每人每日购买物品在8000元之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税,而参与贸易的企业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此外,还享受一般贸易出口退税政策。边民互市减少商品流通环节,降低生活成本,提高边民生活水平。既促进了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加速了边境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增进中越边民的友谊和互信,营造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1]148-149自1991年中越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边贸得到迅猛发展。中越边民互市经历了自由发展期、迅速提高期、规范发展期。自由发展期主要从上世纪90年初期到1996年前后,这一时期互市发展较为粗放,交易产品也主要集中在生活用品上,交易规模也不大。1996-2000年前后是迅速发展期,特别1998年两国政府签订《边贸协定》,双方政府出台了边贸管理的具体文件,对边贸的形式、商品种类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规定,逐渐形成了边境小额与互市贸易相结合、生产资料与生活用品相结合的综合性边境贸易。2001年以来进入规范发展期,中越双方加大边贸的整顿,有关职能部门加强了沟通和配合,逐渐形成了规范管理、严格操作的边贸管理体制。[2]12-15
二 中越彝族边民互市点概述
中越彝族边民互市点主要分布在广西那坡、云南富宁、麻栗坡、马关,河口、金平六县及越南莱州、老街、河江、高平等省与中国毗邻的地区。边民互市点既是边民交往的空间,也是边民来往的通道。中越彝族边民互市点共有55个,其中广西7个,文山有31个,红河有17个。那坡县与越南高平省的河广、通农、保乐、保林及河江省的苗旺等5个县接壤,有平孟国家级口岸,平孟、百南、那布等3个边民互市点,还有念井、岭隘、弄平、弄合等4个边境集市贸易点。富宁县田蓬镇和木央镇7个村委会、142个村寨与越南的苗旺、同文两县的山尾、新街、同文、蔑菜、弄姑等6个社 127 个寨子相接,有木央、木杠、郎恒、龙包、田蓬等5个边民贸易互市点。麻栗坡与越南河江省的同文、安明、官坝、渭川、黄树皮等5县接界,有天保国家级口岸,14个边民互市点,分别是天保、猛铜、茨竹坝、新城、下金厂、八布、杨万、长田、董渡、董干、马崩、马林、普弄、者挖等。马关县有12个边民互市点,分别是都龙、保良街、东瓜林、茅坪、金厂、水头、小白河、小坝子、拉气、田湾、夹寒箐、牛马榔等。在越南渭川、官坝、坝哈、新马街、猛康、箐门、黄树皮、同文、苗旺等县有清水河、普棒、百德、南汀、岩脚街、新街、龙兰等与中方相应的边民互市点。[3]43-45河口与越南老街、孟康、坝洒相接,有国家级河口口岸,坝洒、新店、老卡、山腰、坝吉等5个边民互市点。金平与越南坝洒县、莱州省封土县、孟德县相连,有金水河国家级口岸,此外还有龙脖河、马鞍底地西北、热水塘、隔界、草果山、南科、老白寨、中梁、田房上寨、蚂蝗塘等10个边民互市点,与越南冬瓜寨、迤底岩头、王麻寨、会笼、十二楼、南温、裸马、八围寨、南丹、仆沙等互市点相互对应。中越边民互市周期一般是6天,如富宁县田蓬街,越南边境集市周期也是6天,一般为中国集市的次日。中国马关、河口、金平的互市点基本遵守这个共识的约定。互市遵循以农历为安排的边民生活习俗,以十二生肖为互市的时间,如麻栗坡县猛铜街以农历属猪、蛇日作为交易日,杨万街以农历属牛、羊日作为交易日,八布街以农历属鸡、兔日作为交易日,十里村逢周六,马鞍底以农历属虎日、猴日,勐拉乡以农历属猴日、虎日,者米乡以农历属龙、属狗日。交易语言多为跨境民族使用的语言,汉语主要是西南官话文山及红河等地方方言。
三 彝族边民的分布
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古老民族,在春秋战国时期彝族的人文共祖阿普笃慕在昭通地区进行著名的六祖分支,武祖向西进入楚雄、大理地区成了今天滇西彝族的祖先;乍祖进入红河流域地区成为滇南彝族的祖先;糯祖与恒祖进入凉山地区成了今天北部方言的彝族;布祖和默祖进入了贵州成为今天的贵州彝族的主体。随即繁衍而形成了今天彝语六大方言区,构成彝族滇川黔桂四省区分布主要格局。[4]61-64两汉时期中央王朝积极经营西南彝族地区,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郭昌出兵西南,先后灭劳浸、靡莫,然后到了滇国,滇王主动投降,西汉设益州郡,东汉哀牢王内附在今保山设永昌郡,亦属益州部,对云南的统治进一步深入。三国时期蜀汉积极经营南中地区,进入魏晋南北朝全国大分裂,唐朝时期彝族建立南诏国,有效地对西南地区进行经营和管理,随后的大理国以彝族为主进行统治,加速了西南彝区的发展。元朝实行土司制度,明清在彝族聚居的滇东北地区进行改土归流,加速了滇东北、滇东南彝族传统社会的瓦解,引起大量人口的迁徙。昭通一带的彝族在改土归流中的军事剿灭下进入凉山地区,而宣威、罗平、泸西、开远、马关一带的改土归流中使得彝族向滇越边境进行迁徙。[5]98-100
中越边境地区彝族主要集中在那坡县、富宁县、麻栗坡、马关、河口、金平等6县境内。越南的彝族被越南官方识别为倮倮族和濮拉族,在中国他们均属于彝族,越南彝族还包括少量的自称“尼苏颇”的彝族。越南倮倮族,主要居住在河江省同文和苗旺两县及高平省保乐县,16世纪后从中国云南迁入,与中国彝族有亲缘关系,从事山地农业,有聚族而居的自己独立的村落,其语言和文化习俗与中国彝族大同小异,分布于越南莱州、老街、河江、高平省接壤的部分县,其中广西那坡县彝族与越南高平省保乐县彝族有渊源关系,云南富宁县木央一带彝族与越南河江省同文县彝族相互往来,云南麻栗坡县彝族与越南河江市彝族往来密切。中国自称“濮拉颇”的彝族,越南称为夫拉族或普刺族,主要居住在老街和河江两省,莱州、北件、安沛等省也有少量的分布,与苗族、瑶族和少量汉族杂居在一起。广西马关县金竹棚一带彝族与越南老街省彝族有姻亲关系,云南河口县桥头乡老卡牛场、新店、下大塘、大打拉、岩头、新发寨、龙洞及莲花滩、老范寨等一带的彝族与越南老街沙巴县濮拉族保持往来。云南金平县自称“阿普颇”的彝族,据考,他们从文山一带迁来,进入金平县阿得博、地西北、越南南掌蔓地村,最后又迁回金平县马鞍底地西北村定居,如今与越南还保持着密切联系。金平县保山寨彝族,从昆明迁徙到建水、个旧,从个旧蛮耗渡红河,定居于保山寨,后部分从保山寨迁往越南莱州省封土县居住。云南马关县、河口县一带的傣族和苗族也认为自称“濮拉颇”的彝族是最早开发这片土地的人。自称“濮拉颇”的彝族从事简单的山地农业和牧业,因此需要大面积的游耕,且居住相对分散。据越南1999年的人口普查统计,越南濮拉族(彝族)人口为9046人。[6]4
四 彝族边民互市与交往中的互动
中越边境是中国与越南两国的边界,历史上这个区域随两国力量的博弈,使两国边境模糊不清,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边民过着相对自由的生活,国家权力并没有太多干预边民的社会生活。边境冲突前两国边民是同志加兄弟关系,边境管理相对宽松,而冲突之后两国边境被严格管控。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边民来往频繁。越南高平省保乐一带的倮倮族也常到广西那坡县平孟、百南、那布等一带毗邻的边民互市点进行互市,由于越南倮倮族在云南富宁县与越南苗旺与同文相对较为集中,而且他们之间的距离也相对较近,因此越南苗旺格挡、同文县龙骨、上坝等倮倮族与云南富宁县田蓬、木央等地彝族保持密切,并互动交往,越南倮倮族也就常常出现在云南富宁县木央、木杠、郎恒、龙包、田蓬等一带边民互市点。云南麻栗坡县边民互市点也时常看到越南彝族的身影。居住在越南河江省和老街省的濮拉族也常到云南马关县境内边民互市点交易,在云南马关县与越南接壤的边民互市点如都龙、保良街、东瓜林、茅坪、金厂、水头、小白河、小坝子、拉气、田湾、夹寒臀、牛马榔,都能看到越南濮拉族互市交易的身影。小坝子自称“濮拉颇”的彝族认为,他们祖先是从马关县八寨一带迁徙而来,虽不知具体迁徙年代,马关县小坝子、金竹棚一带自称“濮拉颇”的彝族,也就成为彝族进入越南的重要途径。[7]89-92云南河口县桥头乡一带自称“濮拉颇”的彝族村寨与越南猛康县接连,并该地老卡场、新店与越南孟康的互市点,通过老卡场有通向越南花龙——李堂——孟康的公路,花龙到爱头的公路又与云南马关县拉气乡连接。金平县勐桥乡卡房村则成为龙脖河一带最重要的互市点,与中国接壤的主要是越南老街省坝洒县阿姆冲乡濮拉族也前来互市。金平县马鞍底乡地西北村委会,辖地西北、八底寨、三家寨、鸡窝寨、石头寨等彝族村寨,与越南老街省迤底一带彝族进行互市往来。[8]71-77
(一)互市前的族内互动
越南彝族边民通过边境互市,从互市点上获得了所需要的生产及其生活物资,越南彝族边民把自己种植的如包谷、谷物、蔬菜、瓜果、饲养的牲畜及采集来的野生菌子、蜂蜜、药材运到边民互市点进行交易。由于越南倮倮族与濮拉族(彝族)间存在人文地理空间及其生计模式上的差异,因此在边民互市中交易的产品各有特点。越南濮拉族生活在红河两岸的深山密林里,他们与自然关系密切,因此他们狩猎技术和药物知识相对较为发达,在边民互市点能看到他们采集药材和野菜,能买到他们捕捞的野味。而越南倮倮族种植业水平相对高,边民互市中多以包谷用牲畜驮来进行交易,也有牛羊猪鸡交易。交易完毕,从边民互市上买回自己所需的物品,比如食用油、洗涤剂、洗衣粉、五金、饮料、药品、家电、灯具、手机等生活必需品。此外,还有种子、农药、肥料、机械、发电机、塑料、水管、农具等各种。中越边民互市点,一般离口岸相对较远,与从事大宗交易的口岸相比,因而较之中越边境口岸具有灵活和方便特点。通过边民互市,仅凭中方市场和农科技术,越北边民物资短缺和贫困面貌有所改变。越南不少内地商人也参与到边民互市中,他们销售咖啡、拖鞋、饮料等物品,但越南彝族很少有全职的商人。越南倮倮族居住集中,并婚姻关系盛行族内婚,传统文化制度保存相对较好,内部之间联系较为紧密,他们结伴而行坐车或者骑摩托车积极参与互市。与云南马关县毗邻的越南濮拉族,居住区域多受高山和深谷的纵横切割影响而交通滞后,没有直达互市点的班车,因而需多次辗转才能到互市点,这在云南马关县小坝子互市点上越南濮拉族来的最晚,却散的最早的现象,就可见一斑。
(二)互市中的跨族互动
中越边境冲突之前出生的越南倮倮族汉语水平相对高,用越语交流却不那么流利,可边境冲突后越南通过各种形式教育和边境管理强化国家认同,于是他们的越语水平逐渐提高,并且与侬族和苗族关系融合,随着边民互市的开展,越南倮倮族学习汉语的积极性也不断提升,在互市中越南倮倮族把带来的物资大多卖给中国彝族商人,或卖给中国其他民族如汉族、苗族、壮族商人。笔者在云南富宁县田蓬互市点上,采访来自越南同文县龙骨村倮倮族王某某,他告诉笔者龙骨一带的倮倮族大多都能会讲苗语和壮语。在购置家电用品和大宗货物时,他们常常会反复了解产品的性能,甚至找云南富宁县彝族亲戚帮忙询问。相比之下越南濮拉族互市交易技巧比倮倮族差得多,在云南马关县小坝子边民互相点上,越南濮拉族三三两两来赶互市点,但汉语操控水平不及倮倮族边民。老街省和河江省苗族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濮拉族杂居在苗瑶等民族中,听得懂苗语,但交往能力方面,越南濮拉族没有像倮倮族那么自信和大胆。濮拉族害怕欺骗,一般只会同熟悉商人交易。云南金平县地西北一带自称“濮拉颇”的彝族与越南老街省迤底的濮拉族,由于地西北边民市场建得早,显然越南濮拉族的互市经验也相对丰富,他们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苗语和哈尼语,而且会用汉语和中国商人进行交流,金平县马鞍底的草果经济在几年前就席卷了地西北边境两侧,赋予了中越边境彝族边民超强的商贸能力。
(三)互市后的文化回归
边民互市是一个多民族共生型、共和型的互动空间,越南彝族边民常常有组织有计划进行交易,及时分享产品的价格信息,相互帮助运输互市产品,并互市交易往往是在多民族中展开,巩固了多民族共生的的现实,强化了民族之间的互动和联系,促使边民走出族群和地域文化的边界,去大胆探索尝试民族之间交往的方法和路径及能力。即便是相对封闭的越南濮拉族边民,互市使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拥有更多的现代性,从而赋予他们更多的生存能力。云南马关县自称“濮拉颇”的彝族,已经有本民族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在地方性的社会活动有重要的影响,而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也使得他们更多地关心越南同胞。笔者曾经访谈过与越南濮拉族交易的云南马关县苗族陶姓老板,他认为当地彝族很团结,越南濮拉族诚实守信,他们药材从不掺假。中越两国彝族边民喜欢吃牛羊肉,经常出现在边民互市点的牛羊肉汤锅店。越南濮拉族认为,同中国彝族一起吃牛羊肉汤锅店,是一件很体面的事。吃饱喝足,中越两国彝族边民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谈家族起源、迁徙,或说跳公节和跳掌节的故事,或论族群历史记忆文化。一般情况下,边民通常忙于日常的农耕生计,交往局限于村落内部和民族内部,而边民互市赶集却反常态的跨民族交往,扩宽了彝族边民活动的场域,拓展了族民的社交空间,获取了物资,扩大了视野,结识了朋友,增长了见识。[9]47-49
五 族群互动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是民族成员对民族历史记忆的追溯,对共有文化因子的认定,是一个个体对群体的归类和认知的心理过程,主要体现在文化与心理层面。互市产生的共同交易空间使得境内外的彝族文化要素聚集。首先,彝族边民通过外显的服饰文化,形成了一个视角上的显现,认同也从感官层面开始构建。中越彝族边民基本穿传统服饰,而且相比较而言,越南彝族受到现代化冲击小,彝族传统服饰比境内更加复杂和完备,这样越南彝族也基本上分得清谁不是彝族,谁是中国彝族,谁是越南彝族。其次,用彝语交流,但越南倮倮族语受壮语的影响,有相当一部分有壮语借词;又越南濮拉族语显然也受到了苗瑶语的影响。尽管如此,本民族母语还是他们的日常用语,他们操着边境内外彝族共有和熟悉的语言,有效地缩短了与境内彝族同胞的心理距离,他们在一起聊天时,或讲述本民族远古历史,或探讨家族迁徙的故事,还会讨论民间仪俗、道德礼仪、风俗习惯。在回忆民族历史和分享共有文化传统时,双方的民族认同超越时空的限制。
在物品流动和情感认知流动的边界,逐渐出现边境两侧彝族的相互吸纳和接受,边民互市点上被中国商品吸引的越南女孩,而抱着娶妻生子愿望的中国彝族男孩,在可以接受的通婚半径之内达成认可,民族文化的认同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推动让他们喜结连理。与所有边境男人一样,跨境娶妻是无奈而有为的事,因为人口的繁衍,必须得延续,对于嫁入中国一方的越南籍女子来说,虽没有合法的手续,至少能过上相对安逸的生活。而越南的家庭由于子女的入境,至少也是中国的亲戚,这样更加方便以后在边境上的行走和互市。近年来,边民互市在规模层次上有所发展,参与中越边民互市的边境区域也在逐渐地扩大,跨境民族通婚也在不断地扩大之中,也反映了中越互市中边民和谐发展的一个真实侧面。当然随着互市的深入,中越边民的网络空间也在不断建构,那些通过小买卖积累在互市上站稳的越南彝族商人,逐渐扩展他们的生意,同时也扩大了与中方边民的交往,他们通过“打老根”“拜亲家”“结拜弟兄”构建熟悉社会和边民空间,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相互发展已成为中越两国边民的共识。
在互市中边民的民族认同得到强化,边民的民族认同是一个基于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要素属于内生性情感认知。而国家认同则是对一个公民对于归家归属的认知,是对于国家的领土、政权、文化及其族群等要素的评价和情感,是在公民参与由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逐渐获得归属情感,很多时候它与国家的国际地位和政府治理的成效密切相关。它是人们对国家政策的态度取向,是分析研究人们如何看待国家归属与人们生活秩序的关系,是人们对自己的国家成员身份的知悉和接受。国家认同与民族成员自身的归属并不矛盾,而且还是互为前提,相互补充的。中越边境划界大致延续了清末以来的边境格局,越南倮倮族生活在高平省保乐、河江省苗旺、同文一带,基本上属于三蓬以外的区域,越南政府在此经营多年,尤其是1979年以后越南加强了边境地区的文化与经济建设,越南倮倮族的国家认同得到牢固的建构,而越南濮拉族居住较为分散,族群内部的互动不强,他们与国家政治文化生活的互动较少,国家观念稍弱,但依靠国家的民族识别和社会管理,越南濮拉族的国家认同还是被逐渐建构起来。
中国彝族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都很强,云南文山州彝族人口近35万之多,仅次于自治主体民族壮族和苗族人口,因而在文山州成立了数十个彝族乡。云南红河州彝族有114万人,为自治主体民族。无论是红河州还是文山州,彝族全面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并成为本地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角色。而彝族传统祖灵观念,把彝族的历史和记忆明确地指向云南腹地,在文化归属和区域认同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有的祖先记忆和地域认同。云南富宁县一带的自称“倮倮颇”的彝族送祖灵仪式,按照演唱的铜鼓歌谣,指向文山→滇池→昆明地区;云南马关县小坝子、金竹棚一带自称“濮拉颇”的彝族,也要把祖灵送回马关→文山→开远→昆明等滇池腹地;云南金平县保山寨彝族祖灵也要送回昆明附近。文化传统促使着边境彝族向内地的聚拢和回归。在较之邻国好的国民优越感,由此形成强大的回归意识。[10]1-4
在中越边民互市前,两国均对彼此的边界进行严格的管控,形成边防哨所、村委会军民联合的防控体系。中越两国政府都制定了本国边民政策,越南虽财力有限,但在边境地区教育、医疗基本上是免费,政府制定实施了很多有利于边民的各项政策,构建了越南彝族边民的国家观念和情感。而中方先后出台实施了富民兴边、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合作医疗和义务教育的免费推行,把福利和福祉落到边民实处,因边民政策的调整和充实,也强化了边民的优越感和国家归属意识。中国彝族边民的国家认同既有历史记忆的延续,也有国家政策的强化和巩固。当下中越两国彝族边民都有清晰的国家边界,互市产生了文化互动和婚姻联通,搭建了中越边境地区更大的交易空间,而中越两国彝族边民在两国政府主导的互市中获得了经济收入,并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因此他们都清楚地认识到只有两国政府的通力合作和有效管制才能出现一个制度化、合法化、常态化的交易空间。双方边民均能按照互市管理的规则,按时互市,按时离市。
六 结论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而且与多国接壤,跨境民族是一个庞大的综合群体,跨境民族治理取决于民族国家综合实力、文化自信和跨境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要保持理性和冷静,在没有危及国家主权时,应采取“去政治化”处理;在没有引发民族冲突时,应去民族化处理。[11]50-52越南与我国有长达1400多千米的边境线,有数十个民族居住在国境线两侧,形成跨境民族。每个跨境民族均有跨境的历史、人口、文化等方面有所不同,又有着各自的跨境特征。当下“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跨境民族文化相同与社会发展相似,使它们成为互联互通的文化主体。彝族是中越跨境民族之一,边境两侧的彝族村寨相互接壤,鸡犬相闻,文化相同,语言相通。他们跨境互动和交往,有一定的历史传统,而边民互市不仅传承和巩固了这一传统,而且扩大了民族互动的规模。促进边境地区的稳定与和谐,强化中越两国彝族边民的国家归属意识,在这个过程也出现一些小问题,但是还是值得肯定。
[1]张燕青,冯馨瑶.昆明关区边民互市问题与对策[J].中国市场,2015(12).
[2]邓文云.浅论中越跨境民族关系[C]//“东南亚民族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2003.
[3]杨磊.从滇越东段边界走廊考察壮族与岱侬族的跨境关系[J].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03).
[4]罗希吾戈.彝族“六祖分支”雏议[J].思想战线,1983(03).
[5]梁玉珍.广西那坡彝族源流及民俗考察[J].广西民族研究,2002(02).
[6]范宏贵.婚礼上抹黑脸的越南普拉族[N].中国民族报,2004-04-30.
[7]王英武.云南彝族濮拉人宗教信仰调查报告:以马关县新堡寨为例[J].西昌学院学报,2008(03).
[8]普忠良.越南的彝族及其历史文化述略[J].世界民族,2003(02).
[9]李金发.中越边境边民互市中的族群互动与国家认同:以云南地西北边民互市点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11(12).
[10]龙倮贵.越南彝族传统丧葬仪式的文化象征意义和社会文化功能[J].红河学院学报,2014(05).
[11]吴兴帜.中越跨境民族交往与边民社会治理研究:以云南省河口、金平县为例[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5(02).
[责任编辑 自正发]
Research the Yi people's national identity based on the border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frontier trade
GAO Wen1,YANG Zong-lin2
(1.International center of Yi culture research of Honghe university,mengzi 661199,China;2.Mengzi Economic-Techonlogical Development Area,Mengzi 661199,China)
China and Vietnam border trade,it bring the border area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Relying on the border in the mountains of northern Vietnam market poor governance,and full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border areas.Yi people lived inborder region attend to the frontier trade,it help them to build more stable trading network. Yi people from two countris border areas meet together promote their culture communication,meanwhile it promote cultural and national identity.
China-vietnam border;Border yi peiole;Interactive groups;Identification research
C956
A
1008-9128(2017)06-0010-05
10.13963/j.cnki.hhuxb.2017.06.003
2017-04-18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资助项目:中国彝文古籍文献整理与保护及其数字化建设(13amp;ZD142)子课题:滇南、滇东、滇东南彝文古籍文献整理与保护;云南省省院省校教育合作资助项目:云南彝族重要古籍数字化保护与利用研究(SYSX201420);国家民委基地中国彝学研究中心项目:中越边境彝族边民族群互动与国家认同研究(YXJDY1502)
高文(1981-),男(彝族),云南宣威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民族学、人类学及彝族跨境问题教学及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