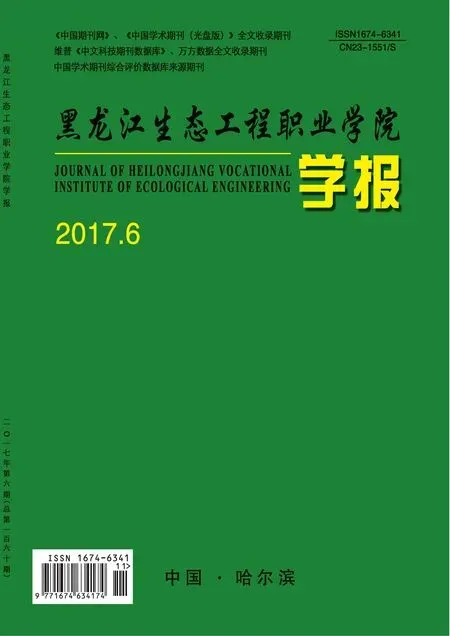国家功利之刑的法哲学批判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贪腐犯罪终身监禁的审视
2017-03-10王合永宋要武
王合永 宋要武
(1.哈尔滨工业大学 法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2.黑龙江科技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2)
国家功利之刑的法哲学批判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贪腐犯罪终身监禁的审视
王合永1宋要武2
(1.哈尔滨工业大学 法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2.黑龙江科技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2)
刑法哲学是人们研究刑法最为本质问题所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自然法作为一种通过人类理性而加以发现的不成文法,是接近人类本性的理想秩序,因此,任何实定法都必须遵循自然法的本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改案(九)》(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九》)中对待贪腐犯罪采取的“终身监禁”①制裁措施,虽然该条款的设定积极响应了刑事政策,有利于消除当下的社会矛盾,但是却有违“正义、自由、公平”等作为自然法价值原则的风险。国家功利主义之刑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渊源,并不是应急之作。从人类理性和自由的角度对贪腐犯罪终身监禁刑罚违反自然法的原因进行考量,并论证法治必须是在自然法语境中才能实现的法的统治。
法哲学;自然法;古典主义;实证主义;国家功利
1 自然法语境下的刑法哲学
法哲学是对法本源性、根基性的问题在价值层面所做的研究,而法是法哲学存在的前提,但什么是法?西方法哲学鼻祖海希奥德认为:“法律是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治安秩序,它强迫人们戒除暴力,把争议提交仲裁。”与此相类似的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法的界定:“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由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1]在实定法层面,这样的定义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过度的法律实证主义必然导致法律基本道德的丧失。例如,在纳粹德国,在形式上没有人认为国会通过的法律不是法律,然而因为其丧失了法律本身所固有的道德属性,在实质上已然不可称之为法律。刑法是法之利器,因此,刑法学在作为教义学面容呈现的同时,必须关注其作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属性,回答刑法如何体现国家政治结构与权力运转,以及国家对公民诉诸强制力的正当性问题。[2]那么,何种属性才是法应有的属性?对此我们不得不诉诸于理性。托马斯·阿奎在《The Summa Theologica》中指出:“永恒法是上帝思想中控制宇宙的永恒的律法,这是存在于现实世界的所有秩序的基础,存在于世界之中的这种意义上的秩序就是自然法。”[3]我们姑且在这里将“上帝”归结于人类所固有的理性,人类运用这种固有理性获得善,那么所遵循的这种行为模式就是自然法。自然法的存在不依赖于人的行为,“它是一种正当理性的命令,它指示任何合乎理性的本性相一致的行为就是道义上必要的行为。”[4]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法即为理性法。
在法律和道德属于不同层次的当今社会,自然法确实构成了法律和道德的共同因素。自然法是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理性,实定法必须遵从这种理性的导向,而这种理性的核心就是自由,同时包括道德、正义②、公平等价值。“人的意志之所以是自由的,就在于他的本质是理性的。”[5]我们通过分析可以得出,理性是自然法的内核,是孕育自然法的基本精神。法哲学研究法律的本源,笔者认为就是要在这种理性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因为要解读法的本质不遵照法律所固有的基本属性是无法展开的。从启蒙时代的法哲学,到思辨时代的法哲学,到如今转向实证主义的法哲学,无不是在理性或者人的本性的基础上对法学展开的讨论,而这与我们探讨自然法实质定位存在契合,所以笔者认为,对法哲学的研讨必须在自然法的语境中进行。
刑法哲学属于法哲学的一个部分,是针对刑法的本源问题进行哲学探讨,主要的领域集中在“自由意志、犯罪根源、刑事责任、刑罚本质、刑罚目的”之上。刑法哲学的研究也必然需要人类理性的参与,并且通过运用理性去发现和推导出人的行为的基本准则和程式。简而言之,这也就是刑法哲学在自然法意义上得以构建的基础。
2 报应之刑抑或功利之刑
《刑法修正案九》中针对贪腐犯罪适用“终身监禁”并且禁止减刑和假释。终身监禁作为死刑的一种替代措施其严重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对于贪腐犯罪适用“终身监禁”并禁止减刑与假释其创立和适用是否具有正义性却值得推敲。刑罚的根源在于刑事责任,刑事责任是由法律规定的。但是实定法必须在自然法的导向下制定,所以必须要赋予刑事责任以正义的形象。在古典主义学派看来,法律责任产生的根据就是犯罪人自身的犯罪行为违反了公众理性的道德或者法律,基于道义给予的惩罚。而道义在精神实质上同自然法相统一。康德认为人是理性的生物,人的意志之所以自由,就是在于人具有动物所没有的理性。具有普遍道德的东西既不是被无所不能的上帝所赐予的,也不是人生而所具有的,而是人类理性所自己创设的。所以,犯罪是一种违反道德“元规则”的行为(同时也是不理性的)。然而人的意志是无限自由的,自由的边界只存在于道德边缘,犯罪是对善良意志的违背,所以刑罚是对所造成危害行为的一种道义上的同等报复,并且这是刑罚唯一的目的,不存在其他。所以对犯罪行为处罚的唯一根据就在于其意志的自由性,犯罪人基于意志自由侵害了他人或者社会的利益,违反了公平正义的准则,那么就应该在道义上进行处罚,这便是道义责任。黑格尔认为惩罚是法律自身的强制回复,所以黑格尔将之称为“法律报应论”。然而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道义报应论”还是“法律报应论”都是建立在“意志自由”的基础之上的,因为“一个处在意志控制之下的心灵,一个拥有美德的心灵,不能够被同于它或优异于它的东西变成过度欲望的奴隶,因为同等于它或者优于它的东西会是正义的。也不能够被劣于它的东西变成奴隶,因为劣于它的东西会过分无力。这样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性了——唯有它自己的意志和自由选择才能够使心灵成为贪婪之伴侣”。[6]而这正与自然法的核心内涵——“自由”相呼应,所以它是符合自然法的。
《刑法修正案九》中贪腐犯罪如果情节严重,便适用“终身监禁”,并且还不准减刑或者假释。从《美国模范刑法典》中“A defendant found guilty of murder in the first degree may be sentenced to imprisonment for life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parole.”可以看出,只有一级谋杀才“可能”而不是“一定”会判处终身监禁并且不得减刑或者假释,因为“生命即使在宪法的价值秩序中也是一切价值的根源”[7],生命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所以适用这样残酷的刑罚。然而对比贪腐犯罪,贪腐犯罪侵害的主要是“职务的廉洁性”法益,其重要性完全不可与生命相提并论,相较于我国刑法中“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侵害人身法益的犯罪,其社会危害性是相对较小的,而那些“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侵害人身的犯罪是限制减刑,贪腐犯罪是不得减刑,这样的规定至少在常理上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在这里并没有体现“罪责刑相适应”。贝卡利亚认为,衡量一个犯罪行为的罪责大小是与犯罪行为本身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的,贪腐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在严重性程度上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同侵害人身权益的犯罪相提并论的,但是在处罚结果上却迥异,这不得不使人产生怀疑。所以,这种刑罚制度并不是道义惩罚,因为报应之刑完全是以罪为界限的,不存在罪外之刑。
与报应之刑对应的是功利之刑。如果说报应主义注重的是结果和行为的话,那么功利主义则是侧重于人。与报应之刑不同,功利主义的目的不在于是否完全做到了“罪责刑相适应”,而在于对预防犯罪是否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国家动刑于个体,完全是出于国家是否能收获相应的利益。贝卡利亚指出,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高明,这乃是一切优秀立法的主要目的。[8]然而这样一部过度以预防为主旨的刑法修正,会将人们置于无罪被动刑的危险之中,同时这也与贝卡利亚的主观意愿相违背的——从全面计量生活的幸福和灾难来讲,立法是一门艺术,它引导人们去享受最大限度的幸福,或者说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们可能遭遇的不幸。[8]对贪腐犯罪的严厉打击虽然大快人心,但是我们利用重刑去预防犯罪必然会陷入功利主义的怪圈,即完全无视犯罪人本身所具有的人权,将人视为解决矛盾的工具。观察贪腐犯罪法定刑的修改根源,不能不归结于刑事政策的影响,以及国民对贪腐成风这种社会现象的厌恶,国家为了缓解社会矛盾,所以适用重刑。可以看出,每一次的“严打”对百姓来说都是值得庆贺的事情。综上,《刑法修正案九》第三百八十三条的刑罚修订,不符合道义之刑,完全是功利之刑。
3 国家功利主义的自然法背反
功利主义的动刑依据并非所犯之罪,而是基于对国家是否有益处。所以,“作为可能的被害人和被保护者,一部以危险性、再犯的可能性、保卫社会目的性为动刑依据的刑法,对每个人而言又意味着虽被害却无刑或轻刑,因而是不公而非保护”[9]。同时也可能出现的就是刑罚过度化,会严重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
此外,还可能出现的另外一种现象就是——无罪有刑。首先展示出来的便是在立法层面涌现了无数的刑法规范——“今天的立法者一开始就急于成为十足的立法癖,似乎每个新发现的社会现象都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规则或一个刑法条文”[10]。然而刑法的谦抑主义则要求刑法作为最后的手段对社会进行规制,必须明确其刑法规制的边界在哪里。休漠曾说:“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会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科学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会通过这样或者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11]然而,何为人性?几乎所有哲学家都指向了两个字——理性。理性其核心内容就是自由。康德认为,自由是每个人据其人性所拥有的一项唯一的和原始的权利。人是有理性和自由的,那么必然会独自作出判断或者独立地生活。人虽然是社会的动物,但是也同时具有保持自我不被侵犯的价值。康德也同时指出:“人只能作为目的对待,而永远不可以被作为工具。”自然法需要人类的自然理性去读取,故而我们认为自然法的实质就是弘扬理性,而理性的精神实质又是指自由。所以在对比个人自由和国家利益的时候我们应以自然法为基准。正如密尔所说:“人类之所以有理由有权利可以个别地或集体地对其中任何成员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目的只能是自我防御……对于他本人,对于他自己的身体和心灵,个人是至高无上的。”[12]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也表示,人们为了避免原始的战争状态,将自己手中的权力尽可能少地交到国家手中,形成契约,以此来保护自己的自由。然而功利主义正是将法律作为手段来达到国家维持繁荣或者生存的目的,在立法方面,将刑法之手不适当地伸向民法、商法等经济领域,扩大自己的调整范围。刑法作为最为严厉的法律基于其自身的强制性受到统治者的偏爱,然而过度刑法化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公民自由的萎缩。在司法层面,因为立法技术不当、兜底条款过多③导致了司法解释权力的膨胀,以至行政权力扩张对司法的干预,进而造成了刑法对社会管理的过度化现象。这种现象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对自由的侵害,即对自然法的违背。
4 由民主到民粹——国家功利主义的悲歌
犯罪意味着主观的恶性,是人身危险的表征。社会危害不仅寓意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更是指对被提升为共同意志的社会伦理秩序的损抑。“这意味着立法者将何种行为界定为犯罪,可以超越客观行为自身的属性、范围、程度,根据某种价值标准去塑造犯罪,这种被塑造出来的犯罪才是刑罚的根据。就是说,功利之罪有时是主观之罪。”[9]然而结合我国的犯罪论体系,以主观恶性来评判犯罪与否存在着极大的危险。综观我国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在外观上存在整体性评价的特征,而四要件犯罪论构成体系又以“社会危害性”统筹,所以“不可避免地存在以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整体思考代替对于四要件的整体分析”。[13]社会危害性是客观危害与主观恶性的统筹,存在量化的风险,即只要其中一个方面的危害达到了较高的标准,那么其他方面便会不予考虑而直接定罪。国家功利主义强调主观归罪,而犯罪论体系并存主观归罪的风险,刑法便成为“杀人”的利器。
国家功利主义的根源还可以从公民角度进行解读。托马斯·霍布斯认为:“对权势的热衷,并不局限于少部分人——它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特性。”[14]正因为如此,公民为了避免战争状态所以要通过协议把自己一部分的权利交给万能“Joe”④,以此来塑造一个强势的权威来保护大家的和平——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功利主义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国家的统治,因为对于民主国家来说,最大的倚仗莫过于选民。犯罪会产生对社会伦理道德的破坏,因为社会伦理在一国内是一种广普价值,所以势必会给人们带来对犯罪行为的愤恨感。“民愤的大小,体现着犯罪对人们既存的价值观念的破坏程度,是人们心理上原有的价值平衡因受犯罪的冲击而失衡的严重程度的外化。同时,民愤的大小又反映了人们对犯罪的否定评价的严厉程度,内含着人们要求惩罚犯罪以恢复价值的心理平衡的愿望的强度。因此,定罪量刑应该考虑民愤。”[15]但是,定罪量刑的依据如果掺杂了民愤,例如本不该判处死刑的,因为产生的民愤极大,所以判处了死刑,或者本应该判处死刑的,却因为民愤不大或者人们有所同情没有判处死刑,这都是对理论和法律的曲解,是站不住脚的,有悖于刑罚目的。这种轻罪重罚、重罪轻罚则是典型的功利主义的表现,同自然法中提倡的理性和人性是完全背反的。康德曾言:“人只能作为目的,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作为工具或者手段。”论及民愤,我们不得不提霍布斯的“情绪”,霍布斯将情绪划分为喜爱和厌恶,而情绪一词“motion”本身具有运动的意思,情绪是打动我们的东西,而运动的基本要素是方向和速度。当我们的情绪被某种方向所引导时,感情的强度便是我们运动的速度。犯罪本身是对社会伦理等广普价值的违背,在情感上必然会使公民产生仇视心理,也即厌恶态度。“如果自我被迫承认它的软弱,它就会处于焦虑状态——关于外部世界的现实焦虑、关于超我的道德焦虑和关于本我中情欲力量的神经症焦虑。”[16]正如费洛伊德所说,“创伤”是与生俱来的,需要社会和政府提供一定的空间和时间来弥合,而我们理解到这种肾上腺分泌的所引发的厌恶情绪也是一种需要弥合的创伤,这种厌恶和愤恨需要国家采取制裁措施(因为公民把自己的惩罚权力让渡给了国家),所以民愤的积怨会在对犯罪者的严惩中得以实现。
5 形势所需:国家功利主义社会解读
任何犯罪现象都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实证学派恰恰因为它旨在寻求个人和社会权利的均衡,所以不满足于支持社会反对个人,它也支持个人反对社会。”[10]在这种理念的支撑下,犯罪社会学派认为惩罚犯罪人是为了守卫社会,刑法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这就为国家功利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所以对贪腐犯罪的严惩便有了实质根据。因为“每一个社会都有其应有的犯罪,这些犯罪的产生是由于自然及社会条件引起的,其质和量是与每一个社会集体的发展相适应的”。[17]因为每个犯罪的产生都是与这个社会的基本物质存在相符,所以不可避免,而贪腐犯罪在我们当下社会是不可避免存在的,犹如附骨之蛆,挥之不绝。《刑法修正案九》的修订对贪腐犯罪施以重刑也是有根本原因的。“由于社会环境的异常,我们有时也发现一种犯罪的超饱和状态。”[17]这种犯罪的超饱和状态可能是由很多状况引起的,但却是最终决定国家对其实施严惩的根据。
“刑法是刑事政策最重要的核心、最高压区和最亮点。”[18]所在《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便展现了刑事政策的需求。刑事政策必须是在社会基底上对社会需求的反应,以此上升到刑法中,以国家强制力量来满足人民意志,使人民意志成为一种有效维护社会和促进社会和谐的权力。刑事政策和刑法是不可分离的,然而刑法过度回应刑事政策就会产生“现象立法”或者“刑法滥化”。“刑法和刑事政策,毕竟在本质属性、制定主体和程序、表现形式与内容、实施方式、调整范围、稳定性程度方面有显著不同,两者的差异决定了应各自归位,各就各位,不能越俎代庖、互相替代、混为一谈。”[19]所以李斯特的至理名言至今广为流传:“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
然而为何会出现这种刑事政策代替刑法规范的现象呢?这其中存在着必然的社会机理。在法治完善的国家,权力能被有效地制衡,立法机关处于独立且超然的地位,在制定法律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理性来制定相应的条款。司法机关与之相同,不存在行政权的干预,或者对立法权的依附从而导致被动地扩张。国家出于功利主义考量则势必会将刑事政策植入刑法,从而来满足自己的目的。并且因为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不会受到民众的批判,反而会令其欢欣鼓舞。但是,这种违背“理性、自由”的实定法是同自然法背反的,因为它完全无视了犯罪人本身的权利,同社会契约中的平等精神决裂。回归到规范学中,即违反了“罪责刑行适应”的基本原则。
6 结语
国家功利主义的出现标志着刑法由“行为中心论”向“行为人中心论”的立场转变,在当今语境下,难免会出现刑事政策取代刑法成为调整公民行为规范的极端现象。功利主义的过分实施产生的必然结果就是对自然法之理性和自由的摧毁。法治是法律治理,更是善法的治理,所以刑法作为法之利器更需要成为善法,将刑法的触角严格谦抑,突出人的个性自由,在精神实质上体现出自然法的理性,由此法治方可实现。
注释:
①在美国模范刑法典中应用较多的翻译是“life imprisonment”,但是也有另外一种翻译是“penalty of life”。笔者认为第二种翻译在直观上表意并不明确,故采用第一种翻译方法。
②拉德布鲁赫在二战以前对法律和正义持新康德主义法学中的相对主义观点,认为法律是人类共同生活的一般准则,法律的终极目标是实现正义。二战以后,他转而信奉相对温和形式的自然法,认为法律是必须有绝对的价值准则,完全否定个人权利的法律是绝对错误的法律。法律实证主义的法律有利于法西斯政权对权力的滥用;在实在法和正义的关系上,如果一种法律规则对正义的侵犯已达到不能容忍的地步,这种法律已成为非法的法律。
③在我国刑法中存在大量的兜底条款,例如“其他”等;还有几个“口袋罪”,例如“寻衅滋事”等。
④这里万能的Joe就是Hobbes声称的国王。
[1][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J].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George P.Flether.Rethinking Criminal Law[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xix.
[3]Thomas Aquinas.The Summa Theologica[M].Translated by M.C.Fitzpatrick and J.J.Wellmuth.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2009:996-997.
[4]Edgar Bodenheimer.Jurisprudence:The Philosophy and Method of The Law[M].Haward University Press,1967:39.
[5]Immanuel Kant.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J].Translated by Mary J.Gregor.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1996:15.
[6]Augustine.On Free Choice of Will[M].Translated by Thomas Williams.Hackett,1993:17.
[7][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M].王昭武,刘明祥,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9.
[8][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103.
[9]白建军.罪刑均衡实证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54.
[10][意]恩里克·菲力.犯罪社会学[M].郭建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100,105.
[11]David Hume.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2.
[12]John Stuart Mill.On Liberty and Other Essay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126.
[13]张明楷.犯罪构成体系与构成要件要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7.
[14]Thomas Hobbes.Leviathan[M].Macmillan Company Press,1962:34.
[15]陈兴良.刑法哲学(上)[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151.
[16]J.Strachey.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Vols.I-XXIV[M].The Hogarth Press,1986:78.
[17][意]恩里克·菲力.实证派犯罪学[M].郭建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183.
[18][法]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刑事政策的主要体系[M].卢建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
[19]卢建平.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论纲[J].法学研究,2011(5).
责任编辑:卢宏业
PhilosophyofLawCritiqueontheUtilitarianoftheState——From thePerspectiveofCriminalLawAmendment(Nine)Life Imprisonment of the Corruption Crime
WANG He-yong1,SONG Yao-wu2
(1.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arbin 150001,China; 2.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arbin 150022, China)
The philosophy of criminal law is the world view and methodology of the most essential problem of criminal law. As an unwritten law discovered by human reason, natural law is an ideal order close to the nature of human nature. Therefore, any real law must follow the origin of natural law. TheCriminal Law Amendment (Nine)sanction measures for the crime of torture in “Criminal Nine-year”, although the setting of this clause is responsive to the criminal policy, is helpful to dispel the social contradiction, but violates the justice, freedom and fairness. As a natural law value principle risk. The emergence of national utilitarianism torture has a profound social origin, not a contingency. Study the reason of the life imprisonment of corruption crime in violation of natural law from the angle of human reason and freedom, and prove that rule of law must be the rule of law which can be realized in the natural law context.
Philosophy of Law;Natural Law;Classicalism;Positivism;National utility
10.3969/j.issn.1674-6341.2017.06.017
D90
A
1674-6341(2017)06-0049-04
2017-08-29
王合永(1991—),男,河南鹤壁人,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