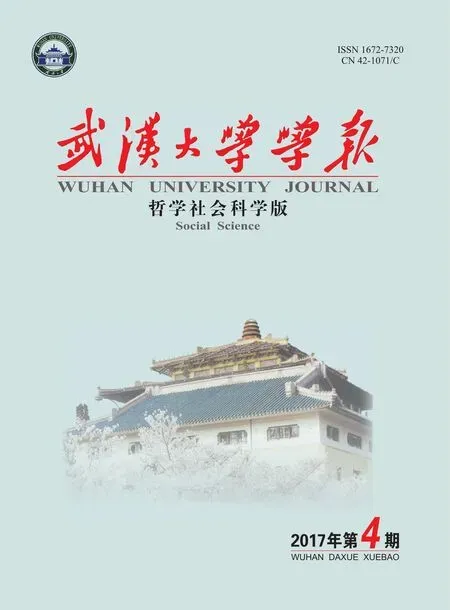依法治国背景下社会保险法制之建构
2017-03-09郑尚元
郑尚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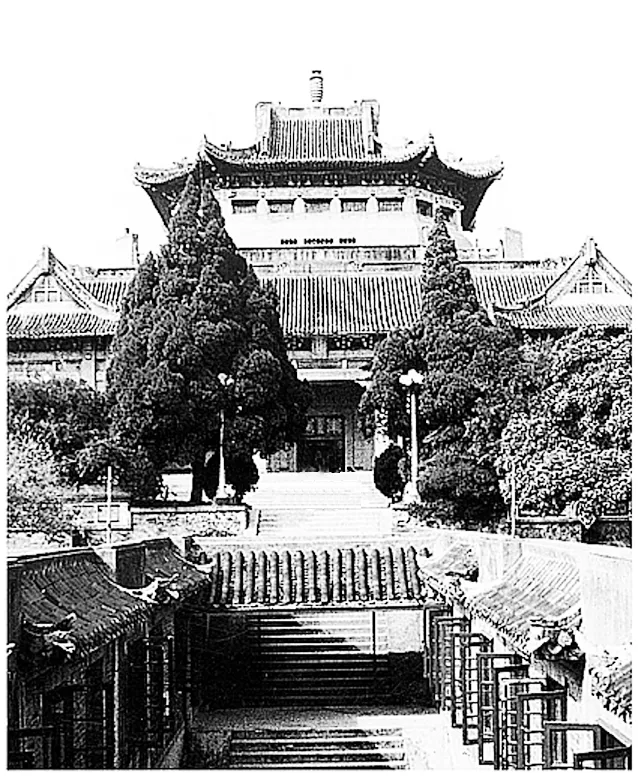
依法治国背景下社会保险法制之建构
郑尚元
社会保险法制系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中的重要内容。社会保险制度起源于德国,早在上世纪初的西法东渐中,该领域法制就卷入了这一历史进程。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先后在不同的社会保险项目中立法,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社会保险法律体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保险法治。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初建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失业保险条例》《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工伤保险条例》和《社会保险法》的颁布实施,开启了法制化进程。但是,目前的社会保险制度,从立法、行政到司法各层面,与依法治国的要求相去甚远。实现社会保险领域的依法治国,立法需要精细、行政须依循法制,司法救济需要打开大门。
社会保险争议; 依法治国; 社会保险法
一、 比较的视野:社会政策实施与社会保险法制之实现
第一,社会政策所涉内容宽泛,社会保险政策属最重要的社会政策之一。社会政策的范围较为宽泛,涉及人口政策、土地政策、劳动政策、农业及农村政策、医疗保健政策、社会保险政策、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政策、社会组织政策等各个方面。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文化政策、科教政策、外交政策一体合成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施政方略及价值导向。社会政策可谓社会立法之灵魂。社会政策之落地于法治国家,必然立足于社会立法之展开,社会政策之灵魂必附体于实体法律、程序法律制度,才能成为“活”的政策。“1881年11月17日,德皇下诏实施社会保险,诏文同时澄清社会改革理由与保障对象,并强调‘就挽救社会败象而言,仅采镇压社会民主暴动的方式并不足以成事,国家应同时关注并增进劳工福祉’。这项改革大体而言是一种手段:‘为确保留给后代一个崭新且持久的内部和平,以后给予贫者较多的保护与慷慨的辅助,这是他们应该获得的。’”(Eberhard Eichenhofer,2006:22)上述政策之实施,史上称之为“黄金诏书”,该项社会政策乃是社会保险制度确立的政策宣言,而此项社会政策之实施仰赖于德国社会保险立法之展开。1880年代,德国国会相继通过了疾病保险法案、伤害保险法案、老年及残疾人年金法案,上述三部法律奠定了现代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基石,衍生出相应的社会保险法理,运用商业保险之保险技术,嫁接社会政策,以求得收入之社会重分配。二战后德国继续秉持其社会保险理念,在其基本法(宪法)中确立了社会法治国原则,落实社会福利政策,并于上世纪70年代在各项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基础上开始编编纂社会法典。德国社会保险政策与社会保险法治之形成可谓理念与制度结合的典范。
第二,社会保险法制形成在大陆法系国家已经成型。上文谈及德国创建社会保险法制的时间脉络,在德国创建社会保险法制的同一时期,欧洲大陆的部分产业发达国家,例如荷兰、丹麦、法国等都开始创建社会保险法制。法律制度与产业发展一样,是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扩散的,东亚地区,日本政治经济率先“脱亚入欧”,其法律制度一样在“西法东渐”的进程中扮演了马前卒的角色。日本系亚洲最早建构社会保险法制的国家。1922年,日本颁布了亚洲第一部社会保险法——《健康保险法》,之后,1938年颁布《国民健康保险法》、1941年颁布《劳动者年金保险法》、1944年颁布《厚生年金保险法》、1947年颁布《失业保险法》和《劳动者灾害补偿法》、1959年颁布了《国民年金法》、1997年颁布《介护保险法》。上述法律覆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护理各项社会保险项目。当然,这些法律历经修正,辅之以配套的其他法律制度,形成了完整的社会保险法律体系。尤其是因应时代变迁、老龄化与少子化所导致失能老年人、临终关怀老年人之护理问题相当突出,日本于1997年颁布实施《介护保险法》,属于近期创建的新型社会保险制度(菊池馨実,2014:16-17)。日本社会保险法制完备,为年老、失业、工伤、疾病以及失能等状态下的弱势人群提供了较安全的社会保护伞。对维系社会的稳定、保障国民生活之安定、分担企业经营风险等各方面都起到了巨大作用。当然,起步于军国主义年代的社会保险法制,团体主义至上,自然不会发生“自由主义”之杯葛。需要指出的是,其“社会”与“保险”的嫁接,立法先行的导向,构成了其法治国家在社会治理领域的精髓。尤其是战后颁布的《失业保险法》在产业凋敝、失业人口激增的情势下,发挥了独特的社会作用;《劳动者灾害补偿法》在工伤领域立法起点高,保障了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受害者的合法权益。至于《国民年金法》和《介护保险法》乃是社会保险保障层次的全面提升。
我国台湾地区之社会保险法制格局已形成。我国近代产业落后,未及工业化,国家即陷入长年战争。1943年,除在四川部分地区实行过零星的社会保险试点外,社会保险在二战之前几乎与我国绝缘。1947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所谓的《宪法》,该《宪法》确立了在社会安全领域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的方略,但大陆地区在1949年之前几乎未有实质性社会保险法制。国民党政府败退到台湾地区后,开始实施社会保险制度。1958年颁布了《劳工保险条例》,同年颁布了《公教人员保险法》,1994年颁布了《全民健康保险法》,2002年颁布了《就业保险法》(指失业保险),2007年颁布了《国民年金法》(郝凤鸣,2008)。目前,《劳动者灾害保险法(草案)》与《护理保险法(草案)》已经完成,准备进入立法审议程序。台湾地区社会保险法制起步较晚,但已经形成了社会保险法制格局,尤其是1994年颁布实施的《全民健康保险法》,系突破所有人群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险法,该法在台湾地区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法律效应前所未有,并被标签为台湾地区社会法的骄傲。
从德国创建社会保险法制,到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效仿、借鉴、创制其社会保险法制的路径看,社会保险法制首先必须立法,没有充分、完备的立法,便无法治可言。一个没有规矩、没有刚性秩序的制度,永无守秩序、守规矩的操行可言。我国虽然颁布了《社会保险法》、《失业保险条例》和《工伤保险条例》,但是从立法的路径看,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保险立法皆以具体社会保险项目而展开,分清轻重缓急,逐步立法,渐次而成社会保险法律体系。
二、 我国现行社会保险法制及其制度的问题
(一) 从立法、行政视角看我国社会保险法制
社会保险法制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之有机组成部分。社会保险领域要实现依法治国,有法可依乃是必然选择,现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之规定远远不能满足依法治国,建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求。我国于20世纪50年代初颁布了《劳动保险条例》,如按照此制度逻辑,今日社会保险法制境况应当远不止此,但该项制度于20世纪60年代末中断。上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及企业负担职工福利机制的崩塌,社会保险制度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近20多年来,我国社会保险成绩有目共睹,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各项社会保险制度都取得了相应进展。毋庸讳言,我国社会保险法制化程度很低,虽然颁布实施了《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失业保险条例》等实体法律法规,但是,从法律的实施效果看,立法反馈结果呈现为法律“操作性差”,从行政视角而言,社会保险行政并不完全仰赖法律法规的规定,至于社会保险争议之司法审理基本上还未起步。就“社会保险制度”而言,多数人不了解政策与法律在该领域的界限,于行政部门而言则更习惯操作于得心应手的“政策”。以我国规模最大、覆盖人数最多的养老保险制度为例,仍未脱离“政策直接治理、制度与理念混沌、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未及形成”的窠臼。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就是依据1997年国务院发布的这一规范性文件而设计的,目前制度运行的依据——国发【1997】26号,这一国务院规范性文件至今未曾修正过(郑尚元,2005:99-107)。近20年来,养老保险制度除体现在《社会保险法》有关十个条文之外,再无任何法律规范出台。
2001年3月9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李鹏委员长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工作报告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七大法律部门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其中民商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法律制度的构建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这些法律部门中的部分学科已经进入大陆法系普遍认知的法教义学、法解释学的研究阶段,法律制度与学术研究已经进入精耕细作阶段。即使经济法部门虽未进入该阶段,但是,其立法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在近20年时间内,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法、反垄断法、产品质量法、价格法、广告法、预算法、各类经济、金融监管法相继出台,至少在立法环节已经将社会法远远甩在后面。我国社会法在基础理论的认知上尚未形成共同认知,但是,社会保险法作为最主要的社会法是不争的事实。“社会保险究竟是一种‘保险’?这看似理所当然的问题,实则仍存在斟酌的空间。对于社会保险制度性质的界定,有两种可能的诠释:保险说及救助说。救助说以为社会保险乃是一种公法性质的、社会政策性的救助措施,而并非保险;相对的,保险说则主张纵使并非所有私人保险的重要原则都能适用于社会保险,这也不影响社会保险之作为一种保险的性质。”(蔡维音,2001:140)从某种程度上分析,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项社会保险制度仍在纠结于社会保险是否属于保险的选择上,如医疗保险、农村养老保险这些制度更多地仍体现出“吃大锅饭”式的“救助”阶段,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虽历经多年,但在保费缴纳与养老给付环节仍未实现权利义务一致的精算阶段,很多情况下依赖财政的直接转移支付。在如此背景下,其立法裹足不前,即使有出台的法律,亦是粗放到无法操作的地步,最终成为社会治理领域或立法领域的“形象工程”。
(2)港口性质、功能定位的前瞻性。正确认识港口的地位与功能的演变,是做好杭州港总体规划的前提与基础。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港口地位与功能正逐步演变。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各领域对物联网应用的不断推进,以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新技术手段朝着规模化、协同化和智能化方向快速发展,港口作为多种运输方式的交汇,是多方数据信息的有机融合。信息化水平对港口功能拥有重要的影响,它不仅是衡量港口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甚至成为港口未来发展走向的决定力量。杭州港港口性质和功能的定位,要充分考虑未来港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推进杭州港的智能化,打造智慧港口,使杭州港的港口性质及功能定位具有前瞻性。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如同交通规则,应具有实践的操作可能,否则,该领域也会出现“拥堵”。社会保险分为养老(老年年金)保险、医疗(健康)保险、失业(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护理保险,我国目前开办的只有前四项。这些社会保险项目具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具有不同的法理差异,虽然扶弱济贫、互助共济的理念一致,但仍存在制度上的差异。由此,各项社会保险应当单行立法,使之能够成为人们“操作得了”、“管用”的法律,而不再只是“观赏法”*参见吴飞(2006).法学教授质疑劳动合同法:不要成为贵族法观赏法.民主与法制时报,2006-04-10.董保华教授认为,我们不要把《劳动合同法》搞成一部观赏法,一部没有任何执行可能性的法律。事实上,我国《社会保险法》的法律适用可行性远比《劳动合同法》要差。。以工伤保险项目为例,《社会保险法》所作规定较之《工伤保险条例》而言,明显具有不可适用的性质,更多属于原则。此外,从1986年颁布的《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起算,经历了1993年颁布的《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及至1999年颁布实施的《失业保险条例》,失业保险项目的法制化程度偏低乃是社会共识。从社会保险行政复议及诉讼的类别看,失业保险争议行政复议的数量极其有限,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窥见的是,要么是当事人普遍放弃了自身权益,要么是该制度所创制的权利救济程序与劳动者权益获得“成本与效益”间发生了逆转,概言之,失业保险项目尚未法制化。尽管《社会保险法》《失业保险条例》以及《就业促进法》对失业保险皆有规定,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规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规范。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社会法作为法律部门,其立法阙如直接形成了法律体系中木桶效应之法律短板,类似如何缴纳养老保险费、如何领取养老金,如何计算保险给付的标准等等皆无法律上的明确规定。法律制度不止于条文的规定,更为关键的是条文中所蕴含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法律范畴的落地。迄今为止,我国社会保险项目中只有工伤保险一类在“工伤认定”上步入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而其他社会保险项目皆止步于程序救济,换言之,《社会保险法》连“工具”都谈不上,更不必说法律信仰、法治思维、法治理念的形成了。法治的实现,体现在立法、行政、司法的有机整合,体现在制度执行与信仰形成的统一上。于此,我们能够看到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最多只能称作逐步形成,社会法部门中最基础的社会保险法制仍停留在立法阶段,中国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完善从立法层面上讲,仍可谓前路漫漫。
由于法律法规规定得过于原则,对于推动法律实施的行政部门而言,依法行政就成为一道难解之题,而且越是率先进入法律实施层面的社会保险项目,此等难题就愈加突出。以工伤保险先行制度为例,该制度系始于对劳动者权益维护、出于对工伤患者及时救治的良好出发点,但是,在制度实施环节出现了两种情形,一则先行支付之后,工伤经办机构几乎未曾出现过追偿回来的先例,基金支付先行之后等同于“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二则是当事人的先行支付申请很少得到批准,因行政部门出于行政问责、审计无法入账等各种因素,使得该制度的实施成为镜花水月,华而不实。实则是在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未参保之用人单位、救治医院、工伤患者之间在立法层面没有形成相应的法律逻辑,换言之,因立法之粗线条所导致的依法行政难题,几乎无解。又如工伤保险补偿与第三人责任之民事赔偿间的关系问题,一直困扰着工伤经办机构,甚至困扰着人民法院和劳动人事仲裁机构。何以如此?法律未有明确规定*德国社会法典关于职业伤害的规定中,工伤职工的权益主张不得向雇主请求,其请求权之相对方只有保险(工伤)机构。雇主承担的是社会法上的工伤保险缴费义务及维护职业安全卫生的义务,雇主的义务更多体现为公法上的义务,第三人造成职工人身损害,按照侵权法原理,该第三人应当履行赔偿义务的,其赔偿对象是保险机构,即保险机构取得了相应的保险代位请求权。。类似的问题对于行政机关、获得授权的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而言,最终也只有一个答案:法律法规未有明确规定。或许会有这样的提问,既然问题提出来了,为什么不把法律制定的详实一些、具有可“操作”(适用)一些呢?显然,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展开从立法到行政,尚未形成“依法行政”的格局,甚至出现法律规定的不明确、不具体、存在相关的逻辑问题,这可能导致包括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内所有社会成员的法律信仰危机。工伤保险率先进入法律实践,行政部门所遇到的问题亦多,如同社会生活中的俗语:少办事少出错,不办事不出错,为了不出错,干脆不办事。如果法律制度也陷入如此怪圈,依法治国将是一句空话。
(二) 社会保险立法空白——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及护理保险为例
如果说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制度的建构,起步阶段即与法律制度相嫁接,即以形式相对规范、规范相对稳定的国务院行政法规而展开,那么相较而言,覆盖范围更广、影响更大的两类社会保险,养老与医疗起步阶段仍脱法运行。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及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发起、委托美国的英特达斯集团(Intrados Group),由该机构联合安永公司、皇家事务所、IOS伙伴公司、道而顿全球咨询公司以及美国商业部人口调查局国际项目中心等机构联合完成的《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项目:终期报告》建议中国政府起草《基本养老保险法》,该《报告》指出:“中国需要制定《基本养老保险法》,加强养老保险领域的法制建设,其政治意义在于使政府政策趋于稳定,使公民增强安全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及亚洲开发银行(2002).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项目:终期报告:55.时至今日,我国运行将近20年的《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仍在运行。2010年颁布的《社会保险法》,该法涉及养老保险的十个法律条文即是中国养老保险的立法现状,当然,部分地方法规涉及了养老保险制度,但需注意的是,养老保险制度系社会基本生活制度之一,相当多国家和地区宪法直接规定了建构社会保险的内容,其后便是专门法律的规定。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先颁布实施了劳工类的养老保险法律,之后颁布实施国民年金法律(大陆地区称之为城市居民养老保险)。《社会保险法》所规定的养老保险,既未规定费基、费率,也未规定保险给付等基本内容,十个条文大多数是“宣誓性”条款。“依法行政的基本内涵就是为了保障公民的权益和公共利益,要求一切国家作用应具合法性,应当服从法。”(余凌云,2010)换言之,依法行政的前提必须是“有法可依”,养老保险项目作为社会保险制度中重要的支柱性保险项目,须依法运行。法律规定如何缴费、按照什么样的标准缴纳、缴纳年限如何累积计算,缴费义务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即可请领养老给付,当事人对缴费、保险给付异议的行政复议和相关法律诉讼制度、养老保险犯罪及其刑罚等,都是构成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关键内容。“在社会保险运行过程中,社会保险权人权利的实现,有赖于相对人合法的作为或不作为,一旦遭受权利侵害,有权提请法律救济。”(林嘉,2012:175-181)只有不规范的制度,没有不规范的国民,如果存在可预期的法律制度和可救济的程序,相信大部分当事人不会寻求信访、上访等非常态救济途径。
医疗保险项目同样属于立法的空白地带,目前存在的法律规范只有《社会保险法》所规定的十个条文,没有其他任何立法成果的体现。医疗保险涉及医院(包括医师)、保险经办机构、当事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等法律主体,实则是医疗资源的社会重分配。现实生活中的医患矛盾,如同厦门纵火案一样,皆因民生问题而起。法律制度的阙如增加了社会成员的不安全感和不稳定感,甚至产生极端事件*我国台湾地区将“SOCIAL SECURITY LAW”直接翻译为:“社会安全法”,社会保障关涉民生优劣、社会安全与稳定。社会保障可靠的国家和地区,社会相对安定,社会收入分配和社会支出(包括教育、医疗、住房及日常生活消费)较为合理,社会相对安全与稳定。。从社会生活的另一个侧面分析,中国社会的高储蓄率和大众存钱防患的心理,多数因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问题所致。如果我国社会保险制度能够走向法制,能够给民众以定心丸,上述问题的严重程度必然会有所减缓。
我国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深度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即将成为全社会的难题之一,且近4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将使该问题更加突出。高龄失能老人及临终关怀问题将成为未来几十年中国社会问题中的症结。二三十年来,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一样面临此等难题,在其强大的经济支撑背后、在其福利国家的政策导向之下,他们先后创建了护理保险(日本称介护保险)法律制度,重构另一种社会重分配。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在问题已经发生的前提下化解的,以日本为例,每年几千甚至上万的“孤独死”老人,催生了日本老年保健法制与老年护理保险法制,催产了日本《介护保险法》。我国台湾地区“护理保险法”(草案)已经草就,拟提交其“立法院”审议,建构长期照护制度乃是近年来各方关注的重点。大陆在该问题上早已不可能是“未雨绸缪”,当下实在呈“见雨找伞”之迫。现实生活中,只有上海、青岛等地开始试点护理保险工作,国家和地方立法尚未提上日程*近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文,推动老年护理保险工作试点。笔者曾在年初的北京市第十二届政协四次会议提案,推行护理保险试点,推动护理保险立法,为求解北京市老龄化、高龄化背景下的失能老人护理与临终关怀难题而建言。。
上述社会保险领域立法的空白与工伤保险、失业保险法律制度所谓的不完善相比较,其制度实施更不可能依法行政,因其无法可依,所谓的制度运行就是谁制定规定,谁负责实施,谁负责解释。
(三) 社会保险争议处理之脱法运行
我国社会保险争议处理,工伤保险制度率先进入了司法救济程序,如工伤认定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尽管出现了类似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予认定工伤而人民法院通过判决或裁定推翻行政认定结果,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重新认定后仍不予认定工伤及二审法院判决、裁定继续推翻行政认定结果的“踢皮球”事件,但是,该制度毕竟进入了司法维权的程序。而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项目则很难启动这样的程序,或者说该行政诉讼程序已经打开,但因实体法未曾跟进,司法救济程序实质上未曾打开。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1条规定:“《劳动法》第82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应作如下理解: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补缴社会保险费的,应从劳动者知道或应当知道用人单位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之日起计算。”这为高级人民法院,而且是改革开放前沿的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此等指导意见,我国社会保险法制状况之棘手、法律理念之薄弱可见一斑。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或补缴社会保险费是劳动者请求的结果吗?实然结果与应然选项是一致的吗?诚然,我国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部分用人单位故意或过失未予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之情形,但是,用人单位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公法关系须依据公法规定处理,用人单位补缴应当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公法上的请求权(部分国家和地区因雇主不缴纳社会保险费须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从法理上讲须依赖劳动者请求吗?在用人单位、劳动者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之三角关系中,为什么把不该其承担法律义务的难题踢与劳动者*当然有人会提这样的疑问,劳动者客观有补缴的请求,法院应当受理并作出裁决,不然劳动者的权益更难以维护。试问,在劳动者社会保险法上的实体权利未置周延之前,其法律上“权益”存在吗?法院真能判决、裁决出合理的补缴额度?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能够按照该额度受理补缴?并为当事人以保险给付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1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之司法解释,一样将社会保险争议视同为劳动争议,将公法关系等同于私法关系来处理。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于加入社会保险的劳动者所予之社会行政给付,是公法上的给付。如果以养老保险为例,其给付义务以劳动者退休或达到养老保险给付法定条件始,直至其生命的结束,当事人之生命余命可能三五年,亦可能三十、五十年,用人单位赔偿是依据《侵权责任法》赔偿,还是依据其他法赔偿?如何赔偿?财产损害和人身伤害可以赔偿,劳动者未来生活的期待,其生存权又如何赔偿?上述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切皆因社会保险立法之粗犷、社会保险法理之缺失。
三、 完善社会保险法制之路径
(一) 社会保险立法精细化
“社会保险法之前便有各险种的制度构建与实践,我们可以从社会保险法所规范的各种制度中去追溯和整理那些已有的制度。这也是中国大陆地区建立社会保险法制的特殊之处,即政策先行、实验在先,而立法具有浓厚的汇总性质。”(郑尚元、李海明,2011:99-116)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存在是客观的,20多年来,从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生育保险已经并入医疗保险,实质上,医疗(健康)保险中的分娩给付即是生育保险的具体体现。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皆未建构专门的生育险种。等各个社会保险项目的实践看,社会保险先有实践,后有由实践总结的制度的轨迹非常明显。社会保险制度的法制孕育则显得相对滞后,而非立法与实践并行,甚至出现类似养老、医疗实践多年,而立法仍裹足不前的现象。我国经历过较长的封建时期,法制不缺而法治始终欠缺,封建年代并不是无法无天,某种程度上,法制甚至比较完备。但是,约束统治者、约束社会所有人的法律制度,受法律约束的社会心理,尤其是官员受法律约束的心理五千年来未及形成。人们总期待青天老爷的公正赐予、期望皇恩浩荡之开怀。权利理念属舶来品,至于晚近以来,欧陆福利国家建构的生存权和社会权利,更加遥远。但是,颁行社会保险法制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权利乃至权利的救济是无法分开的法治系统。对于社会弱者的辅助,要么,回到类似旧时代的济贫实践,济困者与贫穷者之间并不存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完全属于慈善和恩济之类的自主行为;要么,实行具有权利义务内容、具有法律职责约束和当事人救济的刚性法律制度。
法律制度的实施,是法律“活”在社会之中,各类社会主体都在适用或运用这一“工具”,与不同的主体而言,其实施的视角不一。社会保险法同样如此,于行政机构而言,如何依法行政,体现的是如何授权专门的“保险人”运作这项保险项目,如何征收保险费用,如何确定费基、费率、如何核定给付标准、如何确定合理的给付程序、如何确定期间与期日、基金如何精算、相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欠缴、拒缴保费的处理及法律责任的分配。于投保人而言,是如何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按照标准缴纳保费、通过计算和测算估测未来的预期“收益”、判断自身违反法律义务法律责任的大小。于律师而言,是如何在该法律实施过程中,帮助保险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解释法律、理解法律,甚至利用法律漏洞。而于法官及其他执法者而言,在于按照法律规定能够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概而言之,法律制度的价值在于其“用”,如其不好用、没用或不可能用,则法律制度的价值必然减损甚至没有任何价值。
我国现行《社会保险法》属于“不好用”的法律制度,其他国家和地区皆因不同社会保险项目而立法,未见一部单行法解决所有社会保险事项的立法先例。因而,其法律条文的原则、法律规范的宣示以及法律逻辑的缺失自然不可避免。基层部门的同志经常谓之以“操作性差”,实则表现的是:该法律作为依法行政依据的难度较大,多数情形是没有相关规定,也就是没有依据。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其中,立法的精细化成为未来立法的取向,法律的制定尽可能与实践对接,法律的规定不仅“对”,更重要的是怎么“对”,不“对”如何处理的问题。因而,在《社会保险法》颁行的前提下,在工伤保险法律制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可以效仿我国台湾地区起草《劳动者职业灾害保险法(草案)》*该法律草案在台湾地区“立法院”尚未进入审议程序,但该法草案已经草就。,毕竟我国工伤保险的法律实施积累了相当经验、积累了众多的案例,法制实施的人才队伍,包括法官、律师、行政官员以及学界,已有一定的人才积累。而且,该法涉及面较养老、医疗小,行政部门协调难度不大,完全可以先行立法。为其他社会保险法律起草积累经验,之后,失业保险可以在与《就业促进法》综合考量的基础上单行起草法律。之后,可以另行起草《基本养老保险法》、《基本医疗(健康)保险法》。在上述法律制度一一出台的前提下,辅之以众多的行政法规与规章,也就是说,在社会保险法逐步精细的前提下,我国社会保险法治形成才可谓依法治国。
(二) 依法行政与社会保险政事分开
社会保险法系典型的社会行政法,系特定领域的行政给付法,依法行政是法律实施的重头戏。离开了行政部门,社会保险法无法实施,制度无法运转。传统私法是在定纷止争中,法院与法官相对被动地受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维护公平正义,无须行政机关的介入,法律实施无须行政机关主动实施。社会行政法必依赖于行政机关的介入与作为。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形下,行政权力的张力依然存在,行政机关仍可以作为,但是,其合理的限度只能通过自身的衡量来掌握,规矩也只能是行政机关制定的规矩,很容易出现规则的制定者,同时又是规则的执行者的现象。因此,行政机关推动实施的法律制度更需要法律制度的科学与理性,更需要赋权与限权的平衡。所谓的赋权,即是法律授权行政机关设定相应的给付标准和给付条件,“给付行政作用纵使有法律依据,但立法者对于给付要件使用不确定法律概念,或给付项目、方式及标准等事项授权行政机关订定之,亦为常见。”(沈政雄,2011:15)不止于上述内容的赋权,同时,不少国家和地区,针对社会保险争议,其处理程序制度往往设置相应的行政裁决前置程序。由此,行政机关的权力是客观存在的,限权亦为必要和必须,社会保险法实施的可靠保证即依法行政。
行政机关实施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其赋权的过程,亦是专门机构获得相关权力或相关专门机构成立的过程。我国社会保险制度运转多年,现实生活中,各地存在了形式多样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只是从属性上显示该机构的定性,而非该机构的法定名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亦分不同社会保险项目,如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保险局与医疗保险局。因此,必须通过制定专门法律,确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名称、组织规则、经办规则、法定职责与权限等。在中央及省级层面,依照政事分开原则,分清社会保险事务机构与行政机关的业务界限;未置立法权的基层,如地方行政机构等直接执行事务的机构,行政机关人员直接下沉为办事人员,更多地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办理“业务”。总而言之,应当成立名正与言顺的某某省、某某市(县)社会保险局、医疗保险局,依照组织规则、业务经办规则及相关社会保险法律的规定经办好相关社会保险业务。同时,在赋予上述机构法定权力、职责的同时,亦须使其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最主要的是,要使上述公法人完成社会保险人之法律人格塑造,其既可能成为行使权力(包括权利)的原告,如当事人拖欠保险费的追缴、第三人致害后保险人获得代位请求权等,同时,该机构亦应成为行政给付的法定义务人。
“干预行政首在藉由国家公权力,强制人民为特定之作为或不作为,及违反前述义务时之行政执行。社会安全制度之给付行政,则系国家基于对人民保护义务,依据法律授权体统必要之协助与金钱给付,是项给付并非国家对于人民之施舍或恩惠给付,而是社会正义与社会法治国理想之具体体现。”(台湾地区社会法与社会政策学会,2015:419)没有强有力的行政干预与行政介入,社会保险制度便不能建立,自由主义不能形成社会保险制度;但是,行政之有力干预与有力组织在法律授权及相关法律规定的框架下才能可为与有力。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建构20多年来,社会保险业务的发展并不能遮掩该业务法律主体人格不健全、法律制度不完备甚至严重缺失的短板,在各项社会保险项目立法精细化的前提下,各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正名、机构的修正与完善、业务范围的法定、义务的法定事项缺一不可。
(三) 开放社会保险争议救济程序
“提起社会行政救济之先决要件为权益受侵害,行政救济制度应称为行政权力救济(Verwaltungsrechtlicher Rechtsschutzweg),指人民受行政机关违法或不当之瑕疵行政行为或行政处分,只是其合法权益遭受损害时,依法进行行政机关内部(审议、复查、申诉及诉愿)及行政机关外部(行政诉讼)之保护程序。”(台湾地区社会法与社会政策学会,2015:422)2001年5月8日,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了《社会保险争议处理办法》,该《办法》打开了社会保险争议行政复议的救济程序,但是,我国社会保险争议的实体法律制度欠缺,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情形尤为严重的情形下,行政复议无实体依据,该程序之复议多数为无米之炊。这些年来,工伤认定行政复议案件高居不下,并非只是罹患工伤的当事人好争执与闹事,而是该领域实体法律制度建构步伐相对向前的结果。如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规定如《工伤保险条例》及配套规章制度一样,该项社会保险争议之行政复议一样不会少。现实生活中,用人单位不缴、欠缴、低标准缴纳劳动者养老保险费的情形比比皆是,但是,这种情形下,往往是劳动者向相关方面(仲裁机构、人民法院甚至包括信访部门)的诉求。实质上,诚如上文所指出的因“行政机关之违法或不当之瑕疵行为或行政处分”所致,我国社会保险费征缴力度不够是劳动者的错吗?显然,在该问题上,法律关系尚未厘清。笔者认为,用人单位不缴纳、少缴纳养老保险费皆因行政之不作为或行政行为瑕疵所致。当然,我国现行社会保险制度的法制化程度较低、社会保险制度由劳动保障部门一家唱独角戏是客观事实,行政部门甚至叫苦于征缴手段与力度不足等等。但是,社会保险费的费基、费率是否合理?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是否公平保费负担?社会保险费征缴力度不够,能否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学习拒缴社会保险费入刑、欠缴社会保险费缴纳滞纳金等措施?如果一切皆以法治为背景,所有难题都可以解开。
社会保险争议行政救济程序之建构属于依法行政之范畴,亦为专业行政之必需。而社会保险争议诉讼程序乃是权利救济之最终依赖。德国社会法典的实施,社会法院在其中发挥了专业行政法院的关键作用,即便未置专门专业行政法院的日本,其社会保险争议诉讼亦不鲜见。“在日本医疗保险之争讼案例中,以备保险人医疗资格争议有关之诉讼,占大多数。例如,日本健康保险法、厚生年金保险法之适用不同职域单位的失业之对被保险人取得资格之申请程序,保险人须经相当时日之审核,以确认被保险人取得保险资格日期有关之溯及既往争议案例,判决以事业主之申请日并非被保险人资格确认之基准日,而是取得被保险人资格之基准日,判决原告败诉。”(吴震能,2009:232)从应然角度,今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参加保险的日期、期限长度都有可能成为诉讼的争议焦点。我国社会保险争议诉讼之实然状态,上文所提及的工伤认定的行政诉讼案件较为典型,其他类似工伤保险待遇给付*专指由工伤保险基金所予给付的部分(1-4级伤残),而非雇主所承担的责任部分(5-10级伤残)。、期日和期限等其他争议尚无讼争的先例。至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尚无诉讼案件的审理。养老、医疗两大社会保险领域,当事人并非没有相应的诉讼请求,但是,其请求可能不予立案,或立案后被驳回。原因是,当事人的请求并未形成法律上的请求权,如果实体法规定了当事人的实体法的请求权,程序法同时规定了当事人程序法上的请求权,当事人的请求转换成为法律上的请求权时,上述诉讼请求既可以立案,亦不可能被人民法院驳回。概而言之,我国社会保险法制中的程序缺失较之实体缺失更为严重。
四、 结 语
依法治国系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治国理政之基本理念,现代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各领域,皆以法治秩序为主轴而螺旋式展开。社会保险制度系社会基本生活制度之一,该制度的存在必须走上法制化道路,并最终走向法治。我国社会保险制度之法制化道路已经开启,亦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其立法成果的粗糙、法律实施的无序与权利救济的艰难,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期待中国社会保险法制的成长,期待未来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相对弱势的短板能够补足。
[1] 蔡维音(2001).社会国之法理基础.台北:正典出版文化有限公司.
[2] 郝凤鸣(2008).社会法.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3] 菊池馨実(2014).社会保障法.东京:有斐阁.
[4] 林 嘉(2012).社会保险的权利救济.社会科学战线,7.
[5] 沈政雄(2011).社会保障给付之行政法学分析——给付行政法论之再开发.台北:元照出版公司.
[6] 台湾地区社会法与社会政策学会(2015).社会法.台北:元照出版公司.
[7] 吴震能(2009).日本社会保障制度之研究——以权力救济为中心.台湾地区中正大学法律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
[8] 余凌云(2010).行政法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9] 郑尚元(2005).公开、规范与定型——养老保险制度从政策到法律——中国社会保险立法的进路分析.法学,9.
[10] 郑尚元、李海明(2011).社会保险法制之开启——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月旦民商法杂志,12.
[11] Eberhard Eichenhofer(2006).德国的社会保险:俾斯麦模式及其二十一世纪的挑战.郭明政.社会保险之改革与展望.台北: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李 媛
Construction of Legal System of Social Insurance in the Context of Ruling the Country by Law
ZhengShangyuan
(Tsinghua University)
The legal system of social insuran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socialist legal system.Social insurance system originated in Germany.As early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last century, in the course of “the West Law spread to the Orient”, the legal system in this area was also involved in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Japan and Taiwan successively finished different social insurance projects and their legislation in order, form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social security legal system, and then established the social insurance rule of law.China's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was first established in mid-1980s, after which, with the promulg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gulations on Unemployment Insurance, Interim Regulation on the Collection and Payment of Social Insurance Premiums , Regulation on Work-Related Injury Insurance and the Social Insurance Law, started the process of legalization.However,the current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is far from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rule of law on the legislative, administrative to judicial levels. To realize the rule of law in the field of social insurance, the legislation needs to be accurate, the administration must follow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judicial remedy needs to open its door.
social insurance dispute; law-based governance; Social Insurance Law
10.14086/j.cnki.wujss.2017.04.004
2016-08-0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2BFX091)
DF4;F840.61;F8
A
1672-7320(2017)04-0027-09
■作者地址:郑尚元,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