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辈子去偿还
2017-03-09文◎彩霞
文◎彩 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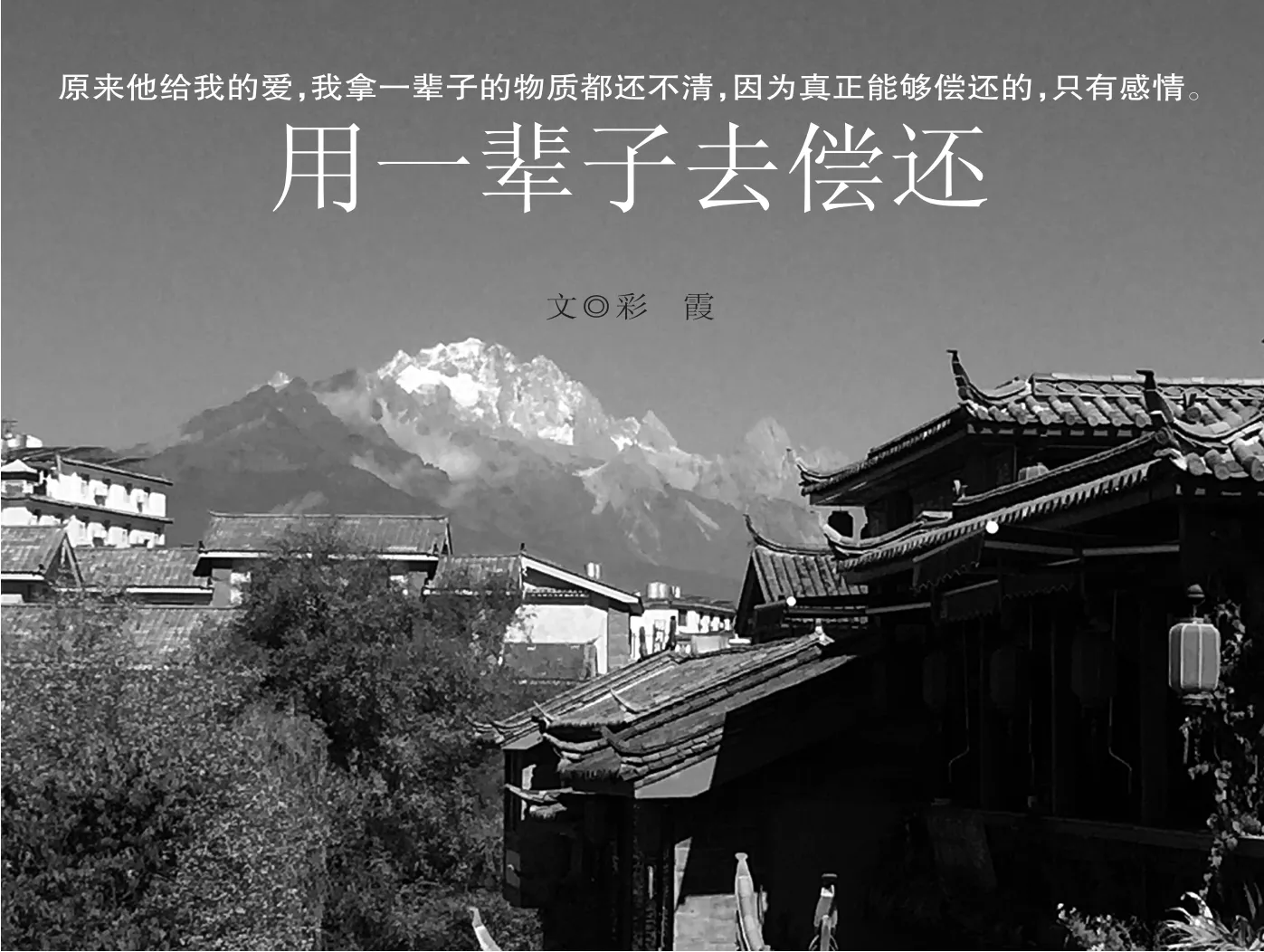
到底是一个陌生的男人
好多年后,我还总做同一个梦,梦见年少的自己小心翼翼地对老何说:“要不,你把我送回姥姥家吧?”
而老何低头不语,只狠狠抽烟。那短短一刻,毫不夸张,在我的感觉中恰如一个世纪般漫长,以至于每次醒来时,脊背都蒙了一层冷汗。那一刻,我多么害怕老何说:“那好吧。”
好在,老何掐灭烟头看了我一眼,淡淡地说:“算了,留下来吧。”
12岁的我松了一口气,感觉腿明显发软,但是并没有哭,直到老何离开,屋子里只剩下我自己时,才抬起头对着妈妈的照片,眼泪流了满脸。
我自小命运多舛,出生后便不曾见过父亲,很小时妈妈将我留给姥姥,独自外出做工赚钱。她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只能在流水线上费精力,收入不多,但也将我一天天养大。只是姥姥和舅舅住在一起,身体又不好,常年吃药,慢慢地,舅妈脸色难看起来,动辄说话给姥姥听。
我也慢慢能够听懂,于是妈妈再回来,就求妈妈:“咱们回家吧。”
妈妈却只是抱紧我不语。再后来,我知道,我们没有家,妈妈在偌大的城里,拥有的,只是集体宿舍里一个窄窄的铺位。
但妈妈还是将我带走了,在我10岁的时候。
于是第一次,我拥有了自己的家,虽然那个家里,除了妈妈,还有老何——妈妈嫁给了她喊老何的男人,那两间位于老街区的旧房子,属于老何。
老何其实并不老,不到四十岁,瘦高,曾是妈妈做工的那家工厂的小领导。不过厂子效益实在很差,老何买断工龄,开起了出租。
老何有过短暂婚史,没有孩子。对老何,我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不喜欢,但多少有些敬畏——心里很清楚,这个家是老何的。我偷偷观察,老何对妈妈很好,给妈妈买新衣,小声跟妈妈开玩笑。
可到底是一个陌生的男人,我对他亲近不起来。这么多年寄人篱下的生活,也让我性格内向,喜怒从不形于色,所以,也不表现出抗拒,不管怎样,老何比舅舅和舅妈好许多。
老何从不叫我的名字,而是叫我小子。有时喊我,“小子,把烟给我拿过来”;“小子,去把垃圾倒了”;“小子,试试这双鞋子合脚不”……
我总是答应着利落去做,那次试鞋子,明显小了一点,但我没有说。后来还是被老何发现了,他兜头给了我一巴掌,“不合适不知道说吗?小鞋穿着舒服啊?”
当然打得不重,我嗫嚅:“也不太小。”
老何嘟哝一句:“闷葫芦!”
有着那样的生活经历,我确实不太愿意主动亲近旁人,但心里是知足的,终于能够和妈妈在一起。有时妈妈也会悄悄试探劝我叫老何一声爸爸。
我不语,“爸爸”这两个字,从小就没有叫过,我叫不出口。或者也并不情愿,因为太清楚地知道,老何不是爸爸。
而多舛的命运并没有完结,两年后,妈妈查出乳腺癌,晚期,已经扩散。
已经没有住院的必要,妈妈跟老何回家。那天晚上,妈妈抱着我哭得天昏地暗。
老何在一旁不语,烟抽得更厉害了。
之后,妈妈没有再哭,而是开始每天拼命给我织毛衣、毛裤。
也给老何织,别的,什么都不说。
两个月后,我12岁升初中的暑假,妈妈离开了,留下厚厚一打毛衣、毛裤,老何的,我的。
是在处理完妈妈后事的那天晚上,我对老何说了那句话,“要不,你把我送回姥姥家吧?”
老何最后还是留下了我,却狠狠在我脑袋上打了一巴掌,“你小子,没准儿命太硬。”
我心一凛,这几个字,小时候听舅妈说过。也为此,舅妈一再让妈妈把我带走。
“不过我不怕。”老何似是自嘲地说一句,“我的命也好不到哪里去。”
唯一收留我的人
我就这样留下来,在妈妈离开后,留在了老何家里。但我心里却并不踏实,常常做梦梦见那晚的情形,也做梦被老何赶走,无家可归。
我开始学着讨好老何,主动给老何递烟、拿拖鞋,还打扫卫生,给老何刷鞋,并在那个假期学会了做简单的饭菜:鸡蛋面条,煎荷包蛋、鸡蛋炒番茄——有时咸了有时又忘记放盐,但老何不计较,还会赞一句“不错”。
始终没有太多交流,因为见面的时候并不多,老何早出晚归,开白班车时,也只是回来吃晚饭,会喝两杯。有一次他想起来,倒了一杯推到我跟前,我犹豫一下,端起来喝一大口,呛得咳嗽起来。老何喝高度的衡水老白干,格外辛辣。
老何呵呵地笑,以后,没再让我喝过。
隔月,老何开夜班车,白天我去上学,老何在家里睡觉,下午我回来,老何已经走了,桌上也会有做好的饭菜,鸡蛋面条或者番茄炒鸡蛋。
有什么可挑剔的呢?我已经觉得万幸,明明成为了孤儿却没有流落街头。为此常常在心里感谢老何,在这个世上,老何不是我的谁,和我一丝血缘关系也没有,却是唯一收留我的人。
我想,以后我会回报的,等我长大了,好好赚钱,加倍偿还老何。
而有能力回报前,我开始约束自己,裤子短了不吭声,把腰部用力往下拉;回家后换上拖鞋,把有洞的球鞋藏起来……
那天晚上,老何还是察觉了,骂我是哑巴,然后去卧室拿出一张存折,“你妈去世的时候给你留了一笔钱。小子,不是我白养活你,你花的是你妈的钱,不用过意不去。”
我愕然,却将信将疑,妈妈会有多少钱?她生前从来没有说过。
老何索性带着我去查,存折果然是妈妈的名字,钱也的确不算少。我才信了,哭了一场,暗暗发誓绝不辜负妈妈。
以后,我照常节俭,但心理上舒缓好多,也不觉得欠老何那么厉害了。感激还是有的,毕竟是住在老何家里。还有,老何对我也的确不坏。
老何的家倒像个收容站
这样过了6年,我考上大学的时候,老何对我说,他又找了一个女人。
我愣了片刻醒悟过来,点点头说:“行啊——”还能说什么呢?现在,我可以离开这个家了,老何也可以自由选择他的生活,我们本就是没有关系的。他本来就是不是我的谁。
“你不看看就说行?”老何问。
我抬头看老何一眼,忽然发现这6年,老何明显有些老了,真的成了老何,依然清瘦,鬓角却全白了,额头也有了清晰皱纹。可是老何,也不过44岁而已。
“你看行就行。”我笑笑,心里还是难受了一下,这些年,我和老何交流始终不多,好像达成了一种默契,倒是彼此也习惯了。但到底,在一起也6年了。姥姥也已去世,除了他,我的生活里没有别人。不过这次老何很坚持,“你快走了,还是见见吧。”
于是那天晚上,我见到老何的女友,一个同样四十多岁的女人,相貌平平、衣着简朴,虽是城里人的气质,但显然生活境况一般。
我主动跟女人打招呼,女人笑,回头看老何一眼,“你儿子挺帅啊,比你好看。”
“那是。”老何拍拍我肩膀,“青出于蓝嘛,也比老子有出息,名牌大学呢。”
此时的我,已经高出老何小半头,也度过了青春期的青涩,确实是英俊帅气,只是我意外,显然,老何没有对女人说实话,没有告诉女人,我们真正的关系。
我看着老何,也终究没有说出实情。
那顿饭,因为多了女人的絮叨,热闹许多,女人对老何和我都很满意,两个男人的家,清洁有序。也满意我的礼貌、少语,兴许是见面之前,担心我会反对令她难堪。
老何还是叫我小子,这样的称呼,在女人看来自然是父亲对儿子的昵称,再正常不过。
送走女人,我对老何说:“我看还行。”
老何看我片刻,点头,“你说行,就行了。”
这样,我离开,去省城读大学,女人搬到了老何那里。我想,老何的家倒像个收容站,一拨一拨,收容不同的、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而这一站,我算是过去了。
真的可以两清吗
大学4年,我只在寒假时回去,还是女人打电话催回去的,电话里也喊我小子,说:“你这小子够狠心,暑假也不回来看你老爸。”
我支吾:“打工嘛。”
我没有撒谎,我算得出来妈妈留下那张卡上的钱,并不够自己4年的大学花费,我不想花老何的,所以自己赚一些。
回去,女人照旧把我当老何的儿子,为讨好老何,拉着我买东买西,做一堆好吃的。
老何笑说:“倒是沾儿子的光了。”
我也就随着老何把这个谎撒下去,反正只是偶尔回去,没有拆穿的必要。
4年转眼过去,我毕业留在省城,最初的工作不是很理想,但我不怕吃苦,愿意从头做起。旁人不知,人生的苦,我自小都吃遍了。
耐得住性子,前程反倒是越来越好。我并不给老何寄钱,但会买一些东西快递回去,衣服、香烟、手表……已经知道老何的喜好甚至衣服的尺码。
电话里,女人跟我唠叨:“老何真是养了个好儿子,争气,还孝顺。”
我只笑不语,觉得自己是在偿还这些年老何的付出,还一些,心里就轻松一些。
是打算付首付买房子的时候,女人给我打了电话,说老何疲劳驾驶,不小心开车撞了人,要赔人家两万块钱。女人说:“你看能不能先借我们一点儿?”
我知道,电话是女人背着老何打的,只是我不太明白,两万块而已,老何开了这么多年出租,不会这点积蓄都没有啊。
“现在不好揽活,份子钱又多。”女人絮叨,“你爸这些年赚的钱,也就只够负担你们爷俩的生活,又供你读了大学,我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现在你爸遇到难处了……”
女人还絮叨什么,我却忽然听不清楚了,眼前只恍惚浮现那张旧存折——这么多年怎么就没细细想过,妈妈哪里会有那么多钱?如果有,早就把我接出来了。那些钱……没错,那些钱是老何的,只是我刻意回避了分析这个问题。老何不善表达,我又生性不主动与人亲近,所以就错过了感受生活背后的温情。总以为只是份恩情,拿物质回报后便可两清。
但真的可以两清吗?那天晚上,我想起和老何一起的光阴,光阴里的点点滴滴,忽然那样想念老何——是对亲人的那种想念,想得心疼。原来他给我的爱,我拿一辈子的物质都还不清,因为真正能够偿还的,只有感情。
我也终于知道了,老何是我的谁。
拨了老何的号码,我说:“爸,我明天回家,等我啊。”
那边,老何只是顿了一下,平静地说了一个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