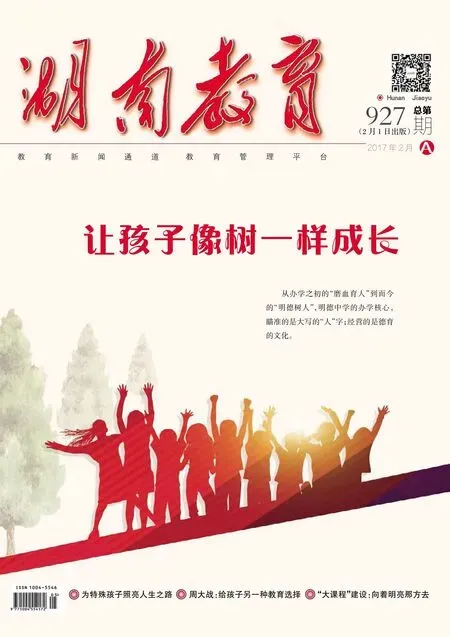约会人性
2017-03-08陈果儿
文︳陈果儿
约会人性
文︳陈果儿
熬夜,一口气读完,破晓的光正丝丝缕缕地缠绕在天幕,尚朦胧的世界如常静谧,可我确信我听到了它稳健的脉搏和蠢蠢欲动的苏醒。合上尾页的瞬间,内心如潮的思绪催促着我走走停停的笔,叫嚣着宣泄纵文的欲望。借着黑暗,我仿佛看到无数的灵魂从屋内飞至天际,壮大着蚕食黑夜的光,而后缓缓消匿于白昼,终不可见。
《不说,就真的来不及了》是纽约大学心理学研究生袁苡程,以二十八个人的临终遗言作为第一手素材,编写而成的文集。字句间缓缓游弋的人性,浮沉在简短的故事中,抬眼笑望着你,待你凝眸,一眼万年。
没有任何一种人生称得上容易,哪怕于外人看来是功成名就、家庭和睦,光鲜靓丽之下也都有着无处言说的遗憾与深深悔恨。匿名来信者在人生尽头选择向一个摆渡人坦诚诉说,倒颇有些似王维的“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
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们在末时记录下的文字,散发着他们各自或大或小的情绪和欲望,“人性味儿”浓重,致使合书许久,我也只是静静地坐着,露水凝结时的寒气无处不在。于压抑中渐渐感到些许悲伤,还有厌倦,继而又萌芽了迷茫,乃至合为浓重的窒息感。然而,不知为何,原本平日十分恍惚的信念,却在某一瞬间突然坚定,挣扎了许久,终于还是决定为此不眠夜难忘的约会留下点什么。
|掠夺是最长情的痛苦|
从原始社会过渡而来的文明,始终烙印着野蛮掠夺的历史,所有的生物在达成自身需求时,往往采取的第一手段便是掠夺获取,直至今日,其本能依旧深藏在社会的一些角落,潜伏着,等待机会出来,肆意妄为。无论是人掠夺他人、还是社会掠夺个体,都是酝酿巨大痛苦的直接来源,而这些,又都会在战争中被撕去伪装,真实得鲜血淋漓。
人掠夺他人的本能,不若将之理解为人体内潜伏的兽性,一旦解放且无法控制,罪恶的累积便生成了痛苦。《前日本侵华士兵的忏悔》主人公大岛中典说:“多数人都知道吸食毒品会上瘾,而只有上过战场的人才会知道,杀人也会上瘾。那才是最残忍的瘾,它能让你产生一种屠戮的快感和掠夺他人生杀大权的自豪感,当杀戮不但被允许且成为必须做的事之时,你就可以由于杀人而感到自己存在的伟大和自豪,我们都成了杀人狂。”他不可能不参与制造罪恶——他们原本就是去那里制造罪恶的。
他归国后妻离子散,所余的仅是陪伴了他六十年的梦魇和无尽的忏悔。那些他曾经夺走的一切,最终夺走了他的一切。人性复杂而脆弱,战争解放的兽性就像无法治愈的病,一旦开始就将无休无止,那因为战争而狂热起来的毁灭别人和毁灭自己的冲动,强烈得仿佛变成了一种不可理喻的饥渴。
社会掠夺个体的内在规律,则更趋向于为了标榜所谓文明而产生的牺牲。用牺牲者的尸骨堆砌而来的繁华,实则是一个深渊,名曰悲怆。如《越战老兵的最后狂言》中,因参加那场广受质疑的越南战争而丢了双腿,归国后又不幸沾染了艾滋病的老兵所说:“从越南回来后,我过了20多年做梦也没梦见过的耻辱到家的生活,可这是我的错吗?当年那些狂热拥护那场战争的人,现在却纷纷指责说那是一场罪恶的战争。当年发动越战的美国总统和后来的政客们也都不必为我们的命运承担任何责任。我不文明吗?什么是文明?战争文明吗?以他人的痛苦和生命换回的不可能是任何正义的东西!”用上千万人的生命和痛苦所换来的民主理想究竟能被称作文明吗?
|追逐以爱之名永不停歇|
如亚当·斯密所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是为了什么?所有这些贪婪和欲望,所有这些对财富、权力和名声的追求,其目的到底何在呢?归根结底,是为了得到他人的爱和认同。”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追逐着爱,且奋不顾身,又犹如童话故事《睡美人》,我读起来总有着别样的悲哀——尘封一生等一个也许等不到的人,合欢孤独却为一个轻而易举的吻绽放——可是爱情,甘之如饴。
如《死刑执行官的心声》所提及:“无论代价是什么,因为没有被爱过的生命是不可能珍惜自己的,他们的暴力犯罪行为正是他们生活里极度缺乏爱的铁证,而当他必须独自为此付出代价时,法律却毫不留情地惩罚了他,让他用一命偿一命这种最古老的方式去表现所谓的法律公正。我们与斯蒂芬并没有绝对的区别,对237个人执行死刑后,我深知他们犯下死罪的简单原因——对得不到爱而生恨的极端、变形的表达形式。”爱是一种太过强大的力量,能转眼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亦能顷刻间风也飘飘、雨也潇潇。
零落在字里行间的无奈与决绝,好不叫人心疼。儿时经历的骇人孤独与无从奢望的丝毫关爱,都成了抵着斯蒂芬走上死刑台的匕首。孤独比死亡更可怕,我们没有去犯罪只能说是幸运,而不能算是美德。我们最想要的其实也就是那一点实实在在的爱,无论它来自家庭还是任何人,它就宛如活着的理由,代表一切;没有它,人就会变态,就会疯狂,就会通过想象去寻找一个爱的替身。正如特蕾莎修女曾说:“上帝的存在只说明一件事:这个世界很缺爱。我的一生也许艰苦,但却是真实地追逐爱的一生,这就足够了。”
如消融寒冰的光与热,追逐爱而驱散孤独和罪恶,其实,有爱的人就是神,他们能把别人也变成神。
这大概是爱经久不息的原因之一吧。
|接受自我抛开羁绊挣扎|
生活有点儿像珍珠,出于砂砾,归于砂砾。晶莹光润的只是中间这一段短短的幻象,而我们颠之倒之甘之苦之的,也大多恰是这短短的一段,这岂非残忍?自以为还漫长的人生,不久即将要以敷衍而虚幻的形式离开,攥不住也留不下,每思及此,我的呼吸便不由得沉重,企图逃避。
故前几日读完《百老汇编剧的临终遗言》,心中无不感于其言:“无所事事对我来说再也不意味着浪费时间了,看着窗外的树叶在每一阵微风中的颤动,听着鸟儿的啾啾吟唱,我感到自己真真切切地活在此时此刻。我可以感觉到自己与世界之间最基本的联系,与自然的联系。明白了多数人对生活之理解的无聊和无可救药,更真切地感到了人来自尘土而归于尘土这一简单真理的美丽。”
赤裸而来,终将赤裸而去,与其要在这简短的幻象中抓住什么,亦或是因抓不住而去逃避什么,不若接受“无所事事”也是自我的一种真实存在。人类看似强大,其实软弱,也很无助,总是喜欢在最不了解自己的时候,急于征服那个远不如他内心世界来得更重要的外部世界。
即便纷纷落尽,繁华消亡,也不能被生活和压力磨平了棱角,接受和包容最真实的自己,无需理会琐碎与羁绊,则能无悔。
人性总爱躲闪于掠夺、追逐和接受之中,不肯轻易露面,但无论是掠夺所堆积的苦痛,还是追逐的爱与被爱,抑或是接受自我与万物的勇气与真诚,只要存在,就值得被宽容与善待。
我想写一封情书给人性,用颤抖的笔尖诉说爱意:
爱,就像风行八千里,不问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