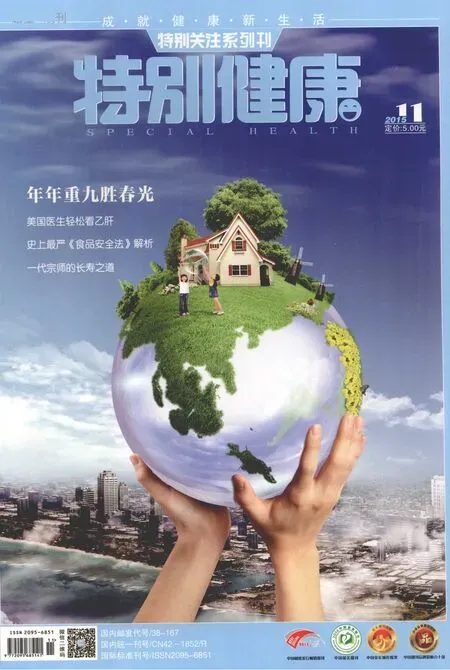隔着四十年的月光往回看
2017-03-07余云
◎余云

我曾是被裹卷在中国两波历史大潮里的水滴:一波是上山下乡,2300万青年从城市到乡村大迁徙;一波是1977、1978年两次高考,1180万青年奔向考场,与分别只有5%和7%的录取率拼死一搏。半年里两次高考我都参加了。在被打入属于95%的失败大军后,我又咸鱼翻身,成了下一年7%的幸运儿之一。
1977年的高考是中国高考史上唯一的冬季考试。12月10日,570万人踏进考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下乡知青。
我的考场在皖南一个农村小学。那一日风雪交加,裹着棉大衣在敞篷卡车上哆嗦了一小时后,我和一批农场考生坐进四面漏风的教室。桌面坑坑洼洼,钢笔在纸上一戳一个窟窿都不算什么,我发现自己的双手已被冻僵,手指整整半小时无法伸开。挤在同一张小课桌的男生同情地看看我,就开始自顾自地奋笔疾书。
结果可想而知。
其实老天爷不开这玩笑,我多半也考不上。大学之前我只上过五年小学,“复课闹革命”后中学四年,念的主课叫工基农基(工业、农业基础知识),然后就是到工厂和近郊去劳动。就这个底子,怎么考大学?
1978年的夏天到来之前,我意外地收到一封上海来信,信封里只有一张上海戏剧学院招生简章。信封上的笔迹出自一个中学女同学的姐夫,他是“文革”前的上戏研究生。我们在同学家认识,他知道十几岁的我看过从被查封的图书馆流出的不少小说。后来他说,见到招生简章时想起我,就随手写了个信封丢进邮筒。
命运之神“随手”降临了首个贵人!
我和一个女友(后来成了陈凯歌、田壮壮的北影同窗)忐忑地站在党委书记面前,说艺术院校招生了,我们要到上海去考试。胖胖的书记是上海下放干部,微皱起眉头:“我们没有收到文件啊?”我拿出招生简章,说:“您看,艺术院校提前单独招生,上海报纸都登了!”刹那间书记眼里闪过什么,是想起了远在黑龙江的女儿?他挥了挥手:“好啦,去吧去吧!”
我们像拿到大赦令,赶紧搭农场卡车回到上海。一连串的报名和考试细节记不太清晰了,只记得除了考政治、语文、文艺常识,以及专业课的初试、复试,就是不断地写文章:命题作文,看图编故事,看电影当场写评论……最后一关是面试。
主考官——后来我的编剧课导师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你是非要上戏剧学院呢,还是什么大学都可以?”我的回答是后者。虽然这极不讨巧,但这是我的心里话,任何一所大学要我,我都会乐疯的!
上海的酷暑来临之时,第一批录取名单公布了,没有我。
父母急了,辗转打听,了解到我的考试成绩排在蛮前列,校方的疑虑是:体检单上我身高165公分,体重仅44公斤。恰巧——为什么这么巧呢,农场党委副书记到上海开会,我妈赶到招待所,请他到学院为我陈情。
后来我一直在想象,高瘦,有一种不怒自威军人气度的副书记,是怎样坐着吉普车进了校园引来诧异眼光,又如何用带着安徽口音的沙哑嗓子说:我来了解一下农场考生的情况,如果没希望录取,我们要动员她回去工作(那时我已在上海待了两个多月)。当校方老师指着那个画上红圈的“44公斤”,表示担心我体质太弱难以适应学业压力时,他沉稳地说了那句关键性的,一锤定音的话:“她身体没有问题,她可以在农场劳动,怎么就不能念你们的书呢?”
你不相信有这么好的党委副书记?
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专业那年从近两千名考生中录取了21人,每个能走进那座红楼的同学都心存侥幸。隔着40年的月光往回看,那条幸运之链环环紧扣,环环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