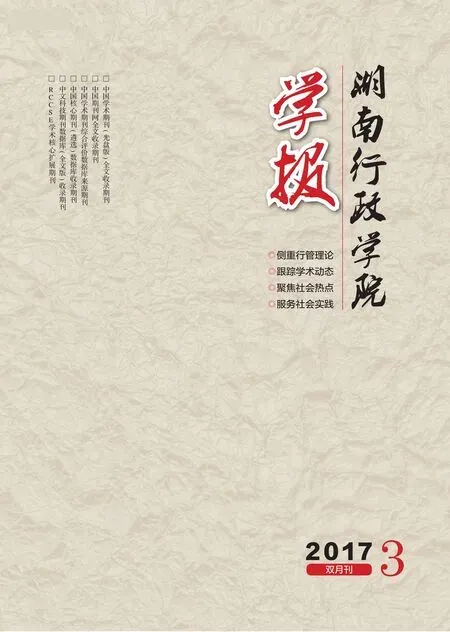问题意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导读课程的启示
2017-03-07王向清李伏清
王向清,李伏清
(湘潭大学,湖南 湘潭 411105)
问题意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导读课程的启示
王向清1,李伏清2
(湘潭大学,湖南 湘潭 411105)
“问题意识”是主体对物质世界万事万物呈现的“问题”所展开的主观反映,是课程教学必须关注的焦点。“问题意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导读课程的教学有三个方面的启示:打破传统教学模式,倡导问题解决式教学;防止犯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的错误;导读课程应聚焦问题的范围。
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导读课程;传统教学模式;教条主义
近年来,学术界日益强调学术研究中“问题意识”的重要性。“问题意识”是主体对物质世界万事万物呈现的“问题”所展开的主观反映,既包括对“问题”所进行的探究和认知及其结果,又包括思维活动中对那些难以解决的、疑惑的实际问题或理论问题所产生的怀疑、困惑、焦虑、探究的心理状态,还包括对这些问题的执着探索所表现的精神状态。无论是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还是博士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育方面,也无不强调“问题意识”。笔者认为,“问题意识”对哲学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导读课程的授课有以下三方面的启示:
一、打破传统教学模式,倡导问题解决式教学
目前课堂教学中大多数教师仍采取一言堂、满堂灌的填鸭式教学模式,学生只作笔记,不会思考,也不愿思考,提不出新颖别致、标新立异的问题。因此,传统的教学模式导致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不敢提问、不知道如何提问、没有机会提问的普遍现象。
然而在今天,是否具有创新能力己成为一个民族是否具有竞争力的关键,而提问能力一定程度上说就是创新能力的前提和基础。传统的填鸭式课程模式就提出问题的方式而言,向学生提供的只是一种可能答案或一种解决途径,其结果是限制了学生的思路,桎梏了学生的创新精神。
问题提出、解决式教学是创造性思维教学的重要方法和途径,它以问题提出、解决的方式组织教学过程。在课堂中,教师作为主体,应当为学生创设开放性的问题情境,激励学生独立探索,自主钻研,提出高质量的问题,启发和培养学生多向思维的意识和习惯,使学生主动寻求解答问题的方法,认识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是无穷无尽的,以此培养学生思维的多维性和灵活性。
问题解决式的创造性教学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敢于发问、敢于想象、自主思维、辩证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发扬寻根究底的探索精神。在哲学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的教学中,这种问题解决式的创造性教学方式要求教师经常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设计不同的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在问题设计、解决式的创造性教学中,教师和学生都是主动学习者,都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导读这一课程而言,在关注问题意识的课堂下,应具有多样化的交互式主体间性:一是教师和学生之间,一是读者(既有教师也有学生)与文本之间乃至读者与文本及其作者之间。就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主体间性而言,聚焦问题意识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成为教学过程中的积极主体,是一种交互性的合作伙伴关系。一方面,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人格,重视学生各自具体的个性化的兴趣爱好,调动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遵循学生依各自具体的经验所形成的具体化的认识规律和个性化的认识水平来安排教学程序,按学生的个性差异因材施教,课前、课中、课后引导学生进行思考。要摈弃传统一言堂、满堂灌的填鸭式教学模式。在这种传统教学模式中,课堂教学权威化,教师完全以权威者的身份面对学生,教师教,学生被教;教师讲,学生听;教师选择学习内容,学生适应内容;教师是学习过程的主体,而学生只是客体。教师唯教材、唯教案至上,而学生作为客体,将教材、教师讲授的内容视为“圣经”,当作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极少怀疑知识的正确性和教师的权威性,缺乏批判性地独立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教师眼中的学习佼佼者,往往并不意味着综合素质高、综合能力强,以致并没有真正成为栋梁之材的原因之一。问题意识要求师生平等、教学民主、营造愉快和谐的教学氛围。另一方面,学生也应尊重教师,包括对教师的喜好、科研兴趣、交往关系、心理认可等方面持平等宽容的态度,通过主动的探索包容教师学术科研的不足。
二、防止犯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的错误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导读课程自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解读和诠释。在文本和读者的对话式展开过程中,问题或提问是诠释学情境之间得以贯通的中介或桥梁,是文本的创新意义得以形成的重要通道。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问题”的创设具有重大的意义。就其开放性而言,教师既要做到问题的提出者对文本和他者的开放态度,又要保证被提问内容的开放性。前者在于强调对传统、外来文化尤其是异质文化、一切他者乃至包括提问者本人以往观点的认真倾听、反思,而非盲目地狂妄自大,妄自菲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导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立足问题意识的本义,教师要注意防止犯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的错误,向时代性、应用性尤其是当代提问的应用性等方面发力。
基于诠释学的理解,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导读课程,如果教师一味致力于追寻“作者原意”或文本的语义学含义,那么在自己的研究中往往会停留于文本、留心于思考文本的作者提出了什么观点、怎样论证等问题上。对于研读原著来说,把握这类问题很有必要,但满足于此远远不够。长此以往,容易形成一种习惯性思维,从而停留于对文本文义问题的简单思考,而忽视从应用性角度来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这样就难免养成思维的惰性,难以凸显“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特性,看不到文本精神的当代性和未来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文本的真正理解必须立足于当下中国社会的具体现实,将两者密切联系。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导读的课程置于我国目前面临的具体历史情境之中来建构“问题”,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更有活力,才能用来真正解决实际的时代问题。
哲学诠释学视角下的问题意识,倡导理解过程中读者与作者、文本的双向度开放。真正的问题,不仅能够使读者与文本开放,而且它还能够使文本与读者开放,这样既能够使读者在文本的回应中吸取有益的东西,又能使文本在不同的诠释学情境中赋予不同的意义。哲学诠释学的提问,是担负着在文本的一般含义和读者特殊的诠释学情境之间架设桥梁与通道重任的问题,而不是漫无边际式的问题和不经意的问题。中国传统哲学的“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的诠释范式之所以让人困惑,原因之一就是提问呈单向度开放的特点,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被简化成读者或文本的单方面的宣告。这一情景下的问题模式也变成了单方面的提问或答复,而不是互为问答的模式。借用伽达默尔的说法,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伙伴之间平等地展开的商讨式的对话,问题呈现的是一种“伙伴”性的交互关系。在他看来:“流传物是一个真正的交往伙伴,我们与它的伙伴关系,正如‘我’和‘你’的伙伴关系。”[1]因此,我们只有打破传统的二元对立式的单向度开放模式,在文本、读者和作者之间实行伙伴关系式的交互性对话模式,才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导读课程中,实现视阈的真正融合,才能让原著导读课程真正步入现实生活,走入中国当下真正的社会现实之中,才能获得时代性的生机和活力。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课程导读应聚焦问题的范围
为研究生导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教师应聚焦以下问题: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撰写文本的根据,包括理论来源、时代背景等。以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为例。该文发表于1898年,当时恩格斯逝世已经三年,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都在向右转,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老牌修正主义者与新康德主义者互相勾结,疯狂篡改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当时俄国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乘机泛滥,如自由主义民粹派一反以往平民化、大众化的主张,重新抬出“英雄史观”,神化个人,否定群众;经济决定论的经济派则崇拜群众盲目的自发性,否定革命领袖的个人作用。在这些复杂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关于个人历史作用问题就特别尖锐地提了出来。结合新的历史条件深入系统地阐发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历史作用问题的理论就成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义不容辞的战斗任务。在个人的历史作用问题上,普列汉诺夫着重批判了三种错误的观点:英雄史观、无为主义和因素论。一般而言,英雄史观属于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无为主义是庸俗社会学反映的机械论的特点,因素论则是多元论、折衷主义的表现形式。普列汉诺夫批判了民粹派英雄史观的三大错误:一是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片面夸大精神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忽略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二是只看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没有认识到决定历史进程的根本力量是社会生产力,是从事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主体——群众;三是在方法论上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错误地把客观和主观、群众和英雄、必然和自由、必然和偶然绝对对立起来,而没有找到沟通两者之间的桥梁。可见,我们只有弄清楚了文本写作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来源,才能深入理解文本的立场、观点及其思路的展开路径,才能明了文本由此表现出来的理论意义、历史作用和现实价值。
其次是文本的版本源流,包括母语版本的变迁,译文版本的种类、版次等。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例。马克思曾对布鲁诺·鲍威尔发表在《维干德季刊》(1845年第3期)上的《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文中对《神圣家族》的责难做出答复,写了短评《对布鲁诺·鲍威尔的反批评的回复》一文,刊发于《社会明镜》(1846年第2卷第7期,未署名),这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的“前奏”。此后,马克思、恩格斯曾一边创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边为该书将来的正式刊印和出版努力联系出版商。在威斯特伐利亚创办一家出版所用来出版这部两卷本著作的计划宣告失败,这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最终未完成产生了直接影响。其中的部分章节尤其是第二卷的内容在当时以零散的方式发表了一些。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倍倍尔、伯恩施坦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先后接手过有关《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恩格斯和伯恩施坦对手稿做过标记及编码。有些手稿散失,有些手稿在发表后底稿被毁,还有些手稿是20世纪60年代才找到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编辑的《马克思手稿和读书笔记目录》中记载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接触过原始手稿的梅林、伯恩施坦、迈尔和梁赞诺夫等人在整理、编辑方面起过各不相同的作用。1932年,MEGA1第一部分第五卷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出版,这时才全文刊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 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1845—1846)》一文,它在国际国内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出版界被视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个完整的、历史考证性的版本。1962年,文献专家西·班纳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整理资料时,意外地发现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3页手稿,上面有马克思所编的页码1、2、29,这是《费尔巴哈》那一章中的佚失稿,遂将其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几处补充文字》为题发表(《国际社会史评论》1962年第7卷第1分册)。这是目前为止搜集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所有遗稿。值得说明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中的《费尔巴哈》一章出现了七种不同的编排方案:如梁赞诺夫版、阿多拉茨基版、巴加图利亚版、新德文版、广松涉版、英文版等,还有MEGA2编者对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了权威的编辑设想。[2]
再次是文本理论方面的建树,包括主要内容、基本观点、理论创新和精神实质等。我们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为例。其博士论文的基本观点在于:马克思分析并批判了对伊壁鸠鲁哲学的种种歪曲和贬低,纠正了思想史上把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等同起来的传统偏见,详细阐明了他们在自然哲学方面的差别,由此揭示出伊壁鸠鲁原子学说的独特的积极意义。其主要内容分析了两者的自然哲学的一般差异和细节上的差别。其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哲学、自我意识与现实关系的新见解;对自由范畴的新诠释;对宗教问题的新思路。
最后是文本的现实启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原著基本上都是分析问题的一种方法论,是对实践、政治和生活问题的处理。而问题的“观念”是“现实事物”的问题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呈现的是“现有”与“应有”,“实然”和“应然”之间的张力。通过对经典的研读,可以让学生以历史主义的眼光去理解过去的哲学,从中真正理解过去哲学所提出的问题如何以新的形式出现,这正是哲学时代性和民族性的体现。《德意志意识形态》基于“实践的人和人的实践”的立场,揭示出人的社会性原则和历史性原则,认为人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以货币为中介,导致社会失去共同体本质,不能实现“人性”或“人的普遍利益”,沦为“普遍的虚假的共同体”。[3]文中强调国家就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是一种与人的力量异化的力量。该文分析了以往国家理论的虚幻性,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理想主义,并揭示了鲍威尔和施蒂纳国家自由主义的本质,由此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是压抑个性发展的。通过对虚幻共同体的批判,提出了“真实的共同体”的观点以及为只有建立真实的共同体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我们通过对文本中“共同体”的分析,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新特点和新问题,引导学生思索现实问题,如“命运共同体”是否可能,如何可能?“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是否有区别,又有何本质区别,为什么学术界会习惯混淆两者的区别?“命运共同体”中“以人为本”中的“人”究竟是什么?“共享”发展何以可能,何以得当?我们如何看待“共同体”中的民主与“民粹”的问题?“自信”如何可能,如何看待“自信”与“自负”的问题?如何看待“命运共同体”中的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问题,我们的话语体系究竟以什么为土壤的问题?等等。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导读课程与现实问题的联系,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的内在要求。
[1][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465.
[2]聂锦芳.文本的命运(上)——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保存、刊布与版本源流考[J].河北学刊,2007(5):11-17.
[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63.
责任编辑:曹桂芝
G4
A
1009-3605(2017)03-0109-04
2017-02-23
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改研究项目“研究生原著课程教学中的方法创新研究——以问题意识为中心”(项目编号:JG2015B044)。
1.王向清,男,湖南邵阳人,湘潭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校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2.李伏清,女,湖南湘乡人,湘潭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