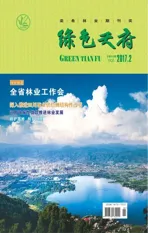看见 看不见
2017-03-07王梓涵王维爽
○文 图 王梓涵 王维爽
看见 看不见
○文 图 王梓涵 王维爽
在森林,聚焦野生动植物沉醉自然的欢愉;在火场,记录战友穿越火线的英勇。这个通过照相机忠实记录生活的人,有着陆战队员的体格、狙击手的眼神以及少女般纤细敏感的心。他就是武警四川省森林总队凉山彝族自治州支队战士程雪力,入伍9年,他经历了从肩扛灭火机到手握照相机、从被记录者到记录者的蜕变。
初见程雪力,他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或许是生养在南方的缘故,这个终日握照相机行进在森林中的汉子,并不像我印象中对常年生活在野外的摄影师的固有刻画——高大威武、皮肤干黑。相反,他瘦而结实,眼神纯净,似乎并没有经历太多风霜的打磨。

2009年,已有102次火场经历的程雪力,浴火重生
但拿起照相机,挺进火场第一线,他的眼神就变得坚强笃定,白皙干净的脸也附着上黑色的草木灰。“我希望把森林部队拍个遍,把森林部队最真实的一面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人了解森林部队。”短短几句话,程雪力将“森林部队”这个词重复了3次。而他的目标也得以实现。迄今为止,他为森林部队拍摄的影像已被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网、《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主流媒体刊发2600多幅,被腾讯新闻《活着》栏目多次进行专题报道。在光与影的交织中,程雪力用镜头记录中国森警的战斗冲锋,铭刻中国军人的使命担当,将发生在森林部队的悲欢离合、大爱小情透过微小的孔隙传递给社会大众,让更多的人看见他们平时看不见的森林部队,走近他们的世界,也走进他们的生活。
程雪力所拍下的森警故事,亦是他的军旅人生。
真我 看得见的森警战士
2007年,19岁的程雪力离开云南建水老家,加入武警四川省森林总队凉山彝族自治州支队。他说,那是得偿所愿的时刻,极为幸福,“小时候,我就常把父亲参军的那顶军帽扣在头上,长大后,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军装”。
当兵第一年,他就遇上了汶川大地震。程雪力第一次以战士的身份,随部队赶赴都江堰抗震救灾。路上,上等兵石蕊落了泪。“刚刚途经的村寨也受了灾,那是我的家乡。我有两年没回家了,每次打电话,父母都说挺好,我知道他们总是报喜不报忧。这次出发前,我还没来得及和家里通电话。”听着石蕊的话,车上的战士都沉默了,程雪力也开始懂得“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的真正含义。
车停了,他们抵达灾区,满是倾塌的房屋、遇难的遗体和惶恐的泪水。来不及悲伤,大家迅速投入战斗,搜救被困群众、搭设临时帐篷、搬运救灾物资。“记得有一户被我们救助的人家,我们要离开时,这家的儿子激动地表示长大后要加入部队,女儿许诺以后要嫁给军人。”回忆起那段苦难又温情的岁月,程雪力说,军人的精神是可以被感染、被传递的。

2010年,部队首届军事比武,勇夺团体第一名
同年,程雪力第一次扛着灭火机走上西昌市黄联关森林火场。部队沿火线向东侧推进3公里后,风向突变,大火在7级风的作用下交叉立体燃烧,形成100多米的树冠火。热浪逼人,他和战友紧急撤退至500米外。在指挥中,中队长杨参和指导员张勇军不慎坠入深沟,幸亏沟底是水潭,身体无大碍。森警战士连续奋战几个昼夜扑灭大火,夜里轮换看守火场时,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挡风的休息地,天亮才发现,靠着睡了一夜的地方竟是坟墓。这是程雪力第一次离“牺牲”和“死亡”这么近。
第二年,程雪力被中队选为班长,深知责任重大的他更加勇于承担。一天,部队在24小时内遇到两起林火,他和战友奋战一天一夜,无眠无休。下山途中,头晕眼花的他掉进3米深的草滩,身旁就是悬崖。“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挺悬的。”程雪力心有余悸。“还有一次我正集中精力扑打火头,突然听到战友喊,‘快闪开,滚石下来啦!’我一转身,有一块大石头砸了下来,砸断了旁边的松树,迸溅的碎石砸到了我的大腿。”在火场生死线,生与死的距离,变得愈加短促。火场的危险与战友的情谊相伴相随,成为程雪力记忆中最重要的存在。
我问程雪力,你是怎样一次又一次从火场上挺过来的。他只用了四个字回答我:浴火重生。
忘我 看不见的记录者
浴火,锤炼真我;忘我,才能重生。
担任班长,见证了程雪力作为一名森警战士的成长,同时,也成了他转型为一个记录者的起点。为了更好地宣传部队,他拿起纸笔写文章,并进行一些简单的日常拍摄。“起初,就把这当作工作,并没有太多的感觉,还想着‘天生我才必战斗’。拍照、撰文的行为一直从2010年重复到2012年,我才感觉到,通过镜头把所见所闻定格下来,可以形成寄托,给精神找到一个出口。”从此,程雪力单反不离手,正式走上摄影之路。
2014年4月16日,他拍下了一张特殊的照片。那是在西昌市开元乡森林火场,战友王帅背着20多斤的装备攀爬悬崖,突然脚下打滑,直线掉落。反应迅速的王帅抓住一棵不粗的树枝,其他战友迅速用攀登绳将他拉了上来。程雪力举起相机,将时光定格在这一刻。“太多战友曾与死神擦肩而过。”他有了一个大想法。
“今年,我把西南的最南边和东北的最北边跑了一圈,已经拍了10个专题几万张照片。”程雪力背着1个单反相机、2只镜头、1台笔记本电脑,遍访云南省建水,四川省凉山、成都、阿坝,黑龙江省大兴安岭等地,“印象最深的就是在阿坝记录的武警卧龙森林中队官兵的故事。”
5月1日,全国人民都沉浸在劳动节小长假的惬意中,程雪力却随卧龙中队巡逻队走进四姑娘山。当晚,他就架起照相机,将镜头聚焦在美丽夜空中、宁静雪山下那几顶官兵居住的帐篷。阵阵寒风吞噬着他早已战栗不止的身体,程雪力却沉醉在光影的世界里,寻找最佳构图,大有“风雪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之势。

坚持灭火一线采访,将镜头对准英雄的战士

扑救森林火灾
但很快,他就有了高原反应。程雪力所在的凉山支队海拔1000余米,而卧龙四姑娘山、巴郎山一带,海拔高达5000多米。“每次蹲下去拍照,一起身就头晕。”但即使身体不适,他也没有降低自己对记录森林部队的标准。第二天,为了拍到在雪山脊上行走的官兵,程雪力又在山下守候了两个多小时。为了追赶上战士,不错过他们巡护的点滴,他背上摄影器材,走直线、攀陡坡,与官兵会合。
“我的坚持是对的,不上来绝对会遗憾。战士们像雄鹰一样,在高处搜索目标,在山顶观察野生中药材,这种照片在别的地方可拍不到。”程雪力显得十分兴奋,脸上看不出一点疲倦。实际上,高原反应强烈的他已经举步维艰。
但这还不是全部。他们还要翻过巴郎山,返回中队。巴郎山的积雪已经深得没过膝盖,程雪力将借来的大了半码的胶鞋的鞋带拴了好几圈,却还总是被雪窝夺去。每次刨鞋,都把手冻得生疼。刚想整顿休息,一阵寒风席卷着雪花“砸”来。大家只能加快速度,但还是免不了摔跤。战士们用装着帐篷、睡袋、给养等物资的背囊当作垫背,程雪力却只能心甘情愿地做手中摄影器材的垫背。
“尽管如此,一天下来,机器全身还是像水洗了一样。脚下巴郎山的深雪把我的腿冻成了‘白萝卜’,头顶火辣辣的太阳把我的脸烤成高原红。脖子红白相间的,还脱了皮。”程雪力“抱怨”了几句,手却骄傲地指了指单反相机,“但是没白来,得了不少好照片。”
或许,对于程雪力来说,在他按下快门的瞬间,就是扣动扳机的战士,必须无惧生死,第一时间抵近战场前沿,才能留下最真实的历史瞬间。
实现了当兵的梦想,程雪力记录军人的生活。背上相机,他不知道自己在记录森林部队的路上能走多远,但既然已经开始了,就不会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