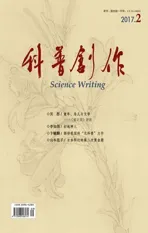童年、鸟儿与文学
——《雀之灵》评论
2017-03-07
《雀之灵——青春望天树》(以下简称《雀之灵》)一书描绘了作者韩开春于儿时在乡土间感受到的雀之精灵的故事。本书封面上印着这样一句话:在童年的天空中自由飞翔,树影斑驳的儿时村庄,闪现出记忆中的小小身影。
《雀之灵》是中国原创儿童生态文学精品书系之一,并且是获得全国孙犁散文奖一等奖的作品。然而,笔者在最初阅读这本书时,并未关注这些信息,而是直接被书的内容引入其中。
笔者喜欢鸟且近年来经常拍摄鸟,拿到此书,首先被作者讲述的几种鸟吸引。作者从身边最常见的麻雀讲起,进而讲述了麻雀、燕子、伯劳、喜鹊、灰喜鹊、乌鸦、松鸦、乌鸫、鹊鸲、八哥、鹩哥、画眉、灰椋鸟、云雀、黄鹂、黄雀、绣眼、柴呱子(苇莺)、白头翁(白头鹎)、布谷(杜鹃)、鹁鸪(斑鸠)、鸽子、戴胜、小翠(翠鸟)、水老鸦(鸬鹚)和野鸭的故事。
笔者不想干巴巴地板起面孔去评论这本书,而是想顺着作者的笔触,跟随作者一起去感悟那些精灵。
基于作者儿时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所以他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村庄中除了常见的家养的禽畜,到处乱钻的虫儿,还有到处放声歌唱的鸟儿。
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城市,麻雀都是人们常见的鸟。麻雀曾一度被列入“四害”名单,被“平反”以后,麻雀害怕人的程度降低了许多。作者在书中介绍说,麻雀是一种不记仇的鸟类,农村的麻雀可能是这样的,然而在城市里的麻雀却不像它的农村亲戚那么没有记性,好像多少还保持着一点点对人类的惧怕。

图1 《雀之灵——青春望天树》(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2016年)
笔者倒希望如此,对人类的警惕,应该是所有动物最应该保持的记忆。不过这一观点,对于喜爱鸟类、喜欢拍鸟的群体来说可不是一个有利的因素,因为这样会让人类很难近距离地接触鸟类。
《小燕子》这首儿歌至今仍广为传唱,最近笔者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了解到燕子在古时被称为“玄鸟”,《梦溪笔谈》(卷三辩证一,第55条)说,“玄乃赤黑色,燕羽是也,故谓之玄鸟”。为此,笔者也去拍摄了一些燕子的照片,通过照片发现,燕子的羽毛黑中透蓝,在阳光的照射下,又会泛起紫红色的光,真是美轮美奂。
在《雀之灵》一书中也有关于燕子的描述,作者不仅写出了燕子的身形与飞翔状态,而且讲述了燕子与人类的关系、燕子的迁徙与回归,认定燕子是有情有义的鸟儿,感叹在外漂泊流浪的人如何能够像燕子一样,每年都回归故里。
然后,作者以“劳燕分飞”这一成语,自然过渡到对于伯劳的描述。作者在描述中,介绍了伯劳杀死其他小鸟如麻雀幼鸟时的残酷。在平常人眼中,伯劳是一种很漂亮的小鸟,其身形大约是麻雀的一个半大小,不如鹰隼那么大。伯劳是很传奇的鸟儿,作者也介绍了那个中国古代的凄婉传奇,让我们知晓了更多关于伯劳的故事。可能是因为作者在小时候亲眼看到了伯劳捕杀麻雀幼鸟的一幕,从而对伯劳产生了厌恶之情。
喜鹊、灰喜鹊和乌鸦都是雀形目鸦科的鸟,长相其实也差不多,不过乌鸦浑身黑色,喜鹊黑白两色,而灰喜鹊是灰黑两色。可是人们对于喜鹊和灰喜鹊基本上是喜多于厌,而对于乌鸦基本上是反过来了。笔者认为可能与乌鸦的叫声以及它浑身黑色的长相有关。
然而,《雀之灵》一书的作者从文学角度收集到很多的历史证据,介绍北方人其实喜鸦不喜鹊,并指出乌鸦在清朝被供为神鸟。乌鸦是非常聪明的鸟,它们也有记忆。在清代紫禁城,乌鸦每晨出城求食,薄暮始返,结阵如云,不下千万;而在今日,在北京的铁狮子坟、小西天附近,也还是当年景象。
如作者所讲述的,人们常常把乌鸫认为是小乌鸦,把鹊鸲认作是小喜鹊。这两种鸟在南方很常见,而在今日的北京,乌鸫常见,而鹊鸲并不常见。乌鸫有一个特点,其叫声多变且会模仿很多种鸟儿,叫声婉转,弥补了它像乌鸦的不足;而鹊鸲,长得小巧玲珑,经常停在一处,翘起尾巴,样子很可爱。笔者在海南等南方一些地方多次拍摄到鹊鸲。
因为作者出身文科,这本书的特点之一是其总是能够把鸟与文学典故联系在一起,或与身边文人墨客以及乡土文学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如杜鹃与“子规滴血”,伯劳、燕子与“劳燕分飞”,这或许可以让蒙童在不知不觉中了解那些文学中的故事以及感受到故事背后的文学和语言表达出的美。
本书中的《戴胜》与《小翠》是笔者认为特别精彩的两篇。
《戴胜》开篇引用了唐代诗人贾岛的《题戴胜》中的诗句:“星点花冠道士衣,紫阳宫女化身飞。能传上界春消息,若到蓬山莫放归。”文章点出了戴胜形貌的特点以及出没的时间,并且有其文化内涵,特别是作者对于戴胜这种鸟的头顶的描写,“我惊奇的是……居然长着一个凤冠状的五彩羽冠,很醒目,打开来如一把小巧的折扇,也如斯巴达战士的头盔”,描述准确、有想象力而且颇有文采。

(姚大海 绘图)
《小翠》一篇中对于翠鸟描写得非常精彩的一处,是关于翠鸟入水的描写,表达特别准确。作者引用唐代诗人钱起的诗《衔鱼翠鸟》:“有意莲叶间,瞥然下高树。擘波得潜鱼,一点翠光去。”作者描写翠鸟入水捕鱼的过程快若电光石火,稍纵即逝,当真是静如处子,动若脱兔。
当然,笔者钟情于这两篇,除了感受到作者对乡土的生活、文人的典籍的熟悉外,还有评论者对于这两种鸟的喜爱,在拍摄这两类鸟时,拍摄者的真实感受也被本书作者描绘得惟妙惟肖。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作者通过本土生活,能够给出当地对鸟儿的“土名”,千万别小看了这些土名,它反映了本土住民与这些鸟的关系。比如,云雀在当地被叫做“的溜坠”(或“的溜追”),其中“的溜”像是云雀的鸣叫声,而一个“坠(或追)”,则是对云雀一飞冲天的英姿的反映。再比如,他们把苇莺称为“柴呱子”,是因为在他们那里,把芦苇称为芦柴,加上苇莺的叫声就是“呱呱叽、呱呱叽”,便组合了这样一个有趣的名字;再如,作者的老家把杜鹃(布谷鸟)称为“刮锅”,是把节约粮食意蕴其中;对于戴胜的名字,作者的母亲给出的本土名字是“臭咕咕”,反映了戴胜用鸟粪垫窝的习性。此外,关于杜鹃用自己的蛋掉包苇莺的蛋的事情,笔者是从书中第一次得知,难怪有苇莺叫声的地方总是伴随着时长时短的布谷鸟的叫声。这恰是以地方性知识中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来看待鸟类的反映。
《雀之灵》一书的作者也会在文中透露出对于人类破坏自然和其他生灵的不满与悲叹。
比如作者哀叹,小时候可以听见黄鹂婉转动人的歌声,看到它们金黄色美丽的身影,而如今,只能在笔尖处怀念它们金色的羽毛和动听的歌声了。
再如,书中描写了人类张网捕捉黄雀,一是为了养为宠鸟(其实是捕捉后驯养卖钱),二是将其沦为算命先生骗人的助手。对此作者感叹,人类的恶习成就了鸟的另类命运,而鸟的命运就是人类的命运,当人们残害鸟类时,是否想到这一点呢。笔者看到书中描写白头翁成为人们桌上的菜肴——将白头鹎做成的炸鸟叫做“白头偕老”——真是觉得可气。
记得在《寂静的春天》里,蕾切尔·卡逊曾经描写了在地球另一端,农药等化学药品对于鸟儿的伤害以及对于地球生命的危害。而我们这一端,曾经扫除“四害”,甚至烹饪等日常生活都会损及鸟类,真心希望这些伤害能够减少或不再。当然,如果更深一步,笔者还希望我们不止有对于鸟儿的记忆与描写,更希望天空中飞翔更多不同的鸟儿,早晨醒来耳边还能够常常听到鸟儿的婉转鸣叫。
如果童年的成长能够伴随各种鸟之精灵的歌唱,那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啊?如今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很难有这样的经历,作者把他的童年历程与雀之精灵关联起来,并且用散文的形式表达与呈现出来,对于现在的孩子确实弥足珍贵。在这里,文学是笔、是纸,而对于雀之精灵的儿时多彩记忆,才是那书写的颜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