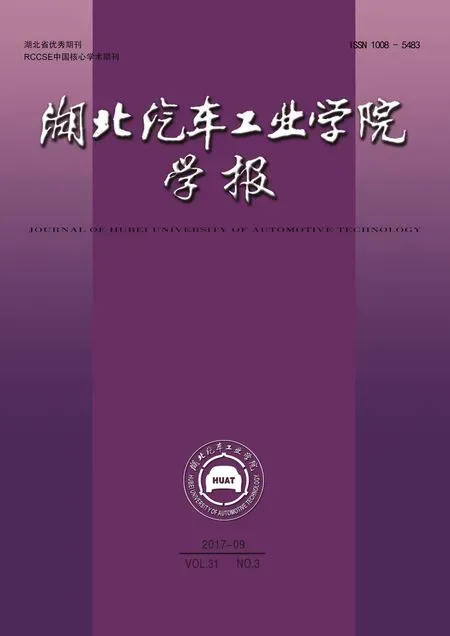视听录制品中表演者权利转让问题研究
2017-03-01张书林
张书林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十堰 442002)
视听录制品中表演者权利转让问题研究
张书林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十堰 442002)
介绍了《北京条约》规定的表演者权利转让模式,结合《北京条约》权利转让条款产生的背景和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及司法实践,对著作权法修订草案(第三稿)的相关修订进行评析,并提出完善转让条款的建议。
《北京条约》;视听表演;权利转让;著作权法修订草案
Abstract:The transfer modes of performer’s rights stipulated by the Beijing Treaty were presented,to⁃gether with the emergence backgrounds of the relevant clause in Beijing Treaty,the stipulations and ju⁃ridical practice of China’s Copyright Law.On this basis,the related modification of the third amend⁃ment draft of China’s Copyright Law was evaluated and some suggestions on perfecting of the transfer clause were proposed.
Key words:Beijing Treaty;audiovisual performance;transfer of rights;amendment draft of China,s Copyright Law
1 概念界定和问题的提出
视听录制品是与录音制品相对应的概念,是从固定表演的媒介上所做的区分。同为乐队的表演,如果用录音设备录下来,形成的是录音制品;如果用摄像机录下来,则为视听录制品。在我国著作权法下,录音制品是作为邻接权进行保护,而视听录制品中的影视作品是著作权的客体,录像制品与录音制品一样是邻接权的客体。与视听录制品和录音制品的概念相对应,载入其中的表演也可分为视听表演和录音表演。其中,对录音表演的保护已经为《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的国际公约》(简称《罗马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简称TRIPS协定)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与录音制品条约》(简称WPPT)所覆盖,但视听表演长期处于无国际公约保护的局面。2012年6月,《视听表演北京条约》在北京“保护音像表演外交会议”上获得通过,从而结束了视听表演无国际条约保护的历史。
《北京条约》赋予视听表演者广泛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精神权利包括署名权和表演形象不受歪曲权,经济权利包括对尚未录制表演的经济权利和已经录制表演的经济权利,前者包括对现场表演的广播权和向公众传播权、录制权,后者包括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提供权(我国称之为“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广播和向公众传播权,第二类经济权利又称“二次使用权”,《北京条约》为后一类经济权利规定了转让条款。此处转让不同于一般民事权利的合意转让,带有自动转让或准强制的性质,即法律规定的转让,或当事人没有相反约定即发生转让的法律效果。本文中将结合《北京条约》签订的背景和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及司法实践,对著作权法修订草案(第三稿)的相关修订进行评析,并提出完善建议。
2 《北京条约》表演者权利转让模式
在视听录制品中同时存在著作权人、表演者和视听录制品制作者三方的权利,如果作品的使用都要经过每一方的许可,势必会降低作品使用和传播的效率,而将表演者的部分经济权利转由制作者行使,将会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在《北京条约》的谈判过程中,表演者权利转让是争议最为激烈的问题。由于美国版权法中没有邻接权或相关权的概念,除对现场音乐表演提供有限保护外,并不保护其他类型的表演。在《北京条约》赋予视听表演者广泛经济权利的情况下,不仅会对美国发达的影视产业造成严重冲击,而且美国也将被迫对其版权法进行大幅度修改。为保护国内发达的影视产业利益及维护其《著作权法》体系不受条约的冲击,美国坚持在条约中规定“推定权利转让”条款,即除非有相反约定,表演者同意将其表演录制在视听录制品上,应推定条约为其规定的所有经济权利均转让给视听录制品的制作者;缔约方也可以规定这种推定转让是无法被推翻的。而欧盟则坚持表演者向集体管理组织等转让权利的自由不应受到限制。由于美国没有获得太多的支持,不得不逐渐放弃“全部权利转让”和“推定转让不能被推翻”的谈判立场,最终形成的转让条款则是各方妥协的产物。
为了协调各方的立场,使条约能够顺利缔结并被普遍接受,条约在表演者权利的转让问题上并没有做出刚性规定,而是规定了3种转让模式,把选择模式的权利交由国内法行使。《北京条约》第12条第3款规定:“缔约方可以在其国内法中规定,表演者一旦同意将其表演录制于视听录制品中,本条约第7~11条规定的进行授权的专有权利应归于视听录制品的制作者所有,或应由其行使,或应向其转让,但表演者与视听录制品制作者之间按国内法的规定订立任何相反合同者除外。”首先,条约规定的转让并非全部表演者权利转让,而仅涉及关于复制、发行、出租权、提供权以及广播和向公众传播权,属于表演的二次使用权。其次,该条款中有“但书”规定,允许表演者和制作者之间有相反约定,并没有完全排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北京条约》为表演者权利转让规定了3种模式:1)表演者权利“归视听录制品制作者所有”,这类似于“法定转让”的模式,使制作者原始取得表演者特定的经济权利,对表演者过于苛刻;2)表演者权利“应由视听录制品制作者行使”,这相当于“推定授权”模式,即所有权仍由表演者享有,但如果没有相反约定,则意味着表演者授权制作者行使其特定的经济权利;3)表演者权利“应向视听录制品制作者转让”,这相当于“推定转让”模式,即如果没有相反约定,表演者的特定经济权利转让为制作者所有。后2种模式在保障视听录制品使用和传播效率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表演者与制作者的利益平衡,是较为理想的转让模式。
3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相关规定及司法实践评析
如同上述概念界定,在我国视听录制品包括电影作品和录像制品,前者是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后者不构成作品,是作为邻接权(或相关权)进行保护,二者的保护水平和适用法律是有差异的。具体到二者中的表演者权利转让问题,应从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和司法实践的深入分析中寻找答案。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38条规定了表演者享有6项权利,没有关于表演者权利转让的直接规定,但从第42条第2款“被许可人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录音录像制品,还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表演者许可”的规定看,录像制品中的表演者权始终由表演者享有,并不存在转让问题,这从“郭德纲诉广东飞乐影视制品公司案”的司法实践得到进一步验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在该案中裁定:郭德纲等作为涉案21段相声的表演者,其享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音像制品,并获得报酬的权利。任何人未经其许可,不得擅自使用其表演复制、发行音像制品。郭德纲等人虽然同意天津电视台使用涉案21段相声录制电视节目并在电视台播出,但并未许可其出版音像制品。因此,天津电视台无权许可飞乐影视制品公司使用郭德纲相声表演的音像制品,飞乐影视制品公司的发行行为侵犯了郭德纲的表演者权。可见,对于录像制品而言,无论是现行立法还是司法实践,都确认了表演者始终享有表演者权的规则,不存在《北京条约》意义上的权利转让问题。
对于影视作品,著作权法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条款涉及表演者权利转让问题。有学者以著作权法第15条关于影视作品著作权归属的规定为依据,利用“举重以明轻”的法律解释原则,推导出“影视演员不能对影视作品行使权利”。此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司法实践的印证,只是二者的法律推理方式有所区别。在著名的《天仙配》著作权、表演者权纠纷一案中,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的继承人王冠亚等起诉安徽音像出版社和深圳南山书城,称其出版和发行行为侵害严凤英唱腔表演著作权和表演者权。对于此案中的表演者权侵权纠纷,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其判决中指出,对于戏曲电影《天仙配》中的唱腔表演,严凤英并不享有表演者权,也无法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的解释是,我国著作权法规定演员、演出单位对其表演享有表演者权。但是,对于包括电影唱腔表演者在内的电影演员的表演者权,法律却未做明确规定。基于电影演员与现场表演演员表演初衷的不同,为方便电影著作权行使,促进电影事业的发展,关于现场演出意义上的演员、演出单位享有表演者权这一法律规定,不应适用于电影演员。对于法院法律推理,笔者认为,在著作权法及其司法解释都没有对演员做出特别限定的情况下,把电影演员排除在演员之外是缺乏法律依据的、武断的结论。但考虑到拍摄电影的目的是为了复制、发行和传播,应推定电影演员同意出演的意思表示包含了同意载有其表演的影视作品的复制、发行和传播,当然这是以其享有表演者权为前提,只是这些权利因其同意出演而转由制片者享有。
综上分析,我国著作权法及其相关的司法实践中是区分录像制品和影视作品的。在我国著作权法体系中,录像制品因为独创性不高,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是作为邻接权进行保护的,而表演者权也属于邻接权,既然二者都是同一位阶的权利,不存在优先保护的问题,自然不发生表演者权自动转让于制作者的问题。而影视作品是享有著作权的,在任何区分著作权和邻接权的立法中,保护的重心永远是著作权。因此,影视作品中表演者的部分经济权利由制片者享有是具有法理依据的。这样的区分既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又兼顾了公平和效率的价值追求。因为影视演员在参与拍摄时明知作品将用于复制、发行和传播,表演者相关权利转让并不违背当事人的意思;而对于录像制品,演员在同意录制时并不必然知道作品将用于复制与发行的目的,如郭德纲案中相声表演的录制,郭德纲等人只知道是用于电视台的播放,并不知晓其将用于公开发行,剥夺其上述经济权利对表演者明显不公。
4 我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第三稿)相关规定存在的问题
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的启动正值《北京条约》达成一致并最终顺利通过之际,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在我国签订并以我国城市命名的国际条约,著作权法的修订必然应对条约内容作出回应。在关于表演者权利转让方面,著作权法修订草案(第一稿)第33条规定:“如当事人无相反书面约定,视听作品中的表演者权利由制片者享有,但表演者享有表明表演者身份的权利。”其规定的权利转让模式是符合《北京条约》要求,也基本符合我国国情,存在的问题是对转让权利的范围没有限定,即表演者除署名权外的全部权利均由制片者享有,这是不合理的。草案第二稿和第三稿对一稿做出了重大调整,删除了“如当事人无相反书面约定”的内容。第三稿第36条第2款规定:“视听作品中的表演者根据第33条第(五)项和第(六)项规定的权利由制片者享有,但主要表演者有署名权。主要表演者有权就他人使用该视听作品获得合理报酬。”从该条规定看,我国采用了严于条约的权利转让模式,不仅直接规定上述权利归制片者享有,而且取消了条约中的“但书”规定,即当事人在此问题上没有任何意思自治的余地。此等严厉的权利转让规定体现了立法者对于效率价值的特别关注,其优点在于能够提高作品的传播效率,使他人在使用视听录制品时只需获得制片者许可,而无需一一征得表演者的同意,简化了作品使用许可方式,有利于促进国家影视业的发展和繁荣。
但著作权法修订草案有关表演者权利转让条款存在两方面的弊端。1)权利转让规定完全排除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有对私权过分干涉之嫌。适用于影视作品中的表演,其合理性在于影视演员在参加拍摄时,就明白无误地知道录制的影视作品不仅会在电影院或电视台播放,而且会用于出版DVD和网络传播。但若适用于录像制品中的表演,由于表演者当时并不明确知道录像制品是否将用于出版发行等目的,则会产生不公平的结果。在著作权法修订草案删除了录像制品,把录像制品并入视听制品后,由于录像制品和影视作品适用同一规则,这一问题便凸显出来。用修改后的规则再审“郭德纲案”,则会得出相反结论,飞乐影视制品公司发行载有郭德纲相声的音像制品行为没有侵犯郭德纲的表演者权。再如,某演员在排练时默许其朋友进行录像,其朋友可以自己或授权他人出版该表演的DVD和网络传播,这对表演者十分不公。2)为与国际社会普遍适用的概念保持一致,修订草案把“电影作品和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改为“视听作品”,同时取消了“录像制品”的规定。关于取消的理由,国家版权局的解释是:单设录像制品作为相关权客体的立法例并不普遍,多数情况下录像制品都可以作为视听作品保护。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我国长期以来一贯坚持大陆法系较高的作品独创性标准,录像制品因其独创性不足而不视为作品,只作为邻接权保护。如果按照国家版权局的解释,多数情况下录像制品都可以作为视听作品保护,则意味着我国关于独创性标准发生根本改变,这势必会对著作权法中作品的概念产生较大影响。另外,对于其他少数不构成视听作品的录像制品,如何适用法律则成为十分复杂的问题。因为修改草稿中删除了有关录像制品的规定,其作为邻接权保护缺乏法律依据,不构成视听作品的录像制品将处于无法律保护的困境。
5 对我国著作权法中表演者权利转让条款的完善建议
综上分析,著作权法关于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的修订偏重对制片者利益的保护,而没有适当兼顾表演者的权益。其删除录像制品的做法,将会对著作权法中作品这一核心概念造成一定的冲击,甚至会导致法律适用上的困境。为解决以上问题,建议对著作权法修订草案(第三稿)进行2点修改:第一,恢复草案(第一稿)表演者权利“推定转让”的规定方式,在第36条第2款中增加“但书”规定,即“视听作品中的表演者根据第33条第(五)项和第(六)项规定的权利由制片者享有,但当事人有书面相反约定者除外”。第二,保留原著作权法中关于录像制品的规定。从而使著作权法的修订既能满足《北京条约》的要求,又能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保持法律传统和司法实践的相对稳定,在促进我国影视产业发展的同时,兼顾表演者和制作者的利益平衡。
6 结束语
利益平衡是民法的精神和社会公德的要求,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也应是利益平衡的结果。制片者的利益和影视产业的发展可以是优先考虑的因素,但表演者的意思自治不能完全被抹杀,因此“推定转让”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转让模式。我国著作权法的修订应从中国国情出发,在尊重法律传统和保持法律及司法实践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尽量实现表演者与制作者的利益平衡。
[1]常公元.视听表演者权归属模式及我国的立法选择——以《视听表演北京公约》为切入点[J].北方经贸,2014(7):105.
[2]王迁.《视听表演北京公约》视野下著作权法的修订[J].法商研究,2012(6):27-30.
[3]唐姗.戏曲电影中唱腔著作权纠纷的处理规则——评王冠亚、王小亚和王小英诉安徽音像出版社、深圳南山书城侵害著作权纠纷案[EB/OL].(2013-10-09)[2016-04-01].http://www.iprchn.com/Index_NewsCon⁃tent.aspx?newsId=648877.
[4]国家版权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的简要说明[EB/OL].(2012-08-20)[2016-04-01]http://economy.caijing.com.cn/2012-04-04/1118007 10.html.
[5]唐艳秋.论表演者权利的限与放——以“旭日阳刚事件”为视角[J].西部法学评论,2011,(03):12-13.
Study on Transfer of Performer’s Rights in Audiovisual Fixation
Zhang Shulin
(School of Marxism,Hubei University of Automotive Technology,Shiyan 442002,China)
D997.1;D923.41
A
1008-5483(2017)03-0077-04
10.3969/j.issn.1008-5483.2017.03.019
2016-04-01
湖北省知识产权培训(十堰)基地研究项目(HBZPO-6-X-2014-019)
张书林(1968-),男,湖北十堰人,教授,法学硕士,从事国际经济法方面的研究。E-mail:johnny@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