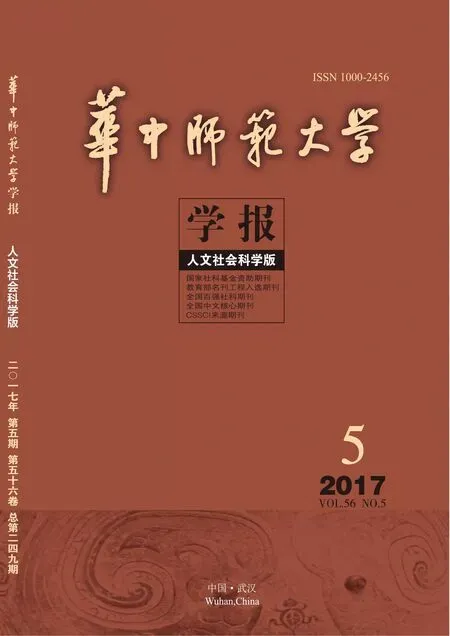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回应与推进
——森和努斯鲍姆的能力论
2017-02-27龚群
龚 群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学院, 北京 100872)
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回应与推进
——森和努斯鲍姆的能力论
龚 群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北京100872)
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理论是当代政治哲学中最重要的正义理论。罗尔斯的理论是以契约论的方法推导的,正义原则实际上是对社会基本善进行分配的原则。然而,立约人只能是具有立约能力的理性人,因而罗尔斯的契约论限制了罗尔斯的正义视域,契约论方法以及理性人的社会合作体系致使其不把先天的残障人包含在正义问题范围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和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等人对于罗尔斯的方法论,对资源平等的分配正义问题提出批评,他们突破契约论的局限,提出了能力平等的方法论。他们从人的基本能力的前提出发,将基本善的分配转向能力平等,指出正义在于基本能力的实现,而非正义在于基本能力的不足,因此他们从罗尔斯的形式正义转向实质性的正义。同时他们也对于契约论不包括残障人的问题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罗尔斯回应了他们的批评,并仍坚持了自己的观点。
能力; 平等; 分配正义
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是当代最重要的正义论。罗尔斯的正义论激发了当代世界哲学界以及法学、经济学等领域里的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并使得政治哲学成为当代学术界的显学。罗尔斯的正义论又称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平等是罗尔斯正义论的核心理念。当代政治哲学在平等方向的探求,既是沿着罗尔斯所开启的方向进行,同时也是在对罗尔斯的批评中推进。这里讨论两种对于罗尔斯来说相当尖锐的批评,一是罗尔斯的资源平等以及契约论的方法问题,二是从契约论的主体引申出来的问题,即残障(残疾)人问题。为了讨论这些批评,我们先简要地论述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其中主要为了引出问题而着重阐述罗尔斯的基本善、立约主体以及社会合作体系观念。
一、公平的正义
罗尔斯的正义论以两条正义原则为核心,这两条正义原则就是他的公平正义观的体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于两个正义原则的完整表述是:“第一原则:每个人对于平等的基本自由的最广泛的总体体系(the most extensive total system)都拥有一种平等权利,这种自由是与对于所有人而言的相似的自由体系相容的。第二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当这样安排,以致于使它们:(一)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以及(二),依系于在机会的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①第一条正义原则指的是平等自由,第二条原则涉及社会机会平等以及平等倾向的经济分配原则。第二原则在经济分配方面,又称之为差别原则,即惠顾最小受惠者或提高最小受惠者的经济期望值。罗尔斯指出,他的两条正义原则的排列是辞典式的,即第一原则对于第二原则处于优先地位,而且第二原则应当贯彻第一原则的平等精神。
理解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关键还在于他的“基本善”(primary goods)的概念。权利、自由与机会、收入与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都包含在他的基本善概念里,这些善可称之为社会善。当然,我们也可说,空气、水等也是基本善,但这是自然性的基本善,不在需要政府调节的范围内。在他看来,正义原则实际上是指对这些社会基本善进行分配的原则。对于社会基本善,不仅有一个如何在公民之间进行公平正义分配的问题,而且有一个如何保护公民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而不受侵犯的问题。正义原则对于这样两个方面都起作用。不过,罗尔斯主要是把他的正义原则看成是分配原则。即人们如何分享社会基本善。罗尔斯说:“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与责任,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②
还有,罗尔斯所说的社会正义是一定社会范围内的正义,因此,这就涉及谁是正义权利与责任/义务的主体。换言之,我们还需理解罗尔斯在表述两个正义原则中所指涉的“每个人”和“所有人”,所指的是谁?为了理解这个问题,就必须联系罗尔斯的“原初状态”来说明。罗尔斯的原初状态类似于洛克、卢梭等的古典契约论中的“自然状态”。以罗尔斯自己的说法,他是把古典契约论提升到一个更抽象的程度,即从实质上继承了这一契约论。这样一种原初状态的设置是把所有进入这一状态的人置于一个自由平等的地位。在洛克等人那里,处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们是自由平等的,他们有着先天的自由与平等权利。这些人在自然状态下,所有人经过契约同意,转让一部分权利从而进入政治社会。在罗尔斯这里,他所设想的人们,也是自由平等的。这种自由平等状态罗尔斯以“无知之幕”来表达,即所有人由于无知之幕的缘故,因而不知道自己的出身、社会阶层或阶级地位、财产状态、受教育程度以及自己的个人天赋状况等。换言之,罗尔斯实际上是以这种方式来形象地指出,他的原初状态如同洛克、卢梭等人的自然状态,所设想的生活在这种状态下的人是平等的,所有个人的特殊信息都已经被屏蔽,也就是说,所有个人之间没有在财产占有、出身地位以及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特殊性,无人知道他们自己的特殊社会运气和自然运气,因而他们处于一种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状态。同时,这种原初状态也如同洛克等人所设想的,是没有至上权威统治的状态,因而他们既是自由的,也是平等的。然而,罗尔斯与洛克、卢梭等人不同的是,罗尔斯的设想是处于原初状态中的人们并非是经过契约直接进入某种政治体系,而是他们在原初状态下以契约同意的方式,选择对于社会体系或基本社会结构有着实质性意义的正义原则,尔后再以这些原则指导国家制度的建设,首先是宪法创立,而后则是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等,从而建立一个以正义原则为灵魂的正义的国家。如同洛克等人一样,在罗尔斯理论中的原初状态中的人们,也就是后来在其政治社会中享有公平正义的成员。
在这里,理解罗尔斯的契约特性是理解他的契约主体与社会主体的前提。从霍布斯以来的社会契约论,都内在蕴含着契约主体并非只是一个人,而是复数的行为主体。其次,任何契约的进行或协议的达成都不可能是无条件的,即使是假设的契约,同样也应当具有真实契约所发生的条件。即立约双方应当是有着意志自由的独立主体,达成的协约或契约要表达立约双方的真实意愿,也就是要处于一种无压制的平等地位,合约就是双方自由意愿的表达。在罗尔斯的契约论中,就是各方都应共同分享这些假设条件。这些条件也是对于各方都平等的条件,罗尔斯说:“假定原初状态中各方的平等似乎是合理的,也就是说,所有人在选择原则的程序中都有同等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提议权,并说明接受它们的理由等等。那么显然,这些条件的目的就是要体现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类存在者的平等,作为有他们的善观念(conception of good)和正义感(sense of justice)能力的人(creatures)之间的平等。平等的基础在这样两方面是相似的。目的体系并不依价值排列,每个人都被假定为具有必要的理解力和实行所采用的任何原则的能力。这些条件和无知之幕结合起来,就决定了正义的原则将是那些作为平等的关心自己利益的有理性的人们,在无人知道自己在社会和自然的偶然因素方面有利或不利情形下都会同意的原则。”③罗尔斯的契约主体就是具有两种道德能力即自我善观念和正义感能力的人,罗尔斯指出,“个人因其在必要程度上拥有两种道德人格能力(powers)——即正义感的能力(capacity)和善观念的能力(capacity) ——而看作是自由平等的个人。”④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还在某处加上理性能力来谈个人。他说:“我们把公民看作是自由平等的人。基本观点是:由于公民的两种道德能力(正义感的能力和善观念的能力)和理性能力,即与这些能力相关的判断、思考和推理的能力,他们是自由的。拥有这些就一个社会充分合作成员最低要求的能力而言,他们是平等的。”⑤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罗尔斯在谈到“两种道德能力”时,所用的是“power”一词,而在谈到正义感和善观念时,所用的是“capacity”一词。使用capacity一词表达能力,是指人本身应当具有的能力,而使用power一词,则是在能力可发挥或起作用的力量意义上使用。就平等而言,罗尔斯不仅从契约主体的意义上谈人的平等,而且从社会合作的意义这样说。因此,这里涉及罗尔斯对社会的规定。
罗尔斯把社会看成是一种合作体系,而对于正义的社会而言,这种合作体系就是一种公平的合作体系。他把“公平合作体系”看成是他的正义论的基本理念。他说:“在这种正义观念中,最基本的理念是社会作为一个世代相继的公平的社会合作体系的理念。”⑥罗尔斯认可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社会政治人的观点,认为一个孤立的人并非是一个社会人,社会作为一个所有社会成员的合作体系,每个人都是生入其中,死出其外。那么,公民在什么意义上被看成是平等的人?他说:“我们认为,他们是在这种意义上被当作平等的,即他们全被看作拥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以从事终身的社会合作,并作为平等的公民参与社会生活。我们把拥有这种程度的道德能力当作公民作为人而相互平等的基础(《正义论》第77节)。也就是说,既然我们将社会视为一个公平的合作体系,平等的基础就是拥有某种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和其他能力,以使我们能够充分地参与社会的合作生活。这样,这种公民的平等在原初状态中就表现为他们的代表的平等。”⑦任何一个人都是处于社会合作体系之中,并且是能够终身从事社会合作,因为社会合作,所以社会成员需要最低限度的能力即主要为两种道德能力。罗尔斯认为每个人都终身充分参与社会合作,人们因自身能力参与社会合作因而是自由平等的。这个平等不仅是说政治平等,而且是体现在对于基本善的分配上的平等。但基本善的所有项目不可能都是完全平等的分配,这尤其体现在财富或收入分配上。罗尔斯的处理是以差别原则来使得最少受惠者得到最大利益,即惠顾最少受惠者,逐步提高其社会期望值。
二、何种能力的平等?
罗尔斯讨论正义的这一路径,如果从原初状态作为出发点和基础来看,可以看作是契约论的方法,如果从把基本善作为分配与再分配的对象来看,可以看作是一种资源平等的方法论,即以资源平等来讨论正义原则问题。罗尔斯的这一理论方法,受到了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和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又译为“纳斯邦”)等人的批评。我们先看看他们对罗尔斯的资源平等的方法论的批评。当代学界对于平等的讨论,也多集中于分配领域,而对于分配正义而言,人们的讨论不是围绕着“为什么要平等”,而是围绕着“什么的平等”这一问题展开的。
我们知道,自由与机会、收入与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都包含在罗尔斯的基本善概念里,而森等人则主要看重的是这个基本善清单中的涉及物质性财富方面的内容,并且从这样一个角度对罗尔斯的基本善的分配正义论提出批评。罗尔斯的基本善清单实际上是对两个正义原则涉及分配内容的概括,而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中的第一原则是公民平等自由的权利原则。因此,当森等人批评罗尔斯的基本善作为一种资源分配时,是回避了这一问题的。正是由于森把罗尔斯基本善中的自由(内在包含权利)这一重要项放在一边,因而他可以把罗尔斯的基本善方面的平等要求看成是一种手段方法。⑧森援引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财富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善,它只是作为我们追求别的东西时有用的工具而有价值。”⑨我们对于财富,并非因其自身缘故而值得拥有它。换言之,它仅仅是我们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并且,在森看来,一个人如果拥有了罗尔斯所说的基本善如财富,并不能因此而说他就是幸福的。A如果拥有比B更多的财富,但A却患有严重疾病,而B却身体健康,我们并非能够因为A的财富而断言A比B更幸福。我们也不能因为A占有更多的财富即资源而认为A比B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依森之所见,财富作为手段是达到什么目的呢?森认为,这个目的是自由。不过,要看到,森的自由与罗尔斯在第一原则中的自由其内涵不是一回事。森的自由概念指的是个人能够在多大范围和多大程度上在人生多重领域里的可支配性。财富在一个患有绝症的人那里,不可能改变他将要离开人世的命运,而占有更多财富即资源,能够使得健康的个人有着更多的实质性自由,即人生机会。森认为,这种区别是罗尔斯的理论无法回答的问题。因此,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即(可行)能力(capabilities)⑩方法。从(可行)能力方法来看,人的能力是多方面的综合体。如在A与B的例子里,财富对于一个患绝症的人来说,没有价值意义,因为财富这一资源不可能转化为他的可行能力。而在B那里则完全不同。
森的“(可行)能力”概念(capabilities)所表达的是具体个人的实际能力,或人在实践中能做对自己有意义或有价值的事或行动的能力。森说:“当我试图根据一个做有价值的活动或达致有价值的状态的能力来探讨处理福祉(wellbeing)和利益(advantage)的某种特定的方法时,也许我本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词。采用这个词是为了表示一个人能够做或成为的事物的可选择的组合——他或她能够获得的各种‘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s)。”如联系到个人利益,那么,就是“根据个人获得各种作为个人生活的一部分且有价值的功能性活动的实际能力来评价利益。”理解森的能力或可行能力概念的一个关键是理解他的“功能性活动”,即因为有了可行能力而能够起作用或发挥作用,这种作用对于个人利益的获得或福祉的增进具有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森把能力与自由联系起来,森的自由与罗尔斯的区别在于,他所说的“自由”是实质性自由。如人们所说:“对于森而言,他把现实的自由看作是有效的选择,一个正义的社会将最大程度的这种自由给予最大多数人。能力方法把我们的注意力从资源转换到它们的结果。如果一个人有更多的能力,那就有更大的有效自由来选择他的生活和工作。”实际能力也就是人们能够有自由来进行选择。
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森通过贫困、收入减少或收入相对被剥夺、失业、医疗保健、文盲、性别不平等等方面,有力地说明了这些因素在实践中对可行能力的消极作用或负面影响。如非洲地区和印度某些地区长期存在的营养不良以及饥饿现象,使得这些地区的人的生命长期处于危机状态,基本的生存能力都受到威胁。就美国而言,美国的黑人与白人在35岁到54岁年龄组的死亡率,前者要远高于后者。因此,“将信息基础扩展到基本可行能力,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不平等和贫困的理解。”然而,森并没有明言哪些可称之为基本(可行)能力。不过,从其论述中,我们可知,“相关的能力具有基本性意义,这种能力的缺乏表明一个人无能满足他自己的基本需要。”所谓“(可行)能力”,即人的生存能力、工作能力、交往能力以及享受自然寿命所给予的生活的能力等。森从这些方面的能力来看待个人自由,如森所说:“我集中讨论了一种非常基本的自由,即生存下来而不至于过早死亡的能力。”人们在这些方面的能力越强也就越有自由,因而他是从发展的意义上来看待自由。他把这些方面个人获得的发展看成是实质性自由的发展,而把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防护性保障等看成是工具性自由,他说:“这些工具性自由能帮助人们更自由地生活并提高他们在这方面的整体能力,同时它们也相互补充。”
值得指出的是,被多数中文版本翻译成“可行能力”(capabilities)一词的英文,与罗尔斯在表述人的自我善观念的能力和正义感能力所使用的英文都是一个词:capability。但森认为,他使用这个概念与罗尔斯不同,因为罗尔斯使用这一概念所讲的是道德能力,而森则不是。罗尔斯使用这一概念表明人人平等的基础和前提,而森使用这一概念所表明的则是多方面的实践能力。因此,森表明了与罗尔斯相区别的一种本体论前提的颠倒。在罗尔斯看来,人的道德能力都是平等的,因为我们都是理性的人,能够获得基本相同的道德能力,或具有这样的潜能。罗尔斯以这样的本体论前提来奠基他的正义论,从而推导出人人自由平等的正义原则,并据此以基本善作为分配物。罗尔斯的契约论方法需要这样一种人人平等的本体论前提。在洛克那里,是人人具有的天赋权利,在康德那里则是理性存在者的理性,而在罗尔斯这里,则是人因具有理性而有的道德能力。森指出,从这样一种进路所得出的正义观是一种先验主义的正义观,其目标是探讨建立一种完全正义的制度(perfectly just institution)。洛克、卢梭和康德以及罗尔斯等人,他们都主要致力于先验的制度分析,是一种着眼于制度安排的正义研究进路。而森从(可行)能力出发,进行的是经验性的研究,指出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性别和不同种族的人们在实质性自由意义上的能力的差别。以他自己的说法,他是着眼于现实的(realization-foucsed)正义研究方法,“关注人们的实际行为,而并不假定所有人都遵循理想的行为模式”,因此森不可能由此推导出一个普遍的正义原则,而只是进行个人可能获得的实质自由的比较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森没有平等观,而是不同于罗尔斯的平等观。在“什么的平等”讲座中,森提出的平等是基本能力的平等,所谓基本能力,即满足最基本需要的能力或可行能力,“这种能力的缺乏表明一个人无能满足他的基本需要(need)。”森对于(可行)能力缺乏的负面研究表明,这种满足基本需要的能力,也就是决定一个正常人存在或正常生活的能力。
森指出,他的(可行)能力方法与罗尔斯的契约论方法或资源平等方法是根本不同的方法,罗尔斯的理论所导致的是使得什么是正义的社会成为关注的中心,而他要进行的则是基于社会现实的比较,研究正义的进步或倒退。森的心目中有一个能力平等的观念,但他则是从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性别、不同肤色等的人生存状况来研究人的(可行)能力的不同。因此,相对于什么是“完全正义的制度”,他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从现实出发,如何才能推进社会正义。以森自己的话来说,这两种进路或方法的对立导致这样的问题:“是否对正义的分析一定要局限于如何改进基本制度和一般规则上?难道我们不仅应该考察下社会中出现了什么,包括在既定的制度和规则下,人们实际上过什么样的生活吗?而且还应考察包括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人类生活的实际行为的其他影响?”换言之,(可行)能力方法从现实出发,来回答现实社会中的正义问题。
从(可行能力)方面发展当代正义理论,还有另一个重要人物,这就是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在森提出能力方法之后,努斯鲍姆与森一道,推进了能力方法的研究。努斯鲍姆也说:“我认为,对某些核心的人类能力的说明应该为政治规划提供一个关注点:作为社会正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必要条件,公民应该保障这些能力的一个阈限水平,不管他们除此之外还具有什么其他的能力。”森与努斯鲍姆在能力研究方面的区别是,森没有提出一个最基本的或核心能力清单,而只是从不同方面来谈论满足人的最基本需要的能力等,而努斯鲍姆经过多年的研究,提出了她的(可行)能力清单。她说,她使用这个方法“是要对核心的人类权利(entitlement)理论给予一种哲学的支持,这些核心的人类权利应当得到所有国家政府的尊重和[从政策]上体现出来,把它作为对人的尊严尊重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一个基本的社会最低限度的观念为聚焦于人的能力(human capabilities)的方法所提供,而‘人的能力’是说,人们实际上能够做什么和能够成为什么,而这是为这样一种直觉观念所把握:人的生命因有人的尊严而有价值。我提出了一个主要(central)人类能力清单,并主张,所有这些能力都隐含在有着人类尊严的生命价值观念里。”努斯鲍姆这里说得很清楚,她是面向现实的,她不仅像森那样从一般意义上指出他们所说的“(可行)能力”概念的内涵是什么,而且她与森不同的地方在于,她提出了一个主要能力清单,并且,她认为这个清单是为尊严概念所涵盖。这个清单有十个方面,包括人的预期寿命,身体健康,感觉、想象与思想能力,情感能力,实践推理,归属感,与环境友好相处,娱乐,参与政治与拥有财产权等。她多次在不同的著述中提出了这个清单,她在《正义的疆界》一书中列举完后说:“基本的观念是,考虑这些方面的能力,我们能够说,想象一个生活如果没有这些(可行)能力,这样一个生活就不是一个有着人类尊严价值的生活。”在她看来,她的这个清单具有全球性的普遍性,但同时又是开放性的,因而可以修改的。她提出这个清单,并非是要像罗尔斯那样,以此为标准,而建构一种完善的政治制度,或一种完全正义的理论。如同森那样,她要回答的是什么是不正义,即“什么对于全人类来说都是不正义的?”在努斯鲍姆看来,那就是缺乏主要(可行)能力。人在什么时候会不要主要可行能力清单里的内容呢?可能确实如森所设想的,只有当他们受到更严重的威胁时,例如人们只有在面临饿死时才会“愿意”做奴隶。而让人作出这种选择本身就有损人的尊严。从这样一个方面也可以说,努斯鲍姆的清单是要说,一个正义的社会是能够在最低限度上保障或实现这些方面人的能力的社会。因此,努斯鲍姆并非是要追求一个完美正义制度的典范,而是把最基本的(可行)能力作为政治原则,追求人人能够发展或实现最低限度能力的社会安排。
应当看到,这样两种理论进路或方法各有其理论上的优势或不足。在《正义的理念》一书中,森也着重以专门的篇幅充分肯定了罗尔斯正义论的理论贡献。在该书的第二章中,森从七个方面谈到罗尔斯方法的积极意义。在其中,森指出罗尔斯的道德能力方法把善观念的能力和正义感的能力置于基础性地位是一重大贡献,因为这完全改变了对于经济学界把人看成是完全自利的看法。因为如果照这样的观点看,则人就完全没有考量正义的能力和意向。其次,指出罗尔斯不仅强调公平平等,而且把自由置于优先地位或首要地位,从而使人们在衡量社会制度的正义性时,有充分的理由考虑自由的价值。然而,其问题在于,如果某一社会没有条件实现或接近完善的正义制度,那么,森认为,在多种不同的选择方案面前,我们只能根据其社会后果或现实结果来评价它。森以印度教中的至尊人格神奎那师(Krishna)即化身为驭手的大神黑天和富有责任感与同情心的大神阿朱那(Arjuna)在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关于战争的一段著名对话为例。阿朱那对于战争后果即战争要杀无数的人感到不安,而奎那师则以责任和道义之名劝说阿朱那进行这场战争,而不是要顾及战争的后果。但森认为,事实上阿朱那是对的,战争虽然符合道义与正义,但战争所带来的可怕后果证明如果不进行这场战争可能更正确。因此,在森看来,“‘即使是世界毁灭,也要实行公正’(Fiat justitia, et pereat mundus)的说法是不可取的。”如果有这样一种极端的后果,那么,并不值得为这样的正义辩护。不过,我们认为,森以这样极端的例子来批评罗尔斯可能是有失偏颇的。一个正义的制度并不是使得世界毁灭的制度,恰恰相反,一个不正义或丝毫没有正义性的制度,如法西斯的灭绝人性的制度,恰恰是使得世界毁灭的制度。
三、残障人问题
森不仅以(可行)能力方法将他的正义论与罗尔斯的正义论区别开来,而且以(可行)能力方法对罗尔斯的基本善的分配提出质疑,柯亨称其是对基本善分配的彻底反驳。在“什么的平等”中,他称基本善是一种商品拜物教(fetishism)的表现,在他看来,拜物教使得人们只关心善品(goods)本身,而不关心善品(goods)“能够对人做什么。”我们前面已述,森的这个意思主要是针对罗尔斯的基本善中的收入与财富等内容,收入与财富的分配是资源分配,强调平等也就是资源平等。而森认为,如果我们不问分配的资源能够对人们做什么,那么,并不意味着能够实现平等。在森看来,同样的物品对于人来说,能够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这是因为,虽然同样的物品对于人来说,能够提供同样的东西,如一种一定量的食品对于个人来说,能够提供一定的热量或营养,但是,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所起作用是不同的。对于一个处于极度饥饿状态的人来说,一片面包可能救命,而对于一个有着正常饮食需要的人来说,一片并不能填饱肚子,因而并不能起多大作用。一顿有鱼有肉的美餐对于一个没有高血脂、高脂肪的人来说,是健康而有益的,而对于一个有这样高血脂症的人来说,则并非是有益的。因此,森认为,仅仅依靠一个人占有多少善品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得益或处于优势地位是极易误导人的。因此,应当把注意力从基本善品本身转到这些善品能够对人做什么或对人起什么作用。换言之,森所强调的不是能给人什么分配物,而是所分配物对不同的人而言,能做什么。
森特别以残疾人的例子来反对对基本善品的平等分配。在他看来,依据罗尔斯的平等原则对一个四肢健全的人与一个下身瘫痪的人进行平等的物品分配就有着严重问题。即使是以差别原则来区别对待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使最小受惠者获得最大利益,但这里的“最小受惠者”如果仅仅从收入水平来识别,并且,以基本善(主要是收入与财富)作为惠及的分配物,那么,如果一个是残疾穷人,另一个是身体健康的穷人,同等的补偿分配物或货币所起作用是很不相同的。如同样的收入低水平,但下肢残疾者需要政府所提供的免费轮椅,而健康人则没有这一额外需要,这无疑使得残疾人有了更多补偿的需要。还有,可能同样是残疾人,因为精神状态或精神气质的不同,人对外在善品的感受或态度可能不一样,但这种不同不应成为我们提供或不提供给他们帮助的理由。如一个人天性是多愁善感,心情阴郁,另一个则是天生的快乐汉,森以一个缺乏基本生活必需品而有着格外阳光气质的下肢残疾者为例,可能他有着天生的快乐气质,因而并不因他自己的身体残疾和缺乏必要的生活必需品而心情沮丧。“因为他有一种快乐的气质,或者因为他志向水平低,每当他看到彩虹时,他的心情激动万分。”但即使是一个人有着这样快乐的心态,我们在直觉上仍然有对他进行补偿的必要。柯亨赞同森对罗尔斯的批评,他说:“考虑一下既穷又跛但有着阳光气质的蒂尼·汤吧。以任何福利主义的标准看,蒂尼·汤实际上是幸福的。并且我们还可以假定,由于一种天生的内在气质,他很幸运地享有大量获取幸福的机会,他并不需要很多努力就可得到它。在这种情形里,平等主义者并不会因此就把他从免费轮椅接受者的行列里排除出去。因此,他们并不认为轮椅的分配应当唯一地为那些需要轮椅的人对福利机会的要求所决定。不论他们为了幸福或为了能够过得幸福是否还需要轮椅,他们都需要轮椅来充当其适当的辅助工具。”柯亨认为平等的直觉告诉我们,残障人需要特殊的资源来帮助他,并不因他的心情或精神心理状态如何而改变。而罗尔斯平等分配基本善的观念,并没有从这样一个方面来考虑人与人的差别。丹尼尔说:“对基本善的批评,一个方面是说,它没有抓住基本的道德直觉,即对平等的关注,这个直觉是,不论何时我们是由于并非我们自己的失败原因或我们不能控制的结果而使自己的处境最坏,那么,我们就有请求他人帮助或补偿的合法要求。罗尔斯用基本善使我们不能以一定的方式来回应处于这种情景中的个人,所以他的原则没有响应这种基本的平等直觉,森和柯亨发展了这种直觉,罗尔斯自己也在别的地方回应了这种批评。另一种批评是在个人能力方面的变化,即从基本善转化为自由或能够做什么的能力,或者是因其功能性活动因而他们成为他们所选择的状态。在人的能力方面的变化,即从基本善到能力的变化表明,基本善的概念是不灵活的,最终将失去基本的道德关注,即在能力方面的较大平等。森发展了这个批评,揭示在罗尔斯使用的‘基本善’概念中有一种拜物教(fetishism)成分,森的理论最终关注的不是基本善而是能力——能力是‘人与善品关系’的结果。”
努斯鲍姆从残障人的问题对于罗尔斯的契约论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罗尔斯的契约论方法是把人类成员的一部分排除在正义领域之外。努斯鲍姆指出,从霍布斯、洛克、卢梭以及康德形成的传统,是把契约论作为探讨正义的一个基本方法,这一方法为罗尔斯所复活,而“所有的契约论都依靠对商议过程中的合理性的说明,都假设缔结契约的人和确立原则的那些公民是同一群人。”这些人之所以能够订立契约,就在于他们都是理性人,能够正常进行商谈讨论。因而契约论方法必然有它不可考虑的方面,即任何社会中都有那种在身体与精神方面不健全或患有残疾的人,这些人不可能进入到契约活动中来。罗尔斯假定所有人都具有理性,因而具有两种道德能力,我们也可以说,这些患有残疾或残障的人,并非是生命的全部时间或过程中都有如此严重的情况,或者如像婴儿,虽然还不具有理性,但应当是潜在具有理性,因而也可以由他/她的代表来参与契约讨论。但是,就真的没有那种终生都不具有理性能力的人吗?有。如出生就有智力缺陷的人:智呆儿。努斯鲍姆指出,霍布斯以来的罗尔斯意义上的传统契约论,契约的订立参与者是“自由、平等、独立(Free, equal and independent)”的主体,这些主体以互利为目的进行社会合作(Mutual advantage as the purpose of social cooperation),参与各方都有自己的动机,而契约的目的就是为了达成对各方相互有利的目标。努斯鲍姆指出,社会契约论的模式在政治哲学中有着非常强的优势,然而,契约方法将一部分残疾人排除在社会订立的契约之外。在契约论正义论中,契约所规定的内容就是正义的内容,无法成为立约人也就意味着将一些严重的问题排除出了正义的范畴。罗尔斯的回答也表明了这一点。他说:“在开始的时候,我将把具有这样严重缺陷的人作为极端情况加以抛开,而具有严重缺陷的人是指他们从来无法成为正式的、有贡献的社会合作成员。相反,我仅仅考虑两种情况:在这两种情况内,我称之为正常范围的东西,即在公民的需要和要求方面的差别范围内的东西,同每个人成为一个正式的社会合作成员是相容的。”如果我们像努斯鲍姆那样,把智呆儿这样可能终生智障病人纳入到契约主体的范围之内,马上就可以看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契约订立的前提是有立约和履约能力。而智障病人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能力的。罗尔斯坚持以正常的社会合作成员作为契约主体是合乎这一方法的逻辑前提的。
人们可能还会以差别原则来为罗尔斯辩护。罗尔斯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把这些有着严重智力缺陷的人纳入到契约主体的范围内,但他的差别原则则是对所有弱势群体给予关照的原则,如果把这类人看成是社会成员,因而仍然是在正义原则所考虑的范围之内。罗尔斯本人也作了这方面的辩护。他说:“公民在需要医疗照顾方面存在差别。这种情况的独特地方在于,公民在这种情况中暂时——在一定时期内——降低到最低必要能力之下,而这种最低必要能力是成为正式的、完全的社会合作成员所必需的。当思考政治正义观念的时候,在开始的阶段,我们可以将注意力整个地从疾病和事故移开,而把政治正义的基本问题视为规定自由平等公民之间的公平合作条款的问题。但是,我希望,作为公平的正义不仅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还应该扩展到能够解决在需要方面所存在的差别,而这些需要方面的差别产生于疾病和事故。”罗尔斯的这个辩护承认了人们有时会因为疾病和事故因而丧失最低必要能力,并且认为差别原则应当对这些问题进行考虑,但他仍然认为任何人并非是终生不能进行有效合作,因而对于社会不会没有贡献。
这里涉及罗尔斯的社会合作论。罗尔斯之所以把人的两种道德能力置于本体地位,在于他把所有人类的成员都看成是充分参与合作体系的成员,而不仅仅是把他们看成是契约中的立约人。然而,罗尔斯所说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是“充分而终身”的。他说:“个人也就是某个能够成为公民的人,也就是说,一个正常而充分并且终身参与合作(normal and fully cooperating member of society over a complete life)的社会成员,我们之所以加上‘终身’(a complete life)一词,是因为我们不仅把社会看成是封闭性的,而且也把它看作是一个或多或少完善自足的合作体系,它自身内部已为一切生命活动——从出生到死亡——和必需品准备了条件。”在罗尔斯看来,人们之所以能够在原初状态中选择正义原则,那是因为人们因为有两种道德能力因而能够合作,并且能够在将来的理想社会中同样能够合作。换言之,他们都是具有理性和道德能力的人。努斯鲍姆等人在这里发现了问题,如果这样认为,那一出生就有身体或智力残障的人呢?那些身体或智力方面有缺陷的人也能够这样进行合作吗?罗尔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一书中,几次说到公民个人是作为“终身、正常与充分”的合作体系的成员,应当看到,这是罗尔斯反复思考之后再次给批评者的答复。在这本书里,罗尔斯还说道:“当由于疾病和事故我们降到最低必要能力以下从而不能在社会里扮演我们的角色的时候,这种观念[指终身合作成员的观念——引者]又指导我们恢复我们的能力,或者以适当的方式使我们的能力得到改善。”我觉得,我们应当更充分理解上面所引的罗尔斯那段话。那段话的意思不仅是说我们都是终身充分合作的成员,而且还说明了理由,即怎样理解我们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罗尔斯看来,作为合作体系的社会是为我们每个来到这个社会的人准备了一切生存条件,而我们是终身生活于其中的。从合作体系的意义上看,这意味着我们就是这个合作体系中的一员,并且,罗尔斯从来没有说什么人不是正常的成员。(我们还可以说,难道罗尔斯不知道婴儿没有理性吗?而罗尔斯这里的意思是说,个人从出生就是正常成员)当然,人们可从契约论的原初状态说理性能力和两种道德能力才是正常成员的条件。但罗尔斯说,即使是因为疾病和事故使我们降到正常必要能力之下,仍然是被看成正常的合作成员,这也就是所谓“这种观念指导我们恢复我们的能力”的意思。我们也可以把这样一个思想推演到原初状态,即虽然作为一个现实的人类群体,不可避免地有着那些先天残疾或发育不全的个体,但他来到这个世界,也就是这个合作体系中的一员。我们也可以设想如果他是正常的理性人和具有两种道德能力的人,他会选择怎样的正义原则。换言之,恰恰是那些具有两种道德能力的理性人,是正常而又能够充分合作的人的代表,同时也代表了那些潜在的理性存在者和那些可以设想为应当具有理性的存在者。即使是那些先天残疾的智障者,他也应当享有人之为人的尊严,他作为人的本质存在是为理性存在者所代表的。
如果按照罗尔斯的回答,我们是否可以说,森与努斯鲍姆等人从(可行)能力方法得出的理论没有意义吗?这要看我们怎样看待罗尔斯的回应。我们认为,罗尔斯的回答坚持了从他的理论基点。在他看来,即使是我们承认社会中存在着终生不能从事合作的残疾人,但不能因此而认为他们就不应享有人之为人所应享有的生活条件或作为人的尊严而有的生活。但罗尔斯这类回答,实际上仍然是承认了,这样的残疾人没有参与到社会契约的立约中,也没有可能参与到真正的社会合作中,只不过是健全的理性人代表他们参与了社会合作体系。从这个意义来看,森与努斯鲍姆等人提出的(可行)能力方法以及他们提出的从(可行)能力来看待人的实质正义问题仍然是强有力的。罗尔斯从理性人作为理论基点推出完美的正义制度,但这种制度本身是形式正确的,因而对于现实的关照明显弱于森和努斯鲍姆等人的可行能力正义论。应当看到,森和努斯鲍姆等人的可行能力正义论,是罗尔斯之后正义理论的重大发展。这一理论推进和深化了当代正义论的讨论:人在自然禀赋方面的不平等同样是社会不平等的一个方面。他们对于残疾人的关注也成为罗尔斯之后正义论关注的一个重心。
注释
①②③Rawls, John.ATheoryof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302, 7, 19.
⑧森认为,基本善的分配只是作为实现或达到人的自由的手段方法,我们认为,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既包含了手段也包含了目的,其目的就是罗尔斯在第一原则即公民的平等自由权利原则所表达的,罗尔斯强调,经济与社会机会方面的第二原则必须体现第一原则的精神,并且可以看成是对于平等自由追求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实现。因此,我们也可以把第二原则看成是实现公民自由的手段。不过,我们也看到,罗尔斯第一原则所包含的平等自由观与森心目中的自由概念不同,森自己说他强调的是“实质自由”,如生存能力,而罗尔斯的第一原则所包含的自由则是以政治自由、思想自由等为基本内容的自由。
⑨Aristotle.TheNicomacheanEthic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17.
⑩“capabilities”这一概念,即为“能力”,然而,由于国内目前多数译者将其译为“可行能力”,故在讨论这一概念是,除中文引文外,以“()”将“可行”两字放入括号内,表明这一概念中文译法的不同。
责任编辑邓宏炎
On Sen and Nussbaum’s Criticism on Rawls’s Theory of Justice
Gong Qun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Rawls’s theory of justice i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Rawls’s theory is derivation from on the contract approach and the distributive justice is of equality theory for resources allocation on the primary goods. Rawls’s theory of contract and the system of social cooperation imply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disabled person is not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social justice. Amartya Sen, Martha Nussbaum and others criticized Rawls’s approach of his theory and the resource equality of distributive justice,and proposed the methodology of capacity equality. They have made a sharp criticism of the contract theory,which does not include disabled patients. Rawls responded to their criticism and still adhered to his own views.
capacity; equal; distributive justice
2017-07-10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方正义伦理思想研究”(14ZXA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