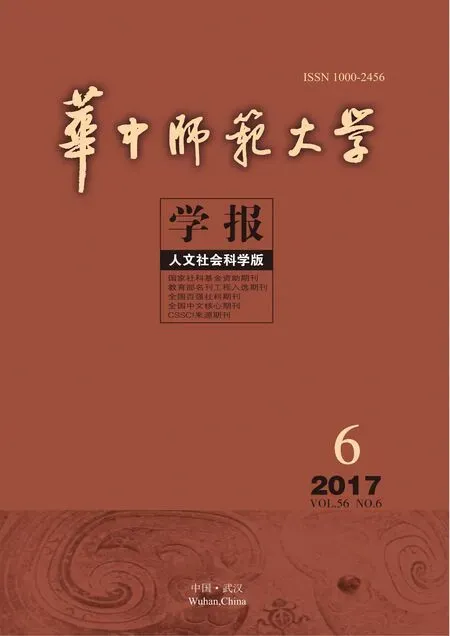关于唐代婚姻立法若干问题的思考
2017-02-27刘玉堂
刘玉堂
(华中师范大学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9)
关于唐代婚姻立法若干问题的思考
刘玉堂
(华中师范大学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9)
唐代婚姻立法不仅系统地总结了以前历代王朝的立法和司法经验,而且完整地体现了唐代统治者的立法思想和原则,充分地表现出唐律“一准于礼”的典型特征;唐代婚姻立法还具有明显的两重性,即许多法律条文中既有专制的、落后的、保守的成分,又透露出些许自由的、先进的、开放的气息;唐代婚姻立法不仅在主张与内容上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性,而且在技术与体制上有着明显的不平衡性。
唐代; 婚姻立法; 婚姻成立; 婚姻效力; 婚姻终止
在中国法律史上,唐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集中国封建立法之大成的唐律,不仅代表了中国封建立法的最高水平,为唐以后历代王朝的封建立法提供了蓝本,而且还以其礼法结合的鲜明特征以及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广泛影响,成为中华法系赖以确立的重要因素。
唐代的婚姻立法主要集中在《唐律疏议·户婚》之中。《唐律疏议·户婚》是在继承和总结唐以前历代王朝立法与司法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当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专门就唐代婚姻家庭关系的调整和规范所做的全面系统的立法,堪称中国封建社会婚姻立法的典型代表。正如刘海年等所说:“唐代的《户婚律》集封建婚姻家庭立法之大成,将封建社会有关婚姻家庭的礼加以条文化、法律化,起到了礼法并用的作用,因而为宋元明清各朝所沿用”①。“唐律是中国古代礼法结合的典范,剖析唐律有助于鉴古明今”②。有鉴于此,本文以《唐律疏议·户婚》为主要依据,对唐代婚姻立法的若干问题予以考察,力求从中得出一些新的见解,从而为当今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某些历史的借鉴。
一、唐代婚姻立法的法理分析与实践考察
唐代婚姻立法从法理和实践的维度考察,主要包括婚姻的成立、婚姻的效力和婚姻的终止三个方面。
(一)婚姻的成立
关于婚姻的成立,唐代婚姻立法从结婚条件和结婚程序(婚约)两方面做了规定。唐代的法定结婚条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结婚的必备条件,另一类是结婚的禁止条件。唐代,结婚的必备条件有四个:一是要有主婚人;二是要有媒妁;三是达到法定婚龄;四是必须符合一夫一妻制。唐代立法者对西周以来奉行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结婚原则进行了重新规范,精心设计了主婚人制度和媒妁制度。唐代关于主婚人的立法,主要集中在唐律中。为便于分析主婚人制度,现将有关法律条文援引如下:
《唐律疏议·户婚》“嫁娶违律”条:
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若期亲尊长主婚者,主婚为首,男女为从。余亲主婚者,事由主婚,主婚为首,男女为从;事由男女,男女为首,主婚为从。其男女被逼,若男年十八以下及在室之女,亦主婚独坐。
【疏】议曰:
“嫁娶为律”,谓于此篇内不许为婚,祖父母、父母主婚者,为奉尊者教命,故独坐主婚,嫁娶者无罪。……期亲尊长,次于父母。故主婚为首,男女为从。“余亲主婚者”,余亲谓期亲卑幼及大功以下主婚,即各以所由为首:事由主婚,主婚为首,男女为从;事由男女,男女为首,主婚为从。……“男女被逼”谓主婚以威若力,男女理不自由,虽是长男及寡女,亦不合得罪。若男年十八以下及在室之女,亦主婚独坐,男女勿论。
将以上法律条文综合起来分析,不难发现唐代主婚人立法实际上包含有以下方面的内容:(1)婚姻的成立必须要有主婚人。(2)法律严格规定和限制了主婚人的范围,只有父母、祖父母、期亲尊长、余亲才能取得主婚人资格。(3)有资格成为主婚人并不意味着必然就是嫁娶的实际主婚人,法律明确了主婚人的主婚顺序。前一顺序的主婚人优于并排斥后一顺序主婚人,只有前一顺序主婚人不存在时,后一顺序的主婚人才能实际行使主婚权。唐代主婚人共分三个顺序:祖父母、父母为第一顺序主婚人,期亲尊长为第二顺序主婚人,余亲为第三顺序主婚人。在第二、第三顺序主婚人中,又是按照先尊后卑的原则来确定主婚人的。(4)不同顺序的主婚人享有不同的主婚权。祖父母、父母享有绝对的主婚权,有权根据自己的意志单方面决定子女的婚姻,有权置丧夫之女的守节志愿于不顾,强制其改嫁,独立承担违法婚姻的全部法律责任。期亲尊长享有相对主婚权,在决定婚姻的问题上起主要作用,对违法婚姻也只承担主要法律责任。余亲则仅享有形式上的主婚权,他们在婚姻成立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要视具体情形而定,不能一概而论。即起主要作用的,对违法婚姻承担主要法律责任;起次要作用的,对违法婚姻承担次要法律责任。
主婚人制度的建立,不仅反映了唐代的婚姻立法是以礼作为重要指导思想的,而且表明唐代立法者在立法技术和经验上已经相当成熟。从西周时期对主婚权的调整和规范到唐代对主婚人的调整和规范,是立法技术上的一次重大飞跃。“父母之命”作为一种权利,从法律上是很难对其进行约束和规范的,更不用说课以法律责任,因为权利是不可能成为法律责任的承担者的。唐代主婚人制度的建立妥善地解决了这一法律上的难题。作为主婚权这一权利的主体,主婚人从权利的背后走进了法律的调整范围,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不仅使得主婚权的权利内容有了明确的主体归属,而且使得建立一个法律责任体系来保证权利的依法运作、惩治权利滥用成为现实。从法理上看,唐代的主婚人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为现实生活中青年男女婚姻自由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法律环境。
对礼法上的所谓“媒妁之言”,唐代立法者也首次从法律上加以确认和规范。唐代关于媒妁的立法规定,主要集中在唐律之中。《唐律疏议·名例》“略和诱人等赦后故蔽匿”条疏:“嫁娶有媒。”《唐律疏议·户婚》“为婚妄冒”条疏:“为婚之法,必有行媒。”《唐律疏议·户婚》“嫁娶违律”条规定:
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未成者,各减已成五等。媒人,各减首罪二等。
法律规定,婚姻的成立必须要有媒人参与,媒人在这一过程中起必要的辅助作用,对违法婚姻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媒妁制度的建立,有两个重大的社会意义:一是极大地提高了媒人的社会地位,能有效地激发媒人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为国家的婚姻政策服务;二是能够有效地提醒和督促媒人谨慎小心地严格依法从事活动,避免出现大量的违法婚姻。
唐代的婚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立法规定。唐太宗时期法律规定的结婚年龄是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唐代第一次关于结婚年龄的立法是在唐初。贞观元年(627)唐太宗颁布诏令:
昔周公治定制礼,垂裕后昆,命媒氏之职,以会男女。……宜令有司,所在劝勉,其庶人男女无室家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皆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若贫窭之徒,将迎匮乏,仰于亲近乡里,富有之家,裒多益寡,使得资送。……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婚姻及时,鳏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导劝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附殿。③
到唐玄宗时期,法律规定的结婚年龄较以前有所降低,为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④。唐代关于婚龄的两次立法规定,在立法目的上是有所不同的。前一次规定,更多的是强调一种义务,为保证男在二十岁、女在十五岁之前都能及时婚配,法律建立了一个以政府、亲近乡里、富有之家为义务主体的法律责任保障体系来保证法律的有效实现。后一次立法规定,则更多的是强调一种资格,即到了这一年龄,才能婚配。从这个意义上看,后一次立法实际上是对前一次立法实践成果的一种法律上的重新确认。
唐代立法严格维护礼法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禁止有妻再娶,违者视为违法,不仅得不到法律的承认,还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唐律疏议·户婚》“有妻更娶”条规定:
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
【疏】议曰:
依礼,日见于甲,月见于庚,象夫妇之义。一与之齐,中馈斯重。故有妻而更娶者,合徒一年。“女家减一等”,为其知情,合杖一百。“若欺妄而娶”,谓有妻言无,以其矫诈之故,合徒一年半。女家既不知情,依法不坐。仍各离之。称“各”者,谓女氏知有妻、无妻,皆合离异,故云“各离之”。问曰:有妇而更娶妇,后娶者虽合离异,未离之间,其夫内外亲戚相犯,得同妻法以否?答曰:一夫一妇,不刊之制。有妻更娶,本不成妻。详求理法,止同凡人之坐。
唐代关于结婚禁止条件的立法较为严密,从全面确认和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到治理官吏均有所涉及,内容十分丰富。这其中有些是科学的、合理的,如同宗共姓不得为婚;唐代则首次将同姓不婚引之入律。《唐律疏议·户婚》“同姓为婚”条:“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并离之”。此后,历代封建法律均有此规定,但处罚有所减轻。
在我国古代,最初同姓都有血缘关系,之所以在同姓之间禁止通婚,除伦常关系之外,还有生理上的考虑,即为了避免对子孙后代健康产生有害的影响。但随着人口增长,姓日渐增加,姓的变化也多了起来,越到后来,同姓之间未必都有血缘关系。特别是到了唐代,姓的变化更为复杂,有的姓是皇帝赐的,有的姓是因避讳、畏罪等原因而改的,这些都使得姓与血缘没有了必然的联系,同姓可以不同祖,也可以不同血缘。唐律如果仅仅如律条所规定的那样,在法律适用上不做任何限定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法律在此简单地沿袭过了时的古制,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其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很难实现的。
但事实上,唐代的立法者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姓与血缘之间的现实联系:
然古者受姓命氏,因彰德功,邑居官爵,事非一绪。其有祖宗迁易,年代寖远,流源析本,罕难推详。至如鲁、卫,文王之昭;凡、蒋,周公之胤。初虽同族,后各分封,并传国姓,以为宗本,若与姬姓为婚者,不在禁例。其有声同字别,音响不殊,男女辨姓,岂宜仇匹,若阳与杨之类。又如近代以来,特蒙赐姓,谱牒仍在,昭穆可知,今姓之与本枝,并不合共为婚媾。其有复姓之类,一字或同,受氏既殊,元非禁限。⑤
因此,他们用限制解释的法律解释方式对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适用做了狭于其字面含义的限定性修改。“同宗共姓,皆不得为婚。违者,各徒二年。”⑥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法律所禁止的只是同宗共姓者相互为婚,对同姓但不同宗者相互为婚,法律不作禁止。⑦有些则是落后的、封建的,如祖父母、父母、丈夫死后三年内不得为婚。《唐律疏议·户婚》“居父母夫丧嫁娶”条:
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知而共为婚姻者,各减五等;不知者,不坐。若居期丧而嫁娶者杖一百,卑幼减二等;妾不坐。
(二)婚姻的效力
唐代关于婚姻的效力集中体现在婚约的法律效力上。对婚约的法律效力,唐代十分重视,把它视为婚姻成立的一个部分。唐代法律规定,婚约有两种形式:一是婚书,二是聘财,其中以婚书为原则,《唐律疏议》卷13《户婚》“许嫁女辄悔条”规定:
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娉财,亦是。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后娶者知情,减一等。女追归前夫,前夫不娶,还娉财,后夫婚如法。
【疏】议曰:
“许嫁女已报婚书者”,谓男家致书礼请,女氏答书许讫。“及有私约”,注云:“约,谓先知夫身老、幼、病、残、养、庶之类”,“老幼”,谓违本约相校倍年者;“疾残”,谓状当三疾,支体不全;“养”,谓非己所生;“庶”,谓非嫡子及庶、孽之类。以其色目非一,故云“之类”。皆谓宿相谙委,两情具惬,私有契约,或报婚书,如此之流,不得辄悔。悔者杖六十,婚仍如约。
以聘财为例外。《唐律疏议·户婚》“诸违律为婚”条:
既应为婚,虽已纳娉,期要未至而强娶,及期要至而女家故违者,各杖一百。
【疏】议曰:
“既应为婚”,谓依律合为婚者。虽已纳娉财,元契吉日未至,而男家强娶;及期要已至吉日,而女家故违不许者:各杖一百得罪,依律不合从离。
婚约的订立一般要经过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唐代社会生活中大量使用的婚书,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格式,亦即由通婚书、答婚书两部分构成。关于婚书的普及化和格式化,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件敦煌所出的唐代婚书样文⑧中得到验证。
通婚书:
某顿首顿首。触叙既久,倾瞩良深(如未相识即云:久籍徽猷,未由展觌,倾慕之至,难以名言)。时候伏惟某位,动止万福,愿馆舍清休(如前人无妻即不用此语),即此某蒙稚免,展拜未由,但坤翘称重(原文如此,恐有误)。谨奉状不宣。某郡姓名 顿首顿首。
(别纸)某自第几男(或弟,或侄某某),年已成立,某有婚媾。承贤第某女(或妹、侄女),令淑有闻,四德兼备,愿结高媛。谨同媒人某氏某乙,感以礼请月正。若不遗,伫听嘉命。某自。
答婚书:
某顿首顿首,久仰德风,意阙披展(如先相识即云:求展既久,倾慕良深),忽辱荣问,慰沃逾增。时候伏惟某动止万福,原馆舍清休(前人无妻即不用此语),即此某蒙稚免。言叙未由,但增企除,谨奉状不宣。某郡姓名顿首顿首。
(别纸)某自第几女(或妹、侄、孙女)年尚初笄,未闲礼,则承贤第某男(弟、侄、孙)未有伉俪,顾存姻好,愿托高媛。请回媒人某氏,敢不敬从,某自。
其内容包括:(1)主婚人与婚姻当事人的身份关系;(2)婚姻当事人的个人情况;(3)结婚的意愿表示;(4)媒人的姓名。法律非常重视婚约的约束力,婚约一经订立,任何一方均不得反悔,违者,要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违反婚约的法律责任主要有三种:(1)毁约责任;(2)妄冒责任;(3)违期责任。法律认可婚约因一定的原因而解除。
唐代的婚姻立法严格维护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封建伦理纲常,妻子无论是在人身关系上⑨,还是在财产关系上⑩都依附于丈夫。
(三)婚姻的终止
婚姻的终止有两种方式:第一是婚姻的自然终止,第二是离婚。唐代的离婚立法相当完善,对离婚的方式、程序、原因以及法律后果均作有相应明确的规定。从立法对离婚意志的支配来看,法律规定了两种离婚方式:一是强制离婚;二是协议离婚。依行为主体的不同,强制离婚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别:一是官府强制离婚,即“义绝”;二是丈夫强制离婚,即“七出”。
关于“义绝”,法律不仅颁布了适用条件,而且从司法程序上作了严格规定。《唐律疏议·户婚》“义绝离之”条:
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
【疏】议曰:
夫妻义和,义绝则离;违而不离,合得一年徒罪。离者,既无“各”字,得罪止在一人,皆坐不肯离者;若两不愿离,即以造意为首,随从者为从。皆谓官司判为义绝者,方得此坐;若未经官司处断,不合此科。
“义绝”必须经过官府依法认定,才能生效。一般情况下,必须由当事人自行起诉,官府才予认定;他人告发,官府大都不予认定。但在特殊情形下,他人告发也可认定。
唐代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对礼制上的“七出”进行了确认和调整。《唐律疏议·户婚》“妻无七出而出之”条规定:
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杖一百。追还合。若犯恶疾及奸者,不用此律。
【疏】议曰:
伉俪之道,义期同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不合出之。七出者,依令:“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若无此七出及义绝之状,辄出之者,徒一年半。“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谓:一,经持舅姑之丧;二,娶时贱后贵;三,有所受无所归。而出之者,杖一百。并追还合。“若犯恶疾及奸者,不用此律”,谓恶疾及奸,虽有三不去,亦在出限,故云:“不用此律”。问曰:妻无子者,听出。未知几年无子,即合出之?答曰:律云:“妻年五十以上无子,听立庶为长。”即是四十九以下无子,未合出之。
唐代法律上的“七出”与汉代礼制上的“七出”,在顺序和名称上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既是唐代社会经济发生变化的必然,又是唐代立法技术向前发展的结果。唐代对“七出”进行系统立法,从法理学上看,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汉代的“七出”是习惯法,唐代的“七出”是成文法,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成文法较之于习惯法,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权益。
唐代婚姻立法还建立了和离制度,即允许夫妻双方就是否离婚进行协议,对于达成一致而离婚者,法律不追究责任。《唐律疏议》卷14《户婚律》“诸犯义绝者离之”条的后一款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疏议对其阐释说:“‘若夫妻不相安谐’,谓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不坐”。唐代关于和离制度的设计,已经完全进入民事立法领域,成为中华法史上的一个亮点。但从立法技术上看,法律关于和离的规定因过于原则和抽象,暴露出明显的法律漏洞。
从法律实践上看,唐代的婚姻立法在社会生活中基本上得到了较好地实现。离婚后,夫妻关系归于消灭,由此会在身份、财产等方面产生一系列法律后果。唐代立法由于时代的局限,对此没有做相应的明确的规定,应该来说,是立法上的一个盲点。
通过法理分析和实践考察,可以看出,唐代的婚姻立法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唐代的婚姻立法,不仅系统地总结了唐以前历代王朝的立法和司法经验,而且完整地体现了唐代统治者的立法思想和原则,充分地表现出唐律“一准于礼”的典型特征。第二,唐代婚姻立法具有明显的两重性。许多法律条文中既有专制的、落后的、保守的成分,又透露出些许自由的、先进的、开放的气息。第三,唐代婚姻立法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性。第四,唐代婚姻立法在立法层面上有着明显的不平衡性。一方面,从立法技术上看,唐代婚姻立法十分成功地运用了列举式和概括式相结合的立法手段,极大地增强了法律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在立法内容和立法体例上有着显著的缺陷,在许多领域存在着立法空白,在体例上也没有摆脱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传统立法模式的束缚。第五,唐代婚姻立法是国家的统一立法,不是地方的分散的立法,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适用。第六,唐代婚姻立法是固有法而不是继受法,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环境中诞生并成熟起来的,并没有受到外来法系的影响。
二、唐代婚姻立法的历史地位
通过以上法理分析和实践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唐代的婚姻立法,无论是在立法思想上,还是在立法技术上,都表现出其先进性,代表了中国古代婚姻立法的最高水平。
(一)立法思想的先进性
以“援礼入法”为主,兼及“缘情立法”,是唐代婚姻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它充分体现了唐代婚姻立法的先进性。
1.援礼入法
唐代的立法活动以成文法的形式加以确认和规范,很显然是注意并认识到了法制与礼制在法律上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有国家强制力来保障其实施的社会规范,它反映的是国家和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意志。而礼制则不然,它只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其实施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人们内心信念来保证,礼在特定条件下还会成为对抗法律和破坏国家整体利益的力量。因此唐代立法者公开宣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而要让那些对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有重要意义的礼制原则和精神成为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并取得刑罚的支持和保护,就必须经过国家的立法活动使之上升为法律规范。
唐代婚姻立法将礼法上的原则规定和精神制度化、法律化,主要集中在结婚和离婚两个方面。在唐以前,结婚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这只是传统礼制上的一种要求,而不是真正法律意义上的要求,是以对其进行保护和规范,只能依靠社会道德舆论和人们内心的认同感来维持。唐代立法者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首次将其制度化、法律化。
就离婚而论,“七出”和“义绝”虽然在汉代的社会实际生活中已经起到了类似法律的作用,但终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规范,既缺乏法律应该具有的可操作性、规范性,也缺乏具体的法律保证和约束。一直到了唐代,才真正将其制度化和法律化。
无数事实表明,将习惯法的礼法规定上升为经由国家立法机构制定的成文法,并非一蹴而就。
首先,要有一个审查和取舍的过程。其判断的标准自然超越了习惯法原有的立法价值和取向,取而代之的,是整个国家的实际社会需要,是否符合国家和社会的根本利益成为立法判断的最高标准。
其次,立法对礼法的规定有一个重大的修改,以使其符合法律的内在要求。唐代婚姻立法对礼法上的规定的修改是全方位、多层面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扩大了主婚人的范围,用主婚人制度取代了自西周以来的“父母之命”,主婚人范围由礼制上的父母扩大到整个期亲范围,变相地赋予了婚姻当事人一定的婚姻自主权。二是根据社会的现实需要,变相地抑止了礼法极力主张的寡妇守志行为,肯定和鼓励寡妇再嫁。三是在婚姻的禁忌方面,对同姓不婚作了重大修改,代之以同姓同宗不婚。四是对“七出”的内容和顺序都做了调整和修改。如将礼之“不顺父母”修改为律之“不事舅姑”,无子、淫、口舌、盗窃的位置前移和妒忌、恶疾位次退后等。这些重大修改,均是根据社会实际需要做出的。
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我们认为唐代的婚姻立法实际上是以国家社会义务为立法特征而不是以家族利益为特征的。
2.缘情立法
如果说,唐律“援礼入法”意义在于将传统的礼法制度化、法律化,那么,“缘情立法”则是唐代婚姻立法的开创之举。唐代婚姻立法的“缘情立法”,首先体现在主婚人制度的确立上。唐律对主婚人制度的确任和规范,为唐代青年男女婚姻自由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法律环境。因为在主婚人制度下,法律排除了除父母、祖父母以外的任何人单方面决定子女婚姻的权利,这无异于赋予了男女一定的婚姻自主权。同样,法律认可卑幼在外的事实婚姻,实际上是承认出行在外的青年男女有某种程度的婚姻自主权的,这等于是为青年男女挣脱礼法的束缚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
唐律关于“寡妇欲守志者改嫁”的规定,也带有较重的人性化色彩。唐律规定非女之祖父母、父母强迫其改嫁判处徒刑一年,这就等于宣称女之祖父母、父母强制寡妇改嫁不必受刑罚处罚。同样,唐律只禁止期亲尊长强制欲守志者改嫁,并没有禁止不欲守志者自由改嫁,也没有禁止期亲尊长强制非欲守志者改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实际上是在默许甚至鼓励寡妇改嫁,唐律所蕴含的情感因素是不难体会的。
从汉唐“七出”的比较上,更可以看出唐律的情感因素。从具体的内容来看,汉代的“七出”只规定了七种出妻的条件,却没有相应的程序规定。唐代“七出”则规定了严格的程序。而程序法是实体法得以公正、合理适用的前提和保障。程序违法很可能导致结果的不公正,故法律一般视之为无效,当事人有权就此提起诉讼。唐代设有程序法,显然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权益,这既是法律公正的需要,也体现了立法者的情感因素。同样,汉代“七出”逐项陈述了应出之理由,而唐代“七出”却未就应出之理由做出陈述,究其原因,前者的指导思想是妇女犯“七出”者,除非碍于“三不去”都应“出”;后者的指导思想则是妇女犯“七出”者虽可“出”,但不一定非“出”不可。唐律对妇女的保护,显然是掺杂有同情弱者的因素。
此外,唐律在规定“义绝”的同时,又强调轻微的行为须当事人自己告诉才受理,法律在这里实际上就为夫妻修补情义、恢复感情提供了条件,给予当事人一个重新改过的机会,这也就为原本冰冷无情的法律抹上了一层浓厚的温情色彩。
(二)立法技术的先进性
从立法技术上看,唐代婚姻立法十分成功地运用了列举式和概括式相结合的立法手段,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法律的可操作性,在中国古代婚姻立法上处于领先地位。
1.从主婚人制度和媒妁制度的确立看立法技术的先进性
唐代立法者将礼法上的“父母之命”法律化、制度化,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主婚人制度,不仅反映了唐代立法者是以礼作为婚姻立法的重要指导思想,而且表明唐代统治者在立法技术和经验上已经相当成熟。从西周时期对主婚权的调整和规范到唐代对主婚人的调整和规范,是立法技术上的一次重大飞跃。“父母之命”作为一种权利,从法律上是很难对其进行约束和规范的,更不用说课以法律责任,因为权利是不可能成为法律责任的承担者的。唐代主婚人法律制度的建立,较好地解决了这一法律上的难题。作为主婚权这一权利的主体,主婚人从权利的背后走进了法律的调整范围,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不仅使得主婚权的权利内容有了明确的主体归属,而且使得建立一个法律责任体系来保证权利的依法运作、惩治权利滥用成为现实。
唐代立法者对礼法上的“媒妁之言”首次从法律上明确地加以确认和规范,建立了媒妁制度。唐代婚姻立法在媒妁制度上的先进性突出表现在对在违律为婚的媒妁的处理上。唐代立法不仅较为科学地界定了媒妁在违律为婚这一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地位,而且较为科学地规定了相应的量刑处罚体系。在婚姻成立过程中,媒妁作为一个中间人,根本无权就是否嫁娶、何时嫁娶等婚姻实质性问题做出任何决定,他在婚姻成立过程中的活动必须通过主婚人的行为和意志来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在违律嫁娶这一共同犯罪行为中,媒妁的地位始终是从属于主婚人的,其犯罪行为也是依从于主婚人的犯罪行为而起作用的。按照现代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理论及其实践,媒妁当以从犯论处。对于从犯,没有独立的处罚原则,应当比照主犯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唐律关于媒妁的认定和处罚,是与现代刑法相一致的。《唐律疏议·户婚》“嫁娶违律”条规定:“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未成者,各减已成五等。媒人,各减首罪二等”。法律在此实际上是确认了媒人的从犯地位,对其处罚比照主犯(首罪)减轻二等,与此同时又根据违律婚姻是否完成、是否已经造成了危害社会的结果的量刑情节分别处罚,这些都是与现代刑法理论相符的,表明唐代的立法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2.从对违律为婚的处理和“七出”顺序的变动看立法技术的先进性
唐代婚姻立法在对结婚的禁止条件进行立法时,不仅确定了违律为婚的概念及总的处罚原则,而且不厌其烦地列举了种种具体的违律为婚行为,并区别具体情形,分别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条款,从而在为执法者提供了具体的裁量依据的同时,也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行动指南。
与汉代“七出”不同,唐代“七出”将“无子”提到首位,淫佚、口舌、盗窃的位次也前移,嫉妒后移,恶疾退至最后。唐律这一变动,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看,有利于唐代婚姻立法更趋于圆满和严谨,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律漏洞的出现。唐代立法者极其重视封建家庭于国家的意义,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家庭秩序,唐律精心营造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唐律疏议·名例》篇疏明确宣称:“刑罚不可弛于国,笞棰不得废于家”。“十恶”重罪之中有五项是有关家庭伦理和秩序的。唐律极力维护尊长在家庭中的绝对权威,而其所确认的尊长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因为整个封建家庭的伦理秩序是以男尊女卑和长幼亲疏原则构建的。无子、淫佚、口舌、盗窃均是对唐律极力维护的封建家庭伦理秩序的严重破坏,因此,如不从法律上做一些调整,加重处罚,就会忽略法律在这方面对封建家庭的保护存在着重大安全隐患,也与整个立法意图和立法体系不相协调,从而形成这方面的法律漏洞。唐律意识到这一点,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这本身就是唐代婚姻立法在立法技术上的一种成熟和先进的表现。
三、唐代婚姻立法的基本特征
唐代的婚姻立法,不仅系统地总结了唐以前历代王朝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而且完整地体现了唐代统治者的立法思想和原则,集中地表现出唐代婚姻立法“援礼入法”和“缘情立法”的特征。
(一)鲜明的封建伦理性
唐代法制建设以儒家学说为基本的指导思想。区别亲疏嫡庶,重视封建伦理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唐律所贯穿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些均在唐代婚姻立法中得到了具体落实。鲜明的封建伦理性也就成为唐代婚姻立法的重要特征。
1.结婚立法上的封建伦理性
唐代结婚立法上的封建伦理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主婚权问题上,依照血缘亲疏确定主婚人的范围、顺序和权利之大小。其次,在结婚对象的选择上,严格以封建伦理标准来衡量。不仅同宗同姓不能结婚,而且有服制关系的外姻、尊卑也不得为婚,甚至即使是没有服制关系的外姻尊卑也不得为婚。违者,其结合一律无效,须强制解除,并依服制之亲疏远近施以刑罚处罚,服制越亲,处罚越重。最后,结婚的时间不得与伦理纲常相冲突:祖父母、父母、夫丧时不得为嫁娶,祖父母、父母被囚禁期间,也不得从事嫁娶活动,违者,即构成“不孝”、“不义”,列入十恶重罪,与对抗国家、危害社稷等同看待。此外,法律还规定在父母丧期内,不得为人主婚,违者严惩。
2.离婚立法上的封建伦理性
封建伦理是离婚的法定标准。如果说结婚立法是为了预防对纲常伦理的破坏,那么唐律关于离婚的立法,则是对违反纲常伦理的严厉制裁。“七出”之法的七项内容,无一不是与家族密切相关,无一不是为了家族利益。无子、不事舅姑是妻子对封建纲常的直接侵犯,不论有无过错,都构成了丈夫单方面休妻的理由。妻虽有“七出”之由,但如果“经持舅姑之丧”,则丈夫不能离之。官府强制离婚的“义绝”,夫妻之间以及双方五服以内的亲属有殴、杀伤、詈、奸等情事时,虽会赦也为义绝,必须离异。可见,封建伦理道德直接决定着夫妻双方婚姻的存亡,即使夫妻双方恩爱和谐,但面对七出、义绝,只能是“忍痛割爱”,无可奈何地任其棒打鸳鸯了。
(二)严格的等级特权性
儒家学说的另一重要内容是等级思想,为具有不同身份的人设定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男尊女卑,长幼有序。唐律也贯穿了这一等级原则,而婚姻立法则使之进一步地具体化了。
“凡是同居之内,必有尊长。”尊对卑享有特权,长对幼享有特权,夫对妻享有特权,男对女享有特权,尊、长、夫、男与卑、幼、妻、女同罪不同罚。尊卑长幼之间,家长对子女有婚姻决定权、财产处分权、不听教令之惩罚权。尊卑之间发生殴、杀伤之行为,准“五服”制罪。以卑犯尊,较凡人加重处罚;以尊犯卑,较凡人减轻处罚。
夫为妻纲被进一步强化。妻未经夫允许不得擅自离去,违者,视为犯罪,施以刑罚处罚。夫妻相犯,妻犯夫,实行加刑主义;夫犯妻,实行减刑主义。在诉讼行为上,妻不得告夫,虽属实,也要受刑罚处罚。夫死三年内,妻不得改嫁。
在男女之间,妇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始终处于从属地位,适用法律男女有别,男女双方已订婚,如女方反悔,杖六十;而男方反悔却不追究刑事责任,只是丧失聘财而已。
良贱鸿沟不得逾越。唐律除赋予官员人身、尊严、财产等特权外,还严格区分良贱,使良贱等级分明,不仅在刑罚上同罪异罚,即便是婚姻家庭方面的民事事宜,也只能在各自所属的阶层中开展,不得逾越良贱鸿沟:禁止良贱通婚。良贱互婚,不仅要受到相应的杖刑、徒刑等法律处罚,而且所缔结的婚姻必须解除,恢复其原有的贱民身份。
(三)突出的内在矛盾性
1.唐代的婚姻立法具有明显的两重性
唐代的婚姻立法在许多律文中既有封建专制的、落后的、保守的成分,又透露出些许平等、自由、开放的气息。
从对种种违律为婚的界定及处罚情况来看,有些是合理的,理应限制。如“同宗”、“近亲”不得为婚等项;有些则从维护社会的安定及婚姻的严肃性出发,也符合人们的意愿,如对“与逃亡妇女结婚”、“欺妄婚”、“重婚”、“枉法为婚”的限制和处罚等。有些则是完全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是封建专制思想、家长观念、等级意识、封建伦理对人们婚姻行为设下的人为障碍,如对“良贱为婚”、“父母或丈夫丧期内成婚”的限制和处罚等,则是不合情理的。对礼之“七出”的确认与维护,基本上是出于封建伦理的需要,具有落后性、保守性,而对协议离婚的建立和完善,则又蕴含着某种倡导平等、人性化的因素。
2.唐代的婚姻立法具有内在的矛盾性
唐代的婚姻立法在实践中表现为“礼”与“情”不断发生矛盾冲突。
(1)结婚立法上的矛盾性。唐代结婚立法的矛盾性突出表现在主婚权的确认和规范上。法律一方面极力确认和维护尊长对子女婚姻的决定权;另一方面却又承认外出子女的事实婚姻具有对抗尊长主婚权利的效力。一方面依礼法之精神,对寡妇守节的行为给予保护;另一方面又根据社会和人性的需要,对寡妇守节的行为从法律上予以抑止,强调祖父母、父母可以强制寡妇改嫁。
(2)离婚立法上的矛盾性。唐代离婚立法的矛盾性,突出表现为“七出”与协议离婚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七出”制极力维护夫权在解除婚姻关系中的统治地位,注重并强调家庭利益,忽视和淡化夫妻情感;另一方面,协议离婚又承认感情婚姻,允许夫妻因感情不和而和离,并为此舍去一贯所采用的刑事立法手段。正是法律上的这种双重承认,不仅导致唐代离婚事件的频繁发生,而且使得离婚形式多样化。
唐代离婚立法的矛盾性,还表现为“七出”制本身就含有一对抗因子:习惯法与成文法。唐代的“七出”制,以礼为灵魂,以律为载体。如此一来,礼之“七出”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就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而礼之“七出”作为一种习惯法,本身就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这就势必对律之“七出”这种成文法的确定性产生冲击,于是习惯法与成文法之间固有的对抗性因素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被激活出来,造成唐代出现大量依礼不依法处理离婚问题的现象。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唐代是中国古代礼法关系、情法关系矛盾较为突出的时代。“一方面儒家德治、礼治思想作为治国治民的基本方针,对各项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统一的中央集权确定,制度较为完备,国力较为强盛,更需要强化国家政治统治对社会的渗透,司法制度上的国家主义,首当其冲,成为统治者规范社会的第一目标。这样,重亲情封建伦理的礼与以维系政治统治目的的法律之间的冲突无可避免,且愈演愈烈”。张晋藩先生的分析是十分中肯的。
四、唐代婚姻立法的主要缺失
唐代婚姻立法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体例上,均表现出明显的缺失。
(一)立法内容的不完整性
从立法内容来看,唐代的婚姻立法在许多领域存在着立法的空白。(1)唐代的婚姻立法没有设立婚姻登记管理制度。唐代婚姻关系的成立,无须进行审查和登记,只要订有婚书或女方接受聘财,就算有婚姻关系,故无法从源头上杜绝违律为婚的现象,唐律强制违律为婚者离异,并处以惩罚,只能算是一个事后补救措施。(2)在程序法上有很大的空白。法律虽然详细规定了违律为婚和义绝的处罚原则,但却没有明确规定对这类行为是按照何种法律程序进行追究和审判,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法律的严肃性,进而影响法律的实现。(3)受时代等客观因素制约,唐代婚姻立法未能就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问题进行明确的规定。依现代民法学理念看,当属重大缺陷,可谓立法上的一大盲区。因为现代婚姻法均把这两项视为是立法的重点。但在周秦以降的中国古代,这两项却都不成其为问题。子女的归属,依礼按照惯例,都是归男方,女方对此无权争议。关于财产,女方根本无权参与对男方家财的分割。
(二)立法体例的含混性
从立法体例上看,唐代婚姻立法不仅没有摆脱传统立法体例的束缚,反而同自身所处的母体唐律一样,成为中国古代传统立法体例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典型。受这种诸法合体立法体例的限定,唐代婚姻立法在立法体例上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第一,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其他法律规范相混杂,共存于统一的法典《唐律疏议》之中,所以独立的形式意义上的婚姻家庭法尚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婚姻家庭法虽有所反映,但不充分、不完备,而且是以分散的形式置于法典之中的。
第二,法律规范的功能作用呈单一状态,普遍用刑罚方法作为处理婚姻家庭方面的违法行为的主要手段,刑罚色彩极其浓厚。婚姻家庭关系本属民事关系,理应适用民事立法,但唐代统治者为了保护封建婚姻家庭关系,却采取了刑事立法的调整方式。因此,其精心构建的只是一个以刑事责任为主,以民事责任和经济责任为辅的法律责任体系。首先看刑事责任。无论违法性质严重的违律为婚,还是违法性质很轻的悔婚,唐代婚姻立法对这类行为一律视为是犯罪,视情节之轻重分别处以不同的刑罚处罚。唐代的刑罚制度基本上继承隋制,是以“五刑”为其法定刑种。笞、杖、徒、流、死五种法定刑,按轻重等级,共分为二十等。在法定五刑中,除了笞刑和死刑没有适用外,杖、徒、流等刑罚都适用上了。其次看民事责任和经济责任。其主要责任形式有解除非法的婚姻关系、丧失聘财(聘财不还)、强制履行(婚如约)三种形式。相对于刑事责任来说,民事责任和经济责任具有很强的附属性,也就是说,它们经常是和刑事责任连在一起适用的,很少单独适用。
第三,对婚姻家庭关系的调整并不是很周全的,它把许多问题都委诸礼,对礼的依赖性比较大,因此,礼在社会中的作用仍然比较突出。
此外,唐代婚姻立法是整个国家的统一立法,而不是地方的分散的立法。唐代的婚姻立法是由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唐王朝的中央政府制定并颁布的,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适用。
注释
①刘海年、杨一凡:《中国古代法律知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5页。
②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30页。
③王溥:《唐会要》卷83“贞观元年二月四日诏”条,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527页。
④王溥:《唐会要》卷83“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勅”条,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529页。
⑤⑥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14“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条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62页,第362页。
⑦关于从西周同姓不婚到唐朝同宗共姓不婚的历史变化及其原因,可参见金眉《从同姓不婚到同宗共姓不婚的历史考察》,《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
⑧所引系参考黄永武主编《敦煌丛刊初集》、唐耕耦和陆宏基主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赵和平著《敦煌书仪释录》所载综合而成。
⑨《唐律疏义》卷2“诸妇人有官品及邑号犯罪者,各依其品,从议、请、减、赎、当、免之律不得荫亲属”条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8页。
⑩《唐律疏义》卷20引户婚律“同居卑幼私辄用财者”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66页。
责任编辑梅莉
ReflectionsontheMarriageLegislationintheTangDynasty
Liu Yutang
(National Cultural Industry Research Center,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The marriage legisl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not only systematically summed up the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experience of the previous dynasties, but also embodied the legislative thoughts and principles of the rulers of the Tang Dynasty, which fully demonstrated the typical feature “ceremony rules first” of the Tang Dynasty. There are also obvious dualities in the marriage legisl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i.e., some legal provisions are authoritarian, backward and conservative, however, others have more free, advanced and open components.
the Tang Dynasty; marriage legisl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marriage; effects of marriage; termination of marriage
2017-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