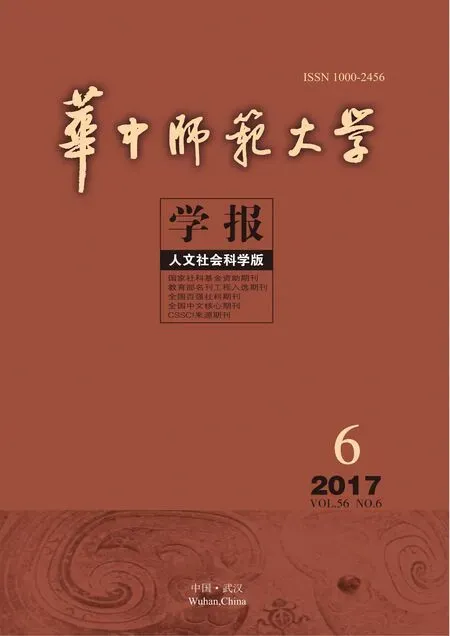限知视角与限制叙事的小说范本
——萧红《呼兰河传》再解读
2017-02-27刘艳
刘 艳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限知视角与限制叙事的小说范本
——萧红《呼兰河传》再解读
刘 艳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呼兰河传》是萧红最后的杰作,也是她文学和艺术上的巅峰之作,从隐含作者、叙事结构、情节性以及限制叙事的可能性,从童心与诗心的意向结构与非成人视角的叙事策略角度,以及如入化境的限制叙事——“我的人物比我高”的层面,可以发现《呼兰河传》的文学性以及其何以成为一部不朽小说的原因所在。《呼兰河传》小说主体层面是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这一类型的叙述潜藏两种不同的叙事眼光:一是叙述者“我”从现在的角度追忆往事的眼光,二是被追忆的“我”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呼兰河传》兼具这两种叙事眼光,而且尤重第二种叙事眼光:既包括有儿童的非成人视角的叙事眼光,又包括固定人物的限制性视角和转换性人物有限视角。这都是隐含作者所采取的叙述行为和方式方法,是令原本缺乏因果链的小说能够情节性强、艺术真实感油然而生的重要原因,同时也令小说更加具备打动人心力量和具有丰沛的文学性。而最真实感人展现童年时家乡的一切、成功地运用儿童的非成人视角的叙事策略,还得益于萧红是一个童心与诗心兼具的作家,而且童年经验作为先在意向结构对她的创作尤其是后期“内观”与“自传体”特征的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第二种叙事眼光所包含的三种叙事视角,其实都在传达和体现萧红对小说学、小说写法的一种认知——“我的人物比我高”,是萧红对小说文体的自觉和一种自觉的创作理念。
隐含作者; 叙事结构; 限知视角; 限制叙事
2000年前后中国文学界开展了一场“回到文学本身”的讨论,目的是对“纯文学”作有价值的反思,希望能够回到文学创作的本身,强调文学性,但由于这些讨论不关注作品文本的形式,仍然是在思想范围内的一种言说,十几年时间倏忽而过,文学评论仍然更多的是一种思想的评论,还是更多纠结于“写什么”而不是“怎么写”,一众文学性的讨论,总是轻轻点到小说的形式和技巧问题之后,迅速又回到内容的问题。2016年,《文艺报》再度开设专栏讨论,呼吁文学批评“回到文学本体”,让我们从最基本的文学要素——语言、形式、结构等方面——开始,重新探讨作品的价值和问题。但研究者真正能够打开小说形式之窗,窥见小说真正的文学性所在的,还是稀见的。
结合叙事学的方法,从形式分析的角度入手,可以掘开文学本体的裂隙,发现作家作品独特性及其文学性奥秘所在。像萧红,虽以《生死场》名世,但在文学性上,毫无疑问《呼兰河传》才是萧红最为成功的作品,代表萧红文学创作在文学性和艺术性上的最高成就。几乎可以说,没有《呼兰河传》,萧红将不成为萧红,而有了《呼兰河传》,不止成就了创作上天才般的萧红,而且令呼兰这个不起眼的边地小城,成为中国文学版图上为数不多的最为闪耀的地方之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呼兰河传》在文学史上,是曾经长时间被遮蔽的。当救亡压倒启蒙、同时代的作家都在写抗战文学、抗日性的小说和宣传品的时候,萧红写了《呼兰河传》,招致了很多的不理解和批评。茅盾当年为《呼兰河传》所作的序,肯定《呼兰河传》的同时,也给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对于《呼兰河传》的评价、对于萧红的文学史定位,定下了调子:他认为萧红“感情富于理智”,“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而“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①……夏志清虽然认为是“最不可宽恕的疏忽”,但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毕竟没有提到《呼兰河传》也并未加评论。所以林贤治才会这样替《呼兰河传》惋惜:“就这样,萧红成了前后两种不同的文学思潮的牺牲品。”《呼兰河传》曾经长期不被重视,原因是什么呢?除了没有直接表达当时的抗日主题,小说的写法上,也是很特别的,“写法上,没有一个小说家像她如此的散文化、诗化,完全不顾及行内的规矩和读者的阅读习惯”②,不仅如此,茅盾当年作序时就已经很锐敏地指出了也许会有人认为《呼兰河传》非小说的担心:“也许有人会觉得《呼兰河传》不是一部小说”,“他们也许会这样说,没有贯穿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都是片段的,不是整个的有机体。”③但是,检验小说的文学性和艺术性的最好的标准,就是时间。大浪淘沙,历久而留下并熠熠生辉的一定是金子。的确如葛浩文的判断,“文评家们在时空上距战时的中国越远就越认为该书是写作技巧上最成功之作。这一看法,即为此书不朽的最有力例证”④;而夏志清则是先疏忽后赞誉有加,2000年时提到了他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对萧红《呼兰河传》的“最高评价”:“我相信萧红的书,将成为此后世世代代都有人阅读的经典之作。”⑤这些评价,是准确的,但《呼兰河传》到底好在哪里呢?结合叙事学的方法、从形式角度加以分析,就会洞悉端倪。从隐含作者、叙述者角度和叙事结构、情节性以及限制叙事的可能性层面,从童心与诗心的意向结构与非成人视角的叙事策略角度,以及如入化境的限制叙事——“我的人物比我高”的层面,可以发现《呼兰河传》不啻为一部限知视角和限制叙事的小说范本,正是由于萧红在限知视角和限制叙事方面的才华,才令《呼兰河传》文学性独具并使其能够成为一部不朽小说。
一、隐含作者、叙事结构、情节性以及限制叙事的可能性
中国文学自现代以来,凡是作家主体较多融入叙事的小说,往往要么因为作者思想意识侵入小说叙事太多太盛而伤害了小说的文学性,要么多令小说呈现情节性、故事性削减和散文化、抒情性增强的特征,这种情况,自五四时期即已肇始。个性主义思潮和民主自由意识的催生,独白式小说,包括日记体、书信体小说,曾经是五四作家最为热衷和喜爱的小说形式。但是独白的过剩,便是小说情节性大受冲击,很多小说比如《狂人日记》根本无法还原为完整的故事或者改编为讲求故事性、情节性的戏剧和电影。郁达夫、郭沫若、王以仁、倪贻德等人的小说,全以小说结构松散著称,微末之小事,也要大发一通议论,甚至痛得死去活来,他们实在是在夸大并欣赏着、甚至津津有味咀嚼着自己的痛苦,以至于忘却了小说的艺术。作家主体过多地融入小说叙事,对小说形式的伤害是明显和严重的,一个极端的例子,便是郁达夫,在他从《银灰色的死》到《出奔》五十篇左右的小说中,属于自叙传小说的有近四十篇。其小说主人公无论以什么样的身份出场,都熔铸了作家太多的主体形象和心理体验,连主人公的长相、穿着、气质、心理,简直就是郁达夫本人的翻版。郁达夫代表作《沉沦》开篇第一句就是:“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以至于有研究者忍不住说:“关键不在人物的处境是否可怜,而是人物自己是否感觉到自己可怜。小说的焦点一下子从外在的故事情节转为内在的人物情绪。表面上不同于‘独白’式小说,有场景描写,有情节叙述,可这一切都服务于人物的主观感受。”⑥要知道,小说是典型的虚构叙事文本(非虚构作品不在此讨论之列),对虚构性、情节性和可读性有着较强的要求,小说求真求的是艺术的真实。所以有研究者曾经从形式层面这样批评郁达夫:“小说则需要虚构,如果一个小说文本缺乏虚构则会近于散文,情节性也会几乎丧失,阅读的快感也会弱得多,郁达夫的小说则是这种情况。从形式上看,他的叙述人与人物角色几乎没有距离,距离感的丧失正是缺乏虚构意识的结果,而且感情毫无节制,成为启蒙之初个人欲望的泛滥。距离的丧失也导致了叙事视点转换的稀少,第一人称叙事带来的极端向内转,其实是与个人经验直接相联系,缺乏虚构性的同时也丧失了叙事的丰富性,最终失去意义层面的丰富性。”⑦
在这种情况下,“内观”的“自传体”型作品,能够在诗化、散文化、抒情性特征之外,葆有很好的情节性、可读性,能够避开将作家主体过多融入叙事的窠臼,具有充沛的文学性,是非常不容易的,将之置于新文学发展的谱系,就更加能够理解这种难得和罕有。萧红做到了,而且显示了她非凡的文学才华。她后期作品的《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家族以外的人》《后花园》等,虽然也是带自传体特征的小说,但却同时也是她最成功、最感人的作品。《呼兰河传》被葛浩文称为是萧红“巅峰之作”、“她那注册商标个人‘回忆式’文体的巅峰之作”。她以极为细腻的笔法回溯往事,几乎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就将小说的散文化、抒情性与小说的情节性、可读性和一定的虚构性并置,几乎形成一种“萧红体”。这一切,都得益于萧红高超的小说叙事能力和叙述的手法。
其实,已经有人约略意识到了萧红《呼兰河传》所呈示的这种繁富多姿的叙事能力,但尚未有人来得及细究根底。茅盾在作序时,其实对此是有察觉的,他说:“也许又有人觉得《呼兰河传》好像是自传,却又不完全像自传”,“但是我却觉得正因其不完全像自传,所以更好,更有意义”——他意识到了《呼兰河传》不完全像自传,而且也感觉到了这不完全像自传更好更有意义,但为何不像,他并没有深究。他甚至也意识到了:“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⑧但茅盾并没有深究,这“不像”之外更为“诱人”的东西,到底是如何产生的?而且萧红《呼兰河传》小说叙事的魅力,在同样带“内观”“自传体”特征并且具有诗化、散文化和抒情性的小说中,是达到极致和巅峰状态的,这又是萧红动用了什么样的叙事能力和叙述行为?他没有进一步思考和分析。葛浩文对萧红的叙事能力和才华,也是有体察的,他也说“这书严格来说,不能算是典型的小说,它大部分牵涉个人私事,叙述性强,但书中却有着像诗样美的辞章,以及扣人心弦的情节”⑨,这句话是对《呼兰河传》小说叙事的一种总结,它所内蕴的矛盾和吊诡之处,恰恰是对《呼兰河传》中叙事魅力的一种呈现。“不能算是典型的小说”、诗化、抒情性,葛浩文的判断是准确的,“大部分牵涉个人私事”,本来就容易影响虚构性、故事性和情节性,但他同时又说它“叙述性强”、书中却有着“扣人心弦的情节”。是什么给他《呼兰河传》叙述性强、情节性强的印象呢?原因就在于萧红运用了非凡的小说叙事技巧,《呼兰河传》的隐含作者,对于小说的叙事结构、叙事节奏、主体行为方式和意义层面等作出了或许出自创作天赋但的确称得上是很精心的安排。小说的叙述者、人物绝对没有成为作者、隐含作者的传声筒。童心与诗心的情感意向结构,带来的是作家主体成人经验的尽可能多地撤离,在萧红《呼兰河传》这里,“以物观物”的“无我之境”的风景描写,得以呈现。而其所取非成人视角的限制性叙事策略,固定人物有限视角叙事和转换性人物有限视角叙事等,都达到了很好的叙事效果,避免了作者、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人物的一种高度混合性和过于全知叙事对于小说艺术真实感的伤害。《呼兰河传》哪怕是作成人视角的叙事,也往往是取人物限知视角的限制性叙事——“我的人物比我高”(萧红),比如对小团圆媳妇婆婆的描写,等等,方才能够在叙事方面,克服郁达夫那种“叙述人与人物角色几乎没有距离”(准确地说是作者、隐含作者与叙述人、人物几乎没有距离)、人物沦为作者和隐含作者传声筒的弊病,令小说产生足够的艺术真实性和可读性。
传统的批评往往将全知叙述者与作者等同起来,而结构主义叙述学则倾向于排斥作者,将全知叙述者视为一种结构体或表达工具。将现实中的作者等同于叙述者,的确是不合适的,而真实作者和叙述者之间,被引入了“隐含作者”的概念,这一概念最早是由韦恩·布斯在1961年出版的《小说修辞学》一书中提出。所谓隐含作者,就是读者从作品中推导和建构出来的作者的形象,是作者在具体文本中表现出的“第二自我”。在有的研究者看来,“隐含作者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叙事学理论发展到后经典叙事学之后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改变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经典叙事学过于形式化的特点,把意义分析与形式分析相结合,相当好地解决了文学的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问题。后经典叙事学的特点类似于把马克思主义代表的意识形态批评与罗兰·巴特等人代表的叙事学相结合,成为一种更有效的文学文本分析方法。”⑩隐含作者不同于真实作者,是作者在文本中的“第二自我”,决定着文本的叙事结构及文本所遵循的价值观和文化规范,他负责场景和事件的选择和组合,即整体叙事结构、叙事节奏、主体行为方式和意义层面等各方面的安排。同一个作家在不同的作品中,可能而且几乎一定表现为不同的隐含作者,因为他们在创作不同的作品的时候其状态、创作理念等都会有所不同。这样的情况在萧红身上,可能表现得更加显著。《呼兰河传》的隐含作者与《生死场》的隐含作者,迥然有异,因为创作两部作品时,萧红的状态是不同的,尤其是她对“小说学”——小说写作与小说文体的理解,差别很大,况且又是面临不同的题材,在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等方面,两部作品也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生死场》中的隐含作者,是一个受“抗日义勇军”战士萧军影响,很想通过写农民生活表达出“抗日”主题、希望启蒙民众和表达抗日爱国思想的知识者。小说是一部描写“九一八事件”前后哈尔滨近郊农村农家生活的一部小说。虽然同样是描写农村和农家生活,但隐含作者的目的性非常明显而且强烈——她要通过描写家乡农民在生死边缘挣扎的情况而写出他们反日斗争的觉醒过程。主题的先行设定和缺乏对农民实际抗日过程的了解——甚至她小说中所提到的少数几个抗日组织的名称,都是她从萧军和其他朋友口中听来的,加上启蒙和救亡的心情过于迫切,又恰逢萧红小说写作相对来说还是起步的阶段,写作受他人影响和模仿的痕迹都在。《生死场》中,隐含作者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的层面,从上而下悲悯她的人物的。在小说的叙事结构和素材的处理上,都比较粗疏,小说结构比较松散,题材和情节处理,都是尽量选取将“生”和“死”尤其是“死”,加以最有视觉冲击力的描写和展现,要以十二分的笔力写出外来的暴力压迫和男性对女性的戕害和压迫……用力太过,对文学性反而是伤害,这些方面在胡风为萧红《生死场》作序时候已经发现:“第一,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全篇现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能够得到的紧张的迫力。第二,在人物底描写里面,综合的想像的加工非常不够。个别地看来,她底人物都是活的,但每个人物底性格都不凸出,不大普遍,不能够明确地跳跃在读者底前面。第三,语法句法太特别了,有的是由于作者所要表现的新鲜的意境,有的是由于被采用的方言,但多数却只是因为对于修辞的锤炼不够。”
与《生死场》一样,《呼兰河传》中没有主要和中心人物,同样是农家、乡间生活题材,素材驳杂,而且根据小说结尾的提示来看,作家选定的叙述人是“逃荒去了”的“小主人”,以一个小孩——未成年人的视角,来写的回溯童年和故乡往昔故事的小说,对作为小说文本叙事世界掌控者的隐含作者来说,就更加是一种考验。对于小说能否具有一种可读性强的情节性,是一种考验,至于达到葛浩文所说的“扣人心弦的情节”的程度,就更加是一种考验。五四作家和现代小说家,一度把淡化情节作为他们心目中当中提高中国小说艺术水准的关键一环,想摆脱故事的诱惑而在小说中寻求新的结构重心。而《呼兰河传》本身的题材和素材,也缺乏具有因果链的情节,缺少有因果关系的故事事件,组成一个有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的整体。具有因果关系的传统意义上的情节,《呼兰河传》里实在缺乏可以滋养它们的土壤。这种情况下,要产生和实际上确实产生了“扣人心弦的情节”,确实颇有些不可思议。虽然中西文学批评家常常在批评实践当中对“故事”和“情节”不加区分,故事和情节常常成了可以换用的概念。但重视结构关系的叙述学家则划出清晰可辨的界限——将情节视为故事中的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呼兰河传》中的“扣人心弦的情节”或许可以从隐含作者对于叙事结构、叙事节奏等的掌控和有关的叙述行为当中找寻答案。《辞海》里对“故事”的定义强调故事中事件的因果关系并把叙事性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混同于故事情节的概念。而英国批评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则认为:“我们已将故事界定为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事件。情节也叙述事件,但着重于因果关系。”这种通过因果关系来区分故事与情节不甚合理、容易导致混乱,但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古典与传统文艺理论都非常强调情节中因果关系的重要性。虽然结构主义叙述学家查特曼将叙事作品的情节区分为“结局性的情节”和“展示性的情节”,但他的“展示性的情节”主要指意识流等现代作品中的情节。从亚里士多德迄今,带事件因果关系的情节一直得到强调和重视。中国自五四开始新小说家们又在有意淡化情节甚至不惜走向强调个人感觉的极致,《呼兰河传》的素材和题材,都决定了无法形成因果链和因果关系的情节。无论是基于故事的层面,还是基于事件形成因果关系的情节方面,《呼兰河传》都不占天时与地利。它所能涉及的故事,甚至不如《生死场》中的故事,可以带给人足够的“震惊”体验,就是那个节奏相对激烈的小团圆媳妇被虐待致死的故事,其实故事性也不强,一旦叙述不当,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乡间轶事,更不要说产生震撼人心的叙事效果。《呼兰河传》整个小说所涉及素材的零零碎碎,也确乎根本无法形成一个有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的整体——具有因果关系的传统意义上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情节”“叙述性强”,我们只能寄望于隐含作者对叙事结构、叙事节奏等的掌控以及她在叙述行为当中所展现的才华,事实上《呼兰河传》的文学性也恰恰归功于隐含作者的叙述行为能力。
仔细研究一下《呼兰河传》的章节设置,就很容易体会隐含作者在叙事结构和叙事节奏等方面的巧心和匠心。小说开篇第一章,以大地冻裂、卖馒头老头跌倒、路人趁机拾了几个一边吃着就走了,而老头子挣扎起来后则以地皮冻裂了、吞了他的馒头自我解嘲来开篇,呼兰的四季风光、民情风俗,隐含作者安排周详,一一尽现。东二道街的龙王庙与祖师庙里的两家小学,西二道街常常让人抬车抬马、并给大家带来吃瘟猪肉借口的大泥坑子,碾磨房、豆腐店、染缸房、扎彩铺,卖着麻花的小胡同,天边的火烧云,等等。“这章不仅是篇研究大自然景色风物的佳构,而且也是对形成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和他们的社会制度的一种注释。”第二章,是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等等,这些呼兰河地方卑琐平凡的实际生活之外的精神上的“盛举”。第三第四章,是小女孩“我”和祖父生活的故事,院子里的各色人等及他们的生活百态。第五章,是小说中似乎可以故事性、情节性最强的小团圆媳妇被虐待致死的故事。第六章,是有二伯的故事,可以与《家族以外的人》作联系和比照,《呼兰河传》中的有二伯,似乎叙写得更加周详和生动有趣。这当然归功于限知视角和限制叙事的成功,后面会再述及。第七章,是磨房里冯歪嘴子的故事,林贤治认为这是小说的“光明的尾巴”,茅盾也在序言中言冯歪嘴子“生命力特别顽强,而这是原始性的顽强”,这章其实可与《后花园》比照阅读。这七章的叙事结构、叙事节奏,素材的剪接和配搭,用葛浩文的话来说,就是:“萧红非常技巧地将每章情节调配得抑扬顿挫,高低有序。时而有令人伤心不已的悲剧章节,瞬时又出现轻松的幽默讽刺场面”;“这七章总体而言,无论在技巧手法上都胜过单一存在。因为此书将呼兰这城镇,也可以说将20世纪早期中国东北的农村社会,置于显微镜下来端详。此书不但让我们大开眼界,而且感人至深。”
叙事结构、叙事节奏等,都是由隐含作者掌控的叙述行为。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1972年在《叙述话语》这一经典叙事学名篇中,曾提出将叙事层次三分法:一是故事,即被叙述的事件;二是“叙述话语”,即叙述故事的话语,也就是文学的文本;三是“叙述行为”,即产生话语的行为或过程,比如讲故事的过程。热奈特反复强调了叙述行为的重要性和首要性:没有叙述行为就不会有叙述话语,也就不会有被叙述出来的事件和情节。叙述行为其实既关及形式,也关及内容、作品的意义。但那时还处于经典叙事学强调形式化的阶段,拒绝把形式明确地与意义相联系。及至后来20世纪80年代,叙述行为在“隐含作者”这一概念那里得到延续,正式把形式层面与意义层面相结合,成为后经典叙事学的一个重要概念……隐含作者掌控所有叙述行为,藉由叙事动因,可以说把形式与内容加以彻底结合了起来,当然,隐含作者还决定了结合的方法。《呼兰河传》中故事性、情节性以及丰富的可读性,要依赖隐含作者对叙事结构和叙事节奏的掌控。而且还远不止于此,小说主体层面是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这一类型的叙述潜藏两种不同的叙事眼光:一是叙述者“我”从现在的角度追忆往事的眼光,二是被追忆的“我”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呼兰河传》中,这两种叙事眼光其实是都具有的,但是,第二种叙事眼光——被追忆的“我”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其中有儿童的非成人视角的叙事眼光,这其中,又衍生出固定人物的限制性视角和转换性人物有限视角,都是隐含作者所采取的最为了不起的叙述行为以及方法,是令小说所描写的人物以及事件真实生动、艺术真实感油然而生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令小说具备打动人心力量和丰沛文学性的关键原因所在。《呼兰河传》的隐含作者,不同于萧红在其他作品,尤其是《生死场》中的隐含作者,正是这个隐含作者,让《呼兰河传》成为限知视角和限制叙事的小说范本。
二、童心和诗心的意向结构与非成人视角的叙事策略
带“内观”“自传体”特征的小说,又是萧红成人后及在离开家乡多年后的一种回溯性叙事,如果是一味地全知叙述和过多地采用叙述者“我”从现在的角度追忆往事的眼光,牺牲的将是艺术的真实感,叙述者和人物会沦为作者、隐含作者的传声筒,郁达夫创作的那种极致状态“感情毫无节制,成为启蒙之初个人欲望的泛滥”,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呼兰河传》的叙述者是后花园的小主人——第一人称“我”,但隐含作者非常恰当地将“我”在小说中直接出现的比例控制到了较小的份额——只占较少的章节,而且很多时候,是取其非成人视角的限制性叙事,达到了很好的叙事效果,避免了作者、隐含作者与叙述人、人物的一种高度混合性和过于全知叙事对于小说艺术真实感的伤害。而且,即便在叙述中“我”没有现身的情况下,叙事眼光和叙事声音往往也是“我”的、非成人的视角和叙事声音,隐含作者安排这样的限知视角和限制叙事,可以最大限度地产生艺术的真实感、带给受述者和理想读者身临其境和感同身受的阅读感受,这其实也是《呼兰河传》在散文性和抒情性之外,同时也是非常好的小说叙事文本的有力佐证。如果将隐含作者采纳限制叙事来还原现场感和产生艺术真实感,放到新文学发展的谱系当中,自然格外凸显其意义和价值。中国古代小说中已见限制叙事的情形,但实在不能与西方现代小说的限制叙事技巧等同。20世纪初西方小说大量涌入中国以前,中国小说家、理论家从未形成突破全知叙事的自觉意识。俞眀震在时人多从强调小说布局意识入手悟出限制叙事时,从柯南道尔选择“局外人”华生为叙事角度,接触到了如何借限制叙事来创造小说的真实感问题。新小说家们很难在限制叙事尤其是通过限知视角和限制叙事方面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一方面想用限制视角来获得‘感觉’的真实,一方面又想用引进史实来获得‘历史’的真实”。以儿童的非成人视角而论,很多研究者注意到了自现代以来,小说家们常有意采用儿童视角叙事。但需要注意的是,小说家设定由作品中人物——一个儿童的口吻来叙述,也并不一定是成功的儿童的、非成人的限知视角和限制叙事。过多受到作家主体干扰的叙事,比比皆是,也就是俗见的“小大人”现象。有很多研究者认为莫言以儿童视角写过不少短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四十一炮》,《四十一炮》以“炮孩子”罗小通的四十一段滔滔诉说结构成篇,莫言是要“想挥霍性地用一下儿童视角,算是一种总结”。但用了一个儿童叙述人,就是儿童视角和限制性叙事吗?似乎并不尽然。儿童叙述人而叙事眼光和叙事声音,并不是儿童的或者受成人视角过多渗透和干预的情况,处处可见。而且,若要想拥有儿童的非成人的限知视角和限制叙事的能力,恐非得具有和儿童能够相媲美至少是相通的思维和情感意向结构才行。由此可见,《呼兰河传》能够在全篇成功运用儿童的非成人视角来叙事,的确不容易。可贵的是,隐含作者不再像《生死场》中隐含作者那样,有着表达启蒙与救亡主题先行的迫切心情,也无意去模仿别人的写作、在作品中刻意填充思想和精神之核。对于童年生活的家乡物事民情风俗的描写,隐含作者的叙述动因,没有一个强大的外部利益关照,即没有一个功利化的创作目的。小说只意在对童年家乡的一切予以最真实感人地展现,这就是隐含作者的叙述动因,这也是我们在小说中看不到深刻地揭露和峻切地批判的原因,作者和隐含作者对文本中所涉及的一切,是怀着理解之同情的。
最真实感人展现童年时家乡的一切、成功地运用儿童的非成人视角的叙事策略,其实还得益于萧红是一个童心与诗心兼具的作家,而且童年经验作为先在意向结构对她的创作尤其是后期“内观”与“自传体”特征的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了儿童的先在意向结构、具备了儿童的思维能力,才令儿童的、非成人视角的限制性叙事,真正地落到实处。童庆炳先生曾提到过童年经验作为先在意向结构会对作家创作产生多方面的影响,笔者在研究中也论述过童年经验以及童年经验作为先在意向结构对萧红创作的影响。《呼兰河传》中,童年经验为小说提供了生活原型和写作题材,它已经作为一种先在的意向结构对作家创作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对作家而言,所谓先在意向结构,就是他创作前的意向性准备,也可理解为他写作的心理定势。根据心理学的研究,人的先在意向结构从儿童时期就开始建立。整个童年的经验是其先在意向结构的奠基物”;童年经验作为先在意向结构的奠基物,影响和制约着萧红面对生活时的感知方式、情感态度、想象能力、审美倾向和艺术追求等。童年经验作为先在意向结构最初却又是最为深刻的核心,而且“由童年经验所建筑的最初的先在意向结构具有最强的生命力”,深刻影响了萧红作品的基调、情趣和风格等,尤其直接关涉和影响着她对于边地人生的女性书写的部分。这点在《呼兰河传》中的表现,就尤为凸出和显著。萧红是有着一颗如儿童一般的赤子之心的,童心与诗心兼具的萧红,自然可以达到相通和使用儿童“我向思维”的思维方式。“我向思维”的特征,是将周围的一切事物等同于有生命的“我”,把物和整个世界都当作有生命的或者说是情感投寄的对象来加以对待,这有点像原始人的思维方式和原始宗教的特点,所以后来的迟子建曾经在《文学的“求经之路”》里讲到了民间神话和原始宗教对自己的影响,鄂伦春和鄂温克民族“这两个少数民族信奉万物有灵,在他们眼里,花、石头、树木等都是有灵魂的”。能够具有“我向思维”的思维方式,恰恰是萧红以及《呼兰河传》的隐含作者能够在叙述行为当中成功使用儿童的限知视角和限制叙事的前提和基础,很难想象一个拥有十足的成人思维方式的人能够使用儿童的叙事眼光和叙事声音。“我向思维”的思维方式,在风景物事的描写里,产生了非常好的修辞效果。《呼兰河传》第一章第8小节里“火烧云”的大段描写,充分展现了儿童“我向思维”特点的叙事眼光和叙事声音:“五秒钟之内,天空里有一匹马”,“忽然又来了一条大狗,这条狗十分凶猛,它在前边跑着,它的后面似乎还跟了好几条小狗仔。跑着跑着,小狗就不知跑到那里去了,大狗也不见了”;“又找到了一个大狮子”,“它表示着蔑视一切的样子,似乎眼睛连什么也不睬,看着看着地,一不谨慎,同时又看到了别一个什么”;“一时恍恍惚惚的,满天空里又像这个,又像那个,其实是什么也不像,什么也没有了”,“必须是低下头去,把眼睛揉一揉,或者是沉静一会再来看”。怀有童心、赤子之心,具备“我向思维”的思维方式,使萧红不会把景物看作与自己拉开距离、仅供自我观照的“他者”或者客体,而是能够打通视觉、听觉、嗅觉等各种感官知觉,把自己和景物融为一体: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703—704页)
在这里,自然与景物,都被赋予了灵动的生命色彩,后花园里的花鸟昆虫、倭瓜、黄瓜、玉米,蝴蝶,等等,都是以儿童的叙事眼光来叙述的,是儿童式的将周围的世界一律加以生命化的做法。可以说,在这段广为大家喜爱和援引的文字里,已经达到了王国维所阐析的“无我之境”的境界。王国维手稿本第33则云:“有我之境,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初刊本对两境的表述略有调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所以学者言两本对勘王国维对两境的理解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只是将两境的“观物”特点作了对比分析,立足于“我”的观物——以我观物,即为有我之境,将“我”物化的观物,或者说淡化“我”的观物——以物观物,即为无我之境。两境都涉及审美主客体的关系,但侧重在对审美主体的要求各不相同。学者还引饶宗颐《人间词话评议》来疏证:“王氏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为二,意以无我之境为高。予谓无我之境,惟作者静观吸收万物之神理,及读者虚心接受作者之情意时之心态,乃可有之……惟物我合一之为时极暂,浸假而自我之我已浮现……以我观物,则凡物皆着我相,以物观我,则浑我相于物之中。实则一现一浑。现者,假物以现我;浑者,借物以忘我。王氏所谓‘无我’,亦犹庄周之物化,特以遣我而遗我于物之中……”(省略号为笔者所加)《庄子·齐物论》中所谓“庄周梦为蝴蝶”而物我不分亦即物我两忘的境界,沈约《郊居赋》的“惟至人之非己,固物我而兼忘”——指艺术创作时候艺术家主体与创作对象的客体浑然为一而兼忘的境界,王国维的“无我之境”,在艺术创作时身与物化,儿童经验的先在意向结构和“我向思维”的儿童思维方式,令这一切成为可能。这其实又是一种成人主体之我和成人经验之我的“淡化”和消褪,风景物事的描写不止可以由此而形神兼备,而且可以避免滑入五四以来现代小说家常常犯的重主体感觉宣泄而轻叙述,乃至郁达夫那种“感情毫无节制,成为启蒙之初个人欲望的泛滥”自叙传特征的小说叙述方式。这只是儿童先在意向结构和儿童思维方式所铸限知视角和限制叙事的一个维度,另一维度,还可以避免五四以来在现代时期,小说家的风景描写,常常是审美主体与外物客体拉开了距离产生的修辞效果——主客体拉开距离后,主体与客体之间,更多是认识和被认识的关系,“所谓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写风景的人“对眼前的他者表示的是冷淡”。外部事物作为客体,是一个被作家观照但却好像跟作家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关系不大的“他者”。以至于有研究者在分析后来《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风景描写时,仍然忍不住指出其透露的情感仍然是那种五四启蒙影响下的小资化情感,却与农民无关,“农村成了被欣赏被塑造的他者,农村风景变成隐蔽地表现小资情怀的场所”。
其实不止是风景的描写,对于物事人情,《呼兰河传》也多采用儿童的非成人视角的叙事策略。小说开篇大地冻裂卖馒头老头跌跤失馒头的细节,大泥坑子的陷马淹猪可以提供“福利”(藉口)给全呼兰河的人心安理得吃着瘟猪肉,那指出是瘟猪肉而挨了两次揍的孩子,小胡同里五个孩子的母亲给他们买麻花而动手追打的戏剧化场面……皆生动、感人,令人印象深刻,回味悠长。如果不是儿童非成人视角的叙事策略,堆积了几年几至发霉的杂物的储藏室,满是花鸟昆虫的后花园,等等,绝没有小说中所叙述得那样生动和富有生趣。扎彩人、跳大神、放河灯、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等民俗事象的表现,也离不开儿童视角里的生活细节的悉数展现。不谙世事的孩子,观察和感受世界的时候,往往能够注意到成人注意不到或者忽略的种种细节,加上儿童非成人视角往往单纯、感性、不事理性概括的特点,常常能够将无数为成人熟视无睹的细节一一突显出来。《呼兰河传》里,萧红就将许多的笔墨花费在以儿童“我”的叙事眼光和叙事声音所讲述出来的小城人许多的生活细节上面。而有些情节,原本缺乏事件因果关系和传统情节需要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完整关系,却由于叙述人是儿童的眼光和心理,而妙趣横生。比如“有二伯偷东西被我撞见了”,“我”也是在藏东西的后房里乱翻东西的,正因为“我”是个孩子,不十分明确和懂得眼前发生的事情,“我”才会津津有味地目睹有二伯偷东西的整个过程,互相发现后,大偷和小偷——有二伯和我,彼此吓一跳……后来偷了大澡盆的有二伯,竟然“就在这样的一个白天,一个大澡盆被一个人掮着在后花园里边走起来了”,“那大澡盆太大了,扣在有二伯的头上,一时看不见有二伯,只看见了大澡盆。好像那大澡盆自己走动了起来似的”。有二伯说自己没有钱,不肯买票带自己看马戏,“我一急就说:‘没有钱你不会偷?’”——只有孩子、非成人,才会有这样的言行和心理与叙事的眼光。
而且,儿童视角的遭遇性、无规划、直接性、随意性和无目的性,反而更容易洞见成人世界的真实,对充斥于成人世界的荒谬、不合理处乃至人性的扭曲,别具一种透视和艺术表现的力度。在萧红的《呼兰河传》里,在“我”看来,“怪好”的小团圆媳妇,在大人们的眼里,却“不像个团圆媳妇”、有病(所谓的病其实是被婆婆吊起来打、用烙铁烙脚心等致)直至要给她洗开水澡,但在“我”看来,她却是没有病的,她还跟我一起玩玻璃球。而当她被婆婆和众人说成是掉了辫子的“妖怪”时候,“我”要说出辫子“是用剪刀剪的”的真相,却被老厨子堵住了嘴。这种儿童的非成人视角的叙事策略,别具人性表现的真实和力度,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严歌苓《穗子物语》系列小说里,又有继承和进一步的叙事探索。比如,《角儿朱依锦》的故事,在通过儿童视角的细节叙述来揭示成人世界的荒谬可憎、人性扭曲方面,与萧红的《呼兰河传》有异曲同工之妙。就像严歌苓在自序中坦言的:“我做过这样的梦:我和童年的我并存,我在画面外观察画中童年或少年的自己”,“当童年的我开始犯错误时,我在画面外干着急,想提醒她,纠正她”,“而我却无法和她沟通,干涉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把一件荒唐事越做越荒唐”,对于童年穗子的种种行为,“成年的我只能旁观”——隐含作者在安排叙述行为的时候,有意地不干涉人物和叙事,反而能够成就儿童的非成人的限知视角和限制叙事。从萧红《呼兰河传》到严歌苓的《穗子物语》,就展现了这种叙事探索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里的呼应和长足发展。
三、如入化境的限制叙事:“我的人物比我高”
如果《呼兰河传》的限知视角和限制叙事,仅仅体现在儿童的、非成人叙事策略的层面,小说断不会包含如许繁富的审美意蕴和文学性、也不会被认为“该书是写作技巧上最成功之作”(葛浩文),而且,这是一部让人读了便感喟不已、被认为越历时将越成为不朽之书的小说。在《呼兰河传》所采取的非成人视角叙事策略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和听到两种不同的视角和声音:儿童叙述者的声音和成人的隐含作者偶尔安排的成年人的视角和声音——两种视角和声音的穿插交错甚至是水乳交融,共同构成了小说文本的复调叙事。在复调叙事的文本叙事结构里面,似乎就是饶宗颐在《人间词话平议》里所说的“惟物我合一之为时极暂,浸假而自我之我已浮现。此时之我,已非前此之我,亦非刚才物我合一之我,而为一新我——此新我即自得之境”。非成人视角叙事策略为主、成人视角与声音为辅,何尝不是小说叙事所缔造的新我自得之境呢?前面已经提到,《呼兰河传》小说主体层面是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这一类型的叙述潜藏两种不同的叙事眼光:一是叙述者“我”从现在的角度追忆往事的眼光,二是被追忆的“我”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呼兰河传》兼具这两种叙事眼光,而且尤重第二种叙事眼光:既包括有儿童的非成人视角的叙事眼光,又包括固定人物的限制性视角和转换性人物有限视角。也就是说,儿童的非成人视角的叙事策略之外,转换性人物有限视角和固定人物的限制性视角,也都是隐含作者所采取的叙述行为和方式方法,是令原本缺乏因果链的小说能够情节性强、艺术真实感油然而生的重要原因,同时也令小说更加具备打动人心的力量和具有丰沛的文学性。
这第二种叙事眼光所包含的三种叙事视角,其实都在传达和体现萧红对小说学、小说写法的一种认知——“我的人物比我高”,是萧红对小说文体的自觉和一种自觉的创作理念。她在1938年与友人的谈话当中已经明确表达了她的这种创作理念,她说:“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鲁迅以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倒应该悲悯我咧!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也不能施之于同辈之间。我的人物比我高”。出于对鲁迅的尊重与敬重,她没有表达她不同意鲁迅小说从高处悲悯人物的写法,但是,她已经表达出了她之不同于鲁迅的小说观和人物观。从高处去悲悯人物的一个直接的效果,便是易将很多思想之核“哽”在小说当中,小说的隐含作者会持有明显乃至太重的功利化写作目的,易使人物变成隐含作者的传声筒、使人物失去其身份及其所应该具有的主体行为特征、思想心理等。思想之核哽在小说里,直接影响小说的文学性,迟子建曾经明确表达她喜欢和乐于点评鲁迅的《社戏》而非其他小说,原因就是:“《社戏》是鲁迅写给自己的一首《安魂曲》,在他的作品中,《社戏》因为没有更多的思想之核‘哽’在其中,呈现着天然、圆润、质朴、纯真的气质。现在读它,依然是那么的亲切、感人。”小说中过多充斥思想之核,不止鲁迅具有,从现代到当代,这条小说的流脉和小说学或者说小说的写法,从来没有断绝过,比如当代的张炜、张承志等作家的创作。可能由于作家表达得含蓄,或者是她自己也还没有达到一种高度的自觉和能够对此作郑重的理论概括和归纳总结,萧红或还只是从感性的层面意识到了她自己所采用是“我的人物比我高”的小说写法。前面所分析的非成人视角叙事策略,其实就是“我的人物比我高”这一限知视角和限制叙事在小说当中的一个维度。下面将结合具体叙述片段,从形式层面分析隐含作者是如何在转换性人物有限视角和固定人物的限制性视角方面,来实现“我的人物比我高”的限制性叙事效果的。呼兰河的大泥坑子一年之中发生多次抬车抬马,可没有一个人说把泥坑子用土填起来,有一天,下大雨的时候,一个小孩子掉下去,让一个卖豆腐的救了上来。救上来一看,那孩子是农业学校校长的儿子:
一、于是议论纷纷了,有的说是因为农业学堂设在庙里边,冲了龙王爷了,龙王爷要降大雨淹死这孩子。
二、1有的说不然,完全不是这样,都是因为这孩子的父亲的关系。他父亲在讲堂上指手画脚地讲,讲给学生们说,说这天下雨不是在天的龙王爷下的雨,他说没有龙王爷。2你看这不把龙王爷活活地气死,他这口气那能不出呢?所以就抓住了他的儿子来实行因果报应了。
三、1有的说,那学堂里的学生也太不像样了,有的爬上了老龙王的头顶,给老龙王去戴了一个草帽。这是什么年头,一个毛孩子就敢惹这么大的祸,老龙王怎么会不报应呢?2看着吧,这还不能算了事,你想龙王爷并不是白人呵!你若惹了他,他可能够饶了你?那不像对付一个拉车的、卖菜的,随便地踢他们一脚就让他们去。那是龙王爷呀!龙王爷还是惹得的吗?
四、1有的说,那学堂的学生都太不像样了,他说他亲眼看过,学生们拿了蚕放在大殿上老龙王的手上。2你想老龙王那能够受得了。
五、有的说,现在的学堂太不好了,有孩子是千万上不得学堂的。一上学堂就天地人神鬼不分了。
六、有的说,他要到学堂把他的儿子领回来,不让他念书了。
七、1有的说孩子在学堂里念书,是越念越坏,比方吓掉了魂,他娘给他叫魂的时候,2你听他说什么?他说这叫迷信。你说再念下去那还了得吗?
八、说来说去,越说越远啊。(序号为笔者所加)(第665页)
之所以作这样大段的引用,就是为说明转换性人物有限视角的问题。叙事学认为,隐含作者、叙述者和人物,都可以体现一种或多种视点。视点与叙事声音是有重要区别的:“视点是身体处所,或意识形态方位,或实际生活定位点,基于它,叙事性事件得以立足、而声音(voice)指的是讲话或其他公开手段,通过它们,事件及实存与受众交流。视点并不意味着表达,而仅意味着表达基于何种角度而展开。角度与表达不需要寄寓在同一人身上,而可能有多种结合方式。”我们看上面第一二三四七段的情况,这五段可以看成是对于五个不同人物的自由直接引语,也就是没有引号等规约性标志的直接引语,有点像第一人称内心独白,只不过叙述者分饰了不同的人物,用人物的感知和利益视点来叙述。但这不是唯一的解释,第二三四七段的第1句可以理解为叙述人在叙述人物的想法、观点和不同人物对泥坑子淹着农业学校校长儿子的众说纷纭,但第2句自由转换成了该人物的自由直接引语,叙述人从人物的角度直接发声,与受述者直接交流,视点也是人物的(第五段,可视为人物的自由直接引语,取人物的视角。第六段,间接引语,视角也是人物的)。无论按哪种解释,在这几段的叙述里,叙述人与人物持同一视点乃至就是合体为一的叙述声音,而叙述人与隐含作者的视点(尤其是利益视点)是分离的,这就形成了转换性人物有限视角。这种视角最大的好处是,符合人物自身的认识水平、意识心理和语言及行为逻辑,这样的人物不再是隐含作者的传声筒,而是有着自己主体行为方式的立体的、鲜活的人物。其实也就是如有的评论者所说的,小说写作要“贴着人物写”的写法:“在小说写作中,人物的性格逻辑是高于作家的想象的,如果你强行扭曲人物自身的逻辑,这小说一定会显得生硬而粗糙。不贴着人物自身的逻辑、事物内在的情理写,你就会武断、粗暴地对待自己小说的情节和对话,艺术上的漏洞就会很多”,“你要了解一个疯子或者傻瓜,就得贴着他们的感受写,如果你用健康人的思维去写,就很难写得真实生动”。在上面引用的几个段落里,叙述人是贴着呼兰河这里的每个人物的感受去写的,叙述人、人物与隐含作者的思想意识和认识水平发生了剥离,我们很明白作者、隐含作者对于农业学校校长儿子掉泥坑子的原因,都不会是这些段落所呈现的这样的认识水平、价值观和道德评判标准。当然,转换性人物有限视角,算是“贴着人物写”里一种比较高超的写作技巧。虽然通常情况下,叙事学的转换性人物有限视角往往并不解决任何特定的问题、也不展开一个因果链。西蒙·查特曼就提出了“对人物内心的转换性有限透视”这一术语,他说:
转换性有限透视没有目的性,不是为结局性情节服务的,它毫无目的地展示各色人物的想法,这想法本身就是“情节”,它变幻无常,根本不为外在的事件服务。在“转换性有限透视”中,叙述者从一人物的内心转至另一人物的内心,但并不解决任何特定的问题,也不展开一个因果链。
由于传统全知叙述和现代叙事方式的本质区别并不是叙述者能透视所有人物的内心与仅能透视部分人物的内心这样一种范围上的区别,而是叙述者究竟是用自己的全知眼光来观察故事世界,还是尽量转用人物的有限视角来观察故事世界这样一种质的区别。所以申丹认为应该用“有限”一词来描述这种现代视角,并将它用于“(叙述者采纳的)人物有限视角”这一含义,而查特曼的“对人物内心的转换性有限透视”这一术语应改为“转换性人物有限视角”。围绕农业学校校长儿子掉泥坑子又被救上来的事件,叙述人从不同人物的转换性人物有限视角所作的叙述,虽然不为结局性情节服务,也不展开一个因果链,看似是毫无目的地展示各色人物的想法,笔者倒觉得《呼兰河传》的隐含作者是有目的的,至少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不同人物的“想法本身就是‘情节’”。藉此,隐含作者不仅做到了还艺术真实于人物——“我的人物比我高”,而且,由于叙述人、人物与隐含作者之间利益视点的剥离,还形成了一种轻微的反讽的效果,也就是葛浩文所说的“轻松的幽默讽刺场面”。《呼兰河传》中很多的轻微的反讽甚至有些幽默意味的叙述,都是藉由转换性人物有限视角而产生的。
除了转换性人物有限视角,固定人物的有限视角,也一样非常出彩。《呼兰河传》中叙述者所采用的固定人物的有限视角,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当属小团圆媳妇的婆婆了。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她是只虐待和打骂小团圆媳妇吗?当然不是:
(据她说,她一辈子的孩子并不多,就是这一个儿子,虽然说是稀少,可是她没有娇养过。到如今那身上的疤也有二十多块。
(她说:“不信,脱了衣裳给大家看看……那孩子那身上的疤拉,真是多大的都有,碗口大的有一块。真不是说,我对孩子真没有娇养过。除了他自个儿跌的不说,就说我用劈柴棒子打的也落了好几个疤。养活孩子可不是养活鸡鸭的呀!养活小鸡,你不好好养它,它不下蛋。一个蛋,大的换三块豆腐,小的换两块豆腐,是闹着玩的吗?可不是闹着玩的。”
(有一次,她的儿子踏死了一个小鸡子,她打了她儿子三天三夜。她说:
“……”
(她这有多少年没养鸡了,自从订了这团圆媳妇,把积存下的那点针头线脑的钱都花上了。这还不说,还得每年头绳钱啦,腿带钱地托人捎去,一年一个空,这几年来就紧得不得了。想养几个鸡,都狠心没有养。(第751页)
在整个的婆婆的视角里,儿子踏死一个鸡子,也值得她如此下狠手暴打,可见她并不是只虐打小团圆媳妇一个。暴打的原因,足以让人一悲三叹。因为订了团圆媳妇,费钱,她最爱惜的鸡子都没有养,却又因把团圆媳妇打出病来,流水一样花钱在抽贴的云游真人身上……各种矛盾和不可思议,都如此真实地汇聚在了小团圆媳妇婆婆身上。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可以说是萧红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所奉献的一个极为经典的人物形象。在这个人物身上所显示的艺术性和文学性,同类人物几无人能出其右者。《呼兰河传》整个第四章的第4节到第8节,所采纳的小团圆媳妇婆婆作为固定人物有限视角的叙述,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发挥,其间还穿插了不同看客和其他人的转换性人物有限视角。在这一章里,也许是为了调节叙事节奏、区分不同的叙述段落和不同人物的有限视角,还大量使用了小括号来作为规约性标志。在小团圆媳妇婆婆这一固定人物有限视角里,叙述人、人物与隐含作者、作者,都天然拉开了距离,人物的心理、思想意识、价值观和道德判断等,都是人物自己的,人物绝没有充当隐含作者的传声筒,而且在这种距离拉开的叙述手法中,人物的真实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还原和展现,人性的复杂性亦远非简单的二元可以涵括。而且,整个事件的反讽意味和悲剧性并存,让人在对人物的理解之同情当中,又对小团圆媳妇的被虐待致死和施虐者不失朴拙但又愚昧并且兼具人性恶与各种人性复杂性之外还对自己所犯平庸之恶毫不自知,而感到一种让人无法释怀的纠结与无力感,纠结与无力当中还对美好生命的被虐杀而备感痛入心髓之痛,审美意蕴可谓繁富无尽。
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中辨析了福勒在厄斯彭斯基的影响下提出视角或眼光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心理眼光(或称“感知眼光”),它属于视觉范畴,其涉及的主要问题是:“究竟谁来担任故事事件的观察者?是作者呢,还是经历事件的人物?”;二是意识形态眼光,它指的是由文本中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价值或信仰体系,例如托尔斯泰的基督教信仰、奥威尔对极权主义的谴责等;三是时间与空间眼光。有关福勒的“心理眼光”,申丹认为,讨论叙事眼光时,叙述学家一般不考虑文本之外的作者,仅关注文本之内的“隐含作者”(即文本中蕴涵的作者的立场、观点、态度等)。在讨论叙事眼光时,他们关注的是叙述者究竟是采用自己的眼光来叙事,还是采用人物的眼光来叙事。由于文本中的叙述者是故事事件的直接观察者,文本外的作者只能间接地通过叙述者起作用(况且叙述者与作者之间往往有一定的距离,不宜将两者等同起来)。申丹认为,福勒对“意识形态眼光”的探讨不仅混淆了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界限,而且也混淆了叙述声音与叙事眼光以及聚焦人物与非聚焦人物之间的界限。尽管如此,福勒对心理眼光和意识形态眼光的论述,还是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隐含作者与叙述人和人物之间,可以发生心理眼光和意识形态眼光的偏离和拉开距离甚至截然相反。这是贴着人物写,还人物真实性于人物、实现“我的人物比我高”小说学的必需的叙述行为和方式方法。有研究者对像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和《群山之巅》那种“作者”无所不在介入到写作中的文本——“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和小说中的人物确实存在着无法分离的混合性——作出分析,认为迟子建在写作过程中,自己其实已经是文本的一个有机部分,也因之认为:也许把这几者划分得界限分明的小说文本能够给研究者提供比较典型的分析案例,但这不应该成为区分文本审美高下的尺度,不然对迟子建这样主观介入和代入,自由出入文本内外的作者是不公平的。同样是写东北边地人生的杰出的女作家,萧红的《呼兰河传》作为小说叙事文本,与迟子建在小说文本中常常存在的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和小说中人物之间确实存在着无法分离的混合性——这样的情形颇为不同,《呼兰河传》里的作者、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人物常常是拉开距离的,存在着价值视点和利益视点(也可以说是心理眼光和意识形态眼光)偏离和巨大距离。《呼兰河传》是限知视角和限制叙事的小说范本,这也是它在文学性上终将成为不朽之书的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注释
②⑤林贤治:《前言:萧红和她的弱势文学》,林贤治编注:《萧红十年集》(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4、15页,第14页。此文中《呼兰河传》所有引文,均出于《萧红十年集》(下)。
⑦刘旭:《叙述行为与文学性——形式分析与文学性问题的思考之一》,《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3期。
责任编辑王雪松
AParadigmaticNovelofLimitedPerspectiveandLimitedNarration——A Reinterpretation ofTheRomanceofHulanRiverby Xiao Hong
Liu Yan
(Institute of Literary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TheRomanceofHulanRiveris the last masterpiece of Xiao Hong which marks the peak of her literary creation. The former studies were trapped in the paradigm of social criticism which over emphasized the novel’s rethinking of national character and its content. The researchers have not fully recognized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the novel from pure literary persp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aims at exploring the true literariness of the novel in formal approach by seeking for the internal and implicit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ology. The analysis will focus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implicit author,narrative structure,plotting and the possibility of limited narration,the intentional structure of naivety and poetry and immature narrative perspective,as well as its sublimity of limited narration——“ my figure is above me”. And all these constitute the true literariness of the novel and leads to its immortality.
implicit author; narrative structure; limited perspective; limited narration
2017-10-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世纪海外华文作家的中国叙事研究”(17BZW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