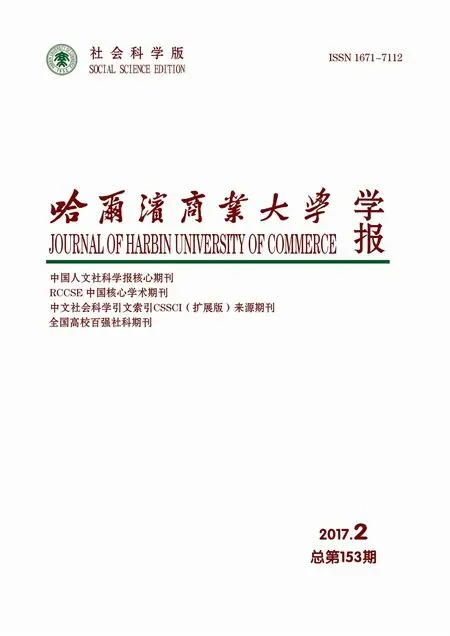法律援助中的政府责任、律师义务及民众权利
2017-02-27王硕
王 硕
(1.吉林大学 法学院,长春 130012;2.吉林大学 珠海学院,广东 珠海 519041)
法律援助中的政府责任、律师义务及民众权利
王 硕1,2
(1.吉林大学 法学院,长春 130012;2.吉林大学 珠海学院,广东 珠海 519041)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维护弱势群体权利的基本制度,在坚守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不断完善和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的同时,法律援助背后的一些基本性理论问题还有待探讨。虽然法律援助以保护特殊群体的权利为宗旨,但政府责任与律师义务的定位却并不明确。如能理顺政府、受援助者以及职业律师之间权责关系,将会对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乃至民众权利的保护大有助益。
法律援助;实质平等;政府责任;行政给付
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一项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的制度,无疑在最后一道防线上实现了民众救助权从形式平等到实质平等的转换。而这种转换的具体实施者大体上是由职业律师来完成的。自20世纪90年代我国就完成了职业律师的改革,律师业已成为自收自支、自我发展的社会中介人员。应当说是否提供法律援助,看起来应是职业律师的自主、自愿选择。但从《法律援助条例》的相关条文当中可以看出,如果律师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要受到相应的处罚。作为政府责任的法律援助,何以将其本应承担的责任转嫁到职业律师的身上。因此,需要从理论上回应这种掣肘关系,理顺政府与律师的关系,建立更加完善的援助模式。对于受援助的群众来说,法律援助从性质上应当界定为行政给付,而给付并非是政府的施舍,应是民众的一项权利。因此,在政府和民众之间,法律援助应是“权利义务式”的“法律关系”。理顺政府责任、律师义务与民众权利三者之间的关系,将有利于法律援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更加有利于群众切身利益的保护。
一、从形式平等到实质平等——法律援助制度的原点
还记得卡夫卡的寓言故事《法的门前》,乡下人面对着敞开的大门却无论如何也晋见不到法[1]。从表面上看,法的大门是向所有的人敞开的。但实际上就是有的人永远徘徊在法的门前。对于经济上的贫困者,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这里所指的弱势群体不仅只经济上的弱势,不使得因经济上的贫困而得不到法律救助。除此之外,还包括控辩对抗上的弱势以及生理心理上的弱势,如对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提供法律上的援助。以及某些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来说,法律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陌生的话语体系,复杂的操作流程。他们相信法律期盼能够“接近正义”但又不知道如何去保护自己。我们想去接近事实真相,但我们却无法真正地还原已经发生过的场景。就像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没有人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对于法律职业者来说尚需花费大量的精力去探究真相、证据,钻研法律条文、判例、原则。对需要得到法律帮助的人,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并且,面对国家控诉机关,在没有专业律师的帮助下,基本上看控辩双方的力量对抗是失衡的。那么,通过对被援助者提供法律帮助,不但可以消除被援助者的经济障碍和心理障碍,还可以实现程序公正,维护民众基本权利。
法律援助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国。私人律师、宗教组织出于慈善的目的,免费为穷人提供法律救助的服务。而这在当时并没有明文的规定,仅仅是基于“一个文明社会的原则”。任何公民面临生活或者自由的危险时,不能仅仅因为他太过贫穷以至于不能负担这样的帮助,就被剥夺律师辩护的权利。从法律援助的历史沿革来看,不可否认的是,最初单就律师这个群体来说,提供法律援助是基于职业道德以及对公平正义价值的追求而进行的一项自发行动。因此,最初的法律援助可定性为慈善行为。但如果将法律援助仅仅定性为慈善的话,将会面临如下问题:首先,从本质上来说慈善行为是一种道德行为而非法律行为。是行善者的乐善好施,是一种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行为。那么救助对象的范围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能得到援助的幸运儿是为数不多的。其次,权利义务的对等性这条法律当中的朴素原理在道德行为中并不适用。因此,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很难保证,更谈不到如何救济。最后,对于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及相关人士来说,提供法律援助缺乏激励机制,很难保障其长期地、稳定地持续下去。而对于急需得到法律帮助的人来说,这种供需的不对称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从慈善行为向国家责任的转变是法律援助发展的一种必然路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意大利法学家卡佩莱蒂的倡导下,各国政府都意识到保护当事人获得司法救济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并将其作为政府的一项义务。不仅从理论上加以论证,而且在制度上为当事人获得司法救济提供应有的保障。由此掀起了一场遍及世界许多国家的接近正义运动。正如卡佩莱蒂教授所言:“我们关注着如何使以前不能有效利用法院或行政机关职能的人今后能够有效地加以利用。对于大多市民而言,19世纪流于形式的选择权实际上就是对有效的正义的拒绝,因此,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努力使之名副其实。”[2]其实这种彰显人权、平等保护的思想早在欧美国家建国之初就写在了宪法性文本当中。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一条:“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除了依据公共利益而出现的社会差别外,其他社会差别,一概不能成立。”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七条:“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人人有权享受平等保护,以免受违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视行为以及煽动这种歧视的任何行为之害。”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种平等保护的宪法性权利为将来的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做出了完好的铺垫。但同时,将形式上的平等转变为实质的平等完全是另外的议题。个人乃至组织的不同境遇,会使得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在实现起来并不是那么如意。为贫困者提供法律上的帮助,也不应是恩惠式的慈善状态,国家应担当起保护弱者的应有作用,为此各国纷纷出台法律,并实际开展法律援助活动。这使得法律援助权不仅成为一项宪法性的权利,并且进一步转变为公民的一项具体权利。如英国1949年颁布了《法律援助和咨询法》,于1988年又颁布了《法律援助法》,1999年另行颁布了《接近正义法》。法国于1972年制定了《审判援助法》。德国于1980年颁布了《咨询援助法》[3]。在美国,刑事法律援助与民事法律援助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刑事法律援助是联邦宪法明确赋予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1963年,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写道:“当被告无力聘请律师时,州政府要有公共资金为其提供辩护律师。”通过在联邦和州政府建立公共辩护人体系,公民获得了律师辩护权(The Right to Counsel)。而民事法律援助的发展则主要得益于约翰逊总统提出的“战胜贫困”运动。在联邦政府内成立了“经济机会局”(OEO),以解决穷人的需要。1974年通过了《法律服务公司法》,私人、民间法律援助机构以及私人律师事务所通过从法律服务公司争取项目资金,从而向贫困人口和低收入阶层提供法律服务。至此,法律援助的发展走向了全新的领域,它使得国家意识到帮助贫困人群获得法律服务是其应有的责任。消极被动式的等待救助变为了积极主动式的要求救助。在坚守司法平等这个法律平等的最后一道防线方面,法律援助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作为政府责任的法律援助制度
我国的法律援助起步于1994年,是在法学精英的倡导下所建立的,由时任司法部部长肖扬提出,并率先在几个发达省份如广东、北京等地探索实施。在随后的几年里,中国的法律援助事业逐步发展壮大。在中央层面设立了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建立了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相应地,各省、地区、县均纷纷设立了法律援助中心。在制度建设上,早在1996年就针对法律援助专门制定了《法律援助实施办法》,并于2003年以法规的形式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条例的颁布为法律援助的开展实施奠定了制度基础。其中第三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从我国目前的法律援助现状来看,一方面我们强调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另一方面,《法律援助条例》第八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政府担当起法律援助的主要任务,但社会法律援助的力量仍不应忽视。虽然两者在定位、资金支持、提供主体等方面不尽相同,但同时也会存在交叉与重叠。政府的法律援助与社会法律援助呈现出二元互动的局面:第一,虽然政府承担起了法律援助的重要责任,使法律援助更加规范化,如在援助范围、财政保证、操作流程等方面。但公益性的社会援助,如由高校、律师事务所及其他社会团体提供的法律帮助仍是重要补充,受到鼓励和支持。第二,政府在法律援助对象的选择上,一般以经济状况和案件性质为标准。而社会援助对象的选择上更加灵活,或以某一群体为标准或以某一类社会问题为标准。第三,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与被援助对象之间是一种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社会法律援助,对提供主体来说是一种道义上的义务,本着律师的职业道德以及自愿服务的宗旨,是自律行为的体现。两者互为补充,共同促进了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
从具体层面来看,法援的提供者当然主要是法律从业者,而这个概念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法官、检查官、公安人员、高校教师、人民调解员等都会纳入其中。但真正适合成为法援主体的,律师群体即成为不二选择。从律师身份来说,又可以将律师分为公职律师与职业律师两类。与政府关系最为密切的有编制的公职律师,数量少之又少,基本满足不了庞大的法律援助需求。加之我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进行了律师职业改革,“不再使用生产资料所有制模式和行政管理模式界定律师机构的性质,大力发展经过主管机关资格认定,不占国家编制和经费的自律性律师事务所;积极发展律师队伍,努力提高队伍素质,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交往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实行自愿组合、自收自支、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律师体制。”*根据国务院于1993年批准的司法部对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的论述,请参见http://china.findlaw.cn/fagui/xz/27/163643.html职业律师群体不再是体制内的人员,面对政府机关所指派的法律援助请求又将作何选择。
三、律师的法律援助义务
厘定和界清政府责任与律师义务的关系即成为法律援助制度中的重要议题。面对法律援助需求的不断攀升,政府与律师之间如何共同担负起救助的重任,西方的法律援助制度值得借鉴。以英国为例,法律援助制度呈现两种模式:一种模式称之为朱迪凯尔制度(The Judicare Model),它是流行于欧美的一种法律援助模式。该模式由几个关键部分组成,即国家资助 (public funds)、开业律师(private lawyers)、贫困人群( poor people)。该种模式的特点在于法律援助是国家义务,而非单纯的个人道义。政府在法律援助的总体开支额度上没有上限,例如我国香港地区。但在民事法律援助当中,法律服务并非完全免费,如果受援助方败诉,基金会为此买单。而如果胜诉,就会要求胜诉方支付部分费用或者直接从其胜诉费中扣除。*例如法律援助署长的第一押记,从受助人收回或保留的财产中扣除本署为他付出的法律费用。另外,在此模式下受援助者可以自己挑选心仪的律师,而非由政府单方指派。这样有利于双方的沟通,建立彼此间的信任,达成一致意见。从政府与律师的关系上来看,政府按照律师的工作给付其相适宜的报酬,这就类似于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政府与律师之间具有对价关系。由于政府承担了大部分律师费用,开业律师也乐于提供法律服务。从数据统计来看,开业律师收入的相当比例来自法律援助。“从民事、刑事的法律援助中获得的报酬约占收入的30%。”[3]既然付出和所得之间具有等值性,在服务的质量上就能够有所保障。当然,朱迪凯尔模式也有其不足之处,如援助范围的覆盖面狭窄、如何控制服务质量等问题的困扰,欧美国家仍然在完善过程当中。另外一项制度是带薪律师制度,也称为专职律师模式,其是由在法律中心工作领取薪水的高级法律顾问及一般律师所开展的法律援助制度。在朱迪凯尔模式下,开业律师的报酬来源主要是其业务活动。而在带薪律师模式下,获得报酬的来源是法律中心的工资,与其开展的业务并无直接关联。正是由于这种差异,两者在业务领域上也有所不同。如在英国,朱迪凯尔制度和带薪律师制度是相互补充的。专职律师在其当事人的案件内容与以下内容相符时,通常不能受理:①不动产交易;②商业案件;③离婚程序;④公正遗嘱(少量私人财产的公证除外);⑤人身伤害赔偿,但赔偿金额不超过在各郡法院中的第二等级(1980年为50英镑;)⑥被告人在21岁以下的刑事案件。限制案件来源的好处是,使得开业律师与专职律师之间避免了业务上的重复,不至于产生不必要的摩擦,各得其所又共同提供法律援助。再者,作为领取薪水的专职律师来说,其薪水来源于政府(暂且不论来自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因此,不得开展与政治运动有关案件的法律援助,如“罢工”“游说”“纠察”等。
如果说朱迪凯尔模式下的开业律师与政府间关系是一种服务合同关系的话,那么在带薪律师模式下的专职律师与政府间的关系是一种职务安排关系。再者,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的法律援助,其分属于民事和刑事两个系统。刑事法律援助通过公共辩护人体系实施,公共辩护人是受雇于政府的律师。公共辩护人的薪水全部来源于政府财政,并且由于薪水较高,吸引了大量的高水平律师。民事法律援助不完全是政府行为,通过成立法律服务公司,政府向法律服务公司拨款。法律服务公司与特定的民间法律援助机构达成项目合同并向其提供资金,以资助其法律援助活动。
不论是朱迪凯尔制度与带薪律师制度,还是美国的刑事法律援助与民事法律援助分立制度,都很好地解决了政府责任与律师义务的相互关系。但回过头来看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对责任的承担、义务的履行还有模糊之处,有待进一步说明。从现有的法律条文来看,《法律援助条例》第六条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第二十七条规定:“律师事务所拒绝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不安排本所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业整顿的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律师可以从事下列业务:接受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者依法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担任辩护人,接受自诉案件自诉人、公诉案件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诉讼。”从法律条文中可以看出,政府与律师之间的关系,要么可看作委托关系,要么是指派关系。委托关系是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但如果将两者之间的关系定性为委托关系,对于拒不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又要给予行政处罚这个条文来看,其显然与委托关系的法理是违背的。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似乎对职业律师来说并不是选择自由,而是义务约束。因此将两者之间的关系定性为指派关系则更为恰当。既然是服从安排下的任务,便会在实际服务中存在诸如办案时间仓促、律师积极性不高、服务质量难以保证等法律援助中存在的问题。对掌握较多案源的律师来说,基本上无暇顾及低“回报”的法律援助案件。虽然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是能够得到办案补贴的,并且,这种办案补贴的标准近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在大幅度地提高。*如《〈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实施细则》第二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法律援助最低经费保障制度,将法律援助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根据当地国民经济发展情况逐步增加,使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但办案补贴仍难以与职业律师日常的服务报酬相匹配,可以说差距还是很大的,即是说,办案补贴并不具有营利性质。这与朱迪凯尔制度下,律师所获得的劳动报酬的性质并不相同。显然,“政府责任,律师义务”这种法律援助的逻辑是存在问题的,政府与职业律师群体之间的关系定性并不明确。首先,作为职业律师来说,同其他职业群体一样,其需要通过输出智力与法律服务来维持基本生活。但又与其他职业不同的是,法律所指向的是公正、平等、正义,如果这些基本价值能够用金钱衡量的话,整个社会的秩序基石将面临崩塌。坚守社会的基本伦理价值的重担就落到了律师身上。所以,提供法律援助毋宁说是律师的职业伦理,更是律师在实践中对司法正义的自觉追求。职业伦理关系到整个社会对律师群体的看法,同时也是这个群体的自我定位。他们不应被看作是一群满眼铜臭、只顾经济利益玩弄文字游戏的诡辩者,应该成为推动法制建设、引领司法改革的先行者。其次,不论是靠法律生存还是为法律而生存的律师来说,仅仅凭借职业伦理来维持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显然是不够的。不然,也不会有从慈善式的法律援助到政府责任的法律援助的发展历程。最后,只有将职业伦理的道德基础与国家制度建构相契合,才能真正助推法律援助的发展。仅靠强制性规定的指派很难长久维系,不仅不利于贫困者权利的保护,也不利于调动职业律师投身到法援当中。因此就有学者提出,借鉴国外改革经验,对现有国办律师事务所进行改造,使其成为由国家核拨编制和经费、专门从事公益性法律服务的机构,建立起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公职律师队伍。界分公职律师与职业律师,并辅之以不同的制度模式,理顺政府与律师之间关系将对未来的法律援助发展大有助益。
四、政府责任与公民权利
既然得到援助是民众的一项权利,那么在民众申请与政府提供的运作模式下,法律援助自身又是一项什么行为呢?对此有学者指出,“审查法律援助申请的行为属于行政许可行为”。[4]这里有必要对行政许可的基本性质进行分析。以行政许可解禁说为例,将行政许可看作是对法律一般禁止事项的解除。许可为资格的取得、行业的准入设定了条件,而条件意味着是一种准入的壁垒。“从行政许可制度建立的目的看,国家一旦对某一事项实施许可证制度,就意味着国家将这一事项纳入了受限制的范围,它将制约人们有任意地、自由地进行这一事项的权利和资格,要进行必须经由行政机关依法根据一定的条件来准许。”[5]确实,得到法律援助是要符合一定条件的(如经济条件、案情条件等),但这些条件并非是对受援助主体的限制,反而是对特殊群体的保护。不使得因自身原因或特殊情况无法得到平等保护的群体得到救助,以实现诉讼权利的平等。将行政许可仅仅理解为是对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活动的法律资格的赋予是片面的。
在公民个人与国家的二元互动当中,一个人之所以成为并一直作为一个国家的成员,就在于国家应当而且能够为其生存和发展提供切实的保障。伴随着人权理论的演进,对个人权利的保护逐渐实现了从消极权利到积极权利的跨越。国家的职能定位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守夜人式的国家模式转向了福利国家模式。服务型政府的作用在于提供积极的手段消除贫困,矫正因市场竞争而产生的贫富分化现象。对于受援助的对象来说,政府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各种方式实现弱势群体在司法诉权上的平等保护,这种平等保护的理念,恰恰是给付行政的价值体现。给付行政是为解决社会发展中的不公平问题而产生,社会公平是给付行政的当然价值追求。[6]从行政给付的最初内涵来看,提供物质帮助是其主要方式,但财产价值的帮助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民众的期待和诉求,全面的安全保护、精神慰藉、尊严保障是给付内涵的更高层次的发展。行政给付已经成为政府的一项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属性于一体的综合性行政职能。既然法律援助是作为政府为经济困难及特殊案件的特殊群体提供的法律服务,实现的是诉权上的平等保护,因此,可将法律援助定性为行政给付。在行政给付形态上看,可将给付分为自为给付与委托给付。如以这种划分方式来看,由政府公职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模式对应了自为给付,而由政府所委派的职业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对应了委托给付。不论是自为给付还是委托给付都有利于明确政府的职责,有助于权利人在行政给付中的法律保护。
将法律援助行为定性为行政给付引申出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法律援助权的救济问题。“无救济则无权利”这是一条基本的权利理念。作为法律援助权的享有者来说,这是不得不提及的一个问题。从目前救助方式上来看,尽管行政内的纠纷解决机制具有诉讼救济难以比拟的制度优势,但如果没有司法最终解决机制的制衡,行政救济也难以保持持久和发挥优势。即是说仅有行政复议这一项单一的救助形式显然是不充分的,也不利于权利享有者最终权利的维护。*从目前我国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上来看,其救济方式主要是行政复议。第十九条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通知有异议的,可以向确定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在收到异议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责令法律援助机构及时对该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从理论上看,行政诉讼的救济是法律援助者享有者的最后正义防线,缺少了它,权利救济的方式是不完善的。从行政诉讼类型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行政给付之诉确实是最近伴随着福利国家时代的积极行政的形成而产生的。行政给付之诉之所以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其体现了公民权利保障的价值理念。行政给付的诉讼机能是“保障公民对国家所享有的公法请求权,通过法院判决督促行政机关积极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法定义务,进而实现现代行政国家的积极给付目的。”[7]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并非“恩惠式”的“伦理关系”而是“权利义务式”的“法律关系”。再者,法律援助权的诉讼救济能够使公众的视线进一步地集中到法律援助制度上来。暂且不论诉讼的结果,这种体现为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方式,会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公众也会从行政给付之诉中收获更多的法律知识,更加注重自身权益的保护。
[1] 【美】彼得·德恩里科.法的门前[M].邓子滨.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意】莫诺.卡佩莱蒂.福利国家与接近正义[M].刘俊祥,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3]马栩生.当代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4]彭锡华.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从国际人权法的视角考察[J].法学评论,2006,(3):64-69.
[5]方世荣.行政许可的涵义、性质及公正性问题探讨[J].法律科学,1998,(2): 29-31.
[6]柳砚涛.行政给付制度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5.
[7]喻少如.论行政给付行为的诉讼救济[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6):73-80.
[责任编辑:姜 野]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ies、Civil Rights and Lawyer Duty in Legal Did
WANG Shuo1,2
(1.Jili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Changchun 130012,China;2.Jilin University,Zhuhai College,Zhuhai 519041,China)
As a basic system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vulnerable groups, legal ai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ast line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expansion of legal aid coverage, we pay attention to some basic theoretical issues behind legal aid. Although the legal aid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special groups, but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obligations of lawyers is not clear. Sorting out the relations between and among government, vulnerable members and lawyer plays a very important practical role in perfecting the legal aid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rights of the people.
legal aid; essential equality;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presentation
2017-01-12
王 硕(1981-),男,吉林长春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法学理论研究。
D926.5
A
1671-7112(2017)02-01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