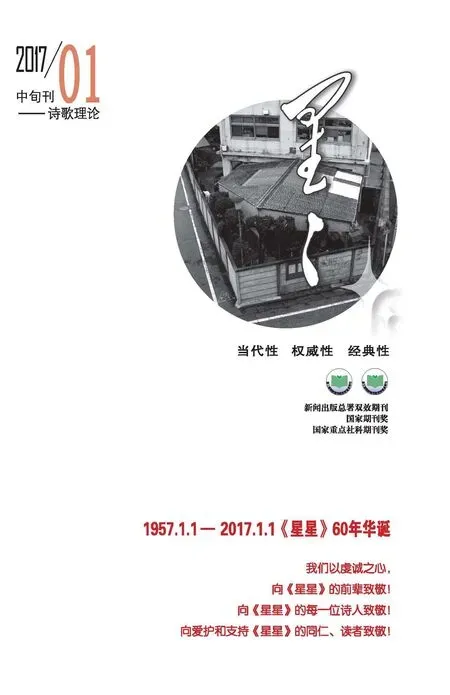新媒时代的诗文艺与诗营销
——2016年中国诗歌印象
2017-02-18赵卫峰
赵卫峰 覃 才
新媒时代的诗文艺与诗营销
——2016年中国诗歌印象
赵卫峰 覃 才
以微信为主角的新媒体进一步推动了诗歌的大众化与价值凸显。2016年,“手机-微信-诗歌”的合体及随身,使诗歌作为大众精神的需求品可以随时随地享受到,另方面,显态蓬勃的诗坛又杂草丛生,“内部或阶段式的热闹”与各种会议、活动及出版物的相对“高冷”反差明显。在诗歌网络时空的惯性变动中,虽然以民谣和诗电影为代表的“诗文艺”创造出了“诗与远方”的美好景象,但在浮躁与张扬的网络风气之下,诗歌显著的营销作为和优质诗文本稀疏是客观存在的问题。
诗与远方
覃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2016年,“诗与远方”仿佛美好的想象通过音乐人及微信与民谣的传播作用,让“诗歌”作为一种通俗性概念广泛地进入大众精神生活。民谣与诗电影这两股潮流把诗歌艺术推向一个“诗文艺”发展的新维度,这可以算多年来诗歌艺术创新与大众化探索意想不到的一次收获?
这一年,诗人翟永明、韩东等在成都成立“十诗人电影公司”,道辉诗电影《蝴蝶和怀孕的子弹》福建开拍,诗电影《我的诗篇》《路边野餐》上映,这些倾向明确、艺术姿态鲜明的“诗与电影”之合力,推动了“诗文艺”发展的意义明显。作为一种声音的艺术,民谣在竭力吸收与转化诗的可弹可唱部分,民谣歌手在传送“歌”的同时也呈现出了“诗”的声音。诗人、民谣歌手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虽然引发众议,但至少从文本的角度直接地说明了“民谣其实是诗”?
“诗与远方”的大众意愿、诗电影的图像、民谣的声音三方面构成的“诗文艺”兴起局面是2016年诗歌大众化的重要发展。不管是大众的诗意愿,还是诗电影和民谣的兴起,它们本质上是建立在对诗歌的运用与转化需求上的。基于这点,我们也应该思考,当下的诗歌写作是否能够支撑“诗文艺”下一个阶段的探索与创新?新的“诗文艺”形式是否马上就会到来?这些答案最终仍会落实到具体的诗歌上,但我们的新诗,真的准备好了吗?
赵卫峰:如果在汪国真席慕容时代就与网络传播遭遇,如果胡适郭沫若在世之时就有手机及微信,那又将是何种的“诗文艺”?我理解“诗文艺”时代的升温式出现,但并不认为它能促进或改变处于徘徊状态已久的当代诗歌。就2016年看,为什么不可以认为是电影及图像、民谣及音乐、戏剧带动了“诗歌”,而非诗歌为主导呢?我也理解你作为诗歌中人,主观上是为诗歌说话的,但事实上对于大众,在意的更多是图像与声音效果,而所谓诗在其中——事实上就广义的“诗意”与“诗性”在起作用,而不是诗人们及他们创作的诗歌在起作用。
各种文体、文艺形式的碰撞交叉是必然和自然的。这多少也体现某种轮回:两周及唐宋时期,诗与歌不也是并肩合力的?不也是娱乐场所的佐料吗?“元曲”更是这种诗入大众生活“实用”的结果。那么,“诗文艺”的下一个阶段,该是何种更别致的卡拉OK呢?
新诗百年
覃才:作为新诗发展的首个百年节点(1916-2016),各种因素决定了2016年是新诗的一个总结与回顾之年。各类诗歌机构、群体及个人,出于不同目标与原因、以各种形式开展了关于“新诗百年”的多种活动,编辑出版了一批相关出版物。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江苏省作协合办、《扬子江》诗刊承办的“中国新诗百年论坛”系列活动,一年多的时间里在拉萨、南宁等地举办“论坛”16场,围绕新诗百年进行总结与回顾。深圳举办“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30周年纪念活动,中国诗歌学会编撰《中国新诗百年大系·安徽卷》,等等。
关于新诗百年的总结与回顾,不管是什么性质的会议与活动,也不管是什么类别的形式与规模,最终的结果应是诗人与文本。二十一世纪以来,在以网站、论坛、微博、微信等为背景的网络写作生态下,新诗数量、体量可谓庞大。相对于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萌生期与八十年代的黄金期,如今,它面对新媒体时代面对大众的需求,其实更需要诗以“自证”其身。当下我们谈论新诗百年,是希望新诗百年的历史能够发挥出更积极与更重要的意义,而不是一味的消费“新诗百年”这个历史的概念。
赵卫峰:当众人都可随意消费“新诗百年”并以此为乐时,这似乎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但,又什么不可以绕过的呢?诗歌史由人造人写,它是费心耗力的有价项目,同时又必然是充满议论与存在漏洞的,这样的结果也是诗歌史应该的。这么多年,各类中小学及大学语文教科书不断更新补充,正体现这个应该。正如诗歌本身——诗歌史理应是一种折腾史。
微信·类型写作
覃才:微信是新媒体的主导形式,在传播诗歌价值与促进诗歌出版方面,它让诗局部表现出多样性的成功。据悉诗刊社官方微信公众号经过3年运营订阅量突破30万,对刊物形象建设与诗歌传播的意义不言而喻。出版方面,民刊《自行车》通过微信平台发起众筹以编辑出版《自行车25年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提前完成3万元的众筹目标,众筹方式的运用还包括个人诗人出版,为诗人解决生活问题等,这是新媒体时期才有诗歌出版现象。对于青年诗人群体来说,微信提供了更好的写作氛围与出版机会。由北鱼、卢山等创建的诗青年微信公众号,成为80后90后青年诗人重要的交流平台,平台发起的“青年诗人成长陪跑计划”公益行动,将为19位青年诗人免费出版5本个人诗集和1本合集。
赵卫峰:诗歌的微信时代这一年仍持续在适应与反适应的动态存在中。可以说所有的诗歌微信平台都是必须的合理的,又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而诗人与微信的关系,则因人而异。几乎每个诗人如今都是诗歌微信的当事人,滋味如何,各有体会。无论如何,微信只是一种社交性工具,如果在诗歌及诗人交流过程中,它变得异常重要,那定是诗歌的不幸。
覃才:类型化写作显然是诗歌在原规则中主动寻求突破的实践。公安与警察视角与题材的类型写作在这一年得到集中的呈现,8月,《琴剑诗系·全国公安实力派诗人丛书》(10卷)由全国公安文联和群众出版社策划出版。10月,105位警察组成的《天津诗人》2016冬之卷“中国诗选.警察诗人档案”编辑出版。而“新诗典”式的口语写作、“工人写作”、“颓荡”诗歌、“地方主义”、“新死亡”诗写,郑小琼的“打工写作”系列等,体现诗人与诗歌对“大一统”格局的反抗及自觉变化。
赵卫峰:网络对于当代诗歌最主要的作用是一种综合的“信息”冲击。原来这也是诗?诗也可以这样写?好诗好在哪儿?诸如此类。具体些说,它的落足点仍然是为何写、写什么、怎么写这三个方面。显而易见,在当下“写什么”这个方面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而“怎么写”尤其是“为什么写”这类前提性的方面则不那么重要了。
重要与不重要的变化,是否潜伏着某些值得关注的倾向:世纪之交以来随着网络行进的诗歌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新传播环境正诱使写作者急功近利,诗歌传播、活动倾向于“虚假的精神行为艺术”,诗歌写作成为分行的“工艺写作艺术”,或可直接称为“工艺诗歌”。网络时空的出现带来综合的“信息”冲击作用,结果因人而异。爱吃素者仍然不会真正喜欢荤腥,大家在一个宽敞的诗歌广场上似乎近距离,实则是面面想觑,各行其道,互不认同。也就是说,网络时空的出现更多是体现在传播工具、速度、渠道与效果上的量变,它并不真正改变诗歌本身,并时常让诗歌在传播的顺境、内在质量的逆境和诗人精神的困境间尴尬不断。
当越来越多的人已懒得考虑“为什么写”,这种状态实也反映出诗歌对于人的作用的变化:人们需要生活的诗意,需要诗意的生活,但不一定需要诗歌本身?这似矛盾却也不矛盾,因为“音体美摄漫影视”的行进直接就是一种诗意张扬的过程,更具体形象地看,“饮食、栖居、旅游、采购、游艺”甚至是拉撒做梦,也无时无刻不体现出“诗意”的实现或期待感,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日常生活化进一步合作与和谐,我们可以说这是“诗意的泛化”,这无可厚非,我们或许需要的是适时自省与提醒,诗歌本身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实在的变化?继续把希望寄托在传播方式与形式的更新之上?
人类精神的进步本来就是在正面反面之间冲突而行的。当看到流派式的诗歌倾向出现至少是可以欣慰的。相较往昔,世纪之交以来,种种诗歌概念或名称,诸如“新死亡”、“下半身”、“梨花体”、“草根诗歌”、“新红颜”、“打工诗歌”、“垃圾派”以及微信时段出现的“颓荡”、“截句”等,都会引起异议,正因诗歌本身的不固守成规或创新特性,这样的情况正常。从类似的概念呈现亦可略见,诗歌在努力地自我更新或“折腾”,它在细化、类型化与自我辨识的曲径上自觉地不断地与风车作战。而今“诗人”的问题是,连风车都找不到或不知它是什么了?
代际·九○后
覃才:诗歌不老,诗人易老。转眼间,年纪最大的90后写作群体也将三十而立。有进有退的诗歌生态,90后们如今依然需要更多的作品与机遇,以证明作为一个诗歌写作群体的价值。作为中国诗歌新生力量重要的发掘与推出平台——《中国诗歌》第六届“新发现”夏令营只招收“90后”学员,对“90后”的扶持力度显而易见。《作品》杂志推出“90后推90后”专栏,并联手《文艺报》推出“新天·90后”栏目,《星星》大学生夏令营、武汉大学主办的全国大学生樱花诗赛、上海交大组织的全球华语大学生短诗大赛,以及《人民文学》、《延河》等均在持续关注在校90后诗歌写作群体。对于部分90后诗歌群体来说,经过几年的持续写作,现阶段迫切的需求或者不再是发表与获奖,而是写作上的风格化与转型问题。
赵卫峰:我通常赞成诗人队伍的代际划分。整个60后事实上都属于“朦胧的一代”或多少都与其有关连,提及70后现在更多是指其生理年龄。虽然曾有关于80后是E世代之说,但准确说90后诗人才是与互联网最为息息相关的一代、真正与新媒体同步的新群体。这也初步形成了90后思与诗的网络特征。我不是说其写作就是约定俗成的略带贬义或暧昧的“网络诗歌”,网络本是一种传播工具及信息集散环境,从观念塑造和更新上,它对90后一代的作用我以为是喜大于忧,但正由于传播的便利,问题相对亦多。我很同意霍俊明关于70后是“尴尬的一代”之语,而我以为80后是“漂泊的一代”,90后则更像是“被动的一代”,现在看这定语并不准确。他们的阅读、写作练习、传播以及发表、获奖等,多由前代诗人及现时环境铺就,这就导致其成长、生活、工作多少也是被动的;但其审美、梦想和观念则很自我、自在和自主,更多地属于“独生子女”的他们似乎更在意个人情感,这恰好是与诗靠近的天然馈赠。但是,入门意味着开门,诗歌能够让“90后”永远对犬儒、媚俗、物化、市侩、功利、虚无、资本、附庸风雅……保持着清醒的距离及认识?这是需要“90后”以后认真处理的。
出版·选本
覃才:处于新诗百年节点,2016年诗集的出版也带有总结与梳理的意味。“作为中国1950年代优秀汉语诗歌的见证与展示”, 严力、 王小妮、王小龙、欧阳昱、姚风5位生于50年代活跃在80年代诗人组合成磨铁图书《中国桂冠诗丛》第一辑。由孟繁华、张清华主编“身份共同体·70后作家大系·诗歌卷”“是对国内70后诗歌创作实绩的一次集中展示”,“最大程度上体现了70后诗歌创作的丰富性”。由麦岸、杨碧薇等6位80后诗人组合的“差别诗丛”“构成了‘80后’诗人的一个强阵”。个体诗人方面,西川、多多、欧阳江河、商震、李少君、池莉、邱华栋、沈浩波、树才、柏桦、臧棣 、伊沙、玉珍和马新朝等个人作品亦结集面世。
新旧自主出版物在这一年陆续创建微信平台,自主出版平台化一方面在快速、便捷地传播诗歌,另一方面也在消解或影响着诗歌“民刊” 的存在意义。2016年,创刊将近40年北岛领衔的《今天》改名《此刻》并由内地出版。在湖北《中国诗歌》、广东《中西诗歌》等之外,四川《草堂》以高酬姿态异军突起,充实自主出版的乐观阵地。随着诗歌微信空间的开拓,诗歌的传播与传统纸本印制物的距离明显,这是自主出版物市场化走势后表现出的新特征。
赵卫峰:为什么“出版”这词复杂且无奈,恰如生活本身?当诗歌徘徊着步入工艺化之时也表明它永远都无法拒绝“诗歌体制化”台阶!值得注意的是,诗歌如今普遍在人间并保持了倔强的生命力之时,自行也形成一种“体制”。这种“体制”是多轨的,比如作为“受保护的文化品种”让诗歌在当代中国时空里有所地位,它包括职称给予及命名,刊物媒介的认可推介,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诗歌奖项设立和打造等。民间资本介入也可谓自成“体制”,民办诗歌报刊及近年的微信诗歌平台的建设也易成大大小小的无数“体制”。另个体制是诗作的成集出版或印制。诗歌体制不是制度,它与当下物质生活水平息息相关,作为精神生活的诗歌运动及圈子化存在只是一种附属表现。
由此,诗歌“体制”通常是相对的也是矛盾的非诗的。我们会看到岭南方面在传播体制上的成熟,也会看到他们特别强调本土的诗歌活动及诗歌奖是创新的质量的;但是,诗歌这种东西一旦形成或变身为某种“体制”化主观存在,它很可能就是反诗歌的。换言之,现行的诗歌外部与内部体制,大都在与诗歌本身调情,作为外在技术环境的网络助长了这些“约”、“撩”之举,而不是用心去推进,但这是诗人自身事情而非网络本身的过错。“出版”有时也仅是诗人自身事情。这是一个变量;这一年,我陆续收到刀刀、木郎、卢山等多位80后诗人自制诗集,它们依然是质量的、特色的和忠于诗歌本身的。
覃才:诗歌选本的公信力在降低,但在总结性、地域性及实用性方面,选本展现也不错的价值与趋向。周瑟瑟等主编《新世纪中国诗选》(2000年以后)、李天靖等主编《有意味的形式:中外现代诗歌精选》以较大的时间跨度与不同的视角观察与总结某段时间内的诗歌的历史面貌。《天津百年新诗》、《浙江诗人地理—群岛诗年卷》、湖北《潜江诗选》、《延伸:焦作现代诗歌大展》等地域性选本,对总结梳理个别地域诗歌写作及反映中国新诗百年格局方面也有意义。霍俊明编选年度《天天诗历》以及由个人、民办诗刊制作出版的诗歌日历、扑克牌形式年选等,展现诗歌在日常当中实用、趣味的一面。
赵卫峰:日常、实用、趣味,不也是手机及诗歌微信功能吗,不也是宋词元典的其时的主要功能之一吗?不也正如前述的“诗文艺”及诗歌营销行为体现?以后会出现积木形式吗?面巾形式吗?那么,“诗与远方”景象其实只是幻像?我们的生活为什么需要这种幻想?!那么,诗也就是生活,是现时及现实,远方亦即近处,最近乃自我的心灵。而有时想,手机在手,科技及机器竟可提供一种“诗与远方”,也是让李白陈子昂们想不到享不到的事情。
翻 译
覃才:当代诗集与诗歌选本的市场化运营并不算很成功,真正受市场欢迎的诗歌出版物应是翻译作品。从2014年的辛波丝斯卡诗歌译本开始,一本本精美的外国诗歌译本,不仅在市场上销量突出,还给翻译者带来很多想像不到的回馈。这一年,由王家新、薛庆国、舒丹丹、远洋、傅浩、杨铁军、王敖等翻译出版《奥登诗选》、《噪音使整个世界静默:耶胡达·阿米亥诗选》、《我的世纪,我的野兽:曼德尔施塔姆诗选》、《高窗——菲利普·拉金诗集》、《夜舞——西尔维亚·普拉斯诗选》、《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达尔维什诗选》、希尼三部曲《电灯光》《区线与环线》《人之链》。
批 评
覃才:批评是一项严肃的艺术创作,然而在新媒体时期与新诗百年之际,诗歌批评被各种诗歌会议与活动所弱化,专门的诗歌批评著作出版明显减少。这一年,张闳《声音的诗学:现代汉诗抒情艺术研究》、余旸《"九十年代诗歌"的内在分歧:以功能建构为视角》、张桃洲《新世纪诗歌批评文选》、吕进《现代诗学:辩证反思与本体建构》、向天渊《中国新诗:现象与反思》、熊辉《翻译诗歌在中国的接受》、张立新《世俗精神观照下的日常生活诗学》、李少君刘复生主编《21世纪的中国诗歌》等相继出版。
赵卫峰:何为严肃?一般解释是:令人敬畏、认真、严格,多指态度;回望之:在理解“学报体”的同时,媒介不正使有着话语便利的“批评家”们的言论武断、被动、主观、碎片化吗?我们并不否认有不少批评家与当代诗歌同步,但众所周知的是,当代诗歌批评更多地成为事后诸葛亮式的另种被动。另者,不少建设性、认真的、尖锐的声音确实来自非专业无职称的诗歌爱好者,旁观者。即使只言片语不乏极端,却体现真诚与严格,他们有时也提醒着,诗文论难道不可以改变少数人写给少数人看,可否不繁文缛节道貌岸然?如果观察、评论、研究、批评的标尺只集中体现有职称有学位有相关社会身份的少数人,真正的诗歌可能会不高兴。
相对于诗歌写作、阅读与诗歌传媒之活泼,诗歌批评相对失效。其主要原因不仅是批评与写作本身存在的“隔”,亦因诗歌网民、诗歌群众本身素质的提升变化,他们的审美观、判断力早已与往昔不同而更多自主选择,而判断与审美,有时与专业机构、学院、文学的官方组织,与职称、学位、职位也是有着实际距离的。就职业研究或专业批评内部,本身也存在差异,从“余秀华”现象引起的众议不难看到这种分歧。正如诗歌写作本身,诗歌批评的良好状态亦该是不确定性的、动态的,它绝非条款式标准化的东西。当然也要注意到,网络的相对开放表面上达成了参与、自由交流、平等对话等状态,但又泥沙俱下。
诗歌奖
覃才:各种名义、各种主题性的诗歌征文依旧种类繁多,2016年,少数民族骏马奖评选,各省区相关文学及诗歌评奖继续,新设立诗歌奖项及胡适诗歌奖、昌耀诗歌奖、杨牧诗歌奖、首届艾青诗歌节等多带有“新诗百年”意味。各种地域性的诗歌(文艺)活动,也是极力挖掘当地与新诗百年相关的诗歌资源,特别是百年新诗时间内的重要诗人。然而,不管是什么性质与类型的“应时”诗歌奖项与诗歌活动,不论是什么机构与个人组织主办的奖项与活动,其结果本身对诗歌写作似乎又没有多大的推动作用。
赵卫峰:不仅如此,诗歌奖进行中产生的“意外”难免拉撒出“负面”效果,比如四川陈子昂诗歌奖抄袭风波,让我们看到了诗歌旗号下的低级娱乐与“诗歌营销行为”的另一面,其时,“诗与远方”景象在哪儿?也正是这一活动的组织者们、一群庸碌而又聪明的似乎与诗沾边的中老年人,通过“网络”进行虚拟评选“当代中国诗歌奖”或“国际十大诗人”奖;浮夸与浮躁,无度包装与恶炒,这样的折腾动机到底为何?而由民间诗歌机构组织的“1917—2016影响中国百年百位诗人评选”之类也风生水起,通过网络拉票评选,由各色人等组成所谓“专业评委”,制作出所谓“影响中国百年诗人百强”,这,是否反复证明,无限网络时空,易产乌合之众。
诗歌营销
覃才:新媒时期,诗歌/文艺粉丝正在形成一种效益优良的诗歌产业链。但诗歌产业化及诗意营销,传播出去的真是诗歌与诗意吗?其意义真的就是大同的广告语所美化的那样?年初的华语诗歌春晚、中国诗歌春晚在全国多省市展开,诗歌冠以“春晚”形式,是否切合诗歌写作及大众的需求?10月,“为你读诗APP”启动“诗歌漫游城市·深圳站”进行原创作品征集。回想近年的地铁诗歌,今年的民谣风与诗电影陆续启动,以及诗集促销、采风等多种多样的传统活动亦花样翻新,其本意到底是希望为诗歌找到一种新的发展可能,还是在进行一种诗歌的营销呢?
乐观地看,时尚的诗歌跨界营销行业形势良好,它未来的形式也会越来越丰富。从写作与文本的角度来看,作为行业基础与产品的诗歌,未来的好与坏有待于时间考量。但在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时期,在诗歌的2016年,受各种类别的诗歌跨界行为哺育与酝酿,诗正在变成一种流行的艺术,一种重要的艺术,一种有意义的艺术。对诗歌艺术,我们的大众也热烈地表现出足够多的诗意需求。
赵卫峰:建立在新传媒基础上的诗歌营销及更多的相关活动,能否解决诗歌是大众还是小众的老问题呢?这看来已不重要。时代变化总是意味着更新,要让一些物事处于边缘与角落。相对传统戏曲、流行音乐或电视,诗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情况肯定还会持续。小品逼退了相声,相声艺术家都不急,诗歌急什么呢?
所以,在最大限度支持和理解诗歌的营销、传播与种种活动必然的同时,诗歌只能尽力清醒自身是否真的繁荣,并要注意一些易被遮蔽的方面,比如如何在新传媒环境里建构新的诗歌文化秩序,诗人如何在新的读写传环境中自我加强主体性建设。这一年我曾以《经济大革命中的诗意扩张与诗性辩证》为题在《诗刊》撰文提及“诗人概念的变化”,“浅诗歌时代”的盛行与“诗歌的传媒写作时代”和“诗歌的写作资源微利时代”,诗歌的营销、传播以及奖项活动,和工艺诗歌或诗歌工艺化趋势,是互为因果的。
文 本
赵卫峰:去年我们对“诗歌文本”有较多陈述。对于一个国家,无数的纸质媒介及无边无际的网络,一年时间里自然会有成千上万的作品产生。一年中可能产生佳作,但能否产生一个火红的或品学兼优的模范诗人呢?百分百不能。我们所知的李白是成熟和去除芜枝的李白,我们看到的诺奖诗人也是如此。对于一个一代诗人的写作,包括若干蠢蠢而动的90后,我们其实只能客观地说潜力、变化、持续、相对的进步。
在必须感谢千百万诗歌写作的耕作的同时,亦可再强调:现在诗歌创作一个重要现象是此诗歌与彼诗歌的相互距离日益缩小,一个选本、一个奖、一首诗、一个诗人能最大限度地获得诗界的普遍认同的可能性基本不再!?这样的同质与无距离现象还将持续。经典的命名有时可以暂时集中在少数人的嘴里,也可以是阶段的“集体”产出,近年来的选本、年鉴其实体现出这种“集体”展现的需要,关于好诗歌的印象,正日益转化成“花园式”的存在而非“独秀式”的标榜,在此并不否认个体的突破,但一个有成绩的诗人的诗作不可能全都是佳作,一个业余或“不著名”的诗人亦可能写出佳作。而无论如何“介入”,不管怎样“娱乐”和“营销”,都不会有一蹴而就一成不变的“中国好声音”,唯可相信的是——明天会更好。诗歌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所有的阅读必然都是局限的。报刊、自主出版、网刊和微信、微博、博客、QQ空间等在365日里构成的诗歌海洋,时间、少数人、自己和诗歌一起见证就已足够。“回头望望,关于时代、诗歌,关于生命、生存与生活,我们的经验、情感与想像是些什么?回头望望,时间的意义也是指变化,所谓发生,就是不应错过。无论如何,诗歌没有错过。虽然它仍未呈现理想的模样。而诗歌本就没有理想的时代,有的是持续的理想,它,本身就是一种理想”。